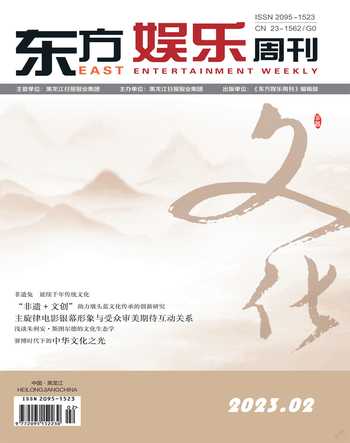后現代包裝下的主流敘事
陳舒敏
[ 關鍵詞]《揚名立萬》;后現代;主流敘事
后現代主義是伴隨后工業時代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思潮,產生于20 世紀60 年代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隨著后現代主義影響力的擴大,電影中也逐漸出現了標新立異、挑戰既定秩序的后現代表征,成為獨具特色和受眾影響的一種表現形式。近年來,國內電影政策不斷強調對于“主流價值觀”的呼喚,而這正是許多后現代主義的電影需加以研究的重要課題。
《揚名立萬》是劉循子墨執導的第一部大銀幕作品,講述了民國時期,一群小人物欲將當時轟動上海的血案“三老案”翻拍成電影,借此揚名立萬的故事。影片雖在表現形式上與后現代類型電影相似,但與后者喪失主體性抑或“壓抑、扭曲甚至變態”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意義的消解與主題上的反叛不同的是,《揚名立萬》塑造了一群有情有義、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并在情節上突出體現了積極正面的價值取向,實現了對主流敘事的書寫,即“通過親切、感人的敘事風格、敘事手法、敘事策略來表現反映歷史與現實積極向上、健康的影視作品,以此來體現主流意識形態,反映主導文化價值觀,倡導國家政策”[1]。
一、解構與重構的狂歡:后現代表征凸顯影片獨特氣質
作為一部借鑒了后現代類型電影而創作的影片,《揚名立萬》具備相當明顯的后現代美學特征,包括類型互嵌、游戲、反諷、拼貼、戲仿等,影片在解構與重構的狂歡中實現了吸引和娛樂受眾、滿足受眾淺層觀影需求的目的。
(一)打破類型邊界的懸疑喜劇
在消費主義盛行、各種媒介甚囂塵上的后現代社會中,文化生產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呈現出媒介自反與跨越邊界的互文性的景觀。在影視制作領域,越來越多的影片選擇將不同類型的元素進行有機融合,以迎合觀眾多樣化的審美期待,擴大受眾群體。“質疑或破壞類型慣例,以創新的方式迎合觀眾期望,是中小成本電影與觀眾對話的方式,也是類型創新的應有之義”[2]。事實上,懸疑片和喜劇片的類型特色有著明顯差異,前者因涉及兇案或謎題,通常被驚悚、嚴肅的氛圍所縈繞,而后者則多是輕松的、愉悅的,若將兩個類型強行拼湊,可能導致兩者相互消解,彼此損害。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懸疑推理與喜劇的有機結合又能使兩者相互調節、互為補充。《揚名立萬》設置了精巧的懸疑敘事,通過“戲中戲”的敘事框架、層層深入的謎題,以及反轉式的結局設置使電影的整體敘事充滿懸念感,滿足觀眾的懸疑期待。在此基礎上,影片將喜劇元素賦予到各個性格鮮明乃至夸張的人物身上,并穿插至人物的互動中,笑料豐富卻不冗長,不會造成整體敘事及邏輯推理的斷裂。從懸疑與喜劇元素的分配上來看,《揚名立萬》呈現出一種從重喜劇到重懸疑推理的轉向。影片的前半部分只是大致地勾勒出了案件的框架,透露出零星的細節與線索,重在以眾人對案件天馬行空的虛構來營造喜劇效果。隨著劇情的發展,眾人在逐漸觸摸到案件真相,并驚覺自己正處于案發現場后,影片又逐漸將重點轉向嚴肅的本格推理。除了《揚名立萬》,國內電影市場近來還涌現了諸如《唐人街探案》《無名之輩》《人潮洶涌》等多部“懸疑+ 喜劇”的影片,均獲得了較好的口碑與票房,體現出懸疑與喜劇相融合的優勢與合理性。
(二)“劇本殺”模式及封閉式空間帶來的游戲化體驗
隨著《明星大偵探》等推理綜藝的走紅,解密式互動桌游“劇本殺”也應運而生,深受時下年輕人的喜愛。作為一部沒有明星大腕、海量宣發的小成本電影,《揚名立萬》正是憑借首部“劇本殺式電影”的標簽賺足了噱頭與票房,成為國內電影市場的一大驚喜。
“劇本殺”游戲有著多重特點,包括桌游的形式感、封閉式空間、主持人與玩家的人物設定等。從整體上看,“劇本殺”的形式感典型地表現為眾人圍桌而坐,通過語言來進行推理解謎與互動。在《揚名立萬》的首場室內戲中,一眾電影人應邀參加電影劇本座談會,而后分別落座于圓桌前,圍繞“三老案”線索展開討論,力圖還原作案手法、殺人動機以及兇手真實身份的行為,即清晰直觀地呈現出“劇本殺”的特色。此外,“劇本殺”常在固定的封閉空間內進行,而《揚名立萬》的故事也主要發生在一棟郊外的豪華別墅中。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封閉狹小的空間容易使得人物自身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心理上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使人物不斷暴露出真實的自身,也引發觀眾的窺探欲望和緊張心理,達到情緒上的高度共鳴。別墅作為一個整體空間,還可對其內部進行細分。在眾人初聚首的會議室中,影片完成了對登場人物、人物關系及整體案件的初步介紹,而后人們又依次來到了塵封的歌舞廳以及案發的房間,以“實景搜證”的形式觸發了新的線索,推動了敘事的發展。在眾人在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同時,死亡的威脅也不期而至,槍聲、呵斥聲、尖叫聲、哭泣聲充斥在這棟充滿秘密的別墅中,恐怖不安的情緒在壓抑的封閉空間中發酵、回蕩,營造出極強的戲劇張力。從人物設定的角度來看,劇本殺游戲通常包含一位DM(游戲主持人),多位擁有個性化角色設置的玩家,有時還會出現輔助游戲進程的NPC(非玩家角色)。影片中,組織劇本會的陸子野擔任的正是游戲主持人的角色,其余7 人則充當需攜手破案的玩家身份,包括商業爛片導演鄭千里、曾經的默片皇帝關靜年、好萊塢武打替身陳小達、花瓶女演員蘇夢蝶、嫉惡如仇的落魄編劇李家輝、幕后真兇齊樂山和菜鳥警察海兆豐。他們職業不同、性格不同、處境不同,因此得以在高強度的互動中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揚名立萬》借用“劇本殺”元素進行敘事,以其沉浸式的儀式建構,限定空間的緊張壓抑以及鮮明的角色設定,達到一種“去現實化”的效果,給觀眾帶來了全新的游戲般的釋放,符合當下的大眾文化心態。
(三)反諷與戲仿的藝術手法
美國學者羅伯特·斯坦姆(Robert Stam)在《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導論》中概括了后現代主義風格的幾個特點:“有暗含的自我意識、敘事的不穩定性和對已有元素的懷舊性利用和拼貼。”《揚名立萬》采用了反諷、戲仿等多種典型的后現代裝置。反諷是影片批判現實的手段,以及塑造喜劇效果的主要途徑。《揚名立萬》的故事背景被設定在民國時期,但它同時也是映照當下現實的一面鏡子。影片一開頭,影院記者以現代化的口吻詢問包不包飯的情節設置,便奠定了全片借古諷今的反諷基調。此外諸如爛片當道、花瓶演員、爛俗的電影套路、敏感題材等電影行業痼疾都成為影片的諷刺對象。“戲仿”又稱“戲擬”“滑稽模仿”,也是一種典型的后現代敘述方式,指對已有元素的諷喻性利用和拼貼。影片多處使用了戲仿手法,尤其在眾人對兇案真相進行反復建構的段落中,高密度地出現了諸如對《英雄本色》中小馬哥的模仿,對《閃靈》《無間道》《功夫》《無恥混蛋》等影片中經典片段及經典臺詞的復現,呈現出荒誕的喜劇效果。創作者故意以拙劣、夸張及高度模式化的手法,突出表現類型片中根深蒂固的符號,以強大的解構力顛覆類型神話,體現出戲仿文本與源文本的對抗關系,在致敬經典的同時,又以一種戲謔游戲的心態實現對經典及現存規范的解構,顯影出影片獨特的后現代主義特征。
二、主流意識形態深化影片內涵
在解構一切的沖動下,后現代作品呈現出情感消逝、深度喪失的重要特征。《揚名立萬》雖極具后現代特色,秉持一種“去現實化”的游戲態度,但并沒有放棄主流的意識形態訴求。影片最動人的地方,也正是在于故事主人公們對真與善的堅持,這是故事的主題內核,也增加了該片的深度。
(一)平民化視角中的人物主體性
后現代主義常以平民化審美視角聚焦于人物個體生命體驗,但作為運用后現代主義的副作用之一,后現代類型電影也消解了人的主體性,“在喧囂混亂的世界上,人的目的性價值和主體性已經消失,人也就在‘上帝死了’之后而遭受到‘死亡’的結局”[3]。《揚名立萬》沿襲了后現代類型電影人物塑造的傳統,以平民化視角刻畫了一群處于社會邊緣的電影人,如被排擠的編劇、爛片導演、過氣演員、龍套替身等,這些角色或身份卑微或處境落魄,但他們并非毫無作為人的意義而存在的某種符號,而是有著獨立思想、美好愿景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如導演劉循子墨所說:“這部影片里沒有所謂的壞人。”這樣一群小人物,都有著自己的閃光點與缺點,有著自己的無奈與不堪。李家輝雖生存窘迫,但始終執著于真理和真相,絕不為五斗米折腰;鄭千山雖開始給人以虛偽、“爛片之王”的形象,但他卻用自己的方式保護了老對頭李家輝、冤家關靜年甚至整個電影行業;齊樂山看似是個殺人犯,實則卻是最神圣的犧牲者,不惜犯下滔天血案以保夜鶯后半生的名聲與幸福安寧。此外,蘇夢蝶對女星、歌女的同情和打抱不平,大海、陳小達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種種設定都凸顯了人物內心的善與溫柔。原本立場不一的眾人最終排除萬難拍出了揭示真相的電影,共同走向了“普遍的善”,片尾李家輝追隨夜鶯而至時伸出的手戛然而止的一刻,既是影片最大的敘事性反轉也是最強的情感爆發點,貫穿影片的成全與溫柔被具化,喚出了人物與觀眾心中最柔軟的部分。影片帶著對人物主體性的關注,聚焦于電影圈中眾多小人物的困境、情感與反抗,彰顯了眾人身陷黑暗但仍不忘心向光明的美好品質,引起了觀眾的情感共鳴。
(二)主線劇情及結局設置顯影正面價值觀
后現代主義認為現今世界的本質是不確定的、荒誕的,人的存在及其所作出的選擇和努力都是無意義的,無法對偶發性結局造成因果上的影響。后現代類型電影拒絕對宏大敘事的書寫及意義的生成,該類影片“既不企圖改變這個荒謬的世界,也不追求終極歸宿,只在淺層地宣泄”[4]。故事中的主人公多難以逃脫“命運的捉弄”,通向非死亡即絕望的黑暗結局。顯然《揚名立萬》的劇情設置與結局走向并非如此。影片聚焦社會及倫理問題,其核心表達為對權勢的批判,對動蕩時代底層人艱難生存的同情和關懷。在這個撲朔迷離的案件中,潛藏的是對權力凌駕于一切的殘酷現實的指認。片中還原兇案時數次提到的神秘勢力,闖入別墅意圖毀尸滅跡的不速之客均指向“三老案”背后深不可測的惡。而明知力量有限、前路艱險的主人公們卻仍奮不顧身地選擇螳臂當車,在重壓之下還原案件真相并將其公之于眾。這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氣正是人物身上最閃耀的人性光輝。正如導演劉循子墨所說:“懸疑和喜劇都只是點綴,我們真正看重的是人性。”而影片也在對“惡”的譴責以及對人性善惡的探討中完成了深層主題的構建,實現了創作的終極目的,使作品在娛樂的基礎上仍具備一定的深度與分量。
后現代主義電影的結局通常是虛無的、徒勞無功的。《揚名立萬》片尾處船撞人亡的消息和照相館無人領取的合影,似乎昭示了眾人終究難逃一死的命運。但實際上,人們的心靈和精神是得到了圓滿的,正如劇中人物所說:“咱們做了應該做的事,問心無愧。”整體來看,眾人希望借以揭示真相的電影成功上映,“三老案”背后的黑暗不再密不透風,關鍵人物夜鶯如齊樂山所愿安穩地生活在了“暖和的地方”,這種對違法犯罪行為進行審判與懲處的傾向,以及溫暖與善意的回歸,體現出影片主流敘事的正面價值取向及親切的敘事風格。
三、結語
《揚名立萬》在實現商業價值的同時也獲得了不錯的口碑。盡管在視聽語言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但影片開拓了類型創新的可能性,通過對“劇本殺”游戲及限定性空間的合理運用,以及反諷、戲仿、拼貼等后現代裝置的深度植入,形成了一種新奇而獨特的敘事方式,滿足了觀眾的審美需求。在形成后現代風格的同時,影片采用主流敘事策略扭轉了后現代類型電影的黑暗基調,在強烈的人文關懷中凸顯了人物的主體性,并通過主線劇情的設置及閃耀著希望之光的結局,宣揚了積極向上的正面價值觀。《揚名立萬》通過對后現代類型電影的借鑒及其與主流敘事的有機結合,實現了影片在商業性與藝術性之間的平衡,期待它的出現能為國產懸疑喜劇片乃至其他類型提供靈感,催生出更多優秀的影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