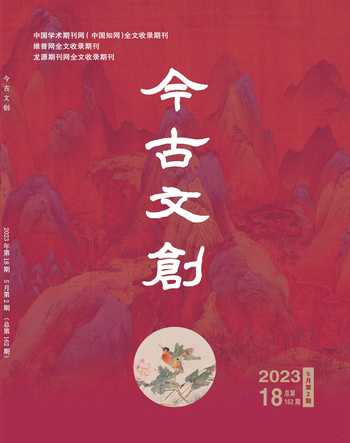隱性進程在曼斯菲爾德小說《幸福》中的運用
【摘要】曼斯菲爾德的著名短篇小說《幸福》描述的是女主人公柏莎在一天內從極度幸福到幸福夢碎的心路歷程。長期以來,該作品被學界認為是批判男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一把利劍,柏莎的不幸遭遇便是男權統治下女性命運的一個縮影。本文從申丹教授提出的隱性進程這一概念出發,關注小說中的細節描寫,重新對文本進行解讀,發現在小說主要情節展開的背后還存在著一股隱性敘事暗流,展現的是柏莎的覺醒與反抗,豐富了人物形象與作品內涵。
【關鍵詞】隱性進程;女性覺醒;梨樹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8-0040-05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8.012
凱瑟琳·曼斯菲爾德(1888-1923)出生于新西蘭,19歲時她就到倫敦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創作之路,主要從事對短篇小說的探索與創新。在34年短暫的生命中,她創作出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說,收錄于五部作品集中。在一向注重詩歌和長篇小說創作的英國,曼斯菲爾德為英國短篇小說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她對于短篇小說的重要性就像喬伊斯對于長篇小說的重要性一樣,并被稱為“短篇小說中的喬伊斯”。在小說創作上,她深受俄國小說家契訶夫的影響,不著重刻畫有深遠背景的宏大敘事,而是癡迷于對平凡生活中的瑣事以及普通小人物的描寫,于細微之處挖掘深刻內涵。
作為一個女性作家,曼斯菲爾德大多數作品的一個特點就是關注女性的生活,《幸福》便是其中的一篇佳作。
1918年,《幸福》發表于《英國評論》上并受到了讀者的關注。《幸福》講述的故事情節可以用簡潔的兩個字來概括——家宴。一位中產階級家庭的中年婦女柏莎心中一直存在著一種幸福感,因為她認為自己家庭美滿、生活富足、朋友高雅,這一天她細心地準備家宴,布置房間,招待朋友,然而在家宴結束后,她卻發現了丈夫哈里與一位參加晚宴的朋友富爾頓之間的私情,心中的幸福感頃刻間蕩然無存。
通過柏莎的不幸遭遇,曼斯菲爾德塑造了一個飽受男權社會禁錮與壓迫的女性形象。學界對于《幸福》的研究大多在作品中的反諷意味以及藝術特征,在主題上關注的是男權主導下女性在婚姻中的悲劇形象。
然而,從隱性敘事進程入手,在女主人公柏莎受壓迫、在家庭中邊緣化形象的情節背后,有著更為復雜的形象。本文旨在借助申丹教授提出的“隱性進程”理論分析曼斯菲爾德的著名短篇小說《幸福》,指出在該作品中,伴隨著小說女主人公在家庭中受男權壓迫失去自我這一敘事情節自始至終有另一股相反的敘事暗流,表達的是柏莎女性意識的覺醒與對男權反抗。通過對于《幸福》中隱性敘事進程的挖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曼斯菲爾德對女性覺醒與女性前途命運的深切關心。
一、“隱性進程”理論
自古以來,情節一直是文學創作時所關注的一個焦點,文學評論與文學批評也聚焦于情節發展。
自1980年代以來,對敘事過程的研究逐漸成為前沿動態。大多數學者關注的是顯性的敘事,也就是人們熟知的情節。
申丹教授發現,“在不少作品的情節背后,還存在一股一股敘事暗流。它既不是情節的一個分支,也不是其深處的一個暗層,而是自成一體,自始至終與情節發展并列運行。這兩種敘事進程呈現出不同甚或相反的走向,在主題意義上形成一種對照補充或對立顛覆的關系。”[1]461申丹教授將這股敘事暗流命名為“隱性進程”,英文名稱為“covert progression”。
申丹教授將隱性進程與傳統的“隱性情節”“隱匿情節”“第二故事”“隱匿敘事”等諸多有關情節的概念加以區分,指出隱性進程的三個特點:第一,隱性進程是從頭到尾持續展開的敘事運動;第二,隱性進程自始至終都與情節并列,形成獨立的表意軌道;第三,隱性進程藏在顯現情節背后,不會影響到讀者理解情節的發展。[2]49
申丹教授認為,作品中“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兩種敘事運動互為對照、互為排斥、互為補充,在矛盾張力、交互作用中表達出經典作品豐富深刻的主題意義,塑造出復雜多面的人物形象,生產出卓越的藝術價值”。[3]84
如果看不到小說中的隱性敘事進程,可能就會導致對于人物形象、文章結構以及作品主題的片面理解甚至是曲解。以狄更斯《霧都孤兒》中費金的形象為例,根據小說中展現出的顯性情節,費金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文學中傳統的猶太惡棍的形象,使狄更斯不斷受到“反猶主義”的質疑[4]78。
但是,當我們從小說中隱性進程入手,便會發現費金身上有許多不符合猶太人的特質,他的善待兒童與基督教濟貧院的虐待兒童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與對比,狄更斯借此諷刺了基督教的虛偽。
借助這條隱性進程,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到狄更斯的創作意圖實際旨在諷刺英國慈善制度的虛偽。
在該理論與上述方法的基礎上研究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幸福》中的隱性進程可以幫助我們更加全面地了解女主個公柏莎的形象,挖掘作者作為女性作家面對女性遭受不公后的反抗嘗試。
二、表層情節敘事:柏莎的受男權禁錮與壓迫的形象
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幸福》的表層情節主要是從女主人公柏莎的視角而展開,表現的是柏莎幸福夢碎的過程,刻畫了柏莎這一家庭婦女的痛苦遭遇。在表層情節中,作品的主題為:在男權制主導的社會中,女性處在從屬的地位,成為男人的陪襯,活動范圍僅限于私人領域,失去了自己的話語權,逐漸成為邊緣人物,從而導致個人的悲劇和婚姻的失敗。
在夫妻關系層面,柏莎曾單純地認為自己是幸福的,但現實卻給了她一記重拳。柏莎不僅沒有得到如標題所說的幸福,反而成為了在這段婚姻中受傷的一方。
在小說開始,曼斯菲爾德描繪了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婦柏莎,雖然已經三十歲了,她還是喜歡在路上跳上跳下,當轉過街角時,她的幸福感突如其來,“渾似突然間吞下當天下午一片燦爛的陽光”。[5]172
她一直認為她和丈夫琴瑟和鳴,他們依舊恩愛如初,是彼此的好伴侶,這也是她覺得幸福的原因。在晚宴過程中,她也不忘記欣賞丈夫哈里身上的拼搏奮斗的激情。
但晚宴結束后,當柏莎親眼看到丈夫和富爾頓小姐幽會,看著丈夫親口對富爾頓小姐說著“我愛你”時,柏莎才從幸福的假象之中走出,知道丈夫背叛了自己,而他們的婚姻其實也早已破碎不堪。
對于柏莎來說,丈夫就像自家圍墻花園中那顆梨樹一樣,是自己全部生活的中心,必須依附于丈夫,自己在這個過程中也失去了獨立的人格與地位;但對于哈里來說,柏莎是家庭主婦,只需要負責家庭內部事物,當柏莎給他打電話想和他親密一會時,他卻只是將柏莎當作工具一樣冷淡地告訴她晚宴推遲十分鐘,不與柏莎有更多的交流。曼斯菲爾德的作品有一個特色,那便是人物特征的泛化,用個人體驗表達共性感受。
也就是說,柏莎的家庭就是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個縮影。丈夫哈里是男權社會的統治者,而柏莎則是處于被統治的中產階級女性。我們從二者的名字中也可以窺探到雙方的不平等關系,“Harry”是“Henry”的別稱,是日耳曼語里的人名,其代表著家和權力,作者無疑是在暗示哈里在家庭中不可撼動的權威地位;“Bertha”則是美麗燦爛的意思,作者再指柏莎就像關在籠子里的小鳥一樣,表面的風光并不能掩蓋其備受禁錮的境遇[6]55。人們將女性看作是男性的一部分,男性可以控制女性,將女性禁錮于家中,失去了話語權。當女性話語權失去時,夫妻間正常的交流也成為難事,夫妻感情容易出現矛盾與隔閡,哈里的出軌也變得可以預料,柏莎的婚姻最終也以悲劇收場。
此外,在母子關系方面,柏莎在母愛中感受到的幸福也受到了限制。當柏莎去育嬰室看她的孩子時,她只能“垂手站在那兒看著她們,活象個窮姑娘站在抱著洋娃娃的闊小姐面前。”[5]174
當柏莎想要給孩子喂飯時,保姆很生氣,不情愿地把嬰兒給了她。在短暫地享受了與女兒一起的幸福親子時光后,保姆又得意地將孩子抱走。
在柏莎與保姆的相處過程中,我們并沒有看到保姆作為家中的仆人對柏莎這個家庭女主人應有的尊重。因此,可以知道柏莎在家中并沒有什么權威,也沒有女主人應有的地位,就連保姆都可以將對她的不尊重直接地展現出來。造成保姆與柏莎之間不和諧關系的原因仍然在于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處于社會的邊緣,沒有自己的主體性地位,在家庭中也沒有了作為家中女主人的尊嚴。考慮到這一點,保姆對于柏莎的不尊重與漠視也就可以理解了。
柏莎的悲慘命運值得引起讀者的注意。通過上述一系列的表層情節敘事,曼斯菲爾德在告訴人們:在男權社會的背景下,女性雖然不必受食不果腹與衣不蔽體的困擾,但是她們沒有獨立的人格,受到了父權的壓迫,影響著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沒有權威與地位,最終落得婚姻破碎的悲慘結局。
三、情節敘事背后的隱性進程
談到《幸福》中的隱性進程,就不得不考慮到該短篇小說創作的歷史背景。《幸福》于1918年寫成,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年份。
在一戰中,家庭中的男性奔赴戰爭前線,而女性則代替男性,從事男性之前從事的工作,女性也很好地適應了男性的工作。考慮到婦女在抗戰中做出的杰出貢獻,聯合國決定授予年滿30的女性選舉權利。曼斯菲爾德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創造本篇小說,其中深意值得深思。
因此,在飽受男權壓迫與禁錮的表層形象之下,曼斯菲爾德筆下的柏莎實際上還有著女權的逐漸覺醒與反抗男權的一面,其思想意識的覺醒也通過文中的隱性敘事進程不斷展現出來。
仔細研讀原文之后,便會發現曼斯菲爾德在文章前、中、后階段都有對于梨樹的描寫,字數不多,還稍顯離題。但稍加思索后會發現,作者對梨樹的描寫就是一條隱性的敘事進程,梨樹的三次出現都嵌在情節之中,并與女主人公柏莎的覺醒歷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隱性進程與情節發展構成不同性質的主題關系,有的呈補充性質,有的則成顛覆性質。”[7]277《幸福》中的表層情節與隱性進程之間呈現的便是互相顛覆的性質,一方面是壓迫,而另一方面是反抗。
梨樹作為隱性敘事進程貫穿于柏莎組織的家宴整個過程中。梨樹第一次出現時,作者是這樣描述它的:“花園盡頭,長著棵修長的梨樹,正盛開著嬌艷的花朵;梨樹亭亭玉立,襯著碧玉般的青空,似乎凝止不動。”[5]177此刻的梨樹是完美的,肆意地盛開在庭院之中。不像在表層情節中梨樹是丈夫哈里的代表,柏莎的生活圍繞著哈里,在隱性情節中梨樹與女主個人柏莎緊密聯系在一起,柏莎的內心世界通過梨樹的不同形態生動形象地描述了出來。
在故事開頭,“幸福”這一字眼不斷地出現,我們感受到的是一個自認為“幸福”的柏莎,柏莎就像花園中那顆梨樹一樣,家庭美滿,朋友雅致,生活幸福,不必為基本的衣食發愁。所以她把自己也打扮得像一顆梨樹,“穿一身白衣服,配上一串翡翠珠,綠鞋和綠襪……她輕曳繡著花瓣的衣裾,窸窸窣窣的進了門廳。”[5]178
此刻的柏莎是沒有覺醒的,缺乏獨立的思考,依舊困于男權的禁錮中而不自知,從丈夫哈里那里尋求安全感,單純地以為將自己依附于丈夫便可獲得幸福。柏莎和大多數處于不平等地位的婦女一樣,還沒有意識到男權之下女性遭受的不公與壓迫,沒有意識到自主權的喪失,只是沉醉于自己幻想的美滿幸福之中,一直活在自我欺騙之中。但是梨樹下的懷著孕的灰貓和黑貓相互追逐已經暗示柏莎的生活可能并沒有看起來那么美好。
梨樹第二次出現時是在月光之下,柏莎和富爾頓小姐肩并肩欣賞著花園中綴滿繁花的梨樹。如果說在表層敘事進程中,這里梨樹表達的意思是這兩個女人對于哈里的明爭暗奪,指的是她們都喜歡同一個男子哈里,她們都指望著男人可以給予自己依靠,成為自己唯一風港,不僅是柏莎,富爾頓小姐也無法掙脫男權的束縛,那么在隱性進程里,梨樹則表達的是柏莎女性意識覺醒并開展相應的反抗與斗爭。
在許多西方文學作品中,月亮是女性的代表,然而在我國近代文學家魯迅先生的首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中,月亮則代表著狂人意識的覺醒,代表著狂人意識到自己所在的社會是一個吃人的社會。如果我們將兩者結合起來,便會發現,此刻的柏莎心中的女性意識初步地覺醒了,而這種覺醒是在富爾頓小姐的影響之下產生的。
雖然在表層情節的敘事中,富爾頓小姐是破壞柏莎家庭的人,是一個反面人物,但是在隱性進程中,富爾頓小姐的身份產生了變化。當柏莎第一次看到富爾頓小姐時,她就十分地喜歡她,被她的獨立個性所吸引,又想到自己在家中所受的種種委屈,柏莎感受到了自己所受的禁錮與壓迫,喚起了柏莎內心深處渴望獨立的意識。在傳統的男權社會中,女性失去了獨立地位,成為男性的財物,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
面對此種壓迫,柏莎尋求獨立與反抗的第一步便是將自己對哈里的愛戀轉移到富爾頓小姐身上。著名女性主義代表人物西蒙·波伏娃認為,“同性戀是一種在某種處境下被迫選擇的態度,也就是說,既有動機,也有自由的采取。”[8]56
柏莎選擇用這種極端的且不被社會認可的方式無聲地反抗男權社會給自己造成的傷害,她寄希望于通過此種方式掙脫男權社會對傳統女性的束縛。梨樹在西方文化中指的是“兩性”,具有十分強烈的性別內涵。在她覺醒時刻,曼斯菲爾德繼續這樣寫道:“梨樹宛若蠟燭的火焰,在清澈的夜空中兀自撲騰閃動,往上直竄,越長越高,越長越高—幾乎快碰到那輪圓圓的銀月亮邊兒了[5]184”,這句話也暗暗指出柏莎在覺醒之后為反抗選擇了為道德所不能接受的行為,她想象著自己與富爾頓小姐完成了愛的交合。戀上富爾頓小姐成為了柏莎離經叛道,尋求反抗男權的一條特殊路徑。此外,得出此種結論,與曼斯菲爾德本人的親身經歷不無關系,擁有者既可以吸引男性也可以吸引女性的特質,再加上受到奧斯卡·王爾德的影響,她本人也成為了一個雙性戀者,而此時的柏莎也成為了作者曼斯菲爾德自己的縮影。
梨樹第三次出現時是在文章的最后,曼斯菲爾德這樣寫道:“可是那顆梨樹還是那么可愛,照樣繁華滿樹,恬然靜立。”[5]188作者對于此刻梨樹的描寫是在這樣的情景之下發生的:晚宴結束后,表現出對富爾頓小姐極端厭惡的哈里竟然在門廳主動提出要求給富爾頓小姐穿衣服,獨留柏莎和另一位參加晚宴的朋友埃迪在家中,然而柏莎卻在門廳中看到自己的丈夫哈里對富爾頓小姐說著情話,舉止曖昧,并約定第二天再見,柏莎最終還是發現了丈夫與富爾頓小姐的私情。行文至此,小說也抵達了高潮部分,柏莎一直認為的幸福夢碎,她與丈夫同床異夢,小說標題的反諷意味也得以充分地體現。在覺醒之后,柏莎選擇用同性戀這一有違倫理道德的行為發出對男權社會的反抗,以期擺脫男性的桎梏,然而富爾頓小姐顯然并沒有和她有同樣的想法,也并不愛慕她,依舊困在男權社會的禁錮之下,這也標志著她覺醒之后的初次反抗以失敗告終。通過這種有違常理的方式并不能幫助她實現獨立,實現對男權的反抗。
在隱性進程中,此種情況下梨樹重新出現在柏莎的眼前,梨樹在園中依舊美麗的獨自盛開著,也絲毫沒有受到外界發生事情的影響。梨樹的獨自開放對柏莎來說則是另一種抗爭的嘗試,是柏莎的女性意識得到了完全覺醒的標志,對抗男權你便要做到最好的自己,相信自己的主體地位。女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尋找真正的自我,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受到男權的禁錮與壓迫,才可實現真正的覺醒與獨立,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幸福。
至此,以梨樹為中心而展開的隱性敘事進程完全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與它緊緊相連的是女主人公女性意識的逐漸覺醒。在梨樹出現的三種不同場合,柏莎的女性意識也經歷了三種不同的變化:從沉睡到初步覺醒再到最后的完全覺醒。申丹教授曾指出,在具有雙重進程的作品中,顯性進程往往會突出人物形象的某一方面而隱性進程則強調其另一側面,使人物形象由單一變得多面[9]86。在表層敘事中,我們了解到的柏莎是男權社會的迫害者,遭受丈夫背叛,忍受保姆不敬,在家中無地位無自我,看似幸福的生活實際上根本經不起考驗,柏莎的孤獨無助躍然紙上。然而,在曼斯菲爾德通過對于梨樹這一隱藏的敘事暗流描寫中,她對柏莎的形象做出了不同于表層敘事的描述,指出柏莎并不是完全地受壓迫于男權社會而不知如何反抗,相反,柏莎在默默地覺醒并做出了自己的反抗選擇。通過這雙重敘事,《幸福》的敘事張力也得以體現,一方面是當時女性在美滿婚姻表象下痛苦的生活實質,而另一方面則是女性的覺醒和獨立,嘗試對男權的反抗。如果我們閱讀時主義不到梨樹這一貫穿于全文的敘事細節,可能就會忽略這一點,影響到柏莎這一人物形象的豐滿程度,從而在對《幸福》的主題把握中出現一些偏差。
四、曼斯菲爾德的女性意識
人生就像小說一樣,多數作家會將自己在現實生活寫入小說。以英國小說家安東尼·特羅洛普為例,在上學時由于家境貧寒,他總是受到富家子弟的欺凌與不公正對待,被其他同學排斥,老師也不喜歡他,久而久之這種孤獨感覺便一直縈繞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巴塞特郡紀事》中,他將自己的這種感受賦予自己筆下的人物,將自己的情感外化于作品,以表達自己的這種被排斥感。申丹教授也曾經指出,敘事的隱性進程和作者的生活經歷和歷史語境有關。
因此,分析《幸福》這一作品在隱性敘事進程中表現得女性覺醒就離不開對于曼斯菲爾德所處時代與她生活境遇的了解。曼斯菲爾德生活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一個社會思想大變革的時代。屬于維多利亞時代最后的榮光正在逐漸散去,受到當時歐洲各國經濟危機的影響,英國的許多工人失業,人們生活貧困。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廣大婦女更是苦不堪言,她們不僅經濟上拮據,在精神上更是備受煎熬。婦女們沒有財產,被迫委身于男人以尋求庇護。女人不是獨立的個體,而是男人的附屬品,可以任人宰割,任人凌辱。
曼斯費爾特在留學英國期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女性的悲慘命運。而后家富裕的她立志于做一位獨立女性靠自己的文學作品維持生計時,她也遭遇了當時女性的不幸生活,她的婚姻并不順利,孩子夭折[10]117。經歷了各種人生痛苦的曼斯菲爾德逐漸認識到,在各個方面受到歧視和壓迫的女性應該努力奮斗,靠自己的力量超越男性,并在思想上進行深刻的變革。
她的經歷也為她替女性言說奠定了一定的基礎。與曼斯菲爾德同時代的著名英國女性主義作家便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她擅長將女性主義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不同于伍爾夫,曼斯菲爾德則更加切實地關注于細節,刻畫女性所受的苦難,深刻思考女性解放的未來以及出路。
因此,人們會發現她許多的作品主要在細微之處見思想,都在關注女性,從就業求職到戀愛生育,可以說她的短篇小說涵蓋了女性生活的各個方面。但是考慮到當時英國社會較為保守的社會風氣,曼斯菲爾德只能用隱蔽的方式表達女性獨立與反抗,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她在《幸福》中選擇了用隱性敘事進程來表達女性覺醒這一觀念,隱晦地表達對男權社會的反抗。
五、結語
研究一部敘事作品時,如果只將自己的關注點放在表層的情節時,就會習慣性地忽略與表層敘事并行的隱性敘事進程。根據申丹教授的隱性敘事理論,可以將《幸福》中的細節串聯起來,而這些細節可能較為瑣碎而顯得對文章情節發展起不到實質性作用。
在仔細挖掘文本細節之后,便會發現另一條表意軌道以及另一種敘事主題,作品中人物形象會更為飽滿,審美價值也有相應的提升。在曼斯菲爾德的短篇小說《幸福》中,表層情節圍繞女主人公柏莎失敗的婚姻展開,表達的主題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的迫害,而隱性進程則著重對梨樹的描寫,圍繞柏莎的覺醒而展開,表達的主題是女性對男權社會的反抗,尋求獨立幸福的道路。
在隱性進程中,曼斯菲爾德將自己對女性覺醒的理解融入了該篇小說中,通過柏莎這一形象展現出來,寄托她對于女性生存的深刻關心與思考。小說通過一明一暗的敘事進程,互為顛覆,從不同的角度入手,對柏莎這一女性形象的刻畫也發生了變化,表達著不同的主題思想。如果忽視《幸福》中的隱性進程,可能就會對作品的主題理解得不夠深刻與全面。
參考文獻:
[1]申丹.不同表意軌道與文體學研究模式的重構[J].外語教學與研究,2020,52(03):461-463.
[2]申丹.何為敘事的“隱性進程” ?如何發現這股敘事暗流?[J].外國文學研究,2013,35(05):47-53.
[3]申丹.敘事的雙重動力:不同互動關系以及被忽略的原因[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55(02):84-97.
[4]黃瑩.費金形象被忽略的異質性:狄更斯《霧都孤兒》中的隱性敘事進程[J].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20(06):78-85.
[5]凱瑟琳·曼斯菲爾德.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選[M].楊向榮譯.北京:外文出版社,2000.
[6]潘明,胡宏宏.表層的幸福,深層的悲哀——評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幸福》 [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28(12):55-57.
[7]Shen D.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Covert Progression Behind Overt Plots[J].Style,2013,47(01):276-298.
[8]潘明,胡宏宏.表層的幸福,深層的悲哀——評曼斯菲爾德短篇小說《幸福》 [J].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09,28(12):55-57.
[9]申丹.西方文論關鍵詞 隱性進程[J].外國文學,2019,(01):81-96.
[10]何亞惠.曼斯菲爾德的女權主義思想[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1998,(04):117-120.
作者簡介:
史偉麗,女,天津財經大學人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比較文學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