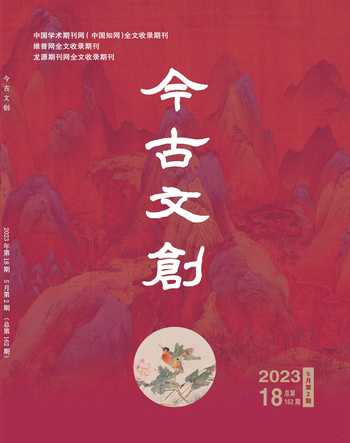細探晚清宇宙觀的重構
薛淼丹
【摘要】張洪彬先生在《祛魅:天人感應、近代科學與晚清宇宙觀念的嬗變》一書中主要介紹了近代科學知識給中國傳統思想帶來巨大沖擊,“天人感應”的人與自然關系不再為人們信服。在古代,人們堅信宇宙包含萬物,不受具體的人格神統領。宇宙觀的變動使得晚清知識分子“開眼看世界”,急于尋找一個相契合的思想坐鎮。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應運而生,促成了晚清世界觀的重塑。該書角度新穎,從自然觀看晚清思想的變動,且論述細致,以小見大,結論令人信服。
【關鍵詞】《祛魅:天人感應、近代科學與晚清宇宙觀念的嬗變》;上層階級;《天演論》
【中圖分類號】K25?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8-005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8.016
一、天演論對宇宙的祛魅
張洪彬先生新近出了一本書,名為《祛魅:天人感應、近代科學與晚清宇宙觀念的嬗變》。其實,近代科學知識對晚清宇宙觀變化的影響的相關研究從上個世紀末就已開始,如宋正海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古代有機論自然觀的現代科學價值的發現——從萊布尼茨、白晉到李約瑟》、郭漢林在1994年《史學月刊》發表的《論晚清思想界對風水的批判》。但是張洪彬先生的作品能夠一以貫之進行說明,闡述自然神學與科學知識對中國傳統宇宙觀的祛魅和挑戰,以及本土知識分子利用以進化論為基礎的天演論回應挑戰。作品將方向立在“嬗變”二字,看思想史的動態變化,有所創新且任務量巨大。
書名采用近些年為大眾關注的“祛魅”一詞,并加上書中主要闡述的幾個論題,具有高度概括力和現代色彩。那么,何為“祛魅”?“祛魅”一詞原屬社會科學專業的概念,源于馬克斯·韋伯所談的“Charm of the world”,翻譯過來為“世界的祛魅”。[1]韋伯認為人的理性發展使得傳統生活中的宗教內容被解密,神秘且夢幻的生活被消解,這是一個解魅的過程,就如大夢初醒一般。從神權社會步入到世俗社會,世界圖景更富有科學性和客觀性,人們精神世界中對神靈的崇拜得以消減。張洪彬先生援引馬克斯·韋伯這一論說,意在表明在晚清社會也出現了如此嬗變。隨著西方科學技術和傳教士進入中國,“天人感應”“善惡有報”等傳統中國制定的道德秩序受到猛烈沖擊,人們的信仰動搖,緊接著感到迷茫,開始找尋更符合本土的新寄托。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因時而出,加速傳統社會除魅。
作者是歷史學學者,主攻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張洪彬先生的博士論文是《天變道亦變:晚清的宇宙論嬗蛻》,該作由博士論文幾經修改完善而成。“天變道亦變”語出董仲舒《舉賢良策》“天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其中“天”指自然,“道”指治人之道、為君之道。[2]張洪彬先生則反向指出隨著時代變遷,原來的道統已不合時宜。他認為是從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先進科學技術開拓大眾眼界,加上傳教士對西方思想的宣傳,一直以來被大眾作為立命之本的思想,如“魂魄二元觀”“天圓地方”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
作者進行思想史的研究,卻能夠另辟蹊徑,從中西方人神關系的差異入手分析,微觀角度看晚清宇宙觀念的演變。作者分析晚清社會情形發現,雖然近代科學知識傳入中國,但是西方生發的自然神學與中國本土文化有諸多抵牾之處。最大的不同是對“天”地位的認知,這是造成在古代中國無法借鑒機械宇宙觀的根本原因。自然神學所推崇的機械宇宙觀強調上帝是主宰,宇宙萬物是上帝安排好的,科學知識也是上帝設定的社會運行法則。而中國的傳統觀念不論道家還是儒家,都信奉“天”或稱“宇宙”是至上的力量,宇宙有自己的運行規律而不受外物控制,包括供奉的各路神仙等級也在宇宙之下。
如此看來,機械宇宙觀和中國傳統觀念在本根上就無法融合。而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恰好規避掉這一沖突,將赫胥黎和斯賓塞的天演論引入并當作一種宇宙觀,認為“宇宙源于非人格化的終極起點”,否定人格化的上帝統管一切的神創宇宙觀。
同時,嚴復將天演論與道家的“天道”思想融會貫通,認為宇宙自行運轉,無需人為干預,宣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天有理而無善”,拋棄一直宣稱的“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德屬性,建立適合新時代的世俗道德秩序。宇宙的運行法則仍在,但與人的善惡行徑無關,只是自然發展的客觀規律。這一系列嬗變對傳統中國來說影響是巨大的,為當時迷茫焦急的知識分子指明了方向。
二、天地人之道的嬗變
該作品是對晚清時期人們一直以來所信奉的世界觀從動搖到重建過程的分析。現今有人對“晚清宇宙觀的根柢性”提出質疑,認為這一時期的宇宙論和傳統文化是相背離的。關于這一疑問的答案作品中顯而易見。張洪彬先生堅持存在觀點,并以之立說,將儒道等思想囊括其中,討論整個思想體系和實踐背后的神圣存在對于傳統中國的意義所在。作者在這里對“宗教”一詞采取較為寬泛的概念,這個概念核心指對“上天”的尊崇。表現范圍上至帝王國策,下至世俗生活。作者在第一章引用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中宗教信仰的判斷標準,其中包括對善惡行為、物性問題的判斷。所謂物性是對食物、藥物涼熱性,以及中醫的認知。可知作者研究貼近日常生活,討論有知覺的宇宙和自然。對于宗教性和善惡關聯的討論,李亦園大體關注的是儒家文化影響下形成的世界觀,對世俗有“規訓”“勸善”的指導意義。而作者則在此基礎上創新,進一步分析時代變革下原形成的世界觀破裂,接受新理念,建立新秩序的過程。
為了清楚展現晚清社會世界觀的變化,作品將視野放至天地人三大方面。天地人三才的說法出自《周易》,《易傳·系辭下》說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三才”即指天道、地道、人道。這里意在把天道、人道、地道統一起來并分別用兩個爻來表示,因此全卦有六個爻。人處于中,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天地人匯聚,多角度展現宇宙觀的嬗變,更有說服力,足見作者巧思。在第二、三、四章中,作者在天地人三才里分別選取兩個例子作為支撐,如“天之祛魅”部分用彗星和求雨作例,“地之祛魅”用地震和風水,“人之祛魅”用疾疫和靈魂。當然,作品里的例子不是隨意選擇的,經過作者反復思考,抉擇而出。所選取的例子具有代表性,是扎根中國傳統文化,很能體現每一個嬗變細節的。每一“才”均采用上層階級和下層社會現象相結合論述,涵蓋天文學、地理學、醫學等多個領域,使論證更加全面。上層社會主要指與上天旨意關聯密切的君臣行為,下層社會則拓展至老百姓中體現天人信仰的活動,具有普遍意義。前者關乎國運,后者關系民生,這正是古代中國宇宙觀從始至終關心的問題。
在傳統看來,彗星的出現是對人世間行為的警示或災禍出現的預示,朝廷設置監測天象并解釋星占吉兇的專門機構。但晚清的傳教士卻有著不同解說,他們宣揚以牛頓學說為代表的彗星新解,這對古代中國傳統認知產生沖擊,人們追尋理性科學的腳步,災異論的彗星說法逐漸為人們拋棄。彗星作為一種預兆,對傳統中國君臣行為有指導作用,那么土地出現的旱災則會及時性地影響百姓的生活。所以求雨活動往往影響更廣,參與人員更多。求雨前需要設立專門的廟宇,凈身修心,以表虔誠。對于求雨一事,大家都認識到其重要性,君民一心,祈求上天。然而完善的求雨制度,在科學解釋到來之后,已逐漸崩塌。地面水汽上升成云,遇氣溫變化后降水,這一解釋更讓人信服。從彗星講到求雨,從上層階級到平民百姓,更為全面地展現晚清的宇宙觀念。彗星所信服的陰陽五行宇宙秩序和求雨的神圣信仰,隨著傳教士帶來的科學新解,一同被沖刷。
第三章介紹天地人三才里屬于“地理”的部分,以地之除魅看天道的變換。作者選取地震和風水,一個是災異氣象,一個是日常現象,共同來分析天道在晚清人們心中地位和作用的變化。對于地震現象,在古代人們認為是陰陽失去平衡導致的,是對人世間不當行為的警示。地震一出,人間修省。這一解說具有濃厚的道德屬性。但到晚清時期,地震對人間行為的規約性逐漸減弱,此時的張之洞已經發現星占學與地震的聯系。
根據當時大體走向可以見出,地震的神魅色彩逐步讓渡給自然科學,地震的舊有解說得到了巧妙轉換。“氣”從構成萬物的宇宙元質變成了自然界中的獨立客體,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氣體,與道德無關。而作為于日常生活中體現世界觀的一種形式,風水術企圖選擇恰當的陽宅和陰宅,使其符合陰陽五行的宇宙運行法則,從而“趨吉避兇”“順風順水”。風水術的流通似乎在告訴人們,一個好的陰宅和陽宅便能影響家中幾代人的前途。風水說道德屬性薄弱,在當時就遭到了儒家的批判和糾正。但此時儒家和風水所認可的是同一宇宙秩序,即源于《周易》的陰陽五行,所以風水說還有存留的空間。它真正面臨存亡威脅的時刻是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地質學、地理學對地球、土地、山水的新解為人們揭開了千古謎底,也顛覆了風水信仰的理論基礎——陰陽五行運行法則,打破了人們的傳統世界觀,理性色彩愈發濃厚。
作者所選的“祛魅”作為標題,意在指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對傳統天人宇宙觀念中人格化的神靈和泛神論的秩序有撥開云霧的作用。第四章從“人”出發,關注身體和靈魂觀念的變化。這與前文地震變化情況類似,僅簡單說明,給其他讀者以參考。在古代,人們治療疾病有兩種方式,一種取悅人驅逐邪怪,一種平衡身體內陰陽二氣。前者毫無科學根據被人拋棄,后者漸漸與科學技術結合,融合發展為中國醫學。而中國傳統的氣化靈魂觀也隨著科學知識的豐富不攻自破,逐漸走向無鬼論。至此從“天地人”三方面共同印證了世俗秩序的嬗變和宇宙觀的解魅。
第五、六章,作者再次回歸到中西方理論的差別,探討機械宇宙觀和天演論兩種學說分別對中西方信仰的獨特意義。機械宇宙觀所涉及的自然神學在科學史占有重要地位,里面的很多內容是科學知識的基礎。它的理念易轉化成近代科學,促進了西方社會的發展進步。再看嚴復譯過來的天演論,它作為一種有機宇宙觀,在中國傳統觀念崩塌之際,因與傳統宇宙秩序認知相近被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內化。當時一眾西方學說盛行,嚴復最終選擇了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學說,也見其智慧。嚴復認為宇宙秩序無善惡之分,無需完全服從;世俗道德秩序是人為建立的;個體的人要聯合起來組成群體,才能得到個體利益,實現“安利”。可以簡單概括為“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基于時代特點和面臨的挑戰,嚴復考慮的“群”是民族國家內部團結一致、積極進取的善性的道德秩序,才能做到提升本國實力、不懼外強、實現文明,這才是“國家”這個有機體的和諧狀態。[3]
三、宇宙觀的重建與疑問
本作主要探源古代中國的宇宙觀念在晚清時期遭遇怎樣的挑戰,又是如何融合科學知識的。中國傳統世界觀尊崇陰陽五行的宇宙運行法則。而西方堅信上帝是超越宇宙的至上神。隨著科學知識和傳教士進入中國,講求善惡有報,上天統管一切的傳統中國觀念開始為人質疑,人們對舊有的道德秩序的信念動搖不定。但中西方將上帝所放置的地位不同,這一根本差異使得傳教士所宣揚的上帝至上論不為中國知識分子接受,沒有出現“一呼百應”的現象。
在新觀念建立的關鍵時期,晚清知識分子在迷茫中探索,找到了與中國傳統宇宙觀相契合的天演論。兩者均認可宇宙至上,宇宙包含萬物這一基本觀點,這更易于人們接受這套理論,并作為行為規范。
在此基礎上,世俗道德秩序有所變化。原來“善惡有報”的天道模式轉變為“向上進取”的社會進化論。它肯定人的拼搏努力,不甘人后,削弱了道德屬性,強調事在人為。這一思想理論為中國社會的后續發展奠定基調,作者的研究也使得當代人深入了解晚清歷史的同時以古鑒今,認識到樹立正確世界觀對塑造民族形象和建立民族地位的重要性,謹慎對待當下的理論建設。
然而,正如緒論中李天綱先生所說,作品中論述的嬗變不是晚清才有的,征兆早已出現。[4]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就發現“天變了”,人們將要面臨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他憂慮世風日下,鉆研天文學、地理學,希冀通過理清天與人的關系,重塑人的信仰。因而看到,嬗變不應以鴉片戰爭為節點,時間線可再向前推移。
在張洪彬的指導老師許紀霖看來,宇宙觀的變化就是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現代性的出現與世俗化的過程。作品主要研究了上層階級的嬗變,分析晚清帝王和知識分子是如何對待這一沖擊。但毋庸置疑,平民社會也受到西方科技和傳教思想的影響。該作品為學界研究社會思想信仰的演變做了嘗試,但現代性是如何融入世俗生活的還值得進一步挖掘。
再者,作品選題范圍較大,使其不能找尋更多例子做論據,論據緊密度稍顯不足。報刊文集是近代思想的重要載體,在參考材料部分,張洪彬先生則選取了大量報刊、日記、回憶錄,具有極強的時代性,更好地還原當時場景去看問題。總的說來,作者著手研究晚清宇宙觀的祛魅對古代中國宗教帶來的影響,選取典型例子進行細致地論證,盡可能地將概念具象化,試圖從科學客觀的角度分析傳統中國自然觀中一些不確定的問題。學界涉及這一話題的探討不多,作品角度新奇,吸引讀者興趣,啟發更多人來研究。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錢永祥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9:188-190.
[2]班固.漢書·董仲舒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5:1915.
[3]王鴻.文野之辨:晚清的“文明”觀念研究[D].華東師范大學,2020:217.
[4]張洪彬.祛魅:天人感應、近代科學與晚清宇宙觀念的嬗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