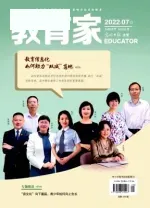李立國:大學要在競爭中形成特色
孫傳愛
人口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世界各地區少子化的出現,我國高等教育布局和發展也將迎來新的挑戰。一方面,從宏觀角度出發,國家和教育相關部門的調控和部署,是高等教育應對變化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則需要在遵循國家政策和教育規律的前提下,依據整體經濟社會發展、國家戰略布局和區域優勢,對高校外部環境、高校學科專業等內部結構進行優化,積極應對未來人口結構的波動。日前,針對人口結構變化等因素給高等教育布局帶來的影響,《教育家》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李立國教授,他認為應對人口變化,最主要的是激發高校改革創新的主動性、積極性,在市場中動態調整,在競爭中形成特色。
《教育家》:李教授,自1962年以來,2022年我國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人口結構的變化會給高等教育帶來什么影響?受少子化影響,大學會不會“一生難求”,應該如何應對?
李立國:我們現在看到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這很有可能是未來中國人口發展的趨勢。最近出現了很多幼兒園關停的新聞,一些人為此感到焦慮,但從高等教育發展的視角來看,我對人口的變動倒沒那么憂慮,因為我國高等教育2022年的毛入學率為59.6%。
按照毛入學率,高等教育的發展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毛入學率低于15%為精英階段,在15%~50%之間為大眾化階段,超過50%則進入了普及化階段。我們的毛入學率看起來很高,但實際上剛剛跨過了普及化階段的門檻。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一般在80%以上,已達到深度普及化階段。對照這個標準,我們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所以,至少在目前,我不太擔憂大學會出現“一生難求”的局面。當然,受絕對人口數量減少的影響,個別地區難免出現要對學校進行優化調整的狀況。我國人口規模龐大,高等院校背后有政府在規劃,相關部門會依據人口變動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最常見的就是高校合并,對現有的學校進行優化調整。
這一措施有利有弊。一方面能避免高等教育在發展中失衡;另一方面弱化了校際競爭,難以激發高校改革創新的主動性、積極性。競爭動力不足,教育改革就缺乏內在驅動,學校難以創新發展、辦出特色,從長遠來看會影響整體的教育質量,不利于構建良性的教育生態。
《教育家》:近年來,從我國人口遷移趨勢來看,人口主要向經濟發展迅速的大都市圈集聚,高等教育布局是否需要根據人口變動做出適應性調整?比如,是否可以在人口聚集區域多增設新的大學?
李立國:這個問題非常好,我不擔憂“一生難求”,我所擔憂的正是流動帶來的人口極端分布。參照世界各國人口變動的情況,很多國家和地區都出現了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的現象,比如韓國,其首都圈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近一半。我國雖然沒有出現這么極端的現象,但也存在類似的趨勢,大量人口涌向東部和中部的中心城市,廣大西部和東北某些地區人口呈現凈流出狀態。
因人口流動導致的人口不均衡傳導到生源上,表現會更明顯,也勢必對高等教育帶來沖擊,這就要求高等教育做出適應性調整,也即教育的“市場化”。教育界很多人不愿意談“市場化”,認為一跟市場沾邊就削減了教育的神圣性,但其實“市場化”的內涵非常豐富,高等教育布局的“市場化”本質是一種動態調整,是從行政導向轉為需求導向。
用動態思維思考教育布局,在人口聚集區設置新大學是必要的,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建立世界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我認為高等教育布局的相關政策應該向大灣區、長三角等區域有計劃地傾斜,通過新型高等教育機構來支撐科技創新和國家戰略發展。
不過現實情況非常復雜,高等教育的布局又不能僅僅依靠市場。比如,在不允許大學異地辦學之前,出現了高校“東南飛”的現象,大家都愿意到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地區辦學。目前來看,我國對新建大學有嚴格的控制,所以,主要的調整方式還是要從學校內部進行優化,比如升格,在內部增設碩士點、博士點等。
《教育家》:去哪里讀大學,將和未來的工作、生活相鏈接。從目前全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現狀來看,您認為區位條件和人口流動將給大學帶來哪些影響?
李立國:影響高等教育發展有幾個重要因素,比如人口和區位條件,區位條件又可細分為區域經濟條件、自然條件,以及區域創新活力。
一般來說經濟條件最重要,它和創新活力、人口流動密切相關。相對優越的自然條件會助推經濟發展,形成優勢的疊加聚合。區位條件優越的地方,人口會不斷流入,教育需求不斷擴大,其帶來的結果必然是高等教育發展的不均衡。這種狀況在各個國家都有表現,比如美國的大學主要集中在東北部、西海岸等地。高等教育和義務教育的不同在于,后者強調均衡,前者則很難做到均衡,它要和區位、人口適配。
一直以來,我們習慣按照行政區域布局高等教育,每個地級市都要辦一所大學,既為滿足當地的教育需求、人才需求,也為了文化的興盛。隨著社會發展,很多地區沒有區位優勢,無法留住人才,而且優秀教師也在不斷流失,其教育教學質量難免會受影響。以小見大,全國范圍內都存在類似現象。
當高等教育呈現非均衡發展狀態,在未來,大學可能出現兩個變化,一個是“市場化”的高等教育布局模式,另一個是逼著大學走內涵化、特色化發展道路,努力發展高水平、有特色的高等教育,不斷提升學校吸引力。
《教育家》:當下,就業形勢嚴峻,高等教育布局和大學內部結構是否需要重新調整?有學者認為,今后以就業為導向的大學會大量出現,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李立國:從某種角度來看,這種導向有一定的合理性。大部分學生選擇學校、專業肯定要考慮就業問題。尤其是現在就業形勢非常嚴峻,2023年我國高校畢業生預計將達1158萬人,招工難、就業難的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
這個現象反映出我們的高等教育存在一定問題,比如專業設置過細過窄,導致專業通用性較差,與此同時,經濟產業不斷發展變化,對人才的需求也一直在變動,于是專業和就業失去了適應性,一方面大學生就業過剩,一方面市場人才緊缺。這就要求高等教育布局和大學內部結構進行重新調整,一方面要注重人才培養的通用性,一方面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根據產業調整不斷優化學科、專業。
我個人比較期待這類大學的出現,但它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要以人才培養為中心。大學是科研重地,更是人才培養的重地。近幾年我們過于強調前者,忽視了大學的本質是培養人、造就人,教師的核心工作就是培養學生,未來應發展一批教學型高校;二是學科專業設置、課程設置要更加實用,更加符合職業需求,更加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三是要真正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學校需要和企業進行優勢互補,企業通過投資改善學校硬件設施、建立實訓基地,學校為企業提供人才,學生畢業即可就業。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以就業為導向,還是要有一部分大學承擔科研項目,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在科技創新基礎研究上發力,避免被“卡脖子”。因此,高等教育整體布局要做好分層分類發展的設計。
《教育家》:高等教育發展與區域經濟模式和產業結構等息息相關,大學應該如何布局學科和專業設置,既對接區域發展,又辦出特色?
李立國:首先從宏觀層面出發,我們要營造良性競爭的教育環境,在競爭中形成特色。只有打破行政力量的保護,在充分的競爭中,大家才能明白自己的優勢和不足,才能明確自身定位,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
其次才是大學如何布局學科和專業的問題。高等教育發展與區域經濟模式、產業結構等息息相關,大學要提升辦學水平,其學科布局和專業設置必然要對接區域發展,與當地的經濟結構、產業布局相匹配,本土即是特色。
這就要求高校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態,強化特色專業、特色學科,對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一定的支撐。這樣一來,當地就能為畢業生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畢業生也愿意為這座城市貢獻力量,高校和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由此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比如,在西部地區,生態、礦產資源比較豐富,高校可以在農業、礦業等領域做文章,匹配當地產業需求,設計特色學科和專業。
另外,我想強調的是,雖然高等教育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但高等教育不能僅僅滿足于適應,還要做一些開創性的工作,要適當引領經濟社會發展。要通過人才培養、科技創新,為地方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新活力。大學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所在、動力所在,要有使命感和創新精神,不斷挖掘自身潛力,為時代、國家、民族的發展服務。
責任編輯:鄧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