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童失蹤事件
[英]歐內斯特·布拉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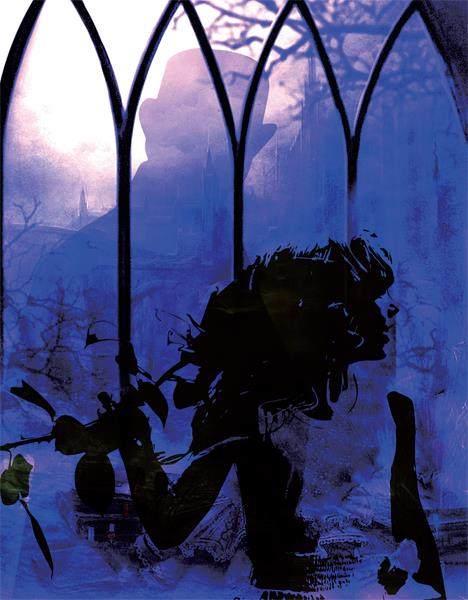
應蘇格蘭場的比德爾探長之邀,麥克斯·卡拉多斯接下了瑪莉·賽威爾失蹤的案子。此事起初鬧得沸沸揚揚,現在——也就是兩周后——已經無人問津。
“我們一個線索也沒放過,但還是一無所獲。我不介意向您承認,我一直認為是瑪莉的父親亞瑟·賽威爾在那天下午帶走了她。”比德爾慢條斯理地說。
“為什么?”卡拉多斯問。
“賽威爾夫婦在四五年前離婚了。賽威爾夫人仍然擁有良好的地位,在斯旺斯蒂德有一棟豪宅,每年有五六百鎊的收入。而賽威爾先生的地位一直在不斷地下降,他現在幾乎是個窮人。賽威爾夫人擁有瑪莉的監護權,她認為前夫太寒酸,不再允許他見孩子。大約一個月前,他倆在街上偶遇。賽威爾先生要求繼續探訪。當時,正好有一個姓朱爾普的女士也在場,她也許說了什么。最后,賽威爾夫人給了前夫一張支票來結束討論。賽威爾先生當場撕毀了支票,把碎片扔進了附近的水溝里,撣了撣手指,舉起帽子走了,沒有再說話。這是兩人最后一次相見,賽威爾夫人自稱從那時起就一直擔心會發生什么事。”
“您因此而指控賽威爾先生?”
“這算不上一個指控。賽威爾夫人認為前夫只是想報復自己,而不會傷害孩子,她甚至要求報紙不再報道此事。事實上也沒有證據表明賽威爾先生和孩子在一起。不過,在瑪莉失蹤的那個下午,他的行蹤實在可疑。他中午十二點出門,下午五點回家,他說這段時間自己在辦公室,但同事都說沒看見他。而且,斯旺斯蒂德車站的一名工人指認他是那天下午從某趟列車上下來的乘客之一。”
“從照片?”
“首先是看了照片,之后又指認了本人。”
“他們在車站說過話?”
“不,那名工人只是看到了他。”
“這樣的指認太隨意了。眼睛易受蒙蔽。”
“但仍然可以作為佐證。”比德爾說,“我們還有一件物證,是賽威爾夫人收到的一封信,很不尋常。”他把一個信封遞給卡拉多斯。
盲人的指尖從紙上劃過。“倫敦,5月15日下午5點30分。”他念出郵戳上的字。
“瑪莉就是那天失蹤的。有一列火車從斯旺斯蒂德出發,于4點47分到達蘭貝斯橋。”
“發車時那位工人在做什么?”
“他那時已經下班了。”
卡拉多斯打開信封,取出里面的信件,立刻就明白了為什么這封信“很不尋常”。“這些字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他說。
“我們已經確認過,是5月13日的《泰晤士報》。”比德爾贊同道,“由此看來,這件事是有預謀的。”
“不要驚慌,女孩很安全。只有急于尋找,才會造成風險。等著,她會毫發無傷地回家。”盲人念完信上的文字,又說:“報紙的日期意義不大,不過,對文字的刻意選擇、精心剪裁和排列,孩子失蹤的時間,以及這封信的寄送時間,的確表明這件事是有預謀的。您對這封信做過化驗嗎?”
“沒有。我們并非完全沒有考慮過氣味之類的東西,警犬嗅過瑪莉的靴子,幫我們確定了她失蹤前的具體位置,之后,線索就斷了。”比德爾說,“與其說我懷疑亞瑟·賽威爾是綁架犯,不如說我希望他是。瑪莉是個漂亮的女孩,如果落在別的什么人手里……”他沒有繼續說下去,但盲人已經很明白了。
“我擔心,這是一場關于機會的賭博。我們要么大獲全勝,要么輸得一敗涂地。”卡拉多斯說,“告訴我瑪莉失蹤的地點,我要走一趟。”
當晚,卡拉多斯的車開往斯旺斯蒂德。大道平坦,一側是廣闊的原野,沒有任何建筑,另一側,經過車站,第一棟豪宅就是賽威爾夫人的,隔壁是一座山莊,山莊的主人埃勒斯利大夫在城里的診所中工作,只在周末才到此度假。沿著大道往前,是一塊沒有圍欄的草地,也就是瑪莉在失蹤前最后一次出現的地方。根據比德爾的調查,草地離學校很近,孩子們常在放學以后來此玩耍,工人路過時會在這里歇腳。山莊的一個側門對著草地,但總是鎖上,很少打開。比德爾曾進入山莊查看,發現只能通過一扇小窗看向草地,窗外又有樹木遮擋,故而什么也看不見。
經過草地,前面的建筑屬于一位退休的陸軍上校,他從印度回來以后一直住在這里。比德爾也調查過上校的家,沒有開向草地的門,從里面也完全看不到草地。
在和前夫發生爭執之后,賽威爾夫人不再讓瑪莉單獨出門,只有上學的時候除外,因為學校離家很近,開闊的街道又給人以安全感。不過,她還是會站在家門口,目送瑪莉沿著開闊的道路,走進學校。
“那天本來也該這樣。”比德爾告訴卡拉多斯,“但在瑪莉快要出門的時候,恰好有客來訪,賽威爾夫人看見校長站在路邊,路上又沒有其他人,就放心地去招待客人了。可是,在她回屋以后,校長也有事走開了。校長遠遠地看見賽威爾家來了客,以為瑪莉那天就不上學了。于是,直到下午4點,賽威爾夫人發現瑪莉沒有回家,才知道出了事。”他把地圖也交給了卡拉多斯。盲人用手指讀著探長畫下的標記。
“警犬帶著你們重走了一遍瑪莉的路線。她本來沿著大道直行,走向學校,卻突然轉彎,走進草地,走到了正中間。”手指停在標記的終點。
“應該是有什么吸引了她的注意,或者有人叫她。現場沒有掙扎的痕跡,也沒有車轍。有個人站在那里,抱起孩子就走了——一定是瑪莉熟識并且親近的人。”比德爾說。
“不要如此肯定,探長。”卡拉多斯這樣評論。
而此刻,他被帕金森扶著,下了車,沿著大道走了一遍,又來到草地上。帕金森仔細地檢視著每一個角落,終于在那扇上鎖的門附近撿到了一片看起來很普通的花瓣。帕金森很快就知道自己沒有白費力氣,因為卡拉多斯在聞了聞那片花瓣以后,就去撬開了那扇門,徑直走入埃勒斯利大夫的地盤。
“你往回走吧。”卡拉多斯說,“我如果需要你,就吹口哨。”
“是,先生。”帕金森答道。不久,他看見自己的主人走回了大道上,在賽威爾家門前來回踱步。他也早已察覺到,賽威爾夫人在窗口看了多時。
“先生!”賽威爾夫人打開了門,“您在這個時候在這里走來走去,是否知道什么消息?我的瑪莉是在這里走丟的,您肯定知道,每個人都知道。”
“是的。”卡拉多斯說,“比德爾探長告訴過我。”
“他!”賽威爾夫人失望地說,“他很善良、誠實,但他什么也沒找到。”
這時,有個女人在樓上叫著賽威爾夫人的名字,語氣急切。卡拉多斯繼續問:“您的女兒喜歡花?”
“她愛把臉埋在花叢里,聞著花香。她幾乎就要住在花園里——您怎么知道她喜歡花?”
“猜測而已。”
樓上的女人又喊起來,賽威爾夫人答應了兩聲,仍然看著卡拉多斯。她還沒有發現面前的人實際上看不見自己。
“瑪莉最近生過病?”盲人問道。
“沒有!”賽威爾夫人立刻用強調的語氣回答,聽上去很為孩子的健康驕傲。
“沒有其他什么事需要醫生的服務?”
“瑪莉從來不需要醫生的服務!”賽威爾夫人斬釘截鐵地說,仿佛受了冒犯,“我的孩子從來不知疾病為何物,我對此很高興。”
“你在這兒!”樓上的女人已經下來了,穿著樸素的衣服,腳步沉重,令人感到肅穆,“你把我嚇壞了。為什么和一個陌生人說話?”賽威爾夫人似乎終于意識到面前的陌生人什么也不知道,語氣冷淡地道了一聲“晚安”,和那個女人一起回去了。
“母親最了解孩子的健康狀況。”卡拉多斯回到車上以后,對帕金森說。回到角樓居,他立刻撥通了蘇格蘭場的電話,比德爾探長在那頭說自己沒什么新發現。
“要是您去埃勒斯利的山莊,堅持要見昨晚在那里過夜的孩子,也許就會有新發現了。”
“埃勒斯利大夫?!”比德爾驚呼道,“你不會想說——”
“這得靠您自己去確定了。埃勒斯利是個鰥夫,沒有孩子。”卡拉多斯陳述道,“瑪莉被下了藥。那是一種新型的麻醉劑,下在花里,順便說一下,如果您化驗過那封信,就會早些知道了。她被抱進山莊,有一束頭發掛在了花叢里,在離門六碼遠的地方,那里種著覆盆子。這就是我所知的一切。”
“可這——埃勒斯利每天都在濟世救人,他怎么會——”
“我知道他在手術室里救人無數,把這樣一個人拉下馬的確不是一件樂事。您想怎么利用這些信息就怎么利用吧,我不想再和這件案子有任何關系了。再見。”卡拉多斯掛斷了電話,放下了這個案子。
不到兩個小時,案子再次找上了他。帕金森說有一位賽威爾先生來訪。
“蘇格蘭場就瑪莉失蹤的事情向您咨詢過?”賽威爾先生開門見山地問。
“報紙上可沒有這么說。”
“我不能依靠報紙去關心我的女兒。比德爾一門心思認定我是兇手,說我綁架自己的親生女兒,被報紙傳得滿城皆知,連車站工人的記憶也受了影響。我現在是個臭名昭著的惡棍。傳說比德爾來找您,讓您來查我。”

大霧彌漫的里士滿公園。這里是卡拉多斯經常散步的場所之一。公園里的樹木也許聆聽過盲偵探的喃喃自語。
“如果這不是傳說,而是真的呢?”
“事實上,卡拉多斯先生,我不會讓瑪莉離開舒適的環境,出來跟著我過苦日子。我的前妻能保證孩子過上體面的生活,雖然她有著許多缺點,比如愛跟風趕時髦,又很輕信,‘吃什么東西就能包治百病這種話也能騙到她。那個叫朱爾普的騙子,把一些迷信的念頭灌進她的腦子里。我已經開始相信,也許瑪莉病了,被她們用什么奇怪的偏方害死了,朱爾普為了掩飾,制造出綁架的假象,她——”
卡拉多斯極少打斷他人的話,此時卻不得不失禮一次,他說:“但瑪莉不是一向很健康嗎?賽威爾夫人說她‘不知疾病為何物。”
“那就是朱爾普教的!要我說,瑪莉的體質是很弱的,她的消化一直不太好。”
“我恐怕犯了一個錯。”卡拉多斯喃喃自語,立刻叫帕金森備車。
賽威爾先生盡管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么,仍然耐心等待。卡拉多斯回來時,臉上帶著歉意。
“我去晚了,沒能攔住比德爾。這樣一來,不得不請您和我一道出發,試著從另一個方向來彌補過失。您還得答應我一些事,我們在路上說。”
“只要能用得上我!瑪莉的安全和幸福,就是我的一切。”
汽車一路狂奔,不斷引起交警吹哨。卡拉多斯敲開山莊的大門時,高興地發現比德爾還沒有到。女仆推脫說大夫在城里的診所,但在客人的強烈要求下,她打了電話。埃勒斯利不一會兒就走進了客廳。
“卡拉多斯先生大駕光臨,有何要事?”
“我想提醒您,比德爾探長即將來訪,要求您交出失蹤的瑪莉·賽威爾,如果您拒絕,他就會搜查整個山莊。您也許可以在他到來之前,做一些解釋。”
“在卡拉多斯和蘇格蘭場之間,我還能說什么呢?”埃勒斯利說,“您認為瑪莉在這里,這一點是不錯的。是我帶她來的。我這么做,是為了報復。也許您猜到原因了?”
“那倒沒有。”卡拉多斯溫和地說。
“十年前,我唯一的女兒,被一個女人害死了。那個女人輕信謠言,不再相信醫學的價值,不允許我救治我們的孩子。闌尾炎,那是我擅長的領域,可我卻眼看著我的女兒死于此病。也許是巧合,另一個輕信的女人成為我的鄰居。每當我周末來此,就能看見她的女兒在附近玩耍。瑪莉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只是身體不太好。我為了觀察她的病情,吩咐女仆允許她到山莊的花園里來玩,不久就發現她的病和我女兒的一模一樣。三周前,她在花園里扎傷了胳膊,我在給她包扎時取到了血液樣本。化驗結果表明,必須盡快動手術。我沒時間去和迷信的人爭論,就在那個早上拿著一束花,站在草地中間,招呼她過來。瑪莉信任有花園的地方,直到現在也沒有意識到自己被‘綁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