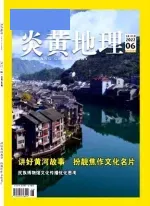對于兩江口爭奪的分析研究
肖思程
兩江口持續百年的爭奪,從家族內訌演變成永順保靖兩大土司之間的較量,其中牽扯多方勢力,且十分復雜。而這場爭奪的最后,使得保靖永順兩大土司都受到了一定影響,明中央朝廷也借此將中央勢力深入到了土司地方,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在這場爭奪中,各方都為了自身利益進行角逐,在爭奪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明代前中期發生的兩江口爭奪事件,開始只是一場家族內訌,后來升級為兩大土司之間的勢力較量,事件發生了本質性改變。永順、保靖兩大土司力量,針對“兩江口”問題進行了長時間較量,最終因明朝中央勢力的介入,事件才得以平息。這一爭奪,致使永順、保靖土司都受到了影響,明中央也借此加強了中央對土司地方的控制。那么,這場爭奪到底是怎樣的?現從起因、緣由、以及對各方勢力的分析幾方面進行簡單闡述。
爭奪起因
公元1412年,保靖宣慰使彭勇烈因病離世,由其子彭藥哈俾襲職,但因年幼,堂叔大蟲可宜以副宣慰之職署理司事。公元1424年,大蟲可宜殺藥哈俾,自稱宣慰。后來雖被明朝廷搜捕入獄而死,革去副宣慰一職,但仍管轄舊有領地。大蟲可宜的后代因隨征有功,授兩江口長官,卻不給印信。而保靖司因其割據兩江口之地,拒不承認其長官之職。這就是“兩江口”爭奪的起因,這一事件在《明史》有著詳細的記載,“勇烈卒,子藥哈俾嗣,年幼。萬里弟麥谷踵之子火蟲可宜,諷土人奏己為副宣慰,同理司事,因殺藥哈俾而據其十四寨。事覺,逮問,死獄中,革副宣慰,而所據寨如故。其后,勇烈之弟勇杰嗣,傳子南木杵,孫顯宗,曾孫仕瓏;與大蟲可宜之子忠,忠子武,武子勝祖及其子世英,代為仇敵。而武以正統中隨征有功,授兩江口長官,勝祖成化中亦以功授前職,并隨司理事,無印署。弘治初,勝祖以年老,世英無官,恐仕瓏奪其地,援例求世襲,奏行核實,仕瓏輒沮之,以是仇恨益甚,兩家所轄土人亦各分黨仇殺……”后來,兩江口長官司與永順土司結為姻親關系,連帶著永順司也開始借此攻擊保靖土司,這一爭奪也逐漸從保靖土司的家族內訌演變成了永順與保靖兩大土司之間的較量,時間長達百年,對永順保靖兩地的土司勢力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爭奪的原因
從一開始保靖土司家族的內訌引發的“兩江口”爭奪,經過不斷發酵,逐漸演變成了永順保靖兩地土司的較量,其中還不乏明朝中央政府的介入。我們不妨思考,這場爭奪,到底為何?
為“地”
事件的開始,是因保靖土司不滿大蟲可宜的后代割據兩江口之地,拒不承認其長官之職而起,后來才有了爭奪的不斷發酵。所以,為何而爭,第一個原因顯而易見,那就是因為“地”。這個“地”,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兩江口的地理位置;二是指對轄地的堅持。
1.兩江口的地理位置
兩江口的地理位置相當于今隆頭鎮,處于今天保靖和龍山的交界處,地處酉水,與深入永順土司境內的洗車河交匯,酉水河順流而下再進入沅江,連接長江,處在河流交匯的中心位置,是當時一條較為重要的水運通道,地理位置十分優越。在交通不便的明代,水運通道對一個地方的交通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因此,為了這條重要的水運通道,兩方勢力都不可能放棄,只會將爭奪進行到底,包括后來永順借口介入此場爭奪,一場內部糾紛逐漸上升演變為保靖永順兩大土司之間的爭端,兩江口優越的地理位置,是推動爭奪升級的一個重要原因。
2.轄地的堅持
兩江口本來是屬于保靖管轄范圍,如果不爭,承認其長官之職,就相當于變相默認了兩江口脫離保靖管區,割地自治的事實。這樣一來,保靖的管區相比之前突然減少,轄地范圍縮小;而且割地自治之例一旦開了,難保之后不會再出現,這對保靖的管轄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隱患。因此,出于對管轄地區控制權的堅持,保靖不可能放棄這場爭奪。
兩江口長官亦是如此,在明朝中央朝廷的允諾下,雖然沒有印信,但實際上兩江口已經擁有了自治權。因此,不管是出于家族之間的仇怨,還是對兩江口控制權的把握,兩江口長官都不會對保靖進行妥協退讓。爭奪,是保住兩江口地區控制權最直接亦最有效的方法。
永順的目的則更加簡單,永順保靖本就同為土司,存在利益沖突,而永順借姻親之名幫助兩江口長官攻擊保靖,一方面可以使保靖的轄地因此縮小,管轄力量減弱;另一方面,對兩江口的拉攏,亦是為自己管轄范圍的安全增加了一層保障。因此,加入爭奪對永順來說是順勢而為。
為“權”
為何爭奪“兩江口”,“權”是一個主要原因。這個“權”,指的是對管地的控制權。
1.保靖
兩江口本來屬于保靖管區,保靖土司對其有著絕對的控制權。可兩江口長官司的設立,讓兩江口獨立出來,保靖土司可以說是完全失去了這一絕對控制權,這對保靖土司的實際權力造成了極大的損害,是其無法容忍的。而且兩江口長官司的設立對保靖土司來說使得其原有的管區縮小,其管制力量也因此有所減弱,從與其他土司的力量角逐來看,會使保靖土司處于極其不利的地位。因此,為了收回控制權,保證勢力,保靖土司對于兩江口,是非爭不可的。
2.兩江口長官
兩江口長官本就與保靖土司之間存在家族恩怨,雙方都互不相讓。而把握住兩江口的控制權,就等于有了與保靖土司對峙的力量保障,一旦失去這一力量保障,就相當于失去了自身最重要的一道護身符。出于對自身利益最大的考量,兩江口長官對于保靖拒不承認其長官地位這一態度是不能接受的,而保靖若想借口收回管區,重新拿到兩江口的控制權,也是其無法容忍的。因此,為了保護好自身利益,兩江口長官勢必要牢牢握住兩江口的控制權,爭奪自然無可避免。
3.永順
保靖與永順同為土司,距離相近,勢力也在伯仲之間,雙方長期以來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互相關注對方的一舉一動。而兩江口的爭奪,對永順土司來說是一個攻擊保靖土司的絕好機會。永順借姻親之名幫助兩江口長官對抗保靖,一來是為自己找到一個同盟,希望對保靖土司產生重擊,使其勢力大大折損;二來也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考量,保靖土司若失去了對兩江口的絕對控制權,其轄地將因此減少,力量自會因此削弱,對永順土司來說,保靖土司的力量削弱,等于間接保護了永順自身力量。因此,為了能夠對保靖土司進行有效打擊以及出于對自身利益保障的考量,永順介入此次爭奪,幫助兩江口長官把握住兩江口的控制權,是必然而行的。
綜上分析來看,兩江口為何而爭,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地”,即兩江口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對此轄地的堅持;另一個則是“權”,即對兩江口此地的控制權。而無論是出于何種緣由,歸根結底都是各方對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而做出的決定。因此,兩江口之爭的根本,其實是土司之間為了利益的爭奪而進行的一場力量角逐。
爭奪中的“角色”
在這場關于兩江口的爭奪中,牽扯進了保靖永順兩大土司力量,而明朝中央朝廷也一度介入調停。那么,在這場爭奪中,各方力量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
“主力”——保靖土司與兩江口長官
這場關于兩江口的爭奪,“主力”無疑是保靖土司與兩江口長官。這場爭奪的起因,本來就是保靖土司不滿兩江口長官司一職的設立,不愿其割據兩江口之地而起。保靖土司與兩江口長官從爭奪的開始到結束一直都是事件圍繞的中心,雙方為了各自的利益考量,在這場爭奪中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爭奪時間達百年之久。亦可以說,正是因為保靖土司與兩江口長官這二者“主力”的存在,才有了關于這場兩江口的爭奪。因此,在這場爭奪中,保靖土司與兩江口長官均是“主力”,而雙方的態度對峙,亦是這場爭奪的起因。并且,隨著事件的不斷發展,這場爭奪逐漸從保靖土司與兩江口長官之間的家族內訌演變為土司之間的力量較量。
“推力”——永順土司
公元1488年,兩江口長官司彭勝祖的兒子彭世英襲位,保靖土司仕瓏輒沮之。據相關史料的記載,永順土司彭世麒和弟弟彭世麟娶的妻子都是兩江口彭勝祖的女兒,兩江口與永順成為姻親。永順土司以這層關系為理由,順勢派兵幫助兩江口與保靖司仇殺。這是史料上對永順土司力量介入到保靖土司與兩江口之間爭斗的首次記載,加上永順與保靖兩司之間關系本就微妙,利益糾葛復雜。由此,這場原本只是家族爭襲內訌的爭奪開始變質,逐漸演變成了永順與保靖兩司之間的較量,事件性質上升為地方土司之間的利益角逐。可以說,永順土司是這場爭奪中最大的“推力”。那么,永順這個“推力”又到底推動了怎樣的發展呢?主要可以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永順的介入,推動了事態的升級與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保靖與永順之間本就關系微妙,保靖土司先于永順土司歸順明王朝。“初,保靖安撫彭萬里以洪武元年歸附,即其他設保靖宣慰司,授萬里宣慰使,領白崖、大別、大江、小江等二十八村寨。”保靖土司得到明朝中央的官方承認,地位發生變化,與永順土司平級,正式脫離永順土司,保靖土司管區就此形成。后來,保靖在管地上捷足先登,亦使永順心有不滿,雙方矛盾其實已經存在。兩江口長官與保靖土司產生爭奪,永順借姻親之名趁機介入,攻擊保靖,亦是將兩江口與保靖的矛盾深化成了永順與保靖之間的矛盾,使得事件矛盾進一步激化。而永順的介入,亦使這場爭奪從本質上產生了變化,即從家族爭襲內訌演變上升為保靖永順兩大土司之間的力量角逐,使得事態進一步升級。第二,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本來只是兩江口長官與保靖土司之間的對峙較量,可永順土司的介入,使得爭奪力量重新分比洗牌,使得爭奪更加復雜,且永順還借助明中央的力量,試圖將事情影響進一步擴大。公元1499年,永順宣慰司借此事上奏明朝中央,以此對保靖施壓。這種種變化,使得爭奪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永順成了兩江口對抗保靖的最大推力,逐漸成了與保靖進行力量角逐的重心。
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場爭奪中,永順逐漸成了不可缺少的一個存在,是爭奪中的最重要“推力”。而且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場爭奪之所以會進行百年之久,少不了永順的推動。
“制衡”——明朝中央朝廷
爭奪如果一直不進行制止,任其繼續下去,影響只會越來越大。因此,總需要有人出面制衡,以保證爭奪的平衡。而在兩江口的爭奪中,起到“制衡”作用的則是明朝中央朝廷。在“兩江口”問題上,中央政權始終注視著事件發展的動態變化,選擇在恰當的時間點出手,做出相應的處置措施。
兩江口爭奪發生的起因,就是因為大蟲可宜及其子孫所占據的十四寨,被朝廷授予“兩江口長官司”,在中央朝廷的默許下,形成了兩江口長官司管區,脫離保靖管制,引發保靖土司不滿。弘治年間,朝廷兵部移文中更是出現了“兩江口長官司”字,中央政權變相承認了這一地區自治的合法性,保靖土司不滿加劇。為了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朝廷“令世英所據小江七寨于仕瓏,止領大江七寨”,并派清水溪堡官兵守兩江口之地。使兩江口長官司管區由十四寨縮減到七寨,明中央則成功地將兩江口這個戰略要地改由清溪堡官軍來駐守。最后,正德年間,兩江口彭惠與彭九霄仇殺數年,朝廷令“大江之右五寨歸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屬辰州”,在中央政權的制衡下,兩江口長官司管區不復存在,改設大喇巡檢司。這場持續百年的爭奪也就此結束。這樣的“制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為了解決矛盾,而是為了借矛盾分化土司力量。從爭奪開始起,明中央政權始終未完全正面介入永、保土司爭斗中,而是一直默默關注事態變化,在背后起著“制衡”的作用,并引導了事件的最終走向。
可以說,明中央從一開始便默默注視著一切的發展變化,并在適當的時間介入,使得這場爭奪最后按照其預想的步伐前進,得到其想要的結果。明中央一開始就決定在其中扮演背后進行“制衡”的角色,事實上它也成功做到了。而從整個事件的發展及結果來看,明中央發揮的“制衡”作用是十分有效的,它成功地分化了當地的土司力量,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在這場爭奪中,各方力量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保靖土司與兩江口長官是“主力”,是爭奪的開始,也是一直在進行爭奪的對象;永順土司是爭奪中最大的“推力”,其介入使得事態升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兩者都是這場爭奪中重要的存在,也是爭奪不斷進行的支撐。而明中央朝廷則一直隱藏在這場爭奪的暗處,起到“制衡”的作用,關注事態變化,在適當的時間出手對各方進行制衡,使得事件向著其所希望的方向發展。如果說一定要為這場爭奪定一個贏家,永、保其實都算不上,明中央才是。因為這場土司內斗,最后成了明中央介入地方土司勢力的最好助力,達到了中央瓦解地方的最好效果。爭奪的最后,一切都終將被“制衡”,明中央朝廷就是進行“制衡”的那只手。
這場爭奪最后的結果是在朝廷的主導下,裁撤兩江口長官司管區,改設大喇巡檢司,并派遣流官主政。這場持續百年的爭奪終于得以平息。在這個過程中,永順、保靖二司利用“兩江口”的爭奪互相博弈,各有得失。而朝廷則利用這場土司之間的矛盾,從大土司中分離出小土司,將勢力深入土司管區的內部,使得土司更替,不再只是依靠傳統的、成王敗寇式的地方角力,而是聽命于中央政府,漸漸蠶食土司制度。可以說,明中央朝廷才是這場爭奪中最大的贏家。而綜合來看,中央介入土司地方,土司力量不斷被分化,中央權力不斷增強,從某種程度來說亦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關于兩江口的爭奪,本來只是一場關于家族爭襲的內訌,但因各方對利益的追逐,事態發酵升級,逐漸演變成了永順保靖兩大土司之間的力量較量。明朝中央朝廷介入調停,一方面停止了事端的繼續發展,起到了有效的“制衡”作用;另一方面借此分化土司力量,成了爭奪事件的最大獲利者。
參考文獻
[1]張廷玉.明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4.
[2]游俊,呂華明.明史湘西史料鉤沉[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
[3]方濤.“兩江口事件”與明代永順、保靖土司管區的變化[J].牡丹,2016(08):174-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