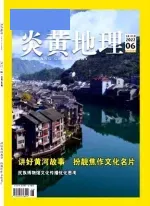旅游開發對旅游目的地老城區傳統鄰里關系的影響
代燕 孫慧蘭

鄰里關系是社區共同體建設的核心,是培育社區凝聚力的社會基礎。旅游開發改變了老城區傳統鄰里關系建立的社會經濟背景與基礎,然而并不必然導致社區凝聚力下降。應用情感團結理論對伊犁老城喀贊其鄰里關系分析,結果表明:旅游業通過提高居民經濟收入和生活質量,增強了居民的經濟意識、共同體意識和地方認同,同時不斷擴大的經濟收入差距激發了鄰里關系的矛盾;鄰里關系“總體弱化、局部更加緊密”,建立基礎逐步呈現“經濟利益+血緣關系+地緣關系(鄰居)”復合的特征,經濟共同體意識突出。旅游發展需要考慮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機會均等性,社會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以產業發展培育新鄰里文化,服務于社區治理現代化。
鄰里關系是居民在長期互動交往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共同生產生活、共同情感的社會關系,有著深刻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1],是城市社區共同體建設的核心基礎、社區現代化治理的社會基礎[2]。在旅游推動的城市更新過程中,老城區的鄰里關系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甚至被分裂、破壞,而目前的相關研究較少關注到這一方面[3],更缺乏對變化的過程性理解。
新疆伊犁老城喀贊其在更新改造過程中被開發為旅游區。當地特色歷史文化資源開拓了國內外游客市場,激發了資源多維價值的同時,也明顯改變了當地傳統鄰里關系的社會經濟背景,鄰里關系的新變化也必然引起共同體重建。由此,把握旅游開發下老城區傳統鄰里關系變化的特征,剖析旅游發展對鄰里內部關系影響的主要方面,深入理解新的鄰里關系對提升共同體建設的思考就很有必要,進而反思如何通過調整旅游發展促進新鄰里關系的建設,提高現代化治理水平。
鄰里關系的研究
鄰里關系的內涵
社會交往是鄰里關系的基礎。交往在人類學和社會學意義上,是個人之間為了生存和彼此需要而進行的交互活動[4];在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為人類從事生產活動過程中形成的生產關系和表現出的交換、流通等行為,內含了交互活動、交換和生產關系等含義。生產技術的進步是交往關系更迭的積極因素。勞動分工水平越高,個人生產的獨立性越強,以產品為中介的社會交換需求越迫切,越需要相對穩定密切的社會關系以保障產品交換。傳統農業活動較低的生產力水平限制了個人從自然環境中獲得生存資本的能力,人與人之間通常以血緣、地緣為紐帶結成無償互助的“人情”關系;工業社會,個人更依賴于社會交換以滿足個體的生產生活需求,人與人之間形成以經濟利益交換為中心的社會關系,導致形成基于物質的經濟利益競爭關系[5],城市產生了新的人際關系和生活方式,鄉村地區傳統的人際關系也被消解。
鄰里關系是具有地域性的社會關系的重要構成。在我國古代時期指主要基于地緣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在現代社會被認為是所有社區成員共有的特征和最基本的社區社會關系,強調地緣臨近的共同生活所形成的關聯、互動、共享及影響等[6]。鄰里關系具有地域差異性,城市中的鄰里關系被認為是缺乏人情等文化因素的共同體,并且改革開放以來受社會結構變動、居民收入水平、街區類型[7]、居民個體特征[8]等影響總體弱化,而旅游開發是主要推動力之一。
喀贊其民俗旅游區所在的伊寧市南部老城區,居民基于地緣、親緣在幾百年的經濟生活過程中結成了較為穩定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因而將其視為城市中一類非行政區劃的“鄰里”單元。旅游開發改變了當地鄰里關系的社會經濟背景,區內集中連片的歷史民居、民風民俗等被開發為主要的旅游商品,日常生產生活成為現代經濟的重要生產資料,地方的鄰里關系也變成維護經濟利益關系的重要部分。
旅游發展對鄰里關系的影響
國外旅游學、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認為,旅游業促使經濟利益逐漸成為當地的核心價值觀,傳統鄰里關系變得冷漠,并引起人際矛盾和沖突[9],為抵制消極影響當地居民會自發地、更緊密地團結起來[10]。我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學領域,關注旅游業影響人際關系的具體表現、影響因素以及效果等,認為旅游開發的經濟效應使得當地居民逐步樹立以經濟利益、個人利益為中心的價值觀念,社會階層、社會關系被分解破壞,并引發矛盾和沖突[11],居民缺乏歸屬感與安全感[12],毗鄰為親、友好互助、組織有序的傳統鄰里關系被逐漸瓦解[13],逐漸轉向現代人際關系[14],其中情感和心理層面的變化較為隱蔽,卻最能反映鄰里關系的本質變化。
情感團結理論是研究旅游發展對社會關系影響的經典理論。情感團結概念的提出者Durkheim認為,情感團結是具有相似信仰和行為的個人通過相互交往而形成的情感聯系,團結是個人相互作用的結果。學者們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構建了基于共同信仰、共同實踐行為、與游客互動親密度的分析框架,用以分析居民—游客關系變化及其對旅游發展的影響[15],而相對忽視鄰里關系的研究及意義。
本研究基于Durkheim情感理論的內涵,建立共同觀念、共同行為和互動親密度三個維度的分析框架,從意識、行為、心理層面探討旅游開發對居民—居民間鄰里關系的影響,服務于現代經濟社會背景下鄰里關系的進步和社區共同體建設。
旅游發展影響伊犁老城喀贊其鄰里關系的實地調研
喀贊其是新疆伊寧南市區的老生活社區。區內居民基于地緣、親緣在幾百年的經濟生活過程中結成了較為穩定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秩序,可視為城市中一類非行政區劃的“鄰里”單元;區內分布的清朝至民國時期的古建筑、特色居民庭院,制鞋、鐵藝、木雕、馬鞍等傳統手工作坊,都被開發為主要的旅游商品,日常生活成為旅游經濟的重要生產資料。新產業的開發重構了鄰里關系建立的背景和基礎。
調研情況
2020年4月1日至4月7日,6月10日至13日赴喀贊其民俗旅游區進行實地調查,對代表性的旅游業經營者(本地居民)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對一般居民開展問卷調查。其中,重點訪談了8位代表性的旅游業經營者,其從事農家樂、民宿、飯店和超市等經濟活動,經營規模在同行業中較大、發展較好,觀點和認識具有代表性。訪談提綱設計了鄰里交往意識、感受到的鄰里關系、鄰里關系變化的具體表現等三個層面的問題,訪談平均時長1.5小時/人。問卷內容設計了自我人際關系認知、外部人際關系變化的感知、影響因素認知和地方認同四個層面,問卷共發放140份,回收140份,有效問卷128份,問卷有效率為91%,見表。
旅游經營者對鄰里關系的認知
1.總體認知:人際關系復雜化、多樣化
根據被訪談者陳述,旅游發展后人際關系已經逐漸冷漠,居民之間的交往逐漸表面化和形式化。民宿老板表示:“如今,自己沒有以前一樣十分看重和周圍居民的人際關系,因為關系都沒有以前那么融洽了,出門遇到只會點頭打招呼,最多寒暄幾句,甚至周圍的幾戶都不怎么熟悉。因為旅游業開發以后大部分人會專注于賺錢,很少特地經營人際關系,人際關系更多存在于自己比較關心的、與自己有經濟利益關系的人,淡化與其他人群的人際交往”。而從事旅游經營活動的居民關系之間比較好。農家樂老板表示,“參與旅游之前自己交往認識的人只限周圍鄰居,但是參與旅游業以后,交往的(人)越來越多了。之前幾乎不相識的人現在成了好朋友,而且經常會彼此幫忙、互相串門,逢年過節生日喜事都會互送禮品。因為旅游業的開發結交的人多了,但是反而忽略了之前關系不錯的人們,會有點遺憾。”旅游業開發以后居民之間矛盾明顯增加,人際關系出現緊張,日常生活小事就會導致鄰居間產生矛盾。超市老板表示,“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有兩家人因為某些小事產生矛盾,大打出手,以至于上了法庭才解決了事,所以會十分懷念之前鄰里間相敬如賓的人際關系,出現矛盾時大家也愿意盡快和解”。
2.情感團結分析
在共同觀念方面,旅游業發展提高了居民收入和經濟意識,鄰里關系出現服務于經濟利益的傾向。旅游區內居民房屋建筑格局緊湊,公共空間的使用權經常成為居民間矛盾的觸發點。一位民宿老板就因為擴建民宿時占用了公共空間與鄰居發生了經濟糾紛,問題解決后兩家關系變得客氣生分,之前的親切感淡化。旅游發展后,互幫互助的需求更為強烈但經濟目的性也更明顯,鄰里間的信任、情感逐漸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的社會資本。
在共同行為方面集中表現為共同的經濟行為。當面臨生產資金籌措、勞動力短缺等問題時,會求助于親戚和關系好的朋友,甚至請親戚幫忙招待客人甚至接送游客。農家樂老板、飯店老板表示,旅游旺季時常出現食材和飲品庫存不足,這個時候通常求助關系好的鄰居或自家親戚,“旅游旺季客人多的時候會請遠房親戚幫忙,主要原因是親戚需要幫助的時候也會找自己(幫忙)”。可以看到,鄰里關系逐漸轉向經濟共同體。
旅游發展也疏遠了鄰里互動。旅游發展擴大了經濟差距,也顯著拉大了居民之間的心理距離,產生道德沖突。農家樂老板表示:“2000年左右每個家庭的經濟狀況都很相似,彼此之間都經常串門走動;旅游業發展提供了新的就業機會,我與鄰居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以至于鄰居并不配合擴大農家樂規模的想法”。
可以看出,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經濟利益逐漸成為影響鄰里關系的重要因素,并引起鄰里關系出現新的變化。旅游經營者之間合作與競爭并存,旅游經營者與未參與旅游發展的居民間關系淡化和不和諧并存,居民間傳統的情感團結有所降低,同時旅游經營者之間建立起新的情感團結。
一般居民對鄰里關系的認知
1.共同觀念:共同體意識增強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67%的居民認為旅游開發前鄰居關系更加緊密和諧;與其他鄰里的關系,54%的居民認為更加緊密,但46%的居民持相反看法,說明總體的鄰里關系在旅游開發區后削弱了。
居民的地方認同明顯提升。旅游業發展后,居民經濟水平得到明顯提高,并且明顯高于周邊地區。因此73%的當地居民有一種自豪感甚至優越感,表現出高度的本地認同感,增強了地方凝聚力。
共同體意識增強。居民間也出現內部競爭甚至惡性競爭現象,但73%的居民認為基本是良性競爭,并未導致人際關系惡化,反而形成了更為緊密的相互合作(63%的調查對象)。“過去村民之間的惡性競爭已經變成了良性競爭,主動維護當地旅游形象和居民之間良好的人際關系,共同努力、合作、互助和共同發展。”
2.共同的行為:鄰里互動利益化
居民個體間的交往行為被經濟化。旅游業發展后,經濟利益成為鄰里互動的重要前提和介質,無償互助的現象越來越少。81%的被調查者認為居民間交往更看重經濟利益。“大部分居民都忙著參與旅游賺錢,如果其他親戚或者鄰居叫自己幫忙時,會要求支付一定的報酬,如果沒有報酬,不會來幫忙的。”居民茶余飯后交流如何掙錢,“以前,居民聚集在一起討論的內容大部分是生產活動與閑話家常方面,而當前居民們聚集在一起討論更多的是如何在旅游發展中做好生意或如何賺更多的錢”。
3.互動程度:陌生感與情感需求
旅游發展促進了社會階層分化,鄰里互動漸趨生疏。旅游開發前,當地的大多數居民以打工或上班為主,居民間經濟收入差別不大,旅游業的發展拉開了收入差距。“部分旅游業經營得相當好的居民旅游旺季年收入可以達到十五萬元以上,而部分經營者的收入才三四萬左右。”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73%的調查對象認為)逐漸成為居民間交往的溝壑,社會交往開始不自然。
外地游客的進入刺激了本地居民對鄰里感情的需求,擴大了居民社會交往范圍。66%的被調查者認為,相比旅游開發前認識的人越來越多,但新結交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出于旅游經營的需求,很少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朋友,還是更看重鄰里關系的真情。這表明,旅游開發增強了本地居民對傳統鄰里關系的情感需求,這對促進鄰里關系的進步有著積極意義。
應用情感團結理論探究旅游發展對老城區鄰里關系的復雜影響,有助于深入理解旅游發展對鄰里關系產生的消極影響,對進一步優化和提升社區共同體建設具有啟示意義。伊犁老城喀贊其民俗旅游區的案例研究表明:旅游發展對旅游地鄰里關系影響是多方面的,重構了鄰里關系的社會經濟背景,改變了傳統鄰里關系的建立基礎,傳統鄰里關系中共同體意識的價值在現代經濟中逐漸凸顯,同時也催生出新的矛盾和問題。具體來看:首先,旅游業的發展增強了居民的經濟意識和地方認同。通過積極參與旅游開發,居民提高了經濟收入和生活質量,增強了地方自豪感和地方認同,逐步樹立了經濟意識和合作意識,外部人際關系的介入則進一步強化了居民經濟共同體意識。其次,鄰里互動的基礎被重構,鄰里關系的親密度也出現下降。旅游開發不斷擴大居民間經濟收入差距,以至于出現搶奪公共資源、社會道德失范等現象,究其原因在于旅游發展機會不平等、發展利益分配不均等。結果是鄰里關系的“人情味”逐漸褪去、包容性降低,鄰里關系親密性整體弱化。再次,傳統鄰里關系逐漸轉變為現代鄰里關系的重要社會資本。盡管經濟利益逐步超越血緣、地緣因素而成為現代鄰里關系建立的重要基礎,然而發展實踐表明,居民在遇到生產資本、生產資料、勞動力短缺等問題時,更多的還是求助于在傳統人際關系中被信任的親戚、朋友和鄰居,并基于業緣結成更緊密的鄰里關系。
總體來看,旅游開發使得喀贊其老城區的鄰里關系呈現“總體弱化但局部更加緊密”的特征,傳統鄰里關系的解體和現代鄰里關系的建立過程相互交織。在新經濟背景下,人際關系的建立基礎逐步呈現“經濟利益+血緣關系+地緣關系(鄰居)”復合的特征,但基于親緣、地緣積累的社會資本仍然對個體經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鄰里關系出現的矛盾和沖突引發對旅游發展的反思。旅游發展需要考慮居民參與旅游發展機會的均等性、社會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以產業發展帶動新鄰里文化的培育,提升居民地方認同水平,也服務于地方的現代化治理。
參考文獻
[1]向天成,趙微.社會交往理論視域下鄉村文化振興的實踐理路[J].貴州民族研究,2020,41(06):42-47.
[2]Shinn M,Toohey S M.Community Contexts of Human Welfare[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3,54(1):427-459.
[3]姜遼,蘇勤,杜宗斌.21世紀以來旅游社會文化影響研究的回顧與反思[J].旅游學刊,2013,28(12):24-33.
[4]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5]Ferguson I.Beyond Power Discourse:Alienation and Social Work[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04,34:297-312.
[6]Ham M V,Manley D.Neighborhood Effects Research at a Crossroads: Ten Challenges for Future Research[J].IZA Discussion Papers,2012, 44(12):2787.
[7]譚日輝.社會空間特性對社會交往的影響——以長沙市為例[J].城市問題,2012(02):59-66.
[8]孫龍,雷弢.北京老城區居民鄰里關系調查分析[J].城市問題,2007,(02):56-59.
[9]Martin K.Tourism as Social Contest:Opposing Local Evaluations of the Tourist Encounter[J].Tourism,Culture & Communication,2008,8(2):59-69.
[10]Gursoy D, Chi C G,Dyer P.Locals' Attitudes toward Mass and Alternative Tourism:The Case of Sunshine Coast,Australia[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0,49(3):381-394.
[11]孫九霞,張士琴.民族旅游社區的社會空間生產研究——以海南三亞回族旅游社區為例[J].民族研究,2015(02):68-77+125.
[12]葉原源,劉玉亭.社區的鄰里性本質:內涵、特征及其實踐意義[J].人文地理,2022,37(03):7-20.
[13]趙玉宗,寇敏,盧松,等.城市旅游紳士化特征及其影響因素——以南京“總統府”周邊地區為例[J].經濟地理,2009,29(08):1391-1396.
[14]呂凱,鄭路.從沖突到合作:旅游發展與當地居民關系的整合——政府引導型社區參與在揚州彩衣街項目的實踐與啟示[J].城市規劃,2014,38(03):78-82.
[15]Woosnam,K.M.Using Emotional Solidarity to Explain ResidentsAttitudes about Tourism and Tourism Development[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2012,51(3):31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