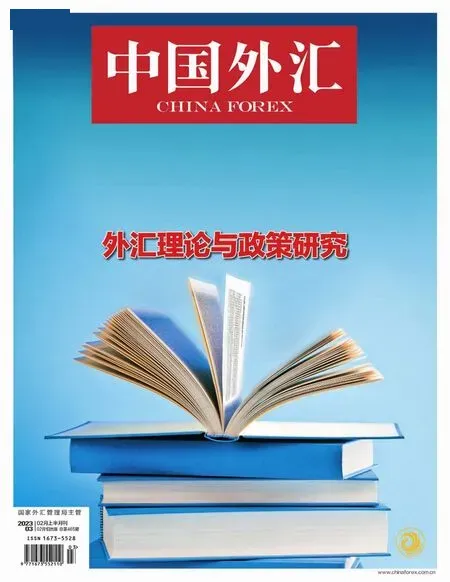人民幣避險能力演變比較分析和實證研究
文/國家外匯管理局山東省分局課題組
一、引言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性、區域性經濟金融危機頻發,匯市、股市、債市、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劇,市場主體風險偏好明顯下降,但美元、日元等主流避險貨幣匯率波幅卻有所增加,引發各方對主流避險貨幣避險能力以及其他貨幣、資產避險屬性的關注。
主權貨幣為國際主流避險貨幣的國家在維護本國經濟金融穩定、保持宏觀政策空間以及維持國際影響力方面具有天然優勢,在當前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地緣政治沖突頻發、中美戰略博弈前景不明朗的新形勢下,全球風險事件規模、頻率、類型和復雜程度或不斷增加。在此背景下,研究人民幣避險能力和避險機制優化方案,對于深化對外開放、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維護我國金融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二、避險資產的概念和特征分析
結合美元、日元、瑞郎、黃金、美債等全球主流避險資產特點,本文從貨幣職能理論出發,從本質屬性、外在表現和影響因素范疇,將避險資產定義為:受政治、經濟、金融等基本面因素支撐,具備安全性、流動性和廣泛接受性,價值相對穩定且與市場避險情緒正相關的一類資產。
(一)貨幣職能理論
貨幣職能是貨幣本質的具體體現,在發達商品經濟條件下,貨幣具有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五大職能。一國貨幣能否成為國際主流避險貨幣,取決于該貨幣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職能的發揮。
從貯藏手段職能看,一國貨幣成為價值形式和社會財富的一般代表,是在危機時期成為國際資產避風港的必要條件。貯藏手段職能主要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國家經濟實力,這是一國貨幣的信用基礎。經濟實力越強,幣值穩定的基礎就越牢固,主權信用風險就越小,貨幣的保值避險功能就越強。二是主權貨幣實力,即幣值穩定性。幣值穩定、通脹率平穩且可預期的貨幣,更有可能被風險厭惡型投資者作為避險資產持有,從深層次看,幣值穩定性取決于一國貨幣政策透明度和跨期可預見性。
從世界貨幣職能看,一國貨幣在計價、流通、支付和價值貯藏中,只有沖破國界范圍,在世界市場發揮作用,為全球市場主體所普遍接受,才有可能成為國際主流避險貨幣。世界貨幣職能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國家貿易實力。一國貿易額在全球商品市場中所占份額越高,該國貿易商的議價能力和交易幣種選擇權就越強,該國貨幣就越有可能作為全球市場上的價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被各國市場主體接受。二是金融市場廣度和深度。一國外匯和資本市場開放程度越高,貨幣和遠期市場工具越完善,該國貨幣匯兌成本和匯兌風險就越低,越容易作為世界貨幣被全球投資者持有。三是貨幣使用慣性。一旦一國貨幣在全球貿易及投資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就會長期保持其市場優勢,市場主體不會輕易更換交易和避險幣種以規避信息搜尋等成本。
(二)避險資產的本質屬性
安全性、流動性和廣泛接受性是避險資產的本質屬性,是避險資產表現出價值穩定性和與避險情緒正相關性的原因所在。唯有具備安全性,才能在危機時期其他資產遭受價值損失的背景下逆勢保值增值,市場主體才愿意在危機時期增持;唯有具備流動性和廣泛接受性,市場主體在做出增持決策時才不會有市場情緒轉變后資產難以拋售的后顧之憂。具體到避險貨幣,安全性由其貯藏手段職能決定;流動性和廣泛接受性則與世界貨幣職能密切相關。
從全球主流避險資產表現看,安全性方面,美元以美國信用為背書,并憑借美國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地位而具備安全性特征,當全球經濟震蕩、需求萎縮時,美元往往是投資者渡過危機的首選,避險屬性突出。瑞士法郎因其發行國具有永久中立國地位,在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尤其是政治局勢動蕩時,成為具有保值性的投資品種。日元發行國具有規模龐大的海外資產,意味著日本經濟不會依賴外部融資,加之大量外匯儲備賦予日本強大的匯率維穩能力,進一步增強了日元的安全性特征和對避險資金的吸引。黃金脫離國家范疇,不以國家信用為背書,無信用風險;且價值穩定,能夠保值增值,在投資組合中加入黃金可有效提高整體投資安全性。美國國債債權人結構穩定,提升了償債可信度,進而提升了美債作為避險資產的吸引力。
流動性和廣泛接受性方面,美元是國際金融貿易中廣泛使用的計價、結算和支付手段,良好的流通性便于美元快速兌換,也使美元更接近其真實價值,從而受到投資者青睞;美國金融市場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全球大多數金融活動都涉及美元使用,使得美元成為國際金融領域中的世界貨幣。瑞士法郎流動性源于瑞士體系完善、歷史悠久、信譽良好的銀行業。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后,瑞士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金融中心,國內經濟發展穩定,銀行業高度發達,金融市場具有足夠廣度和深度,由此確立了瑞士法郎避險貨幣的地位。日本長期維持低通脹和低利率,2016年2月甚至推出負利率政策,使套利交易達到頂峰,國內和國際投資者持有日元興趣高漲,使之具有流動性和廣泛接受性。黃金作為一種天然等價物,具有貨幣和商品雙重屬性,其流動性和廣泛接受性是其貨幣和商品屬性的延伸。在金銀復本位和金本位制下,黃金是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和價值尺度的本位幣,流動性和接受程度最高;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元處于中心地位,黃金避險功能有所弱化。美國國債具有作為全球金融市場定價基準的天然優勢,具備較高流動性和接受度。
(三)避險資產的外在表現
一方面,相較于風險資產,避險資產的價格波動幅度較小,價值相對穩定,為風險厭惡型投資者樂于持有。另一方面,避險資產價格走勢與市場避險情緒正相關。避險情緒高漲時期,資金從風險資產撤出涌向避險資產,推升其價格;避險情緒回落時期,資金回流風險資產,避險資產價格下行。
(四)避險資產的決定因素
避險資產三種本質屬性均由政治、經濟、金融等基本面因素決定。安全性主要取決于發行國信用,進一步取決于發行國經濟基本面、政治穩定性、貨幣政策立場、貿易順差、外債水平和外匯儲備充足程度等。流動性由制度和市場因素共同決定,制度層面主要取決于發行國金融開放和外匯管制程度;市場層面主要取決于該類資產市場廣度、深度以及定價機制(如匯率制度)選擇。資產能否在國際范圍得到廣泛接受,一方面取決于資產安全性和流動性,另一方面取決于市場的歷史交易慣性。
三、人民幣避險能力演變及其與國際主流避險資產的比較
本文對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歷次全球性和區域性危機事件中人民幣表現出的避險屬性進行分析,并與全球主流避險貨幣和避險資產進行比較,主要通過各類貨幣匯率或資產價格與市場恐慌指數VIX走勢之間的關系來分析其避險能力。如VIX指數大幅上升時貨幣幣值或資產價格上升,則認為其具有避險屬性;與VIX指數相關性越高,則其避險能力越強。
(一)全球性危機事件
1.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2007年2月—2010年12月)
全球金融危機以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破產以及2008年9月15日雷曼破產事件為標志,由房地產市場蔓延至信貸市場,進而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
從人民幣避險能力表現看(見圖1),危機初始階段,人民幣小幅升值;隨著危機持續發酵,美元兌人民幣匯率穩定在6.8左右,人民幣因美元表現出避險能力而呈現出一定避險屬性。

圖1 四類貨幣(人民幣、美元、瑞士法郎、日元,下同)在全球危機期間的走勢
從國際主流避險資產表現看(見圖1和圖2),危機初始階段僅在美國境內發酵,導致美元貶值,美元避險能力表現較差;隨著危機蔓延至全球,VIX指數上升,美元避險屬性開始凸顯,美元指數和VIX指數表現出顯著正相關關系。美元兌瑞士法郎匯率自危機伊始至2018年一季度與VIX指數走勢負相關,但后期二者同向變動,說明危機前期瑞士法郎避險能力較強,后期有所弱化。日元在整個危機期間逆勢波動升值,與VIX指數負相關性較強,避險能力突出。黃金價格在危機期間整體上升,但在重要時點有所下降,避險屬性表現不佳。美債收益率(10年期和2年期)在危機期間整體波動下行,階段性走勢與VIX指數負相關,表現出良好的避險能力。

圖2 主流避險資產(黃金、美債,下同)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走勢
2.新冠疫情(2019年12月至今)
新冠疫情于2020年一季度在全球范圍暴發,成為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從人民幣避險能力表現看(見圖3),疫情在全球范圍暴發的初始階段,在VIX指數峰值期,人民幣貶值趨勢明顯。但在危機存續期間,得益于中國有力的抗疫措施,中國經濟率先復蘇,人民幣持續波動升值,表現出良好的避險能力。

圖3 四類貨幣在新冠疫情期間的走勢
從國際主流避險資產表現看(見圖3和圖4),美元在整個危機期間與VIX指數同向波動,依舊是最主要的避險貨幣。瑞士法郎在疫情初期表現出較強的避險能力,但隨著VIX指數的快速上升有所貶值,此后與VIX指數整體反向波動,表現出一定避險屬性。日元在危機期間整體呈現先升值后貶值態勢,說明前期避險屬性突出,后期有所弱化。黃金價格在危機期間整體變化不大,且在VIX指數峰值期出現較小低谷,說明公眾對黃金的避險能力存在擔憂。美債收益率在危機初期與VIX指數反向變化,表現出較強避險能力;在危機存續期間,2年期國債收益率比較穩定,但10年期國債收益率出現階段性上揚,避險屬性有所弱化。

圖4 主流避險資產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走勢
(二)區域性經濟金融危機
歐債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和深化,本質源于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與分化的財政政策帶來的矛盾。危機期間,歐元兌美元匯率一度跌破1.2。
從人民幣避險能力表現看(見圖5),2010年6月匯改重啟后,人民幣持續走強,在VIX指數峰值期多逆勢升值,表現出一定避險屬性。

圖5 四類貨幣在歐債危機期間的走勢
從國際主流避險資產表現看(見圖5和圖6),美元指數與VIX指數整體正相關,表現出較強避險能力。瑞士法郎與VIX指數相關性較低,僅在第一個峰值期表現強勢,避險能力表現整體不明顯,主要由于2011年9月6日瑞士央行宣布瑞郎與歐元掛鉤,影響了瑞郎的避險能力。日元在危機期間升值明顯,且在VIX指數峰值期表現強勢,表現出良好的避險能力。黃金價格危機期間一路飆升,避險能力突出。美債收益率波動下降,與VIX指數整體呈現負相關,表現出較強避險能力。

圖6 主流避險資產在歐債危機期間的走勢
(三)區域性政治事件和突發事件
1.英國脫歐事件(2013年1月—2020年1月)
2013年1月23日,英國時任首相卡梅倫首次提出脫歐公投,英鎊兌美元匯率走低;201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前夕至10月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宣布“硬脫歐”,英鎊兌美元匯率貶值近20%。
從人民幣避險能力表現看(見圖7),脫歐公投期間,人民幣表現出階段性避險屬性。公投伊始(2013年1月—2015年3月),人民幣匯率走勢平穩,但在VIX指數出現峰值時均小幅升值,表現出一定避險能力。公投中期(2015年3月—2017年3月),人民幣在VIX指數上升期貶值,避險屬性弱化。公投后期(2017年3月—2020年1月),VIX指數出現峰值時,人民幣大幅升值,表現出較強避險能力。

圖7 四類貨幣在脫歐公投期間的走勢
從國際主流避險資產表現看(見圖7和圖8),美元指數與VIX指數相關性不大,但在VIX指數峰值期多上升,表現出一定避險能力。瑞士法郎匯率與VIX指數負相關性較強,但波動性較高,避險屬性有所弱化,主要由于脫歐公投沖擊歐元匯率,而瑞士法郎與歐元掛鉤。日元匯率與VIX指數整體負相關,在VIX指數峰值期多升值,表現出較強避險能力。黃金價格相較于脫歐前明顯走低,雖然在VIX指數峰值期有所反彈,但幅度有限,避險能力表現不足。10年期美債收益率與VIX指數顯著負相關,表現出較強避險能力;但2年期美債收益率與VIX指數相關性不明顯,僅在VIX指數部分峰值期下降,避險屬性不夠突出。
飼喂試驗表明,本次試驗所生產山羊顆粒TMR具有很好的適口性,羊愛吃,每次采食時間約1 h,日喂2次,日采食量為0.833~0.889 kg/只,觀察期日平均采食量(0.854±0.031)kg/只。日喂3次,日采食量為0.944~1.0 kg/只,觀察期日平均采食量(0.978±0.031)kg/只。日喂2次,補料2次,采食量為0.944~1 kg/只,觀察期日平均采食量(0.976±0.029)kg/只。

圖8 主流避險資產在脫歐公投期間的走勢
2.中美經貿摩擦(2018年3月—2019年12月)
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對華加征鋼鋁關稅,拉開了中美經貿摩擦序幕。當年7月,中美經貿摩擦全面爆發,并于次年5月加劇,對全球經濟和國際貿易秩序造成嚴重沖擊。
從人民幣避險能力表現看(見圖9),經貿摩擦伊始,人民幣匯率穩定在6.3左右的高位;但于2018年7月全面爆發后波動走貶,相對于美元處于弱勢地位。這是由于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而言并非外部危機事件,人民幣在該事件中未表現出避險屬性。

圖9 四類貨幣在中美經貿摩擦期間的走勢
從國際主流避險資產表現看(見圖9和圖10),美元指數在經貿摩擦期間與VIX指數相關性不明顯,但在VIX指數出現峰值時多上升,表現出一定避險能力。瑞士法郎匯率與VIX指數走勢呈現出一定負相關性,表現出一定避險能力。日元在經貿摩擦爆發伊始波動走貶,但在經貿摩擦全面爆發后表現出階段性避險能力。黃金價格先降后升,但與VIX指數走勢不相關,避險屬性表現不足。10年期和2年期美債收益率均先升后降,在VIX指數峰值期均有所回落,表現出一定避險能力。

圖10 主流避險資產在中美經貿摩擦期間的走勢
(四)人民幣避險能力演變情況總結
從上述現象層面的定性分析看,在歷次全球性和區域性危機事件中,人民幣避險能力整體逐步增強,但尚不穩定,且多數情況下遜于國際主流避險貨幣和避險資產。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起,人民幣避險屬性開始逐步顯現。起初由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保持穩定,因美元具備避險能力而從現象層面表現出一定避險能力,隨著我國金融開放、資本項目可兌換以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逐步推進,人民幣在本質屬性和影響因素層面開始具備避險資產特征,在歐債危機、英國脫歐、新冠疫情等危機事件中呈現出一定階段性避險能力。
四、人民幣避險能力和避險機制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
本文以人民幣兌主要經濟體貨幣匯率收益率為被解釋變量,以各經濟體市場風險因子、政策風險因子、經濟基本面因子、市場干預指標等為解釋變量,對人民幣是否具有避險能力及其與主要貨幣避險能力的比較進行實證研究,構建基本模型:
對于人民幣避險屬性的識別,參考張杰(2019)的做法,通過區分分散與對沖的概念,對貨幣的避險屬性進行強弱區分。即某一資產具有風險分散性表明該資產在一定概率上可以降低風險帶來的損失,某一資產具有風險對沖性表明該資產可以直接彌補風險帶來的損失,后者表現出的避險能力更強。據此,本文將人民幣避險屬性分為無避險屬性、弱避險屬性、強避險屬性三種情形,通過觀察核心解釋變量系數β1符號和顯著性來區分三種情形:如果系數為負且顯著,則人民幣有強避險屬性;如果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則人民幣有弱避險屬性;其他情形下,人民幣無避險屬性。
(二)指標說明
模型中用到的具體指標(見表1)如下:

表1 指標體系一覽表
匯率收益率(be)。選取直接標價法下美元、日元、瑞郎、歐元、英磅兌人民幣匯率作對數差分處理,數據主要來自各經濟體貨幣當局網站及Wind數據庫。
主流資產價格收益率(be1)。該指標為匯率收益率be的替代變量,包括間接標價法下人民幣、日元、瑞郎、歐元、英磅兌美元匯率(bet)、美國十年國債利率(beg)、黃金價格指數(beh)等幾種主流資產價格收益率。數據主要來自英為財情網站及Wind數據庫。
恐慌指數(bv/bv1)。本文選擇VIX指數衡量全球市場風險,同時選取納斯達克100波動匯率指數(bv1)作為bv的替代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時均作對數處理。數據主要來自Wind數據庫。
政策風險指數(bu)。本文選取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EPU指數)作為政治穩定情況的表征,回歸時作對數處理。該指數越大,說明該經濟體當年經濟政策不確定性越高。數據主要來自EPU官方網站。
股票指數(bs)。本文選取各經濟體主要股票指數來衡量貨幣發行國經濟形勢,回歸時作對數處理。數據主要來自Wind數據庫。
GDP增長率(bc)。本文選取GDP季度增長率衡量一國經濟發展基本情況,數據主要來自Wind數據庫。
利差(bi)。本文選取美、日、英、瑞、中五國十年期國債利率及歐盟公債利率,計算上述國家與中國國內利率之間的差額。數據主要來自Wind及CEIC 數據庫。
常態化干預指數(bz)。本文選取外匯占款/外匯儲備作為控制變量,考察人民幣避險屬性是否會受到央行常態化干預的影響。數據主要來自Wind數據庫。
匯率預期(er)。本文參考田拓、馬勇(2013)的做法,選取即期匯率(簡記為SER)和遠期匯率(簡記為FER)的相對值衡量匯率預期水平ER,計算公式為:ER=SER/FER-1。該值較高說明升值預期越強;反之,貶值預期越強。數據主要來自Wind數據庫。
短期跨境資金流動指標(bd)。本文參考世界銀行測算理念和王世華、何帆(2007)做法,采用最常見的間接法對短期跨境資金流動進行測算,指標設定為:bd=外匯儲備增量-FDI增量-貨物貿易收支順差-商業形式存在的服務貿易順差。數據主要來自外匯局網站及國際收支報表。
貨幣政策周期(bp)。本文構造定向降準二元虛擬變量bp,參考郭曄、徐菲、舒中橋(2019)的方法,bp=1表示降準周期(2008年10月—2010年12月與2011年6月之后),bp=0表示提準周期(2008年1月—9月與2010年1月—2011年6月),本次政策發布起至下次政策發布前作為一輪政策周期。
(三)回歸分析
由于貨幣避險能力和匯率變化是一個連續動態的過程,一種貨幣當前的匯率走勢會受其前期匯率變化的影響,當前的避險能力也會受前期避險表現的影響。因此,本文引入被解釋變量的滯后項建立動態面板模型,樣本期選定為2005—2020年。
1.避險屬性整體分析
使用Stata15.0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模型1回歸結果表
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到,lnbv系數為正,即間接標價法下美元匯率收益率和恐慌指數呈正相關關系,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美元是其他5種貨幣的避險貨幣。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和恐慌指數呈負相關關系,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其避險屬性并不明顯,但黃金是顯著的避險資產。此外,各指標滯后變量回歸系數均顯著為負,說明前期資產的正向收益會拉低當期收益,可能與市場在高收益情況下降低未來預期有關。
從回歸結果來看(見表3),lnbv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直接標價法下人民幣匯率收益率與恐慌指數VIX負相關,人民幣在全球范圍內暫不具備風險對沖能力,不是完全的避險貨幣。lnbu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國外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會顯著增強人民幣的避險能力。lnbs系數顯著為負,外國股票市場表現和人民幣匯率收益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當外國經濟發展動力減弱時,其股指收益率下降,人民幣匯率收益上升,人民幣避險能力加強。GDP增長率和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呈負相關關系但并不顯著,說明人民幣無法有效對沖區域經濟風險。控制變量外匯市場常態化干預指標bz系數為負,和人民幣匯率收益率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常態化干預會增強人民幣的避險能力,可能的原因是,一種貨幣的避險能力總是在危機時期得到最好體現,而危機時期常態化干預會穩定市場對人民幣匯率預期,顯著增強避險資金投向人民幣的動力。

表3 模型2回歸結果表
本文使用bv1代替bv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lnbv1系數為正,大于前述lnbv的系數,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其他解釋變量的系數也保持一致且均顯著,說明回歸結果是穩健的。
2.異質性分析
基于模型2,本文進行分幣種的異質性分析,使用Stata15.0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表4 分幣種回歸結果表
分幣種看,瑞郎、歐元匯率收益率對lnbv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68、0.069,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人民幣是瑞郎的避險貨幣,歐元是人民幣的避險貨幣。此外,日元匯率收益率對lnbv的回歸系數為負值,但結果并不顯著,說明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是日元的弱避險貨幣。美元、英鎊的匯率收益率對lnbv的回歸系數為正,結果也不顯著,說明美元、英鎊是人民幣的弱避險貨幣。
3.階段性分析
本節主要選取歐債危機時期人民幣避險屬性表現明顯的2011年以及新冠疫情暴發的2020年作為分析的重要節點。回歸結果顯示,歐債危機時期lnbv系數為-0.14,但并不顯著,說明人民幣在危機時期表現出一定的避險屬性,可以分散風險沖擊,是弱避險貨幣。新冠疫情時期,lnbv系數為-0.14,大于全樣本回歸的lnbv系數-0.069,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人民幣表現出良好的避險屬性,是顯著的避險貨幣。
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角度的回歸結果顯示,2005年匯改后至2008年期間人民幣具有弱避險屬性,一定程度上顯現出改革成效。2008—2010年,由于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保持穩定,具有了強避險屬性。2010—2014年,人民幣無避險屬性,這一階段雖然人民幣處于升值周期,但升值是由中國巨大的外貿順差帶動且升值相對緩慢;從人民幣遠期匯率走勢看,該階段遠期匯率曲線穩定在即期匯率之上,表明市場對人民幣已經形成一致的貶值預期,人民幣或不是避險資金的最優選擇。2015年“8·11”匯改后,人民幣重新恢復弱避險屬性。
4.避險路徑分析
本文參考Boman、Filho、Lam(2013)對日元避險機制的分析角度,從資本流入、貨幣政策預期及匯率預期三個角度分析人民幣的避險機制,分別以匯率預期指標、跨境資金流動指標及貨幣政策周期指標為中介變量進行中介效應分析,建立回歸模型,即:
三步法檢驗結果顯示,當er作為中介變量時,系數c、c1和a的系數為分別為-0.0384、0.0386、0.0154,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系數b為-0.0921,但并不顯著。進一步進行Sobel檢驗,發現檢驗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中介效應占比為0.56,說明危機來臨時,er作為中介變量的效應非常顯著,匯率預期是有效的人民幣避險路徑。當bd作為中介變量時,系數c、c1和b分別為-0.0384、-0.0386、0.0001,且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系數a為-23.813,但并不顯著。進一步進行Sobel檢驗,結果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中介效應占比為0.059,說明危機來臨時,bd作為中介變量的效應顯著,跨境資金流入是有效的人民幣避險路徑,但其中介作用小于匯率預期。當bp作為中介變量時,系數c不顯著,中介效應無效,說明貨幣政策周期不是有效的人民幣避險路徑。
為驗證上述避險機制分析結論的合理性,筆者對三種變量進行調節效應分析。依次在模型中加入匯率預期、跨境資金流動、貨幣政策周期與恐慌指數的交互項,即:
從er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見表5)可以看到,lnbv_er系數為負,且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當經濟危機來臨時,匯率預期會加強人民幣的避險能力。從bd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可以看到,lnbv_bd系數為負,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當危機來臨時,跨境資金流入會顯著提高人民幣收益率,進而提高人民幣避險能力。從er的調節效應回歸結果可以看到,lnbv_bp系數為正,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說明當危機來臨時,寬松的貨幣政策預期會降低人民幣收益率,進而削弱人民幣的避險能力。

表5 調節效應回歸結果表
(四)實證結論
一是人民幣整體看尚不是顯著的避險貨幣,但人民幣是瑞郎的強避險貨幣,是日元的弱避險貨幣,且在歐債危機、新冠疫情等危機時期表現出良好的階段性避險屬性。二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對提高人民幣避險能力有正向促進作用,但避險屬性尚不穩定。三是央行在危機時期對外匯市場的干預非常必要,一定程度可提高人民幣避險能力。四是匯率預期和跨境資金流入是人民幣發揮避險屬性的有效路徑,貨幣政策預期雖不是顯著路徑,但危機時期緊縮的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可提高人民幣避險能力。
五、結論及建議
基于上述定性分析和定量研究,近年來,人民幣避險能力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推進呈上升趨勢,在特定危機事件中或對特定幣種已表現出一定避險屬性;但整體看避險能力尚不及美元、日元、瑞郎等國際主流避險貨幣。未來,應順應上述趨勢,進一步推進人民幣避險能力建設,使我國充分享有避險貨幣發行國優勢;同時,應做好政策儲備,應對人民幣成為主流避險貨幣后的新興風險挑戰。
(一)從避險資產本質屬性入手,推動提升人民幣避險能力
一是依托經濟基本面,優化政策調控管理,提升人民幣安全性。依托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經濟發展格局,充分發揮我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復蘇中的先發優勢,推動經濟增長和產業轉型升級,在國際產業鏈重構中贏得先機,提升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充分發揮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外匯政策的協同效應,確保人民幣匯率和通脹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外貿順差和外債規模在合理區間,進一步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夯實國家信用基礎,從安全性角度提升人民幣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
二是進一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改革,提升人民幣流動性。與美國、日本等國際主流避險貨幣發行國相比,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相對較低。應基于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繼續平穩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大金融開放力度,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
三是提升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接受度。一方面,進一步推進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人民幣計價結算,提升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的接受度和使用慣性。另一方面,通過優化跨境人民幣融資結算產品、強化境外金融服務配套等方式,推動提高人民幣在進出口貿易中的結算比例,提升國外實體企業對人民幣的認可度和使用度。
(二)加強政策儲備,應對新興風險挑戰
主權貨幣成為避險貨幣有利有弊,在推動人民幣避險能力建設的同時,應強化配套政策儲備,以應對新興風險。一是優化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調控機制。通過擴大金融開放、推動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等方式提高人民幣資產流動性,提高人民幣避險能力。進一步完善跨境資金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框架,優化調整現有項目參數設置和調控機制,適時將更多項目納入調控框架。
二是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適應人民幣成為國際主流避險貨幣后匯率波動頻率和幅度加大的新形勢,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充分發揮匯率的自動穩定器作用。極端情形下,可優化匯率報價機制逆周期調節因子使用,及時阻斷極端危機事件下的外匯市場“羊群效應”。
三是強化涉外主體匯率避險意識,優化銀行匯率避險產品和服務體系。一方面,引導涉匯企業樹立匯率風險中性意識,不對賭單邊匯率走勢,及時、足額運用外匯衍生產品對外匯風險敞口進行套保,避免匯率波動對跨境貿易投資業務和財務穩定性造成沖擊。另一方面,引導銀行提高外匯衍生產品普惠程度,針對企業多樣化匯率避險需求,豐富、優化外匯衍生產品體系,為企業提供定制化、個性化匯率避險服務,適度降低產品續作門檻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