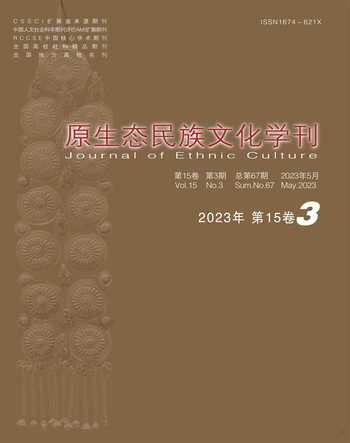生存、生計與生態:黃土高原西部的農業活動與生態保護實踐
李建宗
摘 要:農業是黃土高原西部的主要生計方式,圍繞農業生產開展的相關活動都是為了生存,以土地為中心的生存、生計與生態之間具有密切的關系。黃土高原西部的移民在生存過程中改變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傳統的農業活動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現代社會的生態保護實踐有效實現了水土保持。盡管現代社會的生態問題引發全球的廣泛關注,這是一個無可爭議的話題,然而,現代社會的生態意識在生態保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農業機械的大力推廣和農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改變了農民對土地的利用方式與土地觀念,進一步改善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關鍵詞:生存;生計;生態;農業;黃土高原西部
中圖分類號:C9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3)03 - 0060 - 11
生存、生計與生態是人類社會的重要議題,理解生存、生計與生態之間的關系對于當代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生存是人類直接面對的一個問題,為了生存,人類選擇了從自然界獲取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于是出現了生計,生計方式的選擇就是人類適應生態環境的結果。為了生存與發展,人類從自然界獲取生產生活資料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最終形成了生存智慧與生態知識,又運用生態知識來指導生產實踐。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積淀了豐富的農業生態常識,當然還有一些生態的規律被人們忽視,甚至民眾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違背了生態規律。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環境本來脆弱,隨著人口增長與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當地民眾的生計方式影響了生態系統。在國家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民眾采取了相應的生態保護措施,生態保護實踐與現代農業使黃土高原西部的生計方式發生了變遷,當地的生態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黃土高原是一個地理范疇,是中國北方地區的一個較大的地理區域,其介于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關中平原、華北平原之間。關于黃土高原的范疇,史念海進行過界定:“黃土高原是范圍相當廣大的地區。它南依秦嶺,北抵陰山,西至烏鞘嶺,東抵太行山,有今山西全省和陜甘兩省的大部,兼有寧夏回族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甚至還涉及青海省東部和河南省西北部一隅之地。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說法,乃是其北僅止于橫山之北陜蒙兩省區交界之處,不包括鄂爾多斯高原和河套平原,當然也就不能止于陰山山脈之下。”1就整個黃河流域而言,黃土高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地處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一直影響著整個黃河流域。黃土高原遍布著溪澗小河,如果把黃河比作流域大動脈的話,這些溪澗小河就猶如毛細血管,匯入一些較大的河流,比如湟水、洮河、祖厲河、涇河、渭河、汾河等,進而形成黃河的重要支流。進入每年的雨季,雨水沖刷著黃土高原的地表,挾帶大量黃土流入黃河支流,最后匯入黃河干流,使河水顏色泛黃。黃土高原的地表黃土決定了黃河的顏色,也就是說,黃土高原賦予了黃河之名。在人類文明史上,黃土高原是人類活動比較早的區域,有很多考古遺跡證明了這一點。何炳棣指出:“我國遠古文化的核心區或搖籃區是黃土高原的中南和東南部,即今日陜西渭河流域、山西汾河流域和河南的西部。”2郭永平倡導人類學的黃土文明研究,3黃河文明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黃土高原文明對黃河文明起到了形塑作用,在黃河文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研究黃河文明的過程中,黃土文明是繞不過去的一個話題。
長期以來,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是影響黃河治理的一大難題,黃土高原西部尤為嚴重,這里正好位于黃河中游地段。岑仲勉指出:“黃河挾帶著大量的泥沙,結果必令河床一天一天淤高,兩岸的居民就好像筑垣居水,是再沒有更危險的事,所以從長期治黃著想,應該怎樣消弭或處理泥沙又是最突出最嚴重的問題。”4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帶,坡地的地表土質疏松。從坡地上沖刷下來的黃土進入河谷地帶之后,一部分附著于河谷地表,一部分淤積在河床,使河床不斷抬升,這就是黃土高原西部河谷地帶適宜農業生產的主要原因。攜帶黃土的黃河干支流進入下游平原之后,在灌溉過程中黃土進入農地,增加了土地的肥力。一方面,黃河水道中的大量黃土沉積于下游河床,使河床不斷上升,以致在下游出現“黃泛區”。歷史上黃河下游的水災頻繁發生,嚴重影響了華北平原部分地區民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治理黃河也成了不同時期國家和地方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另一方面,地處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促進了下游平原地區的農業發展。黃土高原丘陵地帶的農民精心耕耘著自己開發的土地,為坡地的土壤改良付出了大量的勞動。他們好不容易在黃土表層培育了一層適于農作物生長,具有營養價值的“肥土”,不料在每年雨季被雨水沖刷到坡下,嚴重影響了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帶的農業生產。部分黃土進入黃河之中,對黃河下游民眾的安全形成威脅。因此,就黃河流域的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而言,黃土高原是一個重點區域,尤其是黃土高原西部地區。
一、生存理性驅使的移民開發與環境變遷
在黃土高原的東部是華北平原,南面是關中平原。平原地區的自然條件好,人口密集度高,歷史上在當地興起了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市,是北方農業社會的經濟、文化核心區域。在平原地區出現了大量具有一定人口規模的市鎮和村落,其中一些市鎮充當了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在商業貿易過程中,新的文化事項首先進入平原地區的大城市和重要市鎮,然后在此基礎上不斷向周邊的村落擴散和傳播。在平原地區也出現了一些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它們既是平原地區的人口密集地區,也是北方的重要文化基地。從明清時期開始,華北平原和關中地區的人口呈現爆發式增長,加之土地集中進程的加快,人口與土地資源之間越發呈現緊張的局勢。平原人口密集區一旦進入社會發展的“非常時期”,比如出現自然災害、社會戰爭以及由此造成的個體家庭變故,這都會引發部分群體或者個體的生存問題。面對社會困境與生存危機,部分民眾做出離開自己故土的選擇,他們開始充當流民。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區,這些流民難以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他們只能選擇走向條件較差的平原邊緣——黃土高原。明清以來北方地區移民社會的基本流向為西向、北向或者西北向、東北向,其中黃土高原是一個重要的流出地。安介生在山西移民史研究過程中指出,光緒四年(1878年)發生的“丁戊奇荒”使山西人口銳減,山西官府實行墾荒政策,招徠大量“客民”進入黃土高原。1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黃土高原出現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其中有些是官府組織的,有些是民眾自發進行的,這自然改變了黃土高原的生態環境。盡管黃土高原的耕作條件并非理想,但在特定歷史時期對于周邊地區的民眾來說還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土地是民眾賴以生存的基礎,黃土高原具有大量的土地資源,在生存理性的主導下,周邊平原地區的很多無地或少地民眾來到黃土高原從事農業生產。
歷史上的關中平原是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人口聚居區,這里地勢平坦,有很好的水利灌溉設施,具備適于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由于關中地區曾經是西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人口的過度增長也為關中平原的人 - 地關系帶來一定的影響,使歷史上的人 - 地關系出現了周期性的平衡與失衡。饑荒既是社會災難,又是改變區域生態的動力,饑民為了生存往往逃出自己的居住地,進入周邊地區。戰爭也是影響人口與生態的重要因素,因為戰爭引發了廣泛的社會流動。“丁戊奇荒”波及山西、河南、陜西等省,關中地區肯定不會幸免。從同治元年(1862年)開始的戰亂對關中地區的人口產生了重創,導致部分民眾進入六盤山附近的地區,即當下甘肅省平涼市的東部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的西(吉)海(原)固(原)一帶。面對自然和社會災害,在關中地區出現了一股移民潮,他們為了尋求生路逃出自己的居住地。這些來自關中平原的移民,大量進入黃土高原的丘陵地帶。關中地區的民眾在向外流動過程中,黃土高原西部是一個重要的流向區域。這些移民首先進入黃土高原西部的河谷地帶,后來河谷地帶人口密集,難以容納大量的外來人口。于是后來的移民只能進駐丘陵地帶,在丘陵的坡地上開發土地,從事農業生產。
侯仁之指出:“我們如果以突起在黃土高原上的呂梁山和六盤山為界,自東向西可以分作山西高原、陜北高原和隴中高原。”2這既是黃土高原的三個基本地理單元,即黃土高原的東部、中部、西部,也與行政區域劃分密切關聯。李學會對黃土高原板塊的劃分與前面基本一致,并指出隴西盆地(隴中高原)的黃河水系主要有黃河干流以及大夏河、洮河、湟水、祖厲河、清水河、渭河等重要支流。1黃土高原西部主要分布在甘肅省中部地區,當然還包括青海省東部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南部的部分地區。1928年,寧夏和青海設省,從原甘肅省劃分出去。因此,黃土高原西部在地理上稱為隴中高原或隴西盆地。黃土高原西部屬于丘陵地帶,在河谷地帶形成了一些面積大小不等的平地。一般情況下,河谷地帶的海拔相對低,有比較好的耕作條件,有些地方用水灌溉,居民飲水相對方便,適于人類生存。根據路偉東的統計,清朝后期甘肅省秦安縣的縣城人口規模僅次于甘肅省城蘭州。2秦安縣城位于渭河流域的河谷地帶,與其相鄰的秦州(今天水市秦州區和麥積區)的平原面積稍大一些,離關中地區更近。秦州的耕作條件也更好,人口稠密,當時對于外來人口的容納空間極為有限。從關中地區西北方向走出的移民,只能沿著渭河流域的河谷地帶向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前行,首先來到甘肅省的秦安縣,然后走向通渭縣、甘谷縣、武山縣、隴西縣等地,甚至進入洮岷走廊和河湟走廊。筆者在通渭縣馬營鎮的調查過程中發現,在當地曾經有影響的望族——魏姓家族的家譜中記載,魏氏家族來自陜西省富平縣。此外,還有一個方向是沿著涇河流域的河谷地帶進入六盤山附近和寧夏南部的丘陵地帶。
在1928—1930年期間,我國北方地區由旱災引發了大饑荒,其中1929年陜西大饑荒的影響之大,死亡人數之多是有史以來少有的。3曾經有一段時間,“民國十八年(1929年)大饑荒”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結構,影響了黃土高原的生態,“民國十八年”在黃土高原西部形成了一種集體記憶。在這次大饑荒中,由于糧食極度緊缺,在黃土高原西部很多地方興起了一股以土地換糧食的風潮,由于當時的糧價過高,自然形成了不平等交換。災荒結束之后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數地主和富戶手里,大部分農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在此之前,甘肅省會寧縣南部山區有大片草原,周邊農區村落的民眾在此放牧。災荒之后,因失去土地而急于尋求生存資源的民眾發現了這一地帶,于是甘肅莊浪縣、秦安縣、通渭縣等地的失地農民向會寧縣南部山區進行大量移民,開荒種地,從事農業生產。在這一波移民浪潮中,大量的草原被開發成農地,這自然改變了當地的生態環境。最早進入會寧縣南部山區的一波移民占有地勢比較低,坡度相對緩和的土地。隨著移民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加,后來者占有的土地質量逐漸下降,聚落地勢也明顯上升。黃土高原西部的一些地區本來不適宜從事農業生產,地處六盤山以西的華家嶺山脈大部分地區海拔在1 800米以上,明清時期是官方的牧馬場,在山麓的安定監(今通渭縣馬營鎮)設有“馬政”機構苑馬寺。《靜寧州志》記載:“康熙三年裁前明苑馬寺之安定監,凡六營并置靜寧。”4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大量移民的出現,黃土高原西部的一些區域從牧場轉變為農地,相應地,當地的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移民社會不僅改變了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環境,還嚴重影響了黃河下游地區。正如杜娟在分析人口對黃土高原生態的影響時指出:“歷史上黃土高原的開墾棄墾、亂砍濫伐已致使這里千溝萬壑的地形地貌更加支離破碎。近代以來的人口激增,社會動蕩,不合理的土地利用過程使水土流失加劇,嚴重危害黃河中下游流域的社會經濟發展。”1
當大量移民不斷進入黃土高原西部的丘陵地帶時,在生存理性的驅使下,他們會從自然界獲取所需要的生產生活資料。自然環境對人口的承載能力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像黃土高原西部這樣的脆弱環境,人 - 地之間的關系一旦失衡,將會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黃土高原的人們長期以來都是以農業為本,因而在相同條件下人口密度可以反映人類對水土流失的影響程度。在相同條件下,人口密度越大,對水土流失的影響就越大”2。在大多數情況下,移民以自己原有的社會網絡為基礎,主要包括親屬和朋友網絡,招引更多的移民進入新的區域。在大量移民進入之前,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帶本為植被覆蓋區。移民進入之后,丘陵地帶的大量荒地變成了農田。隨著移民區域人口數量的增加和聚落規模的擴大,大量荒坡地變成農地。在此過程中,原有的草地植被系統遭到破壞,導致水土流失嚴重。王晗指出:“開荒擴種和植被破壞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開荒面積的增加與人口增長趨勢有共軛性。開荒的地形部位和區域分異隨自然和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有所不同。”3由此發現,大規模的移民開荒種地,其實就是改變當地生態環境的過程。隨著移民數量的不斷增加,當地的土地開發面積也就相應地擴大。大面積的草原變成耕地之后,原有的草地植被遭到破壞,坡地上的地表黃土在雨季被流水沖走,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
二、傳統生計方式與水土流失
黃土高原西部大部分屬于典型的農耕地帶,隨著人口數量的增加,農地面積也在不斷擴大。丘陵是黃土高原西部的主要地形,耕地大部分為坡地。黃土高原西部的雨季沒有明確的時間,不同年份的延續時間也有所不同。在雨季來臨之后,黃土高原西部坡地地表的大量黃土被雨水沖走,嚴重影響了耕地的肥力。黃土高原西部本來長期干旱少雨,與平地相比較,坡地又不保墑,土壤水分容易蒸發,這就是人們常說的貧瘠的黃土地。土壤的質量決定著耕地的產量,進而影響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和質量。由于黃土高原西部土地的貧瘠,大部分區域的人均耕地面積不小,但糧食產量普遍不高,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影響著當地民眾的生存,“隴中貧瘠甲天下”就是黃土高原西部真實的歷史寫照。
雖然黃土高原西部的山地貧瘠,但當地民眾在農業生產過程中還是精耕細作,嚴格按照農業生產的程序進行。在夏秋季節,每當農作物收割完畢,馬上就開始犁地。在這種情況下,一旦遇到大雨,犁得松軟的土壤就被沖下坡地。休耕是黃土高原西部的一種耕作方式,當年選擇一塊耕地,不再進行農作物種植,一年之內要進行2—3次深耕,當地人稱為“圃地”。這些犁得松軟的耕地,大量的地表土壤在雨季自然會被沖走。在農作物種植方面,黃土高原西部的坡地與河谷地帶的平地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在河谷地帶的平地上,因為土地的肥力既好又保墑,農作物的種植密度大。而坡地正好相反,農作物植株之間的距離要大一些,由此坡地農作物固定土壤的能力較弱。在黃土高原西部的丘陵地帶,部分丘陵的海拔比較高,坡度大、風力也強,不適于從事農業生產,在部分丘陵頂部出現了一些荒地。由于山頂荒地的植被長勢比較好,有效防止了這一地區的水土流失。然而,過去在當地的農業生產過程中,為了給農地施肥,便在這些荒地上出現了“燒生灰”現象。人們用鐵鍬挖起荒地地表的植被,曬干之后壘起來,再用柴火燒烤一段時間,挖出的地表植被就被燒成“生灰”,然后作為肥料運送到附近的農地里。在黃土高原西部傳統社會的農業活動中,高海拔丘陵地帶的“燒生灰”活動是當地民眾農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其嚴重破壞了地表植被,造成了大量水土流失。
雖然黃土高原西部以農耕為主,但畜牧也是一種生計方式,是農耕生產的重要補充。耕畜是開展農業活動的前提和保證,人們通常把耕畜稱為“農本”,意味著耕畜在農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傳統社會,黃土高原西部每個家庭的耕畜數量為1 - 2頭,主要有毛驢、黃牛、騾子、馬等。到了每年的夏季,放牧牲口與割草是農民的一項重要活動。為了讓耕畜能夠吃上青草而上膘,以便在秋收之后進行犁地,農民非常注重耕畜的放養。黃土高原西部的牲口放牧形式與草原地區完全不同,由于放牧空間有限,主要在田間地埂和路邊放養牲口,有時候也會在小塊的荒地上放牧。在耕畜放牧過程中,每人負責1 - 2頭耕畜,從每年的夏季一直延續到秋季。一般情況下,一塊耕地的農作物收割之后要立即犁地,犁地活動在上午進行,犁地結束之后要給耕畜喂上青草。由此,在傳統社會很多放牧耕畜的民眾還有割草的任務。黃土高原西部的夏、秋兩季是雨季,原本不在農作物種植區域的植被,起到固定地表土壤的作用,但放牧耕畜和割草活動影響了這些區域的植被,進而造成了水土流失。正如楊庭碩、呂永鋒指出:“固定農田耕作的主要目的是確保農作物的增產,在無意中卻忽略了當地水土資源的另一種利用可能——牲畜的飼養,從而導致了地表覆蓋率的下降。”1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帶出現了一些砂質(石質)的山坡,這些坡地無法耕種,砂質(石質)的地表有一定的硬度,實現了水土保持。在傳統農業社會,山羊和綿羊是黃土高原西部放牧的家畜,陡峭的砂質(石質)荒坡成了放牧山羊和綿羊的草場,這自然影響了當地的植被,特別是山羊對于草場的破壞更為嚴重。
柴薪作為傳統社會的主要燃料,主要用于廚炊和燒炕。黃土高原西部農作物的秸稈是主要的柴薪類型,但農作物的秸稈又是耕畜的基本飼草,在保證耕畜飼草的前提下,作為燃料的柴薪不太充足。在這種情況下,當地農民所需要的部分柴薪還需要從自然界獲取,用自然界的部分野生植物充當柴薪。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有很多無地或失地農民,他們日常生活所需的柴薪全部來自山野。在燃料資源稀缺的年代,拾柴是黃土高原西部民眾的日常勞動。當地民眾夏季割青草,甚至把一些植物連根拔除,曬干之后作為燃料;冬季在生長植被的荒地、地埂、路邊等區域,農民用耙子把植被的枯葉收拾在一起背回家中,用于日常炊飲的燃料。在春季的拾柴過程中,農民把地表的草皮挖起來,然后把草根和土壤進行分離,把草根曬干之后當作燃料使用。這種拾柴的方式對植被的破壞和水土流失的嚴重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土炕是黃土高原西部農村的主要取暖設施,填炕的燃料也經常處于不足狀態,冬季的“鏟填炕”也是當地民眾的一項勞動,他們把荒地、地埂、路邊等區域的植被連根用鐵鍬鏟出來,地表的一層營養土連同植被的根和葉曬干之后就成為填炕的燃料。20世紀50年代之前,在縣城與市鎮的部分民眾不進行農業生產,他們做飯和填炕的燃料主要來源于周邊農業生產區的民眾。于是有些農民把從自然界獲取的柴薪或者填炕的燃料賣給附近的市民,以便維持生活。猶如在林木資源豐富地區的樵夫,拾柴火和“鏟填炕”也就成為部分民眾的一種生計方式。日本學者相原佳子在研究東南地區的山野資源利用時指出:“山野不僅為附近的居民提供生活資源,還可以成為外來人進入并賺錢的地方,更是窮人靠‘樵采度日等方式生活的地方。站在外來人和窮人的立場來說,山野具有一種提供保護傘的功能。”1在黃土高原西部的傳統社會,從自然界獲取當地老百姓所需要的燃料是一種常態化的生產勞動,而此舉對于植被的破壞以及水土流失的影響是他們根本沒有意識到的。
采集與狩獵在人類社會延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即便進入20世紀之后,采集與狩獵還在部分山地區域廣泛流行。黃土高原西部地形多樣,丘陵地區的農地面積遠遠大于荒地。在荒地、地埂、路邊等區域生長的一些野生植物具有藥用價值,屬于中藥材,主要有白刺、柴胡、青艽、冬花、大黃等。這些作為藥材的植物能為民眾帶來經濟效益,在當地也出現了收購藥材的市場。在經濟理性的驅動下,黃土高原西部出現了采挖藥材的群體,對大量藥用植物的采挖嚴重破壞了植被,相應地造成了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歷史上的狩獵也是黃土高原西部的一項重要活動,在食物匱乏的年代,獵物是人們食物的重要補充,同時也是獵人群體的主要經濟收入。過去每當進入冬季,狩獵活動便開始流行。黃土高原西部的獵手可以分為業余獵手與專職獵手兩種類型,專職獵手具有一定的狩獵經驗和較高的狩獵水平。對于專職獵手來說,當地的獵物主要有野雞、野兔、狐貍、狼等。歷史上狐貍皮作為皮衣制作的原料,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當地認為“三九天”的狐貍皮最好,經常在寒冷的冬天出動狩獵狐貍。每年冬天的狩獵活動使數量不少的野生動物消失,狩獵導致的動物種群和數量變化勢必會影響當地的生態系統。
生態環境決定當地民眾的生計方式,生計方式反過來又影響著生態環境。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帶的坡地,氣候干旱,農民無法開展集約農業,農作物的產量普遍低。正如史念海指出:“黃土高原上的廣種薄收、粗放經營是有深遠歷史淵源的。”2土地是農民維持生計的基礎,盡管黃土高原西部的農地質量不是太高,但當地民眾還是盡力耕作,努力提高農作物的產量。在從事農業生產的過程中,當地民眾的深耕和休耕、特殊肥料制作(燒生灰)等都是為了提高糧食產量,以便更好地生存。對于傳統社會的民眾來說,他們誰也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生計方式有什么問題,更不會認為他們的農業生產及其相關活動影響了生態。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也是農民財富的標志。長期以來,農民非常注重土地的積累,為了增加土地的面積盡力開墾荒地。在傳統土地觀念的支配下,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帶的大部分地區被開發成農地。過去黃土高原的生產生活資料一直處于匱乏狀態,當地民眾不斷從自然界獲取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與燃料。黃土高原西部的動植物成了民眾的生產生活資料,在人口數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生物種群出現了一個不斷退化的過程。植被是黃土高原維持生態平衡最為重要的因素,起到固定地表土壤的作用。在生產過程中人們對植被的破壞導致了黃土高原西部的水土流失,嚴重影響了當地和黃河下游的生態環境。
三、現代農業生產與生態保護實踐
進入現代社會之后,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們對土地開發的能力也在不斷加強。20世紀50年代之后,為了提高黃土高原民眾的生活水平,促進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在國家農業開發政策的主導下,黃土高原西部出現過幾次大規模的農業開發。與此同時,在國家層面已經制定和出臺相關的生態保護政策,不斷加強生態保護實踐,實施生態文明建設工程。20世紀50—70年代,在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組與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集體化的特征,這為大規模從事農業開發與農田水利建設創造了條件。1956年鄧子恢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指出:“我們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途徑,只能在現有土地上采取各種增產措施來擴大復種指數,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同時在可能條件下盡可能開墾一些荒地,以擴大耕地面積,這就是當前我們農業增產的基本方向。”1進入20世紀50年代之后,由于農業開發能力的提高和集體化的便利,在黃土高原西部組織民眾進行了一定規模的荒地開墾。然而,集體化時期的農業開發與生態保護是同步進行的。在全國農田水利建設的大背景下,黃土高原西部的梯田建設是重點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初具規模的梯田對于黃土高原的生態保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自國家組織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以來,在耕作條件不好的坡地上種樹種草,固定植被,實現了水土保持。21世紀以來,隨著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和推廣,絕大部分的坡地基本梯田化,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環境進一步優化。
從1950年代開始的農田水利建設工程到現在已延續了半個多世紀,這一工程在國家政策的主導下進行,梯田建設是黃土高原農田水利建設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黃河流域黃土高原地區總面積64萬km2,其中水土流失面積45.4km2,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生態環境最脆弱的地區,同時也是我國率先開展大規模水土流失治理活動的地區,多年來,創造了許多好的經驗,取得顯著的成效”2。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一些失地或無地農民在黃土高原西部較陡的山坡上開發了一些小塊農地,就是梯田的雛形。20世紀50—70年代,黃土高原的梯田建設是農業生產隊的一項重要任務。集體化時期的梯田建設主要在冬季進行,秋收結束之后,由農業生產隊組織分流農民,中老年人留在村里打場,年輕人上地修建梯田。梯田建設以農業生產隊為單位進行,每個生產隊都有梯田建設點,每年在各自的點上進行梯田建設,集體化時代黃土高原西部的梯田修建取得了顯著的成績。20世紀80、90年代,黃土高原西部的梯田建設仍然在有組織地進行,但修建規模與之前無法相比。進入21世紀之后,推土機、挖掘機等大型農業機械開始廣泛用于農業開發,黃土高原西部興起了新一輪的梯田建設,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之內,幾乎所有的坡地變成了梯田。羅興佐指出,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農田水利政策經歷了農業生產取向、農民負擔取向、市場化與自治化取向、糧食安全取向等幾個階段的變遷。1梯田作為農田水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顯然有著不同的實踐形式。梯田建設既實現了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保護,又部分地改善了當地民眾的生活,是一項利國利民的重大工程。郝平在分析黃土高原東部山西省柳林縣的梯田建設時指出:“梯田作為‘高產農田,在水土流失治理過程中逐步實現了與糧食生產間的良性循環,成為黃土高原丘陵溝壑區重要的水土保持實踐方式。”2梯田不僅加強了水土保持,還實現了糧食高產,梯田的這些效應同樣在黃土高原西部有所呈現。在當下看來,梯田已經成為黃土高原西部的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從1999年開始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黃土高原西部是最早實施這項工程的地區之一。由于黃土高原西部的一些山地坡度較陡,農作物產量本身就低,有些農民早就放棄這些坡地的耕作,使其成為荒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當地農民在黃土高原西部丘陵地帶坡地的耕作上花費了一番功夫,經過長時間的耕作發現,山頂坡地農作物的長勢不好,植被固定土壤的能力弱,水土流失嚴重。在退耕還林還草工程實施過程中,政府組織民眾在海拔相對高、坡度陡、不太適宜耕作的丘陵頂部種樹種草,為享有土地使用權的農民發放足額補貼。對于農民來說,他們獲得的補貼高于種植糧食獲得的經濟效益,而且還不需要在這些土地上付出勞動,這當然是他們樂意接受的。退耕還林還草工程既是一項惠民工程,也是一項重大的生態保護工程。通過退耕還林還草工程,黃土高原西部丘陵頂部坡地的植被逐漸茂密,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當然,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的有效實施,還與當地農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有很大關系。進入21世紀以來,黃土高原西部的農民有經濟條件購買自己需要的燃料(比如煤炭等),甚至有些家庭開始使用燃氣灶。隨著現代化農業器械的推廣和普及,原先從事農業生產所需的耕畜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就不為自家日常生活所用的燃料和家畜飼料而操心,也就不再去拾柴或者割草,田間地埂的植被長勢比以前有了明顯的好轉,黃土高原西部的丘陵地帶的防護林和草山得到較好的保護。在農產品市場化的過程中,農民開展產業結構調整,黃土高原西部的農民開始在自家的農地上種植經濟林,比如甘肅省秦安縣的桃樹林、靜寧縣的蘋果樹林,很多地方還在農地上種植苗木,以便更好地實現農地的經濟效益。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實現了水土保持,也是一種變相的生態保護。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民涌進城市,農村出現了嚴重的土地撂荒現象,對于糧食安全來說,這雖然是一個重要問題,但暫時有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盡管以上活動只是當地民眾出于經濟理性的選擇,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屬于生態實踐活動。黃土高原西部的農業生產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遷,這就勢必影響當地的生態環境。如果在政府層面出臺生態保護政策,民眾也不在乎對生態有益還是有害,他們只是對經濟理性的追逐而已。
在歷史上民眾沒有明確的生態保護意識,生態保護措施也難以落實。李榮華指出,清朝政府在治理黃河的過程中,為了確保運河安全,重點關注黃河下游。1民國時期黃土高原部分地區出現了生態保護實踐活動,但成效并不顯著。20世紀50年代之后,在國家層面組織開展黃土高原的生態保護,大規模進行植樹造林和農田水利建設,在生態保護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在當下看來,地處黃河中游的黃土高原對于黃河下游平原地區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歷史上黃河下游的洪水泛濫與水患災害的發生都與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有著必然的關聯,尤其是黃土高原西部地區。就像葛劍雄指出:“黃河中游每年要流失那么多的泥沙,黃土高原的面貌必定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下游河道和洪水流經的地區又要淤積那么多的泥沙,不僅下游的干流河道成為懸河,還使華北平原上曾經泛濫到的地區面目全非。”2這就意味著治理黃河下游的水患就必須重視黃河中游的水土流失,做好黃土高原的生態保護。
在現代農業生產過程中,黃土高原西部的農業開發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方面,大規模的土地開發影響了當地的生態,對當地植被形成了一定的破壞;另一方面,在國家和地方層面有了明確的生態保護意識,不斷加強生態保護實踐。不同時期國家出臺了相關生態保護政策并在黃土高原西部大力推廣,對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產生了非常顯著的影響,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保護實踐為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工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是由國家力量推動和各級地方政府組織的,廣大民眾集體參與的,長時段的一項生態保護工程。現代農業生產改變了傳統的耕作方式,同時影響了生態環境。在現代農業發展過程中,農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農村現代化隨之發生,這就改變了農民傳統的生計與生活方式。現代農業生產告別了傳統的農耕方式,在實現農業生產轉型的過程中改變了生態環境,比如黃土高原西部大面積的地膜種植雖然帶來了新的環境污染,但在防止水土流失方面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現代農業也改變了傳統社會農民與土地的關系,農民不再無限制地從土地上獲取自己的生存資源,實際上變相地改善了生態環境。黃土高原西部最大的生態問題是水土流失,最好的生態實踐就是開展水土保持。無論是國家層面的生態保護實踐還是當地民眾的自主選擇,在當代實現了最大限度的生態保護實踐。
四、結論與討論
生態就是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呈現,自然環境為人類提供了生存資源,在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人類在不斷地改造自然,自然也長期反作用于人類社會。由于生存的需要,人類社會的生計方式與自然環境要發生關聯。人類通過特定的生計方式從自然界獲取生存資源,這又勢必影響生態環境。由此,生存、生計與生態是與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緊密關聯的話題。歷史上平原地區的民眾為生存所迫來到黃土高原開展農業生產活動,隨著黃土高原河谷地帶人口的劇增,外來移民進入丘陵地帶開發農地并形成聚落。黃土高原坡地的開發意味著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黃土高原西部地區傳統社會的生計方式長期影響著生態,在農業生產及獲取燃料和飼料過程中破壞了植被,農業及其相關活動造成了大量的水土流失。傳統社會的民眾也沒有明確的生態意識,他們把生存放在首位,生計就是維持生存的基本方式,他們的生計自然要以影響生態為代價。進入現代社會之后,人類在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出現了生態觀念和生態意識。于是在國家和地方政府的組織下開展生態保護實踐,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國家主導和民眾集體參與的生態保護實踐與生態文明建設,不斷實現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性互惠。這不僅為黃土高原西部的農業生產奠定了基礎,也為黃河下游的社會發展提供了保障。盡管在現代社會全球生態是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但人類普遍的生態保護意識是在現代社會語境中產生的,并付諸生態保護實踐,有效遏制生態環境惡化。
流域是人類社會共同體的一種形式,河流上游的人類活動總會影響下游地區。一旦黃土高原西部的植被遭到破壞,就會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對黃河下游產生嚴重的影響。由于周邊平原地區與河谷地帶有限的生存空間,大量民眾只能進入黃土高原西部的坡地。曾經有一段時間,黃土高原西部的民眾首先考慮的是生存問題,無法顧及生態環境,更不會關注黃河下游地區的水患災害。范可指出:“生態文明因此是一種人與自然互惠平衡的狀態,而努力實現這種平衡過程中的創新與發明構成了生態文明的具體內涵。”1現代社會改進了人類社會的生計方式,催生了先進的生態保護實踐理念,推進了生態文明建設。一方面,城市化促使農民不再過分倚重土地,大量農地撂荒;另一方面,現代化的農業器械的普及,便于開展大規模的梯田建設,這兩個方面有效改變了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長時間的國家生態政策與民眾集體生態實踐從根本上保證了生態保護的功效,在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實現了生態好轉。然而,有一個悖論是生態保護與人類的生存、生計孰先孰后。在糧食安全的背景下怎樣重新認識黃土高原西部的生態,如何實現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相結合,這也是今后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責任編輯:羅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