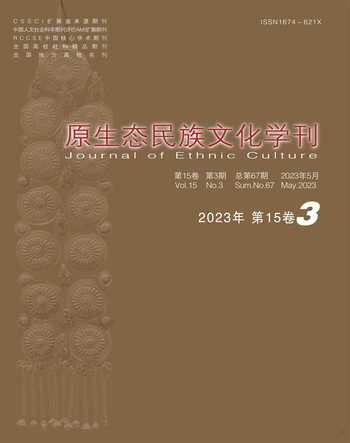低價管制:清前期廣西土司地區的食鹽運銷制度
陳海立


摘 要:清初兩廣鹽政在廣西土司地區推行的食鹽運銷制度是“管制型市場經濟”的典型例證。有清以來,廣西土司地區原不行官引,民間以“瀝灰/酸糟法”代鹽,此時也并存著由水客體系供應的價格較為昂貴的食鹽。自雍正以來,鄂爾泰、郝玉麟提出了在土司地區進行低價鹽供應的設想,并在鄂彌達余鹽改革中予以落地,形成了“余鹽府銷”的特殊制度。該制度一方面實現了低價供應,創設了管制型的市場,另一方面也需要與鹽法中其他運銷制度相協調,以避免制度內在的矛盾。直至乾隆年間,該制度才趨于穩定,最終形成府運與商運結合供鹽的格局。
關鍵詞:廣西土司;食鹽運銷;兩廣鹽政;管制經濟
中圖分類號:C9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 - 621X(2023)03 - 0083 - 12
清代鹽法,長期被學界視為國家擷取賦稅資源的制度。國家通過專賣制度,控制了食鹽的生產與流通諸多環節,并從中獲取了高額的賦稅1。近年來,市場機制在鹽法運作中的作用被逐步發掘出來2。黃國信把明清的食鹽貿易稱之為“體現市場導向價值的再分配型市場”3。以上論斷均隱含了一個“斯密式”的假設,即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市場上存在著競爭性的價格體制,而國家的在場扭曲或者改變了該價格體制。這是把國家和市場對立分析的結果。
事實上,因為食鹽行業的自身的特殊屬性,以及“食鹽產品必須供給所有人”這個價值觀的存在,食鹽是不可能像斯密所描繪的“看不見的手”那般予以資源配置的4。這就導致了鹽業必然由國家管制或者由強大集中的經濟集團壟斷,此點中外皆然1。在本文中,筆者把清代的鹽業稱之為“管制型的市場經濟”,這是與鹽業自身特征高度匹配的一種具有嚴密管制的市場經濟。而廣西土司地區食鹽運銷的案例,恰好給予了這樣的觀察視角,可以解釋該類經濟形成的過程。其一,廣西土司地區是沒有普遍的食鹽消費的,民間多數采取“代鹽”的方式獲取化學意義上的鹽;其二,在鹽法介入之前,土司地區由水客進行食鹽供應,但此類市場的供應是昂貴且小規模的;其三,清王朝在土司地區建立了非常特殊的運銷制度,該制度保障了低價鹽的供給,建立了管制型的市場;其四,為了協調土司地區供應與一般區域鹽法之間的市場,清王朝建立了特殊的管理機制。廣西土司地區的案例展示了一個從代鹽與非管制型市場兼行進入到管制型市場的進程,本文著重分析該進程中的管制制度。
一、清初瀝灰/酸糟法與水客市場供應兩種方式并存
從生理學而言,人類必須攝入鈉、鉀等元素方能維持生存,作為化學成分的鹽是不可替代的。而食鹽是傳統時期一般意義上比較容易獲取此類元素的食品。從商品意義而言,食鹽價格低廉,較易保存,集中包含人體所需的元素,故在傳統時期可以贏得其替代品的競爭。然而,在廣西土司地區,當食鹽價格高昂、不易獲取之時,食鹽常常在日常消費中讓步于其替代品。從這個意義來看,食鹽并不是當地居民生存的必需品。
在廣西,食鹽最常見的替代品是瀝灰水。據考證,瀝取的“灰”成分復雜,包括竹灰、茅草灰、樹枝灰、蕨灰、木炭灰、草灰、舊席灰、蕎灰、蕉葉灰、狗尿樹灰等2。瀝灰的原理在于從燃燒的植物灰燼中提取殘余的無機鹽,其中包含了部分人體所需元素,也一定程度上起到調味的作用。除了瀝灰水之外,土司地區較為常見是制作“酸糟”或“牛醬”以代鹽。據康熙《西林縣志》記載:“土人以燒酒糟同牛豬骨及鼠貯甕中,臭腐則味酸,名曰酸糟。”“牛肚中穢物土人謂其味酸醎,用以代鹽,呼為牛醬。”3酸糟和牛醬提取鹽的原理與瀝灰不同,是利用發酵動物部位的方法獲得鹽分,如此既補充了人體所需微量元素,又有助于飲食中調味。“酸”作為廣西地區常用的調味體系,并不限于《西林縣志》所涉動物及其部位,其實涵蓋了以發酵法為主體、以動物食品加工為主要手段的制作方式,常常被文獻歸于“味酸”一類。此外,還有以辣代鹽的調味方式,在廣西出現時間較遲,未有前二者常見4。
清初瀝灰/酸糟法的應用范圍甚廣。如慶遠府永順土州“民多古樸,瑤人不知倫理,死多不塟,不食鹽”,思恩府西隆縣“種稻山嶺,民無儲積,每椎牛飲生血,不食鹽”,古靈縣“味喜酸辛,食無茶鹽”。鎮安府歸順州“無鹽,常瀝灰取水以代”,下雷土州“酸糟作味,不慣食鹽”,白山土司“味嗜酸糟,素少食鹽”,興隆土司“辣椒作鹽”,歸德土州“少食鹽,以糟和味”5。當然,瀝灰/酸糟法并不限于土司地區,據《粵述》稱清康熙年間廣西“瑤壯”的情況,“各郡山谷處處有之……性不食鹽,日惟淋灰汁、掃堿土及將牛骨漬水,《食丹鉛錄》所載貴州之賈鬼,即是物也。又以牛肚埋地窟內,候客至食之,以為上品,謂之牛醬,其煮肉即以牛皮為釜云”1。可見各府山谷中這些被標識為“瑤壯”的人群,實則普遍用瀝灰等代鹽方式。大體上,采取這些方式的人群分布于廣西較為偏遠的、國家統治能力較弱的鎮安、思恩、慶遠諸府,以及各府內之類似區域。一方面,這些人群是主動選擇瀝灰/酸糟法的,甚至牛醬被視為待客之上品;另一方面,則是清初廣西邊遠地區的食鹽供應緊張,清廷亦未建立這些區域的食鹽運銷制度。
與瀝灰/酸糟法并存的是由水客群體搭建的供應市場。這通過非官方渠道流入土司的食鹽。水客的外稱下,涵蓋的是復雜的各類人群,故水客可以視為小規模分銷模式的范疇。“水客”包括批發商、分銷商、小販、船戶、農民等等,從專業的鹽商到半專業的船戶再到季節性的農閑販運,涵蓋范圍廣,人數較多,實行中長途到短途的食鹽分銷2。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兩廣總督孔毓珣曾破獲一起私鹽案,即新寧“鹽灶附近居民”往肇慶府高要縣售私鹽,在高要縣南村地方被巡丁捕獲。其中“人鹽并獲者”有“邱阿六等四十七名”。后經高要知縣審訊,這些人均系開平縣簕竹村人,在新寧波頂墟上零星收買鹽斤,每人挑鹽約四五十斤不等,一時同行共七十余人3。這些“販鹽窮民”就是典型的水客分銷模式。
水客的網絡是巨大延伸的,可以覆蓋及土司地區。雍正年間兩廣總督兼管鹽政郝玉麟描述,“粵西各土司地方素不產鹽,離場又遠,水路則灘高水急,陸路則山徑崎嶇,運費過重,餉引難銷,是以從來未設有額引”,故土司地方不在兩廣鹽政的銷區之內。“總有私販肩挑背負,盤費亦多,其價自昂”,可見水客的網絡可以延伸進入土司的轄區。郝玉麟轉引時任云貴廣西總督鄂爾泰的意見提到:“間有私鹽挑入,其地遠者每斤賣價一錢,近者五六七分不等。……竟有終身未曾食鹽之人,所以見鹽如寶,深為可憫。”4可見即便有水客進入,但價格極高,五六七分至一錢的鹽價,超過了廣西任何鹽埠的官定價格,當地之人盡管缺鹽,也只能買食少許,見鹽如寶。這意味著,盡管水客的網絡常常有效地覆蓋及邊遠山區,但是這樣的網絡同時也是昂貴的,且并不能充分惠及所有土司地區民眾。而正由于往土司地區供鹽有利可圖,甚至鹽政的官鹽不斷走漏流入這類地區。《養利州志》指出:
窮陬僻壤,昔為羈縻,正供尚無所出,而雜稅罔可計議也。即代銷引鹽,因養利州處土司之中,土司為私鹽出沒之藪,貧民錙銖是利,保無舍貴而食賤者乎。歷年銷引極其艱難。至康熙三十年知州汪溶到任,設捕役,嚴隘口,禁絕私販,疏通官鹽,裕國而不病民,公私兩利5。
養利州的案例揭示了水客分銷體系的有效性。即兩廣鹽政于該地分派的鹽引“銷引極其艱難”,而鹽反而以私鹽的形式流入土司之區。而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汪溶需要積極防堵,方才可以避免食鹽流銷進入土司地區。此舉實際上是站在鹽政的立場上說的,所謂“裕國而不病民”,也是基于鹽法得以順利實施的角度立論。
總體而言,清初廣西土司地區的食鹽供應,是以土民以瀝灰/酸糟法代鹽,和水客體系供應食鹽二者并存的。后者是以水客群體為中心的市場進行供應,該鹽產品的價格是高昂的,或者在個別情況下從官方渠道走漏私鹽,可以提供部分低廉產品。這類水客供應鹽的規模是比較小的。
二、余鹽府銷:廣西土司地區運銷制度的形成
土司地區沒有官鹽行銷的情況持續到雍正年間。雍正七年(1729年)十二月,鄂爾泰提出土司地區行鹽的問題,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重視。鄂爾泰指出:
西省土司向無額引行銷,各土司土人從不敢遠赴城市,間有私鹽挑入,其地遠者每斤賣價一錢,近者五六七分不等,土人窮苦居多,惟于耕種力作時買食少許,其余經年惟食酸糟,竟有終身未曾食鹽之人。所以見鹽如寶,深為可憫。當擇無餉之余鹽,約定官本盈余,平價發售,使彝民不致食淡1。
鄂爾泰看到了土司地區食鹽行銷的要害在于價格高昂。土司地區私鹽0.05 - 0.1兩/斤的零售價格,較之于桂林府(部定價格平均值0.019兩/斤)、柳州府(0.02兩/斤)、慶遠府(0.023兩/斤)、思恩府(0.02兩/斤)、平樂府(0.018兩/斤)、梧州府(0.013兩/斤)、潯州府(0.017兩/斤)、南寧府(0.016兩/斤)等主要行鹽府均顯得異常昂貴2。揆其原因,是因為這部分供應是由水客以私鹽的形式挑入的,其結果自然使土人兼食貴鹽與酸糟。鄂爾泰提出的方案是以不帶西餉(即廣西部分的鹽稅)的余鹽供應土司地區,盡量從官運利潤中調整好價格,“平價發售”,予以照顧。該方案奠定了隨后廣西土司地區食鹽供應的基礎精神,并交予郝玉麟進行討論。
雍正八年(1730年)正月,郝玉麟對此方案進一步完善。郝玉麟為土司地區食鹽供應的價格設定了區間3。一方面不可以過于低廉,以免沖擊官引,造成私鹽泛濫。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運鹽成本(在清代鹽價體系中,成本核算中為利潤預設了空間)來計價,則定價過高,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在此區間基礎上,再“寧少無多”,試圖給“彝”民實惠。鄂爾泰、郝玉麟的方案并未真正落地,但其從降低鹽價的角度去設置惠及“彝”民政策的思路則延續了下來。
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兩廣總督鄂彌達才從制度上確立了土司地區的低價供應。其時恰逢鄂彌達采取高價收購余鹽的時機,官方增加了食鹽發帑采購的力度,廣西確立了“正鹽搭銷余鹽”的運銷制度。據鄂彌達奏疏, 規定了余鹽搭銷的三個原則性問題1。其一為官鹽一包帶銷余鹽50斤,此為參考性的搭銷比例。實則余鹽每年收購數額不同,該比例會隨時變動。“此項余鹽遞年豐歉不一,或多或少,難以懸定。統俟歲底收買若干,搭銷若干,收價若干”2。其二為廣西官運赴場購鹽的鹽價。此鹽價原則上“較引鹽為輕”。其三為廣西各埠賣價,則是按照部價銷售,不區分正鹽余鹽。
搭銷余鹽為鄂爾泰、郝玉麟“惠及彝民”設想提供了落地的契機。鎮安府的個案頗為典型。雍正十二年(1734年),鎮安府知府陳舜明開始“試銷”平塘江灶丁余鹽,主要投放于鎮安府屬的州縣及各土州。陳舜明的詳文今已不存,但府志回顧其部分內容。
平塘江鹽有春夏秋冬鹵耗之分,用簍裝載起運,每斤約解銀一分九毫零,梧州府生鹽每包正耗鹽本等項,解銀一兩四錢五分五厘六毫七絲六忽,熟鹽每包正耗鹽本等項解銀一兩五錢二分三厘八毫零,俱解赴本省驛鹽道投納。其前后詳定鹽法領運回府,分發附郭天保、歸順、湖潤、向武、都康、上映、下雷、小鎮安漢土各屬銷售。奉議州就近田州,兼近府埠,聽從民便買食其鹽,自奉議河邊挑運至府,計程三日,每鹽一包改裝三擔,給挑腳銀九錢。又竹簍雨具給銀一錢五分六厘,又給耗鹽一斤半,由府轉運歸順等六屬,計程二日,每夫一名,給腳價銀二錢,設立鹽埠五處,定價有差,俱知府陳舜明于雍正十二年詳明定價3。
由此可見陳舜明是先從平塘江領運鹽斤,再于鎮安府設有五處鹽埠進行分銷。鹽價方面,以平塘江解銀(每包以150斤計)、挑腳銀、竹簍雨具銀及挑夫腳價銀(按一夫一包算)約略總計,運鹽到埠成本約為4.1兩/包,折合成鹽價為0.027兩/斤,與鎮安府各屬的部定鹽價0.021兩/斤(天保縣)、0.021兩/斤(奉議州)、0.025兩/斤(歸順州)較為接近。考慮到各土屬州路途更為遙遠,如此定價尚屬平緩。陳舜明所請是屬于呼應鄂彌達改革的舉措,故所領鹽包雖以余鹽為主,但并未定額。此后鎮安府屢有所請,如表1所示。
從鎮安府諸次領運銷鹽的紀錄來看,有一個逐步走向定制的過程。雍正十二年(1734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間,鎮安府由知府向廣西驛鹽道領銷鹽包,數額與鹽項不一,包括在平塘江支運廉州、雷州鹽場的鹽斤與梧州支運粵東省配體系的鹽斤,均非定制。而所領鹽包,屬于余鹽與雜項(額外余鹽、秤頭耗鹽)的范疇,屬于場價較低、較為優惠的項目。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方始由廣西驛鹽道呈文確定下來,每年需從平塘江及梧州府支取余鹽,遂成為鎮安府長期銷鹽的責任。鎮安府行官鹽之后取得了明顯的成就,據載:“舊俗土民瀝灰水以代鹽,自本郡遍行官鹽,土人方免淡食,瀝灰之風始息。”1
鎮安府的個案并非孤例。慶遠府“自雍正十一年為始,慶遠配運惠州白沙、坎下二場生鹽,每額十包,加銷余鹽二包,行各土州縣司運銷”2。其中東蘭土州、南丹土州、那地土州、忻城土縣、永定長土司、永順長土司、永順副土司均于雍正十二年奉文領銷余鹽3。南寧府“四土屬原無額引,系本府同知買運廉場灶丁余鹽,在平塘江口配發,至府城領銷賣完解價繳府”4,其中忠州土州、歸德土州、果化土州、遷隆峝均分銷本府余鹽。
那么,這五府具體如何向土司地區配銷余鹽呢?雍正十二年(1734年)的改革逐步確立了一套由知府負責運銷土司地區余鹽的程序。該程序在制度上描述為“領運、轉發、稽查、銷解”四個過程5。所謂“領運”,是由各府赴梧州或橫塘江口購買并運回鹽斤,這是屬于典型的“官運”制度,其核心在于官發鹽本(帑本)的運作,據載:
謹案土司鹽包有流存帑本運腳銀四千一百五十九兩三錢七分五厘,按照各府應銷鹽包分給存貯,聽各府買運行銷。扣留帑本運腳為下年買運之費,尚應完羨余節省等銀三千五百九十三兩三錢八厘,由各府按年批解鹽道6。
即兩廣鹽政于廣西鹽驛道設有購置土司鹽包的專項經費,稱之為帑本運腳銀,分發各府存貯。在領運的程序之中,由各府用此項經費支領鹽斤并負擔運費。而每年完成一個銷鹽周期之后,則把銷鹽回流的資金,扣留下年買運之費之外,在“羨余節省銀”項下解運鹽驛道,此為“銷解”的程序。
所謂“轉發”,即由知府負責把領運鹽斤從流官主掌的鹽埠,結合水陸運輸之便利條件,轉運往土屬鹽埠。制度實行之初,往往會在土屬州縣設置鹽埠或者鹽盆。其中鎮安府向武土州、下雷土州等均設置鹽埠,向武埠的規模為“草房前后六間”。鹽埠是官鹽批發交易的所在,兼具零售功能,而“鹽盆”則更加傾向于零售鹽斤。在廣西普遍情形,鹽盆往往由小販或者商人自行充當,并不由官方管轄7。此時由知府在一些邊遠且較小的土屬州縣設立鹽盆,如湖潤、都康、上映等地,由官方直接接管零售,是非常特殊的待遇。
所謂“稽查”與“銷解”,則是知府負責監管土屬地區的食鹽分銷,由土司進行實際分銷。第一,知府領運、轉發余鹽之后,直接撥往所轄土司,并不由商人乃至縣級屬官染指。在此過程中,土司亦不必“墊支價本”,因為知府已有帑本作為專項經費。第二,余鹽由土司安排分銷。此項具有清廷一貫的政治考慮,即盡力維持土流隔絕的政策。故撥與土司之后,便不再接受此前水客對于土司地區的滲透,亦在制度上否定了私鹽進入土司地區的合法性。甚至,在廣西多數鹽埠采取商運商銷的改革之時,撥與土司余鹽一項仍然堅持官運,其理由是“苗壯與漢人素不往來,未便以銷鹽細故,遽令商人前往交售,致啟漢奸交通之漸”。此項政策是非常嚴謹的。例如廣西龍州“三峝土民鹽斤,仍照向例,由府撥給,不許與商鹽摻越。每年鹽羨發銷,歸入十九土司鹽額,由府完解”1。龍州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上下二龍土司改流而來,所謂“向例”則是改流之前的舊例,三峝土民鹽斤是由知府直接撥給、完額、完解,與商鹽在制度上完全區隔。這也意味著,知府的稽查責任是極重的。
總體來說,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來,廣西土司地區逐步從水客私鹽與瀝灰/酸糟代鹽并重的局面,轉向了府撥余鹽與瀝灰/酸糟代鹽并重的新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套以知府為中心的特殊運銷制度。知府直接負責運銷大部分程序,是頗具成效的,“舊俗土民瀝灰水以代鹽,自府屬行官鹽,方免淡食。瀝灰之風俗始息”2,說明土司地區的食鹽供應落到了實處。當然,這種特殊運銷制度既帶有撫恤“彝民”的初衷,也包含杜絕土漢交通、隔絕土漢往來的政治考慮。隔絕政策反映到鹽法上則是清晰的土漢供銷界限,知府維持該“鹽界”頗為不易。
返觀知府運銷余鹽的制度,清廷并未給予知府更多的制度性優惠,如羨余等經費均要嚴格銷解,鹽埠的建置與維持沒有專項經費,鹽本與運費只給了最低程度的款項。于此同時,對知府的要求卻頗為嚴苛,既要維持官鹽具有撫恤意義的供應,又要恪守土漢之間的界限。這無疑難以給予知府正向的激勵,反而從中滋生弊端。乾隆《鎮安府志》3出于知府視角的一段文字對此予以委婉的表述。
為政之道,不外理財用人,鹽?斯其一矣。鎮安無商,官司鹺政,官即商也。籌策挽運水腳不敷,不免賠貼,途次竊賣,摻和砂鹵,奸偽百出,市肆錙銖高下弊竇,難以指陳。梟徒私販,更難周察,非用人多則不足以董事,而人多則費愈繁。若非得人而任之,腥膻之地垂涎者眾,利歸私飽,毀言日至4。
據此,鎮安府“官司鹺政”,是為官運官銷制。在實際實施時,官方運輸水腳的預算是不夠的,不免賠貼,這就是過于理想化的經費撥給及銷解帶來了額外的財政負擔。由于官運無利可圖,反而負擔沉重,故難免有竊賣、降低鹽質(摻沙)等奸偽百出的情形。于此同時,梟徒私販也提高了監管的難度。若是加大監管的人員規模,又不免“費愈繁”。這段評述恰可反映知府運銷制“責任重、預算少”的內在特征。
三、土司地區低價供應的實現
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來,廣西南寧、太平、鎮安、思恩、慶遠五府的余鹽府撥政策已然形成。那么,這部分府撥的余鹽,是否能夠如鄂爾泰、郝玉麟所設想的低價供應,予“彝民”以實惠呢?清代兩廣鹽價是受管制的官價,源自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廣東巡撫朱弘祚定價5,此后在此基礎上有所增減,由戶部審批確定,稱為部價。故官方試圖在土司地區推行優惠性的定價,便不是簡單地調整價格,而需要遵循鹽政定價的原則,并保證所定價格不會與已有鹽法自相矛盾、相互捍格,方能真正實現。
清代兩廣鹽政定價的形式,是采取成本定價的方法。清代鹽政所謂成本,與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成本不同。該成本包括鹽本(購鹽價額)、各項運費、各項管理費用、各項稅收以及各項余羨,包含余羨意味著在成本之中率先提取利潤,而現代意義的成本則不具備如此寬泛的意涵,尤其成本與利潤是相對的概念,完全分開核算。在成本核算的基礎上,采取“成本等于價格”的方式定價,這是兩廣鹽政定價的原則。該原則只有采取鹽業管制的體制才能得以貫徹。
廣西土司地區的鹽價首先涉及余鹽價格的問題。雍正十一年(1733年)廣東總督鄂彌達對余鹽價格定制時規定,其一,余鹽“照依部定引鹽價值一體銷售”,即與正鹽的賣價相同,延續了廣西食鹽運銷總體的部定價格1。其二,廣西各埠余鹽的成本構成,此時主要包括場價(埠銷鹽本)、運腳、工火、埠羨四項,其中場價又包括鹽本、篾簍、運腳、人夫工食與修倉五項。與正鹽對比,余鹽不包括引課,即鄂彌達所謂“毋庸分晰東餉西稅”2。其三,場價中的鹽本“每包酌定收場價銀九錢五分,尚較引鹽為輕。”這意味著,鄂彌達是采取縮減利潤(場羨取每包三錢)的方法來控制余鹽價格的。余鹽項下,于搭銷比例之外的雜項鹽則更受地方官府的青睞。據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李侍堯指出:“一曰額外余鹽,一曰添買秤頭鹽,此二項成本在于鹽余項下支領,其賣出羨銀以八折九折繳庫,地方官所獲余利甚多,是以向來將正引鹽及正項余鹽乘時發賣。先將額外余鹽及添買秤頭鹽發賣,以致引鹽壅積。”3總之,在廣西投放的余鹽在官價上與正鹽一致,但余鹽的成本顯然更輕,其中羨余部分的比例較大,給了分管埠銷的官、商更大的操作余地。
在余鹽定價的基礎上,鄂彌達進一步提出:“至于遍行土司,必須鹽價稍輕,方可疏通及遠。”4據李侍堯回顧:“嗣因改設流官分轄,每年分撥土司余鹽四千三百九十四包,責令該府轉發土司運銷。照減價每斤賣價一分二三厘不等,歷久遵行。”5可知此番定價為每斤一分二三厘不等,與配銷土司地區五府的平均部價相比,此次定價大體為部價的50%。乾隆十七年(1752年)兩廣總督阿里袞據廣西布政使李錫秦鹽驛道張曾等覆稱:“南寧府屬余鹽,每斤應賣銀一分四厘,太慶思鎮四府每斤應賣銀一分五厘,此系雍正十二年題定之價。嗣于乾隆元年(1736年)欽奉上諭,廣西鹽價每斤減去二厘銷售,自此南寧府每斤鹽應賣價銀一分二厘,太慶思鎮四府應賣價銀一分三厘。歷年奏銷冊報在案。”6可見前者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鄂彌達的定價,而李侍堯回顧的是乾隆元年減價之后的定價。不論哪個定價,都較之于原來的部價有了大幅削減,這固然是給予土司地區土民的優惠政策,但是否有可能落到實處呢?
乾隆十七年(1752年),阿里袞就“南寧、太平、慶遠、思恩、鎮安等五府屬土司及改土歸流地方分賣余鹽,價值與奏銷冊報定價多寡不符”的情況對乾隆皇帝作出解釋。
歷年奏銷冊報在案,而其實各土司賣價不止于此。蓋因各土司分銷鹽斤,原系責令各該知府前赴梧州江口運回轉發督銷解價,而從前題定賣價僅一分四厘一分五厘之時,止系將梧州江口運至該府之腳費等項,核入成本,定價發賣,其自各該府轉運至土司地方腳費等項,并未算入此項。轉運腳費在所必需,既不便于應解之羨余銀內開銷,止可于銷賣鹽斤價內酌增抵補,是以雍正十二年具題定價送部冊內原經聲明,仍令該府將轉運到埠之腳費,依遠近之酌增發賣。彼時即經前督臣鄂彌達撫臣金鉷將各該府轉運至土司腳費分別道路之遠近平險,詳悉酌定每斤自一二厘至一分有零不等。惟東蘭州并土州同、鎮安等三處酌定一分七八厘至二分有零不等,俱核入賣價銷售。嗣奉諭旨減價,亦即遵照減銀二厘。惟是奏銷冊內因從前定價之時,未將轉運腳費核入,是以止照原定之價減銀二厘造報,而未照現賣之價減銀二厘造報。歷久相沿,已有年所。至各府轉運鹽斤至土司地方,在在崇山峻嶺,遠者至十余站不等,肩挑背負,止能三四十斤,日行三四十里,轉運甚為艱難。從前或遇缺鹽之時,有賣至五六分一斤不等,自雍正十二年酌定轉運腳費之后,幾及二十年來鹽無缺乏之虞,價無增昂之慮,每斤不過一分三厘至二分有零不等,即極貴之處,亦止有東蘭州并土州同、小鎮安三處不過賣銀三分有零,土民歡欣稱便,行銷較昔有增。至所定腳費,均系實在必需,并無稍有浮冒多賣等情1。
從成本定價的制度邏輯出發,鄂彌達題定的價格僅僅包括從梧州運回到各府的成本,即知府“領運”的程序中所支出的經費,但是“撥銷”程序所需成本并未計入,即“自各該府轉運至土司地方腳費等項”。在鄂彌達原定規制中是留有余地的,即各府至土司地區的轉運經費根據路途遠近,“每斤自一二厘至一分有零不等”,較遠的東蘭州等三處“酌定一分七八厘至二分有零不等”。在實際運作中,這部分經費也核入成本,進而計入價格,是土司地區的實際定價理應高于奏銷冊所顯示的定價。據阿里袞等強調,自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來“價無增昂之慮”,即每斤一分三厘至二分有零,較遠的三州不超過三分,可見仍在成本定價規定的范圍之內。
這樣的定價邏輯并不僅僅存在于戶部與總督的文書之中,也在各府得到具體的推行。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鎮安府知府領運鹽斤之后,便“分發附郭天保、歸順、湖潤、向武、都康、上映、下雷、小鎮安漢土各屬銷售。奉議州就近田州,兼近府埠,聽從民便買食其鹽,自奉議河邊挑運至府,計程三日,每鹽一包改裝三擔,給挑腳銀九錢。又竹簍雨具給銀一錢五分六厘,又給耗鹽一斤半,由府轉運歸順等六屬,計程二日,每夫一名,給腳價銀二錢,設立鹽埠五處,定價有差”2。據此,以平塘江解銀(每包以150斤計)、挑腳銀、竹簍雨具銀及挑夫腳價銀(按一夫一包算)約略總計,撥銷到埠成本約為4.1兩/包,折合成鹽價為0.027兩/斤,略高于鎮安府各屬的部定鹽價0.021兩/斤(天保縣)、0.021兩/斤(奉議州)、0.025兩/斤(歸順州)。其中府志亦載向武土州、下雷土州所定鹽價為0.025兩/斤,小鎮安土司為0.033兩/斤,與成本較為接近。其中向武土州定價的修正頗能說明問題,“乾隆十年,知府張光宗奉議有小路可達向武,鹽斤不必由府領,運腳鹽價均可稍減,詳明改定價銀二分三厘零九絲”1,約比原定價低二厘。此例正好表明,在交通條件變化的情況下,知府亦有隨之優化成本,并予以成本定價。總體而言,盡管各府采取成本定價的方式,其鹽價優惠的幅度并未如官方經常聲稱的“每斤一分二三厘不等”那么大,但是較之雍正八年(1730年)郝玉麟時期“遠者每斤賣價一錢,近者五六七分不等”,已然明顯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該定價落實在實際交易之中,還會受到各地貨幣供應的影響。當時廣西民間頗為流行“碎銀”,對此總督鄂彌達解釋道:“又如南太等府所屬苗民,日用行使銀色自七八成或五六成不等,每鹽一斤,名雖賣價四分,除去運腳,折算紋銀僅敷部價二分二厘,并無實賣紋銀四五分之事。”2說明即便考慮銀色銀價,土司地區的低價鹽供應基本可以實現。
四、形成定制:土司無引鹽斤及其定額化
自雍正十一年(1733年)以降,兩廣運司供給土司地區的是沒有引額的余鹽,這是由鄂彌達所定發帑收購余鹽的政策決定的。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兩廣鹽法實施“余鹽改引”的變革,其要義在于把余鹽定額化,并改成與正引無異的余引,并在原分銷余鹽的各地形成固定的銷額。與此同時,廣西埠銷制度也發生了轉變。乾隆元年(1736年),兩廣總督鄂彌達把廣西全面官運官銷制調整為平樂、梧州、潯州、南寧、郁林五府州所屬二十八埠商銷,其余桂林、太平、柳州、慶遠、思恩五府所屬二十九州官銷的運銷制度3。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兩廣總督李侍堯進一步把剩余的官銷鹽埠調整為商銷鹽埠。這兩項鹽法制度的調整,對土司地區官鹽供應提出了新的問題。其一為余鹽改引是否涉及土司地區所供余鹽,其二為土司地區是否適用商銷制。
李侍堯認為應該因循舊例,供給土司地區的余鹽不應改引。他陳述了如下理由,其一為“若設土司額引,酌減課餉,則為數無幾”,按照五府每年領銷余鹽算,僅只四千三百九十余包,合引二千八百零四道,況且“倘照民價一律加增,土民更不樂于買食”。其二為若土司供鹽也改商辦,“如令土司官向商人買鹽轉售,勢須墊支價本”“非土官所愿”。若此次改歸商辦,則須由運商自行墊支買鹽、納課(餉)的本錢。故若由商人直接轉售鹽給土司官,則土司官需要墊支本錢。其三為杜絕漢商與土司直接溝通,此項上文已述,茲不贅述。李侍堯的提議得到了戶部意準,其后確立了“土司無引鹽斤”的供應專項及其配額4。
在表2所記錄的定制之中,尚有一個疑問并未解釋,即何以鹽法志所載各府項下,有具體鹽埠的配額?該鹽埠配額實際涉及運銷制度向商運的轉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兩廣總督蘇昌咨稱:
緣官辦之時,所有土司余鹽向系委員買運至梧州江口,該府差役赴領。今各埠均改商辦,運館裁撤,若將土司余鹽仍令知府徑赴廉場配運,勢必假手書役,借官夾私充賺之弊。隨據崇善、宜山等埠商人情愿領出官運土司鹽本水腳,代官雇船到埠,聽各府轉發土司領銷,以免胥役船戶夾私充賺。改配省河,除隆安等埠代運余鹽四百二十六包,慶遠額鹽七百五十包,毋庸改配外,其新寧等埠代運土司余鹽三千二百一十八包,原配廉鹽,每包需用腳價銀二兩二錢四分,至一兩三錢三分不等,改配省河,每包實可節省帑本銀四錢一分,遞年通共計節省帑本銀一千三百一十九兩三錢八分,所有各商代運鹽包及改配省河節省帑項數目,理合分晰造冊咨部,統歸西省奏銷。1
前文已經揭示知府運銷制所產生的“籌策挽運,水腳不敷,不免賠貼,途次竊賣,摻和砂鹵,奸偽百出”等問題,且知府責任較重,卻并未有足夠的預算。此番兩廣大規模改商銷制的進程中,土司地區是否采取商銷則成為一個要題。蘇昌此次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在知府對土司的轉運與配銷環節仍循舊章,而在從梧州(橫塘江口)領運鹽斤的環節該歸商辦。蘇昌接受了崇善、宜山等埠商人的理由,即新寧等埠由廉州鹽改配省河鹽可以節省帑本,故改了土司余鹽的配運點,并把原由知府負責的“領運”環節交予埠商,由彼“領出官運鹽本水腳”“代官雇船到埠”。該調整之后,形成了商運、府撥、土司銷、府解的新運銷制度。在該改制之中,商人可以把知府單獨領運的鹽包合并到各自承領的鹽埠之中,很可能因之節省運輸成本。這也就是鹽法志中無引鹽斤系于鹽埠的由來。
但是,定額制與商運制很快遇到短缺與掛欠的問題2。定額制造成了短缺,“土司引鹽歲額本屬不敷,且今生齒日繁,更虞缺乏”,這就意味著由知府負責供應的鹽斤是不足的。囿于埠商不能直接賣鹽與土司,知府只能向埠商“買運轉銷”。于此同時,知府購買鹽斤的預算(鹽本)是定額的,制度上并未予以追加,故只能循“先鹽后課”之例向埠商掛價,先支取商埠鹽斤撥運土司,再由埠商向鹽運司發折報告掛價數目,然后由運司向知府追繳相關款項。知府待銷鹽之后回收本錢,便支付商人所掛之鹽相關價值。很快,這種官商交易出現了錯位。因為售予土司的鹽斤,是采取管制低價的,該價格低于正常埠價,故知府采取土司地區鹽價來支付預支商鹽,則出現了短少,甚至“積欠至三千八百余兩”。當然,其中也存在著借知府權勢壓迫埠商的行為,常常經年累月不還,而埠商亦不敢追回。此類問題暴露出定額制和土司地區食鹽特殊供應制度的基礎問題,其一為過于僵化的定額適應不了土司地區實際的食鹽消費需求,其二為同一府埠(或臨近埠)卻用兩套供應體系、兩種供應價格,會產生制度內在銜接的矛盾。
對此,李侍堯主持了進一步的修正方案,即“由因定土司余鹽,向系減價行銷已久,是以仍令各該府照數行銷,以示優恤。其不敷食鹽,各該土民既愿照依埠價買食,自可聽其各向附近商埠購買,毋庸由府轉賣運銷,致多挽運之煩,且免輾轉剝除行鹽”。總體來說,新的定制是一套雙重的供應制度,即定額內維持原制,采取商運、府撥、土司(改流土司則以鹽埠為準)銷、府解的方式運作,所謂“嗣后土司余鹽,各照依原定額鹽包數飭商代運,交府按依原定價值行銷,不得逾額,及預交下年未折鹽斤多銷,并于定價外多取絲毫”。而定額以外的鹽斤,則由土民自由向埠商購買,所謂“其土民不敷食鹽,即出示曉諭,令其各赴附近商埠照依時價買食,毋許土司及胥役人等借端阻遏”1,是為純粹的商運商銷制。至此,土司無引鹽斤定額制才真正得以落地,而土司地區的食鹽供應,也逐步趨于與流官州縣一致,融入了兩廣商運商銷體制。
五、結語
廣西土司地區食鹽運銷的特殊制度展示了清代兩廣鹽業的運作邏輯。若沒有官方涉入,土司地區僅僅存在著并不能自發供應鹽斤的市場,土民只能大規模采取瀝灰與酸糟的代鹽方法。而官方涉入之后,從派發無引鹽斤、知府領運與轉運、設置鹽埠、低價供給乃至最終商銷制的介入,均采取了較為嚴密的管制體制。該體制的目的是向土民低價售予鹽斤。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一種管制型的市場經濟,盡管其運作的成本較為昂貴,且在制度上對于知府的行政要求較為苛刻,但基本實現了對于該地區原有食鹽格局的改造。從這個意義上說,清王朝是采取了管制型的市場經濟,替代掉了原有的水客供銷的市場經濟。
盡管土司地區有其政治上的特殊性,官方從“惠及彝民”的立場給予了價格優惠。但是從整體上說,由于食鹽在理念上被視為需要供給所有民眾的,故斯密型的完全競爭市場未必能夠實現這樣的目的。余鹽府銷制度盡管在實施上具有許多弊端,但是基本還是保障了高質量與相對規模的低價鹽供應。這也是清代管制型市場經濟在食鹽這種特殊行業中的意義所在。
[責任編輯:龍澤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