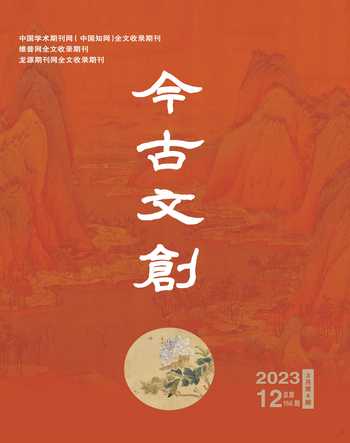梶井基次郎《檸檬》新考
【摘要】梶井基次郎的處女作《檸檬》一直被認(rèn)為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說(shuō)中幻想與現(xiàn)實(shí)反復(fù)交織,一直被認(rèn)為是病人視角的,倦怠、灰暗而又神經(jīng)質(zhì)的。本文依據(jù)時(shí)間先后對(duì)小說(shuō)中的情感變化逐一進(jìn)行解析,并結(jié)合時(shí)代背景解讀小說(shuō)中的關(guān)鍵“里街”“丸善”及“檸檬”之間的聯(lián)系,進(jìn)一步論證梶井基次郎在《檸檬》中所要展現(xiàn)的并非是自我放棄的呻吟,而是死而向生的希望。
【關(guān)鍵詞】梶井基次郎;幻想;檸檬;現(xiàn)代
【中圖分類號(hào)】I313? ?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3)12-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02
一、引言
梶井基次郎生于1901年,母親對(duì)梶井的學(xué)業(yè)非常嚴(yán)厲,不僅從小為他朗讀《萬(wàn)葉集》? 《源氏物語(yǔ)》等古典作品,就連梶井成人以后,還時(shí)常勸說(shuō)其學(xué)習(xí)久野豐彥等人的作品。然而梶井的一生短暫而磨難,7歲患急性腎炎幾近死亡,19歲身染肋膜炎,此后進(jìn)一步惡化為肺結(jié)核。1924年,他進(jìn)入東京帝國(guó)大學(xué)文學(xué)部英文科就讀,后因病情加重而無(wú)奈輟學(xué)。次年,梶井與中古孝雄等人創(chuàng)辦同人志《青空》,并發(fā)表了自己的處女作《檸檬》。直至1932年病逝,梶井僅創(chuàng)作二十余篇作品,并且多以私小說(shuō)、心境小說(shuō)為主。令人惋惜的是,梶井在生前并未能在日本文壇取得一席之地,其作品在他逝世后才被文壇作家們大力推崇,甚至被稱為“昭和的古典”。①
小說(shuō)《檸檬》于1925年在《青空》上發(fā)表,但這部作品早在1924年秋就完成了。《檸檬》在完稿前總共經(jīng)歷了四次改稿,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也就是第三稿《瀨山之話》。就《瀨山之話》的文體結(jié)構(gòu)來(lái)說(shuō),更偏向以作者自身為主體的第一人稱小說(shuō),與私小說(shuō)《檸檬》還是有所落差的,但大致已有了《檸檬》的雛形。《瀨山之話》分為了三個(gè)部分,“檸檬”“感覺(jué)器的惑亂”“深夜彷徨”,《檸檬》的前身則為這第一節(jié)插話。
二、檸檬序曲
《檸檬》開(kāi)篇“不可名狀的不吉始終壓著我的心”,展現(xiàn)了一張因久病纏身、混沌度日而空虛乏力的面容,并奠定了小說(shuō)的主基調(diào)——壓抑與灰暗。
“該說(shuō)焦躁呢,還是厭惡呢——就像飲酒過(guò)后的宿醉一樣……這可有點(diǎn)兒糟糕。這糟糕不是說(shuō)最后會(huì)導(dǎo)致肺結(jié)核或者神經(jīng)衰落,也不是因?yàn)榛馃济慕杩睿愀獾氖悄欠N不吉的感覺(jué)”。
作者在此明確告知,讓“我”更在意的并非肺結(jié)核或神經(jīng)衰落抑或借款,而是那股不祥之感。這也讓我們不禁聯(lián)想到梶井當(dāng)時(shí)所處的狀態(tài),即肉體與精神的雙重痛苦。身處這樣的痛苦之下,即便是曾經(jīng)最喜愛(ài)的優(yōu)美的音樂(lè)和詩(shī)都不能讓“我”開(kāi)心起來(lái)。即使特意去聽(tīng)唱片,聽(tīng)上兩三節(jié)就想要站起來(lái),到底是什么讓“我”如此坐立不安?這里的“什么”或許是與開(kāi)篇的“焦躁”“厭惡”相類似的東西,這東西以音樂(lè)和詩(shī)為契機(jī),由“我”的心頭悄然而生。于是“我”再也無(wú)法忍受,開(kāi)始走向街頭“流浪”。
而流浪街頭的“我”,格外醉心于那些破敗美的東西。如被風(fēng)雨侵蝕根基崩壞的房屋,上面還晾著一些臟衣物的里街。細(xì)想之下,這里其實(shí)是第一段中“我”內(nèi)心的對(duì)外投射——最初的“我”心頭壓抑,而身處的環(huán)境卻凈是一些美好事物,如優(yōu)美的詩(shī)和美妙的音樂(lè),這一切都讓“我”感到格格不入,無(wú)所適從。因而走到街頭流浪后,內(nèi)心陰郁的“我”理所當(dāng)然地不喜那光鮮亮麗的外街,卻獨(dú)獨(dú)鐘情于那偶能看見(jiàn)幾株向日葵和美人蕉的破敗不堪的里街。
如果說(shuō)以上還只是“我”內(nèi)心情感的對(duì)外投射,是對(duì)真實(shí)景象的選擇性接受,那么接下來(lái)便是“我”進(jìn)一步地企圖通過(guò)病態(tài)的幻想來(lái)重構(gòu)世界。“我”走在這樣的街道上,開(kāi)始幻想自己并非處在京都,而是在更遠(yuǎn)的仙臺(tái)或者長(zhǎng)崎。“我”是如此享受將現(xiàn)實(shí)中的自己迷失其中的樂(lè)趣,因?yàn)楝F(xiàn)實(shí)里的自己已經(jīng)如此充滿不幸。想要獲得一絲快慰,似乎只能構(gòu)筑一個(gè)幻想中的世界。然而,“我”終究意識(shí)到了這一切不過(guò)是錯(cuò)覺(jué),于是“我繼續(xù)用想象的畫筆為之添彩”。
這想象的畫筆進(jìn)而將“我”從空間維度上的幻想帶入時(shí)間維度的幻想。“我”想起煙花,想起玻璃球,想起南京玉,想起幼年時(shí)經(jīng)常將玻璃球放在嘴里而遭到父母訓(xùn)斥的場(chǎng)景。弗洛伊德曾說(shuō):幸福的人絕不會(huì)空想,空想的人只是些不滿的人。某種愿望未被滿足正是產(chǎn)生空想的原動(dòng)力。無(wú)論是小說(shuō)中的“我”還是梶井自身,靈魂已無(wú)處藏身,而未來(lái)也因不治之癥而一片灰暗,只能回味過(guò)往暗自舔舐傷口。但或許是童年記憶太過(guò)甘美,又喚醒了長(zhǎng)大后失魂落魄的自己。那種舔著玻璃球的“清幽酣暢的可媲美詩(shī)情畫意的味覺(jué)”與此刻落魄的自己形成了對(duì)照,竟很快地又從嘴里發(fā)散開(kāi)去。
第六段第一句“眾所周知,我身無(wú)分文”,略帶詼諧和自嘲的語(yǔ)氣也是梶井文學(xué)的一大特色。當(dāng)“我”看到破敗里街中盎然生長(zhǎng)的向日葵和美人蕉時(shí),忍不住幻想自己身處仙臺(tái)或長(zhǎng)崎的靜謐的旅館房間內(nèi),忍不住回想幼時(shí)舔著玻璃球,用廉價(jià)的畫筆描繪各種各樣的煙花條形形狀、滿天星和枯芒草……然而這一切終歸是空想,當(dāng)“我”被拉回現(xiàn)實(shí),失意更為鮮明。此刻,盡管“我”身無(wú)分文,但是也急迫地需要一些“奢侈的東西”來(lái)安慰自己。于是,“我”想起了曾經(jīng)最愛(ài)的地方——丸善。
丸善里有紅黃色的古龍水和生發(fā)劑,有華麗時(shí)髦的玻璃工藝制品和典雅的洛可可式浮雕花紋的琥珀色或翡翠色香水瓶,還有煙管、小刀、肥皂等等。然而這對(duì)于此刻的“我”來(lái)說(shuō),丸善里所有東西都像“催債的亡靈”。正如李曉光所言,落魄的他就如同破衣?tīng)€衫之人羞于走在陽(yáng)光下一樣,高雅、繁華、奢侈都成了遙不可及之物,自尊又敏感的神經(jīng)使他對(duì)丸善不得不敬而遠(yuǎn)之。而在破敗臟亂的小巷,他的潦倒似乎被淹沒(méi)了,使他感到一種忘卻的快樂(lè)。②
言及此處,開(kāi)篇所提及的“不吉”似乎已有了清晰的輪廓。這“不吉”既是神經(jīng)衰落、肺結(jié)核、借款所帶來(lái)的精神壓力,也是“我”無(wú)法掌控的隨處游走的思緒。這種思緒對(duì)于當(dāng)時(shí)的“我”來(lái)說(shuō)就是一種“奢侈”,而這種“奢侈”本身就是一種過(guò)剩行為,是強(qiáng)迫癥的表現(xiàn)。這種過(guò)剩想象也被“我”命名為“不吉”。不僅如此,當(dāng)“我”試圖來(lái)到丸善尋找生活還沒(méi)被吞噬的過(guò)往,卻發(fā)現(xiàn)自己本能的逃避抗拒,懼怕正視自己與社會(huì)的落差。由此一來(lái),“我”仿佛陷入莫比烏斯環(huán)中,始終難以擺脫這壓在心頭的難以言喻的“不吉”的集合體。
三、遇見(jiàn)檸檬
時(shí)間過(guò)渡到另一天清晨,“我”在朋友家中獨(dú)自面對(duì)著空虛的空氣。“有什么東西一直追著我”,這好似第一段“是什么讓我待不住”的情景再現(xiàn),只是此刻讓“我”彷徨外出游蕩的契機(jī)不再是音樂(lè)和詩(shī),而是“空虛的空氣”。于是,“我”徘徊到了前面提及的里街,在點(diǎn)心店前駐足,又張望干貨店的蝦干、鱈魚干和豆腐皮,最后走到二條的寺町,在那里的水果店停下來(lái)。這里的“點(diǎn)心店”“干貨店”“水果店”均可對(duì)應(yīng)前文的“破敗的美”,而這都是空虛乏力的“我”所必須要求的一個(gè)靈魂寄托之所。
因此,這家毫不起眼的水果店在“我”眼中也變得極其富有美感,然而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那家店最美的還是夜晚。
“就像深深戴在頭上的帽檐一樣——不,比起這樣的形容,一片漆黑的屋檐上方更讓人疑惑的是它為何像帽檐一樣壓得那樣低。周圍那樣昏暗,可店面被幾盞驟雨似的點(diǎn)燈的光線籠罩著,絢爛奪目。絲毫不受周圍的環(huán)境影響,只是美麗耀眼地存在著”。
在這里,梶井并沒(méi)有對(duì)水果店的外觀以及其他景象有過(guò)多關(guān)注,僅對(duì)水果店的亮光以及周邊的陰影進(jìn)行描述。就是這樣一家水果店竟然能夠讓“我”感到如此興奮。那么我們不妨設(shè)想,梶井在寫作《檸檬》時(shí)已身染肺結(jié)核數(shù)年,這是一種傳染病,當(dāng)時(shí)的他就如同這家水果店一般,仿若被蒙上了一頂深帽頂寬帽檐的帽子,與周圍的世界隔絕開(kāi)來(lái)。因此,筆者認(rèn)為此處也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將自身的情感投射于這家水果店。正如小說(shuō)中的“我”所直言的那樣,如果不是它那樣昏暗,或許也不會(huì)被其吸引。
那天,“我”終于“奢侈”了一回,鬼使神差地在這家水果店里買了一顆檸檬。當(dāng)主角遇見(jiàn)檸檬時(shí)整篇文章開(kāi)始起了化學(xué)變化,原本陰郁、倦怠感極強(qiáng)又神經(jīng)質(zhì)的開(kāi)頭文在檸檬出現(xiàn)后整個(gè)文章變得幽默明亮起來(lái)。為什么看中這顆檸檬呢?原因是在這家普通的蔬果店里還是頭一回碰見(jiàn)檸檬。而它“宛如從檸檬黃的水彩中擠出來(lái)的固態(tài)的單純色彩,還有仿若紡錘狀的形狀”仿佛強(qiáng)勢(shì)撞進(jìn)“我”灰暗人生中的一道光,于是“我”最終買下了它。而拿著這顆檸檬,感受著它冰涼的觸感,嗅著它清新的香氣,此前執(zhí)拗地壓在心頭的不吉竟奇跡般的就此煙消云散……而關(guān)于這顆檸檬究竟為何如此神奇,我們不難想象,當(dāng)時(shí)的“我”肺病惡化,總是發(fā)燒,體溫比常人偏高。當(dāng)意外地接觸到這樣一顆冰冰涼的檸檬時(shí),掌心的快感迅速蔓延至全身乃至心底,彷徨不安的靈魂仿佛也得到了極大地滿足,甚至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動(dòng)和自我的存在。
除了生理感官外,還有學(xué)者認(rèn)為,梶井的文學(xué)深受西歐近代的繪畫與音樂(lè)的影響。日本進(jìn)入大正時(shí)代后,迎來(lái)不少來(lái)自歐美的演奏家。梶井二十一歲時(shí),曾去聽(tīng)過(guò)小提琴家米斯卡·艾爾曼(MischaElman)的演奏會(huì),并與其握手交談。繪畫方面,梶井曾定期購(gòu)讀《中央美術(shù)》雜報(bào),對(duì)保羅·塞尚(PaulCézanne)的畫作尤其傾倒。梶井曾經(jīng)給自己取筆名為“瀨山極”,“瀨山”是Paul,“極”則是Cézanne,由此可見(jiàn)一斑。而當(dāng)時(shí)的西歐畫家們喜愛(ài)將檸檬用作靜物畫的主要元素,保羅·塞尚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對(duì)此,日本學(xué)者安東次男就曾指出,梶井這篇色彩運(yùn)用如美術(shù)畫作般的短篇小說(shuō)很有可能是受塞尚的影響。三高時(shí)期的梶井極具繪畫天賦,想必在他看來(lái),檸檬也并非單純的水果,更是能夠反映內(nèi)心世界的,極具存在感的素材吧。
四、檸檬爆彈
“我”拿著這顆檸檬興奮地在街道走來(lái)走去,把自己想象成身著華服、闊步于街道的詩(shī)人。此刻,“我”那壓抑在心頭的不祥之感早已不復(fù)存在,甚至“自鳴得意”地玩起了幽默。這和前文的“眾所周知,我身無(wú)分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通過(guò)獨(dú)白的方式實(shí)現(xiàn)了自我完結(jié)性。這種幽默詼諧的筆致在梶井早期的作品如《檸檬》和《城街》中還是比較常見(jiàn)的,但到了《泥濘》時(shí)期,這樣明快的氛圍完全轉(zhuǎn)化為陰郁與灰暗。晚年時(shí)期的《愛(ài)撫》,又開(kāi)始流轉(zhuǎn)著一絲輕松愉悅,但由于當(dāng)時(shí)病癥已經(jīng)惡化,這種輕松愉悅終歸只是流于作品表面罷了。
或許是“我”想要試試這顆檸檬是否在哪里都能奏效,又或許是“我”只是單純地游蕩著走到丸善門口,但可以確定地是,“我”對(duì)丸善依舊有著深深地留戀。于是,“我”昂首信步地踏了進(jìn)去。可是不知為何,“我”心中充滿的幸福漸漸地逃走了。“我”安慰自己或許是來(lái)回走路導(dǎo)致的身體的疲倦,但是就連平時(shí)最愛(ài)的畫冊(cè)此刻都不能引起“我”的注意,甚至連將它們抽出來(lái)都顯得格外的費(fèi)勁。于是,“我”想起了那顆檸檬,“我”將所有的畫冊(cè)堆砌成一個(gè)夢(mèng)幻般的城堡,然后將檸檬置于城堡之上。
“我端詳著,只見(jiàn)檸檬把斑斕的色調(diào)悄悄地吸收到紡錘狀的身體中,一瞬間變得鮮艷無(wú)比。我能感覺(jué)丸善充滿揚(yáng)塵的空氣只在檸檬周圍變得緊張起來(lái)”。
這一切完成之后,“我”突然有了一個(gè)更加大膽的想法,那就是把這個(gè)城堡和檸檬留在這里,然后若無(wú)其事的離開(kāi)。想象著這是一個(gè)閃著金色光芒的恐怖炸彈,十分鐘以后以丸善書店美術(shù)書的一角為中心發(fā)生大爆炸……
小說(shuō)最后十行,全然沒(méi)有修飾語(yǔ)或接續(xù)詞,仿若便簽條一般呈加速度地簡(jiǎn)潔有力,切實(shí)地傳遞了“我”強(qiáng)烈迫切的心情。而這正是整篇小說(shuō)的高潮所在。關(guān)于小說(shuō)的舞臺(tái)之一——丸善,也吸引了眾多學(xué)者的興趣。據(jù)考證,丸善的前身是1869年設(shè)立的以販賣舶來(lái)品為主要業(yè)務(wù)的“丸屋商社”。創(chuàng)立者早矢仕有的(福澤諭吉的門生)的創(chuàng)業(yè)理想就在于以貿(mào)易來(lái)推動(dòng)日本發(fā)展,因此丸屋商社的商品主要為當(dāng)時(shí)日本較為落后的如洋書、藥品和醫(yī)用器械等。由此一來(lái),丸善其實(shí)就是外國(guó)文化的移植之所。正如日本學(xué)者近藤のり所言,《檸檬》中的丸善,與破敗不堪的里街(京都是日本傳統(tǒng)文化的中心),實(shí)則分別是近代與前近代的縮影。但小說(shuō)中的丸善并非總店,而是1907年開(kāi)設(shè)的京都分店。當(dāng)時(shí)的大正人正處在西洋與日本的所謂新舊價(jià)值觀的對(duì)抗之中,人們苦于截然不同的兩種文化和歷史的交融與沖突之中,迫切需要某些方式來(lái)宣泄這種困惑與不安。
或許對(duì)于梶井來(lái)說(shuō),丸善就象征著近代日本資本主義的虛飾、文化的淺薄與虛偽。如何打破這種困境,以1923年關(guān)東大地震災(zāi)后重建為契機(jī),大正人仿佛找到了出路。在梶井的筆下,檸檬也充當(dāng)了這樣一個(gè)可以毀滅現(xiàn)實(shí)矛盾與不安的角色。據(jù)記載,檸檬種子是1875年4月由駐美國(guó)加州總領(lǐng)事高木三郎帶到日本的。③而檸檬在日本國(guó)內(nèi)的栽培事業(yè)直至明治末到大正初期才以廣島縣和和歌山縣為中心開(kāi)始,1919年,農(nóng)林省以廣島縣大長(zhǎng)地區(qū)(現(xiàn)在的豐町)為推廣中心,開(kāi)始獎(jiǎng)勵(lì)有計(jì)劃的實(shí)驗(yàn)性栽培。④由此可以推斷,梶井基次郎當(dāng)時(shí)所看到的檸檬有很大的可能是舶來(lái)品,而且在當(dāng)時(shí)算是高級(jí)水果,因?yàn)槿毡驹跒|戶內(nèi)海地區(qū)自行生產(chǎn)的檸檬才剛剛推出市場(chǎng)。而小說(shuō)中的“我”很明顯也意識(shí)到了這一點(diǎn),一邊想象著它的產(chǎn)地加利福尼亞,一邊回想學(xué)過(guò)的漢文文章《賣柑者言》。從這個(gè)角度出發(fā),筆者認(rèn)為小說(shuō)中的“檸檬”或許正象征著“現(xiàn)代”,是梶井筆下的能夠毀滅正在相互猛烈沖突著的近代與前近代的希望。隨著“檸檬爆彈”一聲響起,既宣告了“我”的反叛,也體現(xiàn)了“我”對(duì)自我價(jià)值回歸的渴望,展現(xiàn)的絕不是灰暗的自我放棄的呻吟,而是光明的破繭成蝶的壯烈斗志。⑤一部好的小說(shuō)是人性的廣泛體現(xiàn),梶井的作品能夠跨越世紀(jì)、經(jīng)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對(duì)于生的極致向往以及對(duì)于時(shí)代的無(wú)窮思考。
注釋:
①⑤盛莉:《符號(hào)學(xué)視角下梶井基次郎文學(xué)的“明”意識(shí)》,《芒種》2018年第6期,第71頁(yè),第72頁(yè)。
②李曉光:《惡作劇后的絕望——傾聽(tīng)〈檸檬〉的旋律》,《日語(yǔ)學(xué)習(xí)與研究》2001年第2期,第55頁(yè)。
③岡山県立図書館:レファレンス協(xié)同データベース。
https://crd.ndl.go.jp/reference/detail?page=ref_view&id=1000184920。
④明地柑尚:『レモン:良質(zhì)多収の國(guó)産栽培』,『農(nóng)山漁村文化協(xié)會(huì)』1989年,第11頁(yè)。
參考文獻(xiàn):
[1]明地柑尚.レモン:良質(zhì)多収の國(guó)産栽培[M].東京:農(nóng)山漁村文化協(xié)會(huì),1989.
[2]飛高隆夫.梶井基次郎『瀬山の話』考[J].(日)大妻國(guó)文,1991,(03).
[3]謝志宇.困惑、不安與矛盾——論小說(shuō)《檸檬》的主題思想[J].日本研究,1995,(03).
[4]李曉光.惡作劇后的絕望——傾聽(tīng)《檸檬》的旋律[J].日語(yǔ)學(xué)習(xí)與研究,2001,(02).
[5]小田桐弘子.梶井基次郎私観:レモンから檸檬へ[C].(日)兵庫(kù):大手前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部論集,2005.
[6]河原敬子.美的空間としての『檸檬』[A].奈良:奈良女子大學(xué)大學(xué)院,2011.
[7]近藤のり.梶井基次郎『檸檬』にみる近代と前近代[R].東京:日本女子大學(xué)大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科紀(jì)要,2017.
[8]盛莉.符號(hào)學(xué)視角下梶井基次郎文學(xué)的“明”意識(shí)[J].芒種,2018,(06).
作者簡(jiǎn)介:
歐陽(yáng)麗琴,女,漢族,江西吉安人,蘇州大學(xué)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guó)別與區(qū)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