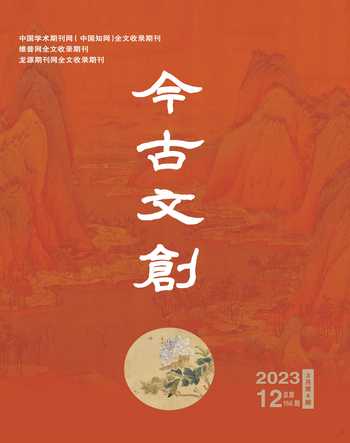古代中西方自傳文學的社會價值表達
【摘要】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語境下,中西自傳隱含不同的社會價值表達。以奧古斯丁《懺悔錄》為代表的古代西方自傳文學緣起于宗教,強調自我表達與社會意識的協同;以《史記·太史公自序》為代表的古代中國自傳文學的史傳形式,體現強社會價值表達與中式自我的塑造。從文化構成差異來說,前者以“人生而有罪”為原點對話上帝,實現神的救贖,突出人與神之間的倫理,表達社會價值;后者以“傳先王之道”為原點對話政治,實現自我塑造,突出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表達社會價值。
【關鍵詞】自傳文學;社會價值表達;《懺悔錄》;《史記·太史公自序》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3)12-0013-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04
自傳作為一種獨特的文體形式,在中西方文學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比較可以發現,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語境下,自傳文體產生的源頭明顯不同,也各自展現出不同的外傾性特征,隱含的社會價值表達令人矚目。
一、古代中西方自傳文學概述
(一)古代西方自傳文學:通過個體探求體現緣起宗教的社會價值表達
在西方文學史中,自傳文體的出現應該追溯到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作為西方文論的第一部自傳,《懺悔錄》給之后的自傳奠定了懺悔自白型自傳文體的基礎,成為宗教自傳的典范。
懺悔與宗教的關聯向上可以追溯至原始巫術與原始宗教,體系化則是依托基督教的“原罪”論,通過樹立“人生而有罪”的宗教觀念確立懺悔贖罪的宗教要求,基督教的懺悔制度由此誕生。奧古斯丁首先使懺悔這種宗教行為進入文學,從而誕生了《懺悔錄》和自傳文體。
隨著思想解放,懺悔自白的自傳文學形式隨后步入人文主義的道路,以盧梭創作的《懺悔錄》為代表的世俗自傳應運而生,此后自傳文學的主題由懺悔逐步走向自我揭露,向著自我探求的方向發展,即使這樣,也無法擺脫宗教帶來的強烈影響,這是一種宗教懺悔意識的時代體現。
縱觀古代西方自傳文學史,懺悔認罪的概念貫穿始終,這種從宗教緣起的社會道德價值觀通過自傳這樣的形式實現了個體化的具現,也反過來不斷補充發展集體意識下的價值表達。
(二)古代中國自傳文學:以史傳形式表現自我獨特性的社會價值表達
在中國傳統文學體系中,其實并不存在自傳這樣一個文體的概念,或者說中國古代的自傳與西方定義下的自傳概念并不匹配。因此,將中西自傳對比的前提是對“自傳”再定義,所謂自傳,“以個人的真實生活經歷為內容的作品即可稱為自傳,它強調的是自傳之‘自的反照功能和自傳之‘傳的真實性,是與虛構相對而言的”。[1]
在此定義下成篇成體例的可考自傳可以追溯到西漢武帝時期,代表性作品即為司馬遷所著《史記·太史公自序》。某種程度來說,它其實是史傳作品,由于在史傳之事歸于朝廷后,傳記型自傳文學陷入沒落,自傳自我表達、自我記錄的方式通過文賦、書信、自作墓志銘等別類文體得以延續。
然而當20世紀西方自傳文體傳至國內,宗教懺悔思想與中國傳統的自省精神相融合,誕生出新文學下的中國自傳,與古代自傳走上了幾乎截然不同的道路。
總而言之,古代中國自傳的史傳形式極大側重于表現個體的社會價值,并且史傳的極簡寫作風格也壓縮了個性的表現空間。可以說古代中國自傳從源頭就與西方自傳存在差距,是一種自我獨立性的社會價值表達,這與中國古代的歷史語境不無關系。
二、從奧古斯丁《懺悔錄》看自我表達與
社會意識的協同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是第一部以自我懺悔為寫作核心的長篇自傳作品,通篇寫滿“罪與罰”,對話“上與下(神與人)”,勾連“自我與社會”。
“一個人,受造物中渺小的一分子,愿意贊頌你;這人遍體帶著死亡,遍體帶著罪惡的證據。”[2]
從其“懺悔”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剖白:出生就身帶罪孽,連幼童都無法展現出完全的純真美好,明顯地體現基督教的“原罪”理念;青年時期與同伴偷梨無可救藥地犯下偷竊之罪,不是貪欲與食欲,而是為了享受作惡的樂趣,從根源體現出人類內心深處的原初之惡;之后沉迷占星術與摩尼教,更是自身難以辯解的無知和傲慢,遠離天主質疑上帝的詭辯曾讓他沾沾自喜,在懺悔中深刻認知到人類認知的有限內心卻潛藏無限的傲慢,本質上是走上了與天主背離的道路。
奧古斯丁的自傳,并沒有詳細描寫自己的生平事跡,更多地側重于內心思維的呈現。從基督教的視角來看,奧古斯丁嘗試通過內心思維的剖析,展現人自發的犯罪傾向,體現人本身不可逃避的原罪,從而進行完全的懺悔自白。
全書可以分為三個主題——人生反思、思想審查與天主贊美,讓我們依托作者的敘述軌跡追索其心路歷程和思想淵藪。
(一)人生反思:個體在接受集體道德準則下的自我內心探求
奧古斯丁將自己從出生到二十三歲母親過世的人生經歷進行了反芻,嚴厲地譴責了自己在未皈依天主之前的罪惡,帶有濃厚的宗教思想。
當然,奧古斯丁進行懺悔的自我之惡很多是宗教基礎下體現出來,這就體現出懺悔話語的獨特背景——特定的社會道德準則,[3]即基督教準則。懺悔的本質是個體通過放棄自我的獨特性以求得群體的接納和認同。與此同時,個體在接受集體準則的情況下進行自我探求,將不合準則的思維與個性進行自我摒棄,從而達成社會意識的一致性,這就是懺悔的過程。
在奧古斯丁的懺悔中,宗教思想呈現限制性的凸現,基督教觀念作為一種集體思維聚合,必然在作者書寫時留下社會性集體性的印記。可以說,在這種集體性壓制的境況下書寫的自傳,開啟了自我內心探索的先河,或者可以說,奧古斯丁為表達社會意識挖掘了新的表現形式——個體的內心體驗。
(二)思想審查:人神對話體的自我審查兼同社會價值審查
眾所周知,自傳的本質就是展現真實的自我,這種自我不僅僅是通過外在的事跡體現的,更多地指向一個人的內心,懺悔正是一種大膽袒露內心揭露自身罪惡的過程,可以說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懺悔錄》的自白是極其超前的,雖然不可避免地帶有宗教目的,但是奧古斯丁對于個體的自我認識高度可以說超乎尋常。因此,《懺悔錄》成為第一部以懺悔為表達中心的自傳文學展現出優越的特性。
奧古斯丁使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進行自我的挖掘,使得懺悔者(自己)與懺悔對象(上帝)建立起了一種相對私密的對話關系。這種個體性的“我——你”的對話關系使得自傳懺悔彰顯自我的價值傾向。
另外,從文學創作主觀愿望來說,作者的創作意愿本身就是一種對高遠精神個體的自我反饋,是在一個宗教的較高標準下進行自我的整理與再塑造。《懺悔錄》奠定的對話體形式承擔了使命,即在對主觀狀態思考下對客觀宗教價值進行思考,例如對自我罪惡源頭的探索,奧古斯丁指出“我們所以作惡的原因是因為自由意志,我們所以受苦的原因是出于你公正的審判。”[4]罪源自亞當夏娃憑依自由意志咽下的禁果,自由讓他們升起了對上帝準則的反抗,對上帝意識的懷疑,這種本質上違背天主的罪是宗教的。這樣的思想又是如何產生的?為何人類要違抗造物的天主?如果是被引誘,那么引誘的惡魔又是什么?
在延續自我反思審查之余,奧古斯丁對寫作時期的思想進行嚴格的反省,通過部分哲學與神學的自我論辯進行觀念上的自我革命。在對過去錯誤思維的懺悔中達成向天主更近一步的升華狀態,在奧古斯丁看來,自我認罪與懺悔是上帝的仁慈與指引,是神的救贖。
(三)天主贊美:在對神的完美贊頌下完成社會價值準則的形塑
“我只能向你請求,向你追尋,向你叩問:只有這樣,才會獲得,才能找到,才會給我打開門戶。”[5]奧古斯丁在對神的完美贊頌下沉思人自身的罪性,審查自我的罪惡從而達成個體的凈化。
在這里,奧古斯丁將思想上升到了哲學的態度。個人認為,作者陷入的沉思狀態其實體現出哲學思維與傳統神學思維的融合過程,如何用哲學的方式去理解神學,這是基督教發展的一個命題。“我”為何去作惡,因為人類存在無可逃避的原惡,是人類社會意識深層中蘊藏的難以理解也難以逃離的罪惡,“我”與人類同。
必然地,當對個人內在的思考深入到一定的程度,上升到人類集體意識狀態的思考,自傳懺悔文學對社會意識的表現就不僅僅是因為本身濃厚的宗教意識,更是由于自我審查自我重塑過程中對社會價值的再塑造。自傳懺悔話語含有的特定的價值準則,通過個人贊頌實現了社會化的認可與推廣,某種程度上是在一定的社會準則上塑造群體,懺悔自白者明面是自我貶低的“罪人”,其實更可能是樹立標桿的“先導者”。在社會普遍認可的準則基礎上,懺悔者通過對自身“罪惡”的揭發與悔改對社會準則再強化,將“舊我”釘在十字架上,由“新我”帶領他人前行。
三、《史記·太史公自序》強社會價值表達與
中式自我的塑造
古代中國自傳與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發源,主要是作為史傳的自序出現的,作者本身就是站在社會歷史的大視角下進行寫作,延續的是史傳的文體標準,并非西方的自傳體例,所以古代中國自傳的強社會性實屬情理之中。《史記·太史公自序》開創了自序型自傳的先河,這種自序下的自傳必然在強社會價值表達下的隱藏著自我,即著書時候的自我。
(一)從創作目的來說,自序是司馬遷個人價值理想的社會性價值表達
司馬氏家族有修史的傳統,修史的價值就是自身的人生價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貫穿于太史公一生的修史心境,不僅僅是對于一個小家而言,更是國家這一大家的成就。
對于史傳的價值,太史公以為,一是關乎自身與家族,二是關乎政治與國家,文中司馬遷引用董仲舒的觀點,說明《春秋》的史學價值——對世間兩百四十二年的時事進行是非評定,從而確定這世間的是非規則。《史記》作為仿效《春秋》之作,自然承接下來政治審查、道德塑造的社會責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雖然中西方自傳的源起不同,但兩者都是在固有社會價值存在的基礎上進行發展與演進的,這種擔負確認社會準則宣教社會價值的創作心理也許是相近的。
從司馬氏世代撰史,到父親司馬談的遺言相囑,司馬遷自身的意愿似乎被壓制了,一個典型的子承父業的形象被塑造起來,在這個狀態下什么才是司馬遷的自我?可以說古代中國自傳中很少出現全然的“個體自我”描寫,往往都是“社會自我”。這也與作者寫作時確定的自我身份是密不可分的,就像上文所述,司馬遷在創作時就是確定了“著書時期的自我”,[6]這樣一個背景,而這樣的自我很明顯是有限的,因為它與社會集體意識有著極大的重合。
司馬遷的個體本身獨特于世間,他選擇了一項特殊的事業,并為此不斷付出,正所謂“發憤著書”。這樣的自我也與前人同,孔子政治失意故著《春秋》,屈原放逐乃成《離騷》,前人都是歷盡艱辛,“意有所郁結”,因此將思想付諸筆下。相同或相似的人生經歷,使司馬遷在感同身受的同時,很容易進入相同的社會價值層面,與前人建立一種關聯,增強其通過著述不朽的自信。這個“自我”,是處身于傳統文化創造傳承中的“自我”。這樣的自我獨特性是與時代共性相融合,方才具有長久的生命力。因此,《史記·太史公自序》作為自傳有著強社會性價值表達,這樣的自傳所創造出的“自我”本身就是一個強社會性的“社會自我”,從本質上講是社會價值的濃縮個體,自然而然,史傳所要張揚的社會價值就顯得尤其突出。
(二)從創作方式來說,自序意欲表達個體存在不可忽視的社會價值
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主流思想體系源遠流長,影響深遠。在“傳先王之道,論圣人之言”社會價值體系下,“太史公自序”這種自傳形式的價值表達伴隨《史記》一起成為社會價值的一部分,甚至在自我塑造中成為價值標桿,豐富和發展社會價值觀念,這樣的中式自我塑造在許多可以被認為是自傳的文本中都有體現,例如曹操的《自明本志令》塑造的就是具有強烈權利意識與自尊態度的權臣形象;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表現出魏晉名士的風姿;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對閑適自在的生活追求……這些“自我”都有著極強的社會普世價值體現。
同時,“中國自傳文學的大部分作品由于受傳統的束縛較深,受社會種種因素的影響和局限,不僅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亦‘為自己諱,遮護隱私,掩蓋缺點”,[7]作者必然會清醒地認識到,隨著作品的流傳,本人的自訴必然會引發閱讀者的注視、思考、評判,行文的時候必然會有所考慮,從而對自傳的自我表達和思想進行適應于社會價值的轉換與適當的隱藏。
社會性的自我塑造是中式自傳的顯著特征,這是自序的一種創作方式,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延續與發展方式之一。社會價值需要不斷的擴充與發展,某些重要的生命個體堪當此任,古往今來,文人大家塑造一個個具有重要社會價值的“自我”, 以此為最高成就,也就達到了所謂的理想境界,從而證明自己的人生存在不可忽視的社會價值。
這種創作傾向對于社會價值塑造與發展有著很大的作用,也有助于個人價值個人身份的認知。當然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過于注重社會價值也是對內在自我的忽視,這也直接導致了古代中國自傳中自我的缺失,體現出強社會價值下個體意義被壓迫的社會狀態。
四、中西自傳文學不同寫作傾向的社會文化構成
差異分析
綜上所述,古代西方自傳文學以“人生而有罪”為原點對話上帝,實現神的救贖,表達社會價值;古代中國自傳文學以“傳先王之道”為原點對話政治,實現自我塑造,表達社會價值。
中西自傳文學的不同寫作傾向本身沒有合理性合規性的差別,只不過自傳這種文體成熟在西方的文化語境下,從而導致后代學者在考察這一文體時習慣將標準傾向西方。重要的是,要看到這種不同寫作傾向背后的社會文化構成差異。
西方自傳文學的寫作根源是宗教,即使后期從宗教自傳轉向世俗自傳后,宗教意識依舊表現明顯。西方文明中宗教的地位根深蒂固,融入在人們日常的一舉一動、一思一想中,而自傳這種自我闡發自我書寫的文體更容易體現作者本身的思想與價值觀念。
自從希伯來文化進入西方主題文化語境之后,基督教發展壯大,其中不乏社會動蕩后思想文化的斷層使得基督教更好地成為西方新的主文化,同時也是基督神學對于苦難大眾的精神救贖讓其在社會下層生根發芽。
文藝復興后,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反對現世腐朽的教會體系。可以說在西方社會中宗教意識與神學思維已經固化,成為了西方價值觀的一個部分,即使在時代的發展中宗教必然地出現了與社會狀態不匹配的問題,人們也多于將其轉化,使之適應新的時代變化,做到宗教意識的現世解釋。宗教意識構建了人與神之間的關聯,人為神所創,是神外化后誕生的個體,是損失了至善至美的個體,但依舊存在與神接近的可能。所以宗教思想本質上是個體的,是直接與神對話的思想,這種思想呈現方式使得其更加傾向于自我自身,也因此促進了自傳的產生發展。
在中國傳統價值體系中宗教思維式微,儒家思想以強勢的姿態融合各家,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正統。儒家思想的根本在于“仁”,代表一種人與人之間的親善狀態,是對社會倫理的一種規范。可以說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中國主流思想專注于社會整體的狀態體現,在這樣的價值體系下個體價值必然需要為社會價值避讓。
同時,奠基于此的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建造了強大的國家機器,“在強大的國家機器前面,個人的意志、感情和利益都是無足輕重的,這種對個性的壓制極大地限制了自我的發展,也從根本上取消了自傳的生存空間”。[8]
但是,古代中國自傳從另一個方向對自我與社會價值的關系進行闡發,作者將自我意識與個體價值融合成為社會集體的一部分,從而在更宏觀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中國文化源頭中就存在集體主義的根基,也必然從這種方向去對個體施加影響,從而誕生了與西方自傳不同的自傳形式。
當然,這種集體性也必然壓縮了文人士大夫對于自傳的創作欲望。西方價值觀中的個人主義為自傳這種文體的出現與發展提供了無比合適的土壤,強烈的個體主義必然會引導作家走上探求內心世界的自傳文學道路,而宗教意識只是為這樣的創作提供了合適的素材。除此之外,由于自我探究塑造出的“自我”暗合了社會大眾的價值體系,甚至能夠成為新的社會價值標識,這是自傳必然的社會表達。
反觀古代中式自傳,根本上說其本身就是在進行社會價值表達,古代的中國作者以自身展現社會意識,甚至擔當張揚社會價值的使者,所以與文人普遍的寫作沒有太大的區別,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自傳并不能被稱為自傳,這也許正是古代中國自傳沒有發展壯大的原因之一。
參考文獻:
[1][6]劉桂鑫,戴偉華.自我獨特性的展示——論漢晉自傳文學的特質與嬗變[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
[2][4][5]奧古斯丁.懺悔錄[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0,222,596.
[3]楊正潤.論懺悔錄與自傳[J].外國文學評論,2002,(4).
[7]張維.中西自傳文學比較談[J].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1).
[8]楊正潤.中國傳記的文化考察[J].廣東社會科學,2007,(3).
作者簡介:
馬兒骎骎,女,漢族,江蘇常熟人,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20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