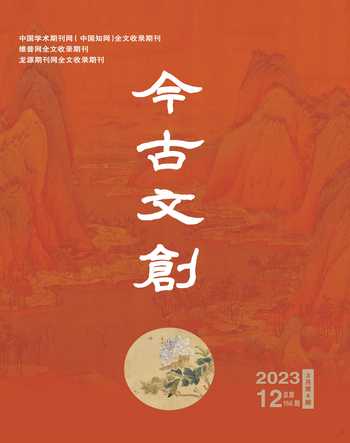莊子“言不盡意”對審美主體的影響研究
李加樂
【摘要】“言不盡意”是中國古代文論的一個重要命題。莊子雖不完全否定語言對于表情達意的社會功用,但仍把其作為破壞生命或事物本真的形式,遂提出“得魚忘筌,得意忘言”。這一論述對審美主體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言不盡意”在不同時期的異化和發展,審美主體對審美對象的獨特思考與啟發,以及文學接受在“言不盡意”下的復雜性和多樣化。
【關鍵詞】言不盡意;審美主體;創作;接受
【中圖分類號】I712?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3)12-0032-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12.010
語言作為一種交流表達的工具,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言”終究是人這一主體所利用以達“意”的形式,在言意相互轉換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其存在的局限,進而提出“言不盡意”的重要論點。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可見人的思維活動和意識流變是相當靈活的。基于此,“言”當如何表達審美主體的“意”成了一大難題。歷代文人包括現今諸多文學家、批評家雖提出各種理論,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本文將貫徹“以人為本”的重要原則,站在審美主體的立場,探討莊子“言不盡意”文論思想下歷代文人的思考與摸索,以及對審美主體的創作、接受的影響。
一、莊子的言意觀
“言”與“意”的關系無論在何種時期、何種狀況下都是存在分歧的,而言意關系無非就是“言能盡意”與“言不盡意”兩種情況。通常來說,儒家是前者的代表,孔子說“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認為“言”是可以傳達人的心志的。至于后者,莊子有一個著名論述:“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莊子·天道》),即“得筌忘魚”“得意忘言”。在莊子看來,“言”是不可能盡“意”的,誠如老子所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五十六章),老子強調一種“不言之教”(四十五章),其實本質上和莊子思想是相通的。
不可否認的是,莊子的言意觀與其“道”的思想及其音樂美學觀同根同源。莊子認為“道”是“無有”的,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的處于朦朧混沌下的虛無狀態,這是不可言說的,是難以名狀的。正是因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四十二章),它是流動變化的,是不斷滋長的,故而人總是不可能“一言以蔽之”。由“道”及“意”,“意”是審美主體對審美對象的獨特審美體驗,是形而上的。而“言”是較為具體的、客觀的物質狀態,故以具體語言去描述抽象概念,本身就是一種不對等的交流活動。
其實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不論是老子,還是莊子,他們都是主張“絕學”“棄智”,排斥一切藝術。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莊子則說:“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他們真的要毀滅一切藝術嗎?實際上不是,他們想毀滅的是那些人為造作的藝術,追求的是天然的藝術。對文學的要求也是這樣。[1]這就類似于老子的“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和莊子《齊物論》中“人籟”“地籟”“天籟”不謀而合。
綜上所述,莊子本質上并不排斥“言”的社會功用,而是注重強調一種“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的純粹的、自然的、無刻意雕琢的言語觀,但“意”雖可通過言語表達,“言”卻不可盡“意”。這是因為一則“書不過語”,語不過意,語言文字不能像照相機般將客觀的人物攝成影片;二是自然及人生之寫成文學,要通過作者的觀察與炮制,而觀察與炮制都有主觀的成分在內。[2]
二、創作主體的獨特思考
既然“言”是不可盡“意”的,那么創作主體又該如何面對這種言意關系所帶來的困境呢?其實在歷代文人創作的過程中,也發現了這一難題,同時提出了作家個體的創作觀念。
例如,漢代的司馬相如提出了“賦家之心”說,他說:“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其傳也。”[3]所謂“賦家之心”,即創作主體的意志,它是遼遠廣闊的,包攬萬事萬物,是作家內心的特有審美體驗,是不可傳與他人的。所以“言”在這種條件下就失去了其傳“意”之功能,所以作者“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齊梁時期劉勰苦于“言不盡意”和“言征實而難巧”而受到啟發,進而提出“義主文外”“文外之重旨”的原理。這都是在“言不盡意”下創作主體的思考與行為,“意”如此桀驁不馴,那么索性在創作時“不言”“無言”,故而形成更加廣闊的審美空間。在中國歷代以來,這樣的創作思維大體可分為兩類:即“意境”與“典型”。
(一)“意境”
一般來說,語言不能完全地達意,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一個優點。因為它能充分運用語言的暗示性,喚起讀者的聯想,讓讀者自己去體會那“象外之象”,去咀嚼那字句之外雋永深長的情思和意趣,以達到“言有盡而意無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效果。[4]
語言本身存在一定的狹隘性,那么創作主體在面臨創作時,何不充分利用這一缺陷,化被動為主動呢?其實古人早已認識到了這一點,“意境”說就是作家在面對言意關系時反客為主的具體體現。語言能夠表達的東西甚是有限,這就要求創作者能夠“以少總多”,寓無限于有限。
在中國歷代文人創作中,也十分重視語言藝術的高度概括性。鐘嶸的“滋味說”,王昌齡的意境論、皎然的情境論、劉禹錫的境外生象論、司空圖的思與境偕和四外說,以及嚴羽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其實都著力于以最少的言語去勾勒出遼遠雄渾的意境。語言可能是有限的,但是語言背后的“境外之境”“象外之象”卻是無窮無盡的,審美主體因而能將神思馳騁于四海,把心境游離于宇外。司空圖在《與李生論詩書》和《與極浦書》中提到,詩歌應注重“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即“四外說”。仔細揣摩不難發現,司空圖極言所在,是一種超越語言界限的不可究詰的“味道”,而并不流于語言文字層面的意義與形象。意境正是這樣虛虛實實,言在意外的獨特審美感受。
當然,這種意境的建構離不開審美主體對于審美客體的實踐與觀察,沒有經歷和體驗,創作者不可能憑空捏造所謂的意境。沒有細致入微的發現和感觸,接受者不可能跳出語言的藩籬,甚至會陷于“咬文嚼字”的泥潭之中。故王夫之說道:“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即極寫大景,如‘陰晴眾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在“言不盡意”的言意關系矛盾下,“意境”顯然是一劑良藥,但是能否健康創作與接受,主要的問題還是在于創作者自身的條件,以及接受者內在的涵養。
(二)“典型”
如果說“意境”是“無言”的狀態,那么“典型”即是“立片言而居要”(《文賦》)。值得注意的是,此處所言“典型”非西方文論中的“典型論”。客觀世界是紛繁雜亂的,諸多事物體態萬千,各有不同,很難用語言對其下確切的定論。當語言作為言說者日常生活中一般意愿的表達方式時,它是有效的,旁人可以通過它而明了說者的意思。然而當語言作為對世界復雜性的表現方式時,它卻往往是無效的,因為它不可能窮盡這種復雜性。在它呈現了事物的某種性質時,總是同時遮蔽了另外一些性質。[5]因此,為了在“言不盡意”下完成創作主體的主觀需求,甚至是為了滿足世人對某一事物的約定俗成的想法與認知,人們遂以“典型”之物來表示該“物系”。例如,將“落花”視為悲涼之“典型”物象,那么在“花謝花飛花滿天”“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小園花亂飛”中,“落花”顯然就寄寓了創作者無限的哀思在其中。而運用這種物象作為自己的話語,創作者是有意識的,由于前人留下的傳統,抑或是讀者有這樣的認知,創作者利用這種通識性的物象,便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即自己的“意”。
總的說來,“典型”是具有普遍認知度的現象,它是傳統性的,久而久之或不知不覺下創作者共同的約束和規范。它雖然在語言的表述范圍之內,但是語言在本質上只是表示那一般的普遍觀念;而人們所指謂的東西卻是特殊者、個別者。因此人們對于自己所指謂的東西,是不能在語言中來說的。[6]因此,創作者在運用這種靈活性的規矩時,也許并無他意,但是讀者在接受時,往往能夠讀出更加豐富的東西。
此外,有的創作者也看到了這種豐富性,從而創作出具有朦朧,多義的作品。這都是“言不盡意”對讀者的啟發,也正是因為“言”不能盡“意”,才使得“意”愈加具有自我超越性。從這個層面來講,“言不盡意”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三、“言不盡意”下的文學接受
在文學接受的價值或意義系統中,基于在莊子“言不盡意”情境下,因此,下文主要從文學作品的審美屬性和交流屬性展開論述。
我們都有這樣的閱讀經驗,讀到某部文學作品時,我們往往被作品優美的語言或生動的描寫吸引,為作品飽含濃郁詩情的故事情節、人物或意境所感染,為作品深邃的思想意蘊所折服,總之,我們進到了文學作品所創造的那個充滿詩情畫意的藝術世界,從而發生某種情緒上的反應。或快適、或欣喜、或憤怒、或悲哀、或驚駭、或振奮……總之,我們是被感動了。[7]讀者之所以被感動,是由于與創作主體筆下的某些“言”產生了共鳴,或是在作者之“意”中流連忘返,又或是在作者“言”“意”之外,產生了屬于讀者自身的言意接受系統。“言”若是盡“意”,那么“言”停即“意”止,讀者很難再去聯想到言外之意。鐘嶸《詩品序》中言:“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興,即有限的文字傳達著無盡的意蘊。恰恰是“言”不可盡“意”,讀者才得以無窮的回味,是故人們常言“每一次閱讀都是一次新的體驗”,原因就在于此。因此,作者在閱讀某一部作品時,才會衍生出各種新義。在審視某一作家作品時,由于評論者之間以及評論者與作品之間的文化差異、時代環境等諸多不同,故而多方言辭難以統一。具體體現為讀者的二度創作和評論者對作品復雜的批評。
(一)二度創作的多樣性
眾所周知,人是社會性的人。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主體都不是封閉和孤立的,他們應該是開放和交流的,而遵循何種法則進行精神、藝術交流則是馬克思主義的“藝術生產”理論所關心的核心。實際上,馬克思已經看到,文學接受不應該是孤獨地闡釋自己(不論是作者還是讀者)的立場,而是社會性的交流實踐。[8]因此作者在用語言表達自身的人生經驗、社會認識時,總是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和個體的烙印。
在文學接受活動中,由于讀者所處的時代、民族的不同,生活經歷、文化教養、思想性格、興趣愛好以及欣賞心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審美傾向、欣賞能力和價值觀念,從而導致了讀者對作者之“言”的內容、格調以及欣賞的深廣程度產生極大的差異。
例如,杜甫的一首《登高》中“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短短14個字,對于當時的杜甫而言,也許只是表達自己的漂泊離愁之苦。但是在后人不斷地挖掘與反思中,這一千古名句便具有了八重意蘊,可能作者本人都不具備這樣的認知。而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是讀者對杜甫的認知程度不同,對杜甫人生的切入點不一致,研究出的成果自然難以統一,故自身思維意識存在強烈差異;其二,杜甫所處的時代,后人即使有相同的境遇,但是終不可再次復制,因而歷史環境相去甚遠,以今世的論前世,最終結論不一在所難免。這就好比鐘嶸所提出的“味之者無極”,強調作品帶給讀者獨特的審美感受,即作品的審美愉悅效果。文學作品若要帶給讀者獨特審美效果,文字卻又是有限的,固定的,唯有“意”是無窮的。文章的“意”隱藏在文字的背后,有著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因而解讀本身就會有障礙。在這種情況下,讀者二度創作之“意”和作者本意也就相去甚遠。
但是不可否認,在語言的規范和體系內,讀者之意同樣是難能可貴的、有意義有價值的。德國接受美學理論家伊瑟爾指出,文學文本是一個不確定的“召喚結構”。它召喚讀者在其可能的范圍內充分發揮再創造的才能,去豐富、補充文本,這種無邊際的讀者發揮更是增加了文學文本的不確定性。因此,語言則更加難以確切地表達出某一種特定的“意”。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因為“言不盡意”,讀者也才重新獲得了更加廣闊的思維活動空間,作者用創作發泄自我,讀者則通過閱讀啟迪自身。每種藝術都用一種媒介,都有一個規范,駕馭媒介和遷就規范時都有若干困難。但是藝術的樂趣就在于征服這種困難之外還有余裕,還能帶幾分游戲態度任意縱橫揮掃,使作品顯得逸趣橫生。這是限制中的自由,由規范中溢出的生氣,藝術使人留戀的也就在此。[9]在語言本身的解讀下讀者存在著超越文本的“自由”,能夠容納讀者的情思,能夠脫離作者的束縛,能夠擺脫一切桎梏,這就是作者的文字下讀者的創作空間。所以我們常說“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萊特”,其實就是因為言不能盡其意而造成的語言意蘊多樣化的現象,它給了讀者更多的審美體驗、更豐厚的審美感受。因而“言不盡意”下讀者的接受是更為深刻、更為具體的作品再次創造。
(二)文學批評的復雜性
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覺的而不是理論的,是詩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點式的而不是整體式的。[10]從這一角度來看,文學批評是極其復雜,難以下定論的。有文學作品就會有文學接受,那么隨即就會產生文學批評。文學作品誕生后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反響,如謾罵或者贊譽,都是一種文學批評。巴爾扎克說過:“作家沒有決心遭受批評界的火力就不該動筆寫作,正如出門的人不應該期望永遠不會刮風落雨一樣。”由此可知,批評是激烈的、復雜的。那么,為何會產生如此多樣復雜的批評現象?下文將從其與“言不盡意”之關系進行闡述。
文學批評與“言不盡意”的關系密切,其可以從現實現象的層面來理解,“言”好比是客觀存在之文學現象,“意”有如主觀能動之批評闡釋。
首先,文學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文學接受,因而批評者也是特殊的讀者。不同的是,普通讀者可以根據自身的興趣愛好,根據以往的閱讀經驗,對文學作品予以個人的、隨性的評價。而批評家作為文學批評的主體,他們接受過專門的批評訓練,文學理論知識深厚,文學批評經驗豐富,還擁有精準敏銳的文學感悟力。[11]但不論是普通讀者或是批評家,都離不開對特定語言的挖掘,否則其主觀批評之“意”便無從談起。
其次,“言不盡意”產生的“意”的朦朧化,也使得批評者由于批評角度不同而對同一作家作品褒貶不一。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如林紓譯注外國經典作品,以傳統文言譯外文,前所未有,也就意味著其在不同時期他所受到的文人學者的批評也大相徑庭。20世紀,很多人都譏諷他這種以東方語言的“套子”去闡釋西方的文學作品內涵的行為,但是后來,隨著人們對傳統文化自信的不斷增強,批判的風聲又日漸消減。那么,對于同一作家為何會有這樣的評判差異呢?那自然與批評者自身的審美要求,評判原則難脫干系。
文學批評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接受雖然具有其相對意義上的客觀性,但總的說來,在批評活動中,批評家仍是具有一定主體傾向性的。如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一經發表引起的兩派截然不同的評判,維護黑奴制的一派大力貶低其價值,而主張廢除黑奴制的一派則高度贊揚此書,從而引發著名的美國南北戰爭。而造成以上文學現象的原因,從根本上來講,即是不同時期、不同階級、不同立場上的人對同一文學作品的批評不同而產生的分歧。簡而言之,則是不同批評家對客觀之“言”的主觀傾向性評判難以調和。
由此可見,對于同一“言”,會引發多種不同的闡釋,同一作家,也會產生不同的評判標準。但是總的來說,文學批評主要受三個方面因素的制約:首先,文學批評的標準受到文學發展狀況的制約。其次,還受到意識形態、審美趣味的制約。再次,也受到作家、批評家、作者的社會理想和審美觀的制約。另外,隨著“言”和“意”內涵的流變,批評與接受會面臨更加復雜的境遇。最后,對于文學批評的道路,“只有疑難的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
四、結語
歷代詩人作者對于“言不盡意”皆有不同的態度和認知,反之,“言不盡意”這一重要思想也影響著作者的創作,讀者的接受,批評家的評論。正是因為“言不盡意”,才一次次的啟發著創作者不斷提出新的詩論、文論觀,更是推動著作家創作,引導著讀者閱讀,促進文學批評的多元發展。同時,“意”的厚重豐韻,“言”的多義朦朧,給讀者帶來更深刻的審美體驗,也給批評家創造了多樣的評論角度和空間,推動著文學批評向更加全面、深刻的道路發展。
參考文獻:
[1]童慶炳.中國古代詩學與美學[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
[2]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3]張少康,盧永璘.先秦兩漢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
[4]曹順慶.中西比較詩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5]李春青.中國文學批評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6]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M].賀麟,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
[7]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8]閻嘉.文學理論基礎[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
[9]朱光潛.詩論[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
[10]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1] 曹順慶.文學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