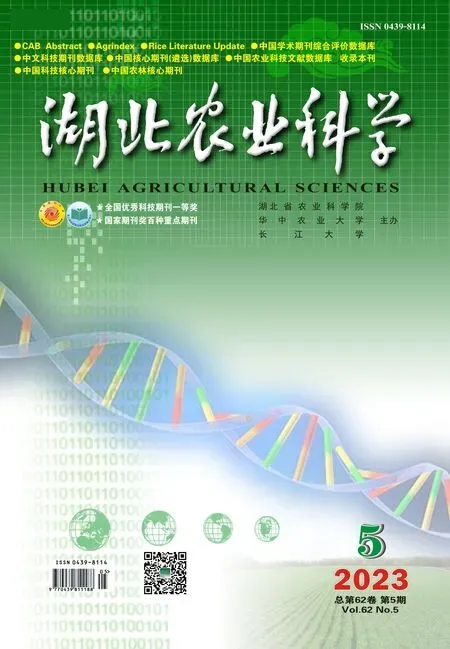山地城市農村居民點時空格局演變與分異特征
——以重慶市為例
江汶靜,劉 燕,張 維,劉 明,何匯域
(重慶市規劃和自然資源調查監測院/自然資源部土地利用重點實驗室重慶研究中心,重慶 400120)
農村居民點是鄉村人口的主要聚居場所,也是鄉村地區國土空間格局、景觀格局的重要構成。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農村居民點用地不減反增[1],亂占耕地、空心村問題凸顯,農村居民點空間格局也俞加多樣化、復雜化[2]。農村居民點格局演變特征與驅動因素一直是地理學、景觀生態學、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研究熱點與焦點,開展農村居民點格局研究對指導農村居民點布局優化、改善鄉村環境、促進鄉村振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以往研究來看,對農村居民點格局特征的研究多從規模特征、分布特征以及形態特征3 個方面加以論述,尺度上多聚焦縣域和鎮域尺度[3]或都市邊緣區[4]、快速城鎮化地區[5]、高山貧困區[6]、低山丘陵區[7]、喀斯特地區[8]、干旱區[9]、糧食主產區[10]等熱點地區,而其數量多、規模小、分布零散也是研究尺度難以擴大的原因之一,且大尺度的研究多采用遙感影像數據,存在精度不高的問題;對農村居民點格局演變驅動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經濟、交通、水源、海拔、坡度等因素[11-15],對政策因素的量化研究較少。重慶集“大山區、大庫區、大城市、大農村”為一體,是著名的“山城”,其農村居民點景觀是中國山地景觀的特色組成部分。目前對重慶市農村居民點格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縣域、鎮域和村域尺度,縣域尺度層面有萬州區[16]、北碚區[17]、兩江新區[4]等,鎮域尺度層面有合川區大石鎮、忠縣拔山鎮和秀山縣梅江鎮[18]等,村域尺度層面有石柱縣冷水鎮八龍村[19]、石柱縣臨溪鎮前進村[20]、潼南區崇龕鎮古泥村[21]等,同時也包括低山丘陵區[18]、都市邊緣區[4]等熱點區域。在中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指引下,對大區域、大環境的整體協調研究有助于宏觀調配資源,便于從整體上對空間布局進行把握。因此,本研究利用GIS 技術和景觀生態學方法分析研究區域2009—2018 年的農村居民點規模、分布和形態特征,揭示其近10 年來農村居民點格局演化特征及其空間異質性,以彌補當前在山地城市、省域尺度的研究不足,且采用的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具有更高的研究精度,以期為國土空間格局優化和鄉村地區整體規劃研究提供參考。
1 研究區域概況與數據來源
1.1 研究區域概況
重慶市地處青藏高原與長江中下游平原的過渡地帶、四川盆地東部,下轄38 個區(縣、自治縣),轄區東西長470 km,南北寬450 km,幅員面積8.24 萬km2,地勢東高西低,分為西部方山丘陵區、中部平行嶺谷區和盆周山地區,山地占比72%,2007 年被批準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集“大山區、大農村”于一體,以重慶市為案例研究山區農村居民點特征具有典型代表性。2018 年,全市有行政村8 031 個、居委會3 128 個,農業人口1 747.92 萬人,占比為51.35%,農村人口密度從2009 年的282人/km2減少到2018 年的212 人/km2。2018 全市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為3 602.59 km2,占全域總面積的4.37%、占建設用地面積的52.02%,人均農村居民點用地206.11 m2,比全國最高標準高37.33%。
1.2 數據來源
采用重慶市2009—2018 年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和重慶市2010—2019 年統計年鑒數據。因變更調查的農村居民點圖斑存在一塊圖斑被分割成多塊的情況,因此對接邊的圖斑進行了融合處理后再進行相關分析。
2 研究方法
景觀生態學注重空間異質性和空間格局的研究,在土地利用、環境和自然保護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較好的研究效果[22],GIS 技術在空間格局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景觀格局指數、空間關聯指數、核密度、空間變差函數開展農村居民點空間格局分析。
2.1 農村居民點規模特征研究
規模特征主要研究斑塊規模特征和規模空間關聯性。根據斑塊面積大小,斑塊分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5,10,23,24],但分級標準不一。本研究采用斑塊個數(NP)、斑塊總面積(CA)、平均斑塊面積(MPS)、斑塊面積標準差(PSSD)、最大斑塊指數(LPI)、斑塊所占景觀面積比例(PLAND)來反映農村居民點斑塊的規模特征,并采用Moran’s I 指數來測度農村居民點規模的空間相關性和集聚性。全局Moran’s I 主要衡量空間關聯性的總體程度;局域Moran’s I 主要反映不同空間位置的離散性,反映居民點規模與其周邊單元的相關程度。根據空間相關性Moran’s I,可分為HH、HL、LH、LL 共4 個象限[25]。Moran’s I指數公式如下。
式中,n為斑塊數量;xi、xj為要素值;wij為空間權重;xˉ為平均數;Si為方差。I′為全局Moran’s I 指數值,取值為-1~1,越接近-1 差異越大,越接近1 關系越密切,接近0 表示不相關;I*為局域Moran’s I 指數值,I*為正,表示要素具有包含同樣高或同樣低的屬性值的鄰近要素,該要素是聚類的一部分,I*為負,表示要素具有包含不同值的鄰近要素,該要素是異常值。Z為檢驗值,Z 為正且顯著,表明i的測度值為高值集聚,反之為低值集聚;E為數學期望值,VAR為方差。
2.2 農村居民點空間分布特征研究
常用斑塊的空間分布情況來反映斑塊的集聚程度,根據斑塊聚集程度可以分為密集區、較密集區、較稀疏區、稀疏區和極稀疏區5 種類型[26]。根據其空間上的聚集分布特征可以開展區位分布特征[27-29]、區域分布特征[30,31]等研究,核密度估計法也在其中得到廣泛應用[9]。本研究主要采用平均最臨近距離(MNN)、平均最鄰近指數(MPI)、斑塊密度(PD)來反映斑塊聚集特征,采用核密度與地形地貌、河流相關關系來反映空間分布特征。
1)平均最鄰近指數(MPI)。MPI 是通過測度要素質心間的平均距離與期望的平均距離的比值來反映要素之間的集聚程度。MPI 小于1,模式為聚類;MPI 大于1,模式趨向于擴散;MPI 趨于1,模式為隨機。其計算公示如下。
式中,M為平均最鄰近指數;L為平均最臨近距離;N為全域的圖斑總數量;hij為要素間的歐式距離。
2)核密度。核密度可以反映要素在其周圍鄰域中的密度,以此反映農村居民點分布密度情況,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f為核密度;h為帶寬;k為核密度函數;x-xi為斑塊x到xi的距離。本研究以1.5 km 為搜索半徑,開展核密度分析。
2.3 農村居民點形態特征研究
形態特征研究主要揭示農村居民點用地斑塊形狀的規則程度和形態上的空間相關性與變異性。本研究主要采用斑塊形狀指數(LSI)、平均斑塊形狀指數(MSI)、斑塊分維數(PAFRAC)和面積加權平均斑塊分維數(AWMPFD)來反映斑塊形態特征,采用變差函數模型來反映空間上的形態分布特征。
1)平均斑塊形狀指數(MSI)。MSI 可以反映農村居民點矢量斑塊的復雜程度,MSI 越大,形狀越不規則、邊界曲折度越大。本研究以正方形為標準進行測度,其計算公式如下。
2)面積加權平均斑塊分維數(AWMPFD)。AWMPFD 可以反映斑塊的不規則程度和破碎程度,分維數越大,斑塊形狀越不規則、越破碎,其計算公式如下。
3)空間半變異函數[γ(h)]。γ(h)反映屬性空間分布的隨機性與結構性,展現其空間異質性,其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xi表示某一點;xi+h為相距h的另一點;Z(xi)和Z(xi+h)表示該點空間位置上的測度值。
3 結果與分析
3.1 規模特征
3.1.1 農村居民點總體呈收縮態勢,數量與規模呈負相關 從農村居民點規模變化(表1)可以看出,2009—2018 年全市農村居民點除數量有增加外,其余指標均呈減少趨勢,表明10 年來的農村居民點總體呈收縮發展態勢,這主要是受到城鎮化發展的影響,原來的城郊農村地區逐步被城市化。10 年來用地規模并非呈持續遞減趨勢,2015 年以前呈穩步遞減態勢,2016 年出現增加后呈小幅遞減趨勢,其減小幅度小于2015 年以前的減小幅度(圖1);2016 年全市農村居民點出現增加主要是因為重慶市為摸清全市農村居民點現狀,利用高精度影像對全市農村居民點進行了補充調查,彌補了過去因為“二調”影像不清晰所造成的解譯誤差。區域上,2009—2018年重慶市中心城區各區縣的農村居民點規模均呈減小趨勢,其他區縣多呈數量增加、面積減少態勢(表2),由此可以看出,全市的農村居民點呈現出“減少成片、增加零星”的特征。

圖1 重慶市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變化趨勢

表1 2009—2018 年重慶市農村居民點規模分析

表2 2009—2018 年各行政區NP 和CA 變化情況
3.1.2 斑塊規模差異減小,微型居民點為主 根據MPS、PSSD、LPI、PLAND 指標,居民點的收縮發展態勢不僅體現在總規模上,也體現在單個斑塊規模上,平均斑塊面積、最大斑塊指數均減小(表1),斑塊間的規模差異也在逐漸縮小。通過對斑塊規模進行分級(圖2),全市總體呈大散居分布特征,全市近1/2的斑塊規模在0.1 hm2以下,在0.2 hm2以下的斑塊數量約占3/4,斑塊規模與斑塊數量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按照杜國明等[23]的規模分級標準,重慶市主要為微型居民點,且通過對比NP、CA、MPS 指標可知,新增的居民點也主要為微型居民點。

圖2 2018 年重慶市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頻率
3.1.3 農村居民點規模的總體空間關聯性有所減弱,但局部仍有高度空間關聯性 利用Moran’s I 測算農村居民點規模的空間關聯性,從測算結果可知,農村居民點規模之間存在空間關聯性,但10 年來的空間關聯性格局變化不明顯。鄉鎮間居民點規模的空間關聯性大于斑塊間的空間關聯性,2018 年的Moran’s I 指數略小于2009 年(表3),表明農村居民點規模的空間關聯性有所減弱。進一步通過局域Moran’s I 分析,全市鄉鎮級農村居民點規模主要呈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2 種類型,其中,高-高集聚型主要分布在重慶西部方山丘陵區,中部平行嶺谷區的江津、永川、璧山、涪陵、開州等地,盆周山地的云陽、奉節;高-低集聚型主要分布在渝北、長壽、墊江、梁平、忠縣等中部平行嶺谷區(圖3)。對比重慶市地形地貌分布,該區域地勢平坦,自然地理條件優越,易產生農村居民點。

圖3 2009 年(a)和2018 年(b)農村居民點規模局部空間自相關

表3 2009 年、2018 年的鄉鎮級和斑塊級Moran’s I指數
3.2 空間分布特征
3.2.1 局部呈集中、聚集趨勢 PD 反映了居民點的空間分布,MNN 和MPI 反映了居民點的空間臨近程度,從MNN、MPI、PD 分析可知,10 年來農村居民點斑塊間平均最臨近距離和平均最臨近指數減小,單位面積內的農村居民點斑塊數量增加(表4),表明空間分布上呈局部集中、聚集趨勢。

表4 2009—2018 年重慶市農村居民點集聚、形態特征分析
3.2.2 空間上呈西密東疏的分布格局,高密度區擴張 根據核密度分析結果可知(圖4),重慶市農村居民點總體呈西密東疏的空間分布格局,密集區域空間分布差異顯著,居民點集聚區主要分布在重慶市地勢平坦的西部方山丘陵區和中部平行嶺谷區。10年來,全市核密度高值區(>40 個/km2)數量顯著增加,呈“由點到面”的趨勢,核密度最高值由59 個/km2增加到66 個/km2,渝西和渝東北片區高值區的規模逐漸擴大,其中潼南-銅梁-大足-榮昌4 個橋頭堡城市、璧山、北碚、萬州-開州-云陽、梁平-墊江的核規模擴大明顯;永川區何埂鎮-吉安鎮-仙龍鎮、綦江區東溪鎮-扶歡鎮-趕水鎮逐步形成新的核密度高值區;渝東南片區的低密度區(0~10 個/km2)也擴張為中低密度區(11~20 個/km2);渝東北沿長江走向兩岸為居民點高密度區;總體向集聚發展。

圖4 2009 年(a)和2018 年(b)重慶市農村居民點核密度分布
3.2.3 斑塊分布地形地貌影響較大,長江一二級河流影響不顯著 通過海拔分級與居民點分布的疊加,得到不同高程下的居民點分布情況。由表5 可知,居民點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區域,其規模與數量均隨海拔的增加而減少,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但2009—2018 年,海拔0~500 m 的居民點數量和規模均略有減少,其他海拔高度的居民點數量和規模均有增加;低海拔區域居民點分布減少主要是因為城鎮化的發展導致城市建設占用了大量的城郊農村居民點。雖然全市農村居民點分布格局與長江流向存在一致性,但通過對長江一二級河流的緩沖區分析結果與居民點分布的疊加可知,農村居民點分布隨距離一二級河流越遠占比逐步降低,但全市大比例的農村居民點仍分布在距離長江一二級河流5 000 m以外,長江一二級河流對農村居民點分布影響并不顯著;2009—2018 年農村居民點與河流距離關系未發生明顯變化。

表5 2009—2018 年農村居民點在不同高程和河流間距的分布情況
3.3 形態特征
3.3.1 斑塊形態不規則度增加,農村居民點建設隨意性明顯 從反映斑塊形態特征的指標看,全市農村居民點LSI 增加,但MSI 減小(表4),表明農村居民點的斑塊邊界形狀不規則程度增加,邊界曲折度增加,這是由于10 年來斑塊數量增加,導致MSI 減小。從PAFRAC 和AWMPFD 可知,10 年來的農村居民點形狀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但分維數均大于1,呈現出形狀的不規則發展狀態,說明全市的農村居民點未得到很好的規劃,農房建設盲目性、隨意性較強,因此表現出形狀上的不規則。
3.3.2 斑塊形態空間差異性明顯,與斑塊規模和集聚度分布特征高度相關 對各鄉鎮LSI 開展變差函數分析,根據分析結果可知,重慶市農村居民點形態空間差異明顯,且10 年來的形態指數變化有擴大趨勢,總體表現為以地勢平坦的西部丘陵山區和中部平行嶺谷區為高值區,盆周山地區為低值區,其中又以江津-永川-綦江、潼南-合川、開州-云陽-奉節以及涪陵等區域的農村居民點形態不規則特征更為突出(圖5)。以全市LSI 分布特征對比核密度分布特征和規模分布特征,三者呈高度相關性,即農村居民點分布越集中的區域也是居民點形態越不規則的區域。

圖5 2009 年(a)和2018 年(b)重慶市農村居民點斑塊形狀指數分布
4 小結
1)從規模上看,2009—2018 年全市農村居民點數量逐步增加、規模逐步減小,二者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其中中心城區各區縣規模、數量均減少,其他區縣主要呈數量增加、規模減小趨勢,呈現出“成片減少、零星增加”的特征。斑塊間規模差異減小,以微型居民點為主,其中近1/2 的斑塊規模在0.1 hm2以下,在0.2 hm2以下的斑塊數量約占3/4,總體呈“大散居”分布特征。從農村居民點規模的空間關聯性來看,全市農村居民點規模的總體空間關聯性有所減弱,但局部仍有高度空間關聯性,主要呈現出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2 種類型。
2)從空間分布上看,全市農村居民點分布的總體格局未發生明顯變化,呈西密東疏分布格局;2009—2018 年核密度高值區的規模、數量增加,局部呈小聚居分布特征。從斑塊分布與地形地貌、河流的相關關系分析可知,居民點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區域,其規模與數量均隨海拔的增加而減少,呈明顯的負相關關系;雖然居民點規模、數量分布隨著長江一二級河流距離增加而減少,但長江一二級河流對農村居民點分布影響并不顯著。2009—2018 年,受城鎮化建設的影響,海拔0~500 m 的居民點數量和規模略有減少,其他海拔高度的居民點數量和規模均略有增加;但與河流距離關系未發生明顯變化。
3)從形態特征上看,全市農村居民點LSI 增加,表明斑塊邊界曲折度增加,形態愈加不規則,說明全市的農村居民點未得到很好的規劃,農房建設盲目性、隨意性較強。從變差函數分析可知,農村居民點LSI 分布存在空間差異性,西部丘陵山區和中部平行嶺谷區為高值區,盆周山地區為低值區,江津-永川-綦江、潼南-合川、開州-云陽-奉節以及涪陵等區域的農村居民點形態不規則特征尤為突出;而LSI 指數的分布與全市農村居民點的規模、密度分布特征呈現出相關性。
本研究以10 年為研究跨度,初步摸清了重慶市農村居民點時空格局演變總體特征,對調整和優化農村居民點布局,推進山地地區的鄉村振興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還可進行更長時間跨度的研究,摸清更長時序的演變規律。此外,本研究對農村居民點演變的驅動力分析還不足,還需進一步分析農村居民點格局演變的成因,找準影響其空間特征和演變的影響因素,關于政策因素的量化也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對調整其空間布局也是需要重點考慮的內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