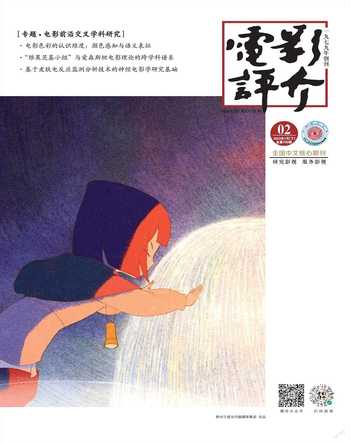電影色彩的認識維度:顏色感知與語義表征
王宜文 史之辰
色彩是電影研究的重要領域。隨著認知科學與電影學跨學科聯動的逐步深入,有關電影色彩及其敘事功能的理解與認知得到了豐富和拓展。借助人腦視神經系統對顏色的識別和感知原理,本文試圖以認知主義的理論視角審視和考察電影色彩的敘事功能與特征。
一、電影色彩的技術沿革與心理驅動
電影早已全面進入彩色時代。由黑白向彩色的過渡,在一定程度上給人們造成了一個既定觀念,即從前的“老”電影是黑白的,而如今的“新”電影是彩色的。但從電影技術的發展史,特別是觀眾的心理欲求層面看,嚴格意義上的“黑白”與“彩色”之分界并不存在。而且在彩色電影成為電影制作標準后,仍有很多電影使用黑白影像進行創作,如《曼哈頓》(1979)、《憤怒的公牛》(1980)、《辛德勒的名單》(1993)、《白絲帶》(2009)、《藝術家》(2011)等。
在電影誕生最初的幾十年里,彩色正如今天的黑白影像一樣,是一種較為特殊的藝術表現形式,對膠片進行著色是較為通行的做法。電影制作者會將夜晚的外景著色為深紫色或藍色,既模擬夜間的光影,也在視覺上將其與白天和室內場景進行區分。彩色電影最重要的發展之一是英國布萊頓學派先驅喬治·史密斯(George Albert Smith)于1906年發明的雙色電影制片工藝(Kinemacolor)。①此工藝通過紅色和綠色濾鏡投影膠片,盡可能貼近被攝物的實際顏色。較之需要多人手工作業的膠片著色法,雙色工藝將電影色彩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但其不足之處則在于無法準確地展現出所有顏色,過亮、褪色或無法顯現的問題時有發生,特別是雙色工藝制片的影片必須安裝與之對應的播放設備,導致播映成本大幅升高。因而,盡管雙色電影在英國本土觀眾中很受歡迎,但雙色工藝技術始終無法得到真正的普遍采用。
大約在1915年,特藝公司(TECHNICOLOR,Inc.)②開發出了自己的雙色工藝,即利用濾鏡和棱鏡的組合使放映出的電影具有色彩。隨后,該公司繼續研發顏色處理技術,將顏色直接印在膠片上。1925年的《歌劇魅影》就曾使用這一技術加入了幾段彩色場景。1932年,特藝公司再次推出了一種利用染料轉印技術的三色膠片拍攝技術③,將彩色電影技術推向了一個高峰。盡管呈現出的效果極佳,但制作三色膠片電影的前提卻是更高的拍攝難度和成本,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前,只有好萊塢的大型制片廠才有能力選擇這種拍攝方式,其著名的影片有《羅賓漢歷險記》(1938)、《亂世佳人》(1939)、《綠野仙蹤》(1939)等。
20世紀50年代后,彩色電影發展得更為迅猛。一方面,技術的演進使彩色影片逐漸具備商業上的可行性;另一方面,電視的出現導致電影受到巨大的沖擊。因此,電影只有提供區別于電視的新奇體驗,才能使觀眾走出客廳,重回影院。由于當時的電視只能放映黑白影像,因此大力發展色彩便成為電影抵抗電視沖擊的首要應對策略。在此后的創作實踐與藝術探索中,色彩成為電影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起著復現現實的功能,而且承擔了重要的表意與主題性作用。
除了技術的革新和商業的探索外,關于色彩進入影像的討論也伴隨其間。早期,彩色電影曾經遭受過不少質疑,例如德國電影理論家愛因漢姆(Rudolf Arnheim)認為,較之可以更自由、隨性地使用色彩的藝術類型,電影只是機械性地記錄了物理現實中的光值,顏色并不能發揮真正創造性的作用。[1]英國電影理論家歐內斯特·林格倫(Ernest Lindgren)也持有同樣的觀點,認為電影色彩不太可能像聲音那樣帶來技術上的根本創新,色彩在拍攝前已經“存在”,而拍攝只不過是一種機械性的捕捉和反射而已。[2]這類觀點曾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占據主流,一些理論家們認為色彩的加入雖然會加強影像還原現實的能力,但也會擾亂觀眾的視覺系統,以無關緊要的視覺信息干擾觀眾本應投注于人物和情節上的注意力。
這些質疑最終都未能阻礙彩色電影的發展,觀眾對電影復現現實的需求本身就已足夠支撐彩色電影到來。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技術的發展和對視覺效果的不斷探索,電影制作者們逐漸發現顏色并不像理論家們預設的那樣刻板,觀眾對顏色的感知也并非是一成不變,不同的文化語言背景及個體生理差異,導致不同的人群對顏色的認識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色彩除了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屬性之外,也是一種主觀化的、多樣化的感受,具有語義上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賦予創作者更大的藝術發揮空間,色彩因此而成為重要的敘事要素和創造力得到彰顯的重要手段。
二、黑白影像的獨特敘事效應
當下,數字制作已逐漸取代了膠片攝影,彩色成為電影影像的主流,曾經被認為是電影標準形式的黑白影像正在逐步消失。這種歷史性的轉變反倒使黑白影像逐漸發展為特殊的藝術手段,影片對黑白影像的調用,也引發了對此類影像認知問題的探討。
美國電影學者惠勒·狄克森(Wheeler Dixon)在其專著《黑白電影:一段簡史》(Black and White Cinema:A Short History)中對黑白影像進行了系統性的學術梳理。[3]狄克森認為,主流影像的環境和現實生活本身都是彩色的,因此當電影人拍攝一部黑白電影時,就有一種內在的風格化和對現實的重新詮釋,從而導致一種完全不同的影像風格模式。黑白影像構成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正在“迅速從當下的世界滑落到過去迷霧中”的世界。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黑白影像逐漸具備喚起過去時態、記憶語境與歷史感的功能。侯孝賢的《刺客聶隱娘》(2015)以一段長達6分鐘的黑白影像開片,就戲劇功能而言,這段黑白影像以過去時態交代了全片的前提背景:聶隱娘跟隨師父學習劍術,學成之后師父命令聶隱娘下山完成刺殺任務,而刺殺的對象正是她青梅竹馬的表哥。開片與正片部分的彩色影像形成了時間區隔,有“前史”之感,也使觀眾能夠更準確地理解此后人物的一系列行為及其動機。主題內容大致相同的兩部電影——1989年的《開國大典》和2009年的《建國大業》,創作年代雖然相隔20年,敘事角度、風格均有所變化,但在毛澤東登臨天安門城樓宣布新中國成立的段落中都選擇了真實的黑白影像,對于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而言,黑白畫面帶出的歷史厚重感符合人們最普遍的心理期望。
從物理學和視覺認知的角度看,人類視覺對物體的基本認知主要是靠輝度(luminance)對比而不是色彩對比來完成的。①這意味著較之形狀、線條等屬性,色彩雖然可以通過強化特定特征來幫助識別、記憶和檢索物體,但卻并不會根本性地影響人對物體的感知與把握。對于人腦的判斷和識別而言,物體的顏色往往是一種非必要的附加信息。在此前提下,黑白影像的優勢也便凸顯出來。在多數認知情況下,黑白影像抹去了紛繁錯雜的色彩信息,在不影響觀眾對空間和物體理解的同時排除了視覺上的干擾,促使信息更為單純和集中。
科恩兄弟于2001年創作的影片《缺席的人》,是一部以黑白影像呈現的電影,獲得第74屆奧斯卡最佳攝影獎提名。影片是以彩色膠片拍攝而成的,但在剪輯時,科恩兄弟與攝影師羅杰·迪金斯(Roger Deakins)發現,出現在背景處的藍色建筑與穿著粉紅色衣裙的行人等顏色信息,無意間成了干擾性的視覺贅余。因此,他們將彩色影像處理為黑白,以使影片傳達出的信息和主題更加純粹。[4]在這種去色彩的處理中,影像也產生了某種特殊質感,例如男主人公艾迪在多麗絲自盡后獨自步行回家,在抽離掉背景中紛繁的色彩之后,艾迪成為畫面的絕對主體,而他人不過是匆匆過客。當艾迪回到家中跌坐在沙發上時,艾迪和他人及周遭均保持著一層疏離感。正如其獨白所說:“我坐在屋里,但屋里空無一人,我是一個幽魂,看不到任何人,任何人也看不到我。”色彩的隱去加深了人物的孤獨,觀眾從影像上獲得的信息有限,反而可以更專注于艾迪與環境的關系之中,并逐漸進入影片試圖傳達的“人的存在”這一重要的哲學命題。
另一方面,黑白影像并不是黑色與白色的簡單并置,而是一種單色攝影及其附屬的所有光影關系。在黑白的影像系統內,涵蓋了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間的所有層次,銀色、米色、灰色等顏色均居于其中,構成了事實上更為復雜的光影和色調譜系。因此,黑白在簡化色彩的同時還保持有其特殊的藝術和想象空間。在20世紀80年代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提供給被試者未著色的黑白線形圖案,要求被試者依據自己的想象給出這一圖案應被填充的顏色;隨后,研究者根據被試者匯報的顏色為這一圖案著色,并將其混入其他顏色的同類圖案中,要求被試者進行圖形識別。實驗結果顯示,比起其他隨意填涂的顏色,被試者可以更快速和準確地識別出以其想象中的顏色進行填充的圖形。[5]這即說明較之給定的顏色,人們根據黑白畫面自行想象的色彩反而是最契合其認知的。因此,盡管黑白影像并未提供確切的顏色信息,但并未阻礙觀眾對色彩的主觀想象和延伸。
三、電影色彩的認知與表征
黑白影像逐漸向特殊的表意形式過渡,主要是由于在當今的媒介環境下,彩色已是最主流的電影制作與觀看模式,這種轉折體現出的是觀眾對色彩接受習慣的深度轉變。然而,無論是黑白電影時代中彩色作為特定形式,抑或彩色時代下黑白作為去色彩化的特殊形式,關于電影色彩最重要的前提性問題始終是作為接受者的觀眾對色彩信息的加工和認知機制。
人對顏色信息的認知加工分為早期的視覺加工和更深層次的語義分類兩個階段。視覺加工階段也即顏色知覺階段,指對顏色的色調、亮度和色度等三個物理特征的知覺。[6]在初級加工之后,大腦會對接收到的顏色視覺信息進行更為復雜的語義判斷,在此階段,個體認知、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因素都會參與進來。初級視覺加工涉及到的主要活動是對顏色的感知,語義加工階段則涉及到對顏色的認知。感知是指將現實世界中的物體或事件映射到大腦中,而認知則是對感知到的物體或事件進行語義和言語分類的高階意識活動。
目前,對語言神經基礎的研究已經表明,顏色的感知、分類和語義加工活動可能涉及不同的神經結構。感知顏色的三個基本屬性(色調、色彩和亮度)的概念依賴于一個神經系統,認識和表達顏色的詞匯依賴于另一個神經系統,而理解顏色詞匯和概念之間的聯系則依賴于第三個神經系統。[7]在大腦感知到顏色信息后,具體是如何建立起顏色和心理意象之間的關系,目前還很難依靠實驗技術手段進行研究,但一些相關的實驗已經證實記憶和語言文化是影響人認知顏色的重要因素。在一項典型的顏色記憶匹配實驗中,被試者被要求觀察并記住他們所看到的顏色,隨后經過一段時間間隔,他們被要求從幾種給定的顏色中選出之前所看到的那個顏色。結果顯示;被試者的選擇和他們最初看到的顏色之間產生了顯著的差別。[8]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被試普遍傾向于對看到的顏色進行分類,然后只記住大類別例如“綠色”而忽略了該顏色的其他屬性,如亮度、飽和度等。與此同時,被試者潛意識里的個體記憶會融入進來,并將所看到的顏色與記憶中的物體或場景進行聯系,如綠色對等于草地的顏色。這一系列過程后,被試者對顏色的選擇往往就是一個經過了多個認知環節的綜合結果,而不再是實驗當中所看到并獲得的準確的顏色信息。
語言對顏色認知的影響一直以來都是語言學與認知科學研究的熱門方向,2007年的一項研究中,實驗人員分別向母語為俄語的被試者和母語為英語的被試者展示了三個一組以品字形呈現的藍色色塊,三個色塊的區別是彼此間的深淺不同,接著被試者被要求指出處于下方的兩個藍色色塊的顏色哪一個更接近于上方的藍色色塊。實驗結果顯示,母語為俄語的被試者做出判斷的速度要明顯快于母語為英語的被試者。研究者認為,產生這一結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英語中藍色被統稱為一個單詞blue,而在俄語中對藍色沒有統一的指稱,但是會使用兩個單詞來區分亮藍色和暗藍色,這一語言習慣使母語為俄語的被試者做出判斷時會更加容易。[9]盡管目前的研究尚未厘清顏色認知在大腦中完整的運作機制,但已有研究充分顯示不同族群和個體之間對顏色的認知并不固定,而是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對電影色彩的考查也應適度跳出主觀化的闡釋,而進入到一種認知的過程與視角之中。
(一)色彩的視覺加工與感知
早在牛頓利用三棱鏡發現了光的色散現象之后,人們就開始意識到色彩也許并不是物體的固有屬性。在此后的研究中,色彩的神秘面紗被揭開:顏色本質上是人類視覺神經系統對光的一種感知。[10]盡管顏色不是物質的本質屬性,但它在人的認知判斷過程中還是會起到一定的作用。在目前的研究中,顏色被認為是一種關于場景的,額外的、詳細的信息,應有助于圖像的識別。在日本的一項研究中,通過給物體增加顏色屬性,并與沒有色彩的物體本身形成對照來考查在兩種情況下,被試者即時的識別結果以及過后的回憶反饋,以此分析顏色是否具有輔助認識和增強印象的功能。最終實驗得出結論:顏色在信息編碼和檢索方面確實是有效的,但是這種作用在即時識別中并不明顯,且僅當顏色在編碼和檢索過程中都存在時顏色才有效。[11]這也就是說,當顏色對應編碼于物體之中時,能輔助人們區分不同的內容并且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美國華盛頓大學心理學教授洛夫特斯(Geoffrey Loftus)的團隊所做的關于人對圖像識別的實驗則進一步證明了顏色的積極作用。實驗的材料是三組圖片:第一組圖片是60張以自然場景為主的照片;第二組圖片是第一組照片中場景的簡化,研究者將照片中的主要景物以線條形式勾勒出來,繪制成60張線條圖;第三組圖片是在第二組的基礎上進行著色,將照片中原有的色彩涂繪在線條圖上。被試者分為三組:第一組觀看照片、第二組觀看線條圖,第三組觀看著色圖;接著實驗者會隨機展示一些圖形,這些圖形有些曾出現在原有的實驗材料中,還有些是新加入的干擾圖形,被試者需要依次判斷看到的圖形是否曾出現在之前觀看的圖片中。研究結果顯示,觀看線條圖和著色圖的被試者,識別正確率均低于觀看照片的被試者。研究者認為,這主要是由于照片含有的信息量太多,而線條圖和著色圖則不同程度地削弱、遮蔽了原照片中的顏色信息,從而降低了被試者對物體識別與判斷的準確率。[12]上述實驗共同說明:顏色與人對物體的識別、感知以及判斷之間存在著較為緊密的聯系。
人眼視網膜包含了數以百萬計的感光細胞,其中每個感光細胞都含有光敏感分子,也稱為感光色素。感光細胞又分為兩種類型,即視桿細胞和視錐細胞,其中視錐細胞是顏色視覺的基礎。不同視錐細胞的感光色素對不同波長可見光的敏感性不同,這些不同的視錐細胞感知到各自對應的顏色后,經過視神經將信息傳遞給中樞神經系統,從而形成人腦對顏色的感知。神經美學之父薩米爾·澤基(Semir Zeki)在其研究中,使用正電子斷層掃描(PET)技術考查了被試者觀看顏色時視覺腦區的活躍情況,最終發現了相對位置靠前的V4區①涉及顏色信息加工時有明顯的活躍。[13]澤基的研究證明了在大腦視覺加工系統內部存在主要負責顏色信息加工的區域。
在考查電影中的色彩運用時,首先應關注人類視覺系統最基本、初級的生理反應。張藝謀的《紅高粱》(1988)對色彩的使用算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即使用強烈的、富有沖擊力的色彩直擊觀眾的視神經。在這部電影中,紅色作為主色調貫穿始終,并且在紅色背景之中,持續疊加不同層次的紅色物品:花轎、服裝、蓋頭、紅色的高粱地和高粱酒,以至最后犧牲場景中生命迸發出的極致的“紅境”(紅色濾鏡片營造出的意境),呈遞出一種強烈且不可抵擋的色彩沖擊感。大片綠色的高粱地,在以上紅色對比色的映襯下,呈現出強烈的分離感,平衡了視覺效果,加強了色彩對比,進而突出了主體顏色的位置,更襯托出《紅高粱》中一抹抹大紅色彩的直觀感受。
在所有可見光中,紅色光的波長最長,折射角最小,在視網膜上的成像位置也最深,所以紅色光會給人帶來最強烈的壓迫感和擴張感。這種客觀物理特性和人類既有的感知構造,決定了紅色一直是最有力量的顏色。誠然,并非粗獷地使用顏色造成視覺沖擊就能夠獲得一部顏色表意出眾的佳作,電影色彩的使用并非是簡單的堆砌,而應營造出色彩的對比和運動。同樣是張藝謀導演的《滿城盡帶黃金甲》(2006)卻在視覺色彩的選擇上飽受詬病,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便是充斥畫面的金黃色造成了所謂的“重復劣勢效應”②,即一個刺激信號反復出現時,并不一定能令人更快速地捕捉到它,反而可能由于該刺激重復多次導致人們形成慣性認識,而無法及時做出反應。2009年的一項實驗說明這種基于顏色的重復劣勢效應確實容易出現,研究者通過要求被試者對顏色進行辨別反應后發現,大量的注意資源分配在顏色信息上,可能促進了選擇性注意機制對色彩信息的加工,進而導致色彩信息返回被抑制,出現基于色彩的重復劣勢效應。[14]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幾位主要人物均身穿金黃色服飾,而兵丁甲士也全部身著黃金戰袍組成方陣,千篇一律的金黃色圖景重復出現在畫面的相似位置,而且沒有任何區分度,再加上缺乏對應的補色進行襯托,導致觀眾無法準確地觀察到畫面的核心信息。即使在面對場景切換時,也難以及時地感知到圖像的差異性,對影片的內容也就未做出積極的反應。同時,黃色又是相對比較醒目的顏色,刺激性較強容易造成視覺疲勞,二者疊加,勢必導致觀眾的觀感較差。
(二)色彩的語義表征
現實生活中的事物通常都具有色彩,人們無時無刻不生活在色彩之中。在電影中,色彩也通常被視為還原和表現現實的基本敘事元素。林德格倫和愛因漢姆等理論家都曾經認為公眾對彩色電影的需求反映了人們對現實敘事的普遍偏好,彩色膠片的發明將使電影呈現出更真實的影像風格,色彩是電影史上更逼近現實表達的重要一步。①
但是,色彩在電影中的逼真還原性只是其基礎功用。如前所述,色彩認知包含了物理、認知和文化成分,它既是生理現象,也是文化事件,因此色彩認知往往也被看作是感覺刺激和非感覺刺激的相互作用。
來自于認知和文化上的差異性決定著色彩的語義表征是多重可變的,如紅色既代表激情,也可暗示血、生命或愛。在中國,紅色可能代表喜慶,在世界的另一些地區則象征危險和邪惡。電影中色彩可以作為敘事手段的原因,色彩的類別數量是固定的,但其表意卻豐富多元,它們不能被用來賦予程式化的意義,而必須在敘事的語境中,并與觀眾的文化身份和經驗相聯系來解讀。顏色和其所代表的語義之間的關系在本質上是多元隨意的,這一現象在電影中意義重大,同樣的顏色可能很容易引起較大的反應。電影中色彩的“意義”必須總是處于一個特定背景之下,色彩與其說是一種現實,不如說是一種感知,而這種感知本身取決于許多變量。由于所有這些變量,包括文化、經驗和期望都會在我們個人對顏色的反應中起作用,因此顏色具備豐富的意義指向空間。
在復現現實之外,電影中色彩的運用往往是通過結構、渲染、變化使觀眾從強烈的視覺刺激或超常規的體驗中感受到超出影像內容本身的內涵。首先,最為簡單的處理是以具體直觀的色彩形象代表特定的意象,如《戰艦波將金號》(1925)中敖德薩階梯段落升起的紅旗,盡管彼時電影的染色技術還過于粗糙,旗幟的染色效果不盡如人意,但導演愛森斯坦選擇讓這面紅旗在銀幕上“紅”起來,用色彩傳達了意識形態功能,體現了色彩的象征作用。“在銀幕世界的造型空間里,形的作用偏重于理性,而色彩的作用則更傾向于人類的情感和本能,它擅于在銀幕空間中傳達與揭示人的情緒、心理和精神信息,使銀幕形象更加豐厚、立體、生動和富有生命質感,它具有使人的內心世界外化的作用,使抽象的概念轉換成可視的形象語言。”[15]王家衛的《花樣年華》(2000)利用電影色彩表現了人物心理和情緒上的不同轉變。男女主人公會面的環境色彩是黯淡灰白的,表達了被壓抑、被束縛的情感,女主人公旗袍顏色的變化使人物精神內里得到了外化:當她與男主人公約會時穿上了紅色的旗袍,昭示出內心的激動與雀躍;而當二人分離,她守在電話前默默無言時,旗袍的顏色則是象征憂郁與悲傷的藍色。觀眾無法直視人物內在的精神世界,但電影卻用色彩將其具化顯現了出來。
電影色彩的使用中,最特殊的形式是不可預測地使用顏色,或者將不恰當的顏色設置在“錯誤”的地方,以形成特殊的表意。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的《紅色沙漠》(1964)用非寫實的色彩來表現自然,主題上是為了反映日益增長的工業化和隨之而來的對環境的破壞,影像認知上則是為了喚起觀眾的注意力,以促使其做出越來越復雜的反應。安東尼奧尼在影像上加入了明顯的人工色彩,通過使用濾光片和為特定物體如水果等涂色,喚起了一個創造性建構和想象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現實本身通過拍攝而改變,從而成為一種人工制品,一種性質被扭轉的自然。在此,色彩不僅僅簡單地演繹影像,更成為一個獨立和開放的象征載體,根據時空語境和每個觀眾的創造性反應而改變其意義。
結語
色彩是電影視聽系統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特定的色彩調用,既可以協助影片完成主題表意,也可以參與奠定創作者的美學風格,進而影響觀眾的情感和心理進程。但另一方面,來自于認知主義的研究及其理論則不斷昭示著,色彩首先是一種作用于視覺系統的信息,在經由腦神經與網絡的加工處理后進入更高級的語義加工層面。從這個角度而言,理解和掌握人對色彩信息的接受和處理方式至關重要。北京師范大學神經電影學研究團隊以fMRI為技術手段重測了“庫里肖夫實驗”,分別以黑白和彩色兩種條件拍攝了模仿歷史上庫里肖夫實驗中的素材(演員面無表情的面孔以及愉悅、中性、恐怖三種場景),隨后招募等量的被試者分別觀看黑白和彩色條件下的庫里肖夫實驗剪輯素材。實驗研究發現,盡管兩種條件下的觀眾主觀行為上均表現出受庫里肖夫效應影響(他們認為演員面孔表現出的情緒與后續所接的場景相一致),但是當演員面孔連接的是愉悅場景時,觀看彩色視頻的被試者要比觀看黑白視頻的被試者而言,更多地認為演員表現出了愉悅的情緒;而當演員面孔連接的是恐怖場景時,兩種條件下的被試者表現得無差異。也就是說,相較于彩色,黑白顏色似乎抑制了觀眾對愉悅情緒的感知判斷,但是fMRI數據并沒有顯示出在二者的大腦接受上有什么不同,這說明影響觀眾做出主觀行為上不同判斷的,并不是顏色的初級接受方式有所不同,而是語義加工時大腦對黑白和彩色的認知處理不同。這也為后續的電影色彩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以不斷挖掘的方向。
本文試圖從認知的層面對電影色彩進行梳理和研究,突出色彩自身的視效特性及更深層次的語義表征,通過對電影色彩認知原理的探究,可以更科學地闡釋一些電影的創作現象,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指導電影色彩的使用。
當下,電影技術的發展已為電影的制作與播映增加了許多新手段,“廣色域”“高動態范圍”等新技術的實現,意味著觀眾已不再滿足于當下的觀影習慣,而開始期待影像可以呈現更加寬廣的色彩區域和光線明暗范圍。這必將會不斷豐富電影色彩的含義并提升色彩的價值,也為電影色彩的認知主義研究提供了較大的發展空間。
【作者簡介】? 王宜文,男,山東日照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電影史論、影像認知研究;
史之辰,男,內蒙古赤峰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影視史論、影像認知研究。
【基金項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神經電影學理論模型建構及電影認知的腦成像實證研究”(編號:16YTA00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認知神經科學理論背景下電影視聽元素結合效果研究”(編號:19BC041)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Rudolf Arnheim.Film as Art[M].London:Faber and Faber,1958:150.
[2]Ernest Lindgren.The Art of Film[M].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Limited,1948:205.
[3]Wheeler Wiston Dixon.Black and White Cinema:A Short History[M].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5:2.
[4]The Coen Brothers interview about The Man Who Wasn't There[EB/OL].(2011-07-21)[2022-12-17]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g27F1iWTt0.
[5]Watkins,M. J.,& Schiano,D. J.Chromatic imaging:an effect of mental coloring on recognition memory[ J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1982:291-299.
[6]Derefeldt G,Swartling T,Berggrund U,et al.Cognitive color[ J ].Color Research & Application,2010(01):7-19.
[7]Damasio A R,Damasio H.Brain and language[ J ].Scientific American,1992(03):63-71.
[8]Macdonald L,Luo R.Colour Image Science:Exploiting Digital Media[ J ].2002:75.
[9]Winawer J,Witthoft N,Frank M C,et al.Russian blues reveal effects of language on color discrimination[ J ].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7:104.
[10]Waldman G.Introduction to light: the physics of light[ J ].vision and color,1983:193.
[11]Suzuki K,Takahashi R.Effectiveness of color in picture recognition memory[ J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2010(01):25-32.
[12]Loftus G R,Bell S M.Two types of information in picture memory[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Learning & Memory,1975(02):103-113.
[13]Michael S.Gazzaniga,Richard B.Ivry,Geroge R.Mangun.Cognitive Neuroscience:The Biology of the Mind[M].W.W.Norton & Company,2019:153.
[14]焦江麗,王勇慧,邊國棟.認知控制對基于位置和顏色返回抑制的影響[ J ].心理與行為研究,2009(01):44-49.
[15]宮林,周登富.電影色彩的意義[ J ].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99(02):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