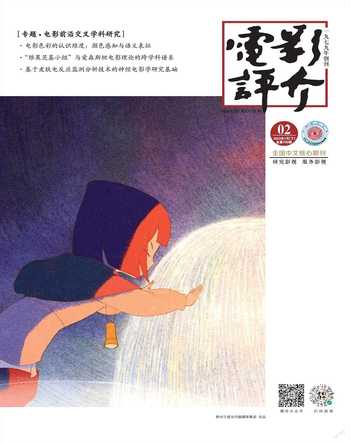新主流影片的現實主義敘事、個性化表達與公共性闡釋策略

王一川教授曾指出大陸電影可劃分為三類,即主旋律影片、藝術影片、娛樂影片。[1]面對好萊塢電影對中國電影市場的沖擊,基于“三分法”的前提,馬寧提出了新主流電影[2]的概念。如今,電影藝術已逐漸成為一種充滿文化屬性的商品,電影的制作成本與票房之間構成了良性循環。新主流電影占盡天時地利人和,呈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它承載了主旋律電影的價值內核,兼具被國家、大眾和市場多方認同的公共鑒賞性。新主流電影彌合了主旋律電影與商業電影的邊界,兼具政治性、審美性、文化性、商業性和創作個體主體性,有五者有機統一的屬性特征。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文藝工作者要有‘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感”[3]。可以看到,現在的中國電影人更加注重電影的文化內涵,堅守文化自覺、自信、自強的戰略,致力于打造展現中國特色、彰顯中國氣派、體現中國風格的主流電影品牌。
主流電影類型化和類型電影主流化是近年來中國電影的發展特色。新主流電影也已逐漸演化為具有相對固定敘事模式,以社會現實為題材,結合商業影片的制作發行方式,并以故事片形式展現的電影類型。《戰狼2》《紅海行動》《萬里歸途》三者就是典型的新主流影片,它們都以海外撤僑救援行動為創作背景,屬于異域營救敘事類的動作影片,在彰顯大國形象的同時,也取得了較為優異的票房成績。《戰狼2》于2017年暑期上映,創造了56.95億元的票房奇觀,一度刷新了中國電影的票房記錄①;《紅海行動》于2018年春節檔上映,與同期上映的《唐人街探案2》《西游記女兒國》《捉妖記2》等影片相比,《紅海行動》既沒有流量明星效應的加持,宣發工作也沒有投入過多,但卻憑借其扎實的內容,成為春節檔的最大“贏家”,最終收獲36.52億元票房;《萬里歸途》于2022年國慶上映,兩個月內突破15億元票房,雖與前兩者存在差距,但在疫情影響的大環境下,這樣的數據也在國慶檔中一騎絕塵,并躋身2022年中國電影票房的前5名②。在它們的影響下,新主流影片早已成為當今電影市場的“寵兒”,隨之而來的是學界對新主流電影的研究熱情。但和主旋律影片一樣,新主流電影同樣存在發展考驗,如何避免形成固定單一的框架結構?如何發展電影的工業美學?如何探索出可持續發展的生產路徑?關于這樣的思索,從《戰狼2》《紅海行動》和《萬里歸途》這三部同類型、同題材的新主流影片中,已經可以看到新主流電影在未來發展的“生存”之道了。
一、現實主義敘事策略與敘事模式的突破
法國電影人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提出:“電影是現實的漸近線”[4]。電影藝術的主題應該是現實的,只有精準地描繪現實才能讓電影突破時間限制。聚焦社會現實,弘揚主流文化是異域救援敘事類影片的主題。據外交部領事司、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公開的相關數據統計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共開展大型海外撤僑行動19次,中國政府以包機、包船、包車的形式,將中國駐外機構人員、港澳臺同胞及華人華僑從戰亂、動蕩和受自然災害影響的地區撤離回國,累計撤離四萬余人。《戰狼2》《紅海行動》《萬里歸途》都以海外撤僑事件為題材,既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以人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執政理念,又展現出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維護和平的外交方針。中國政府對海外公民安全的重視,對人權的保護,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三部影片共同告知世界有一種救援叫做中國速度。
單從敘事策略而言,首先,這三部影片展現出了濃厚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戰狼2》是以2011年利比亞撤僑行動為創作主線創作的故事。主角冷鋒(吳京飾)的定位是退伍軍人,并沒有具象到現實。《紅海行動》改編自2015年的也門撤僑行動,以中國海軍“蛟龍突擊隊”為原型,采取虛實結合的創作手法,塑造了英勇無畏的中國軍人形象,讓觀眾切身體會到了國家帶來的安全感。《萬里歸途》也以2011年利比亞撤僑行動為原型,但還參考了2015年也門撤僑和2022年烏克蘭撤僑行動中的一系列真實事件,用電影獨特的敘事手段,將多位外交官的真實事跡串聯在主人公宗大偉(張譯飾)身上;影片中被困的華興公司,其原型是浙江寧波的華豐公司;影片中宗大偉與成朗(王俊凱飾)帶領125名中國同胞穿越沙漠的情節,也參考了中建八局駐利比亞項目的員工在撤離中發生的故事,此外與武裝人員周旋,在衛星地圖留記號等情節也都有據可依。相比于戰爭片《戰狼2》,“戰爭”只是《萬里歸途》的敘事背景而非主題。其主題在對現實主義敘事策略的運用中已經表明,即以“歸家”為敘事線索,意在樹立國家形象并弘揚中國文化和以人為本的民族精神。這一點與美國學者喬治·格伯納(George Gerbner)提出教養理論(Cultivation Theory)相契合,格伯納指出大眾傳媒提供的“象征性現實”和內部蘊含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傾向,在大眾認識世界的過程中起到的教養效果,悄無聲息地制約著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教養理論與電影藝術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好萊塢影片對美國國家形象的塑造中早已清晰。相較于其他宣傳途徑而言,電影更能將國家和民眾行為直觀地展現出來,其中也包含對該國的認知、判斷與評價。這種異域救援敘事模式經過中國化表達,不僅可以向內傳播主流思想精神、提升文化自信,也可以向外展現我國和平崛起的大國風范。
其次,敘事層次也從單一線性敘事結構,到一波三折、層層遞進的多線、多元強敘事結構的發展轉換。這三部影片中,《戰狼2》是典型的單一線性結構,它以時空轉換為線索并運用平行蒙太奇手法進行剪輯。盡管影片中穿插了許多曲折的情節,如冷鋒染上病毒、穿越火線的撤僑行動等,但總體而言這些都只是為了突出營救行動的曲折性和戲劇性,豐富觀眾的心理感受而已。《紅海行動》采取多線敘事結構,救援者兵分三路展開行動,三條路線輕重有序地以“撤僑”故事為主線展開敘述。相較于單線敘事,多線敘事策略更符合真實情境,也能使鏡頭和場景切換得更加自然,從而更好地表達鏡頭語言,為觀眾呈現出一場視覺盛宴。《萬里歸途》則呈現出多線、多元的強敘事結構,影片以四個環環相扣的小故事串聯成一個大的撤僑敘事框架。起先宗大偉和成朗前往努米亞邊界為丟失護照的中國公民辦理出境手續,過程中遭到該國邊境檢察官的故意刁難,他們的有效應對體現出了中國外交官的智慧。隨后這一批同胞成功撤離,宗大偉又在兄弟之“義”和家國職責的驅動下與成朗逆行至戰亂中心尋找白婳(殷桃飾)與另一批中國同胞,但成功會面后又與大使館失去了聯系,只能憑借經驗與信念努力前行,對困境的進一步書寫也加深了觀眾對外交官的敬仰。第三部分為最后一個故事做了鋪墊,宗大偉與白婳等人落入努米亞叛軍手中,并與叛軍首領玩俄羅斯輪盤游戲,這一部分對人物形象進行了全面塑造,使主角形象更加立體了。第四個故事講述了在邊境撤僑行動順利開展時,叛軍發起突襲,為保護同胞宗大偉只好答應叛軍的無理要求再次進行輪盤游戲,這兩次游戲將主角的人物形象塑造得更加完滿了,四個故事也將戲劇沖突、人性沖突、人物命運走向牽連起來,共同演繹了動人心魄的結局。雖落點在多線敘事結構上,但在撤僑“歸家”的大敘事前提下,也從人性、國際格局、戰爭與和平、真相與謊言等多角度展開了探討。“歸家”是傳統,也是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刻印在每一位中華兒女基因里的東西,無論身處何方,家與祖國始終能給予我們安全感和歸屬感。此外,影片也蘊藏著一個神話原型敘事結構。榮格指出,原型是一種反復出現在歷史中那些“創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達的任何地方”[5]的神話形象。《萬里歸途》中出現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和被誦讀的《航海家辛巴達》的故事與“歸家”主題兩相呼應,使觀眾的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堅韌無畏、充滿熱情的正義形象,自然地觀眾也會將這種感受帶入到觀影過程中。自此,西方神話與中國“歸家”主題的表達形成了閉環。這樣的表達既彰顯了新主流電影的中國性,也使新主流電影展現出世界性和共享性的特征。
二、反英雄化的個性表達與女性力量塑造
這三部影片雖在類型和主題上有相通之處,但在人物塑造和表達上卻各有千秋。《戰狼2》受好萊塢影片的影響,將冷鋒塑造成無懼生死的英雄形象,體現了個人英雄主義色彩。《紅海行動》主要體現了集體主義精神和國家力量。《萬里歸途》與前兩者存在明顯差異,它并沒有講一個大英雄的故事,而是將焦點聚集到平時被公眾忽視的個體外交官身上,從普通人視角和平民立場的表達進一步將宏大敘事與個體小我有機結合,既體現了反英雄化色彩也使影片充滿個性化表達,這種個性既指影片中每一個生動的個體,也指導演饒曉志的個人特色,即從普通人視角出發,展現了對民生的關懷,揭示了人性。
(一)個性表達與反英雄化書寫
小人物的平民視角是饒曉志導演的創作特色,既渺小又偉大的外交官是《萬里歸途》宏大撤僑敘事的落腳點。外交官不似軍人,并沒有強大的戰斗力,只是憑借著智慧在困境中奮勇前行,面對危險的時他們也會脆弱和恐慌。這是人的正常反應,這些活生生的人性并沒有被舍棄而是被完整地展現給觀眾,并不會影響主題的表達,反而使人物更加鮮活立體了,在關鍵時刻他們為了集體利益站了出來,肩負起了護送同胞歸家的使命,克服畏懼后秉持責任和信念英勇向前的獻身精神更能打動觀眾。
不同于好萊塢的英雄塑造模式,《萬里歸途》的人物書寫更能體現出人性的光輝。影片開頭宗大偉一心只想盡早歸家與即將臨盆的妻子團聚。隨后好友章寧(張子賢飾)的意外殉職喚醒了宗大偉的神經,完成章寧的使命,解救被困同胞和章寧的妻女成為宗大偉加入撤僑行動的原動力。真正有助于塑造宗大偉人物形象的就是影片中的俄羅斯輪盤游戲,觀眾在兩次游戲中見證了宗大偉的蛻變。第一次游戲的場所是在叛軍營地,在白婳遭受欺凌時,跟隨她的努米亞老人挺身而出,致使老人成為宗大偉參加賭局的賭注,我們看到了宗大偉的膽怯與退縮,對死亡的恐懼和遠方“小家”的牽掛是其與英雄稱謂漸行漸遠的最大原因。這場賭局隨著老人再次挺身而出至失去生命而結束。在這里老人成為了英雄,宗大偉與老人之間的對照關系,這也在觀眾心中埋下了對主角成長路徑的期待。第二次輪盤游戲的營救對象變為章寧的妻女,此時宗大偉的女兒也已經出生了,他的“小家”與營救對象之間相互呼應,消解了宗大偉“挺身而出”的阻礙,發生地點在海關邊境也使宗大偉有了國家力量的支持。大國與小家的力量在這里共同凝聚在宗大偉身上,使其找到“初心”,運用智慧和膽識與叛軍頭領周旋,宗大偉在最后一次扣動扳機后發現手槍中并沒有子彈,這個情節強化了對宗大偉英勇的展現,此時宗大偉已然成為觀眾心中的英雄,也成為了“自己的英雄”。自此,宗大偉的人物形象也更加完整了,他克服了人性的弱點,最終完成自己的“使命”。觀眾見證了他從玩世不恭的職場人士成長為肩擔道義誓死捍衛中國外交立場的外交官的過程。宗大偉身上體現出了中國傳統的“忠義”價值觀,也間接展現出我國向往和平、堅決維護正義的大國風范。
(二)女性力量的書寫
精良的制作、復雜的敘事模式、符合時代審美特征并彰顯了大國氣勢的崇尚和平理念和濃烈的愛國情懷,使《戰狼》《戰狼2》《紅海行動》成功塑造了許多男性英雄形象,而女性形象則被邊緣化。《戰狼》《戰狼2》中的龍小云和瑞秋實質上只是英雄要救的“美人”。《紅海行動》的英雄群像中雖加入了女機槍手佟莉,但她卻被塑造得男性化、陽剛化。她是在戰場上肉搏廝殺的硬漢,身上缺乏傳統的女性之美。在這兩部撤僑影片中男性居于主導地位,女性成為配角,這種女性力量缺失的情況在《萬里歸途》中得到了改善。
《萬里歸途》塑造了多位彰顯女性力量的角色,如白婳、陳悅(萬茜飾,宗大偉妻子)和鐘冉冉(陳昊宇飾,白婳的助手)。白婳的身份設定就已經體現出了剛強堅韌的女性力量。作為獨自在戰亂國家工作的企業高管,與外交官丈夫聚少離多卻收養了異國女兒,這意味著在日常生活中她要客服許多異于常人的困境。這種剛強在影片中具象于白婳在戰亂地帶領125位中國同胞等待祖國救援的行動中,得知丈夫的死訊后也她沒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而是在第一時間隱瞞丈夫的死訊穩定軍心,在員工擅自離隊時她也主動承擔責任與宗大偉一同出發尋找員工。同樣體現出這種堅韌力量的還有另一位女性角色鐘冉冉,在避難所人們將傷員隔離,生怕他們攜帶埃博拉病毒而不再靠近,僅在紅十字會做過志愿者的鐘冉冉卻扛起了隔離區的醫護職責,她臨危不亂有條不紊地為傷員進行檢測,并將需要的藥品羅列出清單等待救援。這與男性角色劉明輝(王迅飾)對待隔離區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對比中也體現出柔弱勝剛強的意味。《萬里歸途》中雖然女性角色已不再缺席,但真正彰顯女性力量,使女性角色從襯托男主角的功能中解脫出來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盡管白婳身上體現出了女性堅韌、剛強的力量,但不可否認宗大偉兩次被迫參與俄羅斯輪盤賭局都與解救白婳相關,故事情節依然沒有逃出英雄救美的基本框架。如何在男性傳奇的語境中書寫女性形象仍是這類影片需要攻克的難題。
三、公共性闡釋:國家形象的深化塑造與共同體美學的建構
藝術品本身存在可供公共鑒賞的品質,這種品質越凸顯,接受者也會越多。電影藝術作為大眾娛樂的重要來源,本身就具備藝術公賞質特征。近年來在大國崛起的時代背景下,新主流電影更是成為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本質上講,新主流電影的主題仍是愛國主義教育性質的,展現國家風貌、樹立國家形象是其重要的敘事策略。在票房和評價上更有“叫好又叫座”的反饋。鑒于其藝術公賞力[6]特征,對其主旨進行闡釋也被賦予了一種公共性,張江教授提出了“公共闡釋”[7]這一命題,他認為闡釋本身就具有公共性,在人們交流的過程中,交流的雙方以及闡釋者之間構成了一個共同體,闡釋就是圍繞著這個共同體展開的理性活動。
《萬里歸途》延續了前兩部撤僑敘事類影片的主旨風格,承載著傳播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重任,在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播民族意識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其主旨的最大特色就是在人文情懷和家國情懷中塑造國家形象。家國與共、愛國如愛家的家國情懷與以人為本的人文情懷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核心的觀念,幾部撤僑影片都突破了傳統主旋律電影以國家為重而忽視展現個人的創作模式。它們更加注重將個人納入到家國體系中去審視,以平民化視角從尊重個體生命的角度出發展現國家意識形態。個人情感與家國情懷的相互交融,在宗大偉身上展現出的兄弟情、夫妻情為緊張的戰時環境增添了溫情色彩,為“大家”奮斗在一線并做出獻身準備的主角形象也被襯托得更加偉大了,引起了觀眾的認同。此外影片也將個人行為、個人榮辱甚至個人命運與國家相連,展現出人民愛國和國家以人民為重的雙向奔赴的價值觀。《紅海行動》中“一個僑民都不能少”的核心內涵和《萬里歸途》中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人民的宗大偉,都是基于人文視角對生命、對人權關懷的展現。總的來說,這種在家國情懷和人文情懷中展現主流意識形態的創作范式,可以最大程度地引起觀眾共情,更使電影主旨的公共闡釋成為可能。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除了對家國情懷和人文情懷的演繹,影片也體現出了命運共同體理念,內蘊著突破國界的“兼愛”思想與維護和平的反戰內涵,彰顯了大國胸襟與擔當。這三部影片的救援對象并沒有局限在中國僑民身上,如冷鋒救出的朋友多是外籍人士,蛟龍突擊隊不顧個人安危為他國平民拆炸彈,讓宗大偉身陷第二次輪盤游戲的小女孩雖已被收養成為中國人了,但其異域面孔也有很強的隱喻性。這種對生命的無差別守護也展現出了中國傳統的“兼愛”思想,其中蘊含著超越民族、超越國家的話語體系,彰顯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平等是其重要前提。《萬里歸途》將這一點表達得更為突出,在異域拯救的背景下隨處可見中外人民之間的互動關聯,但影片并沒有將中國外交官塑造成救世主,反而從努米亞老人和邊境簽證官等人與宗大偉的互動中,彰顯了相互拯救的內涵。這也揭示了全世界各國人民相互依存的客觀規律,再一次深化了向往世界和平的主題。
結語
這三部以海外救援為主題的影片為新主流影片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啟示。影片具備的藝術公賞質特征與對其進行的公共性闡釋,使文藝共同體美學的構建路徑更為清晰了。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共同體(gemeinschaft)這一概念,他認為共同體的三個基本要素是血緣、地緣和精神。[8]縱觀中國文藝共同體美學的發展,本文認為新主流電影對共同體美學的建構主要體現為:文化、地緣、血緣、精神、情感和敘事這六點。血緣的關聯與空間地域結合產生文化、精神和情感上的統一,這些精神又在敘事中傳播出去,傳播也預示著接受與再傳播,這背后實則蘊藏著一個接受共同體的概念。溝通和傳播是當今文藝發展的重要使命,在科技快速發展,產業不斷升級創新的新時代,始終要以飽滿的熱情建構文藝共同體美學,以中國精神、中國理論作為重要的實踐理論基礎。弘揚時代精神,表達主流價值觀,樹立國家形象,宣傳愛國主義精神,提升人民的凝聚力與號召力,彰顯中華民族的文化軟實力。《萬里歸途》這種敘事角度平民化的創作方法,使虛空的電影形象變得更加生動真實,更能激發觀眾的共鳴,引發觀眾對時代和生命的思考,進而促進電影內外不同維度共同體的發生,推動文化共同體美學的建構。
【作者簡介】? 佟姍珊,女,黑龍江哈爾濱人,黑龍江大學文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文藝美學與文藝原理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1]王一川.從大眾戲謔到大眾感奮——《集結號》與馮小剛和中國大陸電影的轉型[ J ].文藝爭鳴,2008(03):115-119.
[2]馬寧.新主流電影:對國產電影的一個建議[ J ].當代電影,1999(04):4-16.
[3]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學習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5:30.
[4][法]安德烈·巴贊.電影是什么[M].崔君衍,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307.
[5][瑞士]榮格.心理學與文學[M].馮川,蘇克,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120.
[6]王一川.藝術公賞力:藝術公共性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348.
[7]張江.公共闡釋論綱[ J ].學術研究,2017(06):1-5,177.
[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