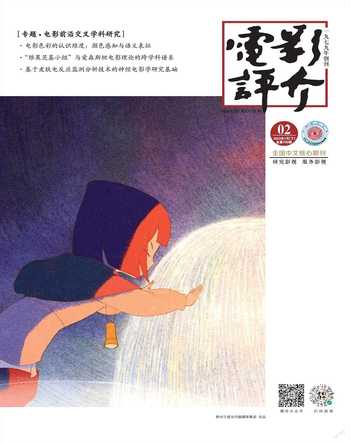通俗表達與沉浸體驗:《奇跡·笨小孩》的文本敘事與主題表達
王加昕 曹飛

電影評論家鐘惦棐提出:“最主要的是電影和觀眾的關系,丟掉這個,便丟掉了一切。”①面對電影受眾群體日益年輕化、多類型等新變化,需要創作者從大眾實際審美與觀影心理出發,通過采用合適的表達技巧與敘事策略,合理利用視聽語言,在為觀眾提供沉浸體驗的同時,確保大眾的觀影體驗感與參與感實現有機融合。電影《奇跡·笨小孩》(2022)將通俗敘事與時代變遷相融合,在生動呈現底層社會景觀的同時,充分肯定了大眾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而不斷奮斗的積極行為,有效適應了受眾群體動態分化與組合的客觀現實,在構建包容、全面的敘事視角的基礎上,實現了影片敘事與受眾鑒賞的有機融合。
一、電影《奇跡·笨小孩》的通俗美學敘事解讀
通俗表達,是以市場邏輯、受眾審美為基礎,對影視作品的敘事內容進行通俗化、平民化處理的表達范式。通俗敘事模式,通常會先交代家庭情感,再具體講述時代變遷下人物的命運變化,通過合理使用音樂,巧妙設計視聽畫面,取得情感共振的理想成效。影片《奇跡·笨小孩》通過將通俗表達與敘事美學相融合,在綜合應用成長、喜劇、愛情等多元主題的基礎上,彰顯了不同類型的審美特征,從深度視野把握成長主題,實現了通俗表達與主題闡釋的有機融合。
(一)通俗表達的重心:豐富表達內容,傳遞成長力量
英國漫畫家皮特·布魯克斯提出“通俗劇”通常以大喜大悲的方式來表現善惡分明,并通過高度戲劇化黑白是非,在主人公經歷多重磨難后,實現“以情動人”的敘事目的。②電影作品在利用通俗美學進行敘事表達時,通常不講述日常生活,而是通過豐富表達內容,設置大量沖突情節,賦予主人公悲情的一面,進而傳遞成長的精神力量。[1]電影《奇跡·笨小孩》以現實主義為創作基調,通過將“情節劇”模式融入其中,使青春、成長、勵志等多元主題與感人主題相融合,既增加了故事內容的鮮活性,也使觀眾生動體會到其中蘊含的多元情感。比如,在講述景浩成長的艱辛時,沒有簡單將其歸結為個人命運,而是從手機通信行業優化及市場治理等現實困境出發,沒有刻意煽情,使影片更具觀賞性。同時,為使“通俗敘事”與豐富主題有機融合,本片設置了大量極具戲劇沖突的故事情節,增強了景浩人物命運的悲情與苦情,引導觀眾更好地沉浸其中。比如,景浩貸款買的翻新機,受多種因素影響,無法出手了。自己不得不重操舊業,用高空洗玻璃的收入來支付工人的工資。還有臺風來襲,工廠毀于一旦等等大量極具戲劇沖突的故事,在增添敘事內容的同時,使觀眾對景浩的奮進意識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認識。
(二)通俗表達的關鍵:塑造人物群像,引發受眾共情
通俗美學以市場邏輯來解構電影創作邏輯,通過對美學理念進行通俗化、平民化處理,形成新的美學范式。隨著大眾審美趣味的變化不斷調整,文本敘事的復雜性日益突出。為實現理想的敘事效果,不僅要充分挖掘敘事素材,還需要將創作主題與時代特征相融合。[2]影片《奇跡·笨小孩》在敘事過程中,通過采用通俗化表達策略,賦予了觀眾沉浸式的體驗。在講述景浩創造奇跡,從“笨小孩”蛻變為成功企業家時,通過采用小人物群像的方式,以趣味、生動的形式,展現了一大批配角,通過簡單交代各自的背景,再用共同合作、完成任務的方式,講述了“奇跡小隊”的成長軌跡,實現大眾審美心理、觀影體驗的成功升級。此外,合理應用喜劇元素,是增強現實主義題材影片觀賞性,彰顯通俗美學風格的重要策略。本片通過增強人物的辨識度,設置充滿喜感的小人物“劉恒志”“張超”,并且將其與成長主題相融合,不僅彰顯了人物形象及故事情節的真實質感,沒有反噬主角人物的人性光環,反而在生活化敘事、通俗敘事中,生動詮釋了影片的現實主義特色,幫助觀眾更好地見證了創造“奇跡”的精神力量。
(三)通俗表達的超越:淡化理論說教,抒發真實情緒
澳大利亞電影學家理查德·麥特白在《好萊塢電影——1891年以來的美國電影工業發展簡史》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通俗美學”的概念。他認為:“好萊塢是電影通俗美學運作的典范,在電影制作中,通過尊重市場和觀眾的要求,優化配置電影的類型、視聽語言和故事等創意資源,以及檔期、評論等營銷資源,尋找藝術與商業之間的結合點,形成自己的美學慣例,并結合觀眾及市場的變化,不斷推出新的慣例。”①以現實題材為基礎的影片創作,既無法回避真實存在的人生矛盾與現實問題,也不適合采用宏大的“說教式”語言。[3]電影《奇跡·笨小孩》在講述真實生活的同時,注重彰顯個人命運與大時代縱向交織的獨特魅力,通過將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情懷相融合,積極關照現實生活,實現了藝術審美與生活美學的深度融合。通過描述景浩無論處境如何,都始終對未來生活充滿信心的狀態,不僅讓觀眾產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鳴,也讓觀眾在感受溫暖的同時,探尋生活的希望,實現了溫暖親情、善良人性及時代變遷的有機結合。
二、電影《奇跡·笨小孩》的文本敘事策略
在敘事文本語態平民化的背景下,文本敘事逐漸向年輕化、青春化等方向發展,通過聚焦、融入大眾的真實生活,采用平民化的敘事語言,在拉近影片與受眾距離的同時,引起觀眾的情感共鳴,更好地實現影片的敘事價值。電影《奇跡·笨小孩》是一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通過將鏡頭對準小人物奮斗的真實狀況,在詩意化的敘事鏡頭中,力圖呈現真實、自然的社會圖景,描摹了成長與奮進的力量,塑造了品格堅毅且韌性十足的時代青年形象,實現了文本敘事的理想成效。
(一)成長力量的文本呈現
1967年,法國符號學家朱里亞·克利斯蒂娃在《巴赫金:詞語、對話與小說》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文本間性”的概念,認為:“任何文本的生成和存在都具有拼接性質,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來自歷史或時代的其他文本的影響。”②在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創作與主題表達的過程中,無論是人物塑造,還是反映真實生活,都需要融入具體的時代場景,并無法回避命運曲折、成長磨難,乃至生活艱辛等話題。[4]電影《奇跡·笨小孩》以現實主義為創作基礎,積極融入時代語境,深入時代變遷,通過采用小人物的悲喜劇敘事策略,將英雄與平民身份相連接,在淡化成長疼痛感、撕裂感的前提下,凸顯人文關懷,以高于生活的藝術方式彰顯青春氣息、成長氣質,用通俗表達、樸素書寫的方式傳遞奮斗的力量,實現了文本敘事的理想效果。“奇跡”既是個人命運的奇跡,也是時代變遷的“奇跡”。景浩所處的深圳,乃至后來投身的通訊行業,都是在時代變遷中,創造巨大“奇跡”的領域。對于景浩個人而言,雖然自己是無任何優勢的“笨小孩”,但是,其始終在以奮斗者的姿態面對一切困難,最終創造了屬于自己的奇跡。通過對景浩個人成長軌跡的描寫,使觀眾能夠從中體會到大時代賦予他的精神氣質與成長力量。以敘事學理論為基礎,引導觀眾從敘事視角、敘事節奏等角度來解讀“笨小孩”景浩成長的敘事文本,不僅能使其從個人奮斗、堅持不懈等多層次、多視角來理解文本內容,更有助于引導觀眾真正走進影片描述的成長敘事境界。
(二)小人物形象的文本呈現
人物及敘事內容是影片意義構建及主題表達的關鍵載體,也是引發觀眾情感共鳴的切入點。“人物塑造”注重文本敘事,強調情節設計是人物塑造的基本途徑,通過設計完整的故事線索,講述人物命運的復雜變遷,在通俗的表達過程中,將“情節藝術”與人物形象有機融合,進而清晰地表現人物形象,見證時代變化。電影《奇跡·笨小孩》通過將人物塑造與故事情節、主題表達相融合,在合理把握敘事節奏的基礎上,積極融入極具生活質感的故事素材,生動勾勒了以展現鮮活人物性格為核心的敘事格局。景浩從倒騰翻新機的“手機販”成長為“少年企業家”,其成長既源自其為給妹妹做好遺傳性心臟病手術的愿望,也包含著個人對事業的執著追求。觀眾可以從景浩的成長軌跡中,感受到其少年老成,頗有擔當的一面,也能感受到其焦慮、困窘的一面,通過塑造平常、易感的人物形象,使觀眾以“鏡像”的方式,感受到景浩身上蘊含的優異品質,也更加直觀地了解了笨小孩創作的巨大奇跡。除了主人公景浩外,本片以通俗表達的方式,塑造了兼顧個性和代表性的小人物,通過描述梁永誠、汪春梅、張超及劉恒志等身處困境,仍樂觀奮斗的普通人形象,使觀眾對奮斗的時代價值、社會意義有了更加直觀的認識。
(三)回歸生活語言的文本呈現
德國哲學家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提出:“言說語境的喪失成為解讀者理解文本、追尋原初意義的根本障礙,閱讀理解文本時,應遠離作者的意圖及未曾表達的傾向。”①文本敘事高度依賴語言,不僅涉及美學思想和創作理念,更強調發揮敘事語言表情達意的功能,通過淡化敘事主題、豐富故事情節,以個性化的人物形象、鮮明突出的敘事語調,增強影視語言與生活語言的關聯性,賦予觀眾更為鮮活的敘事體驗。[5]電影《奇跡·笨小孩》注重捕捉真實、自然的生活細節,積極傳遞自然、細膩的人物情感,通過將個人命運與時代命運、小家庭命運與國家命運結合,講述了極為現實的人物故事,強調普通人通過努力,必然能實現美好生活,展現了小人物奮斗的時代意義。本片通過“原生態”復制了真實、自然的生活場景,詮釋了源自內心的情感理念,淡化“說教功能”,著重突出了個人奮斗、追逐夢想等話題,使現實主義與敘事內容有效銜接,最終在通俗表達中,既保持了生活美學的現實質感,又有效傳遞了主流價值觀,使觀眾在情感共鳴中,建立起良好的精神認同與情感認知。
三、電影《奇跡·笨小孩》的主題表達
電影藝術是一種時空藝術,通過對故事內容、敘事主題及人物性格等元素進行合理解構,并以視聽語言的方式,投射給觀眾。隨著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創作經驗不斷完善,淡化其“說教式”風格,挖掘更多適應、匹配大眾審美和消費認知的內容,成為同類型影片創作的重要訴求。電影《奇跡·笨小孩》在創作過程中,通過對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變遷,以及對成長、奮進等話題進行深度挖掘,在豐富通俗敘事要素的基礎上,以大眾普適的價值理念,使影像敘事與受眾群體間形成深刻、有效的內在關聯,使受眾獲得了沉浸式體驗和心靈滿足,實現了主題表達與情感交互的理想效果。
(一)小切口、緊湊化的敘事節奏
在現實主義題材影片創作的過程中,以線性時間為敘事基礎,對真實故事、創作主題及現實時空的多元理解進行整合,借助獨特的影視語言,實現故事情節與主題表達的有機關聯。[6]本片通過設計極其緊湊的故事節奏,并限定時間,既回應了受眾的期待心理,也讓人物的成長、動機及心理變化都更加合理了。景浩母親因患心臟病離開人世,將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妹妹留給了他。年僅二十歲的景浩獨自帶著年幼的妹妹景彤來到深圳,由于妹妹遺傳了媽媽的先天性心臟病,她隨時都有生命危險。為了延續妹妹的生命,景浩需要在妹妹八歲之前,為她完成手術。為了給妹妹治病,景浩開始想盡一切辦法湊錢。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景浩收了一批“翻新機”,原本可以掙80萬,就能解決妹妹的手術費了。但是,在國家政策、行業整頓等因素影響下,景浩的翻新機生意泡湯了。面對生存壓力、社會壓力的沖擊,景浩只能拆解殘次機中的零件,將其賣給手機公司,來化解自己的現實困境。但是,景浩想要完成手機零件的拆解,并使合格率達到85%以上,就面臨著既沒有廠房設備,也缺乏啟動資金、人手等一系列困難,這不僅對景浩提出了的嚴峻考驗,也為后來展現景浩的優異品質奠定了基礎。
(二)小人物命運與大時代變遷相融的敘事主題表達
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家茨維坦·托多洛夫在《個體在藝術中的誕生》中提出:“敘事時間是一種線性時間,但故事發生的時間是立體的。在故事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一個復雜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條直線上。”①與傳統的現實主義單線敘事模式不同,電影《奇跡·笨小孩》以多時空演繹、跨年代銜接的方式,構建了完整的敘事脈絡,不僅成功串聯起從2013年到2019年小人物的成長軌跡,在合理的敘事時長內,生動講述了景浩本人的成長歷程,構建起了包含諸多層面的生活圖景,成功激發起了觀眾的注意力與感染力,書寫了人物成長的必然性。影片中反復出現的“螞蟻”意象,既反映了勞動者的工作景象,也象征著景浩能夠承擔起超越普通人幾倍的責任,是其性格的象征。本片不僅生動展現了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成長困境,以相似相通的成長軌跡,通俗地表達了成功奮斗者所具備的強大內驅力,也從側面講述了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命運、時代命運與個人命運的有機融合。
(三)小視角融入與多元化呈現的敘事結構
挪威學者雅各布·盧特在《小說與電影中的敘事》一書中提出:“敘事視角是影片本文結構運作的具體切入角度,不同的視點會構造出不同的敘述層次,形成多種多樣的敘述焦點。”①敘事視角作為影片講述故事的實際切入點,通過采用多元化的敘事結構,重構故事情節,使受眾深刻理解敘事內容、表達主題,最終實現理想的敘事效果。[7]成長是能夠獲得認同感、建立情感共鳴的敘事主題,通過將青春、奮斗、真我等敘事元素融入其中,講述更生動、真實的故事情節,使個人價值在自我認同中得到生動彰顯。電影《奇跡·笨小孩》是以成長為主題的影視作品,以宏大、深層的敘事結構為基礎,積極詮釋了“獲得自我與發現自我”的敘事框架,以相對靈活、年輕的敘事方式,彌合了虛構畫面與現實故事之間的間隙,實現了觀眾體驗與銀幕內容的有機互動。本片選擇極具成長性、開放性的“深圳”作為敘事空間,既見證了城市成長、發展的“奇跡”,也創設了笨小孩產生命運奇跡的情感空間。此外,本片將景浩個人的生活狀況與時代變化、城市發展相融合,在時間線索下,將人物成長置于“深圳”這一快速成長的敘事空間之中,并通過敘事性語言,在多元化呈現敘事主題的基礎上,生動展現了小人物在大時代變遷下的成長巨變,使觀眾能夠快速理解劇情,深刻理解影片的敘事邏輯。
結語
積極回歸人性,深切滿足大眾的集體歸屬感,是當前電影藝術創作的重要方向。電影《奇跡·笨小孩》用大歷史觀來反映客觀現實,通過將通俗表達縫合到影像敘事空間,熟練使用通俗敘事的表達手法來塑造人物、設計故事情節,并用通俗表達的方式,將美好善良的人性、堅持不懈的奮斗精神、溫馨的親情友情等多元主題傳遞給了大眾。面對新的審美語境,在電影作品的創作過程中,創作者應堅持回歸大眾視角,通過詮釋契合大眾審美、符合大眾認知的情感理念,積極回應大眾的審美訴求,進而在強化情感認同、增強情感共鳴的基礎上,實現敘事主題的生動書寫。
【作者簡介】? 王加昕,女,山西臨汾人,山西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戲劇與影視學研究;
曹 飛,男,山西陽泉人,山西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主要從事山西戲曲文物研究。
參考文獻:
[1]岳璐,鄧天一.主旋律青春劇的“綠色”書寫——淺析電視劇《最美的青春》的主題呈現[ J ].中國電視,2019(01):39-43.
[2]張晶,李曉彩.文本構型與故事時空:網絡文學IP劇的“跨媒介”衍生敘事[ 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19(05):78-84.
[3]郭建飛,許德金.引導、評論、深化文本主題——《擁有快樂的秘密》中的類文本及其敘事功能分析[ J ].當代外國文學,2020(01):27-34.
[4]竇玥聲.敘事·主題·色彩:動畫電影的表達手法分析——以《白蛇2:青蛇劫起》為例[ J ].電影評介,2021(15):94-97.
[5]武瑤,王曉璐.文本·時空·人物:論互動劇的交互敘事模式[ 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2021(06):110-114.
[6]劉葉子,張學知.公益求助中的“故事”:敘事文本與傳播效果研究——基于“新浪微公益平臺”網絡籌款能力的考察[ J ].當代傳播,2022(05):71-75.
[7]李琦,王靜.“別現代”語境下新主流劇英雄敘事的文本嬗變與話語博弈[ J ].傳媒觀察,2022(03):34-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