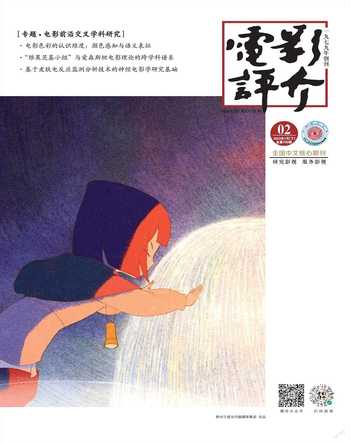抽象中的真實:電影音樂的文化認同功能研究
20世紀20年代晚期,隨著技術(shù)的不斷革新,圖像和包括音樂在內(nèi)的所有相關(guān)聲音終于得以保存在統(tǒng)一的材質(zhì)上,電影迎來了有聲時代,音樂真正成為電影的內(nèi)在元素,成為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電影音樂。電影成為了視聽綜合藝術(shù)。電影中的畫面、光影、人物、情節(jié)等,與電影中的背景音軌、對白以及音樂等一系列元素一起進行組合表達,從視覺和聽覺的維度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意義系統(tǒng)。隨著電影敘事功能的逐步完善,音樂與電影的關(guān)系變得更為復雜了,作為“電影音樂”的音樂,不再只是為了彌補聽覺體驗或是配合電影畫面的附屬品了,而是具有了更為豐富、深刻的作用,“它或為電影體驗的一部分,或為構(gòu)成電影文化背景的一部分。”[1]
最初的電影只是以視覺為導向的娛樂行業(yè)中的一員,憑借其短小且奇特的呈現(xiàn)方式,這種“視覺傳奇劇”成為了傳奇劇場和雜耍場中引人注目的賣點。盡管對于電影誕生初期,音樂是否就從未缺席的事實還存有爭議,但電影史學家們一致認為,在1895年以后,音樂伴奏已是電影放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電影不斷突破其傳統(tǒng)架構(gòu),并最終發(fā)展為一種獨立的娛樂形式后,獨立的電影院也隨之誕生。而電影院的發(fā)展,也為音樂形式的不斷豐富和壯大提供了場所。1910年后,電影院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音樂成為了競爭以及提高影院的聲望的重要營銷噱頭,一些很重要的影院甚至成立了專屬的大型管弦樂團。默片時代(即無聲電影),對于音樂在電影中的作用已經(jīng)引起了電影愛好者、影院經(jīng)營者、音樂評論家等人士的重視,比如劇院的指揮如何用音樂來闡釋電影、音樂伴奏是否適用于該電影等討論成為了重要話題。盡管,音樂與電影的關(guān)系看似密不可分,仍有學者認為,此時的音樂還不能算是電影音樂,只是電影之外的附加物,是整個電影放映活動的一部分而已。
一、音樂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
音樂是否具有意識形態(tài)功能?“意識形態(tài)”(ideology)一詞,最初由法國哲學家德斯蒂·德·特拉西于1796年提出,用以描述一門由他提出的新興學科。[2]在特拉西的構(gòu)想中,該學科通過對觀念和感知的產(chǎn)生、結(jié)果與后果進行系統(tǒng)分析,進而為一般科學知識提供堅實的基礎(chǔ),并得出更為實際的推理,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社會自然調(diào)節(jié)。“通過對觀念和感知的謹慎分析,意識形態(tài)使人性可被認識,從而使社會與政治秩序可以根據(jù)人類的需要與愿望重新加以安排。”[3]也就是說,意識形態(tài)關(guān)乎我們?nèi)绾握J知事物的原本屬性以及如何對其做出判斷,是一整套能夠影響甚至決定我們思考和行動的觀念體系。艾倫·帕·梅里亞姆在其著作《音樂人類學》中提出:“每種音樂體系都是由一系列觀念預示構(gòu)成的,它們使音樂融入全體社會活動……這些觀念決定著音樂的實踐和表演,以及樂音的產(chǎn)生……這些觀念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框架,音樂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人們對于音樂是什么、音樂應該是什么的看法都建立在這個框架之上……”[4]梅里亞姆將音樂放置到“人類整體行為”中來理解,按照不同的觀念來定義音樂的意義,延展了音樂的內(nèi)涵。比如非洲地區(qū)的一些民族認為鳥鳴聲是音樂,但對歐洲人來說就不是,這種差別,完全是觀念不同所致,既然音樂可以作為一種觀念體系,它就能夠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下發(fā)揮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事實上,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將音樂作為“術(shù)”傳遞和重塑觀念的傳統(tǒng)延續(xù)了數(shù)千年:《尚書·舜典》記載了樂師夔將“直而溫,寬而栗,剛而毋虐,簡而毋傲”的道德觀念以樂舞的方式傳授給貴族子弟,“于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5];《史記·周本紀》中記載了周公“制禮作樂”,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袛庸、孝友”[6],將“德音”與“和”的觀念通過音樂教育的方式來重塑個體的行為,于是“民和睦,頌聲興”。音樂使用者正是利用了音樂抽象性,通過對音樂內(nèi)涵的預設(shè),向聆聽者塑造了一個具有想象性的語境,并使聽眾確信這種表達的合理性。通過對音樂內(nèi)涵的重塑,使得音樂內(nèi)容與聽眾產(chǎn)生某種映射關(guān)系,這一過程建構(gòu)了聽眾與音樂之間的想象性關(guān)系。也就是說,聽眾對音樂的聽賞是帶著自己的情感投射和審美想象的,聽眾之所以會有感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聽眾相信音樂所傳達的意義,進而也就認同了作品中所隱含的價值觀。
二、電影音樂如何發(fā)揮意識形態(tài)功能?
電影音樂,無論是原創(chuàng)音樂或是音樂選段,在電影中都具有多重功能。電影音樂既是電影的,也是音樂的。
從音樂的視角來看,電影音樂具有強大的文化暗示功能。音樂普遍存在于人類文化中,是一種無國界的文化現(xiàn)象。但值得注意的是,音樂并非世界通用語言,不同文化賦予了音樂不同的含義,這使得音樂的表達能力以及對音樂的解讀能力會因人們所處的文化語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文化意識通過音樂來彰顯自身。不同的音樂可能指涉特定的歷史時期:比如編鐘音樂能夠喚起國人對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聯(lián)想;也可以指涉特定的國家:比如由尺八音樂聯(lián)想到日本,由風笛音樂聯(lián)想到蘇格蘭等;甚至可以指涉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比如由布魯斯音樂聯(lián)想到酒吧,由古典音樂聯(lián)想到音樂廳,這些音樂因產(chǎn)生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與特定的含義聯(lián)系在一起,于是就能夠在特定場景中傳達特定的含義,從而形成一種蘊含文化意識的音樂慣例。音樂慣例在文化中根深蒂固,以音樂的集體無意識發(fā)揮作用,無論聽眾是否意識到這種慣例,都會受到影響。比如:詹姆斯·霍納為《勇敢的心》作的配樂中,大量運用了風笛和愛爾蘭哨笛,高亢的風笛與明亮的哨笛聲瞬間將人帶入了廣袤的蘇格蘭高地,與影片所呈現(xiàn)的故事背景相得益彰,能夠使觀眾在無意識的情況下自行融入這個來自他鄉(xiāng)的遙遠的故事,增強了故事的“真實性”。個體之所以能夠“理解”這些音樂所帶來的情緒體驗或者審美體驗,是因為在聽賞這些音樂之前,個體已經(jīng)具備了相關(guān)的文化背景和足夠的知識儲備,這決定了個體能在音樂中聽到什么。
在約翰·威廉姆斯為《星球大戰(zhàn)》所作的配樂中,和弦的運用、打擊樂的節(jié)奏推進方式、弦樂通過顫音所產(chǎn)生的緊迫感等,都大量借鑒了古斯塔夫·霍爾斯特于1914年—1916年期間所創(chuàng)作的《行星組曲》中《火星》篇章的創(chuàng)作手法(這一樂章完成于一戰(zhàn)前,被認為是預示了戰(zhàn)爭爆發(fā)的寓言之作,作品運用了大量的打擊樂,配合弦樂用弓子敲擊所產(chǎn)生的獨特音效,制造了大戰(zhàn)在即的緊迫感),為影片中由于銀河系共和國解體,帝國崛起,而導致反抗軍與黑暗勢力抗爭的故事背景定下了基調(diào),對音樂表現(xiàn)手法的認知,比如鼓之于行軍的隱喻、不和諧的音程之于緊張感等,能夠在不知不覺中引導觀眾進入故事的敘事節(jié)奏當中,感受到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的緊張感。有趣的是,威廉姆斯所創(chuàng)作的“星球大戰(zhàn)”的主題曲則是直接運用了與在埃里希·科恩戈爾德為于1942年為影片《金石盟》(Kings Row)所創(chuàng)作的電影配樂中非常相近的音行來致敬這位作曲家,這當中很難排除作曲家受到自身音樂知識積累的影響。作曲家們在為影片配樂時,如何選取創(chuàng)作所需的音樂素材抑或通過風格、音色等特定形式結(jié)構(gòu)以實現(xiàn)音樂自身的可理解性,從而配合影片的發(fā)展,取決于作曲家所受的音樂訓練和文化意識,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音樂慣例。電影作曲家們會依賴音樂慣例來引導和控制觀眾的反應,隨著電影情節(jié)的推進,引導觀眾的情緒和心理。基于音樂慣例,音樂能夠在觀眾與銀幕之間創(chuàng)造情感共鳴,令觀眾產(chǎn)生情感回應,這樣一來,電影音樂使觀眾忽略了電影的虛擬性,具有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控制功能,使觀眾進一步融入影片,甚至失去判斷能力,全盤接受電影中傳遞的文化價值。正如皮埃爾所說:“影視音樂并不只是影視畫面的陪襯。音樂本身及其內(nèi)涵都在一定程度上傳遞了觀眾的價值取向和時代觀念。”[7]
從電影的視角來看,電影音樂能夠讓意義在不同層面具象化。“電影音樂中音樂并非純粹的音樂,而是一個更大的意義系統(tǒng)中的一部分。”[8]電影是一種視聽藝術(shù),也是一種敘事媒介,電影中的音樂作為這個敘事系統(tǒng)中的組成部分,必須在這樣一個大的設(shè)定下來進行。音樂作為一種時間的藝術(shù),能以一定的形式特征,使人聯(lián)想起敘事文本的結(jié)構(gòu),使其能以敘事范疇來表述音樂體驗。
電影音樂規(guī)定了觀眾感知敘事的視角,影像賦予其指稱性而使音樂更加明晰,將音樂的普通表現(xiàn)力特殊化。比如:歐洲傳統(tǒng)宗教音樂中,常使用管風琴演奏(其演奏場所只限于教堂),為人們制造一種“神圣且浩瀚”的聲音,但這種概念是抽象且模糊的,當漢斯·季默將代表了人們對超越世俗生活、超越已知世界、渴望探索未知的管風琴音樂運用到影片《星際穿越》中,觀影者看著浩瀚的宇宙時,管風琴音樂實現(xiàn)了與視覺的匹配,對音樂內(nèi)容的聯(lián)想有了具體的投射,音樂支持和構(gòu)造了電影敘事,而影像則為音樂提供了具體的想象對象;電影音樂可以對影像進行特殊化處理,能夠在眾多意義中強化某一種,比如:馬斯卡尼創(chuàng)作的獨幕歌劇《鄉(xiāng)村騎士》中的《鄉(xiāng)村騎士間奏曲》分別被運用到《教父3》《陽光燦爛的日子》《立春》《導盲犬小Q》等多部影片中,成為眾多影片中的經(jīng)典配樂。這部歌劇描寫了一個悲劇的故事,該間奏曲出現(xiàn)在歌劇的第八幕與第九幕之間,預示著危機重重的故事走向以及男女主人公即將到來的悲劇結(jié)局,樂曲本身包含了諸多復雜的情緒。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將樂段運用在馬小軍對米蘭迷戀與向往的場景中時,音樂本身所蘊含的對結(jié)局未卜的迷茫感便恰如其分地烘托了主人公青春的迷惘;《教父3》中,教父在歌劇院門口遭遇槍襲導致最愛的女兒當場死去,這時《鄉(xiāng)村騎士間奏曲》悄然滑入,音樂作為一條紐帶,呈現(xiàn)了他與女兒跳華爾茲、與妻子在婚禮上擁舞的回憶場景,回憶過后,白發(fā)蒼蒼的教父坐在夕陽下,一人一狗,迎接生命的終點,樂曲本身所蘊含的對美好過往的追憶、對男主角決斗失敗被殺、對故事結(jié)局的哀嘆也恰好映射了教父最美好的回憶、最痛徹心扉的失去以及人生的落幕,為電影中表現(xiàn)的情感提供了聲音定義,令觀眾產(chǎn)生情感共鳴。
三、電影音樂的文化認同價值
電影音樂具備強大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這就提示我們在觀影時,不能簡單地去理解音樂附著在電影中所傳達的表層含義,而是應該關(guān)注為什么會采用這樣的模式來為電影配樂。比如:在描寫宏大的場面的時,通常會采用恢宏的交響樂來配合畫面,在某個寧靜的時刻,舒緩的鋼琴聲就會響起;大調(diào)式能喚起明亮的愉悅感和正義感,而小調(diào)式則會喚起暗淡的憂傷與哀愁;和諧的音樂烘托秩序與平和,不和諧的音樂則暗示失衡與瘋狂,這種音樂體系主要是建立在西方音樂對十二平均律的廣泛使用以及和聲概念之上的,但世界上還有很多音樂體系,比如中國傳統(tǒng)音樂藝術(shù)是以線性形態(tài)、單音體系和五聲、七聲結(jié)構(gòu)為主的(中國的音階體系十分豐富,但明代朱載堉確立的十二平均律,最終卻落得“宣付史官,已備稽考,未及施行”的結(jié)局,十二平均律在17世紀傳入歐洲,才得以發(fā)展壯大);印度音樂和中東地區(qū)的音樂是依靠即興創(chuàng)作來發(fā)展的。作曲家在創(chuàng)作時,會采用某種模式來進行創(chuàng)作,事實上已經(jīng)默認了某種“本該如此”的模式,甚至一些作曲家只按照音樂慣例來配樂,好像只要是影片到了某一高光時刻,就要使用大編制的樂隊音樂,明示“淚點”的到來,這樣的刻意為之反倒令觀眾出戲,影響了其觀影體驗。電影建構(gòu)的并不是某個虛無縹緲的世界,而是用以表達自己和了解他人的象征形式,它部分地構(gòu)成了社會“真實”的一面,電影通過影像傳遞價值觀,潛移默化地影響觀眾的價值觀,影響創(chuàng)作者的價值觀,而很有可能創(chuàng)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某種價值觀,電影音樂貫穿于其中,同樣如此。電影音樂的影響力甚至比影片更加深遠,當觀眾走出電影院后,不一定會反復觀看影片,但配樂卻可能出現(xiàn)在任何一個不可預見的地方,可能是咖啡店、西餐店,甚至路邊的某個廣告中,時刻暗示個體,只有你認同某種價值觀,你才會獲得某種身份或立場。
正因如此,音樂文化同樣可以通過電影獲得一定程度的重塑。最經(jīng)典的例子,莫過于嗩吶主奏的樂曲《小刀會序曲》。《小刀會序曲》是商易先生為中國民族舞劇《小刀會》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作品描寫了1853年8月上海地區(qū)爆發(fā)的為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王朝的雙重壓迫而爆發(fā)的小刀會起義,這段音樂在周星馳主演的《大話西游之大圣娶親》中被用來作為至尊寶登場的音樂,以烘托英雄人物的形象,同樣的一段旋律被徐克用到《龍門飛甲》的片頭,為影片反抗暴政的英雄行為奠定了基調(diào),通過這些影片為觀影者建立了一種心理暗示:當有(正面的)重要人物或者事件(尤其是具有反抗性的事件)出現(xiàn)時,嗩吶音樂便成為一種恰當?shù)倪x擇。嗩吶音樂不再僅限于人們通常認知中婚喪嫁娶等民俗中所使用的野腔濫調(diào),是成為一種有震撼力的、正面的音樂形象,通過電影這種更為隱蔽而廣泛的方式,使嗩吶音樂文化實現(xiàn)了重建,重獲認同,并得以傳播和推廣。(歷史上,出自波斯、阿拉伯的嗩吶從金、元時期傳入中原之后,一直用于軍隊的鼓吹樂中,為軍中之樂,直到明代末期,嗩吶才從官府和軍隊的專屬樂器逐漸走入民間。)近年來,這樣的嘗試比比皆是:電影《英雄》的配樂中,作曲家使用了古琴,古琴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歷來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占據(jù)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件樂器從上古時期作為與神溝通的法器,到成為士大夫修身理性的重要載體,正是由于其包含的特殊的非器樂性與非觀賞審美性,使得古琴音樂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非常神秘,通過電影片段,使古琴音樂有機會“走下神壇”,展示在大眾面前;在電影《臥虎藏龍》的配樂《離》與《絲綢之路》中,使用了二胡來與大提琴的配合,優(yōu)美的旋律充分展現(xiàn)了二胡柔美而深沉的音色特點,也讓這件在很長一段時間背負著“惡名”的樂器獲得了嶄新的面貌。電影音樂向內(nèi)可側(cè)重文化的根植,向外可關(guān)注聽眾的意識,因此,它應當被視為音樂文化在文化領(lǐng)域中的延伸,要將電影作為一種載體或媒介,來傳播中國音樂文化。
結(jié)語
費孝通先生定義“文化自覺”為:“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發(fā)展趨勢,不帶任何‘文化復歸的意思,不是要重復,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tǒng)。”[9]但有自知之明顯然是不夠的,好比我們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來龍去脈如數(shù)家珍,卻備而不用,甚至束之高閣一樣。活態(tài)的傳承一定是建立在認同之上的,這事關(guān)我們從事文化活動的初心和訴求以及對自身文化感知方式的選擇。電影音樂作為現(xiàn)代社會一種重要的音樂文化感知方式、表達形式和表征媒介,有力量去影響認同的建構(gòu)、延續(xù)和轉(zhuǎn)變,通過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實現(xiàn)文化自主性,從而提升文化自信。
【作者簡介】? 羅章菡,女,貴州貴陽人,貴州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1][挪威]彼得·拉森.電影音樂[M].聶新蘭,王文斌,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9:7
[2][3][英]約翰·B·湯普森.意識形態(tài)與現(xiàn)代文化[M].高铦,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30,31-32.
[4][美]艾倫·帕·梅里亞姆.音樂人類學[M].穆謙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65.
[5]吉聯(lián)抗.呂氏春秋中的音樂史料[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54.
[6]徐正英,常佩雨譯注.周禮·春官·大司樂[M].北京:中華書局,2014(02):477.
[7][法]皮埃爾·貝托米厄,著,楊圍春,馬琳譯,電影音樂賞析[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5(03):1.
[8][美]凱瑟琳·卡利納克.電影音樂[M].徐黎,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21:16.
[9]費孝通,文化與文化自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6(07):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