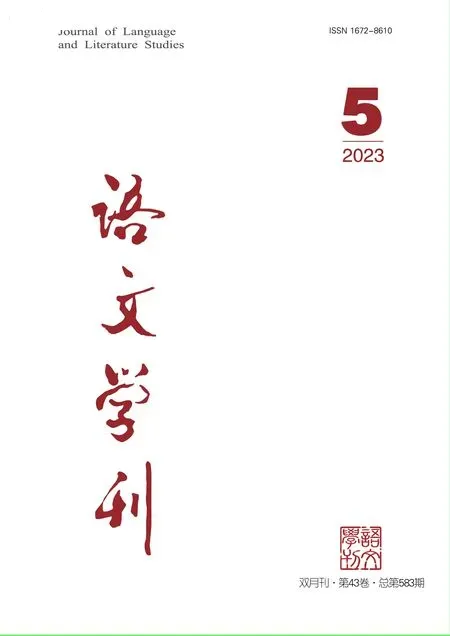翻譯中的文化轉(zhuǎn)換
○ 李玲
(四川外國語大學(xué)成都學(xué)院,四川 成都 611800)
一、引 言
中西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所處理的語言材料不同,所屬的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即其涉及彼此不同的語言文化、翻譯材料和思想體系,因此彼此之間在翻譯實(shí)踐和翻譯理論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差異。而在翻譯理論和翻譯實(shí)踐方面,中西不同的翻譯傳統(tǒng)必定受到各自所屬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和制約,深深地刻上各自社會文化的烙印,顯現(xiàn)出各自相關(guān)社會文化的特點(diǎn)[1]。
我國翻譯界的文化學(xué)派認(rèn)為: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民族之間語言的交流,實(shí)質(zhì)上是不同民族之間文化的交流。在語言的交際過程中,除了對語言本身的理解,不同民族的人對語言文化所負(fù)載的文化意蘊(yùn)的理解也至關(guān)重要[2]。“必須對翻譯(translation)這一術(shù)語有著全面和全新的理解:從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譯(轉(zhuǎn)換)逐步拓展為對文化內(nèi)涵的翻譯(形式上的轉(zhuǎn)換和內(nèi)涵上的能動性闡釋),因此研究翻譯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問題,尤其涉及兩種文化的互動關(guān)系和比較研究。”[3]“譯者的任務(wù)就不僅僅是從語言上再現(xiàn)原作,他要對目標(biāo)語文化的構(gòu)建做出自己的貢獻(xiàn)。應(yīng)該說,這正是所謂的‘文化學(xué)派’翻譯研究者的一個重要使命。”[4]
英國著名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奈特認(rèn)為:翻譯絕不是一個純語言的行為,它植根于語言所處的文化之中。翻譯就是文化內(nèi)部和文化之間的交流。在翻譯研究的文化觀中,文化是翻譯的單位,不同文化的功能等值是手段,文化的轉(zhuǎn)換才是翻譯的根本目的。可以說,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轉(zhuǎn)換,翻譯從本質(zhì)上來說是一種行為,所以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行為”。“語言是文化這個身體的心臟,只有語言和文化之間相互合作活動,身體才能保持精力充沛。”[5]22語言是文化內(nèi)部不可分割的部分,譯者如果精通兩種或多種文化,也就相應(yīng)地精通兩種或多種語言。
那么,所謂翻譯,無非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活動,通過一種語言轉(zhuǎn)達(dá)另一種語言的文化信息,因此可以說任何翻譯都離不開文化。中國翻譯理論家張今對翻譯的定義是:“翻譯是兩個語言社會(Language-community)之間的交際過程和交際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進(jìn)本語言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jì)和(或)文化進(jìn)步,它的任務(wù)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現(xiàn)實(shí)世界的邏輯映象或藝術(shù)映象,完好無損地從一種語言中移注到另一種語言中去。”[6]這表明翻譯的根本任務(wù)和重大意義正是進(jìn)行文化交流,促進(jìn)社會進(jìn)步。
二、中西文化對比對翻譯中文化轉(zhuǎn)換的意義
魯迅說:“如果還是翻譯,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覽外國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時何地,有這等事,和旅行外國,是很相像的:它必須有異國情調(diào),就是所謂的洋氣。”[7]那么,這里的“異國情調(diào)”指的是什么呢?顯然,魯迅指的不是在語言上的一味模仿翻譯,而是指在文化上的轉(zhuǎn)換和傳譯,要保留原文所蘊(yùn)含的異域文化意象。這說明,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處理的妥當(dāng)與否是翻譯是否成功的關(guān)鍵。這就涉及文化在翻譯方法歸化和異化中的處理。翻譯中的歸化(Domestication)和異化(Foreignization),主要指的是翻譯中介入文化因素時對文化的處理方法。達(dá)到“功能對等”和“文化功能對等”是翻譯中歸化和異化處理文化的基本原則。
(一)中西心理文化和語言文化對翻譯的意義
在考慮文化翻譯的同時,首先要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漢語和英語作對比,我們就主要從心理文化和語言文化方面予以對比。
1.中國人重形象和悟性思維,而西方人重邏輯和理性思維。漢語的形象性、具體性和英語的功能性正體現(xiàn)了這種心理文化的差異。中國古代的甲骨文就是象形文字。如“人”(man)字像分腳站立,頂天立地的人的形象;“門”(door)字像左右兩扇門的形狀;“魚”(fish)字是一尾有魚頭、魚身和魚尾的游魚;“月”(moon)字像一彎月亮的形狀;“日”(sun)字就像一個圓形,中間有一點(diǎn),很像人們在直視太陽時,所看到的形態(tài)。漢語用詞傾向于具體,常常以實(shí)的形式表達(dá)虛的概念,以具體的形象表達(dá)抽象的內(nèi)容。如“噤若寒蟬”(keep quiet)、“藕斷絲連”(have not cut off relationship completely)、“牽腸掛肚”(be full of anxiety and worry)和“歸心似箭”(be very anxious to return home)。此外,漢語豐富的量詞也體現(xiàn)了形象性。如“一支筆”(a pen)、“一朵花”(a flower)、“一棵樹”(a tree)和“一輛自行車”(a bike)。而以上例子的英文表達(dá)體現(xiàn)出英語強(qiáng)調(diào)功能性和西方人注重理性思維的模式。
2.中國人重綜合,西方人重分析。中國文化屬于人文文化,重綜合、重意會,崇尚群體意識、強(qiáng)調(diào)同一性,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把人與自然看成渾然一體。西方文化屬于科學(xué)文化,重分析、輕綜合,重概念、忌籠統(tǒng),主張個人至上,強(qiáng)調(diào)人與自然的對立,人對自然的索取[8]。這兩種思維方式的差異體現(xiàn)在語言中,形成漢語詞義一般較概括,英語詞義一般較準(zhǔn)確的特征。如漢語里的“喝酒”,“酒”在英語里可以具體到wine,liquor,spirit,beer,rum,gin和alcohol;“搭車”的“車”在英語里也可以有多種表達(dá),可以指vehicle,car,truck,lorry,cart,bus和taxi。如果要用英語表達(dá)“她是一個好人”,“人”在漢語里是個較籠統(tǒng)的詞,而譯作英語就必須明確“She is a goodwoman.”。再如,漢語里常說的寒暄語“你吃飯了嗎”,漢語一般并不明確說是早飯(breakfast)、午飯(lunch),還是晚飯(supper),根據(jù)問話的時辰就能明白所指。但在英語里必須得具體表明,而且英語里還可指“brunch”(早午餐)。
3.漢語多使用對仗修辭的四字格。中國傳統(tǒng)哲學(xué)思想提倡“中庸”,中正平和,不偏不倚,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以平衡勻稱為美,這一傳統(tǒng)的美學(xué)觀念體現(xiàn)在語言上則表現(xiàn)為漢語里對仗的四字格。如“天造地設(shè)”(created by nature; ideal)、“翻天覆地”(a great and thorough-going change)、“排山倒海”(great in momentum and irresistible)和“四通八達(dá)”(extend in all directions)。
4.漢語重“意合”,英語重“形合”。在傳統(tǒng)上,中國人信奉天人合一、重歸納推理、重暗示含蓄、重言簡意賅,而西方的傳統(tǒng)思想哲學(xué)重邏輯分析、重理性和抽象思維、重立論推理。因此,漢語重意形契合,而不注重形態(tài)或形式,句子結(jié)構(gòu)就像一根竹子,層次分明,嚴(yán)密緊湊,所以稱漢語為竹式結(jié)構(gòu)(bamboo-like structure)。英語特別注重形態(tài)和形式,句子結(jié)構(gòu)就像一棵大樹,主干突出,枝葉茂盛,枝干多借助介詞、連詞、分詞等連接手段層層搭架,所以稱英語為樹式結(jié)構(gòu)(tree-like structure)。漢語重意合(parataxis)指強(qiáng)調(diào)邏輯關(guān)聯(lián)與意義關(guān)聯(lián),不在意詞語之間和句子之間的形式銜接。英語重形合(hypotaxis)指強(qiáng)調(diào)形式和功能。這一特點(diǎn)體現(xiàn)在句子結(jié)構(gòu)上,漢語句子建構(gòu)在意念主軸(thought-pivot)上,句子強(qiáng)調(diào)的是意義,重在意義的表達(dá),不是結(jié)構(gòu)。漢語句子中的主語并不十分重要,有的主語不明顯,還有許多無主句(subjectless sentence),但并不影響句子意義的表達(dá),句子意義仍然一目了然。英語句子建構(gòu)在形式(或主謂)主軸(form-pivot)上,句子強(qiáng)調(diào)結(jié)構(gòu)的完整,特別是要有主語和謂語,其他成分在結(jié)構(gòu)形式完整的前提下也大多必不可少。英語句子中的主語就十分重要,大多數(shù)句子都有主語,主語的位置和表現(xiàn)形式對句子的意義至關(guān)重要,具備“一發(fā)牽動全身”的功能。
(二)語用對比對翻譯文化的意義
語用對比對翻譯文化產(chǎn)生了重大的意義。中國傳統(tǒng)的一些詞語在英語里沒有完全對應(yīng)詞,如陰、陽、抓周、闖江湖等,這就造成語用失效(pragmatic failure)。實(shí)際上,語用失效源于語用沖突(pragmatic conflict),而語用沖突的產(chǎn)生在根本上是由于文化沖突(culture conflict)。如“貓頭鷹”在西方文化中象征智慧,可在中國文化中它只是一只夜間捕食的普通鳥,與智慧完全搭不上邊。“蝙蝠”在中國文化中諧音“福”而被視為“福”鳥,可在西方文化中它卻象征邪惡。同樣,“龍”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是權(quán)勢、高貴、尊榮的象征,又是幸運(yùn)與成功的標(biāo)志,可是在西方文化中,龍卻是邪惡和暴力的象征。如果要將“望子成龍”譯成英語“l(fā)ong to see one’s son become a dragon”,西方人就無法理解,只有加注譯“win success in the world”,或者意譯為“l(fā)ong to see one’s son succeed in life”來彌合中西文化上的差異。再比如,在廣告或商業(yè)品牌的翻譯上,也必須結(jié)合中西方的審美心理與文化。“芳芳牌牙膏”,漢語里的“芳芳”會讓人產(chǎn)生美的聯(lián)想,一位花容月貌周身散發(fā)香氣的少女緩緩走來,可是如果英語音譯為“Fang Fang”則會讓西方人大驚失色,避而遠(yuǎn)之,因?yàn)椤癋ang”在英語里的含義指的是“狗或狼的長牙”(long sharp tooth,esp.of dogs or wolves)或者“蛇的毒牙”(snake’s tooth with which it injects poison)。“白象牌方便面”,“象”與“祥”諧音,所以白象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象征吉祥、穩(wěn)重、權(quán)威等,寓意美好,但如果英語譯為“White Elephant”,寓意就完全變了,因?yàn)榘紫笤谟⒄Z里指“累贅、廢物、大而無用的東西、貴重卻有害的贈品”(possession that is useless and often expensive to maintain)。
三、文化轉(zhuǎn)換的翻譯策略
翻譯作為文化交流的工具,其核心問題是“異化”和“歸化”。“異化翻譯”(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和“歸化翻譯”(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是實(shí)現(xiàn)文化轉(zhuǎn)換的重要翻譯策略。“前者主張譯文應(yīng)以源語或原文作者為歸宿,后者則主張譯文應(yīng)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9]翻譯已不再僅僅停留在語言層面上,更涉及兩種語言背后的文化轉(zhuǎn)換。異化的翻譯以源語文化為歸宿,歸化的翻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
如何處理好這兩者的關(guān)系呢?美國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dá)的“功能對等”理論要求“原語與譯語之間語言與文化的最大程度的對等”[10]。根據(jù)奈達(dá)的“功能對等”和英國翻譯理論家蘇珊·巴斯奈特的“文化功能對等”理論,如果文化的共性在理解上進(jìn)行文化意象的移值不存在障礙,可直接將原語成語或比喻傳譯到譯語中去;如果文化的個性存在沖突,原語和譯語中成語和比喻的意象各不相同,從譯語讀者接受效果的角度考慮,可將原語文化的功能傳譯到譯語文化中以達(dá)到功能等效的目的。所以,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yīng)盡量在譯語文化中找到與原語文化的對等功能。
“習(xí)語的翻譯使我們進(jìn)一步考慮到意義和翻譯的問題,因?yàn)榱?xí)語,如雙關(guān)語,與文化緊密相連。”[5]30中西文化和語言中有很多表達(dá)完全一致的語句,給人鬼斧神工、渾然天成的感覺,用異化的方法處理中西文化都能夠接受。如ivory tower,paper tiger,a castle in the air,to 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和Walls have ears.在漢語中則說“象牙塔”“紙老虎”“空中樓閣”“趁熱打鐵”和“隔墻有耳”。而有些語句用歸化的方法處理,英漢語之間雖說不上完全一致,但有異曲同工之妙,中西文化成功傳譯。如英語的成語“A drop in the ocean”類似漢語的“滄海一粟”;“to shed crocodile tears”類似漢語的“貓哭耗子假慈悲”;“New booms sweep clean”類似漢語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此類表達(dá)還有“笑掉牙齒”(to laugh off one’s head)、“亂七八糟”(at sixes and sevens)和“一箭之遙”(as a stone’s throw)。再如,關(guān)于中西文化移植有一個生動的例子。一個中國人去游泳,去了看看就回來了,原因是游泳池里人太多,水太臟,早該換了,那場景簡直就像芝麻醬煮餃子。中國人熟悉芝麻醬煮餃子的情形,覺得這個比喻很別致、生動。但如果照直翻譯,多數(shù)外國人都會不知所云,因?yàn)樗麄兏静恢乐ヂ獒u和餃子是何物,更談不上覺得這個比喻幽默了。可如果用歸化的方法譯成“It was packed like sardines.”,“sardines”指罐裝的沙丁魚,這個情形和“芝麻醬煮餃子”情形大致相似,都表示“人多擁擠”,在功能上兩者是對等的,外國人就能明白這句話的含義。然而,中西文化既存在文化的共性,也存在文化的個性,正因?yàn)槲幕瘋€性的存在,中西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異化的翻譯方法才有了理論上的依據(jù)。除了前面提到的,還有很多例子成功地用異化翻譯方法實(shí)現(xiàn)了中西文化之間的傳譯,達(dá)到功能對等。例如,“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謀事在人,成事在天)、“to praise to the skies”(捧上天去)、“to fish in troubled waters”(渾水摸魚)、“to add fuel to the fire”(火上加油)和 “to be on thin ice”(如履薄冰);還有“時間就是金錢”(Time is money.)、“酸葡萄”(sour grapes)、“滾石不生苔”(A rolling stone gathers no moss.)、“一石二鳥”(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和“條條大路通羅馬”(All roads lead to Rome.)。異化翻譯方法有利于中西文化和語言之間進(jìn)行相互交流和滲透,促進(jìn)彼此之間的交融。
四、結(jié) 語
我國許多翻譯家、翻譯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都比較重視文化與翻譯的關(guān)系。王佐良說:“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人們都說:他必須掌握兩種語言,確實(shí)如此;但是,不了解語言當(dāng)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11]譚載喜說:“翻譯中對原文意思的理解,遠(yuǎn)遠(yuǎn)不是單純的語言理解問題。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它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對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確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對有關(guān)文化的了解。對于譯者來說,沒有兩種文化的對比知識,就無從談起對語言文字的正確理解與表達(dá)。”[12]因此,譯者不能只是從事著語言之間的轉(zhuǎn)換,還要具有強(qiáng)烈的文化意識,做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
綜上所述,任何翻譯都離不開文化,翻譯和文化密不可分,實(shí)現(xiàn)文化轉(zhuǎn)換是翻譯的根本目的;進(jìn)行文化交流,促進(jìn)社會進(jìn)步,是翻譯的根本任務(wù)。中西文化的對比實(shí)現(xiàn)和促進(jìn)了翻譯中的文化轉(zhuǎn)換,中西文化在心理文化和語言文化方面對漢語和英語的形成和發(fā)展,特別是對兩種語言之間的相互翻譯有著重大的意義,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而語用對比對翻譯文化的意義也舉足輕重。根據(jù)奈達(dá)的“功能對等”和巴斯奈特的“文化功能對等”理論,譯者在采用歸化和異化這兩種翻譯方法時,可進(jìn)行文化意象的移植,要盡量將原語的文化功能傳譯到譯語文化中,達(dá)到功能等效的目的。譯者要有強(qiáng)烈的文化意識,要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