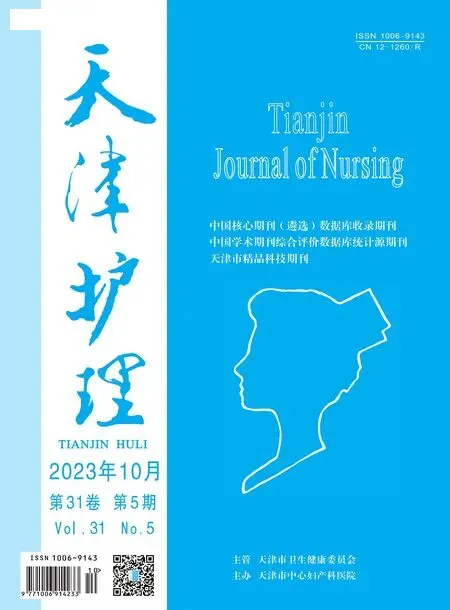家庭賦權護理在早產兒父母中應用的研究進展
漆永林 尹麗
(1.大理大學,云南 大理 671003;2.昆明市兒童醫院)
據統計,中國早產數量是僅次于印度排名世界第二的國家,發生率為6.9%[1]。隨著“全面二孩”政策的開放,高齡產婦的生育意愿較為強烈及輔助生殖醫學的發展,早產兒的出生率將持續增長[2-3]。當前,對早產兒的關注點不再局限于生存問題,也將后期生活質量納入關注范圍。尤其是早期和中期早產兒出生后,由于各系統發育不完善,需入住新生兒重癥監護室(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獲取病理和生理方面的支持。一方面,住院期間父母常因親子分離、對疾病的不確定性和育兒知識的缺乏,常感到悲傷、焦慮和抑郁,使之不能順利適應父母角色[4];另一方面,早產兒出院后的家庭護理有別于足月新生兒,照護經驗缺失的父母不利于早產兒家庭照護的開展[5]。家庭賦權護理通過賦予父母一定權力,使其獲得相關知識、技能和資源,可以縮短早產兒住院時長,提升母乳喂養率和照顧準備度,加強父母與孩子的親子活動,從而促進父母心理健康及家庭的構建[6-9]。因此,家庭賦權作為一種過渡式的護理模式,可滿足早產兒持續發展和父母照顧需求。目前,家庭賦權護理被廣泛應用于慢性病管理以提升患者及照顧者的生活質量[10],而在早產兒家庭應用的報告較少。本文綜述國內外家庭賦權護理在早產兒父母中的應用,以期為家庭賦權在我國早產兒護理領域的發展提供參考依據。
1 家庭賦權概述
20 世紀70 年代初巴西教育學家Paulo Freire首次提出了“Empowerment”,即賦權,意為“賦予權力,能動的做某事”,隨后逐漸應用于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等多個領域[11]。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領域在關注到WHO 提出“健康賦權”的概念后,家庭賦權應運而生[12]。家庭賦權強調賦權程度與賦權能力,注重患者和家庭成員獲得知識、能力和行為的表達方式,旨在發揮家庭在健康促進中的重要作用[13]。在自閉癥、哮喘患兒的應用中主要強調患兒及家庭的生活質量[14-15]。中國家庭結構較傳統而言發生了明顯變化,同住人員從多人向3 人及以下轉變[16]。此外,早產事件發生后父母想通過后期高質量的照顧彌補[17]。這說明早產兒父母是家庭賦權的主體。本文家庭賦權護理指賦予患者家庭成員(主要指早產兒父母)部分權力以調動積極性,使其參與到診療及護理決策中,與醫護人員共同制定照護計劃,幫助家庭成員學習并獲取照顧知識、技能和資源。近年來,“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理念成為研究熱點,在早產兒護理領域興起了家庭參與式護理、以家庭為中心的護理等模式,其目的在于讓家屬參與到早產兒的照護活動中[18]。因此,家庭賦權已融入到早產兒的護理活動中。
2 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中應用的基本要素
美國學者UMBERGER 等[4]對NICU 患兒父母行家庭賦權總結出4 個基本要素:尊重、控制、單獨的家庭房間、社會心理支持。尊重是實施家庭賦權的前提,需醫護與患兒父母共同促進。家庭賦權護理的實施過程中,護理人員應將父母視為促進早產兒康復的護理合作伙伴,尊重他們合理的要求,并做出正確的應對策略[19-20];患兒父母則需相信醫護是促進患兒康復的重要人員。早產兒進入NICU 使父母產生了預期照顧足月新生兒與現實親子分離的矛盾,對父母來說是失去控制的感覺[8]。鑒于此情況,護理人員應確保父母能及時探望剛出生的孩子,并支持后續的探視。此外,家庭賦權護理的實施應聽取并合理采納早產兒父母及相關人員的建議,使本項目得到質量的控制。研究[19]表明,與NICU 大房間相比,單獨的家庭NICU 房間可以為父母及患兒提供更多的隱私,促進親子活動,增加親密度。早產兒進入NICU后,父母認為自己無法履行理想的父母角色而感到壓力、焦慮和抑郁[21]。除醫務人員提供足夠的心理支持外,同伴支持作為社會支持的一種,由具有相似經驗和性格的社交網絡伙伴提供情感、評價和信息等支持,可緩解父母焦慮、抑郁等情緒[22]。
3 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中實施的步驟
為父母賦權創造機會(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Parent Empowerment,COPE)計劃是MELNYK 等[23]在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的理論基礎上,為改善母親應對結局和嬰兒認知障礙而開發的。COPE 計劃是一種理論與實踐并重的家庭賦權方式。COPE 計劃一般以小冊子(含圖片和文字)、錄音或面對面的形式開展,具體實施步驟可歸納為以下4 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患兒入住NICU 的2~4 天,向父母介紹NICU的環境及早產兒的特性;第二階段是從第4~8 天,講解早產兒照護知識并鼓勵父母參與到早產兒的護理中;第三階段為出院前1 周,強化并評估父母關于早產兒的照護信息;第四階段為出院2 周后的家庭隨訪[24-25]。VOICE(The values,opportunities,integration,control,and evaluation)計劃是一種從產前到出院后全過程的賦權,利用5 次會議,每次會議的重點分別是價值觀、機會、整合、控制、評估,支持和賦予早產兒父母權能[26]。我國對早產兒家庭賦權護理的落實主要以傾聽、對話、反思和行動為主題,主要步驟包括:傾聽需求,調節負面情緒;了解賦權意愿,初次評估照護能力;開展理論講座、模型實操、知識測試等多種形式的教育;制訂和實施個性化父母參與護理計劃,最后評估掌握情況[9]。我國學者吳倩[27]為NICU早產兒父母構建的賦權方案是在COPE 計劃基礎上添加了入院24 小時這一階段,主題包括熟悉環境,消除疑慮;知識宣教,擬定護理計劃;部分賦權,床旁參與照護;完全賦權,指導照護;出院隨訪,延續照護。國內外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的研究中,主要利用多種形式的理論教育和實踐指導滿足父母的照護需求,并在這一過程中提供情感支持。
4 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中實施的效果
4.1 縮短早產兒住院時長
早產兒的病死率高于其他任何年齡組,導致早產兒入住NICU 的時間延長[28-29]。家庭賦權的實施使父母參與早產兒的照護活動,對早產兒的病情穩定和發病率的控制有著積極的影響,進而縮短了早產兒的住院時長。MELNYK 等[24]將260 個早產兒家庭隨機分為兩組,對147 名早產兒父母實施COPE 計劃后縮短了早產兒的住院時間。同樣,GONYA[30]等根據住院進程對168 名極早產兒父母按COPE 計劃進行賦權,促進了家長在病房中參與的積極性,并顯著降低了住院時間和再入院率。此外,一項研究[24]通過對父母賦權進行成本分析,證實這一項目可以減少患兒住院時間和費用。但是,NIEVES 等[8]納入了20 名早產兒父母為賦權組,結果顯示家庭賦權與早產兒的住院時長沒有顯著相關性,分析可能與組間胎齡差異及樣本量較小有關。上述相關研究結論存在不一致性,可能與賦權方案實施及納入樣本的差異有關。目前,國內關于家庭賦權在早產兒家庭中應用的住院時長及成本分析還未見報道,建議未來納入大樣本深入探究家庭賦權與早產兒住院時長和成本的關系。
4.2 促進母乳喂養
母乳喂養被認為是新生兒最適宜的喂養方式,其可以提供多重營養物質和多種生物活性因子,改善新生兒的健康狀況和免疫功能,降低胃腸道疾病的發生和死亡率[31]。家庭賦權的實施為早產兒父母提供母乳喂養理論知識和實踐技能。在我國,母乳喂養是家庭賦權在早產兒這一人群研究的主要評價指標。李梅等[7]采用方便抽樣對73 個早產兒家庭在常規護理的基礎上,添加了傾聽、對話、反思、行動這4個階段的賦權計劃,使賦權過程增加了多樣化的健康教育,結果發現家庭賦權可以提升母乳喂養知識水平和喂養率,以改善早產兒營養狀況,促進生長發育。這與黃麗冰等[32]的研究相一致。刑翠等[33]通過賦予家庭成員部分權力,使初產婦得到親屬的支持,提升母乳喂養自我效能及純母乳喂養率。研究[34]表明,當母親掌握了足夠的母乳喂養知識和技能,可促進母乳喂養的信念形成,這就形成了母乳喂養的賦權。進一步證明了增加對婦女的賦權可以提升母乳喂養率[35]。家庭賦權促進母乳喂養是提升知識、形成信念、促進行為的過程。
4.3 促進親子活動,調節負性情緒
早產兒對家庭來說是創傷性生活事件,大多數早產兒父母會經歷壓力、焦慮和抑郁等負性情緒[36]。在護理人員指導父母照護早產兒時及早產兒情況穩定后與父母獨處的階段,近距離接觸為親子活動提供了有利條件,父母與孩子在這一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快樂與放松。同時,家庭賦權可以使父母了解患兒的相關信息,減少對疾病的不確定感,學習照護知識和技能提升照顧準備度和出院后的應對能力,緩解壓力、焦慮和抑郁的情緒。黃芝蓉等[9]通過家庭賦權使父母了解早產兒信息,鼓勵父母傾訴自己內心的壓力并進行合理的心理疏導,以降低疾病的不確定感和緩解壓力情緒。VAN DEN HOOGEN 等[26]通過VOICE 計劃對早產兒父母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結果表明賦予父母權力的過程中支持他們扮演父母的角色,增加父母與早產兒的互動,可以促進親子關系的建立并減輕早產兒住院期間父母的壓力和焦慮。一項Meta 分析[37]顯示賦權可以顯著改善父母的心理健康,且與父親相比,母親的壓力和抑郁改善更明顯。
5 家庭賦權護理的不足與展望
5.1 完善制度和設施建設,提供保障
制度和設施的完善是家庭賦權實施的基本保障。目前,考慮到探視會增加早產兒的感染率,因此國內大多數醫院嚴格限制探視,而歐洲國家有部分醫院父母探視不受時間限制[38-39]。未來可進一步探索探視對早產兒感染率的影響,促進國內NICU 探視制度的發展,進而促使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中實施具有制度上的保障。家庭賦權的設施應包括環境、用物及資料準備。對早產兒父母進行賦權,單獨的家庭房間是一個重要的要素,在單獨的房間內可進行一對一的健康教育和照護指導,也可以使父母更自由的與孩子相處,促進親子關系的建立。
5.2 完善家庭賦權的流程,提升護理人員賦權能力
目前,國內關于家庭賦權研究的流程形式多樣,沒有統一的流程和評估體系,可能會使整個研究方案失去質量控制,而達不到預期效果。需要從家庭賦權方案的制定、實施、評價等環節進行規范,不斷優化該方案的實施,尤其是在賦權小組能力培訓、授權度、質量控制等方面。調查發現,NICU 醫務人員關于父母參加早產兒照護的體驗,存在不自在與溝通不暢等問題[40]。溝通作為賦權中的橋梁,對家庭賦權的實施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對醫護人員提供有關家長需求的培訓,可促進家長賦權與參與,是滿足家長需求的關鍵[41]。因此,針對為早產兒父母實施家庭賦權的護理人員,應明確自身角色,掌握溝通技巧,了解家長需求,提高賦權能力,提供全面的護理支持。建議未來根據我國情況,制定出符合我國的家庭賦權方案,選拔出專業家庭賦權人員,優化賦權流程,促進家庭賦權在臨床發揮積極作用。
5.3 多學科聯動,豐富家庭賦權的內涵
家庭賦權方案的目標人群是患有不同疾病的患者及其家屬,加上疾病的特異性及家庭的特殊性,要求賦權團隊成員是多學科的融合,以豐富家庭賦權的內涵。例如,對早產兒的父母進行賦權,賦權團隊應包含NICU 主任、醫生、護士長、護理人員、早產兒現存疾病的專科醫生、藥物治療師、社區工作人員、有類似經驗的社會人士等,集合更多的專業信息和資源促進患兒盡快康復。早產兒各器官發育不成熟,免疫功能低下,有病情復雜、發展迅速的特點。因此,為確保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中的順利實施,應加強家庭賦權的宣傳和普及并建立相關組織,緊急情況下能迅速集結多學科人員進行有效救治。
5.4 其他
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的研究更多偏向于母親而忽視了父親的重要角色。研究[42]顯示,父親在早產兒出生后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過對父親賦權,更有利于父親對母親的支持。因此,建議增加對父親甚至是整個家庭的研究。對NICU 醫護工作者來說,面對NICU 本身繁雜的工作,家庭賦權的實施會進一步增加工作量,導致家庭賦權的執行者持消極態度;對非專業的早產兒父母來說,賦權過程中理論和實踐教育可能會消磨學習的積極性。獎勵機制有必要在家庭賦權方案中體現,以增強賦權者和被賦權者的積極性。目前,國內家庭賦權在早產兒父母的研究較少、樣本量較小、評價指標局限,建議未來進行多家醫院聯合的大樣本隨機對照試驗。
6 小結
家庭賦權對早產兒的生長發育、父母的心理健康、乃至整個家庭有促進作用,是一種應用價值較高、值得推廣的護理模式。縱觀研究現狀,國內早產兒父母的家庭賦權與發達國家相比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在賦權步驟和內容上仍需不斷完善。建議未來借鑒國外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深入探索家庭賦權護理在早產兒父母中的應用,為早產兒的護理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