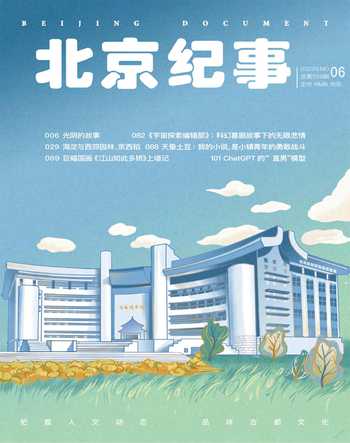“垮掉的一代”:變化的文學與電影
李嘯洋

美蘇冷戰、嬉皮士、越南戰爭、肯尼迪遇刺、黑人運動、阿波羅登月……動蕩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成為美國年輕人的“鎏金歲月”。1948年,26歲的杰克·凱魯亞克創造了“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一詞——一個屬于50年代文化的專屬詞語,總結性詞語。“垮掉”不僅指年輕人扶不起來,也指他們與傳統社會的脫節狀態,這個詞語頗有點五四新青年的意味。“垮掉的一代”和“憤怒的青年”,和開始用藝術引領美國電影的文化潮流,他們拋棄父輩的文化苦旅,開始用腳投票,重估世界的價值。
凱魯亞克、金斯堡和巴勒斯等人同為垮掉派文學運動的創始人。凱魯亞克在35歲時出版了小說《在路上》,書中“我還年輕,我渴望上路”,成為一代又一代年輕人上路的座右銘。他后來的一系列作品《達摩流浪者》《荒涼天使》《孤獨旅者》等,都和“上路”有關。《在路上》寫出了一種流浪的狀態,一種孤獨的狀態,一種和西部片相類似的拓荒精神。拓荒既是地理探險,又是心靈尋找。杜魯門·卡波蒂輕蔑地嘲諷《在路上》“不是寫作,是打字”的時候,凱魯亞克已經開始在書中思考美國文明:“丹佛第二十七街和韋爾頓之間的黑人區已經萬家燈火。在這兒溜達,我希望自己也是黑人。因為我覺得白人世界給我的最好東西不足以讓我入迷,沒有足夠的生活、歡樂、刺激、罪惡、音樂,沒有足夠的黑夜……我希望自己是丹佛的墨西哥人,甚至是窮苦的、過分勞累的日本人,什么人都行,只要不是現在這個活得膩味、理想破滅的‘白人。”凱魯亞克最后一部自傳體小說是《杜洛茲的空虛》,菲茨杰拉德在小說《了不起的蓋茲比》中豪情壯志的美國夢在這本書中消退,杜洛茲是凱魯亞克的化身,小說中主人公下海經商、吸毒、參軍、入獄,他的信條是法國詩人蘭波的信條“生活在別處”,最后被生活折磨得筋疲力盡。
凱魯亞克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結識了愛倫·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他們兩人,一個寫下了驚世駭俗的長詩《嚎叫》,一個寫下了自傳小說《癮君子》。“別把瘋狂藏起來”,這句話成了金斯堡的美學宣言。《嚎叫》中密密麻麻的長句,竭斯底里的語氣和驚世駭俗的抨擊,終為金斯堡招致了官司。1957年,《嚎叫》在通過美國海關時被查收,海關稅員切斯特· 麥格菲宣稱此書為淫穢作品,因為書中充斥著幻覺和欲望。警察逮捕了銷售此書的城市之光書店店員,出版人勞倫斯·費林蓋迪也被告上法庭。經過文學專家和媒體的辯護,最終該案以支持言論自由的名義告結,費林蓋迪被宣判無罪。電影《嚎叫》(Howl,2010)真實地記錄了這一過程。
威廉·巴勒斯的《癮君子》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該書描寫社會邊緣人群癮君子的心路歷程。巴斯勒的父親做木材生意,從小家境殷實。林肯汽車、花園、魚塘雖然給童年的巴勒斯帶來富裕舒適的生活,但他總不能在精神上獲得滋養。巴勒斯從小怕黑,經常夢魘,時不時的高燒害得他時常精神錯落。成年后的巴勒斯厭惡上大學,大學沒畢業便在歐洲飄蕩了一年,回到美國后靠父親留下的信托基金生活。在陸軍待了幾年后,巴斯勒因妄想癥被開除,之后做過私家偵探、滅蟲員、調酒師,每個月靠僅有的一百五十美元生活。窮困使他喪失了生活的動力,染上了毒癮。《癮君子》講述了地下世界人群的生存狀態,吃白食者、同性戀、騙子、小偷、皮條客,作者潛入小說的靜脈,赤裸地描述垮掉者的消極世界。小說精確地描述了邊緣人的這種生活狀態:“自我分成兩半,有意識的一半從那雙屬于流氓的、呆滯而遲鈍的眼睛里往外看。另外那半被拋棄的自我則承擔痛苦,這痛苦來自神經系統,來自肉體、內臟、細胞。”
文學在變化,電影也在時代的潛流里暗動。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的電影,可以用離經叛道形容。舊好萊塢中感傷主義、逃避現實、回避問題的影片,已經無法引起年輕觀眾的共鳴。1951年,伊利亞·卡贊執導了電影《欲望號街車》(A Streetcar Named Desire),該片根據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創作的劇本,講述美國南方種植園淑女布蘭奇在敗落以后,不肯放棄舊日貴族的生活方式。布蘭奇來到北方投靠妹妹斯黛拉,與其家人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布蘭奇遭到妹夫強奸,最后被送進瘋人院。《欲望號街車》是一部感傷主義色彩濃厚的電影,故事本身稀松平常,沒有驚心動魄之處。但從電影史和好萊塢新舊交替的意義上考量,該片就顯得意義非凡。電影理論家大衛·波德威爾這樣評價古典好萊塢:“好萊塢的電影制作在何種程度上遵從完整和限定的風格。好萊塢所宣稱的自身的原則仰仗于下述概念:體統、比例、形式和諧、尊重傳統、模仿、不事張揚的技藝和對認知者的冷靜控制——這正是批評家們所謂‘正典的標準。”《欲望號街車》是古典好萊塢和新好萊塢交替之際的產物,這部電影預示著古典好萊塢處理欲望時的浪漫詩意模式正在受到時代的沖擊,年輕觀眾對于陳舊的題材無動于衷。
新舊之交的《欲望號街車》是一則深刻的文明寓言:美國北方工業文明開始全面取代南方的種植園文化,張狂的物質欲望開始吞噬靈魂,詩意的時代逐漸消逝。布蘭奇和斯坦利代表了兩種文明的特征,布蘭奇代表的舊貴族是古典的、詩意的、文明的、纖弱的,斯坦利代表的工人是原始粗魯的野蠻人。幸虧是費雯麗的表演,大部分人才不會對矯揉造作的布蘭奇感到厭惡;幸虧是馬龍·白蘭度的面孔,大部分人才會忍耐斯坦利的暴虐。
古典好萊塢已經滿足青年觀眾的審美,電影也迫切需要轉型。垮掉的一代的審美趣味改變了好萊塢電影。《天蝎星升起》(Scorpio Rising,1963)是一部描述年輕人生活狀態的搖滾短片,全片將摩托車為文化、性、宗教以及骷髏死亡意象,電影用黑夜和搖滾營造出一種神秘、糜爛、狂歡的氣息,片子帶有明顯的自戀傾向。以《無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和《邦尼與克萊德》(Bonnie and Clyde,1967)為代表新好萊塢電影,開始關注內容的真實性,影片對傳統道德和價值采取了懷疑和批判態度。阿瑟·佩恩根據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轟動一時的犯罪新聞拍攝了電影《邦尼與克萊德》,該片描寫的“罪惡狂歡”迎合青年胃口,片中男女劫匪模仿美國歷史上劫富濟貧的英雄形象羅賓漢,兩人一起搶劫銀行,開車浪跡天涯,逃亡途中二人將戲弄警察的照片寄給報社,公眾將二人視為“英雄”,引發巨大的轟動。傳統好萊塢當中的警察,反被嘲諷為冷血動物。這對雌雄大盜雖然被警察打成彈孔,但觀眾看后卻產生了一種同情的結果。
《無因的反叛》是“憤怒的青年”的電影代表作。該片一舉捧紅了青年演員詹姆斯·迪恩,迪恩扮演的吉姆是他本人的生活寫照。影片中,吉姆和父母關系很差,在學校里無法與其他同學共融。洛杉磯的一所高中里,他仍舊遭到了同學的排斥,但認識了他心愛的女生朱迪,交到了真正的朋友柏拉圖,三個人組成了一種類似于家庭的關系。弗蘭克是當地的小混混頭目,也是朱迪的男友,迪恩和他決定以賽車來定勝負。飆車比賽中,弗蘭克不幸墜入懸崖身亡,警察的調查過程中,柏拉圖被意外槍殺,電影以悲劇性結尾。電影中,吉米、朱迪、柏拉圖三個青年逃離家庭,他們用刀子比賽,為搶女友進行飆車。為了拯救朋友,迪恩與父母吵架辯論。他們似乎與社會格格不入,看不到出路。“無因”是什么呢?電影沒有說明。“無因”是年輕人感到無力與虛無,“憤怒”是因為他們感到社會慣性的強大,父輩的懦弱與死板。頹廢的青年演繹的反叛式浪漫,正是年輕一代觀眾的心聲。
詹姆斯·迪恩一生只拍了寥寥數部電影,另外一部《伊甸園之東》 (East of Eden,1955)也與缺愛有關,每一部都和父母關系緊張有關,他脆弱敏感、邪魅癲狂的形象,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最酷的文化偶像。詹姆斯· 迪恩甚至不顧自己的明星形象,在棺材店拍照,甚至與豬合影。看完1953年馬龍·白蘭度主演的《飛車黨》(The Wild One),詹姆斯·迪恩開始喜歡穿皮衣,后來他把皮衣和飆車戲搬進了自己的電影《無因的反叛》。巧合的是,《無因的反叛》成了演員迪恩命運的讖語。片中,弗蘭克開車跌進懸崖,迪恩中途跳車僥幸逃生。1955年9月30日,詹姆斯·迪恩駕駛著保時捷超速行駛,意外與一輛福特車相撞,最后車毀人亡。那一年,迪恩剛剛24歲。原本他準備在百老匯扮演哈姆雷特,在舞臺上以憂郁而光輝的王子形象去世。迪恩生前曾言:“活得就像你今天要死一樣。”《卡薩布蘭卡》的主演漢弗萊·鮑嘉認為,迪恩死在了正確的時間。如果活著,他將無法彌補自己的名聲。迪恩之死是意外,也是必然。“他什么都想嘗試,他想用生活本身作為考驗。”迪恩的一位朋友說。巨星隕落后,無數青年模仿他的紅皮衣和牛仔褲,模仿他抽煙的動作,效仿他放蕩不羈的形象,安迪·沃霍爾評價他是1950年代最偉大的男明星,媒體則稱他為好萊塢經久不衰的陽剛之氣。
尼采說上帝死了,《逍遙騎士》里有句臺詞升級了尼采的說法:“如果上帝不存在,我們有必要創造它。”作為青年的“我們”雖然沒能創造出上帝,但創造出了《逍遙騎士》。《逍遙騎士》(Easy Rider,1969)是公路電影的里程碑。電影記錄了一對騎著摩托車的嬉皮士青年的漂泊生活,他們風餐露宿,只為千里迢迢前往墨西哥參加音樂聚會。二人在前往佛羅里達的公路騎著摩托車飛行,因為怪異的發型,被一名卡車司機開槍打死。及時行樂,上路尋找生命的意義,成了許多公路電影的標配。旅行對抗虛無,但這樣的對抗并無盡頭。《逍遙騎士》電影的制作成本為40萬美元,最終獲得2500萬美元票房,堪稱奇跡。《逍遙騎士》在拍攝時沒有完整劇本,大多時候是青年導演丹尼斯·霍珀和演員們率性而為,很多戲是在演員喝醉的狀態下完成的。有評論家認為,影片結尾主人公遭遇不測象征著“自由主義之死”。與《邦尼與克萊德》中展示的瘋狂不同,《逍遙騎士》充滿惶惑與否定的存在主義基調,這一基調深刻地影響了七八十年代的公路電影。
1971年的《最后一場電影》(The Last Picture Show)也描述青年生活,但是片中再無激情,主人公索尼經歷了戀愛打擊和好友去世之后,去電影院看了最后一場電影,以此告別灰色的青春。“我們痛苦,因為我們自由。”存在主義的這一名言也體現在亞文化電影中。1989年,芬蘭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拍攝了公路電影《列寧格勒牛仔征美記》(Leningrad Cowboys Go America)。片中,俄羅斯的幾名牛仔脫下皮大氅,戴上黑墨鏡,燙起飛機頭,蹬著火箭鞋,買了一輛二手車,來到美國國土開啟了搖滾事業。饑餓和失業困擾著他們,一名貝斯手被凍死,樂隊成員遂在棺材里放滿冰塊,拉著棺材上路。他們在廉價酒吧賣唱,臺下觀眾喝倒彩。然而,紐約并非遍地黃金,來自列寧格勒的牛仔們依然困窘。最后,牛仔們又重新上路,他們開車前往墨西哥,只為得到一個婚宴演出的機會。
美國電影中“垮掉的一代”喜歡開車上路宣泄,英國則喜歡反叛。六十年代影片對于垮掉的一代的描寫還中規中矩,多少帶有感性的實驗性質。七八十年代,庫布里克的《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1972)和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墻》(The Wall,1982)開始轉向政治議題,聚焦青年暴力犯罪等社會問題。
性與暴力是好萊塢“青年電影”的兩個主要元素,這兩個元素通常鑲嵌在社會議題中。《發條橙》有“嬉皮士”文化色彩,電影思考了青少年的犯罪問題以及社會對犯罪問題的處理。主人公埃里克斯一面哼著“雨中曲”的柔情音樂,一面殘暴毆打作家,一面強奸他的妻子。因宣揚暴力,《發條橙》一直被英國政府禁映。《猜火車》(Trainspotting,1996)是一部英國黑色電影,該片使導演丹尼博伊爾聲名大增。電影講述英國癮君子的墮落史,男主角瑞登深陷毒品,過著垃圾般的生活。影片開頭,瑞登拒絕中產階級生活方式:“選擇工作,選擇職業,選擇家庭……選擇按揭,選擇套裝、便服和行李......選擇你的未來,選擇生命……太多選擇,你選擇什么,我選擇不選擇。”經歷過渾渾噩噩的虛無生活之后,瑞登心理備受打擊,最終他選擇金盆洗手,悔過自新,背叛隊友之前,他輕輕給對方點了一根煙。影片結尾,瑞登信心滿滿上路:“事實上,我能改。我能改過自新,這是最后一次。從現在起,我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的前途跟你一樣,有工作、家庭、大電視……”臺詞收尾呼應,彼此循環,最終作者選擇擁抱主流社會。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整個垮掉的一代才褪去了青春的激情,重新思考正統與激情,社會與青春的關系。格斯·范·桑特導演的公路電影《不羈的天空》(My Own Private Idaho,1991)描述了兩個不同階層的人的命運:麥克是一個流浪漢,上路后便開始暈厥,童年與家庭總是縈繞在他心頭;斯考特是市長的兒子,他的自甘墮落屬于玩票性質。兩人一路從波特蘭來到西雅圖,又從美國的愛達荷輾轉到意大利。最終斯考特結婚,回歸上層生活,麥克卻依然在來往的路上彷徨。同六十年代的垮掉的一代電影相比,《不羈的天空》更憂郁更傷感,因為它正面觸及了破碎的美國夢。《阿甘正傳》(Forrest Gump,1994)是對垮掉的一代的文化總結:阿甘傳統保守,珍妮廝混墮落,兩人是60年代“秩序”和“反秩序”的象征。阿甘傳統老實,是保守派的代表,最終憑借自身的努力實現了美國夢。珍妮是叛逆的,她吸毒濫交,最后染上了艾滋病。珍妮人生暗淡,她是自由派的代表,也是垮掉的一代無信仰的象征。
垮掉的一代塑造了新好萊塢電影,這使新好萊塢電影兼具文化與反文化的雙重特征。電影中所表現的欲望和需求,并不被主流意識形態所認可。“垮掉的一代”借助銀幕上的夢,表達了主流社會觀眾被禁止的情感和欲望,被主流社會默認批準。從荷馬創作的《奧德賽》開始,歐洲文藝中的羈旅和上路,充滿文化的鄉愁。希臘導演安哲羅普洛斯的《霧中風景》(Landscape in the Mist,1988)和《尤利西斯的凝視》(Ulysses' Gaze,1995)均如此。對歐洲人來說,上路是艱辛的,旅程是痛苦的。對美國人而言,上路是輕松的、快樂的。透過《荒野大鏢客》等一眾西部片,觀眾便能了解美國人開拓的性格。“垮掉的一代”是年輕人的精神游牧,他們反對經典電影中的紳士淑女,他們用文學和電影發明了屬于自己的文化圈層。“垮掉的一代”以一種波西米亞式的生活方式,挑戰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重塑了一個時代的文學和電影。
編輯 張子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