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兒進女廁所事件
孫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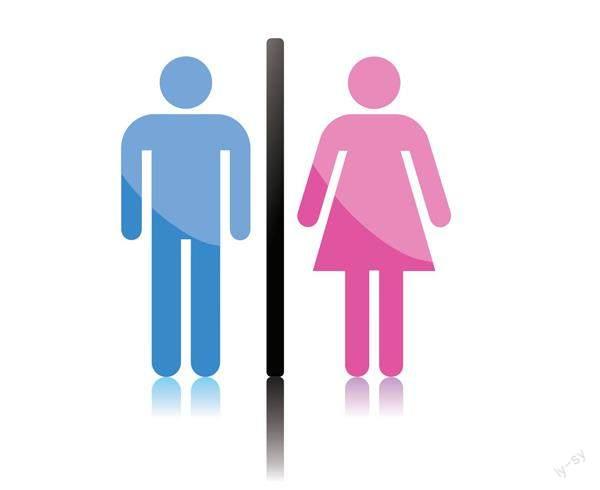
近年,經常有男孩子被媽媽帶進女廁所引發爭執的新聞事件。媒體報道出來的時候,大眾便在爭論:是否應該帶男孩子進女廁所?這對男孩子的心理影響是什么?
現在的廁所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可以關上門的隔斷了。所以,嚴格地說,帶男孩子上女廁所,對于男孩子,以及在場的其他女性,通常并不會有什么影響。那一個個隔斷可以理解為一個個單獨的廁所。就像旅游點有很多單間的廁所,本身就是不分性別的,前面男人進,后面女人進,大家根本不會有什么想法。男孩子進女廁所的隔斷,性質差不多。
除非,這件事被放大了。比如,有人對這個孩子強化了男孩子進了“女”廁所這件事,突出它的不合理性,甚至“變態感”,“犯罪感”。
帶男孩進女廁背后隱藏的問題
針對2023年初,東北某地商場中6歲男孩子被媽媽帶進女廁所事件,如果事件中女青年真的很嚴厲地指責了孩子,那對孩子的心理是不好的。但是,對孩子影響更不好的是那位媽媽的做法。媽媽通過堅持要求女青年道歉的舉動,將事件放大,引發現場對抗,將孩子置于一個非常激烈的沖突當中。這對孩子的影響遠遠大于上了女廁所本身。
這是從孩子心理的角度,分析進女廁所事件。我更愿意從社會性別的角度思考這類現象。
為什么媽媽要帶兒子進女廁所?因為兒子太小,媽媽不放心他自己進男廁所,那么,男人哪里去了?
當媽媽帶孩子上街、逛商場等場所的時候,為什么爸爸不在?
為什么我們平時看不到“爸爸帶女兒進男廁所”的新聞?
原因都是一個:爸爸們很少照顧孩子,爸爸缺席了。
媽媽帶兒子進女廁所,意味著爸爸的缺席。
在“東北事件”中,更詭異的是,爸爸明明也在商場—— 當媽媽和女青年爭執之后,爸爸出現在廁所門外。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爸爸不帶孩子去男廁所呢?爸爸嫌麻煩唄。父親的缺席已經到了如此荒唐的地步。
所以,這是一個社會性別問題。
父親缺席帶來錯誤的性別觀念
關于父親缺席對于孩子成長的許多不利影響,分析的文章很多,我們不在這里列舉了。只想說:父親缺席會從小培養孩子錯誤的性別觀念。在這樣的家庭環境影響下,孩子就會形成如此的概念:照顧孩子都是媽媽的事情,爸爸什么也不用管。這種影響可能是更深遠的,直接影響他對女性的態度,以及在未來親密關系中的角色實踐。這個男孩子在公共空間與女性的關系,在私人空間與女性的關系,都不會是支持平等,不會是很和諧的。
同時,這樣一代代影響下去,整個社會的性別平等不可能實現。
所以,在推進性別平等的過程中,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男性參與的力量。
1994年,“男性參與”的概念在開羅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行動綱領》中首次被提出;在1995年的北京世界婦女大會上得到進一步強化,《北京宣言》第25條明確呼吁:“鼓勵男子充分參加所有致力于平等的行動”。
2004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48屆會議呼吁政府、聯合國組織、公民社會從不同層面及不同領域,包括教育、健康服務、培訓、媒體及工作場所,采取行動以提升男人和男孩為推進社會性別平等作出貢獻。
2005年8月31日通過的《北京+10宣言》第25條也寫到:“關注男性的社會性別屬性,承認其在男女平等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承認其態度、能力對實現性別平等至關重要,鼓勵并支持他們充分平等參與推進性別平等的各項活動。”
2009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第53屆會議進一步呼吁男女平等地分擔責任,尤其是照護者的責任,以實現普遍可及的社會性別平等。
這些說的都是男性要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才能促進性別平等。這不僅對女性有利,對孩子有利,也對男人自己有利。

“男性參與”樹立更加科學的性別觀
在公領域,以幼兒園缺少男教師這一現象為例,現在一個支持增加男教師的主流聲音是:因為幼兒園沒有男教師,所以男孩子們整天和女老師在一起,都不像男孩子了,所以要增加男教師。這是錯誤的性別主張,在強化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從男性參與的角度,我們也主張增加幼兒園男教師,但目的是打破社會性別分工的刻板印象,讓男性參與到傳統上女性從事的社會工作中,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同時,也讓小朋友們知道男人也可以從事“女性職業”,也可以照顧孩子,這將影響到他們成年后對女性的態度以及親密關系。這就是從小進行的社會性別教育。
在私領域,以父親角色為例,美國學者羅蘭·馬克和羅伯·帕克維茨依據父親的參與方式劃分了四種父親類型:新的、參與型的父親;好的養家者父親;游手好閑的爸爸;父子關系自由的男人。新的、參與型父親就是我們倡導的。這類父親被認為是“好父親”的一種,他們參與到孩子生活中的許多方面里,他們會積極主動地照料、養育孩子以及料理家務等。這類父親使用一種更親密的和更富于表達的方式來參與到他的孩子的成長當中,與他們的父輩相比,他們在孩子的社會化進程中起到了更多的作用。
回到媽媽帶兒子進女廁所這類的事件,它更大的意義是一個社會性別議題,準確地說,是一個推動男性成為促進性別平等一分子的議題。
期待著看到更多的男人成為全參與型父親,承擔父職,那時,就不再需要媽媽帶男孩子進女廁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