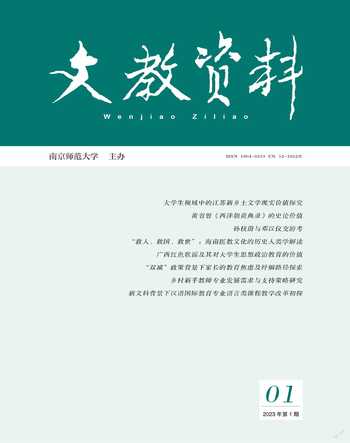“救人、救國、救世”:海南醫教文化的歷史人類學解讀
陳思然 余敬
摘 要:海南島的醫學發展具有深厚的傳統醫學及民族醫學基礎,但因醫學教育起步較晚,對于醫教文化的研究往往呈現較強的綜述及概覽性質,如個人生活史等個體層面微觀敘述仍具有較大研究空間。本文通過歷史人類學的文化視角,以海南醫療發展中重要的歷史轉折為支撐,以具代表性的個人敘述為內核,試圖梳理風物特殊、文化多元、傳統深厚的瓊崖醫療文化在相對隔離的地理環境中蓄力自助之脈絡,呈現醫學在地化發展從技術探索到精神飛躍,“救人、救國、救世”的層次累進。
關鍵詞:瓊崖文化 醫學教育 歷史人類學 醫學社會學
在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化格局中,海南文化以熱帶、海洋為主要特色,以黎族文化為代表的少數民族文化、因地理特色而彰著的海洋文化、多民族移民與華僑文化為主體,別具一格。[1]
“救人救國救世,醫病醫身醫心”為戴季陶先生于1927年所題寫,描繪、歌頌與希冀醫學生德才兼備的家國情懷。本文通過歷史人類學的文化視角,以海南醫療發展中重要的歷史轉折為骨架,以具代表性的個體敘事為血肉,試圖解讀風物特殊、文化多元、傳統深厚的瓊崖醫療文化如何在相對隔離的地理環境中尋找自身發展路徑,從技術探索到精神飛躍,實現“救人、救國、救世”的層次累進。
一、歷史人類學視野下的海南醫教
歷史并不是過往之舟,其對于現代社會生活及文化傳承而言意義深重,也是繼往開來精神傳承的文化符號。在現代醫學教育中,與醫療相關的本土歷史文化資源能夠提供深刻的人文力量、增強醫學教育與社會、文化及歷史的聯結,使醫學工作者能夠在深長遠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秉持唯物史觀,正確且深刻地認識自身的社會責任。全面而深刻地解讀歷史,細致入微地認識歷史中的個體,是在現代醫學教育中把握醫教文化歷史資源的重要方法論。
歷史人類學從文化的視角剖析歷史,講求宏觀記述與微觀敘事的互相映照:歷史的角度能夠進行縱貫的分析,而文化的角度則能把握其存續的功能。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視角便于我們更深入地了解瓊臺醫療文化,在新時代講好海南故事。近代以來,大量關于海南醫學發展史料的研究集中在海南醫學院及其附屬醫療機構,少部分來源于海南其他高等院校。海南島具有豐富而寶貴的歷史文化資源,其中也體現出宏觀歷史與微觀個體的交融。海南島醫學發展具有深厚的傳統醫學及民族醫學基礎,具有熱帶醫學的獨特性(尤其體現于長期和熱帶流行性疾病鏖戰之歷史),但醫學教育起步甚晚,對于醫教文化的研究往往呈現較強的綜述及概覽性質,在個人生活史等個體層面微觀敘述仍具有較大研究空間。
“海南島是中國人類學的實驗室”,中山大學和當年的嶺南大學作為華南的研究中心,關于海南島的調查著述頗豐,尤其自1981年中山大學復辦以來,在海南島進行了為數不少的田野調查[2],陸續有相關研究發表,但都集中在關于海南島少數民族或生活模式的探討,或是對于黎族等少數民族醫藥文化的關注。時至今日,社會科學領域對于海南島醫療體制或醫療文化發展仍鮮少關注。因此,海南島醫學相關歷史文化資源的挖掘仍然存在較大的探索空間,尤其缺乏醫學、社會與文化相交織的生命故事敘述。這一部分資源能夠成為新時代講好海南故事的歷史積淀,與推動本土醫學人文教育的內在動力。
二、“人”:嵌入歷史的微觀敘事
古代中國對于海南島的認識往往呈現出經驗文本與民間口傳事實之間的差別。如《宋史》中記載“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3],當時的地方志亦對海南島居民的健康狀況做出如下評論:“夏不至熱,冬不甚寒,鄉邑多老人,九十、百年,尚皆健步。”[4]蘇軾等人對于海南島自然環境、風土人情的理解,以他們傳世的詩文著作為載體,無形間也改變了外界對于相對與世隔絕的海南島的認識。瘴癘之地怎會蕩漾著生活情趣?“蠻夷”百姓又有何可能擁有長壽淡然、頤養天年的生活?蘇軾的生活經歷的記述呈現出與長久以來神州大陸對海南島固有之蠻夷記憶的不同表征。歷史記述與個體敘事的矛盾之處,漸漸凸顯出“珠崖”相對鮮活的形象。
漢學家薛愛華追尋12世紀之前海南島的風土人文面貌時,出于其社會學與人類學背景,海南島的歷史人文面貌尤其吸引他的好奇心。海南古稱“儋耳”“珠崖”,即使是在漢代以后的文獻記載中,對于這一方土地也只有模糊的了解[5],“珠崖在大海之中,南極之外”[6]。海南的歷史,是一部大陸與海島之間相互觀照的歷史,它本就誕生在文化互動的眼光之中。近代以來,當我們重新梳理這段歷史之時,依舊具有濃厚的“我看人看我”之目光,這與歷史人類學甚至是人類學本身進行研究時的主要價值觀是一致的。
歷史人物的個體敘事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歷史中的海南。它凝合了社會文化視角、醫學人文視野、對宏觀變遷及微觀互動的追溯及今昔交互的歷史啟迪。比如,在北方將海南島視作瘴癘之地的北宋時期,被貶謫到此的歷史名人蘇軾深受道家思想影響,認為只要無爭無思,與環境合一,便可以在這片濕熱的土地上延年益壽: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為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余歲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7]
薛愛華試圖用“地氣”的概念來總結蘇軾對于海南生活的認識:“人不能違抗至關重要的當地之氣,這種氣,每個地方各有不同,但每個人都能夠擁有。” [8]蘇軾對于海南風土人情理解糅合了他的道家思想,漸漸形成其特有的養生觀念,體現了人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蘇軾在他的流放歲月中充分地釋放五官,盡情感受這瘴癘之地,卻意外發現了宏觀歷史敘事及官方文本之外的不一樣的歲月。
時至今日,關于蘇軾養生觀的闡述常常以民間逸聞或故事為載體廣為流傳,社會科學界對其養生思想略有研究,但往往傾向于從整體角度去剖析解讀其養生觀點的思想基礎及具體實踐,忽視瓊州風土與蘇軾個人生活歷時性的互動。海南島獨特的自然地理、社會人文環境,在對于蘇軾晚年養生思想的發展和實踐提供了啟迪、作用及影響。與海南獨特社會背景(social milieu)相結合的蘇學養生觀,亦能回應大健康時代下今日的海南醫學、社會與文化發展。著名文學家的醫學思想并不僅僅是一個浪漫的論題,它更因為蘇軾的個人經歷而產生了古代中國南北生活經驗、中原與邊疆、中心與邊緣醫學思想及社會文化思潮的交織與碰撞。
蘇軾作為極具代表性的古代政治家與詞人,為瓊州歷史刻下了深刻烙印,他對于瓊臺風物的認識也成為我們全面探尋古代海南歷史的鏡鑒之一。歷史人類學的研究視角習慣于從文化的角度考察歷史,研究方法則體現民族志方法與歷史方法的結合,體現人類學的文化論與歷史學過程論的協調,以克服傳統歷史觀的局限性。[9]其特點在于強調文化的歷史向度,強調歷史的多元特征,強調歷史的文化解釋、記憶對“歷史制作”的重要性及歷史的力量。總而言之,文化的多元性及互動性、主體與客體的交織、人作為社會實踐者的主觀能動性,深深刻印在歷史人類學的思維模式及研究脈絡之中。
三、“國”:歲月流變中的瓊崖醫學
除了流放至此、旅居瓊崖的蘇軾,海南本土也曾誕生有志于傳統醫學并作育社會之賢達。林筱海曾對海南島醫藥發展史進行梳理,溯源海南中醫的代表性人物,首推明朝一代文宗邱浚(1420—1495年)。邱浚為海南歷史名人,瓊山縣人,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史有盛名,廣為人知;但其亦出身于世代醫家:
先祖為福建晉江醫科訓導,邱公長子邱成浚,酷嗜《素問》,著醫史,群眾到其家療疾者眾。邱公季子邱京為名醫,性習仁愛,重義樂施,瓊州大疫時,大施良劑,救活者甚眾。邱浚著有《本草格式》。[10]
海南島醫學發展的歷史也是一部人民群眾的奮斗史。在關于海南史的研究中,趙全鵬等人對于海南古代醫療發展史進行梳理,認為其不甚發達[11],因“瓊俗無醫”[12],唐時玄宗專門下詔令海南傳入藥書。然而宋代蘇軾居留海南時發現此地仍無醫療,“海南風俗,食無肉,出于輿,居無屋,病無醫,冬無炭,夏無泉”[13]。于是,在傳統醫療領域,海南島最早有史料記載可考的醫療設置于南宋始,明代洪武初年各州縣由官府牽頭設置醫學,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總量為三十家。[14]除了官辦醫療,也有許多民間醫士創辦私人醫療診所。隨著科舉等文化事項日漸鼎盛,許多鄉賢舉人、仁人志士的知識組成都體現了傳統醫學知識與儒學的結合,因此出現了大量“懂醫術”,將醫學知識以文化形式向海南民間大量傳播的文人學士。[15]
瓊崖醫療發展以公益慈善融合社會發展的社會思潮為基礎,以回應民生世情為己任。以如今的海南省省府海口為例,當地第一家中醫診所始建于乾隆五年(1740年),由當時的瓊山縣知縣杜兆觀號召士商捐款于城北五里亭處興建,為民治病。
瓊崖醫療文化的孕育發展也深刻體現出作為主體的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古代海南民間醫療深受當地黎族“以巫為醫”的影響[16],當時多地地方志均記載,百姓不崇尚醫術,面對疾病時更相信信仰的力量。直至民國時期,“先巫后醫”仍是海南百姓面對醫療問題的主流態度。然而少數民族,如黎族,作為本地原住民,其醫療思想和傳統文化在與漢族文化的互動中,漸漸退居客位。這一過程涉及大量的社會文化因素互動,仍待研究考察。
瓊崖醫療文化的發展體現了以傳統醫藥文化為基礎、回應家國動蕩時代巨變之浪潮、中西醫相互碰撞并相互協調以提高社會文化兼容性之過程。民國時期以中藥店、中醫診所為主體,海南島醫療機構蓬勃發展。自清末起,海口出現傳教士興辦的醫院,如海口福音醫院(1885年)、海口中法醫院(1906年)等,此類醫療機構主要體現了西方先進臨床醫學技術、社會慈善性質和傳教服務的結合。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社會力量方面,許多海南青年奔赴國外留學,帶回了包括西方醫學在內的科學技術體系。如徐天恩、朱潤深、蔡時椿、林筱海、李家鳳等近四十人均于1921年后陸續回到海南,投身于醫療事業。醫療建制方面,在各種海外華僑的支持下,海南人的西醫醫院漸漸走上歷史舞臺。如海南醫院(1927年)、以中法診所為基礎的海口市人民醫院(1953年由海口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收)、瓊崖麻風院(1933年)等。 [17]
在近代海南醫院體系探索式發展的時期,傳教士與留學歸國人員如醫學生等也創辦了一系列醫學院校,進行醫學人才的培養。[18]如1931年海南醫院附設了護士技術學校,1932年福音醫院附設了護士學校等。當時教學體制以西醫教育體制為基礎,教師大部分為外籍人士。總體而言,直至解放前夕,海南衛生機構數量較少、設備簡陋、技術水平低下,老百姓仍然面臨著缺醫少藥且醫學科學素養和衛生健康知識嚴重缺乏的情況,在許多地區仍存在逢疾病時不知如何求醫問藥,唯有禱告神靈之現象。
本島的腸道寄生蟲病這樣嚴重,其原因除地理氣候外,與人民群眾的生活習慣, 如隨地大便和用生大便施肥等有關。為防治須著重宣傳教育, 提高衛生知識水平與防治結合才可收效。[19]
解放初期,全島衛生技術人員不足一千人,現已增加到二萬五千七百八十三人,增長二十五倍多。 這些衛生人員除部分是島外大專院校培養者外,大多數都是我島幾間學校自行培養的。他們遍布全島城鄉各個角落,基本改變了海南島過去那種嚴重的少醫缺藥狀況,為海南人民的保健事業做出不可磨滅的成績。[20]
甚至到了1950年5月海南解放后,于1952年開建海榆中線公路, 全長僅二百多公里,民工患瘧者眾,至公路建成通車,幾乎“一公里一條命”。現經過多年建設和艱苦奮斗,已把瘧疾發病率從過去的90%以上下降至1984年0.18%。從此人民得到安居樂業,貧窮落后面貌有所改變。[21]
革命與新中國的成立為瓊崖醫療文化的發展帶來了真正的曙光,拂去籠罩這片土地已久的醫療蒙昧思想之陰霾。中國革命傳統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瓊崖革命精神是黨在領導海南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形成的“二十三年紅旗不倒”精神。其基本內涵是信念堅定,不屈不撓;自立自強,敢為人先;依靠群眾,甘于奉獻;五湖四海,丹心向黨。[22]在革命精神的引導下,歷經艱辛革命與艱苦建設的歲月,社會風貌出現了歷史性的變革。瓊臺醫療文化的脈絡由個人化的醫療實踐轉變為具科學性和規制性的醫學科學實踐;醫療機構由自覺開設、零散存在、主體多元化的醫療機構轉變成為國家驅動、政府保障的醫療保健事業;民間醫療思想由封建迷信占主流漸漸轉化成為現代化的公共衛生觀念。
四、“世”:瓊崖醫學與歷史社會
隨著西方醫療技術的傳入、臨床醫學循證思維的普及、近現代公共衛生觀念及傳染病防治方法的擴散,海南島的醫療狀況及公共衛生條件得到極大改善。但是,因處于熱帶地區,當地的疾病譜和相對應的醫療實踐仍然極具熱帶醫學特色,具有獨特性。因此,海南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對于醫學、社會、文化的綜合認識。新中國成立初期絲蟲病的防治經驗,就充分體現了現代醫療技術與地方性知識及群體傳統的結合:
對絲蟲病的防治經驗,海南區寄生蟲病防治研究所采用了海群生仍是較佳的藥物。但為普治方便,則用海群生拌食鹽作為病區群眾日常食用的療法,收到較好的效果。海群生藥鹽配方每人每月用食鹽量0.25 kg,每50kg食鹽中和海群生300 g(含海群生0.6%)……在絲蟲感染率5%以上的地區均可用此療法。曾用此診法治療絲蟲病患者 199000多人,又在重點流行區進行全民服藥45000多人。截至1985年,全島已有八個縣二個市,基本上消滅了絲蟲病。[23]
然而,海南島特殊的地理條件、環境特點及疾病譜,也使得災荒和瘟疫成為瓊臺醫療文化史中不可忽視的、對社會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力的關鍵。瘟疫,即大規模且對群體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的流行病,往往考驗著一個地區甚至是國家的社會治理能力。在近代瓊臺醫療史中,因為海南島自古以來并不是糧產充沛之地,氣候突變等意外狀況往往導致災荒,而瘟疫也常常伴隨災荒接踵而至。無論是歷史中抑或是地理中,孤懸海中的海南島往往難以通過這樣的“大考”,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以海口市為例,歷史上有記述的、其發生災荒的頻率不在少數。[24]道光年間、咸豐年間、同治年間、光緒年間均發生過由于地理或氣候環境等各種各樣因素導致的饑荒。伴隨著災荒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流行性疾病,如光緒三年(1877年)的雨雹、大水,導致幾年后郡城接續發生瘟疫、地震、寒霜、大旱、颶風等災害,尤其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起,海甸、白沙、新埠各村發生鼠疫,后府城內外也發生了鼠疫等。
新中國成立之前,自光緒年間第一次記載始,55年間鼠疫共發生38次。[25]學者考據,平均兩年就發生一次災荒。[26]《海南島新志》中記載,近代美國長老會在海口所設福音醫院院長拜爾科比茲經過調查,認為疾病發生的類型主要包括瘧疾、鉤頸蟲病、鼠疫、癩病、痘瘡、紅痢、膽石病、虎疫。[27]西方醫學體制的傳入增加了對于流行性疾病的整體了解、西醫治療的特點也輔助了當地流行病的治療,同時為海南醫療史中關于地方性流行病的記述增加了統計學意義,將碎片化的記述通過醫學思維凝練成海口市乃至海南島的瘟疫版圖。
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在霍亂、鼠疫或是麻風病等疾病流行時,缺醫少藥及無法在正規醫療機構得到及時治療并遭遇社區排斥的患者常常無處求醫、流浪街頭,甚至出現倒斃街頭的悲慘現象。林筱海記述了其親身經歷的海口及定安等地霍亂、鼠疫等流行病爆發期間的醫療狀況。以1937年2月定安鼠疫流行為例:
正在當年進入冬季的十二月之間,專員黃強又來找我,謂定安縣城發生兇惡疫癥,已死亡不少,要我去視察。我雖不是專職防疫人員,但從一個醫務工作者的良心和天責遣使,我也欣然應諾,單槍匹馬走去察視。我先到定安縣署,見署中寂然無人走動,最后找到留縣署中看守的一位老頭秘書,據說縣長都已逃之夭夭了,街上死人很多,叫我自己去探查。我走到街上,見行人稀少,商鋪住宅多已關門閉戶,居民也多疏散。我見門戶開處即逐戶檢查,發現患者是腺性鼠疫證實,心中焦急,立即趕返匯報,并囑黃強急電南京中央衛生研究院,不久,國際著名鼠疫專家伍連德趕來海口查詢,隨后由福建調來一隊鼠疫防治隊,領隊者為德國醫師蘭多雅,我和他見面后,又邀我偕往定安縣進行防治工作。當時定安縣民眾居住的房屋建造特殊,多系用破缸碎罐等疊筑墻壁當地出產瓦窯土磁外面薄敷泥巴,從而壁上千孔百洞,正適于老鼠藏匿繁殖,全屋有鼠經常出沒無阻。而地面又是松軟沙土,少經打實的,又利于鼠蚤生長活動,因此,造成鼠疫易于發生的良好的自然環境。
我們防治隊除對患者進行治療外,并進行滅鼠、滅蚤及預防注射等措施。由定安縣城沿南公路線,邊查邊治,至進入文昌縣境交界處一個小村莊, 據說該村曾有一家三代急病死了數人。我們親到該村查訪,據說該家中只存留了一個極袍嬰兒被帶走而幸存,連當時代收殮的件作也患同樣病死亡。由此,我們推測鼠疫流行至此期變成“肺鼠疫”階段。但經過一個多月時間,我們也將這次發生的鼠疫撲滅了。[28]
林筱海等近代海南醫學先驅在醫學技術的傳播、醫療實踐的開展以及大量探索性公共衛生工作的實踐方面,以個體的努力鍛造出醫學發展的歷史面貌。“見署中寂然無人走動,最后找到留縣署中看守的一位老頭秘書,據說縣長都已逃之夭夭了,街上死人很多,叫我自己去探查”,面對瘟疫時,醫學技術是唯一且最有效的武器,而不具備醫學素質和衛生健康知識的百姓無異于手無寸鐵的難民,唯有選擇感染不治身亡或是流亡,然而無人能逃過瘟疫的手掌。醫療工作者的記述呈現了瘟疫之下的時代風貌,在當時社會情境下,擁有醫學專業知識的人成為逆行者,找出流行病的癥結、醫治方法,挽救生命,乃至挽救社會。這樣的經歷,無論是作為口述史,抑或是前輩親自寫下、化為史料的醫學文獻,都是非常動人及富有科學、人文價值的。與流行病作戰的經驗,也是人為了守護群體健康與疾病負隅頑抗的經驗。醫療工作者孤身逆行,循證溯源,厘清流行病病因、脈絡、軌跡的實踐,在每一個時代,都意味著對本土社會的進一步深入了解,對在地社會秩序的扎實掌握,對風土人情及氣候地理的充分認識。
醫學不僅僅是針對個體和病例的救死扶傷,它也具有保家衛國、挽救社會的結構功能。同時,唯有了解當地的醫療工作者才能醫治本土社會:躬耕熱帶醫學的醫生才能在霍亂與鼠疫面前和時間賽跑,和死神搶生命,和傳播軌跡斗智,使社會秩序得到匡正。這一點在瓊崖醫療文化的脈絡中得到大量清晰呈現。
五、結語
希波克拉底在《論空氣、水和地域》中曾表述,一個醫生進入一個城市,首先應該觀察當地的土壤、氣候、空氣、水等等,并思考探究這些環境因素與當地疾病之間的關系。時至今日,對于海南島醫學社會史的挖掘仍然有極大的空間,需要繼續體現熱帶風土人文與醫學發展之間的聯系。以文化的視角解讀醫學發展的歷史因素、以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眼光看待醫學發展的社會聯結、以動態的視角看待醫學發展與歷史變遷之間的相互嵌套、以比較的眼光看待個體在歷史之中的作用,恰恰是現代醫學人文教育所需要的:我們志在培養出了解社會、理解社會的醫生,他們也必須清晰明確地掌握歷史的脈絡,以及擁有明哲知古今的思辨能力。
無論是歷史檔案對于瓊崖社會風氣樸素的縱向描摹,抑或是蘇軾、邱浚等仁人志士的躬耕心跡,乃至近現代醫學工作者苦學報國、服務于海島社會之過往,種種載于史冊內外之事件,皆為寶貴的精神財富及文化沿革。今人在歷史中看見先賢,看見每一個富有意義的個體,才能更好地認識到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以及醫療工作者作為一個社會角色的能指和所指,醫學和社會發展中人之主觀能動性的應然與必然。
習近平總書記曾于2016年的“七一”講話中提及,“明鏡所以照形,古事可以知今”“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辯證是一種過程和文化的辯證,以歷史人類學的視角對于具體的歷史個案進行重新解讀,使得該個案因被放回歷史過程中重新解釋而獲得反思的可能,同時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也可能賦予歷史過程一定的反思價值。[29]在挖掘瓊崖文化中的醫學人文資源時,尋找主體與客體結合的歷史敘述方法、反思支配當時歷史敘述的意識形態,是新時代醫學教育中立德樹人、育人育心的新途徑。重視歷史個案及個案中“人”的價值,歷史文化不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群像,也賦予了醫學人文教育更加深刻的敘述軌跡,更貼近醫學生心靈的情感聯結。
參考文獻:
[1] [11] [15] [16] [18] [24] 趙全鵬.海口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3-6,130,131,131,206,179.
[2] 麻國慶. 海洋資源共享與人文價值——海域研究的人類學反思[J].文史哲,2022(3):64-74,166.
[3] (元)脫脫.宋史·卷二七〇:第二十六冊[M].北京:中華書局,1977:5225.
[4] (南宋)王象之.瓊管志·輿地紀勝:卷一二四[M].北京:中華書局,1992:6a.
[5] [8] [美] 薛愛華.珠崖:12世紀之前的海南島[M].程章燦,陳燦彬,譯.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49,49.
[6] (晉)劉欣期.交州記[M]//太平御覽:卷一七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b.
[7] (北宋)蘇軾.書海南風土·東坡題跋:卷六[M].北京:中華書局,1985:34a-34b.
[9] [29] 藍達居.歷史人類學簡論[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1):2-7.
[10] 何銘文. 瓊山縣志:2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99:22.
[12] (明)曾邦泰.萬歷儋州志[M].林冠群,點校.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42.
[13] (清)方岱.輿地志.光緒昌化縣志:卷一[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44.
[14] (明)唐胄.正德瓊臺志:卷十三[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316.
[17] 林詩泉,林書勇.海南西醫之傳入和發展[M]//海南文史資料:第8輯.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3:204-207.
[19] [21] [23] [28] 林筱海. 海南島醫藥衛生史略[J].海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1989(4):65-73.
[20] 林詩泉. 海南島近代醫學教育發展簡況[J].海南衛生, 1984(2):3-4.
[22] 李德芳, 楊娜. 對加強地方特色革命傳統教育的思考——關于瓊崖革命精神的教育功能[J].社會主義研究,2007(3):117-119.
[25] 海南島北部地區鼠疫流行史料[M]//海口文史資料:第3輯.[出版地不詳],1986:172-173.
[26] 朱為潮.民國瓊山縣志:卷28[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837-1839.
[27] 陳植.海南島新志[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1:111.
基金項目:2021年海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思政專項) “瓊臺醫藥文化紅色基因融入醫學生思政教育的方法與路徑研究”(hnsz2021-26),2021年海南醫學院校級教育科研課題“醫學模式轉變與醫學社會學教育研究”(HYYB202174),海南省人文醫學基地重點課題“海南省農村基礎醫療設施用地法律問題研究”(QRYZH201803Z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