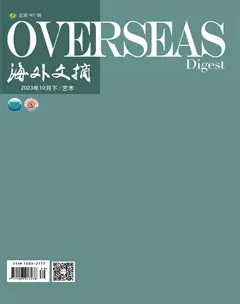文旅視域下探索羌族舞蹈發(fā)展新路徑
在全域旅游和鄉(xiāng)村振興的推動(dòng)下,我國羌族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的鄉(xiāng)村旅游業(yè)近年來得到了快速發(fā)展。羌族舞蹈在羌族人民生活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具有獨(dú)特的民俗文化風(fēng)情和鮮明的地域性,是羌族文化的重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本文從羌族文化的旅游業(yè)發(fā)展出發(fā),展開探討,就如何充分發(fā)揮羌族舞蹈資源所具有的優(yōu)勢(shì),進(jìn)一步探索羌族舞蹈發(fā)展的新可能、新路徑,提出一些看法,提出將羌族文化與鄉(xiāng)村旅游相結(jié)合、打造“文旅+”模式的方案。將當(dāng)?shù)孛窬迎h(huán)境與舞蹈相融合,打造沉浸式實(shí)景舞蹈,使游客在游覽過程中融入當(dāng)?shù)卣Z境,既可以增強(qiáng)當(dāng)?shù)芈糜螌?duì)游客的吸引力度,形成當(dāng)?shù)芈糜蔚奶厣推放疲贿€能將實(shí)景舞蹈與旅游相融合,有助于羌族舞蹈的傳承。
1 羌族的定義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國西部的一個(gè)古老的民族,古羌對(duì)中國歷史發(fā)展和中華民族的形成都有著廣泛而深遠(yuǎn)的影響,民族語言為羌語,屬于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分北部和南部方言。
羌族自稱“爾瑪”或“爾咩”,被稱為“云朵上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汶川、理縣、松潘、黑水等縣以及綿陽市的北川羌族自治縣,其余散居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縣、綿陽市的平武縣以及貴州省銅仁市的江口縣和石阡縣。大多數(shù)羌族聚居于高山或半山地帶,少數(shù)分布在公路沿線各城鎮(zhèn)附近,與藏、漢、回等族人民雜居。
2 羌族舞蹈的文化底蘊(yùn)與功能作用
羌族舞蹈與羌族文化緊密相連,是羌族人們?cè)谏a(chǎn)生活實(shí)踐中創(chuàng)造出的一種藝術(shù)形式。羌族舞蹈因此反映了羌族文化的歷史文化、宗教習(xí)俗、生活習(xí)慣以及獨(dú)特的民族個(gè)性等特點(diǎn),具有鮮明的時(shí)代性和地域性。羌族舞蹈藝術(shù)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瑰寶,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羌族舞蹈自身有著獨(dú)特的藝術(shù)特征和表現(xiàn)形式,這源于羌族人民有著十分悠久的民族信仰。羌族的舞蹈具有遠(yuǎn)古氣息,帶著遠(yuǎn)古時(shí)代母系氏族文化特色。群舞是羌族舞蹈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之一,也正是群舞這種舞蹈類型,使得羌族文化具有極強(qiáng)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促進(jìn)羌族人民始終團(tuán)結(jié)一致,促進(jìn)了羌族文化延綿傳承。
羌族民間舞蹈多和民俗活動(dòng)相結(jié)合,主要形式大致可分為自娛性、祭祀性、禮俗性三種類型,主要用于節(jié)日、祭祀、婚喪三種類型的活動(dòng),羌族的傳統(tǒng)節(jié)日主要有:祭祀節(jié)、女性節(jié)日“瓦爾俄足”、歌仙節(jié)、羌年等節(jié)日,主要表演形式有:“薩朗”“羊皮鼓舞”“跳鎧甲”“席布蹴”等。其中,祭祀節(jié)是羌族人民祭奠祖先、祭祀宗教的傳統(tǒng)節(jié)日。羌族傳統(tǒng)文化非常重視祭祀祖先,歌舞以娛神(包括祖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羌族民間祭祀性舞蹈是“跳鎧甲”和“羊皮鼓舞”。“跳鎧甲”和“羊皮鼓舞”有多重意義,包括為了躲避天災(zāi)人禍,祈求神靈庇護(hù);表達(dá)戰(zhàn)爭(zhēng)給族群帶來的災(zāi)難和痛苦,表現(xiàn)他們悲痛情緒;悼念死者;辟邪驅(qū)鬼等。后經(jīng)過改造,“跳鎧甲”和“羊皮鼓舞”中封建迷信等文化糟粕被去除,成為振奮民族精神,激勵(lì)后人不拋棄、不放棄,團(tuán)結(jié)全民族共同奮斗的舞蹈。今天羌族人民在跳“羊皮鼓舞”和“跳鎧甲”時(shí),雖然服飾裝扮、表演場(chǎng)地有一定的變動(dòng),但是在舞蹈中所表現(xiàn)的精神內(nèi)涵卻是不變的,展現(xiàn)了羌族人民同天災(zāi)人禍作斗爭(zhēng)的悲壯情懷以及羌族人民團(tuán)結(jié)奮斗,自強(qiáng)不息的進(jìn)取精神,激勵(lì)著現(xiàn)在的羌族人民為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懈奮斗。而“羌年”是指羌族特有的新年,即羌?xì)v年,是從羌族日歷的每年第一天(農(nóng)歷十月初一)開始慶祝。羌年有著較為傳統(tǒng)的慶祝方式,在每天的不同時(shí)間和地點(diǎn)都有詳細(xì)的慶祝方式。羌族人民會(huì)在特定時(shí)間,通過歌曲舞蹈來慶祝這個(gè)節(jié)日。羌年是羌族最重要的節(jié)日,意義類似漢族的春節(jié),是羌族人民用來慶祝豐收,祈求來年風(fēng)調(diào)雨順、平安健康的節(jié)日。除以上傳統(tǒng)節(jié)日外,羌族也會(huì)在慶祝糧食豐收、進(jìn)行婚喪嫁娶等活動(dòng)時(shí),舉辦較為隆重的儀式,并用特定的舞蹈形式來表達(dá)內(nèi)心的喜悅,慶祝節(jié)日[1]。羌族的自娛性舞蹈如“薩朗”和“席布蹴”,與節(jié)日、喜慶活動(dòng)密切相關(guān),是羌族人民表達(dá)喜悅和歡慶的重要方式。羌族的禮儀性舞蹈則是羌族人民在迎賓待客時(shí)展現(xiàn)的一種特殊舞蹈,表現(xiàn)了羌族原始古樸的審美意識(shí)。集會(huì)性舞蹈則以男性為主,通過渾厚、威武的吼聲和踏步走出不同的隊(duì)列和陣形,表現(xiàn)古代出征戰(zhàn)士高昂的士氣。羌族舞蹈的步法豐富多樣,如前文提到的羊皮鼓的主要步法有甩鼓步、兩邊踮跳步、開胯下蹲跳步、松膝繞步等,這些步法不僅節(jié)奏明快,而且動(dòng)作激烈而敏捷。羌族舞蹈還通常在火塘邊圍圈起舞,形式上很接近于藏族舞蹈中的“鍋莊”。舞蹈中,男女老少手拉著手,圍著火塘或場(chǎng)院一圈,沿逆時(shí)針方向邊歌邊舞,這種圍圈起舞的形式不僅體現(xiàn)了羌族人民的團(tuán)結(jié)和和諧,也展示了羌族舞蹈的獨(dú)特魅力。
3 羌族旅游業(yè)與羌族舞蹈發(fā)展現(xiàn)狀
3.1 羌族旅游業(yè)發(fā)展類型單一
在全域旅游和鄉(xiāng)村振興的推動(dòng)下,我國羌族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的鄉(xiāng)村旅游近年來得到了快速發(fā)展。但是與其他地區(qū)相比,羌族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的鄉(xiāng)村旅游業(yè)依然存在增長速度緩慢、產(chǎn)業(yè)層次較低、產(chǎn)業(yè)特色不鮮明、融合效應(yīng)不顯著等問題。由于羌族本身很少與外界交流,長期封閉,無民族文字,導(dǎo)致羌族文化傳播范圍小。近些年來,隨著外來文化,尤其是以西方商品經(jīng)濟(jì)為代表的流行文化的沖擊,羌族民俗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技藝正面臨著喪失的危險(xiǎn),急需采取措施,保護(hù)和傳承并舉。以桃坪羌寨為例,桃坪羌寨是目前世界上歷史極為悠久、建筑風(fēng)格奇特、民俗十分古樸、保存相當(dāng)完好,且唯一還有人居住的古堡式建筑,被譽(yù)為“東方古堡”。作為古羌文化的代表村落,桃坪羌寨近些年來越來越受國內(nèi)外旅游界、建筑界關(guān)注,目前已成為國內(nèi)外民俗人文旅游的重要品牌。但桃坪羌寨仍存在一些問題,如衛(wèi)生環(huán)境管理方面欠缺、發(fā)展定位與國內(nèi)其他品牌過于相同、特色文化與旅游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融合沒有新意等。至于其他的羌寨,一進(jìn)入寨子,許多當(dāng)代建筑映入眼簾,沒有古色古香的風(fēng)味。住宿餐飲店鋪占據(jù)了大部分街道,影響游客的參觀感受。部分建筑為了迎合當(dāng)代審美和外地旅客生活習(xí)慣逐漸失去了羌族的特色,無法讓游客體會(huì)到獨(dú)特的羌族風(fēng)情,感受到在羌寨旅游的閑適感。羌寨目前吸引游客的,是羌族地區(qū)的自然風(fēng)光、民俗風(fēng)情體驗(yàn)街,但這些羌寨具有濃厚的商業(yè)氣息,游客無法真正體驗(yàn)到純正的民族文化,影響到了旅游品牌的打造[2]。
3.2 羌族舞蹈的現(xiàn)狀
羌族文化因自身的“封閉性”,出現(xiàn)了“孤島現(xiàn)象”。具體體現(xiàn)在由于長期的封閉和無民族文字,區(qū)域內(nèi)民族語言十分豐富,各方言之間具有很大差別。即使相隔不遠(yuǎn),一個(gè)地區(qū)和另一地區(qū)的人也存在一定的溝通難度。封閉性也體現(xiàn)在羌族民族舞蹈方面。羌族民間舞蹈有著十分獨(dú)特的民族魅力,在羌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羌族受地理環(huán)境和經(jīng)濟(jì)方面的限制,民間舞蹈與其他民族相比發(fā)展較為緩慢。羌族的舞蹈是建立在羌族聚居的基礎(chǔ)上的,有羌族聚居聚落的存在,就有羌族舞蹈的存在。羌族民間舞蹈采取師生、家族相傳的形式,進(jìn)行傳承。傳承模式比較傳統(tǒng),主要以口傳身授的方式來傳承。這種傳承模式的優(yōu)點(diǎn)在于能夠保留羌族文化中最原始的藝術(shù)特色,而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這種具有封閉性的傳承模式使得羌族舞蹈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上、文化水平上都有很大的限制。而隨著社會(huì)的發(fā)展,封閉的文化藝術(shù)傳承,自然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沖擊。受全球化的影響,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爆炸的時(shí)代來臨,羌族文化被外來文化和當(dāng)代思潮打開一個(gè)缺口。想要羌族舞蹈文化永葆特色,不會(huì)在外來文化沖擊之下,被外來文化同化,就要主動(dòng)進(jìn)行融合,不能抱殘守缺,只有“源頭活水”,羌族的舞蹈文化才能歷久彌新,在當(dāng)今時(shí)代才能具有生命力和吸引力。
4 融合羌族舞蹈與羌寨實(shí)景,探索“沉浸式體驗(yàn)”旅游發(fā)展的新路徑
民間舞蹈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中華民族文化重要的傳播載體,是中華56個(gè)民族精神文明的結(jié)晶。
在國內(nèi)方面,近年來羌族非遺文化領(lǐng)域的研究取得了顯著成果,羌族舞蹈也越來越受專業(yè)人士的重視。近幾年興起的舞蹈情景劇,滋生于旅游景區(qū),通過傳承了民族文化精神的優(yōu)秀民間舞蹈,加強(qiáng)了與觀眾的互動(dòng)交流,在滿足了觀眾的審美趣味的同時(shí),提升了觀眾的文化素養(yǎng);在拉動(dòng)了旅游經(jīng)濟(jì)的同時(shí),加強(qiáng)和優(yōu)化了旅游經(jīng)營項(xiàng)目,促進(jìn)了周邊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融合羌族舞蹈與羌寨實(shí)景,探索“沉浸式體驗(yàn)”旅游模式,是整合旅游資源、推動(dòng)旅游業(yè)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項(xiàng)目之一,也是旅游景點(diǎn)長遠(yuǎn)發(fā)展的必由之路。而這種模式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從現(xiàn)狀來看,融合羌族舞蹈與羌寨實(shí)景,探索“沉浸式體驗(yàn)”旅游模式能夠?qū)⑾胍磉_(dá)的民族文化內(nèi)核與游客的精神文明需求相結(jié)合,實(shí)現(xiàn)雙贏。融合羌族舞蹈與羌寨實(shí)景,探索“沉浸式體驗(yàn)”旅游模式能夠放大和傳播羌族文化獨(dú)特的精神面貌,使得旅客在參觀當(dāng)?shù)仫L(fēng)景環(huán)境的同時(shí),耳目一新,促進(jìn)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fā)揚(yáng)。融合羌族舞蹈與羌寨實(shí)景,探索“沉浸式體驗(yàn)”旅游模式,要推出優(yōu)秀的舞蹈情景劇。在旅游地所表演的舞蹈情景劇要因地制宜進(jìn)行制作,彰顯差異性,突出特色化,滿足游客的觀賞需求、參與需求、精神需求,從而促進(jìn)當(dāng)?shù)匚幕囆g(shù)的繁榮發(fā)展,促進(jìn)文化的傳承、保護(hù)和發(fā)展[3]。
4.1“沉浸式體驗(yàn)”可發(fā)展路徑的優(yōu)點(diǎn)
守正創(chuàng)新,立足鮮明。為實(shí)現(xiàn)對(duì)羌族文化特色的保護(hù)和傳承,可將羌族文化與現(xiàn)代化、數(shù)字化相結(jié)合,推動(dòng)羌族文化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具象化、直觀性、創(chuàng)新性的沉浸式體驗(yàn),往往更富有吸引力。通過舞蹈情景劇、實(shí)景舞臺(tái)劇等方式,實(shí)現(xiàn)情景相融,使游客融入當(dāng)?shù)卣Z境,能實(shí)現(xiàn)觀眾的沉浸式體驗(yàn),提升觀眾的參與感。
4.2 “沉浸式體驗(yàn)”可發(fā)展路徑的重點(diǎn)
以當(dāng)?shù)厝嗣裆顬楹诵摹⒁月糜螢檩d體,對(duì)羌文化進(jìn)行系統(tǒng)性保護(hù),重點(diǎn)在“融合”,通過融合,讓羌族舞蹈“活”起來,推進(jìn)羌族舞蹈和羌文化的傳承、發(fā)展與傳播。為此,要探索通過“沉浸式旅游”模式促進(jìn)對(duì)羌族舞蹈的創(chuàng)造性保護(hù)、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與此同時(shí),探索羌族舞蹈與旅游、鄉(xiāng)村振興等領(lǐng)域雙向賦能的新路徑。以情境為中心,在生活情景劇、實(shí)景舞臺(tái)劇中融入羌族的花兒納吉、釋比戲、薩朗、羊皮鼓舞等表演形式,不斷突出羌族文化特色,讓游客能深入體驗(yàn)到羌族舞蹈、羌族文化的魅力。例如,釋比戲是一種具有高度文化價(jià)值的傳統(tǒng)戲劇形態(tài),對(duì)其進(jìn)行充分利用,能發(fā)揮出其他傳播媒介無法代替的“深度教化”功能;羊皮鼓舞有鮮明的羌族文化特色,是羌族人民生活習(xí)俗中必不可少的文化表現(xiàn)形式,將這種形式與旅游業(yè)有機(jī)結(jié)合,可以吸引外來游客,讓他們主動(dòng)了解羌族文化的內(nèi)涵、理解羌族文化的底蘊(yùn),并自覺主動(dòng)地加入廣泛傳播羌族舞蹈和羌族文化的行動(dòng)中來。
4.3“沉浸式體驗(yàn)”可發(fā)展路徑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
羌族文化作為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代表之一,將羌族舞蹈與當(dāng)?shù)鼐用裆顖?chǎng)景相結(jié)合,既能形成當(dāng)?shù)芈糜螛I(yè)的特色,也有助于羌族舞蹈的傳承與發(fā)展。通過挖掘羌族自身獨(dú)有的民族個(gè)性與舞蹈特色,為游客打造“身臨其境式”體驗(yàn)的全新模式。文旅融合背景下,推動(dòng)羌族非遺文化和羌族舞蹈的緊密結(jié)合,還需要不斷探索結(jié)合方式。為此要重視具體實(shí)踐和考察工作。任何創(chuàng)作都是一種表達(dá),更是一種情感和理念的傳遞。通過考察,了解羌族特色文化理念,在此基礎(chǔ)上,思考羌族文化深層次內(nèi)涵的創(chuàng)新表達(dá)。在創(chuàng)作中,借用民族節(jié)日、儀式、觀念價(jià)值、人物形象、動(dòng)作元素、文化特性,但并不局限于這些素材,而是對(duì)場(chǎng)景、情緒和人物加以實(shí)景和舞臺(tái)化的藝術(shù)處理,提取和借用原生態(tài)內(nèi)容強(qiáng)化舞臺(tái)風(fēng)格,直接表達(dá)羌族人民對(duì)于美好生活與生命的思想追求,體現(xiàn)羌族文化特色和非遺文化傳承發(fā)展的有機(jī)統(tǒng)一。
5“沉浸式體驗(yàn)”可發(fā)展路徑的優(yōu)秀案例
《微光》作為全國首個(gè)落地在黨群服務(wù)中心的沉浸式戲劇,改變了傳統(tǒng)的觀演關(guān)系,創(chuàng)新戲劇結(jié)構(gòu),與黨建融合,對(duì)開展黨史研學(xué)、黨群互動(dòng)等有著重要意義。“沉浸式戲劇”是現(xiàn)當(dāng)代戲劇藝術(shù)的新生兒,在當(dāng)代生活中具有自己的獨(dú)特價(jià)值,給實(shí)景舞臺(tái)劇提供了實(shí)踐可參考的范本。以環(huán)境為景,以天地為幕,讓環(huán)境與舞臺(tái)融為一體,讓觀眾走出劇場(chǎng),走進(jìn)羌寨,直接與演員面對(duì)面交流。
不同于傳統(tǒng)舞臺(tái)戲劇演出場(chǎng)地中的固定座位,在空間設(shè)計(jì)中,《微光》通過空間改造,以虛實(shí)結(jié)合的方式,為觀眾搭建起了深度體驗(yàn)空間。空間的狀態(tài)突出戲劇當(dāng)下的交互性。充滿特色的實(shí)景建筑,既給了觀眾滿滿的沉浸氛圍感,又給了觀眾一定的想象空間,其中融入瓦爾俄足、釋比戲、羌繡、薩朗等民俗文化,大大豐富了戲劇內(nèi)容。虛實(shí)結(jié)合的舞臺(tái)效果讓場(chǎng)景和情節(jié)相互聯(lián)系,能夠增強(qiáng)觀眾的文化認(rèn)同感,使其更快更好地融入舞臺(tái)情境中來。
顛覆了傳統(tǒng)舞劇中觀眾與演員具有距離感的典型模式,轉(zhuǎn)變?yōu)閮烧吖餐幱谝粋€(gè)空間的狀態(tài),突出沉浸式實(shí)景舞蹈當(dāng)下的互動(dòng)性與觀眾參與感。將所有演員表演的舞臺(tái)延伸到各個(gè)建筑和實(shí)地空間里,使體驗(yàn)者們從入場(chǎng)開始就沉浸到羌族民風(fēng)中,融入到空間當(dāng)中,讓他們本身與空間之間構(gòu)建起聯(lián)系,由此產(chǎn)生出一種對(duì)于自我本體的感知[4]。觀眾可以在羌寨的原始建筑的空間里主動(dòng)探索,體驗(yàn)民風(fēng);可拿起道具參與其中或觀看欣賞;與演員零距離交流。每一位觀眾都能有自己獨(dú)特的體驗(yàn)。當(dāng)然,沒有了空間的限制,也不代表觀眾和演員完全沒有隔閡,“零距離”還是要遵循舞劇規(guī)定情境的制約。
虛實(shí)空間,相互交融,強(qiáng)化了觀眾的沉浸感,讓觀眾有更強(qiáng)的感官體驗(yàn)。這種身體在空間內(nèi)的參與介入不僅能改變觀眾與作品之間的關(guān)系,也使得游客們能切身感受羌族文化和羌族舞蹈的羌風(fēng)古韻,把羌族舞蹈從單一、古樸的形式逐漸向多樣化、多元化、精致化、藝術(shù)化的方向發(fā)展。
6 結(jié)語
合理有效利用旅游資源,將羌寨實(shí)景作為載體,以羌族文化為核心,是傳承、創(chuàng)新羌族舞蹈這一藝術(shù)形式的重要手段,能保護(hù)羌族民族特色,推動(dòng)羌族文化在眾多民族文化中求同存異、守正創(chuàng)新,是大力發(fā)揚(yáng)羌族民族文化特色的可行之策。■
引用
[1] 徐兵.羌族舞蹈“巴絨”文化特征研究[J].阿壩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8,35(3):10-13.
[2] 賈芙豪.文旅融合視域下民族村寨旅游高質(zhì)量發(fā)展路徑研究——以理縣桃坪羌寨為例[J].村委主任,2023(10):103-105.
[3] 陳思彤.淺談舞蹈情景劇對(duì)旅游業(yè)的影響[J].黃河之聲, 2019(2):132.
[4] 史航宇,賴逸平.論沉浸式戲劇的審美特征:不完整與不可言說——以《成都偷心》為例[J].劇作家,2021(3):107-112.
作者簡介:盧冠同,女,回族,四川成都人,本科,就讀于四川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