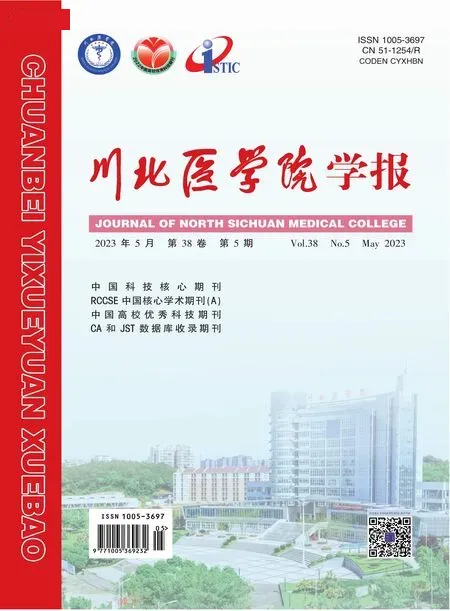三陰性乳腺癌中MIF與D-DT的表達及其臨床意義
吳燕,陳碩,龍瓊先,文彬,黃一凡
(1.川北醫學院第二臨床醫學院·南充市中心醫院病理科;2.南充市中醫醫院骨科;3.川北醫學院病理學教研室,四川 南充 637000)
乳腺癌(carcinoma of breast,CA)是導致全球女性死亡的最常見癌癥之一,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中,居女性癌癥發病和死亡之首。在中國,女性惡性腫瘤中乳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分別位于第一位和第五位[1-2],乳腺癌的發病率逐年遞增,且發病年齡趨于年輕化。三陰性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指雌激素受體(ER)、孕激素受體(PR)和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HER2)在免疫組織化學中均為陰性的乳腺癌,大約有80%與固有的“基底樣”亞型重疊,占所有乳腺癌的15%~20%。與其他亞型相比,TNBC組織學分級高、侵襲性強、復發轉移率高,預后差,目前尚缺乏標準有效的治療[3-4]。因此,為TNBC尋找新的生物標志物及治療上的新思路、新靶點,是目前臨床科研亟待解決的問題。巨噬細胞移動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MIF)與許多癌癥表型的腫瘤發生、血管生成和轉移有關,在多種惡性腫瘤中高表達[5]。D-多巴色素互變異構酶(D-dopachrome tautomerase,D-DT)是人類基因組中唯一已知的MIF同源物,兩者具有重疊的生物活性譜,在控制細胞存活、腫瘤形成、細胞遷移等方面表現出顯著的功能重疊和協同作用,是缺氧誘導因子的直接轉錄靶點,是瘤內低氧的標志[6]。目前,國內外對 D-DT和MIF在惡性腫瘤中聯合檢測的研究相對較少,兩者在TNBC中的聯合檢測尚未見報道。本研究通過免疫組化法檢測MIF、D-DT在三陰性乳腺癌中的表達情況,并探討其臨床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根據納入標準收集2010年1月至2014年12月川北醫學院附屬醫院收治的99例TNBC患者的存檔石蠟組織塊及臨床資料,同時隨機選取同期乳腺瘤組織20例、TNBC相應癌旁組織99例作為對照。納入標準:(1)行根治手術的原發乳腺癌女性患者,有完整的臨床病理資料;(2)術前未行放化療,未出現遠處轉移,術后接受規范化的輔助治療;(3)未合并其他部位腫瘤及全身性系統疾病。TNBC組患者平均年齡(49.83±10.77)歲;病理類型:浸潤性導管癌97例,其他病理類型兩例(浸潤性小葉癌1例,腺樣囊性癌1例);97例浸潤性導管癌參照Scarff-Bloom-Richardson(ESBR)分級系統[7]進行組織學分級:Ⅰ級2例,Ⅱ級64例,Ⅲ級31例;腫瘤大小(最大直徑d):≦2 cm者19例,2 cm﹤d≦5 cm者69例,﹥5 cm者11例;有淋巴結轉移者50例,無淋巴結轉移者49例;TNM分期[參照乳腺癌TNM分期(AJCC)第六版[8]]:Ⅰ期11例,Ⅱ期66例,Ⅲ期22例;Ki-67指數:低表達者11例,高表達者88例。
1.2 方法
鼠抗人MIF單克隆抗體購自臺灣Abnova公司(稀釋濃度1∶50),鼠抗人D-DT單克隆抗體購自ORIGENE公司(稀釋濃度1∶150)。所有標本均為10%中性福爾馬林固定,所有蠟塊均連續切片,每張切片厚度3 μm。免疫組化采用SP法。
免疫組化結果判讀標準:MIF、D-DT蛋白以細胞質中出現棕黃色顆粒為陽性表達。免疫組化評分方法:根據染色強度(不著色0分,淡黃色1分,黃色2分,棕黃或黃褐色3分)和陽性染色范圍(以陽性染色細胞所占百分比劃分,<5%為0分,5%~25%為1分,>25%~50%為2分,>50%為3分)評分,結果將兩者分數相乘,0~1分為陰性(-),2~3分為弱陽性(+),4~6分為中度陽性(++),7~9分為強陽性(+++)。結果均由兩位資深病理醫師進行獨立評分,取兩者平均分。
根據住院病歷所留的聯系方式,以電話對患者或其家屬進行隨訪,隨訪時間從手術之日起至2019年10月31日或患者死亡。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n(%)]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生存資料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及Log-rank檢驗。P<0.0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MIF、D-DT在TNBC、癌旁組織及纖維腺瘤中的表達情況
MIF、D-DT在TNBC中的陽性表達率均高于癌旁組織和纖維腺瘤,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及圖1。

表1 MIF、D-DT在TNBC、癌旁組織及纖維腺瘤中的表達情況[n(%)]

2.2 MIF、D-DT的表達與TNBC臨床病理特征之間的關系
MIF在TNBC中的表達與年齡有關(P<0.05),D-DT的表達與組織學分級有關(P<0.05)。見表2。

表2 MIF、D-DT在TNBC中的表達與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
2.3 MIF、D-DT在TNBC中表達的相關性分析
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結果顯示,MIF與D-DT在TNBC中的表達呈正相關(r=0.254,P=0.011)。見表3。

表3 TNBC組織中MIF、D-DT蛋白表達之間的關系
2.4 MIF、D-DT的表達及臨床病理特征與TNBC患者生存率的關系
自術后起截至隨訪日期(2019年10月31日或患者死亡),獲訪具有完整信息病例47例,13例死亡,總生存率為72.3%。對獲訪資料的臨床病理特征、MIF、D-DT采用Log-rank檢驗方法進行單因素分析,顯示淋巴結轉移情況、MIF、D-DT表達情況與患者生存率具有相關性(P<0.05)。見圖2-圖4及表4。

表4 MIF、D-DT及淋巴結轉移情況與術后隨訪資料



3 討論
乳腺癌是絕大多數國家最常見的癌癥[1],目前應用最廣泛的診治手段和策略是根據乳腺癌腫瘤病理學上不同的分子分型制定不同的治療方案[9],TNBC目前尚缺乏標準有效治療,因此,為其尋找新的生物學標記及治療靶點,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MIF是一種多功能促炎蛋白,是抗癌治療的靶點。多項研究[6,10-12]表明MIF可通過腫瘤抑制因子下調、誘導 MAPK/ERK 和 PI3K/AKT等途徑的活化從而在腫瘤的發生發展中起關鍵作用,且在多種惡性腫瘤中高表達,與不良預后相關。田玉偉等[13]發現膽管癌組織中MIF陽性表達率顯著高于癌旁組織,MIF高表達與患者病情嚴重程度、復發和生存明顯相關。有文獻[14]表明MIF在膽囊癌組織中高表達,促進膽囊癌細胞遷移和侵襲,且與患者不良預后有關。Balogh等[15]實驗結果顯示MIF在乳腺癌模型MMTV pMYT和4T1中通過抑制抗腫瘤免疫反應,促進腫瘤的進展。Guo等[16]發現MIF在胰腺導管腺癌的發生發展中具有診斷和治療的雙重作用。本研究結果顯示,TNBC患者MIF陽性表達者總生存率及平均生存時間明顯低于陰性表達者,Kaplan-Meier生存曲線顯示MIF的表達與患者預后相關(P<0.05),提示MIF陽性患者預后差,阻斷MIF可提高患者生存率、延長生存期,這與既往的報道一致。以上結果提示MIF可作為判斷TNBC預后的重要標記物和分子治療的靶點。
D-DT在癌癥進展中的作用與MIF相似,眾多實驗結果表明D-DT在多種惡性腫瘤中高表達,參與腫瘤的發生發展,與腫瘤的不良預后相關。Kobold等[17]的研究結果顯示D-DT在B16F10黑色素瘤和4T1乳腺癌模型中高表達,靶向D-DT可以減緩該模型的腫瘤進展。Guo等[16]的實驗研究表明D-DT在胰腺導管癌組織和細胞系中過表達,D-DT的敲除可減弱PANC-1細胞的增殖、侵襲。Wang等[18]發現D- DT在宮頸癌組織中過度表達,體內外實驗顯示D-DT的敲除能抑制宮頸癌細胞的侵襲、遷移和移植瘤的生長。Cavalli等[10]發現D-DT的高表達與神經母細胞瘤較差的預后相關,抑制D-DT能夠在體外逆轉長春新堿的敏感性,導致較好的總生存期。本研究結果顯示,TNBC中D-DT陽性表達患者總生存率和平均生存時間明顯低于陰性表達者,Kaplan-Meier生存曲線顯示D-DT的表達與患者生存率和生存期相關(P<0.05),提示D-DT陽性患者預后差,抑制D-DT可顯著改善患者預后。這與Cavalli等[10]的報道一致。以上結果提示D-DT是一種不良預測因子,可作為判斷TNBC預后的指標和分子治療的新靶點。
有研究[19]發現淋巴結轉移是影響乳腺癌和三陰性乳腺癌患者預后的獨立因素。本研究結果顯示有淋巴結轉移者的生存率顯著低于無淋巴結轉移者,淋巴結轉移是影響TNBC預后的顯著因素(P<0.05),與上述報道一致。
腫瘤的發生發展是多因素、多步驟、多基因相互作用的結果。相關研究[6,16,18]提示,MIF和D-DT在多種癌癥中的表達呈正相關,共同導致不良預后,本實驗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結果顯示,MIF與D-DT在TNBC中的表達呈正相關(r=0.254,P=0.011),與既往報道一致。目前抗MIF策略成為了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已經開發了許多在癌癥研究中抑制MIF生物學功能的方法,包括用小分子MIF抑制劑破壞MIF的活性、MIF的間接失穩和抗MIF抗體等,其中應用最廣泛的是競爭性抑制劑(如Iso-1、Iso-66等)和不可逆抑制劑(如4-IPP),這些方法的應用在多種癌細胞系和癌癥模型中均顯示可導致腫瘤生長、血管形成和細胞增殖的減少[5]。例如人抗MIF單克隆抗體Imalumab適用于轉移性結腸癌、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已經完成了二期臨床試驗[20],Iso-66已被證實可延緩結直腸癌的進展[21]。但這些靶向藥物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活性低、效力低等, 而針對MIF/D-DT雙靶點的抑制劑4-IPP則能取得更好的靶向效果,這表明當前抗MIF的治療效果可能通過兩者的聯合靶向而得到加強。
綜上,MIF、D-DT及淋巴結轉移是影響TNBC患者預后的危險因素。聯合檢測MIF、D-DT可能為TNBC患者的預后判斷及個體化治療提供新指標、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