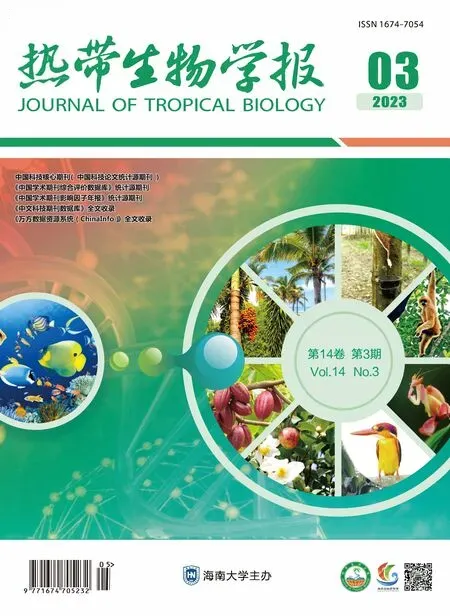基于紅外相機技術的海南長臂猿分布區林冠層伴生鳥獸多樣性的研究
蒙金超,楊雪珂,馮悅恒,齊旭明,劉 輝
(1. 海南大學 林學院,海口,570208; 2. 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管理局,海口, 570203)
紅外相機監測作為一種非損傷性的野生動物監測方法[1],具有晝夜連續工作、人力投入少、對研究對象干擾小等優勢[2-3],目前已被廣泛應用于動物生態學的研究[4]。通過分析紅外相機所拍攝的動物圖像數據,可以獲得物種豐富度、空間分布、活動節律和種群密度等信息[5-6],能一定程度彌補傳統調查方法的不足,尤其是針對一些夜間活動的、隱蔽的和珍稀物種的調查更為有效[7]。我國最早在云南省高黎貢山地區和臺灣地區使用紅外相機技術監測野生動物[8-9]。經過20 多年的發展,紅外相機技術已發展成為地棲大中型獸類和鳥類的重要常規監測技術[10-11]。但該技術應用于高度樹棲的林冠層動物多樣性的研究相對較少,且布設相機臺數少及安裝高度較低,僅5~15 m[12],在林冠層中使用紅外相機調查樹棲哺乳動物的潛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的。
海南長臂猿(Nomascus hainanus)為長臂猿科(Hylobatidae)、黑冠長臂猿屬(Nomascus),是我國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由于在歷史上受棲息地破壞及狩獵等因素導致海南長臂猿種群數量極低[13],2007 年10 月保護國際(CI)宣布海南長臂猿名列全球25 種瀕危靈長類物種之首[14]。我國高度重視該物種的保護,基于自然恢復方法的科學保護使得海南長臂猿成為全球20 種長臂猿中唯一處于數量增長的類群[15],種群數量從20 世紀80 年代2 群7~9 只增至2022 年的5 群36 只[16],目前僅分布在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霸王嶺片區斧頭嶺及南崩嶺區域[17],屬于高度樹棲的晝行性小型猿類[18-19],以成熟果實、嫩葉、嫩芽為食[20-21]。
海南長臂猿作為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野生動植物保護的標志性物種和生態指示種[22],對于該物種的保護和研究有助于提升熱帶雨林生態系統原真性和完整性。目前對海南長臂猿的研究集中在種群現狀、食性和棲息地等方面[23-24],缺少海南長臂猿同域分布區伴生鳥獸多樣性組成及季節性變化相關研究。本研究擬使用紅外相機技術分析海南長臂猿林冠層同域分布物種的多樣性、年活動格局以及海拔分布格局,探討海南長臂猿與其同域分布鳥獸物種的共存機制,為未來基于生物多樣性的海南長臂猿棲息地修復和生態廊道建設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域概況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霸王嶺片區(以下簡稱為霸王嶺片區)地處海南昌江縣和白沙縣境內(19°02′~19°08′N, 109°02′~109°13′E),總面積約850 km2,海拔75~1 655 m,年平均溫度21.9 ℃,年平均相對濕度84.2%,年均降水量1 657 mm,屬熱帶季風氣候,旱季雨季分明,5—10 月為雨季,11 月至次年4 月為旱季,4—8 月常有臺風;其核心保護區內覆蓋有熱帶低地雨林、熱帶山地雨林、熱帶山地常綠闊葉林和熱帶山頂矮林[13]。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有海南長臂猿、海南山鷓鴣(Arborophila ardens)、大靈貓(Viverra zibetha)、海南孔雀雉(Polyplectron katsumatae)等8 種,國家二級重點保護動物有水鹿(Rusa unicolor)、白鷴(Lophura nycthemera)、蟒蛇(Python bivittatus)、獼猴(Macaca mulatta tcheliensis)和巨松鼠 (Ratufa bicolor)等50 種[25]。
1.2 相機安裝和數據收集根據海南長臂猿各個家庭群分布現狀、海拔分布和猿食植物分布,選擇5 個家庭群中的B、C、D 群分布區作為研究區域,面積約15 km2。B、C、D 群分布區主要為熱帶山地雨林,其他林型分布較少。2019 年1 月開始,布設33 個紅外相機監測位點66 臺紅外相機(圖1),紅外相機安放主要考慮長臂猿實際利用區域(護林員記錄的長臂猿活動強度及猿食植物分布),兼顧較高和較低海拔(600~800 m 熱帶低地雨林布設16 臺,800~1 100 m 熱帶山地雨林布設40 臺,1 100 m 熱帶苔蘚林布設10 臺)。將相機安裝在離地13~25 m 的樹冠層,選取海南長臂猿可能經過或者附近有猿食植物且視野開闊的樹干進行安放,避免樹枝遮擋鏡頭;鏡頭與地面呈5°~15°俯視角,避免陽光直射。每個監測位點安裝的2 臺相機機身相靠、鏡頭相反,各自反方向拍照,相鄰位點之間的直線距離在100~500 m[26-27]。拍攝模式設置為連拍3 張照片同時錄制視頻10 s,拍攝間隔為0 s,靈敏度為中。安裝前進行性能測試,安裝時記錄每個位點相機的編號、GPS 位點、海拔和生境因子等信息。

圖1 海南長臂猿分布區林冠層紅外相機監測點分布圖
2019 年8 月,完成第一次紅外相機的數據回收(替換SD 卡)和維護(更換電池),同時發現有11 臺紅外相機長時間受到雨水沖刷從而徹底損壞,最終實際正常工作的紅外相機為55 臺(海拔600~900 m 14 臺,海拔900~1 100 m 31 臺,海拔1 100 m 以上10 臺)。2019 年11 月和2020 年6 月完成第二次和第三次數據回收,未有相機損壞。熟悉海南本土物種的專家人工對照片和視頻進行物種識別,剔除模糊不清或沒有明顯物種特征的照片,所拍攝到照片和視頻中的物種鑒定主要參考《中國鳥類分類與分布名錄》和《中國哺乳動物多樣性》[28-29]。
1.3 數據分析
1.3.1 海南長臂猿分布區林冠層物種組成利用相對豐富度指數衡量海南長臂猿分布區林冠層獸類和鳥類各物種相對種群數量。獨立有效照片是指同一相機位點含同種個體的相鄰有效照片( 或視頻)間隔時間至少為 30 min[30],1 個相機工作日以單臺紅外相機在野外持續工作24 h 為標準,每臺紅外相機有效工作日以該位點拍攝到的第一張野外工作照片(顯示有正確設置信息)和最后一張野外工作照片的日期間隔為有效工作日。將拍攝到各種鳥類和獸類物種的獨立有效照片與所拍攝物種獨立有效照片總數的百分比作為每個物種的相對豐富度(relative abundance index, RAI)[31]。
1.3.2 分布區內鳥獸年活動格局依據統計所得數據,計算月相對豐富度指數(monthly relative abundance index, MRAI),分析獨立有效照片較多的動物年活動規律。
1.3.3 分布區內鳥獸海拔分布格局根據海南長臂猿棲息地類型和相機實際安裝情況將研究區域分為3 個海拔梯度(600~800、 800~1 100、1 100 m 以上),并統計不同海拔梯度的獨立有效照片,采用Shannon-Wiener 指數、Pielou 均勻度指數和Simpson 指數判斷不同海拔梯度的α多樣性水平[32]。
Shannon-Wiener 指數(H')是將物種豐富度與種的多度結合起來的指數,通常來說H'值越大,物種多樣性越豐富。由于每個海拔梯度布設的紅外相機臺數的不同,在比較不同海拔梯度的物種數和多樣性指數時,以每一臺相機作為獨立樣本,計算每一臺相機的物種數、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通過比較其平均值表示不同海拔梯度的物種多樣性情況[33]。采用Kruskall-Wallis test 來比較不同海拔梯度物種多樣性的差異,差異顯著水平設定為0.05。所有數據都在SPSS 24.0 和Excel 2021上進行處理。
Pielou 均勻度指數(J)反映物種分布的均勻程度,能夠表征分類單元中每個物種個體間的差異。均勻度(J)數值越大,群落中物種個體間的差異越小。
物種優勢度(C)采用Simpson 指數計算,C 值越大說明群落內物種數量分布越不均勻,優勢種地位越突出[34]。
2 結果與分析
2019-01-20—2020-06-30 期間,55 臺紅外相機累計監測到16 266 個有效相機工作日,共拍攝到獸類、鳥類照片和視頻14 136 份,鑒定出獨立有效照片1 747 張, 其中獸類1 569 張(89.8%)、鳥類178 張(10.2%)。記錄到3 目4 科10 種獸類,6 目11 科20 種鳥類。拍攝到海南長臂猿(21 個)、海南鼯鼠(Petaurista hainana)(16 個)、紅頰長吻松鼠(Dremomys rufigenis)(16 個)和果子貍(Paguma larvata)(15 個)的位點數居于前4 位,其他獸類和鳥類較少(表1)。

表1 海南長臂猿同域分布區林冠層獸類與鳥類動物名錄
2.1 鳥獸相對豐富度記錄到的10 種獸類中,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2 種,即海南長臂猿和小靈貓(Viverricula indica);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3 種,分別是獼猴、巨松鼠和椰子貍(Paradoxurus hermaphroditus),國家一、二級重點保護動物合計占所有獸類物種數的50%。海南長臂猿被IUCN 紅色名錄列為極危物種(CR),巨松鼠被列為近危物種(NT)。此外,獸類中相對豐富度指數居于前三的是海南長臂猿(RAI =58.44)、海南鼯鼠(RAI =17.78)和紅頰長吻松鼠(RAI =14.34),其他獸類的相對豐富度指數均低于3,小靈貓僅有1 張獨立有效照片(表1)。
記錄到的17 種鳥類中,國家二級重點保護鳥類8 種,分別是黃胸綠鵲(Cissa hypoleuca)、大黃冠啄木鳥(Chrysophlegma flavinucha)、斑頭鵂鹠(Glaucidium cuculoides)、鷹雕(Nisaetus nipalensis)、紅頭咬鵑(Harpactes erythrocephalus)、厚嘴綠鳩(Treron curvirostra)、山皇鳩(Ducula badia)、和藍須蜂虎(Nyctyornis athertoni),占所有鳥類物種數的53%。記錄到的17 種鳥類中,3 種為近危物種(NT),分別是白翅藍鵲(Urocissa xanthomelana)、大黃冠啄木鳥和鷹雕。鳥類中相對豐富度指數居于前三的是山皇鳩(RAI=44.92)、厚嘴綠鳩(RAI=20.23)和斑頭鵂鹠(RAI=6.74); 赤紅山椒鳥(Pericrocotus flammeus)、紅頭咬鵑、黃嘴角鸮(Otus spilocephalus)和藍須夜蜂虎的相對豐富度指數較低(表1)。
2.2 林冠層鳥獸年活動格局獸類各月份活動強度較高,鳥類則較低,在11、12 月份未拍攝到鳥類照片和視頻。海南長臂猿和海南鼯鼠年活動格局相似,且與季節(旱季和雨季)顯著相關(海南長臂猿:χ2= 8.308, df = 1,P= 0.002; 海南鼯鼠:χ2=3.124, df = 1,P= 0.047)。海南長臂猿在9 月份活動強度最低,10 月份快速上升,3 月份達到全年活動峰值,旱季則較低。海南鼯鼠在3 月份出現活動峰值,在5—10 月份趨于平緩。其他獸類如紅頰長吻松鼠、椰子貍、倭松鼠(Tamiops maritimus)的年活動格局均與季節無顯著相關,在各個月份的活動強度較為平緩。5 種鳥類的年活動格局均與季節無顯著相關,其中山皇鳩和厚嘴綠鳩在1 月份出現活動峰值,斑頭鵂鹠和白翅藍鵲在8 月份出現峰值,黃胸綠鵲在4 月份出現峰值,其他月份鳥類月相對豐富度較低,主要集中在1—4 月份和7—8 月份活動(圖2)。

圖2 獸類和鳥類的年活動格局
2.3 物種海拔分布格局不同海拔梯度下鳥類和獸類物種數均不存在顯著差異(鳥類:χ2= 2.085,df = 2,P=0.339;獸類:χ2= 5.53, df = 2,P= 0.061);鳥獸物種總數則存在顯著差異(鳥獸:χ2= 6.399,df = 2,P= 0.038),主要表現為,海拔1 100 m 以上的鳥獸類物種總數低于其他海拔梯度(圖3)。比較不同海拔梯度的物種多樣性指數、均勻度指數以及優勢度指數,只發現鳥類的優勢度指數存在顯著性差異性(鳥類:χ2= 18.585, df = 2,P= 0.000 1),主要表現為,鳥類優勢度指數在海拔1 100 m 以上明顯低于其他海拔梯度;獸類和鳥獸的多樣性指數和均勻度指數隨著海拔的升高呈單調遞減;獸類中海南鼯鼠和紅頰長吻松鼠是優勢種,優勢度指數分別是0.13 和0.10;鳥類中山皇鳩和厚嘴綠鳩是優勢物種,優勢度指數分別是0.40 和0.20(圖3)。

圖3 不同海拔梯度下鳥類和獸類的物種數和多樣性分布差異
3 討 論
3.1 海南長臂猿及同域物種的多樣性密切相關的同域物種會采用導致生態位分離或資源劃分的過程,從而使物種共存成為可能[35-36]。本研究監測到與海南長臂猿同域分布的獸類包括巨松鼠、赤腹松鼠、海南鼯鼠,果子貍和椰子貍等,盡管這些獸類與海南長臂猿的食物生態位存在重疊,但在活動模式和空間利用的差異使它們可以共存[37-38]。在活動模式方面,海南長臂猿是晝型性靈長類,椰子貍、果子貍和海南鼯鼠則是典型的夜行性動物[39],這些物種時間生態位的高度分離有利于物種共存[35]。在空間利用方面,海南長臂猿是高度樹棲動物,幾乎不會下到地面尋找食物,而其他物種均有地面活動現象,如赤腹松鼠會在果實資源豐富的季節下到地面層搜尋食物[40]。此外,研究區域還發現另外一種靈長類獼猴,雖然該物種與海南長臂猿的食物、時間生態位高度重疊,但海南長臂猿出現位點并未發現獼猴,海南長臂猿在與獼猴的生態位競爭中可能處于優勢。海南長臂猿缺少自然天敵,但少數大型猛禽,如蛇雕(Spilornis cheela)等可能會攻擊長臂猿幼崽,本研究共記錄到2 種猛禽,即鷹雕和草鸮(Tyto longimembris),紅外相機監測和人為跟蹤均未發現對海南長臂猿幼崽的傷害行為。
3.2 海拔分布格局及年活動格局的差異物種豐富度的海拔分布格局可分為4 種常見的格局:遞減型、低高原型、低高原中峰型和中峰型[41],本研究獸類物種數雖然在海拔梯度間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整體上表現為隨著海拔的升高呈單調遞減趨勢,隨著海拔的升高,溫度、植被類型、食物資源等會呈現出一定的垂直分布和變化,進而對動物分布產生重要影響[42]。該研究區域海拔600~800 m、800~1 100 m、1 100 m 以上分別對應的是熱帶溝谷雨林、熱帶山地雨林和山地苔蘚林。在山地苔蘚林區域樹木稀疏且缺少高大喬木,會引發食物資源短缺,物種間競爭變大,亦或不能為某些樹棲動物提供隱蔽的棲息場所,如海南長臂猿會選擇胸徑更大,高度更高、冠幅更大、枝下更高的喬木夜宿[43]。鳥類的物種數指數先升高后減少,是典型的中峰模式,隨海拔上升氣溫下降,導致鳥類在海拔1 100 m 以上的分布種數、分布數量逐漸下降,這可能是高海拔區域鳥類物種多樣性指數較低的原因[33];分布區內低海拔區域較強的人為干擾,可能影響了鳥類的分布[34]。
海南長臂猿以及其他獸類年活動格局表明,海南長臂猿和海南鼯鼠的月活動強度有季節性變化,旱季月活動強度較高,雨季較低,這與海南長臂猿分布區的植被類型和氣候有關。在雨季,霸王嶺片區雨水充沛,大部分植物生長茂盛且處于結果期,故食物資源豐富且分布均勻;旱季降雨量偏低,植物果實減少引起海南長臂猿和海南鼯鼠的食物短缺。海南長臂猿等因移動需要付出一定的能量,可能也需要增加對葉芽類取食的策略或增加食物的攝入來彌補所消耗的能量[24],活動強度往往會因食物資源的時空變化而存在季節性差異[44]。雨季結束,旱季到來食物資源減少時,布設在果樹附近的紅外相機拍攝到的視頻顯示海南長臂猿和海南鼯鼠取果、采食畫面的滯留時間變長,也表明旱季的月活動強度比雨季高。其他獸類在雨季和旱季活動強度相對穩定,與食性有關,如飲食靈活的獼猴可以通過改變其食料偏好來避免與其他類群的種間競爭[45]。鳥類的生殖期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生活在我國的鳥類一般在3~8 月份生殖[46],研究區域的鳥類活動規律與此相符,活動峰值主要集中在1— 4 月份和7—8 月份。在繁殖期間,雌雄個體相遇的概率大幅提升,從而提高了月豐富度指數。然而,在1—2 月份山皇鳩和厚嘴綠鳩的月豐富度指數高,這可能與該地區的溫度較高有關。
3.3 樹棲紅外相機的監測優勢傳統的調查方法傾向于關注晝行性的野生動物,紅外相機技術可以監測到動物夜間活動,從而實現對目標物種的24 h 適時監測[47]。在監測活躍的、體型較大的樹棲物種,如海南長臂猿等也特別高效,盡管該物種實際數量很少,但拍攝到最多獨立有效照片,而且發現動物不會回避紅外相機,在自然條件下各種行為可以詳細地、近距離地記錄下來[2]。此外,雖然樹棲紅外相機高度暴露在雨水和陽光下,但此次林冠層紅外相機的故障率17%低于其他地方報道的熱帶雨林紅外相機的故障率70%[48]。本研究結果表明,在樹冠層中使用紅外相機調查樹棲哺乳動物效果與陸地相似,是調查林冠內隱蔽、夜間活動和活躍動物群落的有效方法。國內應用樹棲紅外相機調查林冠層野生動物的研究極少,可以在未來的調查工作中嘗試定義和標準化安裝規范,如樹棲紅外相機安裝的高度和樹種的選擇以及考慮到熱帶雨林較高的生物多樣性,在1 個布設位點安裝多個紅外相機等。
致謝:海南熱帶雨林國家公園霸王嶺片區對研究予以大力支持,護林員張志誠、李文永、謝贈南等對野外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幫助;陳少蓮和楊川在鳥類鑒別方面給予許多幫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