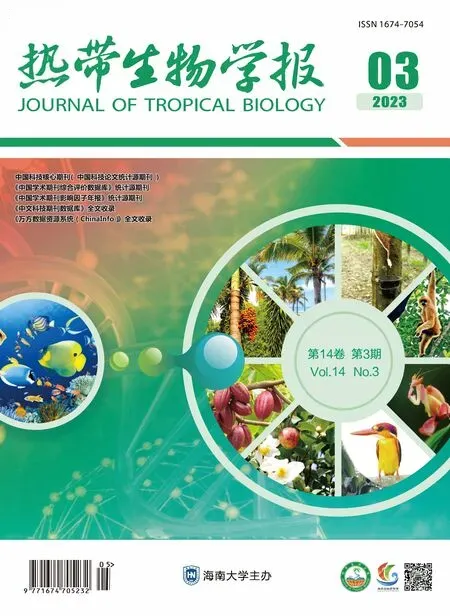豆大薊馬在海南的發生動態及其卵和蛹的防治藥劑初篩
郭靈杭,吳圣勇,唐良德
(1. 海南大學 植物保護學院,海口 570228; 2. 中國熱帶農業科學院環境與植物保護研究所/農業農村部熱帶作物有害生物綜合治理重點實驗室,海口 571101; 3. 中國農業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植物病蟲害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193; 4. 貴州大學綠色農藥全國重點實驗室/綠色農藥與農業生物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貴陽 550025)
豆大薊馬(Megalurothrips usitatusBagnall)又稱普通大薊馬或豆花薊馬,是豆科作物上的重要害蟲,尤其對海南、廣西、廣東、貴州等地的豇豆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和經濟損失,成為這些地區豇豆生產的重要限制因素[1]。近年來,海南豇豆種植面積穩定在2 萬hm2以上,產量近60 萬t,僅次于辣椒,是海南冬季瓜菜的主要栽培品種之一[2]。薊馬早期危害可造成豇豆葉片皺卷、生長點壞死,開花結莢期受害可造成大量落花減產和豆莢“黑化”,嚴重影響產量和品質[3]。為了有效防控薊馬,已開展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探索,如化學防治[4-7]、理化誘控防治[8-13]、生物防治[14-16]以及農業防治[17]等,但是目前生產上主要還是依賴于化學防治。由于豆大薊馬自身特性如蟲體微小、隱匿危害、繁殖力強、發育歷期短、世代重疊嚴重以及土壤中化蛹等,常造成對其的化學防治效果不理想,而高頻次高劑量地施用化學農藥可導致豆大薊馬對多種常用殺蟲劑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18-19]。提高防效和延緩抗藥性產生的重要途徑是科學地進行化學防治。科學化學防治一是要找準防治時期,二是要合理地選用殺蟲劑。不同殺蟲劑品種對豆大薊馬不同蟲態有著較大的毒力差異[20],因此,需要根據豆大薊馬田間發生的主要蟲態來選擇性地使用殺蟲劑,這就要求掌握不同殺蟲劑對薊馬各個蟲態的毒性。多種殺蟲劑對豆大薊馬成蟲和若蟲的毒力[19-22]已見報道,但未見對其卵和蛹的毒力報道。基于此,筆者選擇生產上多種常用殺蟲劑對豆大薊馬的卵和蛹進行室內毒力測定。種群動態和體型特征是昆蟲生態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對制定害蟲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義。已有研究報道豆大薊馬在豇豆上的空間分布[23]、色板誘集[3,11-12]、踏查[24]和基于性比的成蟲時空動態[25]研究。關于昆蟲在體型上的差異及其影響方面的研究表明,體型大小與昆蟲的生殖能力和抗逆性具有相關性,從而對害蟲的種群動態變化產生影響[26-28]。目前關于豆大薊馬在海南的全年發生動態以及地理種群體型大小還缺乏系統的調查研究。因此,筆者以海南豇豆主產區澄邁縣(海南北部)和三亞市(海南南部)為代表調查了豆大薊馬在海南豇豆的全年發生規律及不同地理位置種群的體型大小,以期為豆大薊馬的綜合防治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供試蟲源用于體型大小測定的豆大薊馬成蟲分別在2022 年4 月采集于澄邁縣大豐鎮信宜村(19°51′N;110°2′E)、在2021 年1 月采集于三亞市崖州區南濱農場(18°22′N;109°11′E)、在2021 年4 月采集于儋州市寶島新村豇豆田(19°30′N;109°29′E),室內飼養一代后的3 日齡成蟲用于體型大小測量。用于毒力測定的豆大薊馬蟲源采自海南省澄邁縣永發鎮豇豆田,在室內用豇豆豆莢飼養多代后用于實驗;飼養方法參照唐良德等[20]的方法。
1.2 供試藥劑97%高效氯氟氰菊酯(鄭州農田化工有限公司),76%甲氨基阿維菌素苯甲酸鹽(簡稱甲維鹽,河北天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92%阿維菌素(南通農藥劑型開發中心),96%吡蟲啉(四川國光農化股份有限公司),96%啶蟲脒(石家莊伊宏化工有限公司),97%溴蟲腈、95%溴氰蟲酰胺(湖北康寶泰精細化工有限公司),96%螺蟲乙酯(廣西南寧綠豐化工有限公司),上述藥劑均為原藥;99%綠穎礦物油(韓國SK 杰克株式會社,市售),乙基多殺菌素(艾綠士?60 g·L-1懸浮劑,美國科迪華公司,市售)。
1.3 豆大薊馬田間種群動態調查根據海南南部冬季種植和北部冬春種植為主全年均可種植豇豆的特點,南部選擇在三亞市崖州區南濱農場不定期對豇豆花期豆大薊馬進行隨機采樣調查(踏查),北部選擇在澄邁縣大豐鎮全年種植豇豆調查豆大薊馬的發生動態,并對全年氣溫進行監測。采用小米智能溫濕計(型號:LYWSD03MMC)每小時記錄1 次溫度,以每日24 時溫度的平均值為當天平均氣溫。采用隨機采樣調查法,每次調查30 朵花(芽)或葉片,將采集的花朵一一裝入封口袋內帶回實驗室進行鑒定和計數,現場計數葉片和花芽上的豆大薊馬,以平均每花或每葉的薊馬數量繪制種群發生動態圖。
1.4 豆大薊馬體型大小測量體長和體寬是昆蟲個體大小的度量[29-30]。采用基恩士(KEYENCE)超景深顯微鏡(型號:VHX-7000)對三亞、澄邁和儋州豆大薊馬雌雄個體分別進行體長和體寬的測量。測量蟲態為各地理位置種群飼養一代后的3 日齡成蟲,測量前將待測薊馬樣品置于-20℃冰箱中冷凍處理使其失去活動能力。
1.5 毒力測定方法卵的毒力測定方法采用浸漬法。在玻璃瓶(200 mL)底部墊一層粗糙的手紙,放置一節長約5 cm 的豇豆豆莢(切口兩端平整不留豆粒孔),然后每瓶接入20 頭5 日齡的薊馬雌成蟲,用74 μm 防蟲網和橡皮筋扎緊封口。產卵24 h 后,將豆莢取出放入預先配制好的藥液中,浸漬10 s 后取出轉移到墊有濾紙的培養皿(Ф=9 cm)中,置于(26 ± 1)℃、光暗比14 h∶10 h、相對濕度65%的培養箱中,培養96 h 后調查孵化的薊馬若蟲數量,以清水浸漬為對照處理。因薊馬卵產于植物組織內無法觀察,以孵化的若蟲數表示卵的存活數,以清水對照處理卵孵化若蟲數表示薊馬的產卵量[31-33]。每處理一節豆莢即一個重復,每個藥劑設置5 個濃度梯度,每個濃度4 次重復。
蛹的毒力測定方法采用POTTER 噴霧法,噴霧條件設定參照Tang 等[34]報道的方法。在培養皿(Ф=6 cm)中分別接入20 頭薊馬蛹,置于POTTER 噴霧塔下噴霧(噴霧壓強為100 kPa,沉降時間為10 s),每個處理噴霧量為1.5 mL,噴霧后將薊馬轉移至預先鋪墊一層濕潤的粗糙手紙作為化蛹基質的培養皿(Ф=6 cm)中,用74 μm 防蟲網和橡皮筋扎緊封口。置于(26 ± 1)℃、光暗比14 h∶10 h、相對濕度65%的培養箱中,每48 h 后觀察記錄蛹的存活情況,直至活蟲全部羽化,以羽化數表示存活數。根據預試驗,每個藥劑配制5 個濃度,每個濃度設4 次重復,以噴清水處理為對照。
1.6 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豆大薊馬的種群發生動態(數量)以及不同地理位置種群間體型大小的顯著性差異在SPSS 17.0 分析軟件中采用Tukey 法在0.05 水平上進行比較。不同藥劑對豆大薊馬卵和蛹的毒力測定實驗中,因豆大薊馬卵產于植物組織內無法觀察,以孵化的若蟲數表示卵的存活數,卵的死亡數(響應數)以對照組卵孵化若蟲數減去藥劑處理組卵孵化若蟲數計算。不同藥劑對豆大薊馬的致死中濃度(LC50)采用SPSS 分析軟件中的Probit 回歸分析法計算。
2 結果與分析
2.1 豆大薊馬在海南的種群發生動態由圖1-A 可知,豆大薊馬在豇豆的全生育期均可發生,以花期發生數量最大,苗期發生數量最低。豇豆屬于循環花序植物,通常可采收2 個花期,第2 花期薊馬發生數量顯著降低。從圖中還可看出,第2 茬和第3 茬豇豆整個生育期氣溫明顯高于第1 茬,且豆大薊馬發生的種群數量也顯著高于第1 茬同期豆大薊馬發生的數量,表明氣溫顯著影響豆大薊馬的發生。

圖1 豆大薊馬在海南的種群發生動態
由圖1-B 可知,在主要種植時段(冬春季)豆大薊馬在豇豆上的發生數量呈明顯單峰型分布,從12 月中下旬到翌年的2 月中下旬,豆大薊馬的種群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數量水平(>10 頭·花),在1 月下旬至2 月初達到最高峰(約 30 頭·花)。在非主要種植時段(4 月后)豆大薊馬數量迅速下降,并長時間維持在較低數量水平(<5 頭·花)。
2.2 不同地理位置種群豆大薊馬的體型大小通過對不同地理位置種群豆大薊馬體型的比較(表1),儋州種群的雌雄個體體長和體寬均顯著大于三亞種群和澄邁種群,且三亞種群也顯著大于澄邁種群。

表1 豆大薊馬不同地理位置種群體型大小
2.3 不同藥劑對豆大薊馬的毒力不同藥劑對豆大薊馬卵的毒力表現顯著不同(表2)。其中,螺蟲乙酯對豆大薊馬卵的活性最高(LC50=18.51 mg·L-1),乙基多殺菌素、溴氰蟲酰胺和啶蟲脒對豆大薊馬卵也表現較高的毒力,LC50分別為46.17、52.54 和58.53 mg·L-1,其他測試藥劑對豆大薊馬卵的活性較低(LC50> 110 mg·L-1)。

表2 不同藥劑對豆大薊馬卵的毒力
不同藥劑對豆大薊馬蛹的毒力也表現顯著不同(表3)。乙基多殺菌素和溴蟲腈對豆大薊馬蛹的活性最高,LC50分別為26.18 和27.71 mg·L-1,其次為高效氯氟氰菊酯(LC50=35.84 mg·L-1)和甲維鹽(LC50=37.32 mg·L-1),再次是阿維菌素(LC50=56.31 mg·L-1)和溴氰蟲酰胺(LC50=62.98 mg·L-1),新煙堿類殺蟲劑吡蟲啉和啶蟲脒對豆大薊馬蛹的活性較低(90 mg·L-1< LC50< 115 mg·L-1)。

表3 不同藥劑對豆大薊馬蛹的毒力
3 討 論
明確害蟲田間發生種群動態是開展害蟲綜合治理(IPM)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薊馬是典型的r-對策害蟲,具有發育歷期短、世代重疊嚴重、繁殖力強等特點,且既可營兩性生殖又可營孤雌生殖,種群增長迅速。通過田間種群動態監測發現,豆大薊馬在海南全年均可發生,但受豇豆生育期顯著影響,表現為花期發生數量顯著大于其他生育期,與花期發生尤為嚴重的報道一致[3,35]。另外,在花期對薊馬監測發現在海南南部(三亞)豇豆主要種植時段發生數量大,非主要種植時段發生數量驟減,表明寄主及其生育期是影響豆大薊馬種群發生動態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昆蟲作為一種變溫動物,其發生又受到環境溫度的顯著影響[36-37],豆大薊馬在田間的種群發生動態也印證了這一現象。豆大薊馬在日平均氣溫30℃左右的環境下(第二茬和第三茬)種群發生數量顯著高于同期溫度下(< 25℃,第一茬)的種群數量。有研究表明豆大薊馬產卵量在30℃時最高,平均產卵量達到232.78 粒·雌[38],這與本研究結果是十分吻合的。但溫度過高,也不利于豆大薊馬的田間發生,正如本研究的調查結果發現在海南南部(三亞)豇豆的非主要種植時段,正值高溫階段,既不利于豇豆生長也不利于豆大薊馬的發生(圖1-B)。
體型是昆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特征之一,包括卵的大小、卵質量,蛹質量,成蟲體長、體寬、體質量等,昆蟲雌雄個體之間體型存在差異的現象被稱為性體型二型性現象,同時這種現象存在著地理差異[27,39]。本研究發現豆大薊馬成蟲不僅存在性體型二型性現象,而且發現各地理種群存在顯著體型差異,體型從大到小依次為儋州種群 >三亞種群 > 澄邁種群。有研究結果表明,環境因素在昆蟲體型的地理差異中起到重要作用[40],包括溫度、濕度、光照、光周期、寄主植物以及種群密度等[27-28]。本研究結果發現,豆大薊馬不同地理位置種群體型大小存在顯著差異,但受何種因素調控還不得而知。此外,體型大小對昆蟲的繁殖能力、競爭能力和抗逆性等生物學特性會產生重要影響[28,41]。總體來說,體型大的昆蟲的繁殖能力更強,更具有交配選擇優勢,可提高后代的適合度[42];體型大的昆蟲在食物的競爭、領地的侵占或保衛、天敵防御等方面均表現出一定的優勢[43];體型大的昆蟲的體內儲存著相對較多的能量物質,對逆境的耐受能力也較強[44]。然而,本研究發現體型大的儋州種群田間發生并不嚴重,反而體型小的三亞種群和澄邁種群在田間發生更為嚴重(圖1)。這可能是受當地的種植模式(儋州零星種植,三亞、澄邁規模種植)、寄主品種、環境因子以及人為干預(化學防治)等綜合因素調控所致。豆大薊馬體型差異的生物學意義及其調控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
薊馬是纓翅目昆蟲的總稱,分為錐尾(鋸尾)亞目和管尾亞目,屬過漸變態昆蟲,其生活史經歷卵、若蟲、蛹和成蟲4 個階段。錐尾亞目具鋸狀產卵器將卵產于植物組織內,蛹通常在葉背面葉脈的交叉處、葉柄基部、萼片間、葉鞘間、果實凹陷處及枯枝落葉層或土壤等場所化蛹。豆大薊馬的卵在豇豆上主要產于花器、生長點和嫩莢中,老熟若蟲轉移到土壤中化蛹,這一習性給生產上防治豆大薊馬帶來巨大挑戰。在害蟲整個生態控制體系中,需要各個環節均采取相應的措施,防治才能更有效和可持續的控制害蟲的暴發危害[45]。生產上對豆大薊馬進行防治時,通常僅考慮肉眼可見的成蟲和若蟲,往往忽視了看不見的卵和蛹,缺乏防治的科學性和針對性,造成防效不理想。因此針對此類害蟲防控時需要對其生活史的各個蟲態采取有效措施,在對黃瓜作物上的西花薊馬和煙薊馬進行生物防治的例子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防治理念[46-47]。本研究發現,乙基多殺菌素、螺蟲乙酯有較好的殺卵效果,乙基多殺菌素、溴蟲腈和高效氯氟氰菊酯有較好的滅蛹效果,這些殺蟲劑對不同蟲態的毒力差異與蟲態習性、殺蟲劑的作用方式緊密相關,薊馬的卵產在植物組織內,而化蛹則在土壤或落葉層中,因而殺卵就對藥劑的內吸性或滲透性提出要求,而殺蛹則要求有較高的觸殺活性[48-49]。另外,毒力差異也可能與毒力測定方法有關[50-51]。
種群動態監測對于豆大薊馬的田間用藥防治具有很好的指導作用。通過調查發現,每一茬豇豆都存在明顯的豆大薊馬發生高峰(圖1-A),且高峰期均為豇豆花期,因而豇豆花期是化學防治豆大薊馬的主要時期。考慮到豆大薊馬世代發育歷期短(30℃下為10.57 d)[36],因而花期豆大薊馬成蟲數量大時,除了選用對成蟲有較高活性的殺蟲劑外,還需要選擇具有高殺卵活性的藥劑,做到既殺滅成蟲又殺滅卵;而在若蟲大量發生時,除了選用對若蟲有較高活性的殺蟲劑外,也需要選擇對蛹有較高活性的藥劑,做到若蟲和蛹兼殺的效果。根據田間蟲態發生規律選擇防治藥劑,有利于提高豆大薊馬防治的針對性,從而達到提高防效的目的,同時田間作業時要盡量對植株/地面壟溝噴霧均勻,以提高對豆大薊馬各蟲態的防效。
4 結 論
豆大薊馬存在性體型二型性和多態性現象,在海南全年發生且是豇豆上的主要害蟲,并受物候期和氣溫的雙重影響。卵產于寄主組織中,在土層或落葉層化蛹,卵和蛹對化學殺蟲劑表現出敏感性差異。其中,螺蟲乙酯具有較高的殺卵活性,而乙基多殺菌素和溴蟲腈具有較高的殺蛹活性,可推薦螺蟲乙酯、乙基多殺菌素和溴蟲腈作為豆大薊馬卵和蛹的田間防治藥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