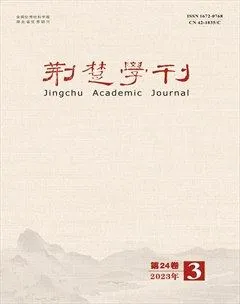魯迅文化自信簡(jiǎn)論
周甲辰
摘要:在中華民族積貧積弱、內(nèi)憂外患的時(shí)代,魯迅始終保持堅(jiān)定的文化自信。他力主審視傳統(tǒng),大膽與過(guò)去告別;他倡導(dǎo)“睜開(kāi)了眼看”,直面血淋淋的現(xiàn)實(shí);他提出“拿來(lái)主義”,要求主動(dòng)拿來(lái)他國(guó)他民族的東西為我所用;他以“抉心自食”的勇氣,不斷進(jìn)行自我剖析與自我反省。學(xué)習(xí)與借鑒魯迅的文化自信,對(duì)于我們?nèi)嫣嵘褡逦幕孕牛霌P(yáng)與發(fā)展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關(guān)鍵詞:魯迅;民族文化;文化自信
中圖分類號(hào):I01? ?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 ? 文章編號(hào):1672-0768(2023)03-0034-04
中華民族在魯迅所處時(shí)代積貧積弱、內(nèi)憂外患,文化自信一再遭受碾壓摧殘,部分國(guó)人自卑自棄,文化自信完全喪失。在他們眼里,“世界上的五色人種中,白人是最為優(yōu)等的民族”[ 1 ]? 552。他們甚至得出了“中國(guó)必定滅亡,黃種人必定剿絕”的驚人結(jié)論[ 2 ]。但是,魯迅始終是一個(gè)“清醒的文化自信者”[ 3 ]。他堅(jiān)持認(rèn)為,“說(shuō)中國(guó)人失掉自信力,用以指一部人則可,倘若加于全體,那簡(jiǎn)直是誣蔑”(《中國(guó)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圍繞弘揚(yáng)與發(fā)展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魯迅曾提出一系列思想觀點(diǎn),值得我們認(rèn)真學(xué)習(xí),深入研究。
一、審視傳統(tǒng),大膽與過(guò)去告別
自信與自大自傲有著本質(zhì)區(qū)別。“君子之過(guò)也,如日月之食焉:過(guò)也,人皆見(jiàn)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yǔ)·子張》)。真正自信的人不會(huì)自以為是,固持己見(jiàn),而是敢于甚至樂(lè)于直面自身的不足與錯(cuò)誤,一個(gè)自信的民族也是如此。高高在上,滿腦子“中央之國(guó)”意識(shí),完全以自我為中心,熱衷于自我美化與神化,這從表面上看似乎非常愛(ài)國(guó),也非常自信,但實(shí)際上或是出于夜郎自大,無(wú)知淺薄;或是源于欲望膨脹,迷失自我,都是與文化自信相悖的。“要談中國(guó)文化復(fù)興,必須有一個(gè)批判清理的過(guò)程;要談中國(guó)文化的自信,也必須有面對(duì)‘國(guó)民性糟粕的勇氣。”[ 4 ]魯迅對(duì)傳統(tǒng)文化始終持冷峻的批評(píng)態(tài)度,他認(rèn)為自尊自大,故步自封會(huì)將整個(gè)民族拖入到危險(xiǎn)的境地。他警告說(shuō):“中國(guó)既以自尊大昭聞天下,善詆諆者,或謂之頑固;且將抱守殘闕,以底于滅亡。”(《文化偏至論》)而對(duì)于部分人“時(shí)時(shí)念輝煌之舊有”,就像阿Q一樣總是炫耀過(guò)去比人家闊多了,老祖宗比人家闊多了,魯迅特別反感,曾給予辛辣的諷刺。他說(shuō):“只要從來(lái)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wú)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guó)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艷若桃花;潰爛之時(shí),美如乳酪。國(guó)粹所在,妙不可言。”(《隨感錄三十九》)他明確警醒國(guó)人,必須正確認(rèn)識(shí)和辯證對(duì)待民族文化,注意辨明善惡高下,決不能抱殘守缺,以丑為美。
魯迅自喻為“毒蛇”和“游魂”,常以非凡的勇氣毫不留情地清理與揭批傳統(tǒng)文化的糟粕。他敢于質(zhì)疑:“從來(lái)如此,就對(duì)么?”(《狂人日記》)在他眼里,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都是為了治民眾者,即權(quán)勢(shì)者設(shè)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diǎn)沒(méi)有”(《在現(xiàn)代中國(guó)的孔夫子》)。他曾說(shuō)過(guò):“佛教和孔教一樣,都已經(jīng)死亡,永不會(huì)復(fù)活了”[ 5 ] 44。他還嘲笑老子:“用盡哲學(xué)的腦筋,只是一個(gè)沒(méi)有法”(《出關(guān)》)。他認(rèn)為,中國(guó)的國(guó)魂里大概總有兩種魂:官魂和匪魂,個(gè)人則永遠(yuǎn)不被發(fā)現(xiàn)(《學(xué)界的三魂》)。1925年3月18日,他在給許廣平的信里提到:“中國(guó)大約老了,社會(huì)上事無(wú)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wú)論加進(jìn)什么東西去,都變成漆黑。”他還認(rèn)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是“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國(guó)歷史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shí)代”和“暫時(shí)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shí)代”兩種(《燈下漫筆》)。他甚至說(shuō),傳統(tǒng)仁義道德的本質(zhì)就在于“吃人”(《狂人日記》)。也正是由于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與中國(guó)社會(huì)倍感失望,魯迅才遠(yuǎn)赴日本留學(xué),“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吶喊〉自序》)。魯迅還提出過(guò)一系列著名觀點(diǎn),像“中國(guó)國(guó)粹等于放屁”“中國(guó)古書(shū)葉葉害人”“中國(guó)漢字必須廢除”“青年要少讀或不讀中國(guó)書(shū)”等。他擔(dān)心中國(guó)如若“恃著固有而陳舊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于要走到滅亡的路”(《〈出了象牙之塔〉后記》)。他說(shuō):“我們此后實(shí)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無(wú)聲的中國(guó)》)在此基礎(chǔ)上,他呼吁青年們“敢想,敢說(shuō),敢作,敢當(dāng)”“沖破一切傳統(tǒng)思想和手法”;呼吁“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燈下漫筆》);呼吁洞達(dá)世界大勢(shì)的明哲之士“取今復(fù)古,別立新宗”(《文化偏至論》)。魯迅的這些闡述明顯呈現(xiàn)出憤激與偏頗。但是,由于他處于一個(gè)新舊斗爭(zhēng)十分慘烈,反封建任務(wù)極其艱巨的年代,因而他對(duì)傳統(tǒng)文化持全力批判與矯枉過(guò)正的態(tài)度,其實(shí)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的這種憤激與偏頗對(duì)于促進(jìn)國(guó)人的思想覺(jué)醒與個(gè)性解放,促進(jìn)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新發(fā)展,在某種意義上說(shuō)也是必須的。
二、睜了眼看,直面血淋淋的現(xiàn)實(shí)
自信與自憐自戀也有本質(zhì)區(qū)別。習(xí)慣于自我否定與自我矮化,對(duì)于本民族的東西“雖一石一華,亦加輕薄”(《破惡聲論》),連月亮也都認(rèn)為是西方的圓,這肯定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xiàn);而沉迷于中央大國(guó)的舊夢(mèng),習(xí)慣于歌功頌德,文過(guò)飾非,諱疾忌醫(yī),也同樣是文化自信缺失的表現(xiàn)。魯迅提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談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紀(jì)念劉和珍君》)在他看來(lái),閉目塞聽(tīng),耽于幻想是弱者的表現(xiàn);真正自信而強(qiáng)大的人決不會(huì)懼怕真相,也不會(huì)逃避矛盾。但是,魯迅卻痛苦地發(fā)現(xiàn),中國(guó)歷史上“真正的猛士”實(shí)在太少了,“中國(guó)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只好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lái),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guó)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他說(shuō):“中國(guó)的文人也一樣,萬(wàn)事閉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瞞和騙。”他還說(shuō),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jiàn)一切圓滿,“于是無(wú)問(wèn)題、無(wú)缺陷、無(wú)不平,也就無(wú)解決、無(wú)改革、無(wú)反抗。”在他眼里,古代才子佳人小說(shuō)便是“瞞”和“騙”的典型,因?yàn)樗鼈兛傄幵煲粋€(gè)“才子及第,奉旨完婚”的完滿結(jié)局。魯迅認(rèn)為這種“瞞”與“騙”的作品是非常有害的,它所維護(hù)的無(wú)疑只是統(tǒng)治者的神圣形象與既得利益,同時(shí)它也顯露出作者個(gè)性化思考與獨(dú)立人格的缺失,而從審美接受的角度講,它“更令中國(guó)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甚而至于已經(jīng)自己不覺(jué)得”。因此,魯迅一直旗幟鮮明地反對(duì)“瞞”和“騙”,疾聲呼吁國(guó)人“睜開(kāi)了眼看”(《論睜了眼看》)。魯迅認(rèn)為,我們只有“睜了眼看”,發(fā)現(xiàn)畸形,揭示病痛,引起療救者注意,方能促進(jìn)社會(huì)改善與進(jìn)步,也方能提升國(guó)人的文化自信。
在反對(duì)“瞞”和“騙”的同時(shí),魯迅不遺余力地倡導(dǎo)藝術(shù)的真實(shí)性。他說(shuō):“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dòng)中國(guó)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為此他鼓勵(lì)作家“大膽地說(shuō)話,勇敢地進(jìn)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kāi)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fā)表出來(lái)”(《無(wú)聲的中國(guó)》)。他認(rèn)為,一個(gè)作家“只要寫出實(shí)情,即于中國(guó)有益。”(《致姚克》1934年月25日)。他還充滿激情地說(shuō):“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誠(chéng)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lái)的時(shí)候早到了,早就應(yīng)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chǎng),早就應(yīng)該有幾個(gè)兇猛的闖將!”(《論睜了眼看》)因?yàn)樽非笪乃嚨恼鎸?shí)性,在魯迅眼里,“辱華”的書(shū)籍和電影其實(shí)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閉目不視,充耳不聞,拒不改進(jìn)(《立此存照·三》)。作為一個(gè)作家,魯迅曾感慨“敢于指摘自己國(guó)度的錯(cuò)誤的,中國(guó)人就很少”(《兩地書(shū)之廿九》),因此他將自己比作貓頭鷹,說(shuō)自己的言論是聲聲“梟鳴”。在創(chuàng)作中,他勇于揭開(kāi)層層假面,擊穿種種謊言,呈現(xiàn)血淋淋的現(xiàn)實(shí),報(bào)告那些“大不吉利的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魯迅一直十分留意他國(guó)他民族民眾眼中中國(guó)國(guó)民的形象,他自己也曾以“立人”為目的,以小人物為對(duì)象,全面剖析與呈現(xiàn)了多疑、巧滑、虛偽、好面子、重名目、冷血麻木、調(diào)和折中、安于當(dāng)奴才、喜歡當(dāng)看客、說(shuō)話不算數(shù)、做事總敷衍,以及對(duì)羊顯兇獸相,對(duì)兇獸顯羊相等種種“不長(zhǎng)進(jìn)的民族病態(tài)”,他對(duì)國(guó)民劣根性的表現(xiàn)全面清晰,入木三分。在學(xué)者們眼里,魯迅寫的全是講真話的書(shū),他的第一個(gè)特點(diǎn)是“最清醒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魯迅的創(chuàng)作,從總體上看不僅深入展示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的凋敝、混亂與黑暗,揭示了婦女、農(nóng)民與小知識(shí)分子等小人物的生存困境,彰顯了改革與革命的必然性;更為重要的是他重新發(fā)現(xiàn)了中國(guó)與中國(guó)人,并以強(qiáng)烈的文化自信嘗試培育與構(gòu)建新型人格,“他在傳統(tǒng)文化研究與表現(xiàn)方面的地位無(wú)可替代”[ 6 ] 。
三、放手拿來(lái),一切皆為我所用
自信不等于自守自閉。崇洋媚外,鼓吹全盤西化,總是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趨,東施效顰,這固然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xiàn);而盲目排外,閉目塞聽(tīng),閉關(guān)鎖國(guó),關(guān)起門來(lái)當(dāng)皇帝,也同樣應(yīng)該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xiàn)。一般而言,戰(zhàn)戰(zhàn)兢兢,畏寒怕風(fēng),視他國(guó)他民族的東西為洪水猛獸,只能說(shuō)明自身體虛膽怯。自信總是與包容開(kāi)放聯(lián)系在一起,自信而強(qiáng)大的民族具有博大的胸懷、非凡的氣度,總會(huì)放心大膽地敞開(kāi)大門,從容擁抱和接納四方來(lái)賓;也總會(huì)昂首闊步走向世界,縱覽全球風(fēng)景,兼收并蓄,博采眾長(zhǎng)。魯迅既堅(jiān)決反對(duì)“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lái)”的“閉關(guān)主義”,也反對(duì)以“發(fā)揚(yáng)國(guó)光”為名,遵照“友邦”喜好,將民族文化作品簡(jiǎn)單送往歐洲展覽的“送去主義”。他一直大力提倡并始終堅(jiān)持“拿來(lái)主義”。他的拿來(lái)主義強(qiáng)調(diào)以我為主,主動(dòng)拿來(lái),以主人翁的態(tài)度對(duì)待外來(lái)文化,使一切外來(lái)的東西都為我所用。魯迅認(rèn)為,對(duì)于他國(guó)家他民族的文化,我們不能被動(dòng)地等待人家送來(lái),因?yàn)槿思摇八蛠?lái)”的東西,未必就是我們需要的,像英國(guó)的鴉片、德國(guó)的廢槍炮、法國(guó)的香粉和美國(guó)的電等。他說(shuō):“我們所要明白的,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他人來(lái)化我們”。他提出,我們要以“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的態(tài)度對(duì)待世界各國(guó)文化,不問(wèn)新、舊,古、今,洋、土,只要有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占有,“拿來(lái)”,然后再甄別,挑選,根據(jù)具體情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拿來(lái)主義》)。他還舉例說(shuō),我們應(yīng)該像漢唐盛世時(shí)那樣,魄力雄大,根據(jù)自己的需要主動(dòng)地去“將彼俘來(lái)”“自由驅(qū)使,絕不介懷”。而不應(yīng)該像宋朝時(shí)那樣,實(shí)力衰弊,神經(jīng)過(guò)敏,“每遇外國(guó)東西,便覺(jué)得仿佛彼來(lái)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tuán)。”(《看鏡有感》)魯迅這種對(duì)于民族文化的態(tài)度,無(wú)疑就蘊(yùn)含著堅(jiān)定而強(qiáng)烈的文化自信。
魯迅很早就明確倡導(dǎo)“別求新聲于異邦”(《摩羅詩(shī)力說(shuō)》)。他認(rèn)為,中國(guó)要想避禍就福,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在立人,立人而后凡事舉”(《文化偏至論》)。而欲立人,則離不開(kāi)“別人的精神燃料”。他還認(rèn)為,文藝對(duì)于培育新型人格非常重要,而要發(fā)展新文藝,也同樣離不開(kāi)“異域的營(yíng)養(yǎng)”。閉關(guān)鎖國(guó),一味拒棄他國(guó)他民族先進(jìn)的思想文化,勢(shì)必會(huì)導(dǎo)致文藝的衰落,也勢(shì)必會(huì)導(dǎo)致國(guó)民的愚弱。他說(shuō):“沒(méi)有拿來(lái)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méi)有拿來(lái)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拿來(lái)主義》)他曾疾聲高呼:“屈尊學(xué)學(xué)槍擊我們的洋鬼子”(《忽然想到·十一》)。要求我們坦然承認(rèn)差距,廣泛向其他國(guó)家和民族學(xué)習(xí),以人之長(zhǎng)補(bǔ)己之短。他曾這樣總結(jié)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此后如要?jiǎng)?chuàng)作,第一須觀察,第二是要看別人的作品,但不可專看一個(gè)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縛住,必須博采眾家,取其所長(zhǎng),這才后來(lái)能夠獨(dú)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國(guó)的作家。”(《致董永舒》1933年3月8日)1927年9月,他為辭謝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提名寫信給臺(tái)靜農(nóng),明確說(shuō)自己因?yàn)樽髌贩至窟€不足,還不配得這獎(jiǎng)金,“要拿這錢,還欠努力”。同時(shí),他提出中國(guó)文學(xué)還比較薄弱,應(yīng)該多向外國(guó)文學(xué)學(xué)習(xí)(《致臺(tái)靜農(nóng)》1927年9月25 日)。在民族文化建設(shè)方面,他堅(jiān)決反對(duì)文化專制主義的封閉與保守,他非常重視世界性的眼光,強(qiáng)調(diào)以更宏闊的視野來(lái)審視與發(fā)展民族文化。正是基于這樣的一些認(rèn)識(shí),魯迅舍身求法,自比普羅米修斯,盜他國(guó)他民族之火,“煮自己的肉”,在30多年時(shí)間里先后翻譯出100多位作者共300多萬(wàn)字的作品,享有“現(xiàn)代玄奘”的美譽(yù)。而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明顯可以看到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爾扎克、勃?jiǎng)诮椈莸聽(tīng)枴⑺雇蛱睾拖哪渴热说挠绊憽?/p>
四、抉心自食,深入剖析自我
自信也不等于自滿自欺。孤芳自賞,孤高自許,總覺(jué)得自己超人一籌,這往往不是源于自信,而是源于自卑與虛榮。在魯迅看來(lái),一個(gè)人越是缺乏自信,往往越是講究臉面,維護(hù)聲譽(yù),阿Q就是如此。阿Q雖然身處社會(huì)底層,卻總是要維護(hù)畸形的自尊,連自己的癩頭瘡也被認(rèn)為是光榮的標(biāo)志,是別人不配有的。相反,“明哲之士,反省于內(nèi)面者深”(《文化偏至論》)。自信而有智慧的人往往能直面自身的缺點(diǎn)與不足,樂(lè)于且善于自我檢討與反省。魯迅認(rèn)為,這種自我檢討與反省對(duì)于民族的振興非常重要:“欲揚(yáng)宗邦之真大,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jué)”(《摩羅詩(shī)力說(shuō)》)。因此,他很早就希望中華民族能夠“淵思冥想之風(fēng)作,自省抒情之意蘇”(《文化偏至論》),時(shí)刻不忘自省與自強(qiáng)。魯迅還提出:“在小說(shuō)里可以發(fā)見(jiàn)社會(huì),也可以發(fā)見(jiàn)我們自己”(《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這里的“發(fā)現(xiàn)我們自己”,應(yīng)該既源于作者“連自己也燒在這里面”的切身體驗(yàn),也源于作者的自我省視與自我剖析。作為一個(gè)作家,魯迅特別重視審視與剖析自我。他認(rèn)為,我們不僅要研究讀書(shū),還要研究自己;不僅要有“知人之明”,還要有“自知之明”。他痛惜“中國(guó)人總不肯研究自己”,他自喻為“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長(zhǎng)蛇”(《墓碣文》),對(duì)自我的解剖與反省一直是冷峻而嚴(yán)苛的。他說(shuō):“我的確時(shí)時(shí)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wú)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寫在〈墳〉后面》)在魯迅無(wú)情的自剖與反省里,我們不難看到他追求浴火重生的自由意志,看到他始終面向未來(lái),不斷提升與完善自我的自信與堅(jiān)定。
魯迅關(guān)于民族文化的自信,“建立在自我解剖的基礎(chǔ)上”[ 7 ]。作為“二十世紀(jì)中國(guó)最痛苦的一顆靈魂”,一個(gè)追求“精神獨(dú)異”的個(gè)人,魯迅在創(chuàng)作中并不是一個(gè)站在云端“超人”,嘴角掛著莊嚴(yán)的微笑,一味指斥世人的愚劣;相反,他始終不忘聚焦自己的內(nèi)在世界,冷峻地審視與呈現(xiàn)自己情感的傷疤、性格的弱點(diǎn)與靈魂的暗斑,坦承自己的孤獨(dú)與徘徊、迷惘與無(wú)奈、虛無(wú)與絕望。他對(duì)自我的批判是冷峻的、深廣的、赤裸裸的。他明確意識(shí)到,自己不僅不是一個(gè)振臂一呼,應(yīng)者云集的英雄,而且置身在吃人的家族中,還曾無(wú)意間吃過(guò)幾片人肉(《狂人日記》)。他從不避諱自己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想要去除而不能。他感覺(jué)自己存活在這個(gè)世界上就是一個(gè)疲憊不堪的匆匆“過(guò)客”(《過(guò)客》),一個(gè)顫動(dòng)著身軀的“垂老的女人”(《頹敗線的顫動(dòng)》),一個(gè)彷徨于明暗之間的“影”而已(《影的告別》)。他的作品因而常呈現(xiàn)“反省”與“懺悔”的特征[ 8 ],也常具有自我宣泄與自我救贖的意味。而在以“立人”為目的,揭示民族劣根性的過(guò)程中,魯迅始終不忘將自己也擺進(jìn)去,視野由外而內(nèi),將關(guān)注點(diǎn)更多地轉(zhuǎn)向啟蒙知識(shí)分子本身,在自我審視、自我剖析與自我否定中,完成自我超越、自我革新與自我涅槃,從而擺脫“彷徨于無(wú)地”的困境。作品里的人物因而常帶有作者自身的影子,孔乙己穿著破爛的長(zhǎng)衫,在眾看客嘲笑聲中普及“茴”四種寫法之類的學(xué)問(wèn),折射出魯迅自己對(duì)啟蒙知識(shí)分子身份與職責(zé)的堅(jiān)守(《孔乙己》);夏瑜身陷囹圄,還不忘對(duì)獄吏進(jìn)行啟蒙教育,卻反挨獄吏耳光,折射出魯迅及其戰(zhàn)友們推進(jìn)啟蒙教育的尷尬與痛苦(《藥》);面對(duì)祥林嫂關(guān)于人到底有沒(méi)有靈魂的詢問(wèn),“我”只能支吾、逃逸,折射出魯迅等啟蒙知識(shí)分子面臨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時(shí)的無(wú)奈與困惑(《祝福》)。而《一件小事》《在酒樓上》《孤獨(dú)者》《傷逝》《風(fēng)箏》等作品,更是均以深入的自我剖析而著名,曾被研究者定義為“自剖作品”。
五、結(jié)語(yǔ)
在世界多極化、經(jīng)濟(jì)全球化與文化多元化的現(xiàn)代語(yǔ)境中,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會(huì)與對(duì)立沖突日益頻繁,堅(jiān)定民族文化自信較之以往更為重要。“沒(méi)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méi)有文化的繁榮昌盛,就沒(méi)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fù)興。”魯迅還是一個(gè)埋頭苦干的人,在民族文化的研究與建設(sh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魯迅的文化自信,不是口號(hào)和宣言,而來(lái)自親身實(shí)踐。”[ 9 ]魯迅被譽(yù)為現(xiàn)代中國(guó)的“民族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曾說(shuō):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0 ] 698。因此,學(xué)習(xí)與借鑒魯迅的文化自信,對(duì)于我們進(jìn)一步提升民族文化自信,促進(jìn)社會(huì)主義文化強(qiáng)國(guó)建設(shè)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梁?jiǎn)⒊?飲冰室文集點(diǎn)校[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2]章太炎.演說(shuō)錄[J].民報(bào),第6號(hào).
[3]李繼凱.魯迅:現(xiàn)代中華民族魂[J].魯迅研究月刊,2018(3):4-8.
[4]張釗貽.魯迅“國(guó)民性”思想與中國(guó)文化復(fù)興與自信[J].齊魯學(xué)刊,2019(3):146-152.
[5]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6]溫儒敏.為何讀魯迅,怎么讀魯迅[N].深圳特區(qū)報(bào),2021-10-9(08).
[7]張妮. 透過(guò)家書(shū),走近真實(shí)的魯迅[N].環(huán)球時(shí)報(bào),2021-09-24(13).
[8]伊藤武丸.魯迅的“生命”與“鬼”──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J],文學(xué)評(píng)論,2000(1):135-141.
[9]黃喬生. 立此存照:拿來(lái)主義與中國(guó)人的自信力——魯迅晚年文化定論[J].名作欣賞,2021(13):107-110.
[10]毛澤東.毛澤東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責(zé)任編輯:陳麗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