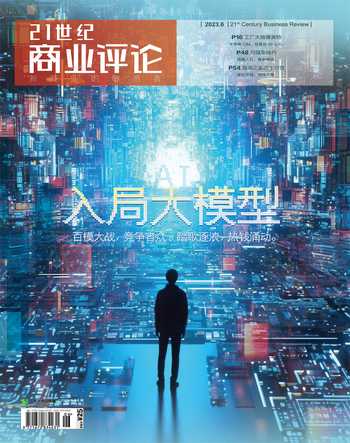麻省理工學院的開關
吉米·索尼 羅伯·古德曼

“學院傳說,眼尖的人有時候能夠看到走廊墻壁上的鉛筆痕跡。這些線與肩同高、與地面平行,據說是學院校友留下來的痕跡,他們對走廊的環境十分熟悉,能夠閉著眼睛走......。”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家弗雷德·哈普古德寫道。
在還是新生的時候,克勞德·香農有時候會路過一排雕塑,上面都刻著偉人的名字:阿基米德、哥白尼、牛頓、達爾文。
麻省理工學院是新古典主義之島,位于波士頓的一個工業區內。學院中間隧道上方建有萬神殿式的圓頂,距離查爾斯河數英里遠,圓頂與附近的工廠形成鮮明的對比。
隧道上方的圓頂本就是建筑師們之間妥協的產物,他們中有些人認為新校院應當同河畔的其他大學有所區別,另一些人則堅持,應當“秉承效率的原則,避免師生做無用功,它相當于最好的工業作品”。
這就是麻省理工學院在世界上定位的一個縮影,它既是工業的補充,又追求“更純粹”的科學,工廠和圓頂兩者的結合正體現了這一點。
這些建筑本身就是量化思維的產物,它們以數字而非名字為人們知曉。
在這里,21歲的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開始注意到,可把布爾代數的“真”與“假”,和電路系統的“開”與“關”對應起來,并用1和0表示。
用布爾代數分析并優化開關電路,香農一舉奠定了數字電路的理論基礎。
重復開關
一張關于布什分析儀的明信片,將香農帶到了13號樓。
正是范內瓦.布什(美國科學家、工程師,有“信息時代教父”之稱),批準了他的申請,錄取他做碩士項目。他們都是忙碌的工程師。為更好地工作、賺錢養家,布什曾成功同時拿到本科和碩士學位。
香農用了3年時間讀完了高中,在4年里拿到兩個學士學位,在短暫的暑假休整之后,他就要開始攻讀研究生課程了。
布什讓他的這位新學生,管理分析儀最先進、最精密的部分。
直到1935年,就是香農到MIT的前一年,微分分析儀(一種求解微分方程的機械式模擬計算機),已達到它的極限。機械設計精巧,每個新方程都必須先使之解構再重組。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布什要發明一種分析儀,可以在運轉的過程中,對自身進行基礎性重組。
它裝有自動控制器,能夠使自身不間斷地從一個方程式自動轉到下一個方程式,或者甚至能夠同時解決多種相互作用的方程式。它裝了開關,來代替螺絲刀。
在經濟大蕭條時期,麻省理工學院的經費預算,遠遠不能滿足布什的雄心,他仍然能從洛克菲勒基金會募集到265000美元私人捐款,來研發新一代計算機。
同時,他將克勞德.香農帶進麻省理工學院,來幫助他開展新的研究。接下來的3年,香農的世界,就是灰色的長廊和嗡嗡作響的機器間。
在那個房間里,有一個小盒子裝有100個開關,它們被綁在分析儀上,這里是這個世界的另一番天地。
盒子里就是大腦中的大腦,開關和繼電器控制了機器,當機器旋轉時能夠使之重構,詹姆斯.格萊克寫道,是“由電力控制的電氣開關(循環的想法)”。
打開,關閉,香農日復一日地重復著這樣的工作。
當克勞德.香農按動開關時,會發生什么?
想象開關或繼電器就像吊橋一樣,電流由此通過:如果關閉它,開關就會允許電流傳遞到其他目的地;如果打開它,開關就會阻止通道中的電流運行。
它們的目的地可能是另一個繼電器,它會根據輸入端接收到的指令打開或者關閉開關,或者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它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小電燈。
這一切對于香農來說得心應手,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學,他進行了系統化學習,與其他電氣工程師一起盡職盡責地繪制電路圖。
串聯就是電流必須通過兩個開關才能被點亮;并聯就是電流可以自由通過任意一個或兩個開關。
這一區域,有數百個連接到微分分析儀上的開關邏輯箱、裝配線的電構件,以及控制整個國家電話網絡的成千上萬個繼電器系統。
這里的電路被設計為,只有當兩個開關被關上時,電流才能夠通行,不關開關,關1個或3個開關都不行;電路被繪制成分枝樹、對稱的Δ以及密集的網絡,其中涉及的全部電氣集合,香農都用心學習過。
香農在這個房間里與機器為伍,這個機器被設計為能夠自動化思考,在工作中,香農明白了另一種自動化思考的方式。
這種方式最終證明了,新一代計算機遠比模擬計算機更有影響力。
布爾定律
邏輯如何能像機器一樣呢?
20世紀初,一名邏輯學家這樣解釋道:“正如材料機器是為了節省力氣,符號演算機器則是為了節省智力。”
邏輯,和機器一樣,是一種使力量大眾化的工具,它具有足夠的精度和技能,無論是對于天才還是對于普通人來說,它都能使他們的能力倍增。
20世紀30年代,世界上只有少數人,能夠既精通“符號演算”或嚴格的數學邏輯,又擅長電路設計。
這比聽起來更令人乏味,在香農思索將二者進行融合之前,幾乎沒有人認為兩者之間有共同之處。
在密歇根大學,香農在哲學課上學到,任何邏輯陳述都可以通過符號和方程式來表達,這些方程式又能夠通過一系列簡單的、數學式的規則解決。
即使你不了解一句話的含義,也能夠判斷它的對錯。
將變化莫測的語言,以精確明晰的數學方式表述出來,起關鍵作用的人是19世紀的天才喬治·布爾——一名自學成才的英國數學家。
他的父親是一名鞋匠,在他16歲之前家里沒錢供他上學。布爾出版過一本實至名歸的書《思維的定律》(The Laws of Thought),證明了自己的天分。
布爾揭示的這些定理都建立在基本運算的基礎上,例如,和(And)、或(Or)、非(Not)和如果(If)。
假設我們指定所有倫敦人都有藍眼睛,且他們都是左撇子。將藍眼睛的固有屬性定義為x,將左撇子的固有屬性定義為y。
使用乘號代表“和”,加號代表“或”,撇號(代替減號)代表“非”。這一切的目的都是證明“真”或“假”。用1代表“真”,并用0代表“假”。
這些就是把邏輯學轉化為數學的基礎部分。所有倫敦人都有藍眼睛且是左撇子的假設,就可以表示為xy;所有倫敦人都有藍眼睛或是左撇子的假設,可以表示為x+y。
如果一個倫敦人既沒有藍眼睛又不是左撇子,命題就是假的;如果倫敦人有藍眼睛或是左撇子或兩者兼具,命題就是真的。
布爾認為,這一切都是有邏輯的。
x和y,以及我們所選擇的許多其他變量,要么真要么假,可以表示我們所想要表達的所有命題。同時,根據幾條規則,幾乎無須思考的簡單運算,我們能從中推導出可以被推導的一切。
這一切很有趣,近一個世紀以來,它都沒有實際用處。
鑒于哲學家的好奇心,它被教授給一代又一代的學生,其中有香農。
當他努力嘗試理解裝有數百個開關的小盒子時,布爾代數的部分內容影響了他——簡單的布爾代數與他試圖為布什解決極其復雜的方程式,交織在一起。
關,開;是,否;1,0。
符號洞察
當他在1937年夏,從麻省理工學院到紐約的時候,部分邏輯思想依舊影響著他。
香農在那里實習了一個暑假,他為貝爾實驗室科學家帶去了一種深刻的思索,它包括數學邏輯和非同一般的電路設計知識。
同時,他還帶去了令人困擾的想法,邏輯和電路兩者,通過一些基本方法,可以被連接在一起的。
他還將它們帶入電話公司的核心業務,該公司擁有最復雜的遠程電路網絡,他的工作就是運用數學使網絡平臺更穩定,且成本更低。
至關重要的是,在這段時間里,他著手記錄了他所洞察到的布什分析儀、貝爾網絡和布爾邏輯中的共性。
半個世紀后,香農試圖回想這頗具洞察力的一刻,并試圖解釋他是如何成為第一個理解這些開關意義的人。
他告訴一位記者:你提到的“開”或“關”,“是”或“否”其實并不重要,真正關鍵的是這兩種類型連在一起時,被邏輯中的“和”所描述出來,因而你會說這個“和”那個;而當兩者平行時,你會用“或”來描述......
當你操作繼電器的時候,會有一些觸頭被關閉,而有另一些仍然開著,因為“非”這個字與繼電器的這個方面相關......
布爾代數中的每個概念,在電路中都有相對應的物理表示。
一個打開的開關可以代表“真”,關閉它則為“假”,整個事件可以通過1和0來表示。
更重要的是,正如香農所指出的,布爾代數的邏輯運算符“和”“或”和“非”就像電路一樣,能夠被復制。
串聯連接即是“和”,因為電流必須連續通過兩個開關,除非兩者都通過,否則電流不能到達最終目的地;并聯則是“或”,電流可以通過任一或兩個開關。
從邏輯到符號再到電路的飛躍,香農依然欣喜地記得:“我覺得這比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有趣。”
他當時只是一個21歲的年輕人,他滿心激動于從開關盒子和繼電器中,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出來的東西。
他漫無目的地孕育出數年來最有價值的成果,最終在閣樓里塞滿筆記和半成品論文,并在格子紙上記錄下各種“頗具價值的問題”。
1937年秋,香農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向評委會演示了自己的碩士論文《繼電器和開關電路的符號分析》(A Symbolic Analysis of Relay and Switching Circuits),在第二年被發表在“Career-making Applause”雜志上。
在他的新體系中,香農寫下了他最枯燥的科學散文:
“任何電路都是由一組方程式表示的,方程式的每個部分,剛好對應了不同的繼電器和電路的開關。”
“這可能是本世紀最重要、最著名的一篇碩士論文。”哈佛大學霍華德·加德納教授說。
電路科學
在香農之后,設計電路不再僅憑直覺了,它變成了由方程式和便捷規則構成的科學。
將技術變為科學,將成為香農職業生涯的標志。
這一體系的一個亮點在于,一旦開關被簡化為符號,開關就不再重要了。這一符號體系,可被運用到任何媒介中,無論是笨重的開關,還是微觀的分子排列。
唯一需要的,就是能夠表達“是”或“否”的“邏輯”門,這個門可以是任意事物。
給像房間那么大的機械計算機的工作減負,其規則與真空管、晶體管、微芯片電路中的規則一樣,每步都是0和1的二進制邏輯。
香農說:“這很簡單。”
只有在發現了這種方法后,它才有幸能夠變得簡單。
香農論文中最本質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隱含在論文中,而沒有被言明,它的重要性是伴隨著時光流逝而日益清晰的。
當我們意識到,香農繼布爾之后,將“如果”用作條件符,才開始對它隱含的價值愈加明確。
人格化的進步在于,電路能夠做出決定,進行邏輯運算,大量電路能夠進行無數復雜的邏輯運算。
它們能夠解決邏輯難題,根據前提條件推導出結論,就像人類使用鉛筆推導出的那樣準確、值得信賴,甚至更快捷。
同年,英國數學家艾倫·圖靈發表一篇著名的、邁向機器智能的核心文章。他證明了,任何能被解決的數學問題,原則上都可以通過機器解決。
圖靈指出一種方法,計算機在工作的過程中能夠自行改編指令,以及設計出遠比當前許多發明更靈活的、能夠解決多種問題的機器。
香農則證明,任何有意義的邏輯表述,原則上都能夠使用機器判斷,任何電話配電盤中都能夠找到電路的邏輯可能性。他“追根溯源”地分析了,工程師和程序員,未來可能將邏輯輸入機器中。
傳記沃爾特·艾薩克森寫道,這一飛躍“是支撐一切數字計算機的基本概念”。
在香農發表論文后不到10年,微分分析儀就迅速過時,而被數字計算機所取代。
毫不夸張地說,數字計算機,比微分分析儀的速度快1000倍,能夠迅速地解答問題,并由數以千計的“全有或全無裝置”的邏輯門電路驅動。
現在,計算機的媒介是真空管,而非開關,這一設計直接基于香農所發現的成果。
結識圖靈
6年后(1943年),香農和圖靈在一間戰時科學家餐廳相遇,他們各自負責的項目,都是絕密的,兩人只能隱晦地談論。
他們都在鉆研同類型的前沿問題。
據香農回憶,在一起喝茶聊天時,“我們會談一些數學方面的話題”。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已有了思維機器這類想法。用香農的話來說就是,“創造能思考的電腦,以及可以用電腦做些什么,等等”。
香農說,他和圖靈面臨相同的困擾,因此,常常會談論這些問題。那時候,圖靈開始寫那篇很有名的論文——《計算機器與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兩人常常花費很長時間,討論一些概念,探討人類的大腦中有什么。
比如,大腦是如何構建的,是如何工作的,計算機能做什么,人類能不能用電腦完成大腦的工作,等等。
早期,兩人深陷于電腦計算的前景中,無比著迷于弈棋機的想法。
1942年,計算機剛剛出現,賓夕法尼亞大學有幾臺電子數值積分計算機(ENIAC),那是最早的計算機,它們運算速度慢、外形笨重、體積有幾個房間那么大,計算功能,和70年代一個10美元的小型計算器差不多。
“那時我們知道,如果能使計算機的價格更低廉、運作的時間更長,比如連續工作10分鐘以上,計算機就有無限潛力,這令我們激動不已。”
香農回憶說,當時,圖靈和他曾探討過,用計算機完全模擬人腦的可能性,且認為在不遠的將來,10年或15年后它就能實現。
香農骨子里是一個喜歡安靜的人。他很少參加科學界的活動,密友就更稀少了。他從不追隨名人參會,只應邀參加過少數會議。除電話外,他不喜歡其他任何聯絡方式。
在貝爾實驗室的短短幾個月里,香農能贏得圖靈的信任和友情,兩人對對方都評價頗高。
用香農的話來說,圖靈是“一個讓人印象十分深刻的人”。圖靈還曾邀請香農到家里做客,這對喜歡獨處的兩個人來說,都是一件稀罕事。
“二戰”后,圖靈和香農見了最后一次面。
1950年,香農去倫敦參加會議,抽時間去拜訪了圖靈,并參觀了他的實驗室。
香農回憶道:“圖靈的實驗室位于曼徹斯特大學,在去實驗室的路上......他想制作一臺用來下象棋的計算機......我對此同樣十分感興趣,那時他已經在編程了。他的實驗室里有一間辦公室,樓下放著一臺計算機,它就是現代計算機的雛形。”
兩人談論了圖靈在編程上所做的工作,10年過去了,香農依然記得圖靈的一項發明。
他問圖靈,在干什么,圖靈答,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得到電腦的反饋,以便了解電腦內部正在發生什么。
那時,他已經發明了這個神奇的指令。那些天,他們一直在研究各種指令,想從中找到最合適的一個。
總的來說,這是一次愉快的拜訪,是信息時代的兩個開創者在戰后的重聚,這也是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4年之后,圖靈被指控犯有“嚴重猥褻罪”,死于氰化物中毒。他的死亡被定性為自殺,至今這仍存在爭議。
那時,兩人剛剛開始打造自己的機器,已為計算機時代奠定了基礎。他們揭示了數字計算的可行性、記錄的可能性,以及一個又一個獨立的結論。

本文選編自《香農傳——從0到1開創信息時代》,吉米. 索尼和羅伯. 古德曼著,楊曄翻譯,中信出版社授權刊載,2023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