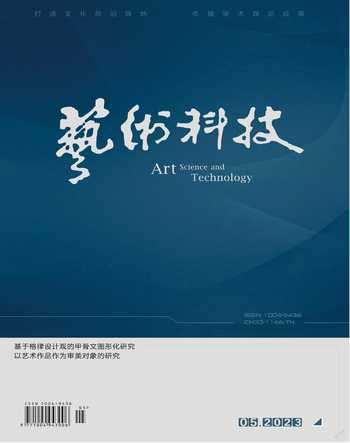藝術史中的詩畫關系探究
摘要:文章探究藝術史中詩畫的關系。詩畫關系一直都是中國繪畫史和文學史中廣受關注的問題,文學家們將詩看作中國藝術的核心,認為詩發揮著以情感人的重要作用,而畫家們則將筆墨之間構成的意境看作中華美學的重要方面,認為繪畫能夠包容更多形象化的內容,從而形成圓融整一的東方神韻。西方藝術史也是一樣,從古希臘時期的詩人西蒙尼德斯到英國畫家威廉·布萊克,諸多畫家、哲學家、理論家都曾對詩畫關系發表自己的見解。從他們的觀點中可以總結出藝術史中詩畫關系的兩個基本方向,即詩畫相異、詩畫相諧。梳理各種詩畫關系的論述可以看到,兩種藝術形式其實都是追求對美感的完美呈現,所以無論是哪一種形式,都要回到以情感人的本質上。選擇繪畫,就要填補時間上的空白,從而使欣賞者感動。選擇文字,就要填補空間上的空白,從而使欣賞者感動。因此,在填補空白的過程中產生的藝術內蘊的參差,才是使詩畫形成對比的根源。如今,視覺藝術常常被看作更占據發展優勢的藝術門類,無論是線上流媒體平臺還是短視頻平臺,都比傳統的文字平臺有著更大的流量和更廣泛的受眾群體。所以,用今天的審美標準再次回顧經典的詩畫關系問題,可以不再執著于孰高孰低的斗爭關系,而是嘗試找出二者之間的聯系,從而更好地發揮二者之所長。
關鍵詞:西方藝術史;詩畫相異;詩畫相諧
中圖分類號:I561.072;J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05-0-03
詩的要素是音韻與文字,畫的要素是線條和色彩。這二者之間在媒材上并無斗爭和比較關系,但是在審美的立場上,二者確實呈現出極強的交叉和關聯性。在中國美術史上,詩與畫在文人畫的蓬勃發展過程中握手言和,共同成就了意境相生相諧的文人畫境界,成為世界藝壇上獨屬于東方的文化奇葩。而在西方,詩與畫各自演繹著自己的魅力,往往并不像中國的文人畫一樣,有機會和諧地融于同一平面中。即便是在表現同一題材的過程中,以詩為代表的文學和以繪畫為代表的美術也呈現出不同的表達方式,進而從不同角度傳遞出美的力量。除此之外,詩與畫之間的關系在某些歷史時期是以斗爭的方式表現出來的,產生優劣之分,但也有一些美學家和藝術家看到了二者之間和諧共生的可能性。基于此,本文梳理詩畫相異以及詩畫相諧兩種觀點,探究各種觀點背后蘊藏的藝術規律,從而更好地理解西方藝術史中的詩畫關系問題。
1 詩畫相異
西方繪畫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史前時期的洞窟壁畫,內容往往基于其生活或宗教信仰,表達出原始先民對于未知力量的崇拜或恐懼以及對于生活本身的樸素愿望。文學的源頭則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詩歌和神話,也就是從古希臘開始,人們才有意識開始將詩歌和文學這兩種藝術形式聯系起來討論,這樣一種帶有審美屬性的藝術觀點也從側面說明了人類的藝術發展邁向了新的階段。如古希臘的一位詩人西蒙尼德斯就曾提出“畫是一種沒有聲音的詩,詩是一種帶有聲音的畫”,從二者的審美特性,即聲音介質出發,使詩與畫的美有可能被緊密地聯結。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藝術著作《詩學》中也曾提到,“有些人用顏色和姿態來制造形象,摹仿許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則用聲音來摹仿”。這是亞里士多德從摹仿論的角度出發對繪畫與詩歌兩種藝術形式關系的認識,暫時沒有直接涉及對于這兩種藝術形式高下的判別。
由此可見,古希臘時期對于詩歌和繪畫并不存在明顯的對兩者藝術價值高低的判斷,只是對其藝術特性進行相關分析。在隨后漫長的中世紀歲月里,西方的各個藝術門類都以傳遞宗教內容為主,以反映神學思想為旨歸,試圖以此種方式完成對上天的告解。而對于美術發展十分不利的反圣像運動,從宗教規范的角度打擊了形象創作。因此,這一時期以詩歌為代表的文學確實獲得了比美術更高的成就,如中世紀英雄史詩。因此,宗教因素的介入使得詩歌與繪畫的對比形成了力量懸殊的詩大于畫的形勢。
不過,隨著藝術逐漸脫離實用功能,以及藝術家地位逐漸上升,文藝復興時期的詩畫關系開始形成比較甚至是斗爭的趨勢。無論是繪畫還是詩歌,無數優秀的藝術作品在這個階段誕生,并成為后人膜拜的名作。
1.1 畫優于詩
文藝復興時期,繪畫藝術代表人物當屬人們熟知的“文藝復興三杰”,他們不單單從繪畫實踐方面發展自己,在理論創建方面也有所貢獻。其中,達·芬奇就從人的感官出發,認為繪畫直接服務于人的眼睛,而眼睛是人靈魂的窗戶,因此繪畫才是更能貼近靈魂的藝術。相比之下,詩歌只能通過次一級的聽覺與觀眾建立聯系,所以詩不如畫。
達·芬奇將人的感官區別成不同的層次,然后將視覺視為最高級別的感官,因此,服務于視覺的藝術自然就是最高級的藝術。在今天來看,這種觀點確實有其片面性,但是在達·芬奇生活的年代,藝術贊助人的肯定以及畫家地位的普遍提高確實會讓他對視覺藝術更有自信。在他的作品中也能夠體會到他對于繪畫技巧的純熟運用,以至于這些作品確實可以讓人們產生觸達心靈的直觀感受,而這種美的感受是絕對不遜色于任何詩歌的。
時間來到19世紀,法國畫壇上各種風格爭奇斗艷,其中法國浪漫主義繪畫的佼佼者德拉克洛瓦也認為畫是比詩更高級的藝術。他認為畫高于詩的理由是:“觀眾應該直接面對繪畫,這時不要求觀眾作任何努力。”這顯然是一種從審美的直接經驗出發的淺層理解,他只看到了在欣賞繪畫的過程中人們的目光與畫面的接觸,忽視了閱讀文字時,人腦對于所接收的文字信息也可以通過想象等手段加工,從而升華審美感受。但這確實也體現出這位浪漫主義畫家對于繪畫創作的熱情。此時,浪漫主義繪畫正在向新古典主義繪畫發難,新古典主義繪畫以典為尊、以正為雅的詩學特質所呈現出的刻板一面也可能間接引得這位激情澎湃的藝術家對于文學的輕視。他認為古典詩歌對于繪畫的進犯導致繪畫無法充分發揮自身形象性的優勢,以至于淪為文學的附庸,從而形成呆板僵化的新古典主義風格,這樣的看法也是有一定依據的。
1.2 詩優于畫
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雖然不能直接為欣賞者構建現成的畫面,但可以通過一系列的詞匯和邏輯來構建起可供欣賞者想象的新的世界,用語言推進情節,從而在時間維度上超越繪畫中定格的單一場景。啟蒙思想家狄德羅就是因此認為詩歌優于繪畫的。他認為畫家只能在平面的繪畫中完成一瞬間的景象,不能同時畫出兩個時刻的場景,同理也不能同時畫出兩種姿態。所以,繪畫無法達到詩歌一般的藝術效果,這一觀點與萊辛的觀點也是相近的。
萊辛的《拉奧孔》是西方討論詩畫關系問題最有影響的著述之一。“在傳統詩畫關系向現代語圖關系研究的轉化過程中,萊辛的觀點和方法也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1]他在書中還宣稱繪畫和詩歌屬于“姊妹藝術”,但是這對“姊妹”之間也存在競爭關系。他認為,詩用在時間中進行的語言表現動態的情,而畫則用在空間中展開圖像來表現動態的美。美是造型藝術的最高法律,而真是詩的最高法律,如果要詩等同于畫,那就只能削弱詩的表現能力。因此,可以判斷出在萊辛的觀念中,求真是藝術的最高目標,當求真的詩歌想要與求美的繪畫相比較時,詩歌只能屈尊。
黑格爾作為現代哲學的奠基人之一,對于美學中的諸多關鍵問題也有所闡發。黑格爾雖然也認可繪畫的藝術表現力,但是他也認為繪畫在抒情層面遜于詩歌和音樂,因為繪畫只能表現面容和姿勢。在《美學》中,黑格爾從藝術的內在精神出發,將詩放在比繪畫和音樂更高的維度,從而進一步抬高詩的地位。這也可以說是哲學探入藝術領域后,對藝術進行抽象化提煉的必然結果。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象”終歸于“道”,早已完成抽象任務的“詩”,確實在這個邏輯閉環里更勝一籌。
其實,無論是詩優于畫還是畫優于詩,都承認了這兩個藝術門類的最終目的是調動欣賞者的感情,但是在具體如何實現的層面產生了分歧。認為詩優于畫的一邊輕視了形象思維在審美中的作用,認為畫優于詩的一邊則輕視了抽象思維在審美中的作用。所以,從本質上來講,對于詩畫關系中對立一面的探討并非不可調和。
2 詩畫相諧
2.1 中國的詩畫相諧觀
詩畫相諧是指詩歌和繪畫能夠和諧統一或者擁有平等的審美地位。這在中國古代畫論中有不少的詮釋,如蘇軾所言“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清代葉燮也有言曰:“畫者,天地無聲之詩;詩者,天地無色之畫。”在中國古典哲學圓融并包的境界以及文人畫傳統的影響下,這一概念強調了詩與畫在抽象層面的完美統一。從藝術批評的角度出發,有學者指出:“優秀的中國詩畫本是一種‘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彼此包含的呈現狀態,可稱為‘本位即出位。”[2]也就是說,在人們欣賞一幅優秀的中國畫時,可以從畫面的布局感受到詩的結構,在筆墨的游走中感受到詩的意象,從而體會出詩一般的情味。而當欣賞一首優秀的中國詩時,可以在詩的結構中想象到畫面的鋪展,在詩的意象中想象到畫面的景色。言而總之,中國詩與中國畫在不同的語境中,往往存在著孰高孰低的論爭,但是從藝術鑒賞的具體實踐來看,人們的審美習慣往往將二者視為密不可分的兩個藝術門類,互參互鑒早已深入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
2.2 西方的詩畫相諧觀
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美學中相互聯系的范疇往往建立在對立之上,如悲劇和喜劇、美與丑等。因此,西方的詩畫相諧觀點也往往是建立在對立基礎之上的和諧。早在古羅馬時期,賀拉斯就曾提出過類似詩如畫的概念,原話是:“詩就像圖畫:有的要近看才看出它的美,有的要遠看。”單獨截取一句來看,賀拉斯確實表達了詩歌如同繪畫的觀點,但是如果聯系上下文就會發現,賀拉斯原意并不是指詩歌與繪畫有著相同的審美功能和審美地位,而是說欣賞詩歌可以采用欣賞繪畫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中去代入,從而發現不同的審美體驗,并沒有從二者的功能和地位出發闡述。但這確實也是詩歌與繪畫這兩個獨立藝術門類被相提并論的源頭。
與萊辛同一時期的溫克爾曼則從古典主義美學標準出發,認為藝術創作要重現古希臘藝術的榮光,展現出“高貴的單純,靜穆的偉大”。例如,雕像中拉奧孔以冷靜的面目忍受著肉體上的痛苦,就是對人內在力量的美的顯現。繪畫也要追求這般詩學的意蘊,而詩則要追求描繪真實。由此可見,溫克爾曼對于詩與畫的討論并非如萊辛一般,對詩與畫進行高下判別,而是想要調和二者的美學特性,取長補短,從而達到重塑古典美的目的。
歐洲18世紀主張詩畫相諧的代表人物是威廉·布萊克,他如米開朗基羅一樣,既是畫家,又是詩人。他與妻子合作,出版了一本名為《純真之歌》的詩畫集。其中的作品以豐富而瑰麗的形象詮釋了其詩歌作品中真實的一瞬。“布萊克的藝術直接將詩的文字圖像化,打斷文本敘述在時間上的連續性,使文字向著屬于空間藝術的圖像轉化。同時,他的圖像則具有流動性,蘊含強烈的敘事色彩。”[3]這種將詩歌與繪畫大膽結合于平面中的創作,體現了對前代“詩如畫”觀念的繼承,更在實踐層面超越了前代對于二者間融合的簡單想象,呈現出獨特的個人風格和深邃的意蘊,是詩畫融合觀念影響下的創作高峰。
無論是詩畫相異,還是詩畫相諧,其實各種爭論的最終目的都是用更恰當或者更美的方式表情達意,從而實現直指人心的目標。從這一點上來看,詩歌的優點是可以在時間的維度上,容納更多的要素,通過語言的蘊藉,形成整體的氛圍感。所以,是否能夠依賴文字充分調動起欣賞者的想象力就成了判斷詩歌藝術水平高低的關鍵。相比之下,繪畫則要依賴在空間的維度上,運用構圖、色彩、線條等方式,在短暫的一個景別中,將氛圍盡可能推向高潮,從而使欣賞者感受到詩一般的深長意味,以此使人動情。所以,詩畫孰高孰低以及具體詩畫如何融合,都需要在具體的作品內容中探討,因為一切關于形式的假設在內容面前都是無效的。
3 結語
詩畫關系問題作為文學與美術兩個學科的交叉部分,在研究的過程中必然面臨著以詩為尊或以畫為尊的立場問題,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已經認識到了藝術問題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這也使相關研究有了越來越強的應用層面的可能性。在圖像時代的今天,古今中外的各類詩歌創作都面臨著逐漸式微的窘境,而繪畫補充進入公共視野,從視覺上發揮與詩歌類似的審美功能,有了更廣闊的發展空間。那么,如何在圖像的傳播過程中更好地發揮出詩歌的情味,就成了未來可以探討的重點。
參考文獻:
[1] 李新.論《拉奧孔》詩畫關系在語圖關系史中的地位[J].西安石油大學學報,2021,30(5):107-112.
[2] 袁俊偉.“詩本位”并非“詩畫高低論”:中國古典詩畫關系再探[J].中國文藝評論,2023(2):85-94.
[3] 章燕.論布萊克詩畫合體藝術及其與西方“詩如畫”傳統的關系[J].外國文學,2016(6):36-45.
作者簡介:彭雨涵(1997—),女,黑龍江大慶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美術歷史與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