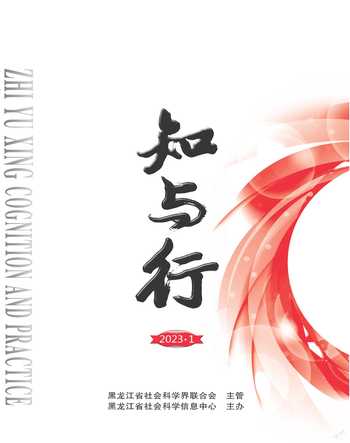人機關(guān)系的歷史唯物主義透視
史娜娜 王娜
[摘 要] 歷史唯物主義認(rèn)為,生產(chǎn)力是變革和推動社會歷史發(fā)展的根本力量,作為生產(chǎn)資料的機器則是其中一個關(guān)鍵性要素。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機器從最初的勞動工具發(fā)展演變而來,并隨著技術(shù)的進步逐漸由馬克思所論述的“工業(yè)機器”發(fā)展為計算機、物聯(lián)網(wǎng)等“信息機器”。到了智能時代,智能化、數(shù)字化和完全自動化成為機器發(fā)展的必然趨勢。而這些機器的不同形態(tài)在它們所處的經(jīng)濟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fā)揮的功能不盡相同,與人類的關(guān)系也在不斷改變,而人與機器關(guān)系所反映的實際上是人與人的關(guān)系。如今,人工智能機器所引發(fā)的社會結(jié)構(gòu)的改變、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及對“人之為人”標(biāo)準(zhǔn)的挑戰(zhàn)都使得人類社會處于巨大的不確定性和風(fēng)險當(dāng)中,并使得關(guān)于未來歷史創(chuàng)造者問題的爭論日漸突出。因此,我們必須正視已經(jīng)或者正在到來的新異化現(xiàn)象,堅持以人為中心的合倫理設(shè)計,構(gòu)建人機共同體,以此在智能社會中實現(xiàn)人真正意義上的解放。
[關(guān)鍵詞] 歷史唯物主義;人機關(guān)系;人工智能
[中圖分類號]B03 [文獻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2096-1308(2023)01-0024-08
2021年6月1日,清華大學(xué)計算機系知識工程實驗室迎來了中國首名原創(chuàng)虛擬學(xué)生“華智冰”,其外貌和聲音都依托于中國“悟道2.0”超大規(guī)模智能模型生成,不僅會作詩、繪畫,而且具有一定推理和情感交互能力,并隨著思維訓(xùn)練的進行,為“華智冰”一這類型的人工智能機器人最終像人類一樣具有感性和理性提供了可能。清華大學(xué)還為“華智冰”注冊了學(xué)生證和郵箱,使其具有了“學(xué)生”的權(quán)利。“華智冰”的誕生是我國智能應(yīng)用開發(fā)的成果,意味著通用人工智能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值得追問的是,“華智冰”能夠進入學(xué)校進行學(xué)習(xí)是否意味著智能機器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性?而適用于人類的權(quán)利與規(guī)范等是否同樣適用于智能機器人?隨著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不斷突破,人類對人工智能機器人的開發(fā)超越了對人類外形和一定能力的模仿,繼而追求對人類意識、情感陪伴等“人之為人”的內(nèi)在模仿,模糊了“人類”與“類人”的界限。人工智能是否能夠取代人成為社會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高度的擬人特質(zhì)使人工智能機器融入了人類的社會關(guān)系當(dāng)中,挑戰(zhàn)了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涉及人的本質(zhì)是否發(fā)生變化,以及機器是否可以作為人而存在等問題。因此,需要在歷史唯物主義視域下探究人機關(guān)系,厘清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實踐禁區(qū),在人機共生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彰顯人的主體性地位。
一、從勞動工具到工業(yè)機器:人的本質(zhì)力量對象化與異化
1.作為人類本質(zhì)力量的對象化的勞動工具
生產(chǎn)工具作為人的外化功能體,在人類直接生活的物質(zhì)生產(chǎn)當(dāng)中具有關(guān)鍵作用,標(biāo)志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程度。在現(xiàn)實生產(chǎn)中,勞動者通過勞動資料將勞動作用于勞動對象之上,以此來獲取生存資料。這是馬克思所提出的勞動過程,包括了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而在勞動資料當(dāng)中起決定作用的就是勞動工具。馬克思提出,“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chǎn)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chǎn)物質(zhì)生活本身。”[1]31人對物質(zhì)資源的需要的滿足只靠有限的自然供給是難以維系的,只有通過實踐來開發(fā)和利用自然達(dá)到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而“勞動是從制造工具開始的”[2]。人類通過生產(chǎn)工具這一人造之物擺脫了蒙昧狀態(tài),區(qū)別于動物界,向擺脫自然的限制和壓迫邁出了第一步。
生產(chǎn)工具的發(fā)展程度影響著人類的主觀思維轉(zhuǎn)化為客觀實踐的現(xiàn)實條件和程度。在資本尚未介入人與勞動工具的關(guān)系之前,生產(chǎn)工具表現(xiàn)為手工工具的形式,經(jīng)歷了從石器工具、金屬工具等形態(tài)的一般轉(zhuǎn)換,從而完成了對人類勞動的簡單部分代替。人通過勞動工具這一中介來延長人自身的主體性的發(fā)揮,將自己的本質(zhì)力量外化,創(chuàng)造性地改變自然以不斷滿足人的需要。從本質(zhì)上來說,這時的勞動工具與人是簡單的應(yīng)用與被應(yīng)用的關(guān)系,人作為主體,絕對支配工具,勞動者的技術(shù)能力的專業(yè)性和創(chuàng)造性在價值生產(chǎn)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勞動工具在生產(chǎn)過程中只擔(dān)任價值轉(zhuǎn)移的角色,形式上將人的勞動能力外化。
2.資本邏輯支配下人對工業(yè)機器的依賴及其異化
工業(yè)革命時期,生產(chǎn)工具出現(xiàn)了本質(zhì)上深刻的形態(tài)變革和功能角色的翻轉(zhuǎn),表現(xiàn)為機器形式。機器與人相結(jié)合,在社會生產(chǎn)方式變革中實現(xiàn)了其本身的經(jīng)濟范疇意義。“手工磨產(chǎn)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chǎn)生的是工業(yè)資本家為首的社會。”[3]144生產(chǎn)力對于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決定性作用,作為生產(chǎn)資料核心要素和生產(chǎn)技術(shù)物化形式的機器,不僅代表著技術(shù)發(fā)展的水平,更是促進生產(chǎn)方式和人的存在方式變革的革命力量。然而,在私有制條件下,資本邏輯主導(dǎo)并貫穿整個生產(chǎn)過程,機器淪為資產(chǎn)階級實現(xiàn)資本增殖的工具。隨著社會生產(chǎn)力的迅速發(fā)展,資本主義大生產(chǎn)的社會化程度也隨之提高,生產(chǎn)資料和勞動產(chǎn)品本應(yīng)該由勞動者共同所有,卻集中在少數(shù)資本家手中,導(dǎo)致生產(chǎn)社會化和生產(chǎn)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深埋于資本主義社會當(dāng)中。在整個勞動過程中,勞動者使用歸資本家所有的生產(chǎn)工具來生產(chǎn)產(chǎn)品,但“他給予對象的生命作為敵對的和異己的東西同他相對抗”[4]92。也就是說,機器使人依賴于物的發(fā)展,無法擺脫物化對人的控制。這就導(dǎo)致人與其自己本身的勞動相異化,人自由自覺的勞動在為他人生產(chǎn)的過程中變?yōu)楸黄刃缘臒o意識勞動,人的存在方式也由人對自然的能動性改造轉(zhuǎn)變成人對資本和技術(shù)的依附。
分工的精細(xì)化使勞動者的異化程度不斷加深。在工廠中,“工人要服從機器的連續(xù)的、劃一的運動,這早已造成了最嚴(yán)格的紀(jì)律”。[5]單個的有意識的工人被分布在作為總體分配物質(zhì)資料生產(chǎn)的機器體系的不同環(huán)節(jié)上,屈從于機械規(guī)律和工廠嚴(yán)格的制度,作為機器體系的“器官”進行勞動。在馬克思對人的界定當(dāng)中,他首先認(rèn)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qū)別開來”[4]96。勞動本應(yīng)是人的本質(zhì)特性的展現(xiàn),是自由的創(chuàng)造性勞動。但這種“流水線工作”使得工人的勞動性質(zhì)趨于同質(zhì)化發(fā)展,繼而工人生產(chǎn)出來的勞動產(chǎn)品也不再是對人類主體勞動能力的本質(zhì)反映,更多的只是反映出機器體系的生產(chǎn)效率,勞動者淪為機器的附庸。馬克思認(rèn)為,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起決定性作用,正是資本家牢牢把控著機器這一客觀物質(zhì)性力量,資本邏輯下的機械機制才能夠成為社會權(quán)威。“對技術(shù)的服從成了對統(tǒng)治本身的服從;形式的技術(shù)理性轉(zhuǎn)變成了物質(zhì)的政治合理性。”[6]機器作為具有意識形態(tài)特征的新型社會控制工具,使得人類在工業(yè)機器時代處于技術(shù)理性統(tǒng)治的社會之中。工人的自我意識和實踐在這種異化勞動中逐漸單向度化,造成勞動者與自己自由的類本質(zhì)的“異化”。
從另一個角度看,機器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自然對人類的約束,增加了人們消費形式的多樣性,這些都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提供了可能。“隨著新生產(chǎn)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chǎn)方式,隨著生產(chǎn)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guān)系。”[3]144工業(yè)機器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的應(yīng)用打破了傳統(tǒng)手工業(yè)以地緣為基礎(chǔ)的原始紐帶,社會結(jié)合出現(xiàn)新的形式,人們在生產(chǎn)基礎(chǔ)上建立起普遍交往。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本性強迫工人將機器節(jié)省出的自由時間轉(zhuǎn)化為“合理”的剩余勞動時間,來創(chuàng)造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更多的物質(zhì)資料并沒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狀況,受機器排擠的工人“游離”出生活資料,而依靠必要生活資料生存的工人也處在隨時被替換的環(huán)境當(dāng)中,生活和就業(yè)無法得到保障。“機器資本化”促使工業(yè)機器從原本只具有工具屬性和轉(zhuǎn)移固定價值功能的技術(shù)產(chǎn)物顛倒為一種操控勞動者的力量,從而導(dǎo)致人的主體性地位被削弱。
二、信息機器對社會生產(chǎn)與生活的塑造
1.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對人的生存空間和時間的重塑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工業(yè)時代的人機關(guān)系之間的嚴(yán)重沖突狀態(tài)隨著媒介新技術(shù)的產(chǎn)生和革新發(fā)生了新的變化,呈現(xiàn)出人機關(guān)系的新形式,機器對人影響由現(xiàn)實空間延伸至了虛擬空間。“如果動力化機器構(gòu)成了技術(shù)機器的第二個時代,控制論的及信息的機器則形成了第三時代。”[7]第三次浪潮當(dāng)中,作為人的本質(zhì)力量外化載體的機器的研發(fā)方向發(fā)生了新的轉(zhuǎn)變:機器的開發(fā)和應(yīng)用從人們的生產(chǎn)領(lǐng)域逐漸滲透和覆蓋到生活領(lǐng)域,以計算機和媒介工具等為主的“信息機器”則成為滿足人們消費欲望的工具。在信息時代,信息網(wǎng)絡(luò)空間的飛速擴展處于一種新的現(xiàn)代知識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即網(wǎng)絡(luò)結(jié)構(gòu)當(dāng)中,給我們在信息獲取和披露、公開評論、消費者維權(quán)等方面都帶來了新的權(quán)力賦予,提升了人類個體的自由程度。網(wǎng)絡(luò)交往“去空間化”的特質(zhì)打破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社會交往的空間阻隔,顛覆了人類主體的交往形式,為主體提供了平等發(fā)聲和無門檻參與的“公共廣場”。相比于工業(yè)時代,信息時代的人的存在方式開始呈現(xiàn)出獨立的狀態(tài),現(xiàn)實的人能夠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自由隨意地開展主觀的精神生產(chǎn),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對“物的依賴”,但同時又沉淪于信息機器所構(gòu)建的網(wǎng)絡(luò)社會當(dāng)中。
網(wǎng)絡(luò)空間是擴展人類社會交往形式的新路徑。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zhì)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實際上,它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1]5人具有社會屬性即人是類存在物,在社會實踐中必然會形成不以其意志為轉(zhuǎn)移的社會關(guān)系,包括生產(chǎn)關(guān)系、政治關(guān)系等,并且,人的社會關(guān)系是具體的、歷史的,會隨著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發(fā)生變化,從而造成個體的差異。計算機的應(yīng)用使人的實踐活動拓展至虛擬空間,人在現(xiàn)實與虛擬的社會關(guān)系的構(gòu)建中不斷完善自身的社會屬性和社會身份。計算機為人類的存在開辟了新的非自然維度的信息空間,延伸了人類存在的時間和空間屬性,但網(wǎng)絡(luò)虛擬空間的擬現(xiàn)實性會導(dǎo)致人的時間感的相對化和內(nèi)在化,削弱了人們對于現(xiàn)實的真實感受,從而在虛擬空間中沉淪,喪失人的現(xiàn)實存在感。在信息社會,人在網(wǎng)絡(luò)空間建立了虛擬的信息化身份,獲得匿名的非直接表象,而匿名隱藏現(xiàn)實主體真實社會身份的虛擬角色以符號化方式建構(gòu)了一個“社會空間”,按照網(wǎng)絡(luò)設(shè)定賦予虛擬空間中的自我以獨特的情感與行為意義,區(qū)別于現(xiàn)實中的社會關(guān)系。虛擬身份和現(xiàn)實身份所導(dǎo)致的多元自我并沒有為自我認(rèn)同帶來太多積極影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導(dǎo)致自我分裂,喪失自主性。信息消費者在網(wǎng)絡(luò)空間中被直指意向性的信息所誘惑和操控,使得人與信息機器進一步異化,反因信息而焦慮,導(dǎo)致自我控制能力的喪失。實質(zhì)上,計算機在人機關(guān)系中并不只是簡單的工具,它超越了對人們身體肢體的延伸,而將意識延伸至另一個“社會”當(dāng)中。人通過計算機所構(gòu)成的界面體驗到虛擬空間交流和日常交往互相交織的狀態(tài),這種交互性使機器成為與人共生的合作者。
2.移動終端: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和大數(shù)據(jù)對人的身份認(rèn)同、交往方式和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的重構(gòu)
不同于傳統(tǒng)工業(yè)機器,以信息機器為媒介的互聯(lián)網(wǎng)體系構(gòu)建了一系列新經(jīng)濟業(yè)態(tài),通過大數(shù)據(jù)技術(shù)逐漸實現(xiàn)了普遍性的社會化交流與共享,推動生產(chǎn)力發(fā)展實現(xiàn)了質(zhì)的飛躍。生產(chǎn)社會化日益顯現(xiàn),推動人們的生產(chǎn)方式和社會交往形式發(fā)生變革,移動終端的出現(xiàn)打破了現(xiàn)實與虛擬空間涇渭分明的分界線,時空格局呈現(xiàn)出線上與線下高度融合的狀態(tài)。信息時代這一背景下特定出現(xiàn)的大數(shù)據(jù)作為新型生產(chǎn)資料普遍出現(xiàn)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由此人們在虛擬空間中所創(chuàng)造的身份逐漸“實名化”,這有利于人們實現(xiàn)多元自我的統(tǒng)一。馬克思強調(diào),人是類存在物,而虛擬空間中人的生存狀態(tài)也與人類在現(xiàn)實世界的“類存在”相對應(yīng),呈現(xiàn)出“群體虛擬生存”的生存形態(tài)。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造就的社會交往形態(tài)既包含著基于現(xiàn)實交往的社會關(guān)系,又孕育著新的社交生態(tài),出現(xiàn)了基于網(wǎng)絡(luò)的社會交往形式。人們通過“身份認(rèn)同”和“價值認(rèn)同”組成一個個網(wǎng)絡(luò)圈層,以社群化的狀態(tài)存在于虛擬空間中,實現(xiàn)了從信息互動到滲透后的利益共享,出現(xiàn)了以實現(xiàn)商業(yè)價值轉(zhuǎn)化為目的的社群經(jīng)濟。這種基于網(wǎng)絡(luò)人際交往建立起來的網(wǎng)絡(luò)社群以“人—移動終端—人”的間接互動方式為特征,不同于傳統(tǒng)意義上基于地緣和血緣的“人—人”的直接交往模式,而是通過跨時空的多人在線溝通滿足了人們信息共享、情感交流和利益互惠的社會需要,打破了線下信息傳遞的形式障礙。人類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所構(gòu)建的社會關(guān)系把“處于一定社會關(guān)系當(dāng)中的人”這一關(guān)于人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延伸到“處于一定現(xiàn)實和虛擬空間中的社會關(guān)系中的人”,但網(wǎng)絡(luò)社群作為“類群體”,以觀念認(rèn)同作為入群標(biāo)準(zhǔn),極容易形成“知識繭房”,將自己孤立起來。
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的發(fā)展,每個人都有自身特有的“地址”,人與人、人與物之間將實現(xiàn)互聯(lián)互通。但隨著大數(shù)據(jù)算法在人們生產(chǎn)和生活領(lǐng)域的深入應(yīng)用,每個人的生活逐漸公開化與透明化,但信息隱私權(quán)得不到有效保障,人的精神話語面臨被信息機器操控的風(fēng)險。“網(wǎng)絡(luò)仍然是一種基于各種資源的不平等權(quán)利結(jié)構(gòu),是一種具有強大的控制性的技術(shù)社會體系。”[8]在數(shù)字鴻溝和信息壁壘依舊存在的背景下,諸多算法決策正在發(fā)展為“算法權(quán)力”,技術(shù)理性正在變革著人的觀念世界。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開放性的實質(zhì),對人的行為的數(shù)據(jù)追蹤和分析可以看出個人的思想傾向、愛好和興趣,從而為精準(zhǔn)定位個人提供了基礎(chǔ)。“技術(shù)統(tǒng)治論的命題作為隱形意識形態(tài),甚至可以滲透到非政治化的廣大居民的意識中,并且可以使合法的力量得到發(fā)展。”[9]6信息時代的資本對虛擬網(wǎng)絡(luò)這一非實體機器的把控更加嚴(yán)格,通過數(shù)據(jù)追蹤和數(shù)據(jù)圖繪等手段向個人用戶精準(zhǔn)推送相關(guān)信息,其意識形態(tài)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用戶個人的思想和行為。這種“算法化”能夠預(yù)判人們的政治傾向,干擾其客觀地進行價值評判,從而進一步實現(xiàn)資本的更大獲利。也就是說,在某些決策方面,人們自認(rèn)為是自身作出的自主選擇,而事實上他們的想法已經(jīng)被算法預(yù)測,成了被數(shù)據(jù)所穿透的工具人。實質(zhì)上,基于信息機器構(gòu)建起來的龐大網(wǎng)絡(luò)體系促使人的異化從工業(yè)時代的勞動異化轉(zhuǎn)而變?yōu)槌潭雀畹臄?shù)字異化,人機關(guān)系出現(xiàn)了新的異化形態(tài)。
三、人工智能與人類未來
在大數(shù)據(jù)、云計算等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推動下,人工智能機器具有了機器學(xué)習(xí)與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相結(jié)合而產(chǎn)生的深度學(xué)習(xí)的能力,智能化程度不斷提高,為人的自由解放帶來了機遇,但同時也使人類這一歷史主體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智能機器延續(xù)并加深了信息時代的機器對人所造成的技術(shù)異化,包括出現(xiàn)技術(shù)性失業(yè)現(xiàn)象和對人的主體地位的沖擊等問題,而這些問題需要在社會生產(chǎn)方式的變革當(dāng)中得以解決。馬克思強調(diào),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是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自然歷史過程”,而按不同標(biāo)準(zhǔn)所劃分出的技術(shù)社會形態(tài)與經(jīng)濟社會形態(tài)之間具有關(guān)聯(lián)性。也就是說,以智能機器為依托的智能社會將為馬克思所設(shè)想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提供具體的實現(xiàn)條件。
1.人工智能機器人對“人的界定”的沖擊
“華智冰”“微軟小冰”等人形智能機器人的出現(xiàn)和應(yīng)用沖擊了傳統(tǒng)關(guān)于人機之間界限的認(rèn)知,對“人是什么”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提出了挑戰(zhàn)。在智能時代,智能機器人不僅越來越像人,而且逐漸以各類身份進入人們的社交圈,成為人類的工作伙伴和生活助手,甚至充當(dāng)伴侶這種具有情感陪伴的角色,這足以說明智能機器人能夠以特定的社會角色與人形成一定的人際關(guān)系。在這樣的人機交往過程中,智能機器人不再只是作為單純的傳播中介,而是被當(dāng)作了“平等”的交流對象,導(dǎo)致人與人工智能所建立的社會交往已經(jīng)部分取代人與人之間所建立的社會交往關(guān)系。因此,人工智能機器處于人類一定的社會關(guān)系中,具有了擬主體性和自主性的特征,逐漸超越客體-主體的關(guān)系,向主體-主體的關(guān)系靠攏。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作為主體的人與智能機器間的原則界限,“這些改變觸及的會是人類的本質(zhì),就連 ‘人的定義都有可能從此不同”[10]。不可否認(rèn)的是,在智能時代,人機關(guān)系的二元對立的局面不再存在,有機融合成了人機未來的發(fā)展趨勢。但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來看,人是作為“社會人”而存在的,社會性是人的意識所固有的本質(zhì)屬性。而目前智能機器從根本上來說沒有真正具備自立、自主、自覺的社會活動,難以成為獨立的具有行為后果意識、自律意識和社會責(zé)任感的社會主體。并且“人是知情意行的統(tǒng)一”[11],人的邏輯判斷等理性思維是可計算的,但人的感性思維至少在相當(dāng)一段時期內(nèi)還無法轉(zhuǎn)換為數(shù)據(jù)信息。
可以明確的是,現(xiàn)階段的人工智能的勞動與人類的實踐還是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人工智能機器雖然能夠獨立執(zhí)行人類的指示,但其并沒有從滿足自我需求出發(fā),“自主行為”與“自由意志”是相差甚遠(yuǎn)的,其實質(zhì)還是缺乏自我意識的機械行為。并且研發(fā)和極少數(shù)操控人工智能機器的活動仍然是人的活勞動,智能機器對人類專屬技能的替代和實踐自主性的增強的發(fā)展最終還是為人這一主體服務(wù)。歷史唯物主義認(rèn)為,實踐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區(qū)別于動物和其他一切生命的根本特征。人的實踐具有目的性、創(chuàng)造性和自覺性等特征。而人工智能機器無論是機械模擬還是情感模擬,從本質(zhì)上都是對人類智能的模擬,是人類智能外化的產(chǎn)物。這種模擬是無意識的機械式活動,和人類有意識的認(rèn)識事物完全不同,不存在主觀能動性。并且人工智能對外界的反應(yīng)是被動的,對問題的解決是機械的,解決問題的目的性來源于人本身。雖然智能機器已經(jīng)融入了人類社會,突破了原來的那種自動化形象,具備了相當(dāng)程度的自主性,但這種自主性都是在人為之設(shè)計的程序和應(yīng)用設(shè)備中進行的。也就是說,智能機器都只是提升人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水平,不能實現(xiàn)對人的各個方面的代替,而它的不斷更新也只會按照人機交互的趨勢來發(fā)展。
2.人工智能機器的發(fā)展為解放生產(chǎn)力奠定物質(zhì)基礎(chǔ)
“目前的人工智所創(chuàng)造的機器智能在合成智能和人造勞動者兩個方面出現(xiàn)了突破,并向自主智能體發(fā)展。”[9]6包括工業(yè)機器人和家用機器人等在內(nèi)的人造勞動者的產(chǎn)生和應(yīng)用相比較于之前的普通機器,能夠更加精準(zhǔn)地將不同領(lǐng)域中的人們從繁瑣和枯燥的重復(fù)性工作中解放出來。并且,由于人類工作的雇傭成本和培訓(xùn)成本遠(yuǎn)遠(yuǎn)高于制造智能機器的生產(chǎn)成本,促使智能機器代替人類勞動者包攬基礎(chǔ)性工作更加合理。人類勞動者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為生存而進行的傳統(tǒng)勞動,從而為自身從事“使人成為人”的自由勞動打下基礎(chǔ),通過新的分工方式來抵制資本邏輯的消極屬性,但人造工作者對人類專業(yè)技能的取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技術(shù)性失業(yè)現(xiàn)象。智能機器的發(fā)展和改進促進了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升級、智能產(chǎn)業(yè)崛起,創(chuàng)造出更多新的職業(yè)和崗位,而這一創(chuàng)新紅利緩解了技術(shù)性失業(yè)、收入差距過大導(dǎo)致的社會不平等問題。但新產(chǎn)生出的職業(yè)和職位的數(shù)量并不能完全對等于被淘汰的舊職業(yè)崗位,而且毋庸置疑的是,這些新職業(yè)和崗位將提出更高的關(guān)于知識和技能方面的要求。但正如在工業(yè)革命中因機器生產(chǎn)而失業(yè)的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和手工業(yè)勞動力,最后在工業(yè)生產(chǎn)的其他領(lǐng)域也重新找到了新的就業(yè)機會。人類經(jīng)歷的三次科技革命都會引起失業(yè)率的上升,但都符合就業(yè)破壞—再創(chuàng)造的規(guī)律。智能機器的發(fā)展和改進促進了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升級、智能產(chǎn)業(yè)崛起,創(chuàng)造出更多新的職業(yè)和崗位,而這一創(chuàng)新紅利緩解了技術(shù)性失業(yè)、收入差距過大導(dǎo)致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并且智能社會特定環(huán)境下所激發(fā)出的新型智能服務(wù)職業(yè),如微商、網(wǎng)絡(luò)主播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削弱社會的就業(yè)風(fēng)險。
相較于以土地、廠房等實體要素為主的傳統(tǒng)經(jīng)濟形態(tài),智能時代催生下的數(shù)字經(jīng)濟形態(tài)創(chuàng)造的財富總量更多,將人工智能技術(shù)貫穿于生產(chǎn)、交換、分配和消費的社會生產(chǎn)全過程,對社會財富總量的貢獻越來越大。馬克思曾將工業(yè)機器納入到當(dāng)時的經(jīng)濟領(lǐng)域中考察,而在當(dāng)代社會,智能機器人、智能化生產(chǎn)系統(tǒng)等生產(chǎn)工具的廣泛應(yīng)用推動社會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和產(chǎn)業(yè)鏈不斷升級,進而催生出“智能經(jīng)濟”,智能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崛起成為新的拉動經(jīng)濟增長的新興產(chǎn)業(yè)。“智能勞動”作為智能經(jīng)濟產(chǎn)業(yè)化下的新型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手段和過程都區(qū)別于傳統(tǒng)勞動:相較于傳統(tǒng)大工廠生產(chǎn),科技要素在價值創(chuàng)造和形成過程中越來越處于主導(dǎo)地位,不變資本的比例不斷提高。智能社會所出現(xiàn)和發(fā)展起來的無人工廠生產(chǎn)體系當(dāng)中的價值創(chuàng)造能夠獨立自主地完成生產(chǎn)活動,但也要求更加嚴(yán)格的協(xié)作才能完成,促使生產(chǎn)過程更加需要智能勞動者的主導(dǎo)與參與。并且由于人工智能機器自動化的優(yōu)勢,智能機器創(chuàng)造價值更加快速和高效,創(chuàng)造價值的途徑更加多樣,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解放了人類勞動。基于此,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空前提高,人們所需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日益豐富,人類正在邁入一個“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dá)、物質(zhì)財富極大豐富”的社會。而在馬克思的按個人能力發(fā)展劃分出的社會三階段理論當(dāng)中,個人只有處于社會財富極大豐富的最高社會形態(tài)中,才能發(fā)揮出“個人全面發(fā)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chǎn)能力”[12]。也就是說,“個人的全面發(fā)展”以共同的社會財富為前提,超越對物的依賴。人工智能機器所創(chuàng)造的巨大生產(chǎn)力為人實現(xiàn)全面發(fā)展提供了物質(zhì)保障。
3.智能機器的發(fā)展帶來社會關(guān)系的變革
人工智能技術(shù)作為知識要素參與分配,與有形的實體性生產(chǎn)資料相結(jié)合,創(chuàng)造了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促使社會分配方式更加公平、更加豐富,按照生產(chǎn)要素分配的形式將成為發(fā)展趨勢。智能機器參與進社會分配過程中,能夠更好地解決現(xiàn)有矛盾,比如醫(yī)療、教育等方面的人工智能機器應(yīng)用于解決某些落后地區(qū)資源不均衡的問題,工業(yè)機器人代替人類進行繁重勞動等,使人的基本需要能夠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得以滿足。同時,智能機器能夠自主發(fā)現(xiàn)、創(chuàng)造并滿足人們?nèi)找嬖鲩L的多樣化和個性化需要,以情感陪伴為目的的機器人和虛擬現(xiàn)實(VR)將豐富人們的生命體驗,智能產(chǎn)業(yè)提供的服務(wù)在標(biāo)準(zhǔn)化生產(chǎn)模式下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個人需求。因此,人工智能為人類社會實現(xiàn)按需分配提供了物質(zhì)保障。
智能機器發(fā)展帶來的社會職業(yè)結(jié)構(gòu)的改變和生產(chǎn)力的極大提高也使得傳統(tǒng)社會分工的形式發(fā)生變更,社會所有制形式朝著更加合理的方向發(fā)展。馬克思強調(diào),“只要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發(fā)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qū)使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1]37。這種分工方式使腦力和體力勞動形成了對立,阻礙了人全面的發(fā)展。而“分工的階段依賴于當(dāng)時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水平”,在智能機器奠定物質(zhì)保障的基礎(chǔ)上,人工智能自動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不斷提升縮小了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距,降低了以體力勞動為主的職業(yè)在社會職業(yè)結(jié)構(gòu)中所占的比例。而在消滅舊的分工形式的過程中,新的分工自然又會出現(xiàn)。人工智能催生的新興行業(yè)和崗位對精神性勞動的需求大大增加,大量重復(fù)性的簡單勞動方式被取代,擁有知識、技術(shù)等生產(chǎn)資料的勞動者逐漸占據(jù)勞動中的主導(dǎo)地位,獲得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自主性。在這個階段中,勞動者才可以從復(fù)雜的勞動環(huán)境中解放出來,并在豐富的勞動種類中選擇其樂意從事的行業(yè),從而克服資本邏輯的消極屬性,最大程度上增加絕大多數(shù)人的自由可支配時間,這就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自由的人實現(xiàn)的可能。并且,舊式分工形式的消失會進一步縮小社會階層分化所固有的矛盾,從而使生產(chǎn)資料合理歸人們所有成為可能。而“分工產(chǎn)生了所有制”,基于人們興趣愛好而產(chǎn)生的社會分工推動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形式朝著公有制方向發(fā)展,同樣推動社會財富趨于按需分配。
4.基于人機共生的自由共同體的構(gòu)建
馬克思將科學(xué)技術(shù)這一生產(chǎn)力發(fā)展當(dāng)中的革命力量作為劃分社會階段的標(biāo)準(zhǔn),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可劃分為漁獵社會、農(nóng)業(yè)社會、工業(yè)社會和智能社會,從低級向高級技術(shù)社會形態(tài)不斷發(fā)展。而這由此對應(yīng)的就是以生產(chǎn)方式為基礎(chǔ)、以生產(chǎn)關(guān)系特別是生產(chǎn)資料所有制形式為依據(jù)劃分出的經(jīng)濟社會形態(tài),“現(xiàn)實的人”在實踐活動中不斷創(chuàng)造歷史,并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共同體,從“自然共同體”到異化的“虛幻共同體”,最終發(fā)展為“自由人聯(lián)合體”。“隨著新生產(chǎn)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chǎn)方式,隨著生產(chǎn)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guān)系。”[3]144在一定社會階段的生產(chǎn)形式當(dāng)中,生產(chǎn)力不斷發(fā)展進而達(dá)到頂峰,而后生產(chǎn)關(guān)系便會阻礙生產(chǎn)力發(fā)展,將被適應(yīng)于先進生產(chǎn)力的新生產(chǎn)形式所代替。“共同體形式……按照生產(chǎn)力來改變。”[13]隨著人工智能社會的到來,智能機器在人類社會生產(chǎn)和生活中廣泛應(yīng)用,促使人類向著“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dá)、物質(zhì)財富極大豐富”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這一真正自由共同體邁進,為人成為真正自由的人提供了現(xiàn)實途徑。
人工智能促使人類更有尊嚴(yán)、更加自由地參與勞動,同樣為人的自由發(fā)展提供了可能性。馬克思認(rèn)為,自由時間是人實現(xiàn)自由發(fā)展的前提,只有擁有自由時間,人才可以有多種選擇、根據(jù)自身興趣從事各種活動,才可以自由全面地發(fā)展、展示自己的聰明才智,最終實現(xiàn)人的解放。勞動實踐是人發(fā)展的本質(zhì)需要,促進人的自我實現(xiàn)和提升。但長期以來,人們?yōu)榱嘶旧娑黄鹊貏趧樱坏貌槐肮ァ⒌腿滤牡乇毁Y本家所剝削,這種勞動是迫不得已的屈服,是對人的勞動異化。但是,當(dāng)人工智能機器應(yīng)用促使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達(dá)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時,在相同條件下智能機器能夠創(chuàng)造更多的物質(zhì)財富滿足更多人的物質(zhì)需求,由于對物的依賴的擺脫,雇傭勞動消失,勞動的異化和人的異化消除。個體的自由勞動就成了可能,大部分人將獲得勞動自主性。并且,人工智能機對人類繁重勞動的代替,使人類所耗費的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人類不再作為機器附庸受制于分工,有更多的屬于自己的自由時間來從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等精神性活動,真正從私有制的資本邏輯中解放出來。勞動將成為個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不僅僅是維持生命的手段,成為各個人自己提出的目的本身。人工智能機器帶來的各方面的變革都為共產(chǎn)主義的實現(xiàn)奠定堅實的基礎(chǔ),未來人類會因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將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更加接近自由共同體。
[參 考 文 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4.
[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0.
[6] ?馬爾庫塞.現(xiàn)代文明與人的困境——馬爾庫塞文集[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8:104.
[7] ?杰瑞·卡普蘭.人工智能時代[M].李盼,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6.
[8] ?段偉文.信息文明的倫理基礎(ch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45.
[9]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技術(shù)與科學(xué)[M].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xué)林出版社,1999:63.
[10] ?尤瓦爾·赫拉利.人類簡史:從動物到上帝[M].林俊宇,譯.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390.
[11] ?成素梅.人工智能的哲學(xué)問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66.
[1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0
[13]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2-726.
〔責(zé)任編輯:杜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