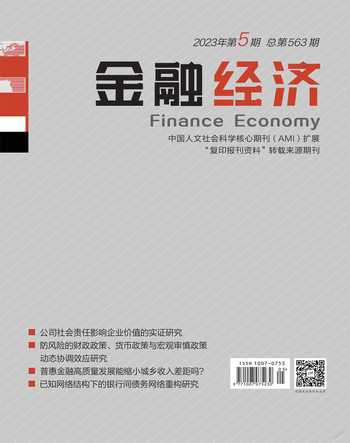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嗎?
羅荷花 姚璇



摘要:本文基于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數據,實證檢驗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且能通過提高農村人力資本與就業水平發揮作用。異質性檢驗發現,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具有地區異質性,表現為在東部地區能夠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在中西部地區沒有顯著影響。門檻效應檢驗發現,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城鎮化的單一門檻。最后,本文提出要提升普惠金融發展質量、提高農村人力資本與就業水平、適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加快城鎮化進程等建議,以期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助推共同富裕目標實現。
關鍵詞: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城鄉收入差距;農村人力資本;農村就業水平;門檻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2?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7-0753(2023)05-0030-12
一、引言
當前我國已消除了絕對貧困并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走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新征程,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顯著提升。然而,我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依舊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我國是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一直是不平衡發展的重要部分,是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十八大以來,盡管我國城鄉收入相對差距持續縮小,但2022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達2.45,城鄉收入差距過大的現狀依舊嚴峻,制約著人民總體生活質量的提升與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影響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對此,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要著力推動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與此同時,“十四五”規劃指出要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增強金融普惠性。近年來,我國普惠金融蓬勃發展,在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有研究指出,普惠金融可以消除或最大限度地減少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均(Dahiya和Kumar,2020),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帶來新的機遇。
國務院發布的《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提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負擔的成本為有金融服務需求的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適當、有效的金融服務。換言之,普惠金融就是為每個人提供公平的機會,確保每個人都可以獲得現代社會和經濟所需的金融服務產品,以獲得更高的家庭收入,過上更好的生活(Sankaramuthukumar 和 Alamelu,2017;Corrado G和 Corrado L,2017)。在普惠金融測度方面,Beck等(2007)初次從使用深度和覆蓋廣度兩個維度去構建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評價體系;而Sarma和Pais(2011)采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的構建方法,從使用滲透度、可利用性和使用狀況三個維度對比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金融服務可獲取性方面的區別;Dahiya和Kumar(2020)則通過金融服務使用、滲透和可及性三個維度測度普惠金融水平;鄒克(2019)從滲透性、使用效用性與可負擔性三個維度對普惠金融指數進行測度;戴鵬和何佳(2022)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使用成本三個維度構建普惠金融發展指標體系。
少數學者對普惠金融能否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進行了研究并得到了不同的結論。有學者認為普惠金融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且存在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與地理區域上的差異(張愛英和孟維福,2021;郭雪等,2020;張春海等,2022)。吳茂國和武振宇(2020)、張建波(2018)、楊虹和張柯(2020)則指出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具有非線性影響,可能存在門檻效應,呈現倒“U”型關系。此外,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與數字科技的發展,普惠金融數字化進一步增強了金融普惠性,以數字化驅動的數字普惠金融迅速形成。相關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機制包括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優化收入結構、優化信貸配置、提高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等(楊德勇等,2022;楊怡等,2022;周利等,2020)。
目前我國普惠金融已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強調要深入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周孟亮和李向偉(2022)提出借助有效的社區治理促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路徑,而孫兆斌(2018)則探討了商業銀行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路徑。當前雖然關于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測度的成果較多,但鮮有學者關注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指標構建及測度問題。殷越(2022)依托于五大發展理念,從金融創新、金融協調、金融綠色、金融開放及金融共享五個維度測度了我國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但并未涉及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測度。在數字技術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有學者同時考慮了傳統普惠金融和數字普惠金融兩者的影響,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與傳統普惠金融在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方面具有協同效應(宋科等,2022)。也有少數學者將數字化指數納入現有普惠金融指標體系,形成綜合普惠金融發展指數,用以研究綜合普惠金融發展在緩解相對貧困中的作用(吳慶田和王欣玲,2022)。
綜上所述,部分學者關于普惠金融或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為本文奠定了基礎,但該領域仍存在拓展空間。一是數字普惠金融即普惠金融數字化是數字科技在金融行業的應用,是對傳統金融、普惠金融的深化與完善,本質仍屬于普惠金融范疇,是普惠金融的重要部分,但現有研究集中于傳統普惠金融或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獨立研究,較少將兩者進行綜合考慮。二是現有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對普惠金融的發展質量并未給予充分重視。三是關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多為理論研究,暫未涉及指標構建與實證分析。因此,在數字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構建囊括傳統普惠金融與數字普惠金融,并考慮發展質量的普惠金融發展指標體系十分有必要。本文將傳統普惠金融與數字普惠金融均納入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理論剖析了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基于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11—2020年面板數據,實證探究了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否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最后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Maurer和Haber(2007)指出,由于金融發展使得更多的信貸資源流向富人,富人借此獲得更多收入,進而使得收入差距持續擴大。而普惠金融能夠有效改善傳統金融的結構性問題,增加低收入群體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機會,緩解城鄉收入不平衡(張新月等,2022)。如今,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還是在農村。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降低金融服務門檻,緩解金融抑制與金融排斥,提高農村居民等長尾群體的金融可得性,其減貧增收效應與收入分配效應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具體而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拓展普惠金融對農村居民的覆蓋廣度與農村居民使用普惠金融服務的深度,促使農村居民通過信貸等金融服務獲得社會閑置資金,增加生產經營資本,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形成規模化經營,延長農業產業鏈條,使得農村家庭經營性收入穩定增長。第二,農民與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是普惠金融重點服務對象,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為農村居民創業提供信貸資金,支持農村居民參加創業培訓與工作技能培訓,提高農村居民人力資本和農村居民自主創業的意愿與能力,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回報率更高的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從而為農村居民提供更多的經濟機會。第三,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拓寬了理財業務和保險業務的覆蓋范圍,為農村居民提供更多可獲得的金融工具,提高了理財業務與保險業務的服務效用。農村居民通過利用這些投資理財工具、風險管理工具來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并防范收入遭受損失,進而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此外,倘若普惠金融發展不具備可持續性,可能導致普惠金融在短期內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從長期來看則后繼無力,甚至使得普惠金融難以存續。因此,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只有具有可持續性才能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發揮更深遠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說1。
H1: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為農村居民提供了長期可獲得的金融服務,增強金融服務三農等弱勢群體的效果。隨著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農村居民有更多的機會獲得信貸資金,并將其用于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訓,進而實現農村居民人力資本積累。根據內生增長理論與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的增加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長期提高勞動者的收入。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提高會促進農村地區技術創新與技術進步,提高農業生產力,延長農業產業鏈,增加農產品附加值,進一步推動農業發展,提高農村居民農業收入。同時,人力資本提高使得農村居民掌握更多數字技術相關知識與技能,使他們能夠利用互聯網平臺拓寬銷售渠道,降低銷售成本,從而實現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與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說2。
H2: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通過提高農村居民人力資本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私營企業在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過程中可以獲得發展機會。首先,私營企業多為小微企業,在融資方面往往面臨“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而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拓展了金融覆蓋廣度,能夠為私營企業提供信貸資金,滿足其融資需求,從而促進其擴大生產規模。同時,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為有創業意愿的人提供了創業資金,這部分創業活動促使私營企業規模進一步擴大。私營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為社會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在保就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私營企業進一步發展,其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工作崗位,使農村居民獲得更多就業機會,提高農村居民就業水平,增加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進而實現城鄉收入差距縮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說3。
H3: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通過提高農村居民就業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我國地域遼闊,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情況與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等都存在較大差距。我國東部地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金融門檻相對較低,能夠充分惠及農村居民,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進而有效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中西部地區,鑒于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后,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夠完善,金融專業人才較為缺乏,當地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受到限制,而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阻礙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導致中西部地區這一收斂作用較小甚至不具備顯著影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說4。
H4: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地區異質性。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城鎮發展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使得政府加大對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促進農村地區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為農村居民享受到更優質的普惠金融服務提供了有力支持,增強了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此外,城鎮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農村居民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就業機會與福利,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進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因此,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存在城鎮化的門檻。當城鎮化超過一定的門檻值之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增強。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說5。
H5: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存在城鎮化門檻效應。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我國2011—2020年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以下簡稱省份)為研究樣本,構建省級層面的面板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國家統計局官網、《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等統計資料。對于個別缺失值,通過線性插值法補齊。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城鄉收入差距
現有研究主要使用theil指數、城鄉居民收入比、Gini系數等衡量城鄉收入差距。考慮到城鄉人口結構的影響,且theil指數對分散于兩端的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變動較為敏感,選取theil指數衡量城鄉收入差距。theil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theilt代表用于衡量城鄉收入差距的各年份theil指數,i=1代表城鎮,i=2代表農村,Iit代表t年城鎮居民收入或農村居民收入,It代表t年城鎮居民收入與農村居民收入總和,Pit代表t年城鎮人口數或農村人口數,Pt代表t年城鎮人口數與農村人口數的總和。theilt越高,說明城鄉收入差距越大。
2.解釋變量: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
普惠金融的內涵可以用“普”和“惠”進行高度概括。其中,“普”是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普遍性、普及性,體現的是一種平等權利。“惠”是指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惠民性、優惠性,體現的是一種便民目的(楊艷琳和付晨玉,2019)。“普”是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外在形式,“惠”是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實質內涵。《中國普惠金融指標分析報告(2021年)》指出,從中長期來看,普惠金融服務的廣度和深度仍然不足,下一步要推進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和實體經濟多樣化的金融需求。由此可見,普惠金融服務的廣度與深度仍是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部分。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服務實體經濟,提高所有群體福祉水平,普惠金融是否真正發揮作用仍取決于其服務效用。值得注意的是,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考慮其普及性與有效性,也需要考慮其可持續性,保證普惠金融長遠發展,持續服務實體經濟。此外,在金融科技時代背景下,我國宏觀經濟正由高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普惠金融也向數字普惠金融轉型(胡濱和程雪軍,2020)。普惠金融數字化作為一種趨勢,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帶來了新機遇。為此,參考吳慶田與王欣玲(2022)的研究,將普惠金融數字化指標納入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綜上,本文將從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服務效用、普惠金融可持續性4個維度共19個具體指標來測度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指數越大,說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熵值法是一種客觀賦權方法,其根據各項評價指標的離散程度來確定各指標權重,避免了人為因素帶來的偏差,具有較高的準確性。本文采用熵值法確定各指標權重,并得到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指數,具體步驟如下。
3.中介變量
本文選取農村人力資本與農村就業水平為中介變量,農村人力資本以農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支出衡量,農村就業水平以私營企業鄉村就業人數衡量。
4.控制變量
參考傅巧靈等(2021)的研究,選取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對外開放程度、政府財政支出以及城鎮化水平等可能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作為控制變量。主要變量及其說明如表2所示。
(三)描述性統計
根據表3的描述性統計結果,theil平均值為0.091,標準差為0.040,最小值為0.018,最大值為0.202,說明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較大,且不同省份、不同年份具有較大的差異。fin最小值與最大值分別為0.223與0.696,表明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差別也較大。將各省數據對比發現,北京市、天津市等地城鄉收入差距較小且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云南省、甘肅省等地城鄉收入差距較大且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此外,根據fin與theil的時間趨勢圖發現①,2011—2020年我國31個省份theil整體呈下降趨勢,fin整體呈上升趨勢,表明這10年來我國各省份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同時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穩步提升,說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存在負相關關系。為進一步探究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否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本文后續進一步進行實證檢驗。
(四)模型設定
考慮到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關系,為避免模型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用滯后一期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作為解釋變量,采用固定效應模型來探究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theilit代表i省在t年的城鄉收入差距,L.finit代表i省在t-1年的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指數,β0為常數項,β1、γ為變量系數,Xit表示控制變量,δ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誤差項。
四、實證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4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基準回歸結果。由第(1)列可知,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系數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可能是因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可以緩解金融抑制與金融排斥現象,其減貧增收效應與收入分配效應可以有效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降低城鄉收入差距。由此,假說1成立。就控制變量而言,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即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會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然而,回歸結果顯示產業結構升級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這與現實不符。考慮產業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可能存在非線性影響,本文加入產業結構的平方項再次進行回歸,結果如第(2)列所示。在列(2)中,產業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而產業結構平方項的影響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產業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U”型影響,即產業結構對城鄉收入差距起到了先收斂后擴大的作用。這可能的原因在于,前期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農村勞動力轉向收入更高的第二、第三產業,此時將降低城鄉收入差距,但當各種生產要素向第二、第三產業過度轉移時,則不利于農業發展與農村居民收入的持續提高,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此外,對外開放程度與城鎮化水平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政府財政支出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政府財政支出在支農方面的力度不夠。
表4第(3)列、第(4)列分別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inc_rural)與城鎮居民人均收入(inc_city)的回歸結果。由此可知,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可以顯著提高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且對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更大,從而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這也說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再次驗證了假說1。
(二)機制分析
為驗證農村人力資本與農村就業水平在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的中介作用,本文參考江艇(2022)的做法,對中介作用機制進行檢驗。回歸結果如表5所示。
表5第(1)列為基準回歸結果,即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2)列回歸結果顯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農村人力資本的估計系數為3.989,在1%的水平下顯著,表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夠促使農村人力資本不斷提升。人力資本的提升能進一步推動農村地區的技術創新與進步,提高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業發展,并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提高農村居民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由此,假說2成立。類似地,第(3)列結果顯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農村就業水平的估計系數為6.864,在10%的水平下顯著,說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可以提高農村就業水平。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意味著金融的服務廣度、服務深度與服務效用都得到了提升,為私營企業與有創業意向的居民提供資金支持,有利于私營企業數量的增加與生產規模的擴張,為社會提供更多工作崗位,提高農村就業水平,進而促進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由此,本文假說3得到驗證。
(三)異質性檢驗
根據地理位置的不同,將31個省份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分別研究不同地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差異性影響。從表6地區異質性檢驗結果可知,在東部地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顯著為負,在中西部地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即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在東部地區能夠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在中西部地區不具備顯著影響。由此,假說4成立。可能的解釋為,中西部地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還不足以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東部地區,經濟整體發展狀況較好且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完善,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也更高,能夠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顯著的收斂作用。
(四)穩健性檢驗
本文采取以下三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替換被解釋變量,用城鄉居民收入比(shourubi)衡量城鄉收入差距。由表7第(1)列可知,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顯著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二是替換解釋變量,第(2)、第(3)列為分別使用變異系數法與因子分析法重新構造的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指數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三是改變樣本范圍,考慮到直轄市與其他省份在經濟發展、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異,本文剔除北京市、天津市、重慶市、上海市這四個直轄市的樣本數據,重新回歸得到余下省份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結果,如第(4)列所示。在剔除四個直轄市樣本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仍能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表7的結果表明,替換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與改變樣本范圍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系數符號均未發生變化且依然顯著,說明前文所得結果是穩健的,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確實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五)門檻效應檢驗
為了驗證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否存在城鎮化的門檻效應,本文通過重復抽樣1 000次確定門檻值個數,使用Bootstrap法檢驗門檻效應是否存在。根據表8可知,單一門檻的F統計量為29.53,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單一門檻效應檢驗,門檻值為0.405 0。雙重門檻與三重門檻的F統計量分別為23.59與11.85,P值分別為0.137 0與0.299 0,未通過雙重門檻與三重門檻效應檢驗。
門檻回歸估計結果如表9。結果顯示,當城鎮化水平小于等于0.405 0時,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當城鎮化水平超過0.405 0時,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系數為-0.051,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這說明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增強。這可能是由于在城鎮化過程中,政府持續加大對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促進農村地區普惠金融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基礎。同時,城鎮化水平提高為農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發展機會,進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促使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增強。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普惠金融服務效用與普惠金融可持續性四個維度測度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構建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并使用theil指數測度城鄉收入差距,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實證探討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否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研究結果表明:(1)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能夠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一結論通過了穩健性檢驗。(2)機制檢驗發現,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通過提高農村人力資本與就業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3)異質性檢驗發現,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地區異質性,在東部地區具有顯著影響,而在中西部地區影響不顯著。(4)門檻效應檢驗發現,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存在城鎮化的單一門檻效應。隨著城鎮化水平提高,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作用增強。
根據本文結論,為了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目標,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提升普惠金融發展質量。加強傳統普惠金融建設,大力推動普惠金融數字化建設,促進傳統普惠金融與數字普惠金融協同發展,拓寬農村居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長尾群體獲得普惠金融服務的渠道,有效解決傳統普惠金融在農村地區覆蓋不足的難題,使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在農村地區扎根與推廣。此外,鼓勵金融機構創新針對農村居民的普惠金融產品,加大普惠金融服務農村地區的力度,提高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服務精度。
提高農村人力資本與就業水平。政府應當重視農村居民的教育,為農村居民提供文化教育與合適的技能培訓,同時積極配合宣傳手段,引導農村居民自覺重視人力資本積累,提高農村居民就業競爭力與創業能力。另外,鼓勵私營企業發展并為社會提供更多工作崗位,提高就業水平。
適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增加對中西部地區的資金投入,完善中西部地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為中西部地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提供硬性條件。同時,支持中西部地區培育普惠金融專業人才,吸引東部地區人才進入中西部地區發展,提高普惠金融創新水平,改善中西部地區普惠金融服務質量,提高中西部地區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
加快城鎮化進程。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統籌城鄉發展,加速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流動,健全配套政策措施,推動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構建要素自由流動和城鄉收益共享的一體化發展機制。同時,推動城鎮基礎設施向鄉村延伸,加快農業與第二、第三產業融合發展,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升級,激發農業農村發展活力,帶動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
注釋:
①? fin與theil的時間趨勢圖省略,有需要請與作者聯系。
參考文獻:
[1] DAHIYA S, KUMAR M. Linkage between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merging Indian economy[J]. Vision,2020,24(02):184-193.
[2] SANKARAMUTHUKUMAR S, ALAMELU K. Financial inclusion: African scenario[J]. Insight Africa,2017,4(02):121-135.
[3] CORRADO G, CORRADO L. Inclusive finance for inclusive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Current Opinion in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2017,24:19-23.
[4] BECK T, DEMIRGUC-KUNT A, MARTINEZ PERIA M S.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7,85(01):234-266.
[5] SARMA M, PAIS J.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1,23(05):? 613-628.
[6]鄒克.普惠金融、農業TFP變動與城鄉收入不平衡——基于普惠金融結構性問題視角[J].金融經濟學研究,2019,34(02):41-53.
[7] 戴鵬,何佳.普惠金融發展與城鄉收入差距:門檻特征和作用機理[J].區域金融研究,2022(06):28-34.
[8] 張愛英,孟維福.普惠金融、農業全要素生產率和城鄉收入差距[J].東岳論叢,2021,42(09):63-76+191.
[9] 郭雪,雷雨簫,董繼華.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抑制效應的檢驗[J].統計與決策,2020,36(05):142-144.
[10]張春海,楊彩濤,于惟.普惠金融發展促進區域經濟包容性增長了嗎?——來自全國2 116個縣域數據的經驗分析[J].金融經濟,2022(11):17-27.
[11]吳茂國,武振宇.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實證研究[J].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6(04):63-78.
[12]張建波.關于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的門檻效應研究[J].甘肅社會科學,2018(01):146-152.
[13]楊虹,張柯.普惠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城鄉收入差距影響研究——基于云南省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20,36(05):52-65.
[14]楊德勇,代海川,黃帆帆.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門限效應研究——基于不同發展維度的實證分析[J].經濟與管理評論,2022,38(03):89-101.
[15]楊怡,陶文清,王亞飛.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J].改革,2022(05):64-78.
[16]周利,馮大威,易行健.數字普惠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數字紅利”還是“數字鴻溝”[J].經濟學家,2020(05):99-108.
[17]周孟亮,李向偉.融入社區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新思路[J].社會科學,2022(06):128-136.
[18]孫兆斌.商業銀行普惠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與路徑[J].新金融,2018(11):57-62.
[19]殷越.金融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及時空演進[J].統計與決策,2022,38(17):129-133.
[20]宋科,劉家琳,李宙甲.數字普惠金融能縮小縣域城鄉收入差距嗎?——兼論數字普惠金融與傳統金融的協同效應[J].中國軟科學,2022(06):133-145.
[21]吳慶田,王欣玲.綜合普惠金融發展質量與共同富裕目標下相對貧困緩解——基于CHFS調查數據的分析[J].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46(04):46-52.
[22] MAURER N,HABER S.Related len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Mexico[J].J.Econ.Hist.,2007,67(03):551-581.
[23]張新月,師博,甄俊杰.高質量發展中數字普惠金融促進共同富裕的機制研究[J].財經論叢,2022(09):47-58.
[24]楊艷琳,付晨玉.中國農村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多維貧困的改善效應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19(03):19-35.
[25]胡濱,程雪軍.金融科技、數字普惠金融與國家金融競爭力[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73(03):130-141.
[26]傅巧靈,游濤,李媛媛,等.京津冀地區普惠金融政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J].中國軟科學,2021(S1):148-156.
[27]江艇.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中國工業經濟,2022(05):100-120.
(責任編輯:張艷妮/校對:曾向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