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好大王碑》的書法藝術
武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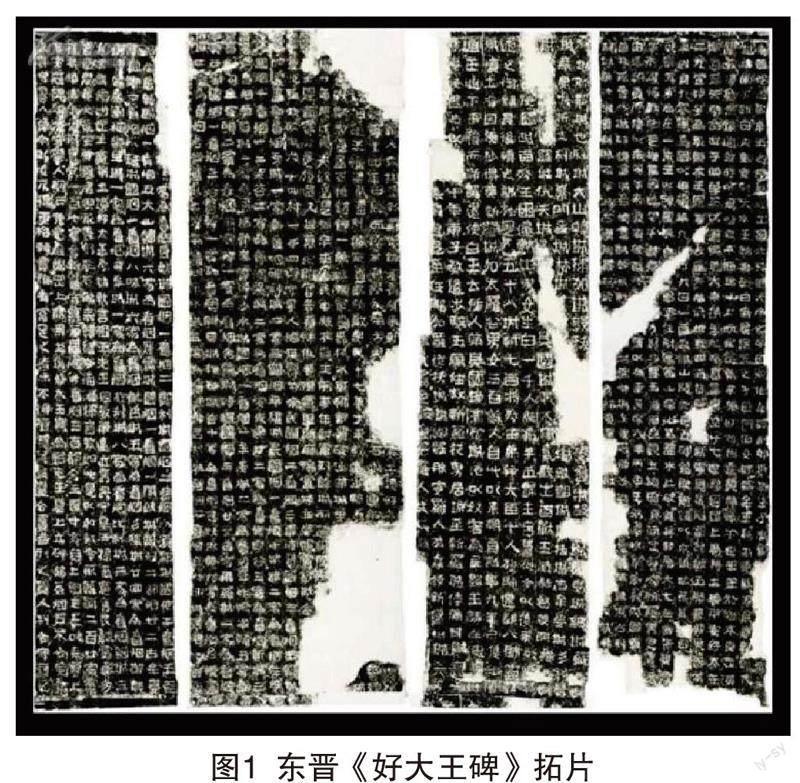
摘 要:《好大王碑》書體介于“篆、隸、楷”之間,是中國書法史上新舊書體的交替時期的特殊產物。古拙典雅,氣勢磅礴,用筆簡散,結字樸茂沉穩,章法天真爛漫,以樸實無華、不矯揉造作取勝,暗合于傅山著名“四寧四毋”之審美價值取向。在書法史上以其鮮明的個性獨樹一幟,是書法藝術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瑰寶。
關鍵詞:魏晉時期;隸書;《好大王碑》
中圖分類號:J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905(2023)05-0-03
《好大王碑》(見圖1),全稱《高句麗廣開土境平安好大王碑》,又稱《好太王碑》,是中國現存最大的石碑之一。此碑系高句麗第20代王長寺王為其父親第19代王好太王所立,碑文記載了永樂大王在位時討高麗、攻百濟、敗倭寇、救新羅的赫赫戰功。此碑設立于好太王陵寢東側,因永樂大王死后謚號為“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故又稱“好太王碑”。碑文為隸書,刻于一整塊長方形巨石的四壁,字形方平工整,氣勢雄渾博大。書法雄強渾厚,樸茂沉穩,結構恢宏。用筆簡單散漫,字形天真爛漫,無波折頓挫,線條凝練扎實,以鮮明的個性獨占一隅,是書法藝術史上一朵為數不多的奇葩。此碑為東晉書法名碑,被后人列入隸書的范疇。
一、魏晉朝時期隸書的發展
隸書,又有“史書”,還有“八分”“分書”等稱呼。隸書是由篆書演變而來的,它是中國書法史上一種十分重要的書體。隸書以前的文字屬于古文字,隸書以后包括隸書統稱為今文字,后來的楷書、行書、草書是由隸書演變而來的。許慎《說文解字》有:“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1]正如西晉衛恒在《四體書勢》中言“隸書者,篆之捷也。”[2]實際上隸書就是篆書的簡約與快寫。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隸書在不同的時代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因此在不同的時代也就有著不同的書寫風格。在中國書法史上,每一種字體的產生都是量變到質變逐漸形成的,雖然說早期形成的風格與其成熟時有些許不同,但是其連續發展的主要特征還是基本保持一致的。
漢代時期是隸書發展的一個頂峰,這一時期的隸書被統稱為漢隸。漢代書法的雄強樸茂之風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漢代隸書蘊含著一種博大的氣勢,充溢而涌動著雄健的力量。精美絕妙的漢隸至今仍然散發著無窮無盡的藝術魅力。現在所能被人們熟知的漢代隸書,都是因為當時刻在石碑上因此能保留下來的,但可惜當時篆刻碑文的作者沒有留下他們的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銘文內容為其命名。與此同時,因書寫材料的不同還出現了寫在木板上或者竹簡上。竹簡上的漢隸遠不像碑刻上的那樣嚴整、肅穆、氣勢恢宏,而是活潑靈動、變化多端,甚至漫不經意,富于幽默感。在這眾多碑刻中大致可分為五大風格,第一類是端莊典雅之作,此類碑刻法度森嚴,多是典范,代表作品有《熹平石經》《史晨碑》等;第二類是清勁秀逸之作,此類碑刻書風精美,雋永秀麗,代表作品有《禮器碑》《曹全碑》等;第三類是雄渾奇絕之作,此類碑刻樸茂遒勁,工穩精巧,代表作品有《張遷碑》《鮮于璜碑》等;第四類是質樸天真之作,多為摩崖刻石,代表作品有《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等;第五類是簡帛書,活潑靈動,變化多端,代表作品有《居延漢簡》《武威漢簡》等。
進入魏晉時期后,隸書由漢代的巔峰開始步入衰微,雖然沒有被廢棄,但變化不多而出現了一個較長的沉寂期。
魏晉后,隸書式微有著各方面的原因。此時期國家政權更替頻繁,各民族相互交融、思想自由開放,從而人們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文化的發展也日益進步。在文學、思想、藝術等方面都對后來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一時期的文化藝術大發展已成為中國歷史上一頁輝煌的篇章。宗白華先生曾這樣評價道:“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精神史上卻是極自由、極解放的,是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在這幾百年是人類精神上的大解放、思想上的大自由。”[3]
在這一時期,各種書法風格交相呼應,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其時,漢字書體的演變已經全面完成,篆、隸、楷、行、草都已形成了完備的體系。草書由章草已經發展演變到了今草的階段,楷書在演變過程中日趨成熟,散發出耀眼的光彩,行書達到了完美的頂峰,而隸書逐漸失去了主體的地位,呈現出衰落的趨勢。因之,隸書正統地位的下降也是中國書法藝術的進步和書法藝術發展之必然結果。
在這一時期,隸書主體地位的下降,雖然使其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影響,但隸書依舊存在著它獨有的魅力。建安十年,曹操主張薄葬,禁止樹碑立傳,因此三國時的碑刻發展迅速下降。現在出土的三國碑刻大多出土于河南,三國的書家大多是由漢入魏,因此此時的隸書大多繼承了漢隸的風格。碑刻大部分不會寫下書家的姓名。字形端莊工整,規矩呆板,入筆時會刻意地尋求方筆,收筆的波折也變得更加華麗妖嬈,形成了“魏隸書風,有漢隸遺韻”。
這種書體用筆遒勁厚重,結構大部分形成了變體,即謂之“黃初體”。西晉存在的時間較短,學隸書、寫隸書的人也較少,在古樓蘭發現的魏晉簡牘帛書中,隸書也是為數不多的存在。現如今所能見到的西晉隸書遺跡,大部分的書風都是繼承曹魏時代,但就是因為繼承了魏晉的書風,導致程式化的趨勢更加嚴重。東晉的碑刻銘文大多是采用了隸書這一書體。東晉的隸書傳承和發展了曹魏、西晉的隸書法度,但是形體上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大致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基本繼承了曹魏、西晉書風的隸書;第二類是用筆多為方筆的隸書;第三類是書寫風格較為草率天真的隸書;第四類是將書法轉變成裝飾性的隸書磚文。
范文瀾曾在《中國通史》中評:“就文學藝術說,漢魏西晉,總不離古拙的作風,自東晉起,各部門陸續進入新巧的境界。”[4]漢代隸書是書法長河中的隸書巔峰時代。唐代張懷瓘《書斷》所引王愔說:“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2]近人康有為極力推崇漢隸,他在《廣藝舟雙楫》中寫道:“吾謂書莫盛于漢,非獨其氣體之高,亦其變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飛白,劉德升作行書,皆漢人也。晚季變真楷,后世莫能外。蓋體制至漢,變已極矣。”[2]當隸書發展到魏晉時,由于曹魏時期碑刻藝術被限制,隸書的地位大大下降,出現了回光返照的現象,隸書字形端莊工整,規矩呆板。
《好大王碑》便是這與眾不同的“另類”。其大大地擺脫了漢隸時期的“格式化隸書”,用獨特的書寫手法展現了當時另一種隸書的風格。從當時的社會角度看,《好大王碑》也是具有打破當時常規創作精神,不隨波逐流的逆時代的代表之作,也為魏晉書法達到新高峰奠定了堅實基礎。它的出現也為隸書的發展開拓出一條蹊徑,成為承上啟下的重要碑刻。
二、《好大王碑》的藝術風格
《好大王碑》的書法雄強厚重、樸茂沉穩,結構恢宏,平實、穩正,布局嚴整、古樸、肅穆,用筆簡散,無波磔頓挫,如錐畫沙,在書法史上以其鮮明的個性獨樹一幟,是書法藝術寶庫中不可多得的瑰寶。《好大王碑》的藝術特點大致通過以下幾個方面表現。
(一)圓渾澀勁、雄渾豪邁的用筆
《好大王碑》,首先是其氣勢恢宏。雖然其點畫放蕩不羈,但卻圓渾澀勁,雄渾豪邁。在《好大王碑》中,那些線條看似簡單、隨意,但以簡單的線描繪出了面,卻存在著極強的空間感。線條雖沒有什么變化,卻存在著極強的節奏感,造成了讓人眼前一亮的視覺效果。《好大王碑》用筆簡單,有些筆畫甚至略顯隨意,但其筆畫所表現出的隨心而欲的效果卻是完全符合隸法的。起筆或逆鋒或順鋒,力求圓渾澀勁,雄渾豪邁,完好地保留了篆籀的傳統筆法,使其線條凝練而富有生氣,筆畫無波磔頓挫,卻也能做到收放自如,隨心而欲。《好大王碑》的用筆無漢碑中典型的“蠶頭燕尾”,但在這種看似簡單隨意的線條中,卻蘊含著不被規則所約束的風流和極強的視覺效果。這種古樸、圓渾、直率的線條,既表現出了書寫者不畏懼規則而隨心書寫的酣暢淋漓,又使線條出其不意地充滿古拙。縱觀此碑,不難發現,它的用筆大多數都存在著篆籀之氣,整篇碑刻都是中鋒行筆。臨摹時要把握好用筆的力度,避免書寫速度過快,行筆中始終保持中鋒運筆,把退澀的味道表現出來,進而更容易去追求古拙的趣味。
(二)樸茂沉穩、欹側多變的結字
楊守敬《學書邇言·評碑》中評曰:“《好大王碑》,近時出見,醇古整齊。”[5]《好大王碑》字形古拙,不僅繼承漢隸亦兼具楷意,憨態可掬,樸茂沉穩,氣勢莊重。此碑字形結體變幻莫測,其體內在的氣息,與外部空間之松緊,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緊湊而不呆板,氣象圓渾樸茂。
《好大王碑》獨特的線條造就了獨特的結字風格,而由這種特殊的線條來構成的結字,猶如閑云野鶴之輩,形態自然,憨態可掬,將作者心中所蘊含的放蕩不羈自然而然地展示在世人的眼前。雖說《好大王碑》的結字看起來立足于平正,看似呆板,但其中所蘊含的欹側,字勢開張,卻被作者不經意地在字的筆畫的穿插之間展示出來,字勢縱橫交錯,收放自如,當斷則斷,力求做到整體看似呆滯,但卻充滿動感。《好大王碑》結字多為橫勢,具有明顯的八分之勢,雖然也有個別字做了縱勢的變化,尋求多變的姿態,但放之通篇中卻也不顯突兀,而是成為貫穿行氣的點睛之筆。《好大王碑》這種以楷隸為體、篆籀為用、呆板而不失生機、欹側而不失平正,古拙而不失雅致,在漢代隸書刻石以及之后的隸書中也是極難得一見的,即使將其放之于漢隸中,其藝術品格也是極其具有研究價值的一部石刻。
(三)不拘小節、天真爛漫的章法
《好大王碑》屬于隸書的范疇,但又與漢代隸書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按傳統意義上的漢碑去看待,而必須對其字內外空間關系的營造予以特別的關注,同時也不能忽略字與字之間的呼應關系。縱觀此碑,可以發現它的字距大于行距,橫有行,豎有列,字字獨立,章法頗顯茂密,基本接近傳統意義上的漢碑,但《好大王碑》的構成仍帶有明顯的從隸到楷的過渡特征。一方面,雖然有的字形大小不一,使它無法規規矩矩地存在于后來北朝碑版所使用的縱橫界格之中;另一方面,它又試圖擺脫漢隸所使用的“左挑右波”的束縛來力圖求變,這就使得《好大王碑》不可能采用以往漢碑的那種大幅度的拉大字距,加強行氣來放大內外空間對比的手法。因此,《好大王碑》運用了一種新的排列方式,這種排列方式十分靠近“楷法”。這種布局自然而然地成了《好大王碑》此時最合適的選擇。《好大王碑》書法章法別具匠心,看似行距、字距分配均勻,排列有序,但實際上卻是隨字形大小組合一體,參差變化強烈,別有情趣。雖然它的字形近似正方形,但因為用筆帶有古樸的篆籀意,并且能夠在平正中尋求欹側,方正中運用變化,在字疏行密的排列中大小不拘,錯落天成。
三、《好大王碑》對后世的影響
東晉《好大王碑》對后世的影響頗為深遠,它創造了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的書法藝術形式,該碑之精神為文人書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使書法成為表達書法家情感的載體。清代伊秉綬作隸書,與《好大王碑》的書寫思想暗合,他不追求用筆的粗細變化,反而極重視結構的安排,加強字筆畫之間的留白,營造空間感。他寫的隸書,筆畫的粗細近乎相等,但在空間布白上,運用巧妙的錯位,就形成了一種給人更加強烈的視覺效果。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中稱《好大王碑》為:“若高麗故城之刻,新羅巡狩之碑,啟自遠夷,來從外國,然其高美,以冠古今”。[2]當代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在其編著的《書法講義》上對《好大王碑》也有著極高的評價:“清光緒間在吉林集安縣出土。碑高二丈余。為高句麗英主廣開太王之巨碑。好太王名淡德,十八歲即位,稱永樂大王。四面環刻,刻于廣開大王薨后三年(公元414年)。碑頌王之功績,且錄其守墓煙戶。碑文中記助新羅與日本開戰端之事,書為古隸。共四十四行,行四十一字。書法方整純厚,遒古樸茂,體在隸楷之間,并多含篆書遺意,甚古雅可賞。”[6]
近年來,《好大王碑》書法被越來越多的人重視,在古今不斷創新、書風多元的書法新時代,運用其字法、筆法、章法,對熱衷于隸書創作的書家來說,該碑是具有極大的啟迪作用的。同時,該碑對研究新舊書體也具有重要意義,成為研究魏晉時期隸書的重要依據,也在書法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參考文獻:
[1]許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2015.
[2]黃簡.歷代書法論文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4.
[3]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4]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楊守敬.學書邇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歐陽中石.書法講義[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