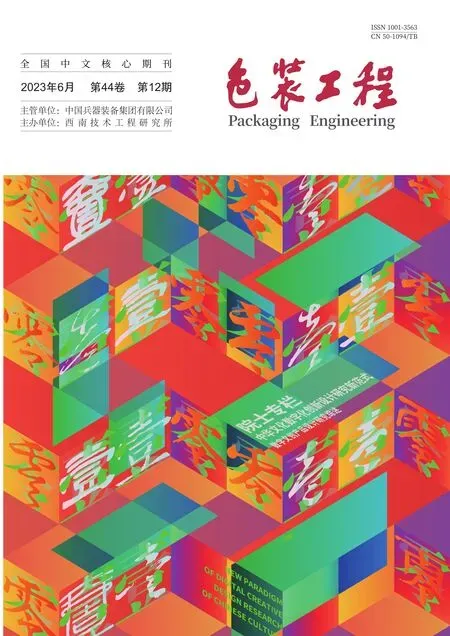兒童視角下紅色文化主題展服務體驗研究
王艷艷,鞏淼森,陳超
兒童視角下紅色文化主題展服務體驗研究
王艷艷1,鞏淼森2,陳超3
(1.寧波財經學院,浙江 寧波 315175;2.江南大學,江蘇 無錫 214122;3.寧波博物院,浙江 寧波 315199)
研究博物館紅色主題展如何有效增進兒童對紅色文化的體驗與認知。以兒童視角為研究基礎,運用影隨法和照片引談法,梳理用戶體驗地圖,以寧波博物院《三江潮涌——1921—1949年中國共產黨寧波革命歷程展》為例,通過對兒童觀展行為觀察和體驗受訪感受記錄,探究兒童視角下紅色文化體驗類型與影響因素。得出多維度體驗是促進兒童深入學習紅色基因的關鍵因素,有利于兒童滲透式的紅色文化學習。歸納出四種兒童觀展體驗類型,分別為深化認知的感官式、由表及里的探究式、協作反饋的社交式、深化記憶的延續性體驗,并分析了不同體驗類型的影響因素,為博物館紅色文化展覽提升兒童觀展體驗提供借鑒。
兒童視角;紅色文化體驗;寧波博物院;兒童體驗類型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用好紅色資源,傳承好紅色基因”,紅色博物館、紀念館、紅色主題展作為兒童、青少年紅色教育的“立體百科全書”,應將專為兒童設計的體驗和服務視為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的重要內容。在目前國內的博物館紅色展覽中,為兒童專門開展的或以兒童視角切入的教育實踐相對較少,且大部分以老師或講解員解說觀展的形式開展。在這樣的活動中,雖然兒童能夠在有別于傳統學校課堂的博物館環境中進行探索,其本質卻仍然是與傳統課堂類似的聽講式學習,其教育效果欠佳,難以讓愛國主義價值觀深入兒童的內心。本文以寧波博物院《三江潮涌——1921—1949年中國共產黨寧波革命歷程展》(以下簡稱“三江潮涌”展)為研究案例,從兒童觀眾觀展體驗的視角探索紅色文化展覽的展陳內容、形式、教育活動與服務設計,探索兒童參觀紅色展覽的體驗類型,希望為國內博物館在紅色文化展中構建具有普適性的兒童體驗體系提供些許借鑒,并從學理上豐富兒童紅色文化體驗的相關研究。
1 研究綜述
20世紀80年代新童年社會學對兒童社會角色的顛覆性重構推動兒童研究范式轉變,而后國內文博界對兒童參與博物館的關注度持續升溫。近幾年相關政策文件的頒布,推動博物館成為兒童教育的“第二課堂”,博物館也積極轉向以兒童視角為中心的研究重點和發展方向。關于如何從兒童體驗的視角出發,創設有效的展覽與服務體驗,學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部分學者立足于“5R”的博物館教育體驗構建模式,從情感互動的視角幫助兒童理解展覽,引導兒童探索與表達[1],主張“沉浸式”“操作式”“創設情境”等展覽方式,引導兒童將獲得的新認知與真實情境相關聯[2]。部分學者則從兒童認知的角度出發,提倡注重感知學習與情感體驗的博物館學習形式,主張針對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認知發展特點,集成多樣化感知、交互性探索、創新性活動等體驗設計[3]。比如,針對兒童的認知特點,設計配套的博物館圖像化信息學習平臺,并使用人工智能技術,提升兒童快速解讀展覽信息的效率和效果,提高兒童在博物館學習中的針對性和自主性[4];再比如,打造符合兒童認知特點的游戲探索式主題與陳列,構建系統化、邏輯化的文化認知體系,從而達到文化傳承與教育的目的[5]。還有部分學者關注到有關兒童參與的研究方法,嘗試運用兒童視角梳理博物館教育活動的維度模型[6],創用馬賽克方法(特別針對5歲以下幼童),整合傳統研究方法和參與式工具,將其運用到兒童的研究實踐中[7],建構兒童參與服務體驗共創的模型[8]。
綜上所述,既有文獻從表層參觀到深層體驗,又從單向參觀模式到完整服務系統,為面向兒童的博物館提供借鑒,為進一步探究兒童視角下博物館展覽的改進奠定了基礎。此外,已有實踐案例如“美國俄克拉何馬市藝術博物館”的兒童參與式體驗[9]、澳大利亞悉尼博物館“兒童島”納入兒童意愿[10]、中國大運河博物館”大明都水監之運河迷蹤“展構建兒童游戲型教育模式[11]等,為國內博物館推動兒童高質量參觀和參與提供了參考,也啟示人們,作為博物館主要利益相關者的兒童不應被邊緣化。
2 研究設計
2.1 研究問題
近年來,為更好地傳承紅色基因,加強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全國各大博物館如火如荼地推出紅色主題展,開展各種紅色主題社教活動。以浙江省為例,浙江革命歷史紀念館“錢江潮”展,結合復原式景觀、多通道投影及大型革命油畫、雕塑作品等現代化展示手法,再現了重要的歷史時刻和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跡;桐廬博物館“紅色印記”以流動巡展方式,傳播“紅色記憶”;杭州博物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通過“人、物、城”交織敘述,形成多維度的展覽敘事鏈,還原紅色印記;同時,為加深兒童對紅色百年歷程的深入了解,博物館還推出紅色主題系列展覽活動,紅色主題拓片、紅色視頻展播、紅色遺址研學、紅色小講解員培訓及線上紅色書籍讀書會等。
大量的紅色主題展各有特色,注重展陳方式方法創新,旨在豐富整個觀展體驗,為觀眾帶來強烈的歷史沉浸感。然而,兒童在紅色主題展覽中的體驗感尚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存在如觀展體驗模式未能兼容兒童群體、缺乏與兒童認知特點匹配的體驗活動、展覽中的藝術表達難以激發兒童理解與共鳴等現象,其原因在于未將兒童作為觀展的主體觀眾,未能切實考慮兒童的觀展期望與體驗。基于此,本文對寧波博物院“三江潮涌”展的兒童觀展體驗進行了研究。
2.2 研究場景
本研究將寧波博物院的“三江潮涌”展設定為調研的主要場景。該展覽以時間順序作為邏輯主線,由“星火燎原”“前赴后繼”“抗戰烽火”“迎接曙光”4個部分構成,見圖1,梳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4個重要歷史階段——大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戰爭時期。展覽囊括了來自寧波地區的紅色歷史文物287件,紅色歷史教育宣傳圖片近400張,說明牌280個,紅色文化場景5個,紅色影片宣傳2個,紅色文化主題活動9期;其中,每個時期具有標志性的展示內容包括:入口處的“人民烈士紀念碑”浮雕、皮挎包、“星云坊”場景、竹編筐和“共產黨人”介紹墻;“南昌起義”及“井岡山會師”圖文;農民運動使用的鐵大刀、游擊時使用的子彈和榴彈、“浙東區委成立處”場景、破舊的棉襖、“梁弄戰斗”場景和糧票;軍帽、旅行袋等物件、“解放寧波”視頻、“開國大典”場景圖片與視頻。該展覽完整呈現了寧波地方黨組織的百年風雨歷程,突出了奮勇抗爭的英雄人物,以寧波這座城市的革命史實與革命人物故事為主要內容,以點帶面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的歷史征程。
2.3 研究方法
不同年齡段兒童受個人因素(包括年齡、性別、知識背景、父母學歷、行為習慣等)影響,對同一物理環境、主題內容、共同展品會產生不同的學習體驗。為縮小這些體驗的差異,本研究將目標對象選定為7~12歲兒童。根據皮亞杰的認知發展階段論,此階段兒童開始發展抽象邏輯,并具有一定的抽象能力,可憑借具體形象性事物來進行邏輯分類及認知,但這一階段仍不能脫離具體事物及形象形體的支配。為了更有效地觀察兒童的觀展體驗動線、行為和情緒,以獲得真實客觀的行為結果,本研究在調研前期階段采用觀察法,即跟蹤目標對象,并實時實地做好觀察記錄;調研中期借用了服務設計工具——用戶體驗地圖,從兒童在參觀展覽的前、中、后過程中的“看”“聽”“說”“做”里找出“痛點”和機會點;調研后期則采用照片引談法(Photo-elicitation Interviews),即利用影像來幫助兒童觀眾回憶、反思其個人經驗與印象,所使用的照片是研究者或兒童觀眾創造的,以補充兒童觀眾主觀的思考和感受視角。
2.4 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調研階段從2021年7月持續至2021年8月,共有125名兒童參與調研。在調研前期,研究者通過現場觀察及照片與視頻拍攝,對兒童的觀展行為進行追蹤及記錄,觀察的內容包括:兒童聚集的展品及其停留時間、兒童是否閱讀說明牌、兒童與隨同家長的交流、兒童的肢體表現與表情等。總體上看,兒童的展覽參觀時長為45~60 min,在參觀過程中反映出共性特征:在展品、圖像的說明文字前基本較少停留,而在能產生情感共鳴的展品、較為真實的立體場景里則會停滯較長時間。后者包括兒童熟悉的“人教版”課本中出現過的畫面,如“人民烈士紀念碑”浮雕墻、《開國大典》油畫等;融入“視聽”效果的真實場景;手榴彈、子彈夾等部分武器;輔助靜態畫面并能結合現實場景的視頻等。
在調研中期,研究者根據拍攝與記錄,將兒童參觀展覽時對展品、圖像、視頻、場景等所產生的行為、肢體與口頭語言、表情等進行匯總,將兒童在觀展時表現出的觀察、靠近、觸摸、停留、沉浸、提問等動態表現與設計點進行對應(見表1),并進一步梳理出展覽的用戶旅程圖(見圖2),從中歸納出“三江潮涌”展兒童觀眾體驗的“痛點”及相應機會點。其中痛點表現為參觀前沒有相關的宣傳冊等信息資料;參觀中標識指引不明確、文字信息不易于兒童理解、視頻中解說性陳述過多、展品陳列高度與亮度不符合兒童可觀察視角;參觀后學習內容未得到延伸,家庭觀眾的共同學習止步于觀展結束等。由此推導出可優化的機會點為展前設置兒童版宣傳冊或問題包,聚焦觀展重點;展中增加兒童觀展路線導引、兒童版說明牌或搭建“腳手架”解說展品背景故事,增設腳踏板等可參與的互動體驗;展后借由互聯網平臺推送主題內容,開展紅色教育文化研學活動等。
表1 兒童在參觀過程中的動態表現

Tab.1 Children's dynamic performance of visit process

圖2 “三江潮涌”展用戶旅程圖
為獲得更有針對性的觀眾體驗、思考和感受數據,研究在調研后期階段對8名兒童進行了照片引談,通過照片展示及相關提問,邀請兒童回憶觀展經歷,描述所看到的場景、展品、文字信息等。在此環節中,兒童普遍表現出對大幅場景及視頻留有較深印象;對滿載歷史滄桑的革命文物,如烈士使用過的物品、戰場使用的武器及課堂中學習過的歷史故事等展覽照片記憶猶新;對文字信息的印象相對模糊等。這些基本與調研前期觀察中所記錄的共性特征表現一致。
3 研究結果
“體驗”驅使兒童在參觀中探索,帶動他們的想象和創造,并不斷修正獲得平衡自我認知的構建過程。通過對本次展覽,研究者歸納總結了兒童參觀過程的跟蹤圖像、數據記錄、照片引談的結果,以及后續關于兒童在展中所看、所聽、所說、所做及所想的訪談,發現本次觀展過程中的兒童觀眾體驗大致能夠總結為4種類型:深化認知的感官式體驗、由表及里的探究式體驗、協作反饋的社交式體驗、深化記憶的延續性體驗,見圖3。此外,通過相關受訪記錄與觀察分析,發現不同體驗類型受不同因素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在后續紅色文化教育展覽在考慮全齡觀眾情況下,試圖給予參考。

圖3 兒童觀展體驗類型
3.1 深化認知的感官式體驗
感官式體驗與五感(視覺、聽覺、味覺、觸覺和嗅覺)密切相關,每種體驗都通過刺激一種或多種感官來觸發兒童的好奇心,并為兒童提供特定的信息。在對兒童的訪談與觀察中,研究者發現,兒童對視覺與聽覺相結合的展陳方式表現出較強的敏感度。比如,在展覽場景“梁弄戰斗”中,斑駁的墻體、散落的沙堆、身臨其境的炮火轟鳴聲等為兒童營造了極強的視聽沖擊力,引發兒童的沉浸體驗與反思。再比如,在展區尾廳,“解放寧波”“開國大典”兩個視頻通過紀錄片、沙畫特效表現等多種視聽手段,還原歷史場景、講述歷史故事、重溫經典瞬間,再現了當年寧波不同區域解放的歷史細節及開國大典上振奮人心的畫面,讓歷史更加可感、更易激起兒童的情感共鳴。相比之下,“竹林”場景只放置部分竹子、石頭作為點綴,在空間中呈現的視覺情境過于單一,兒童的停留時間相對較短,在后期訪談中也未對此產生深刻印象。因此,在博物館空間中營造更為具象的多感官視聽環境,能夠有效拉近兒童與歷史人物、歷史場景的距離,形成較深層次的歷史與文化認知。
為了促進深化認知的感官式體驗,首先,在尊重兒童人體工程學標準的基礎上,給予視覺刺激,此次展覽包括遺留的青花印盒、竹躺椅、戰斗武器等鮮活的物證,真實再現物證歷史印記;其次,觀察每個展示單元前的時長與投入狀態,多維度感官融合提高參觀投入程度,包括誦紅色童謠、放紅色電影、唱紅色歌曲、閱紅色文學、觸歷史痕跡等烘托展廳氛圍,讓孩子零距離去直觀感受共產黨人浴血奮戰的革命斗爭故事;最后,選擇與主題同一題材的故事模塊,借由沉浸式虛擬技術重現歷史場景、歷史事件,以兒童可接受的認知與語言模式,使其萌發對革命先烈的崇拜和熱愛之情。此外,本次展覽利用3D繪畫表現、模型搭建還原“中共浙東區委成立處”“中共寧波地位機關所在地——星云坊”等重現可視化歷史場景,而環境因素中照明、濕度、溫度、配色、風格等也是激發兒童空間感知的關鍵。
3.2 由表及里的探索式體驗
探索式的學習方式來自喬治·E.海因(George E. Hein)的教育理論模型,這種學習方式主張學習是“主動的、重構思維的過程”,強調學習者通過動手探索的方式,主動參與學習過程,獲得某個特定的結果[12]。本次研究觀察到,物質因素極大地影響了兒童的觀展體驗。比如,兒童面對放置在玻璃柜內的物件,表現出了發現、選擇、吸引、湊近、觀察等行為,但單純的標簽、展板等說明性文字與“隔空”的體驗不能有效實現博物館與兒童的“對話”與“交流”,難以加深他們對展品的理解。為此設置兒童易于理解的文本內容或預先發放“兒童專屬導覽單”“問題包”等外在物質引導因素,如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周六博物館”館方教育部篩選適合提問的展品,以局部顯示或設置問題尋找的形式來促進探究式體驗,見圖4。有利于搭建展覽傳達內容與兒童觀眾既有知識的橋梁。

圖4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尋物游戲
此外,本次展覽在2個月內開展了9場社教活動,對不同年齡階段兒童進行精準劃分,結合展品開展動手式的探索體驗活動,鼓勵兒童與博物館展品進行更深入的互動,加深兒童對展品的認知發展和情緒共鳴,構建與展品相關的個人意義。比如,在“懷舊陶瓷杯”活動中,兒童需要結合個人經驗,繪制專屬陶瓷杯,深入了解陶瓷杯在革命時期作為日常生活必備品的重要價值,深刻體會革命時期的光輝歷史與當時人們的愛國情懷。然而單一的社教體驗只強調單次活動的動手能力,對物的由表及里認知,還需要更多探索體驗方式的介入。如波士頓“憲法號”巡洋艦博物館孩子們除了參觀軍艦及探索海上生活和海洋歷史的互動博物館展品,可參與體驗19世紀真實水手生活——跪在甲板上擦地板,見圖5,通過此種方式對生活在“憲法號”巡洋艦上水手們困難之處有了深刻的認知,并對當時社會和軍事歷史有了更好的理解。

圖5 “憲法號”巡洋艦博物館
后續訪談也反映出,兒童在探索展覽時的參觀動線、展品選擇受到先前經驗、興趣和既有知識等個體因素的影響。在展覽中適當展出兒童在生活或學校學習中熟悉的畫面和展品,能夠有效增加兒童的觀展時長,增強兒童的觀展熱情與主動性。除此之外,博物館與學校聯合開發革命教育系列課程,建立兒童紅色文化數字化傳播平臺,為兒童提供觀展前的信息鋪墊,這將有利于提升兒童在紅色文化展覽中的探索式觀展體驗。
3.3 協作反饋的社交式體驗
事實上,展覽空間中的兒童有其自身獨特的社交網絡。心理學家維果茨基(Lev Vygotsky)提出的“最近發展區”概念說明了社會交往過程對學習的重要意義。在最近發展區內,如果采取適當的支持(或稱作“支架”“腳手架”),也就是由一個能力更強的同齡人或成人提供幫助,學習者就能達到更高的水平。[12]在此次調研中,大部分兒童的參觀過程都有家長陪同與交流。在訪談中,研究者發現,兒童與家長的溝通極為頻繁,一半以上兒童表現出對父母陪伴與同伴學習的積極反饋。當兒童的交流訴求被家長或同伴及時滿足,兒童的學習動機也會大大增強。而作為社交體驗的利益相關者,如檢票員、講解員、保安等工作人員的行為態度,館內的空間密度、標簽信息易理解性等都是輔助社交體驗的一部分。
積極的社會交往有利于發揮紅色文化教育引導優勢。從主觀因素看,博物館不僅應當鼓勵親子共同觀展,也應為家長提供與兒童一同觀展的支持。比如,配置親子說明牌或家庭指南,設置面向家長的“腳手架”式觀展貼士,引導家長與兒童圍繞展品展開有層次、有意義的深度對話,將展品的情感意義、物證價值、象征意義等有機結合,讓兒童在體驗中知情、懂情、怡情,增強愛國主義情感。如1946—1948年丁友燦在南山區一代堅持革命斗爭時使用的鋁鍋,通過物理屬性、實際功能與當下物質生活對比來強化記憶;從客觀因素看,家長、工作人員“腳手架”協助程度與同伴“合作式”社交互動服務形式起到正向調節作用。如“參與式”“角色式”“游戲化”“劇場式”等體驗方式,真正在實踐中用好紅色文化“活教材”。
3.4 深化記憶的延續性體驗
并非所有體驗都能同等地被記起,兒童在回憶事物時通常是有選擇性的。調研發現,本次展覽后的延伸教育能夠促進兒童對紅色文化進行長期性記憶。因此,博物館應考慮到兒童觀眾整體在體驗感方面的系統性和周期性,積極拓展展覽以外的教育體驗。其一媒介因素,博物館可以借助互聯網等,建設與兒童學習認知特征相適配的信息服務平臺。比如,寧波博物院微信公眾號為本次展覽特設“每日一物”“黨史問答”等欄目,并以兒童喜愛的長圖漫畫形式呈現。本次主題展還定期安排講解員將紅色戰役、紅色人物等紅色素材加以解說,見圖6,以兒童視角輸送更多紅色故事。

其二載體因素,博物館可以依托多元的物質載體,讓博物館體驗覆蓋到兒童的生活中。比如,寧波博物院地鐵專列以“地鐵里逛‘博物館’”這一全新的“走出去”方式,延展博物館體驗時空,讓兒童在公共空間中感受紅色文化氛圍。同時,寧波博物院也通過研發兒童常用的紅色文創衍生產品、打造紅色傳承的卡通IP形象等方式,見圖7,實現紅色教育在兒童日常生活場景的延續。其三服務因素,博物館可以從兒童認知視角出發,搭建“展館—學校—社區—家庭”的延伸服務體系,形成主題宣講、館校合作、社區宣傳等“以兒童為中心”的影響力驅動,協助兒童逐步構建起更為完整、系統的“紅色記憶”知識圖譜。

圖7 “三江潮涌”展的IP形象與部分衍生品
Fig.7 IP image and some derivatives of "Red Tide Rising" Exhibition
4 結語
本文聚焦“三江潮涌”展,結合觀察、用戶體驗地圖、照片引談的研究方法,力圖分析兒童在紅色文化主題展中的體驗,總結出兒童觀展體驗的四種類型:深化認知的感官式體驗、由表及里的探究式體驗、協作反饋的社交式體驗、深化記憶的延續性體驗,希望為之后紅色文化展覽的兒童觀展體驗研究與實踐提供參考。好的紅色文化展能夠鼓勵兒童尋訪紅色足跡、追尋紅色記憶、浸潤紅色思想,從而深化對祖國的理解與熱愛。然而紅色主題展是否能夠真正達到兒童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其關鍵并不在于展覽的規模與體量大小,而在于能否在展覽中圍繞兒童的認知能力、既有知識、學習方式與社交需求設置多模態的展覽體驗形式,聯合家庭、學校等多方力量,提供更具系統性的全周期紅色教育服務體系。
[1] 杜瑩.“5R”,搭建兒童在博物館學習的橋梁——情感互動視角下博物館的兒童展覽解讀[J]. 博物院, 2021(1): 94-100. DU Ying. 5R, a Bridge for Children to Learn in Museums: Interpretation of Exhibitions in Museums for Childr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Interaction[J]. Museum, 2021(1): 94-100.
[2] 王旖旎. 關于博物館體驗學習若干問題的探討[J]. 東南文化, 2020(5): 134-140. WANG Yi-ni.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Museums[J]. Southeast Culture, 2020(5): 134-140.
[3] 楊靜, 張嘉敏. 基于兒童認知的博物館交互體驗設計策略研究[J]. 包裝工程, 2021, 42(8): 57-62. YANG Jing, ZHANG Jia-min. The Design Strategy of Museum Interactive Experience Based on Children's Cogni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42(8): 57-62.
[4] 瞿子慧. 針對兒童認知的博物館圖像化信息平臺設計研究[D]. 上海: 東華大學, 2021. QU Zi-hui. Research on the Design of Museum Image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Children's Cognition[D]. Shanghai: Donghua University, 2021.
[5] 李茜, 毛天斌. 城市文化的傳承: 城市博物館的兒童認知構建[J]. 文藝爭鳴, 2015(11): 206-208.LI Qian, MAO Tian-bin. Inheritance of Urban Culture: The Cognitiv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 in Urban Museums[J]. Wenyizhengming, 2015(11): 206-208.
[6] 王杰. 基于兒童視角下的博物館教育活動研究[J]. 江西科學, 2019, 37(3): 456-464. WANG Jie. Research on Museum Education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J]. Jiangxi Science, 2019, 37(3): 456-464.
[7] MOSS P. Listening to Young Children: The Mosaic approach[M]. 2nd UK ed. edition. London: National Children's Bureau, 2011
[8] 李婉瑩, 袁姝, 董華. 兒童參與的服務共創設計模型[J]. 設計, 2020, 33(15): 82-85. LI Wan-ying, YUAN Shu, DONG Hua. A Design Model for Service Co Creation Involving Children[J]. Design, 2020, 33(15): 82-85.
[9] 付婧莞, 張書銘, 陸明. 為兒童服務的藝術博物館參與式設計——以美國俄克拉何馬市藝術博物館為例[J]. 裝飾, 2019(2): 74-77. FU Jing-wan, ZHANG Shu-ming, LU Ming. Participatory Design of Art Museum for Children: A Case Study of the Oklahoma City Museum of Art[J]. Art & Design, 2019(2): 74-77.
[10] DOCKETT S, MAIN S, KELLY L. Consulting Young Children: Experiences from a Museum[J]. Visitor Studies, 2011, 14(1): 13-33.
[11] 鄭晶. 游戲型教育模式構建在博物館中的應用探索——以青少年互動體驗展“大明都水監之運河迷蹤”為例[J]. 東南文化, 2021(3): 161-166. ZHENG Jing.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Based Education Model in Museums: Taking the Youth Interactive Experience Exhibition "The Lost Canal of Daming City Water Supervision" as an Example[J]. Southeast Culture, 2021(3): 161-166.
[12] 莎倫·E·謝弗. 讓孩子愛上博物館[M]. 于雯, 劉鑫, 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8. SHARON E. Shaffer. Engaging Young Children in Museums[M]. YU Wen, LIN Xin, Transl. Nan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YILIN, 2018.
Service Experience of Red Culture Theme Exhib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WANG Yan-yan1, GONG Miao-sen2, CHEN Chao3
(1.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Zhejiang Ningbo 315175, China; 2.Jiangnan University, Jiangsu Wuxi 214122, China; 3.Ningbo Museum, Zhejiang Ningbo 315199, China)
The work aims to study how the red theme exhibition of the museu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children's experience and cognition of red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shadow following and photo introduction were used to comb the user experience map. With the Ningbo Museum's "Red Tide Rising: Exhibition on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Ningbo from 1921 to 1949"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children's viewing behavior and the record of interviewees' feelings, the typ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d culture experience were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multi-dimensional experience wa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children's in-depth learning of red gene, which was conducive to children's learning of red culture in a penetrative way.Four types of children's experience are summarized, namely, sensory type of deepening cognition, exploratory type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 social type of collaborative feedback, and continuous experience of deepening memor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experience types are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museum's red culture exhibition to improve children's exhibition viewing experience.
children's perspective; red culture experience; Ningbo Museum; types of children's experience
TB472
A
1001-3563(2023)12-0250-07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12.027
2023–01–06
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19NDQN319YB);高等學校國內訪問學者教師專業發展項目(FX2020066)
王艷艷(1983—),女,碩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服務設計與社會創新、博物館兒童教育。
責任編輯: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