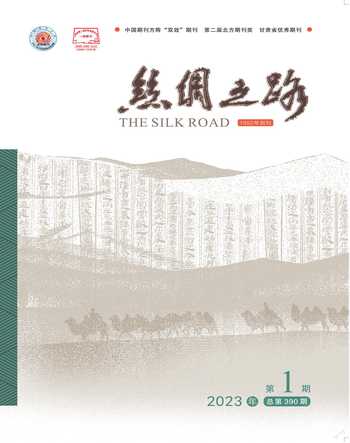敦煌懸泉置出土古紙考述
常燕娜



[摘要]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漢代古紙以麻類植物纖維為主,其數量眾多,產生時代跨越漢晉兩個歷史時期,時代最早的麻紙可追溯至西漢時期。這批古紙展現出我國古代造紙技術從早期澆紙法逐漸改良為抄紙法、從最初用于物品包裝逐漸成為書寫材料的發展趨勢。同時,簡牘作為當時的主要書寫載體,其在尺寸形制上的規定也成為紙張等其他書寫材料制作的標準。
[關鍵詞]古紙;敦煌懸泉置;造紙術;簡策制度
[中圖分類號] K875.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5-3115(2023)01-0143-08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過程中發現大量古紙。一直以來,敦煌懸泉置出土古紙尤其是西漢時期的紙張備受學界關注,關于造紙術的起源更是爭議的焦點。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400余件古紙殘片進行分類整理,筆者亦認為紙張在西漢時期就已經存在,這批古紙對我們了解造紙技術的演變提供了第一手實物資料。
《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中對這批古紙的形貌特征、時代、成分、用途等進行了初步分析判斷:“麻紙,460余件。根據顏色和質地可分為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褐色薄、白色厚、白色薄、黃色厚、黃色薄8種。紙上寫字者多為白色和黃色紙。時代從武、昭帝始,經宣、元、成帝至東漢初及晉,沿用時間較長,并與簡牘伴出,對研究紙的發展變化提供較多的實物資料。從殘留在紙面上的殘渣看,紙質主要用麻織物和很細的絲織物制作,用于書寫文件、信件及包裝物品。用于書寫者質細、光滑、較厚;用于包物者則很粗糙……”在這批紙張整理公布后,國內學者先后對此進行分析研究,也由此引發了關于紙張產生年代、造紙技術等問題的爭論。
按照發掘簡報記載,根據同出紀年簡和地層判斷最早的紙張產生于西漢早期。國內許多學者依據考古發掘簡報內容及相關檢測和研究工作,對這批紙張產生的時代等問題持有不同的觀點。陳淳和王菊花認為敦煌懸泉置遺址長期受風沙等環境因素的影響,以同出簡牘來斷代是不可靠的[1]。他們所提出的環境因素確實存在,暴露于風沙之下,對表層文物的斷代確實存在一定的干擾,表層文物在斷代上可能會出現一定的偏差。李曉岑對此也進行了分析,認為“第3層和第4層均是西漢層……這兩個層位并沒有受到非西漢層的擾亂,所出器物應該就是西漢時代的遺物。這明白無誤地表明,懸泉遺址第3層和第4層出土的紙確實是西漢時代的古紙”[2]。正如李曉岑依據根據考古發掘情況做出的判斷,在敦煌懸泉置深層發掘的文物包括紙張在內,是不會受到風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的,在西漢時期就已經有紙張出現是不可否定的事實。而王菊花在陳淳研究觀點的基礎上又認為出土的紙文書文字記載中沒有出現紀年,說明在漢武帝元鼎六年(前川)至東漢永初元年(107)的200多年間沒有紙張[3]。王菊花的觀點是基于將紙張作為書寫載體,與簡牘在同時期并用的情況之上。實際上,早期紙張可能更多是用于物品的包裝,隨著造紙技術的發展才逐漸與簡牘并用,直至取代簡牘最終成為主要的書寫載體。從大量的懸泉古紙的科學檢測中,不難發現這批古紙在造紙技術上的差異,這也說明了造紙技術是不斷探索改良的。因此,王菊花的這一觀點不符合造紙術的產生發展的規律,不能以此來證明東漢之前沒有紙張。
一、敦煌懸泉置出土古紙的制造時代
敦煌懸泉置出土紙張中有少量紙張存有墨跡。據考古發掘簡報記載,紙文書共有10件,9件為漢代紙張,1件為晉紙,并對這些紙張做了斷代[4]。本文擬根據紙張同出簡牘和地層,并從紙張尚存字跡書體對敦煌懸泉置出土有字古紙做簡要分析。
(一)西漢時期古紙
出土號為90DXT212④:3、4(圖1)紙張上書“細辛、薰力”,出土號為90DXT212④:5(圖2)紙張上書“付子”,圖3紙張上書“二人”,此三件殘紙同出土于一個地層,上面所書寫文字均為隸書。
90DXT212④:3、4和90DXT212④:5上分別書寫的“細辛”“薰力”和“付子”皆為中藥名,紙張褶皺明顯,應為包裹物品痕跡。出土號為90DXT212④:14(圖3)紙張殘片上寫隸書“二人”兩字,是否還有其他文字不可知,但從這兩字來看,紙張所書內容應是相關人數的記載,內容上可以歸為文書類。
出土號為Ⅱ90DXT0114③:608(圖4)紙張上書兩行草書,第一行文字為“愿偉君”,第二行文字為“不可□”。出土號為Ⅱ90DXT0114③:609(圖5)紙張上書兩行草書,第一行文字為“□持書來”,第二行文字為“置嗇夫”。①
關于Ⅱ90DXT0114③:608紙張的用途,結合懸泉置出土帛書簡牘上的文字記載可做判斷。與Ⅱ90DXT0114③:608紙張在同一探方及層位出土有帛書一件,其中一面文字內容為:
不可忽こ②置舍所圣人こ不可已強飯自こ愛こ幸
甚萬幸こ甚こ謹因趙偉君奉書再拜
白·知君謝子恩敬君強飯自こ愛こ
知君病偷矣
(Ⅱ90DXT0114③:607)
此件帛書上同樣寫有“偉君”“不可”字樣,雖然紙張與帛書在同一探方同一層位出土,但紙張上的“偉君”和帛書上的“偉君”是否同為一人不可考,筆者只能以此來判斷紙張出現的文字大概是一封書信的殘件。
另外,在敦煌懸泉漢簡中“偉君”一詞也多有出現,均作為人名來使用。如:
孫昌叩頭白記
□□勉力諷誦請偉君坐前
(Ⅰ90DXT0109②:63)[5]
傳移□□□行□
偉君足下□者
□□□□□
偉君足下□者□
(Ⅱ90DXT0113③:62)
雖然上列簡牘有殘缺,簡上的文字亦有缺失,但從簡牘釋文內容來分析,“偉君”也應是作為人名出現,簡牘記載的內容也有可能是書信往來的記錄。結合上述帛書和簡牘的文字內容進行推測,圖4紙張書寫的“偉君”應為人名,這張古紙可能為書信殘件。
Ⅱ90DXT0114③:609紙張上書的兩行文字,一行文字為“持書來”,其中“持”字左上稍有殘缺。懸泉漢簡中有枚草書簡“持”字做 (Ⅱ90DXT0111②:8)[6],與這張古紙上“持”字的書寫極為相似。從當時草書的寫法看,紙張上“持”字上端殘缺才導致字體不完整。殘紙另一行文字發掘簡報中釋為“致嗇”。但根據“嗇”字上下部殘留筆跡來看,似為“置”和“夫”字,“置嗇夫”作為官職名稱在敦煌懸泉漢簡中也是常見的。我們根據殘存的兩行文字推測,圖5紙張書寫內容為文書類,很有可能是某位置嗇夫所書或傳遞給另一位置嗇夫的文書紙殘片。
根據同地層出土簡牘的紀年來看,以上5張發掘于敦煌懸泉置遺址的有字紙張在時代上都屬于西漢時期。由此可知,在西漢時期已經有紙張產生,而且早期紙張不但用于包裝,也開始嘗試作為書寫材料來使用。
(二)東漢初期古紙
出土號為Ⅱ90DXT0111①:469(圖6)紙張根據同地層出土簡牘的紀年來看,為東漢早期的紙張殘片。上書兩行文字,一行文字為“巨陽大利”,另一行文字為“上繕皁五匹”。從所書文字內容看,這件紙張記錄了絲織品的等級和數量,此件紙張為包裝用紙或為絲織品記錄的標識。
(三)西晉古紙
出土號為Ⅰ91DXT0409①A:1(圖7)紙張上書“□□輒往□”,出土號為Ⅰ91DXT0409①A:2(圖8)紙張上書7行文字:“以下即詣”“□既得表”“□解僑朱”“一日之恩今”“此鄙者今”“府內安隱”“恐惶恐白”。根據同地層出土簡牘的紀年以及書寫字體來看,這兩張殘紙應為西晉時期的書信殘件,原應為一張,因殘損過甚而破裂為兩張,文字內容上亦有缺失。這件紙張上所書文字達30余字,書寫文字數量的增加,一方面說明紙張用于書寫載體已經開始普及,另一方面也說明紙張工藝的提高已經滿足其作為書寫載體來使用。
二、敦煌懸泉置出土古紙的用途及來源
在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古紙歷史時期跨越漢晉,時代最早的紙張可以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定為西漢時期。懸泉紙張殘片共有400余件,上面書寫文字的卻極少。僅從有書寫文字的紙張來判定,早期紙張有用于包裝,也有用于簡單的書信來往和文書傳遞。
早期紙張更多是用于物品包裝,如圖1和圖2,紙張書寫文字均為中藥名,褶皺明顯。圖2和圖6紙張有明顯的形狀輪廓,字體書寫方向可基本判定為斜向書寫,這比較符合用方形紙張折對角包裹物品后,在包裹紙張外部書寫物品名來做標識的習慣。而尺寸較大的殘紙,褶皺更為明顯,且褶皺縱橫交錯沒有規律,這都有可能是作為包裹或者襯墊物后留下的印跡。在這批紙張中有一件殘紙上粘有少量漆器殘片,推測這件殘紙當時用來包裹漆器,長時間受所處自然環境的影響,與殘紙粘連一起。這件殘紙所殘留的文物印記,與灞橋紙用于包裹銅鏡后紙張表面殘留銅銹的情況相似。
除此之外,如前文所言少量紙張可初步判斷為用于書信往來和文書傳遞,這類紙張只占極少部分。書寫文字的紙張占比極少且存字不多,這一現象說明早期紙張并未普遍使用于書寫,這與造紙技術發展情況密切相關,當時紙張并未達到可以取代簡牘作為主要書寫材料,甚至還未出現簡紙并用的情況。
紙張一旦作為新型包裝或書寫材料開始使用,必然有一定量的生產。在敦煌懸泉置遺址考古發掘大量古紙,其來源也可作為古紙研究的內容來進行探討。
早期紙張生產技術掌握在內地,由內地生產再輸入邊塞地區有極大的可能,但也不排除漢代邊塞地區也已經具備紙張生產的能力。首先從內地生產運輸成本相對較高,其次就目前考古發掘來看,西北地區發掘出大量漢代早期紙張,這雖與當地干燥的環境氣候易于保存下來有關,但同時也說明當時可能會有一些紙張制作工坊存在。
河西地區在漢代屬于邊塞地區,應漢代行政管理以及軍事防御的需求,從內地征集大量的戍卒,同時也從內地遷入了大量的人口。除了行軍戍備,在這些遷移人員中也會有一定手工制作技能的人員來滿足生活生產需要。在內地人員往邊塞流動的同時,也可能從內地帶來了當時先進的技術,加之當地有可實現造紙的原材料,所以在河西邊塞地區制作出早期紙張并非全無可能。在新疆等更為邊遠之地也出土有少量漢代紙張,這些早期紙張也有可能是由河西生產后傳入新疆等地。在甘肅西和縣,現在仍有以家庭作坊生產形式為主的麻紙制作手工坊,手工制作工藝形式傳承年代久遠。這些手工作坊是否與早期紙張有一定關聯現在已無法考證,但我們也可由此僅作推測,在漢代河西地區可能就有古紙生產地或者小型手工作坊。適宜的保存環境,是西北邊塞地區發掘出早期紙張的必要環境條件,同時生產原材料、人員、技術和工坊場所等要素,也可以成為生產早期紙張所具備的條件。
三、敦煌懸泉置出土古紙與造紙技術的改良
潘吉星對傳統紙張的定義為:傳統上所謂的紙,指植物纖維原料經機械、化學作用制成純度較大的分散纖維,與水配成漿液,使漿液流經多孔模具簾濾去水,纖維在簾的表面形成濕的薄層,干燥后形成具有一定強度的由纖維素靠氫鍵締合而交接成的片狀物,用作書寫、印刷和包裝等用途的材料[7]。在這個定義中,潘吉星也強調紙張在原料上必須是使用植物纖維。同樣許鳴岐等在定義“紙”的概念時,也強調“植物纖維原料”[8]。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對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紙張殘片進行了抽樣檢測,通過顯微鏡觀察,其造紙成分主要是麻類植物纖維無疑,這一點也與西北地區歷次考古發掘出土的古紙相同。同時在顯微鏡下可見這些紙張的纖維雖有不同程度的加工,但都經過了切斷、漚煮和舂搗的過程,纖維均有不同程度的分絲帚化。由此可見,至少在西漢時期,人們已經開始運用麻類等植物纖維來制作紙張,在敦煌懸泉置發現大量西漢古紙也是當時社會生活的歷史遺存。
麻類植物是我國常見的植物種類,因此麻類植物纖維很早就成為古人手工制品中較為易得的原料。在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其他文物中,以麻類植物纖維為原料的除了紙張之外,還有麻鞋、麻布等文物。這些文物為漢代邊塞戍卒的日常用品,其紡織技術及編織水平較高。可以看出,麻類植物纖維在漢代是較為易得并且廣泛使用的材料。簡便易得又廉價的材料,是造紙生產的基本條件之一,這也使紙張的推廣使用實現可能。
《后漢書·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9]這種工藝制作出來的紙張也被稱為“蔡侯紙”。與《后漢書》記載的蔡侯紙不同,西北地區考古發掘的西漢古紙在原料上使用的主要是麻類植物纖維,包括麻布、麻繩等廢棄的麻制品,而未見“樹膚”“魚網”成分。由此可見,至少在西北地區發掘的早期麻紙成分相對單一。至蔡倫時對造紙技術進行改進,同時對造紙成分也進行了調整,以提升紙張的質量,傳世文獻中對造紙原料的記載應是基于蔡侯紙的使用材料。在整理懸泉古紙過程中,尚有肉眼可見未打散分離的麻布及麻繩殘塊,這也是早期古紙制作技藝尚不精湛的實證。
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古紙雖在材料使用上都為麻類植物纖維,但在超景深顯微鏡下,可觀察到這些紙張在制作工藝上還是有一定的差異。先后有多位學者也對這批古紙做了科學檢測分析,以此來對早期紙張的造紙工藝技術進行探究。韓飛通過對這批古紙的厚度、色度、定量等進行分析,認為早期紙張在造紙技術上尚不成熟[10]。李曉岑通過對樣品的實驗分析,觀察到這批古紙從早期的澆紙法逐漸發展為抄紙法,并有部分紙張使用淀粉施膠的技術,這些在造紙工藝技術方面都是巨大的進步。
筆者綜合紙張纖維檢測等分析結果,將這批紙張大致歸為三類,以方便對這批紙張的造紙工藝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究:第一類紙張在工藝上比較粗糙,纖維束較明顯,這類紙張因為纖維疏松,因而較厚,紙張呈暗黃色,并在一些紙張上甚至可觀察到尚未打散的麻布、麻繩殘留。第二類紙張纖維分散度較好,但仍有少量尚未打散的纖維束,紙張色較比前一類淺,厚度也較前一類薄。第三類紙張纖維分散度較好,纖維組織結合緊密。紙張在顯微鏡下可見大量顆粒狀物質,在工藝上應是加入了滑石粉等物質,紙張纖維的緊密度增加,這類紙張色較白,明顯更為薄透,紙張有明顯的抄造痕跡,甚至少量紙張可通過透光觀察到簾紋。
這些紙張制作工藝的差距呈現出造紙技術不斷改進發展的情況,據此可對紙張產生的年代加以推論:在傳世文獻記載中,蔡侯紙從出現即作為簡帛的書寫替代品,而適于書寫的紙張的產生必定要經歷一個不斷改進的過程。也就是說至少在西漢時期,已經有較為粗糙的紙張出現,并且在實際使用過程中,當時的人們也在不斷改進造紙方法以提高紙張的質量。在蔡倫之前,紙張就已經進入改良的階段,只是蔡倫又繼續推進了造紙技術的發展并且取得較高的成就。我們也可觀察到帶有文字的少量紙張都書寫在纖維組織結合較為緊密、分散度較高的紙張上面,書寫墨跡與紙張纖維貼合較好,而在粗糙的紙張上并未見書寫文字或墨跡。這一現象說明早期造紙技術也是在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們才開始意識到紙張可以作為新型書寫材料來使用,進而對紙張的制作工藝進行提升,增加紙張的平整度以滿足書寫的需求。
四、敦煌懸泉置出土古紙與早期古紙的尺寸
如同漢代簡牘的尺寸有一定的規定,早期紙張產生的時候,在幅面大小上也應該會有一定的規定。這種幅面的大小,會和當時造紙的模具、技術水平有關,同時作為新型的書寫載體,可能受到了當時作為主要書寫載體的簡牘的影響,即在尺寸上與竹木簡牘保持一定的相似性。并且從實用性角度來說,紙張制作時有相對固定的尺寸,在一定程度上便于紙張的制作、整理和存放。
在這批紙張中,沒有保留下來完整的,因此關于早期紙張的尺寸也是歷來討論的焦點之一。劉仁慶對古紙的尺寸推測時認為:“從西北地區墓葬中清理出來的多種西漢古紙,通常紙的殘片幅面都在20厘米以下,紙的原有尺寸不詳。如果把古書記載和出土實物結合起來考慮,漢代的尺牘為一漢尺(23.70厘米),從而推測漢代紙的尺寸一般都不大。”[11]劉仁慶對古紙的尺寸推測雖不夠全面和詳細,但是依據簡牘尺寸來推測這一方向是正確的。
其實在劉仁慶之前,潘吉星就結合漢代簡牘的形制尺寸對早期古紙的幅面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觀察研究和理論推測。潘吉星實測魏晉古紙的直高多在24-24.5厘米,由此推測魏晉古紙應是沿襲漢代書寫材料尺寸。而漢紙會受漢代簡冊書籍制度的影響,直高可能為1漢尺,即24厘米左右。潘吉星還參照漢代簡牘、魏晉寫本等實物的尺寸,復原早期使用的抄紙器直高24-25厘米、橫長35-50厘米。
早期的造紙器具按照潘吉星推測為長方形,并且在尺寸上參照簡牘的尺寸形制是科學的。漢代古紙特別是成為書寫載體后必定會受當時書籍制度的影響,從而在直高上會依據簡牘的尺寸。簡牘編連成冊鋪展后呈長方形,紙張按照這個形態制作也是合理的,這一點也可以從后期紙張幅面的沿襲上來證明。從敦煌懸泉置出土紙張中挑選可以進行印證的材料時,沒有相對完整邊角的紙張對于研究漢代紙張尺寸大小,特別是紙張直高的研究沒有參考價值。筆者對懸泉置殘紙進行篩選,挑選出可辨識邊角的殘紙進行測量,以此來推測漢代古紙的尺寸。
在懸泉置考古發掘簡報上提到編號為90DXT416④:1的一張殘紙。這張殘紙雖有殘缺,但四邊相對完整,基本為長方形,殘長34厘米寬25厘米,因此被認為是一張紙的尺寸③。這張古紙的幅面尺寸是符合潘吉星的推測的。在敦煌懸泉置出土的這批紙張中,還有三張麻紙雖有殘缺,但基本可見紙張的原始形狀,也是可以作為古紙尺寸推測的印證材料。
出土號為90DXT114③:201的紙張殘長28厘米、殘寬21.2厘米。出土號為90DXT114③:200的紙張殘長27厘米、殘寬22.5厘米。出土號為90DXT114②:261的紙張殘長21厘米、殘寬16厘米。這三張殘紙尺寸上都有一個相近值,分別是21.2厘米、22.5厘米、21厘米,我們如果把這三個數值視為紙張的直高,那么三張漢紙的直高相近并且接近1漢尺。三個數值的差異除了與紙張殘缺有關,主要是和紙張的褶皺程度有關。紙張如在平整狀態下,直高基本上可以達到1漢尺,因此潘吉星所復原的抄紙器的直高是基本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說紙張在制作時會參照簡牘的長度作為直高。
但上述三張漢代古紙的寬度卻差別較大,因無完整的紙張可做考證,筆者只能對此進行部分推測。如同簡牘可根據書寫內容的多少、使用用途等的不同,編連后簡冊的寬度也會有較大差異。紙張相比簡牘來說,可塑性更強,可根據包裝物品體積的大小或實際需要而進行剪裁,更容易改變幅面的大小,這對證實漢代古紙的尺寸會較大的影響。截至目前對漢代古紙寬度的推論是缺乏實證的,潘吉星也只是根據操作的可行性推測早期紙張的寬度范圍。
在紙張出現之前,竹木簡牘是記錄文字最重要的載體,我們也以此來對紙張幅面進行了推斷。但除簡牘之外,同時作為書寫載體的還有帛書等材料,其中帛書也就是范曄在《后漢書》中提到的“縑”。帛書與紙張在形狀上均具有扁平化、可塑性強的特點,并且在制作材料上也有相似的特性,不得不說紙張的產生和帛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我們在探究紙張的尺寸時,是否也可從帛書材料中獲得印證信息,在對漢代帛書進行整理探究后,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目前已知居延遺址、長沙馬王堆、敦煌馬圈灣、敦煌懸泉置等遺址出土有漢代帛書,這些帛書大多殘損,能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信息的是敦煌懸泉置出土的一件完整的書信帛書和長沙馬王堆帛書。敦煌懸泉置出土的這件帛書,內容為私人書信。帛書長23.2厘米、寬10.8厘米,直高正好與1漢尺接近。而馬王堆帛書在書寫文字時更是畫有邊欄以統一尺寸。資料記載:“馬王堆漢墓帛書,共計十萬余字,五十余種,分別抄寫在寬四十八厘米的整幅帛和寬二十四厘米的半幅帛上……”[12]從馬王堆帛書的尺寸上來看,亦有直高為1漢尺的帛書。漢代帛書在直高上與漢代簡牘的長度一致絕不是巧合,而是在制作時有意為之。漢代最重要的書寫載體是簡牘,但無論是簡牘、帛書、紙張,在尺寸上均呈現出相似性,這就說明至少在漢代時期,在書寫制作時尺寸上都有要遵循的標準,即當時的簡策制度。
甘肅、陜西、新疆、內蒙古等地的漢代墓葬和邊塞遺址都先后發掘出土有漢代古紙,但如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數量眾多的古紙還是首次。正是因為數量多,造紙工藝呈現出多種類型,這批古紙在研究紙張的產生和發展等方面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原始資料。同時,敦煌懸泉置出土古紙的尺寸也反映出漢代簡策制度對紙張等其他書寫載體的影響。
[注釋]
①《甘肅敦煌漢代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中釋為“致嗇”,參見《文物》2000年第5期,第14頁。
②重文號,表示與前一字相同。
③參見《文物》2000年第5期,第15頁。
[參考文獻]
[1]陳淳.虛妄與荒唐的“西漢紙”——讀《中國古代造紙史淵源》一書[N].文匯讀書周報,2002-07-19.
[2]李曉岑,王輝,賀超海.甘肅懸泉置遺址出土古紙的時代及相關問題[J].自然科學史研究,2012,31(03):280.
[3]王菊花.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M].太原:山西出版社,2006:75-76.
[4]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敦煌懸泉置遺址發掘簡報[J].文物,2005,528(05):14.
[5]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一)[ M].上海:中西書局,2019:14.
[6]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二)[M].上海:中西書局,2021:184.
[7]潘吉星.中國造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5.
[8]許鳴岐.中國古代造紙術起源史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1991:51.
[9]范曄.后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5:2513.
[10]韓飛.從紙的一般性能看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麻紙[J].絲綢之路,2011,(04):29-31.
[11]劉仁慶.論中國古紙的尺寸及其意義[J].中華紙業,2010,(17):83.
[12]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一)[ M].北京:中華書局,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