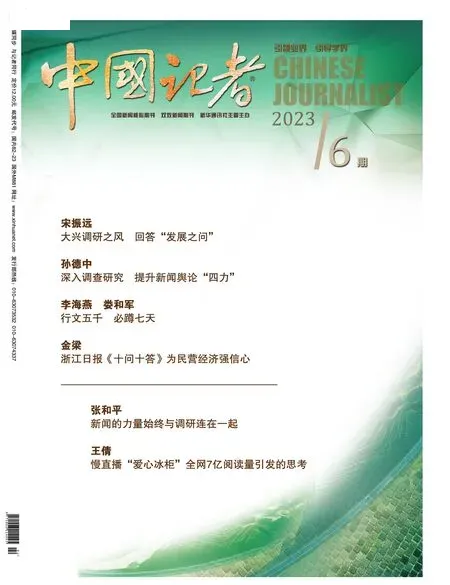民營經濟調查報道的四個講究
調查研究與經濟報道有著天然的緊密聯系。20世紀八九十年代,著名學者費孝通以多次田野調查而寫就的《小商品大市場》《家底實創新業》《筑碼頭闖天下》,讓世界看到浙江蓬勃興起的民營經濟。此三篇為學術文章,其深入淺出的說理、通俗易懂的文筆,亦成為不可多得的傳播佳作。
同樣,學者吳敬璉于1993年至2004年間,對浙江民營經濟發展進行多次調查研究,以實例論證“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必要性”,其調查研究的諸多成果,亦成為流傳甚廣的至理名言。
從眾多學者深耕民營經濟調查研究可以證明,對經濟現象和內在機理的捕捉、觀察、梳理、溯源、探究、論證,都離不開深入細致、腳踏實地的調查研究。學界如此,新聞界更應如此,這既是對黨一貫堅持調查研究優良傳統的繼承,也是新聞人踐行“四力”科學方法的指引。可以說,調查研究更應該是經濟報道的基本功,沒有調查就沒有經濟報道。
一、當前民營經濟報道存在的問題
一直以來,對民營經濟的調查研究,是學界相當感興趣的重點,亦是經濟報道的熱點。然而,當前對民營經濟的報道仍存在如下問題:
(一)“大而全”較多,“小而精”欠缺
經濟報道包羅萬象。從大處看,它瞭望宏觀經濟大勢,涵蓋國民經濟各類支柱產業,延伸至城建、交通、港口、全球貿易等重磅領域;從小處看,它觸摸民生衣食住行各個方面,人間煙火氣的些微波動都可能牽連整個社會的波瀾壯闊。
站在全局高度展現宏觀經濟的潮起涌奔,是當前重大主題報道較為常見的方式,而觸摸企業個體,尤其是小微企業、個體戶全生命周期的細致報道,則相對稀缺。其實,這類“小而精”的報道不僅能從細微處見真章,而且能以更深邃的視角指向新聞人觀察經濟、呈現經濟、探究經濟的獨特方式,把大時代中經濟體變遷的客觀事實與內在本質,盡可能準確地傳遞給受眾,有著“大而全”報道所不具備的縱深度。
(二)“盆景和花團”較多,“后院和角落”欠缺
經濟報道中,“盆景和花團”固然要擺出來,給予經濟發展以榜樣的力量、信心和底氣,但也要繞到“后院和角落”里仔細觀察、認真傾聽,去揭開蓋子,探究表象背后的內里。一篇有思想厚度的經濟報道,必然是以問題為導向的報道,在“后院和角落”里發現問題、揭示問題、研究問題,是新聞人做調查研究最直接的在場證據,通過細致的采訪和涉及關鍵意義的細節,可以呈現不必用過多言語去探求的真相。
當前,在部分認知里對“后院和角落”的采訪有顧慮、有退縮。但志不求易、事不避難,新聞人的使命職責所在,就是察實情、聽實話、收實效,既要到經濟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采寫典型,又要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查找真相,在“后院”采訪清楚了,才能更好地為經濟發展鼓與呼。
(三)“急就章”較多,精耕細作欠缺
經濟報道與其他類型的報道一樣,在移動互聯時代,新聞簡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在短新聞“快”的驅動下,本以洞察和發現見長的經濟報道,亦陷入淺薄之境。在企業走馬觀花走一遭,拍段短視頻推送,就完成新聞報道;拿部門通稿上的數據抄一抄,或做成長圖,就算一篇經濟稿;把各地材料復制粘貼一下,就組成經濟發展“新氣象”。誠然,簡潔明了的短視頻可以瞬間擊穿經濟原理與大眾認知之間的“次元壁”,成就一個個爆款。但任何一位負責任的新聞人都會深思:我們的爆款,不僅是一時之快,更應在任何時候閱讀都會覺得有價值,都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
顛撲不破的真理,依然是新聞業那條古老的原則:精耕細作地挖掘經濟現象背后的內核、機理,據實據理地呈現問題、矛盾,讓經濟報道富有耐力、張力。這需要拿捏快與慢的節奏、處理淺與深的比例,體現經濟報道的格調與思想。
二、對民營經濟的調查報道要有講究
今天,我們再一次倡導“掌握調查研究這個基本功”,亦是在重申“新聞精品”理念,只有持續不斷的內容生產力,才是新聞業長青的基石。民營經濟報道的內涵起于精準切入、深度打磨,使新聞性與專業性同向聚合。
(一)在全局視野中找到問題切入點,體悟小微企業切身之痛,讓民營經濟報道更有力度
于地方媒體經濟報道而言,調查研究的著力點,首先須解決“外行看不懂、內行不愿看”的問題,其迫切性比經濟專業類媒體更甚。我們力求使新聞性與專業性同向聚合。
“看準了的東西就堅決報道,就敢于獨立地負責。”從1980年率先報道“離土離鄉、務工經商”的農村改革開始,溫州日報就敢于為民營經濟新突破搖旗吶喊。在優良傳統指引下,我們堅持經濟報道要敏于發現問題、敢于觸碰問題,深入調查研究,激蕩思想火花。
2019年5-6月,我們抓住中小企業發展困境的問題追蹤報道《一家小微企業的“1000萬之困”》,是一組在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大政方針下,直面小微企業發展痛點、精準捕捉社會公共議題的經濟系列報道。從小微企業為何邁不過“年產值1000萬元”這道坎切入,整組報道的“魂”在于三個自省,即企業對創業創新如何進行到底的自省、政府對營商環境如何優化的自省、社會對民營經濟“兩個健康”如何發展的自省。
發出叩問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我們與相關部門合作,發揮媒體融合所長,將經濟報道延展為一系列新聞行動。不僅在線上引發超話、問答、熱議,而且在線下舉行座談、互學、共商,參與企業達2000多家,并組建專家團隊、對接金融扶持、搭建服務平臺,推動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支持民營企業“內創業” 助力高質量發展的實施意見》,實實在在地解決了部分企業難題。


(二)從剛性數據中找到柔性共情點,共商危機之下民企突圍,讓民營經濟報道更有溫度
深融時代,我們在探求地方經濟報道的全媒體切口時,既秉持嚴謹客觀的新聞傳統,又充分調動讀者的共情共鳴。
2020年2-5月,我們深入一線,歷時3個多月踏訪多個產業和中小微企業,選取外向型經濟之典型的溫州眼鏡產業為特寫對象,推出通訊《甌海眼鏡逆境中“破鏡重圓”》一文,以民企在逆境中奮斗、奮進之舉,著力刻畫全球疫情下中國企業堅韌不拔、砥礪前行的縮影,對外釋放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穩中向好的信心與決心。
采訪中,我們一次次走進企業,記錄員工到崗、生產線開工、直播賣貨、新產品出廠的點滴變化,為企業終于發出一車貨而開心雀躍。
正是從共情起筆,將萬千艱辛匯于筆端,讓讀者從字里行間感受中國經濟的精神內核,使特殊時期的經濟報道有了特別的暖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調研時所言:“中國的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有活力、有靈性,有一股子精神,這么大的疫情發生了,我們的中小微企業還在迎難而上,還在自強不息地發展。”
(三)拓深思想,挖掘時代主題與民營經濟報道“交匯點”
正因為在基層、在民營經濟、在柴米油鹽與人間煙火氣中間,所以經濟生活的每一次脈動,都可能隱藏著熱點訊息;小微企業的每一次掙扎,都可能預示著宏觀調控;產業更新的每一次波折,都可能孕育著新生力量……在這方民營經濟熱土中,做深做足做好地方經濟報道,更需要去調查研究、挖掘深度、貼近群眾,力求與時代主題交相輝映。
2015年,民營經濟報道在宏觀大背景中立足于更深層次著力點。當此際,一些人把溫州發展過程中產業低小散、實業空心化、資本熱錢化等問題,歸因于“溫州模式”衰敗過時,以此來否定“溫州模式”。
我們在基層調研與深思之后發出叩問:在當下及將來,“溫州模式”是否仍具有價值?
不回避、不敷衍,以千鈞之力深挖問題根源。秉持這一原則,我們于2015年5月、“溫州模式”見諸報端30周年之際,策劃推出《潮起甌江競奔流——再看溫州模式》重大主題報道,用溫州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作答“溫州模式創新與發展”的時代命題。在激發社會大討論中,“溫州模式”的價值被進一步挖掘——其本質是民本經濟、精髓是市場經濟、基石是實體經濟、政 府治理是有限有為有效,這正與改革開放精神相契合,和新發展格局下的中國道路相一致。
(四)貼近群眾,挖掘人間煙火氣與民營經濟報道“交融點”
新聞界前輩范敬宜先生曾說:“寫經濟建設、經濟生活的變化,一定要著眼于那種靜悄悄發生的、不為人們注意的,但一經點破之后會使人恍然大悟的事情。”
這些年,我們一直希望能采寫好貼近群眾的人間煙火氣,把繁華市井背后的柴米油鹽講給大家聽,著眼于那些靜悄悄的變化,看似細微,卻讓讀者在平凡生活中體會靜水深流的愛與力量。
在浙江省“縣縣通高速”的最后一段——文成—泰順高速公路通車現場,我們記錄下106歲老人夏祿第一次乘車上高速公路去泰順縣城;在鹿城區南郊街道安置房摸文現場,我們把在外過渡已10年的錢嵐一家,舉著鑰匙開懷大笑的樣子定格在鏡頭里;在長三角一體化國家戰略中,我們將視線投向交通暢達,溫州人刷著溫州市民卡就能乘坐滬杭寧地鐵,體驗著最切實際的“雙城記”;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中國(溫州)青年科學家峰會等全球盛會中,我們循著“為天下謀大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核心理念,對外傳播浙江民營經濟好故事。
最好的新聞是真實,最深的思考是求真,這與調查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恰恰統一,正是經濟報道始終追求的初心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