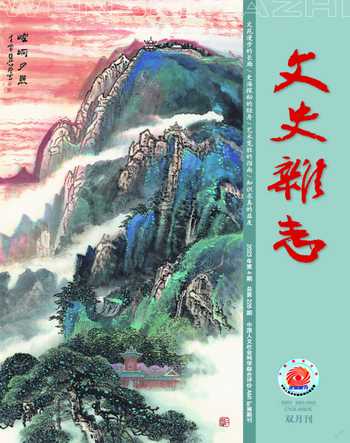周瑛與第一部詞譜《詞學筌蹄》
謝桃坊



摘要:
《詞學筌蹄》八卷,明代周瑛編著,選詞調一百七十七,詞三百余首。每調列圖為譜,作為填詞的格律規范。此編參照宋人編唐宋詞選集《草堂詩余》之作品,以調分編,詞題系于詞后。近世《續修四庫全書》收入此編抄本,始為詞學界所關注。它雖然存在諸多錯訛,但為中國第一部詞譜,曾開創明清詞學整理詞體格律之途徑,故在詞學史上具有重要的首創意義。
關鍵詞:
周瑛;林俊;詞學;詞譜;填詞;律詞
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學者周瑛編著的《詞學筌蹄》八卷,今傳之清初抄本原藏上海圖書館,于1998年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詞譜著錄,2014年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此本版框高212毫米,寬300毫米,藍格通行,每半頁10行,每行20字。編者周瑛原序于弘治七年(1494年)。林俊序于弘治九年(1496年)。其選調177,詞353首,分調編排。每調先列圖為譜,以圓圈(○)表示平聲字,以方框(□)表示仄聲字,分句用小圓圈,前后段之間空一格。以名家之作或流行之詞為譜例,詞后小字標注詞題,詞下注作者名,前后段之間以圓圈隔斷。每調選一詞或數詞為譜例。周瑛編著之旨是“使學者按譜例填詞”,故此編實為中國第一部詞譜。此編名《詞學筌蹄》,此“詞學”是指填詞規則。《莊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蹄”借指達到目的所使用的工具或者手段。周瑛希望學習填詞者以其所編之詞譜作為填詞的工具。此編的問世,為考察詞體格律的整理過程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文獻資料,是詞學史上的重大發現;其所體現的詞學觀念,參照之詞籍,存在之錯訛,以及在詞學史上的意義,茲試作探討。
一
周瑛,字梁石,號翠渠,生于明代宣德五年(1430年),福建莆田人,景泰四年(1453年)鄉試中式,甚得主司聶大年賞識,成化五年(1469年)進士,知廣德州(安徽廣德),成化十四年(1478年)任南京禮部儀制司郎中,繼為江西撫州知府。弘治元年(1488年),他因吏部尚書王恕薦,起為四川參政,尋轉四川右布政使,此后服母喪,遂請求致仕,卒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周瑛于理學深有理解,認為:“學當以居敬為主,敬則心存,然后可以窮理。自《六經》之奧。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窮。積累既多,則能通貫,而于道之一本,亦自得之矣,所謂求諸萬殊而后一本可得也。”[2]因此其學識極為淵博,鄭岳記述:
瑛豐神癯古,其學不專于該博,而于天文地志,造化物理,皆嘗究心體索。為文渾深雅健,有根抵。詩格高古。字畫初學晦翁,變為奇勁,應酬至老無倦意。所著有《經世管篇》《律呂管篇》《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蓍龜》。晚年尤注意《周易參同契》作本義,屢加刪定。詩文有《翠渠類稿》若干卷。[3]
今其著述存《翠渠摘稿》八卷,《詞學筌蹄》八卷。周瑛自弘治初年任四川右布政使時期與蜀昭王之關系密切,其《詞學筌蹄》于弘治七年(1494年)在蜀中編成,蜀王府教授蔣華和蜀士徐樀山參加編訂工作。周瑛序云:
詞家者流出于古樂府。樂府語質而意遠,詞至宋纖麗極矣。今考之,詞蓋柔間濮上之音也,吁!可以觀世矣。《草堂》舊所編,以事為主,諸調散入事下。此編以調為主,諸事并入調下,且逐調為之譜,圜者平聲,方者側聲;使學者按譜填詞,自道其意中事,則此其“筌蹄”也。凡為調一百七十七,為詞三百五十三,厘為八卷。編錄之者,托蜀府教授蔣華質夫;考正之者,則蜀士徐樀山甫也。[4]
自南宋滅亡之后,由于詞樂的散佚,詞因被視為“小道”而為學者所忽視,以致明代學者已難認識詞與音樂的特殊的關系。周瑛僅能從純文學的觀念而認為詞體之源是出自漢魏樂府詩。周瑛的詩文集內存其擬古樂府題之作《有所思》《上之回》《艾如張》,原注“樂府自漢始,詩詞之變,此其最古者”。其存詞九首,標明“詞調”,原注“此樂府之變”。詞為樂府之變,這認為二者皆為音樂文學,但樂府詩是以樂從辭的,而詞是以辭從樂的;它們配合音樂的關系是不同的。關于樂府詩與詞的體性,周瑛以為樂府詩語言質實而托意高遠,詞則發展至宋代達于纖麗之極,這見到詞體的艷科性質。他還認為詞的此種性質同于春秋時期的“鄭衛之音”。春秋衛地桑間、濮上為男女幽會之處,而詞體文學亦多表現男女私情,故由此可以觀察到世道民風。周瑛的這種認識否定了南宋以來關于詞體的“復雅”與“尊體”的傾向,應是進步的詞體觀念。中國詩論中的“言志”與“性情”說的影響深遠,形成牢固的詩教觀念。周瑛關于詞的創作本質則以為是“自道其意中事”,這特別突出填詞不同于詩,以表現創作主體的思念、意念中的對事物的感受,此乃個人情感的真實。宋人以為詞人張先詞中表現的是“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故稱他為“張三中”[5]。周瑛所說的“意中事”應是對宋人說的“三中”之概括,是由對詞的體性引發的必然的結論。今存周瑛之《翠渠摘稿》乃部分之詩文,佚散甚多。他是詞人,茲錄其詞三首:
臨江仙·書懷
高閣日長人語靜,風鈴時動簷牙。故鄉道路望中賒。只恁寒夜夢,和月到梅花。春事闌珊雙鬢短,襟懷半在桑麻。落英無意念枯槎。東君猶自錯,留我美人家。
浪淘沙·書懷
宦思與羈情。慣見頻頻。丈夫淚不等閑傾。得喪路頭勘破久,寵辱誰驚。詩社訂新盟。玄酒大羹。鹿聲鳥語共呦嚶。只因昨夜思親苦,白發齊生。
滿江紅
寓南鄭題西園池亭用宋僧晦庵警世韻
宇內寓形,何須問、足與不足。天生物,五行均賦,有贏有縮。譬如車輪三十輻,迭為上下交翻覆。履前途,孰謂皆夷平,無礫碌。荒山下,一間屋。敗壁底,一瓶粟。少有人于此,肯著雙目。器小不能勝大受,命窮豈是膺多福。謂從今,消釋此身心,休多欲。[6]
以上三詞可見作者熟諳詞之體性,并能“自道意中事”。周瑛與林俊為同鄉友人。林俊(1452—1527)字待用,號見素,莆田人,成化十四年(1478年)進士,歷官南京刑部署員外郎,云南按察使。周瑛有《林見素赴云南憲副過鎮遠贈予〈臨江仙〉〈浪淘沙〉二詞依韻答之》,可見他們有詞唱和。林俊于弘治九年(1496年)作《詞學筌蹄序》。他追溯中國韻文出于古代歌謠,經多次變化之后,又變而為詞體,“則《青門引》《帝臺春》《金人捧露盤》《魚游春水》,是故言出為章,今固拘以體制;辭出為聲,今固拘以音律;洪殺翕辟,伸縮正變,為天然,今固拘以刻意苦思。於呼,亦極矣。”[7]這表明中國韻文發展至詞體,它的體制、音律、字聲均有嚴格的規范,異于此前的諸種韻文,因而周瑛對詞譜的編訂以創建詞體格律便具有重大的意義。
二
宋人作詞稱為“填詞”,這與作詩不同。詞人創作時是按照某樂曲(詞調)之節拍、旋律譜寫歌辭,要求句式、字音、分段與音樂的和諧,故稱“填詞”。北宋時王安石談到詞與音樂的關系說:“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詞。”[8]這表明詞的創作是以辭從樂的,異于其他諸種音樂文學。宋末沈義父記述從詞人吳文英學習詞法說:“癸卯識窗。暇日相與倡酬,率多填詞,因講論作詞之法。然后知詞之作難于詩。”[9]某些不諳音樂的詞人依據創調之作的句式、句法、字聲平仄、分段、用韻而作詞同樣可以達到歌詞與音樂的和諧,亦可付諸歌唱。我們可見南宋初年葉夢得作的《念奴嬌》全依蘇軾的聲韻句式,南宋中期陳亮與辛棄疾倡和的三首《賀新郎》的聲韻句式相同,而南宋楊澤民、方千里與陳允平遍和周邦彥詞更嚴于四聲相合。故在南宋時,唐代和北宋的許多詞樂散佚之后,詞人們是可以依據創調之作或名篇的句式、字聲和用韻填詞的,因此可以從文學體裁的觀念而總結詞體格律的。周瑛正是在詞樂散佚之后,詞體文學創作缺乏規范的情形下,編著詞譜而試圖重建詞體格律規范的。他以詞調為單位,每調列圖為譜;圖以方框(□)表示仄聲,圓圈(○)表示平聲,以小圓點標明句,分段處空一格;譜后附例詞。茲試舉小令與長調各一例:
長相思
○□○。□□○。□□○○□□○。○○○□○。□○○。□○○。□□○○○□○。○○○□○。右譜一章八句
紅滿枝綠滿枝宿雨厭厭睡起遲閑庭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
春園
右馮延巳
憶舊游
○○□□。□□○○。○□○○。□□○○□。○○□□。□□○○。□○□□○□。○□□○○。□□□○○。○○□□。□□○○。○○□○□。□□□○○。○□○○。□□○○□。□○○○□。○□○○。□○□□○□。○□□○○。□□□○○。○○□□○□○。右譜一章二十一句
記愁橫淺黛淚洗紅鉛門掩秋宵墜葉驚離思聽寒蛩夜泣亂雨瀟瀟鳳釵暗脫云鬢窗影燭光搖漸暗竹敲涼疏螢照曉兩地魂銷○迢迢間音信道徑底花陰時認鳴鐮也擬臨朱戶嘆因郎憔悴羞見郎招舊巢更有新燕楊柳拂河橋但滿眼京塵東風竟日吹露桃秋思
右周美成
填詞者必須熟讀譜例之詞,然后對照圖譜,依照句式、字聲、用韻、分段之規范而作,這樣所作之詞便合格律了,而且可以體現某種音樂的效應。填詞確實難于詩,但卻可體現此種音樂文學的藝術形式之精美,可以藝術化地表達主體的復雜的情感。
關于詞譜,我們現在所見之唐代敦煌琵琶譜,其中的《傾杯樂》《西江月》《伊州》等后來被用為詞調,但僅是用燕樂半字所記之音譜,無詞。宋代之詞譜實為歌譜,今存之標本為姜夔自度曲是注明宮調,詞字之右旁綴以燕樂半字符號;南宋《樂府渾成集》殘譜亦是如此。它們皆供樂工歌妓之用。南宋中期以來流行的詞選集《草堂詩余》是以事——春景、夏景、秋景、冬景、節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等分類編排的,可供熟悉詞調音樂的樂工和歌妓選用以歌唱,但不注音譜。周瑛之譜采用符號以表字聲,制圖以為譜,這是中國韻文史的首創,重建了詞的文學體裁的格律規范。唐宋的詞選集如《花間集》《樂府雅詞》《花庵詞選》《絕妙好詞》等,皆是以詞人為單位錄選作品的。周瑛之譜首先采用以詞調為單位分類編排。他分調是按詞調名之“子”“令”“引”“慢”“吟”“犯”匯列各調的,如《瑞龍吟》《水龍吟》《丹鳳吟》《塞翁吟》《青門引》《華胥引》《梅花引》《陽關引》《蕙蘭芳引》《側犯》《尾犯》《花犯》《天仙子》《卜算子》《風流子》《女冠子》《更漏子》《何滿子》《南鄉子》《行香子》等等。此種分調的遠源可以追溯到唐代崔令欽《教坊記》所記教坊曲名。以詞調分類列譜,這樣便于填詞者選用詞調并可按譜填詞。周瑛于譜后所附之詞例,有的調有數首或者十余首,這樣為填詞者提供名篇佳作為文學的典范,有助于理解該調之表情及適應之題材。
在《詞學筌蹄》問世之后,引發了詞學家們整理詞體格律,制訂詞譜的新的詞學途徑的開辟。明代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張艇編訂《詩余圖譜》六卷,采用分調類,以詞調字數由少至多為序排列,以白圈(○)表示平聲,以黑圈(●)表示仄聲,標注每段之字數及韻位,制以為圖,圖后附詞例。清代康熙十八年(1679年)查培繼編的《詞學全書》收入之賴以邠《填詞圖譜》六卷,依《詩余圖譜》之例而擴大了詞調收錄范圍。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朝廷組織王奕清等學者編訂的《詞譜》四十卷,收入之詞調與每調之別體堪稱完備,采取以詞調之字數為序編排,于詞例之右旁遍注字聲平仄,以白圈表示平聲,黑圈表示仄聲,半黑半白圈表示可平可仄之字,使圖譜詞例合一,每調下注明體制,每調內標明句或韻位,后附簡要說明及別體。《詞譜》的刊行標志詞體格律整理的完成,成為近三百年詞體的規范,推動了詞學的發展和詞體文學創作的繁榮。當我們回顧詞體格律的整理與詞體規范的建立的過程,則可見到周瑛之譜在詞學史上的首創意義與啟發意義了。
三
在宋代以來的各種詞選集中,影響最大和流傳最廣的是南宋中期書坊編的以事分類的《草堂詩余》,今傳之《增修箋注類選群英草堂詩余》是南宋末年書坊重編,明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翻刻元代至正本。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顧從敬據明初洪武本《草堂詩余》以詞調分類,以事為題系于詞下,為《分調類編草堂詩余》。周瑛編著《詞學筌蹄》時,分調本尚未問世,他所依據的是明初書坊翻刻的分類本《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余》[10]。周瑛以詞調分編,將事類分注于詞后,制以為圖譜,使此編具有全新的性質,可作為填詞的標準。
洪武本《草堂詩余》之總目標書名為《類選群英詩余》,分前集和后集。前集分為春景類、夏景類、秋景類、冬景類;后集分節序類、天文類、地理類、人物類、人事類、飲饌類器用、花禽類。這應是保留宋本之原貌。洪武本之內文,所列之每事類之細目與總目存在差異,例如秋景僅有秋景和秋怨,而無秋望、秋思、閨怨、秋閨;尤其是總目的地理類之金陵、赤壁、西湖、錢塘亭之各詞在洪武本中失收。由此可見洪武本之錯誤疏失,但宋人舊本在明代尚有存者。周瑛據洪武本《草堂詩余》為主,應同時參考了宋人舊本;因保存舊本地理類所收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懷古》,柳永《望海潮·錢塘》,周邦彥《西河·金陵懷古》,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等詞,周瑛所用之詞調《海棠春》《訴衷情近》《解語花》《花犯》《行香子》《西河》《桂枝香》均不見于洪武本。此亦是另據宋人舊本者。《詞學筌蹄》實用一百七十六調,內有重復者六調,另據舊本補七調,實為一百七十七調。它們是宋代流行之詞調。
洪武本《草堂詩余》乃明初書坊據宋人舊本編刻,雖遺漏地理類之各詞及失收數調,卻仍保存了宋本舊貌。周瑛編訂詞譜關于某些詞之詞話與注解全抄于洪武本《草堂詩余》,例如蘇軾《賀新郎》詞調下注云:“舊注云:本作《賀新涼》,有一營妓得罪于郡倅,東坡作此以解之,訛作《賀新郎》云。”詞后注云:“官妓秀蘭者黠慧,湖中有會,諸妓畢至,秀蘭后來。郡倅怪責之。蘭自言結發沫浴,不覺困睡。倅怒不解。東坡作此詞以解之,蘭始得免。”此注釋全抄自《草堂詩余》前集卷下引用之《古今詞話》。柳永《醉蓬萊》詞后,周瑛注釋:“舊注:宋仁宗朝老人星現,上宴禁中,令作樂章。時耆卿為屯田員外郎,方冀進用,作此。奏詞呈上,見首有‘漸字,不懌;讀至‘朕游鳳輦何處乃與御制真宗挽詞暗合,上慘然。又讀至‘太液波翻,曰‘何不言波澄,投之于地。自此不復擢用。”此全抄自《草堂詩余》后集卷上所引用之《花庵詞選》。此外像康與之《喜遷鶯》詞后注解乃全抄《草堂詩余》后集卷下按語;黃庭堅《念奴嬌》詞后注乃抄錄《草堂詩余》后集卷上所引之《苕溪漁隱叢話》;蘇軾《西江月》詞后注釋乃抄錄《草堂詩余》前集卷上之“東坡自序云”亦如是。詞譜應只講格律,不應附錄詞話、詞評之類的資料,周瑛偶然抄附詞話、詞評,是于體例不合的,但可見其編詞譜時所依據的文本資料。
《草堂詩余》因出自書坊編刻,本多訛誤,周瑛以之作為制訂詞譜之資料遂相沿而致誤者甚多。詞人姓名相沿致誤者如《點絳唇》“春雨濛濛”“鶯踏花翻”兩首本是無名氏詞,《草堂詩余》于此調前五詞《生查子》調名下標明“晏叔原”,周瑛錄此兩詞沿誤;又“紅杏飄香”一詞本為蘇軾作,《草堂詩余》于此調前四首《如夢令》詞標明為“李易安”,周瑛錄此而沿誤。《青玉案》“凌波不過橫塘路”本為賀方回名篇,《草堂詩余》于此調前第三首詞《如夢令》標明“李易安”,周瑛相沿致誤。《蝶戀花》“夢斷池塘驚乍曉”“海燕雙來歸畫棟”兩詞實為歐陽修作,《草堂詩余》于第一首標名為俞克成,第二首未標作者名,周瑛錄此兩詞均誤為“俞克成”。《滿庭芳》“紅蓼花繁”詞本為秦觀名篇,《草堂詩余》于此詞未標作者姓名,而前此第三詞《醉落魄》標明“張子野”,周瑛相沿誤作“張子野”詞。如此之類的錯誤極多。關于詞調名相沿而致誤者,例如《秋霽》無名氏詞,題為“秋晴”,胡浩然詞寫“春晴”,而改調名《春霽》,《草堂詩余》錄《春霽》與《秋霽》兩詞,誤為兩調,周瑛相沿而誤,但于《秋霽》不制譜,于調下注云:“譜與《春霽》同上篇,疑準此而作。”《念奴嬌》辛棄疾“西湖和詞”,洪武本未收入,周瑛沿宋人舊本以詞調為《酹江月》,而又另收《念奴嬌》之詞,誤以為兩調。以上諸例乃周瑛沿襲洪武本《草堂詩余》而未加考辯以致誤者。他還在編訂詞譜時由于草率粗疏而致諸多訛誤。
四
我們現在所見到的《詞學筌蹄》僅有清初抄本,此本未留下所據之原刊本或原抄本,亦未留下抄錄之年月和抄錄者之任何線索,故其諸多錯誤是出自原本或抄錄者之誤,己難辨析。茲僅對此抄本之訛誤以及圖譜之缺陷試舉例辨析:
(一)句韻不分。周瑛所制之圖譜雖然標明每調每段句數,并以小圓圈(●)表示句位,但未標明韻數及韻位。例如《如夢令》為仄韻,一疊韻;《長相思》三平韻,一疊韻;《清平樂》前段四仄韻,一疊韻;《念奴嬌》前后各四仄韻。因譜未標明韻數與韻位,填詞者尚須辨別用韻情況,甚為不便,以致出現用韻之錯誤。
(二)字聲之誤。圖譜以圓圈(○)表示平聲字,方框表示仄聲字,制譜之標準是依所列之第一詞例。茲將圖譜與詞例對照,圖譜時有誤標者。例如《瑞龍吟》之“愔愔”為平聲字,而標為仄聲字;《憶舊游》之“門”為平聲而標為仄聲;《青門引》之“被”為仄聲而標為平聲;《浪淘沙慢》之“漏”為仄聲而標為平聲;《賀新郎》之“手”“白”為仄聲而標為平聲。制譜為規范,不應有此等明顯之誤。
(三)不辨可平可仄之字聲。譜所列之詞例,有一詞者,而多數為若干詞至十余詞,周瑛僅以所列之第一詞例制譜,未能比勘諸作以定字聲,而每調確有某些詞字之字聲是可平可仄的。例如《踏莎行》周瑛錄四詞,制譜以第一首黃庭堅詞為標準。茲比勘前段第二、三句,以白圈(○)標示平聲,黑圈(●)標示仄聲:
倚墻繁李。長楊風掉青驄尾。
●○○●? ? ○○○●○○●
鶯聲漸老。紅英落盡青梅小。
○○●●? ? ○○●●○○●
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人處。
●○○●? ? ○○●●○○●
溪橋柳細。草薰風暖搖征轡。
○○●●? ? ●○○●○○●
以上可見第一句第一和第三字,第二句的第一和第三字均是可平可仄的。《蝶戀花》,周瑛錄十一首,以第一首俞克成詞為標準。茲比勘前四詞前段第一、二、三句:
夢斷池塘驚乍曉。萬舌無端,故作枝頭鬧。
●●○○○●●? ? ●●○○? ? ●●○○●
海燕雙來歸畫棟。簾影無風,花影頻搖動。
●●○○○●●? ? ○●○○? ? ○●○○●
春事闌珊芳草歇。客里風光,又過清明節。
○●○○○●●? ? ●●○○? ? ●●○○●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來時,綠水人家繞。
○●○○○●●? ? ●●○○? ? ●●○○●
以上可見每句之第一字均是可平可仄的。《西江月》,周瑛錄詞六首,以柳永詞為標準。茲比勘前四詞前段第三、四句:
兩竿日影上花梢。春睡厭厭難覺。
●○●●●○○? ? ○●○○○●
當年戲馬會東徐,今日凄涼南浦。
○○●●●○○? ? ○●○○○●
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原來有命。
●○●●●○○? ? ●●○○●●
遠山橫黛蘸秋波,不飲旁人笑我。
●○○●●○○? ? ●●○○●●
以上可見第一句之第一字、第二句第一字、第五字是可平可仄的。律詞同律詩一樣,某少數字是可平可仄的,不致影響整體的格律。周瑛未能進行比勘工作,沒有總結出字聲之可平可仄處。
(四)不辯別體。《憶秦娥》,周瑛錄詞四首,以第一首康與之詞仄韻制譜,其余三首中孫夫人用平韻。此調宋人多用入聲韻,亦有少數用仄聲韻者,又有詞人用平聲韻者。周瑛雖錄有平聲韻者,但未能辨識為別體。《浣溪沙》,周瑛錄詞十四首,其中十三首均為雙調,四十二字,前段三句三平韻,后段三句兩平韻。周瑛錄有李璟一首為雙調,四十八字,前段四句三平韻,后段四句兩平韻。此為《攤破浣溪沙》乃《浣溪沙》之別體,但周瑛未能辨識。
(五)例詞未校勘而致混雜亂竄。《千秋歲》錄歐陽修詞:
楝花飄砌。蔌蔌清香細。梅雨過,萍風起。情隨湘水遠,夢繞吳峰翠。琴書倦,鷓鴣喚起南樓睡。當年攜手處,游遍芳叢。聚散若匆匆。此恨元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
此詞分作三段,第一段乃摘自謝逸《千秋歲》,第二、三段取自歐陽修《浪淘沙》,經竄亂而以為《千秋歲》并以為歐詞。《浪淘沙》錄宋謙父詞:
把酒視東風。且共從容。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人生南北如歧路。世事悠悠等風絮。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見都如許。伊周功業何須慕。不學淵明便歸去。坎止流行隨所寓。玉堂金馬,竹籬茅舍,總是無心處。
此詞“總是”以上確為歐陽修《浪淘沙》詞,而此下乃無名氏之《青玉案》,又誤作宋謙父(自遜)詞。《應天長》以周美成詞為譜,但脫落前段起四句“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塘遍滿青色。正是夜堂無月”,故據以制之圖譜亦殘缺。周瑛又另列《應天長》康與之詞為譜,是為別體,但脫落“歸”“朱”“轡”三字,致字數與句式錯亂。周瑛于此調制訂之兩譜皆嚴重錯亂,將貽誤填詞者。
《詞學筌蹄》是中國第一部詞譜,周瑛編著此譜采用宋代最流行的唐宋詞選集《草堂詩余》,因所收之詞雖一百七十余調,但多為名篇與盛行的作品,尤其未雜入聲詩及其他韻文體式,故有簡明精要之特點。周瑛第一次以詞調為單位,以符號列圖制譜,試以作為喜好詞體文學者填詞之用,由此創建了詞體格律規范,是為詞學發展的突破,具有開拓學術研究途徑的重大意義。周瑛本是詞人,他今存之詞是嚴守格律規范的,體現了對詞法的嫻熟。當其編詞譜時則力圖從簡,甚為粗疏,未能進行每調作品之比勘考辨的工作,但應不會出現諸多嚴重的錯訛。今本《詞學筌蹄》之諸多訛誤或者應是抄錄者之疏忽所致。雖然如此,然而它確曾在當時有助于詞體文學創作的規范,啟發了后來詞學家們整理詞體格律的工作,并提供了圖譜的模式,致使詞體格律的規范在清代初年得以完成,促進了詞學的復興與詞體文學創作的繁榮。《詞學筌蹄》的刊刻及流傳情況雖無線索可求,亦不見諸藏書家著錄,但明代萬歷四十七年(1609年)程明善編訂《嘯余譜》時,顧從敬的分調類編本《草堂詩余》已經問世,程氏仍采用《詞學筌蹄》的分調模式。這或者出于周譜的影響,可惜不能詳考了。
注釋:
[1]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72頁;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73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2]張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二,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7253頁。
[3]鄭岳:《周瑛本傳》,周瑛《翠渠摘稿》卷八附錄,見《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4冊,第878頁。
[4]周瑛:《詞學筌蹄序》,《詞學筌蹄》卷首,《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35冊。以下凡引用《詞學筌蹄》隨文注明詞調,不再詳注出處。
[5]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七,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頁。
[6]周瑛:《翠渠摘稿》卷六,《四庫全書》第1254冊,第282—286頁。
[7]《詞學筌蹄》卷首。
[8]趙德麟:《侯鯖錄》卷七,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84頁。
[9]沈義父:《樂府指迷》,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77頁。
[10]《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余》,《續修四庫全書》,第1728冊。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資深館員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杰出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