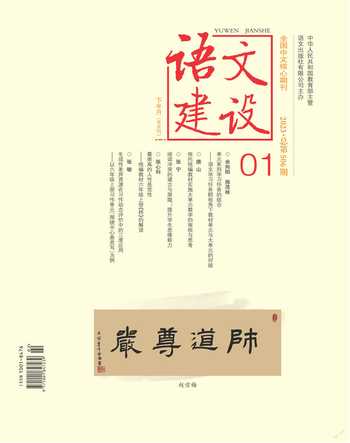最崇高的人性是黨性
張心科
【關鍵詞】《橋》;詩化小說;人性;黨性
《橋》是統編教材六年級上冊第四單元的一篇課文,與托爾斯泰的《窮人》、楊旭的《金色的魚鉤》共同構成小說單元。小說該如何解讀和教學?筆者認為,固然要關注人物、情節、環境三要素,但是相比單元內其他兩篇小說,《橋》又有其獨特性,是一種將詩的意蘊內化到小說中的“詩化小說”。作為“這一篇”,它又與一般的詩化小說以及西方的情節小說、我國的傳統小說在結尾的設置方面不同。因此,本文將從詩化小說這一小說大類中的亞類出發,解析《橋》的文本特點,進而明確它不同于其他小說的獨特之處,并在此基礎上,探究小說的主旨內涵。
一、“這一類”的文本特點:作為詩化小說的《橋》
作為小說中的一個亞類的詩化小說,在情節的安排、人物的塑造、環境的設置上都會呈現出一種詩意,或者詩味。比如,孫犁的《荷花淀》和沈從文的《邊城》,都是詩化小說的代表。具體到這篇文章來講,其詩化的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環境營造的意境化
意境是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藝術表現方面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將內在的情感、情緒、情趣與外在的景物、景致、景況相交融。環境的意境化,是詩化小說非常重要的特點。
首先,是自然環境的散點化。在《橋》這篇小說中,開篇沒有細致地描摹當時的自然環境,只是提到黎明的時候突然下暴雨,山洪暴發;在人們奔跑的過程中沒有寫洪水如何洶涌,只是用了“逼近”“躥上來”“舔著人們的腰”“吞沒了”等形象化的詞語來表現洪水的狀態。寥寥數語,便足以讓我們感受到雨水之大、洪水之洶涌。
其次,是社會環境的虛設化。這篇文章發表于1989年12月25日的《北京晚報》,從文章本身來看,并沒有具體交代當時的社會背景。這種虛設也恰恰給了我們莫大的聯想空間。文章中設置的環境是—個在山區的村子,有黨員、有群眾。平時生活中,黨員和群眾一樣,都是普通百姓。然而,在危難的時刻,黨員會第一時間站出來承擔責任,這其實就是當時中國大部分村子的樣子,甚至到現在也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特點。
2.情節設置的片段化
所謂情節的片段化,就是小說不是完整地展現故事的首尾,而是在中間似斷實連、忽實又虛,營造出一種詩意的氛圍。
在這個故事中,在山洪暴發之前,對于村子里的老支書以及人們的生活我們是不清楚的;兩個人被洪水吞沒之后的情節,我們也是不清楚的;最后老太太來祭奠之前發生的事情,我們依舊是不清楚的。這三個片段中間有許多空白點和未定性,給我們留下了相當大的想象和聯想空間。這與傳統小說有頭有尾、嚴絲合縫是不一樣的。另外,通過結尾,我們可以推斷出山洪暴發時,老支書的妻子也在撤離的群眾中,但作者不直接在故事情節中將其表述出來,而是讓讀者自行揣摩,不知不覺中便產生了一種詩意。
3.人物描寫的寫意化
人物寫意化是借用中國繪畫的概念,指在文章中以簡潔洗練的語言將人物的主要特征表現出來,而不對其作細致的描摹。
這篇小說中,主要寫了三類人:老支書、小伙子(兒子)和群眾。無論是單個人物的表現,還是對人物群像的描摹,人物的描寫方法主要是寫意,而非工筆描繪。我們不知道人物的長相和穿著,只是看到其語言和動作。這便是魯迅先生所言的“正如傳神的寫意畫,并不細畫須眉,并不寫上名字,不過寥寥幾筆而神情畢肖”。這種大筆勾勒,而非工筆描繪,也充滿了空白點和未定性,引導讀者聯想,從而產生一種詩意。
二、“這一篇”的獨特意蘊:《橋》的結尾藝術
相比孫犁的《荷花淀》和沈從文的《邊城》等詩化小說,《橋》除了與二者一樣采用意象化、情節片段化、人物寫意化等手法,還有兩點不同。一是內容。《荷花淀》《邊城》雖然寫到了戰爭、軍人,但是寫得如田園牧歌;《橋》寫的是災難、逃離,寫得非常悲壯。二是結尾。這一點更為特殊。一般的詩化小說,除環境意象化、情節片段化、人物寫意化以外,在結尾處往往也會采用詩意的寫法。這種充滿詩意的結尾有幾種寫法:戛然而止,也就是留白;不確定性,也就是模棱兩可,如沈從文的《邊城》,以“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結尾;寄寓或渲染某種思想、情感甚至某種情緒、氛圍的景物描寫,如《受戒》的結尾,寫蘆花、蘆穗、野菱角等,營造了一種詩意的悵惘。而《橋》的結尾則有以下特點。
1.內隱性的逆轉
在《橋》這篇小說中,結尾并沒有采用傳統的詩意寫法,而是采用了西方三大短篇小說家莫泊桑、歐·亨利、契訶夫在寫短篇小說時常用的手法——逆轉,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隨著情節的推進,我們發現老漢和小伙子兩個人都在這次山洪中喪生了,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兩個人竟然是父子。稍有不同的是,西方短篇小說結尾的逆轉常常是一種顯性的逆轉,就是延續前面的情節來轉折,如《項鏈》《麥琪的禮物》等;而《橋》的逆轉是暗示,就是沒有明確且故意地表現出老漢和年輕人的關系,而是通過老太太祭奠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含蓄地告訴我們喪生的兩個人是父子,體現出一種東方式的含蓄。
2.未團圓的結局
除此以外,這篇小說的結尾還通過悲劇的結尾展現了一種“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的詩意之“悲”。傳統小說通常有頭有尾,采用大團圓式的結局,但《橋》并沒有采用大團圓式的結局讓所有人都得救,作者甚至“殘忍”地沒有設計偶然的情節讓小伙子僥幸地活下來,而是讓老漢和兒子全部失去生命。作品如果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處結束,不交代他們最終的結局其實也是可以的,同樣留下詩意的想象空間;或者采用相對團圓的結局,如老漢去世,但是兒子活下來了,也可以像我們常見的傳統小說結尾一般——當一個家族面臨滅頂之災,一些人不幸死去,只要能讓孩子(年輕的生命)活著就能給人帶來希望。由此看來,老漢和兒子的去世正是讓人在這樣的“了無希望”中受到震撼,讓讀者明白“黨員”二字的真正內涵。在我看來,小說這么設置,既有其深意,也產生了極具震撼力的藝術效果。
三、最崇高的人性是黨性:《橋》的主題及主旨探索
理解了“這一類”(詩化小說的特點)和“這一篇”(《橋》的獨特價值),我們還需要關注這篇文章到底表達了怎樣的主題和主旨。正如前文所說,這篇小說社會環境的虛設化可給我們帶來一種超越時空的推想,每個時代、每個地點,都可能發生這樣的故事。其著意體現且比較顯豁的兩個中心:一是舍己為人,二是父子情深。除此以外,文章似乎還有另一層的含義,就是“黨性”和“人性”的關系。文章之所以讓我們深受觸動,還因為它內在的隱含主旨,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最崇高的人性是黨性”。筆者擬從“黨性”內涵的彰顯,小說三要素的互動關系及小說標題的內涵、外延三個方面來談談自己的理解。
1.犧牲的凜然:“黨性”對“人性”內涵的升華
入黨宣誓的時候,誓詞中有“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而《橋》這篇文章中老漢的所作所為便非常鮮明地表現了他身上的黨性——犧牲自我,舍己為人。他時刻不忘自己的黨員身份:在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受到威脅時挺身而出,“清瘦的臉上淌著雨水”,像一座山一樣,“不說話,盯著亂哄哄的人們”;當人們慌亂逃生的時候,他在擁擠和混亂中讓群眾先走,選擇犧牲自己;當自己的兒子和群眾利益發生沖突時,他提醒兒子黨員的身份,讓兒子不要先走。文章中的老漢像領頭羊,帶領村子里的人走出危險。當然,在兒子身上,也彰顯了他鮮明的黨性:父親把兒子從隊伍中揪出來,讓兒子“站到后面”,此時兒子的行為不單單是在服從父親,更是在服從組織的命令。
當然,文章中彰顯的“黨性”并不是與“人性”割裂的,而是對“人性”的升華。當人們都離開了,只剩下父子二人,“小伙子推了老漢一把”,讓父親先走,這是小伙子以兒子的身份表達對父親的愛。父親卻吼道“少廢話,快走”,然后用力把小伙子推上木橋。作為一個普通人,當我們愿意為另外一個人奉獻生命的時候,大多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方是自己的子女,愿意為孩子獻出生命;二是應激性情況,比如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有人在看到別人落水時奮不顧身地去救人,而在事后的采訪中,救人者常常會說自己當時沒有想太多,也沒有害怕,只是不忍心看著另外一個人失去生命。這就是人性善良的地方,而這種善良的人性的最高境界,就是黨性——愿意為了別人,為了大家的利益主動選擇犧牲自我。
2.“黨員也是人”:小說三要素的互動關系
在《語文有效閱讀教學》一書中,筆者曾經提到小說閱讀及其教學在于重構三要素的關系,也就是以獲取文本內容信息為切入點,圍繞人物自身的表現及人物之間的關系(情節)來探討,并分析人物某種言行舉止及其處理與他人之間關系時的處境(通過設置處境來呈現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目的(通過各種人物的塑造來表達主題的不同側面),最后結合文本的敘述、描寫以及作者對人物、事件等直接評說的文字來探究作者的看法(主題)。在閱讀《橋》這篇文章時,我們也可以此探尋其內在主旨。
在小說中,有這樣的一個情節:
老漢沙啞地喊話:“橋窄!排成一隊,不要擠!黨員排在后邊!”
有人喊了一聲:“黨員也是人。”
老漢冷冷地說:“可以退黨,到我這兒報名。”
競沒人再喊。一百多人很快排成隊,依次從老漢身邊奔上木橋。
有人喊了一聲“黨員也是人”。這句話是文章中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點。“有人”,這個人是誰?作者為什么要說“有人”而不具體指出是誰?我們可以假想,這里的“有人喊了一聲”可能有三種情況:第一,喊話的人是除了老漢和兒子以外的其他黨員;第二,喊話的人是老漢的兒子;第三,喊話的人是群眾,而非黨員。接下來,我們逐一探究三類人的表現,思考他們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出于什么目的喊出了這句話。
第一,如果這個人是黨員,這是極端的情況,他當時的處境可能是在危急之中。此時,人主要出于本能,目的是求生,這樣的一句喊話暗含的是對老支書的不滿。然而,從在老漢“可以退黨,到我這兒報名”的呵斥之后“競沒人再喊”的結局來看,“退黨”在這個人心目中的嚴重性比失去生命有過之而無不及,更凸顯了“黨性”在黨員心目中的分量。
第二,如果這個人是老漢的兒子,他的處境同樣是在危急之中,出于求生的本能。不過其目的不單單是求生那么簡單,還有對父親的憐惜。他深知,在這種危急的情況下,年邁的父親隨時可能被吞沒。另外,我們聯系上下文可知,年輕人的母親也就是老漢的妻子,也在慌亂撤離的人群中。所以,即使是站在有些人的前面,從兒子保護母親的角度來看也是情有可原的。接下來,老支書在人群中揪出了自己的兒子,讓兒子站在后面,他便服從地站在了后面,且在最后關頭推了父親一把,讓父親先走,可以看出兒子是既有“黨性”又有“人性”的。
第三,如果這個人是群眾,那么結合前面所寫“人們翻身下床,卻一腳踩進水里。是誰驚慌地喊了一嗓子,一百多號人你擁我擠地往南跑。近一米高的洪水已經在路面上跳舞了。人們又瘋了似的折回來”,在這種情況下,群眾能說出這樣一句話,更顯可貴。他們憐惜其他人的生命,更不愿意“他們的黨支部書記,那個全村人都擁戴的老漢”犧牲自己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黨性”既有了來源,也有了歸宿。老漢如果是一個更在意自己利益的人,群眾是不會擁戴他的;群眾如果對黨員不是這么的擁戴,也難以激發其更深層次的“黨性”。
無論喊出“黨員也是人”這句話的人是其他黨員、老漢的兒子,還是普通群眾,通過探析他們所處的境地和目的,均能發現黨員身上那種源于人性之善,又超越普通人性的黨性。
3.“橋”的隱喻:小說標題的內涵和外延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再來看本文的標題“橋”,不難發現隱喻之義。這也是理解文章主旨的一個重要線索。
就文章所寫的故事內容來看,首先,“橋”是有形之物,在危急的時候,“東面、西面沒有路。只有北面有座窄窄的木橋”,橋是一種有形的憑借,是人們逃生的必經之路。其次,這里的橋還是生命之橋。“一百多人很快排成隊,依次從老漢身邊奔上木橋”,老支書和小伙子,這對父子,這兩個共產黨員,在危急的時候為大家搭建的生命之橋。最后,橋還是精神的橋。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有時可能會為蝸角虛名東奔西走,為蠅頭微利斤斤計較,但是讀了這篇文章,其中黨性的光輝和人性的善良讓我們深受感動,內心會油然而生一種崇高感。在這個意義上,橋就是救贖的意思,讓我們從現實生活中脫離出來,變成一個精神高尚的人。或者像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最后寫到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見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簡而言之,《橋》這篇小說雖然短小,卻呈現了一種詩化的美好,帶給我們心靈的震撼。在大的災難面前,最能夠體現人性,也最能夠體現黨性。文章通過寫一個老漢、一個年輕人,凸顯了我們黨和中華民族所具有的在特殊時期、特定情境下舍己為人的崇高精神。讀罷這篇小說,我不由得想起《我和我的父輩》這部電影里的一個情節:因為日本軍隊的到來,村子里的人需要轉移,為了保護村民,父親把戰火引向了兒子的那一邊。兒子戰死,父親送給兒子的戰馬獨自跑回……這種詩化的留白,正如《橋》的結尾一樣,有生命之哀,更有人性的美、黨性的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