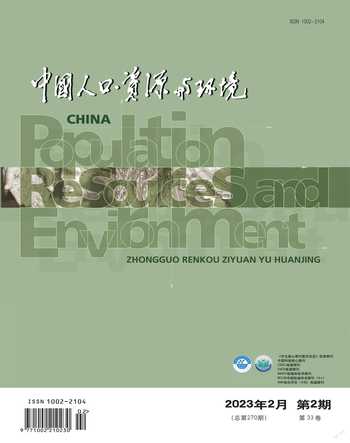損己不利人:僵尸企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
孫博文 尹俊



摘要 僵尸企業是產能過剩和污染排放的重要源頭,加快推進僵尸企業處置是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及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抓手。該研究采用最新公布的2006—2014年中國工業污染數據庫與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微觀匹配數據,在測算微觀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上,實證檢驗了僵尸企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作用及微觀機制。為緩解數據遲滯問題,同時,基于2004—2018年上市公司僵尸企業的識別以及省級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數據進行了交叉驗證分析,結論穩健。研究發現:①僵尸企業不僅自身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低于正常企業7. 9%,還表現出顯著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負外部性,僵尸企業占比每增加1個百分點,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降低2. 733%,最終僵尸企業的存在使得總體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絕對水平損失3. 27%,相對水平下降22. 4%。②異質性分析中,僵尸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負外部性對于非國有企業、小規模企業以及融資約束強的企業更為顯著。③微觀機制檢驗方面,僵尸企業通過阻礙正常企業技術進步、抑制規模效率提升而不利于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但對純技術效率(管理效率)反而表現出一定的短期促進效應,而且微觀機制在非國有企業、小規模企業以及融資約束較強的企業樣本中更顯著。研究還發現,僵尸企業顯著降低了正常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環境生產率水平。針對結論,提出了加快推動僵尸企業處置,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 僵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負外部性
中圖分類號 F426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3)02-0038-13 DOI:10. 12062/cpre. 20220619
新發展階段,加快推動僵尸企業處置不僅是化解產能過剩、打通供需梗阻、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任務,也是協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必要舉措。僵尸企業本質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破壞,不僅使得低效僵尸企業無法正常退出市場,加劇了行業資源錯配與產能過剩問題[1-2],還對正常企業造成諸多負外部性影響,如投資擠出[3]、創新抑制[4]、就業擠出[5]、逃稅效應[6]等。除了上述經濟負外部性之外,有研究表明,僵尸企業還對正常企業有顯著環境負外部性、加劇了其污染排放水平[7-8],因而不利于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在于推動技術進步、優化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兼顧環境約束下,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已經成為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重要實踐抓手[9]。但梳理已有研究發現,對于僵尸企業的危害作用研究,大都基于僵尸企業的經濟或者環境負外部單一視角,鮮有學者將其二者結合起來,討論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外部性作用。鑒于此,該研究在有效識別僵尸企業與測度微觀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礎上,除了分析僵尸企業自身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外,還探討了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非僵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不利影響,詳細分析僵尸企業的這一“損己不利人”特征,有助于進一步揭示僵尸企業對宏觀層面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破壞機制、并量化其負面作用大小,為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提供新的政策視角。
該研究邊際貢獻在于:研究視角上,不僅基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負外部性視角豐富了僵尸企業危害國民經濟發展的有關研究,還從僵尸企業處置的視角,為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提供新的政策抓手。研究方法上,基于松弛的方向性距離函數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測算了微觀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進一步修正僵尸企業識別標準、力求以FN?CHK修正標準精確識別僵尸企業。研究數據上,采用2004—2014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工業企業污染數據庫的微觀匹配數據開展研究,為僵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負外部性的研究提供了微觀證據;此外,考慮到工業企業數據庫的時間滯后性,研究還基于2004—2018年上市公司僵尸企業的識別以及省級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數據進行了省級層面結論再檢驗。研究內容上,證實了僵尸企業自身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及影響正常企業負外部性的作用,并量化分析了僵尸企業的綜合損失大小;分析了不同企業所有制、規模、融資約束下研究結論的異質性以及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技術進步、綠色規模效率與綠色純技術效率的微觀機制渠道,并結合二者進一步剖析了僵尸企業影響正常企業的微觀機制異質性特征,對于明確僵尸企業處置重點、分類施策、提高處置效果有重要政策價值。
1 理論機制與命題假說
1. 1 僵尸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負外部性
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與環境保護下,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突破單一經濟效率提升或環境治理維度評價的重要抓手。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本質在于考慮環境約束下的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僵尸企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僵尸化導致自身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二是通過外部性渠道對正常企業帶來負面影響。對于前者,僵尸企業自身具有技術研發動力不足、效率低下、缺乏自生能力、污染強度高以及產能利用率偏低等特征,可能比正常企業表現出更低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對于后者,由于供應鏈和產業鏈內部、之間關聯的作用,僵尸企業還可能通過“資源擠出效應”以及“市場破壞效應”不利于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圖1)。
具體地:①資源擠出效應。僵尸企業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低于市場利率的優惠信貸支持,對正常企業的投資具有顯著的擠出效應,加劇了正常企業的融資約束,不利于正常企業創新研發、污染治理、人才引進以及資產重置投入等,損害了企業的可持續經營能力。僵尸企業的金融資源錯配效應最為突出,中國金融市場制度不健全,以銀行體系為代表的間接金融制度占主導地位,信貸歧視和信貸錯配廣泛存在[10],這使得僵尸企業的存在通過扭曲資源配置,抑制正常企業的投資,加劇了社會資本投資動力不足、企業融資難與融資貴的問題[11]。此外,僵尸企業還抑制了正常企業的創新研發投資和污染治理投資等,損害了企業長期創新能力,加劇了企業污染排放和地區環境污染[12-13]。②市場破壞效應。在市場機制有效運行的情況下,社會資源會從低效率企業流向高效率企業。僵尸企業的存在破壞了市場資源配置機制,使得正常企業無法獲得公平的市場競爭地位,政府補貼、銀行貸款等社會資源流向僵尸企業,阻礙了正常企業的生產經營,降低了正常企業產能利用率[14]。而且,正常企業難以根據價格信號調整自身的生產經營行為,進一步加劇了市場資源錯配,使得企業在市場的低效率均衡中“鎖定”,損害了其長期發展能力。
最終,在資源擠出效應和市場破壞效應的作用下,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的綠色研發投入、污染治理設備引進、生產流程優化重組、高污染企業市場退出都有不利的影響,可能損害了正常企業長期綠色技術進步和內部資源、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進而不利于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據此提出命題1。
命題1:僵尸企業不僅自身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低于正常企業,還不利于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1. 2 微觀機制
1. 2. 1 基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的影響渠道
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可以測度存在環境污染非期望產出時的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并可將其進一步分解為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兩部分開展進一步實證研究。因此,僵尸企業可能通過綠色技術進步、技術效率改善渠道抑制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一是技術進步渠道,僵尸企業加劇了正常企業融資約束,不利于其綠色技術研發投入、科研人員引進、污染處理設備購買等,通過企業技術進步渠__道抑制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二是技術效率改進渠道,僵尸企業的存在破壞了市場機制,抑制了低效率企業的市場退出和新陳代謝[2],使得大量的低效率、高污染企業茍延殘喘。
技術效率可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兩部分[15]。①純技術效率渠道。純技術效率代表每一個生產決策單位利用現有要素投入生產相應產出的能力,體現了企業對既有資源的利用效率或者管理效率提升[16]。僵尸企業強化了正常企業的資源約束,在資源擠占的負外部性壓力下,可能會倒逼正常企業優化生產流程、提高企業管理效率、促進(勞動、資本、能源)資源節約以及提高生產效率,反而有助于正常企業效率提升,但這一結果可能僅僅是企業被動應對資源緊約束的短期效應。長期來看,僵尸企業對市場機制的破壞不利于正常企業生產效率的改善。僵尸企業的存在破壞了市場機制,不利于正常企業利用市場機制、價格信號、靈活調整其生產策略,抑制了其純技術效率的提升,而且也不利于低效率企業退出市場。②規模效率渠道。規模效率來自于決策單元規模擴大帶來的邊際成本下降[17]。僵尸企業強化了正常企業的資源約束,通過擠占正常企業的要素投入、抑制了其生產能力提升和規模的擴大,進而損害了企業規模效率提升。僵尸企業破壞了市場機制,使得生產要素無法自由流向高效率企業、提高企業生產規模以及市場份額,同樣不利于企業規模效率的改善。僵尸企業還破壞了正常企業的生產合作網絡,不利于其市場規模的擴大。在產業鏈一體化、生產網絡化的背景下,僵尸企業通過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傳導,破壞了正常企業的分工合作、資源互補、一體化能力,具有顯著的企業合作負外部溢出效應,不利于地區形成布局合理、分工明確、資源互補、要素自由流動、產供銷一體化的產業體系,形成了微觀“腸梗阻”,不利于其市場規模的擴大以及規模效率的提升[18]。故提出命題2。
命題2:在資源擠出效應和市場破壞效應下,僵尸企業通過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等機制渠道影響正常企業全要素生產率。
1. 2. 2 基于企業生產率與綠色創新的微觀機制
除基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分解探討有關影響渠道外,還有必要進一步打開僵尸企業影響正常企業微觀行為(如要素投入、產出、污染排放)的“機制黑箱”。一言蔽之,僵尸企業可能通過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環境生產率和綠色創新等機制發揮作用,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負面影響。一方面,機制“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以及“環境生產率”均體現了企業“投入產出比”特征,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分解中的“技術效率”渠道對應,需要指出的是,與勞動、資本要素投入不同的是,環境生產率中將污染排放視為非期望產出或者投入要素,體現了污染排放強度的內涵。另一方面,綠色創新反映了企業的綠色技術研發水平,體現了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分解中的技術進步渠道。
具體機制如下:①企業生產率機制。一方面,僵尸企業的預算軟約束、所有制優勢特征,對正常企業就業、技能人力資本、資金使用具有擠出效應,導致企業可用要素投入降低、產能利用率下降和產出降低,降低了企業勞動生產率以及資本生產率水平,不利于總體生產率的提升。另一方面,僵尸企業極大地破壞了市場機制以及價格信號作用發揮,加劇了企業投入產出行為優化調整的市場交易成本,即便企業市場份額下降,其也往往難以通過減產、縮小生產規模保證生產效率穩定。除不利影響外,僵尸企業還可能通過加大正常企業生存壓力,倒逼其通過優化管理、壓低不必要支出等方式提高正常企業的生產率水平,表現為短期技術效率的改善。②環境生產率機制。僵尸企業擠占了正常企業的資源,使得企業污染治理投入、處理設備引進資金約束偏緊,而且環境治理領域的人才引進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進而加劇了企業單位產出污染排放水平,不利于環境效率的改善,這一點已經得到部分研究證實[8]。③企業綠色創新機制。從僵尸企業的資源擠占效應來看,其不利于正常企業綠色技術研發投入,從僵尸企業的市場破壞效應來看,其弱化了正常企業綠色創新的市場激勵。雙重因素下,僵尸企業不利于正常企業綠色技術創新,可能降低了企業的綠色技術研發投入以及綠色專利授權數量。故提出命題3。
命題3:僵尸企業通過企業生產率、環境生產率和綠色創新等機制影響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1. 3 異質性特征
僵尸企業具有顯著的資源擠出效應和市場破壞效應,對不同所有制、規模與融資約束下的正常企業存在影響差異。①企業所有制異質性。僵尸企業對正常非國有企業的影響作用更大,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具有顯著的預算軟約束特征,地方政府為維持就業穩定、稅收增加以及經濟發展,對國有企業存在政策偏袒和“父愛主義”,這一政策保護效應使得國有企業表現出更強的市場資源控制力,而且作為國民經濟的命脈,在產業鏈供應鏈競爭方面也存在絕對優勢。由此可推斷,僵尸企業對正常國有企業的資源擠占效應、市場破壞作用可能影響偏低。反倒是非國有企業,僵尸企業的存在不僅造成其資源渠道淤堵,而且通過破壞市場競爭環境,導致非國有企業難以發揮其靈活適應市場的優勢。②企業規模異質性。企業規模越大則邊際成本越低,還具有較強的市場議價能力、市場盈利能力和__創新發展能力,并通過深度參與市場生產網絡,體現出較高的產業鏈、價值鏈前后一體化水平,能夠更好地抵擋市場風險[19]。鑒于此,與規模較小的企業相比,僵尸企業對正常規模較大企業的負面影響可能更低。③融資約束異質性。企業低融資約束意味著更強的市場流動性,能更好地根據市場信號調整企業經營行為,充分利用市場信息生產要素與資源供給[20],能夠有效緩解僵尸企業帶來的資金擠占效應,因此,僵尸企業對融資約束較低的企業影響可能更小。鑒于以上分析,提出命題4。
命題4:僵尸企業對不同所有制、規模和融資約束下的企業影響存在差異。
2 研究設計
2. 1 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為檢驗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模型設定如式(1):
其中:gtfpijt為被解釋變量,表示城市j 企業i 在t 年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zratejt表示城市j 在t 年僵尸企業數量占比。X 表示控制變量,參照已有研究[21-24]的做法,分別設定企業與城市層面控制變量。企業層面:①企業年齡(lnage),企業年份與企業成立時間之差加1取對數;②企業規模(lnlabor),采用企業職工人數取對數表示;③企業資產流動性(flow),參照吳清揚[8]的做法,計算企業流動資產占比=企業流動資產(/ 企業流動資產+年末固定資產余額);④企業所有制(stateown),國有企業定義為1,其他定義為0;⑤出口密度(expden),企業出口值/工業增加值;⑥企業內部管理水平(lnmfr),采用單位就業管理費用支出(企業管理費/就業總人數)表示,并取對數處理。城市層面:①城市經濟發展(lnpgdp),城市人均GDP的自然對數;②城市經濟密度(lndensity),采用城市單位土地面積GDP表示,反映了城市經濟集聚水平[25]。ai為企業固定效應,vt為時間固定效應,λc為城市固定效應,eijt為隨機擾動項。含價數據均經過消脹處理。
2. 1. 1 被解釋變量: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gtfp)及分解變量
基于方向 性距離函數的Malmquist?Luenberger 生產率指數(ML指數),可以測度存在“壞”產出時的全要素生產率[26]。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數據庫的可得數據,構造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投入產出指標體系。具體地,投入指標有:企業職工人數、企業固定資產年末余額、能源(煤炭、燃料油、潔凈天然氣)消費量、工業用水總量等。產出指標包括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兩類。期望產出為企業工業增加值,非期望產出有工業廢氣(SO2、NOX、煙塵、粉塵)排放量、工業廢水排放量。含價指標數據均平減處理。采用MaxDEA Pro 軟件計算。根據Ray 等[15]分解方法(式2),在可變規模報酬的假設下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分解為技術進步、技術效率變動與規模效率變動三部分,三者具有重要的現實含義,技術進步是指企業在有關技術創新促進下,生產前沿面發生了移動,在既定的資源下可以得到更多理論產出,現實中表現為企業創新能力的改善,投入層面表現為企業技術研發、R&D人員投入的增加,產出層面表現為企業專利、新產品產值的提高。技術效率變動是指,在企業生產前沿面不變情況下,企業資源配置效率得以不斷優化,根據有關理論,技術效率通常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兩項,純技術效率是指規模不變下企業內部資源配置效率、管理效率的改善,現實中,表現為企業內部勞動力和資本跨部門流動、企業生產流程重組優化等;規模效率是指,企業規模擴大帶來的邊際成本下降、規模報酬遞增效應等。
2. 2. 2 解釋變量:城市僵尸企業比重(zrate)
城市僵尸企業數量占比等于城市僵尸企業數量與當年企業數量總數的比值。前提是對僵尸企業的精準識別,方法如下。
(1)基于企業是否接受銀行信貸補貼的CHK標準進行初步識別Z1[14]。
首先,計算出企業i 第t 年的理論最低應付利息:
其中:RSt - 1是t-1年短期最優貸款利率,由6個月內和6個月至1年貸款基準利率的年化平均計算得到;RLt - 1 為t-1年長期最優貸款利率,為1~3、3~5和5年以上貸款基準利率算術平均值,BSi,t - 1 和BLi,t - 1 是為企業t~1年的短期借款和長期借款,分別以企業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衡量。其次,計算企業i在第t年的實際利息支出:
其中:Interestit 為企業財務費用中的利息支出凈值,Depositi,t - 1 為企業i在t-1年的銀行存款。RDt - 1 是企業t-1年的短期存款利率,由活期、3個月、半年和1年存款利率進行年化平均計算得到。
再次,計算企業實際利息支出與理論最低應付利息之差:
(2)在Z1的識別基礎上,基于FN?CHK標準[27],將企業利潤為負、資產負債率高于50%且連續增加的企業識別為僵尸企業Z2。
(3)在Z2的識別基礎上,進一步對FN?CHK標準修正調整如下:基于避免正常企業被“誤傷”或部分僵尸企業成為“漏網之魚”的原則,對FN?CHK標準進行調整。首先,采用工業企業數據庫中的“營業利潤”指標而非“利潤總額”,因為企業的利潤總額包含了當年的非經常性損益,導致實際發生虧損的僵尸企業因為獲得政策性補貼而顯示正的賬面利潤或利潤總額,導致僵尸企業數量低估[28];其次,采用連續若干年(兩年)實際利潤的“平滑均值”作為當年的真實利潤情況,將真實利潤連續兩年平滑均值小于0的企業在當年識別為僵尸企業。最后,進一步增加企業“連續兩年為僵尸企業方能被識別為僵尸企業”的條件。最終得到本研究所識別的僵尸企業Z3。
2. 2 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該研究用到了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數據、城市數據庫和上市公司數據庫等四套數據。微觀企業數據來自最新2006—2014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工企污染排放數據庫匹配,兩者指標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具有詳細的企業財務以及企業屬性等信息,但缺乏企業能源投入、污染治理行為以及企業排放等指標。相比而言,近兩年學界應用較多的中國企業污染排放數據庫則有詳細的企業能用利用、污染排放指標,其指標的有效性已經得到了有效證實[29],但缺乏有關企業財務指標。對于數據的處理,首先以法人代碼、企業名稱、行業代碼、主要產品、開工年份、郵政編碼、國有控股情況等基準變量,逐步分鄰近兩年、鄰近三年和最后統一匹配到全體年份的非平衡面板數據集。手工對四位數行業代碼進行統一,并確保兩位數行業代碼統一到2002年標準,僅保留制造業行業樣本。并對所有的連續變量進行1%縮尾處理。剔除污染物排放小于0、工業增加值大于工業總產值等異常值,最終得到9 449家工業企業有效樣本。城市層面數據來自歷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部分缺失數據通過中經網、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數據庫補齊。上市公司數據來自于Wind數據庫。表1為樣本變量的統計描述。
3 實證結果討論
3. 1 基準回歸
表2報告了微觀數據回歸結果。列(1)至列(4)探討了城市僵尸企業占比對正常企業的影響。列(1)僅控制了年份和城市固定效應,發現城市僵尸企業比重的系數顯著為負,命題1初步得證。在列(1)的基礎之上,為進一步排除企業及城市層面相關因素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列(2)和列(3)分別加入了企業年齡、企業規模、企業資產流動性、企業所有制、企業出口密度以及企業管理費用等微觀企業因素,以及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密度等城市因素,發現城市僵尸企業比重系數都顯著為負,但解釋力有所降低。列(4)則在列(3)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控制了企業層面固定效應,發現城市僵尸企業比重的系數顯著為-2. 733,且通過1%的顯著水平檢驗,這意味著,城市僵尸企業占比增加1%,則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__率則下降2. 733個百分點,命題1得證。基準結果證實了僵尸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負外部性存在,且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
進一步,為評估企業從正常變為僵尸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凈損失,基于列(1)至列(4)的模型設定思路,列(5)至列(8)以僵尸企業虛擬變量為解釋變量,以全部樣本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發現企業僵尸化使得其自身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了7. 90%,結論穩健。
為緩解工業企業微觀數據庫樣本陳舊問題,并從宏觀層面對僵尸企業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進行交叉驗證,該研究進一步采用時間窗口為2004—2019年上市公司和省級層面樣本數據進行側面印證分析。不同數據庫的回歸結論大小可能有所不同,但要求保持一致符號。涉及到的關鍵問題有兩個:上市公司僵尸企業識別以及省級層面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計算,為求結果總體可比,研究對上市公司僵尸企業識別同樣采用FN?CHK方法。具體而言,首先根據上市公司的短期與長期負債、短期與長期最優貸款利率計算企業市場利息支付下限,通過與企業真實利息支出比較判斷其是否接受了信貸補貼,這一方法未考慮上市公司未消償債券余額及利率,如企業債、公司債、可轉債、中期票據及短期融資債券及其利率等。其次,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計算類似工業企業,等于企業年末固定資產總額與長短期負債總額之比,最后上市公司利潤采用扣除補貼、稅收、非經營性收入后的年利潤進行計算。另外,省級層面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同樣采用基于非徑向距離和非期望產出的ML指數計算:投入指標有勞動投入,采用各省份年末就業人員數;資本投入,采用永續盤存法進行衡量;能源消費量,為省級萬噸標準煤能源投入量;期望產出為各省市自治區的實際GDP,以2004 年為基期折算;非期望產出的選擇為工業廢水中COD排放量、工業SO2排放量等。
分析不同省份僵尸企業占比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均值變動趨勢特征可知,兩者呈現出明顯的負向變動關系,尤其是2013年之后,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這一關系更顯著:省級上市公司僵尸企業占比從2013年的7. 5%迅速降至2018年的1. 8%,省級綠色全要素也從2013年的1. 46增至2018年的2. 18。進一步,基于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回歸發現,在控制一系列固定效應和有關控制變量之后,省級僵尸企業占比(x)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y)存在“y=-2. 71x+1. 64”的擬合關系,即省級層面上市公司僵尸企業占比增加1%,則省份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下降2. 71 個百分點,且通過5% 的顯著水平檢驗(P=0. 04)。研究結論為探討僵尸企業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提供了宏觀證據支撐。但對比發現,這一結果低于微觀層面加總3. 25% 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值,可能是因為,上市公司僵尸企業數量相對偏少,造成省級層面僵尸企業比重低估,而且宏觀數據層面也未考慮不同省份之間僵尸企業負面溢出效應。
3. 2 結論穩健性
微觀實證穩健性檢驗見表3。具體包括:①資產加權指標替換。列(1)中選擇僵尸企業資產加權方法計算城市僵尸企業比重(zkrate),發現其系數同樣顯著為負。②調整僵尸企業識別策略。為緩解測量誤差帶來的內生問題,采用經典FN?CHK標準重新識別僵尸企業并構造解釋變量,列(2)與列(3)中城市僵尸企業數量占比(znrate_fn)與資產占比(zkrate_fn)系數分別顯著,為-1. 368和-0. 789。③剔除僵尸企業所在行業特征的影響。構造了城市內本行業僵尸企業數量比重(znrate_cic2)和資產比重(zkrate_cic2)的指標,列(4)和列(5)顯示,兩指標系數分別顯著,為-0. 737和-0. 580。④考慮跨行業溢出效應。設定城市內非本行業僵尸企業數量占比(znrate_other)和資產占比(zkrate_other)等指標,列(6)與列(7)顯示,系數分別顯著,為-1. 368以及-1. 012。⑤刪除低質量樣本數據。剔除2010年樣本后,列(8)和列(9)中城市僵尸企業數量及資產比重系數均為負,但資產占比變量未通過顯著水平檢驗。綜上,相關回歸結果證實了研究結論的穩健性,部分回歸中核心解釋變量系數絕對值雖有所波動,但系數符號均為負,未發生變化。__
3. 3 內生問題討論
僵尸企業識別方法引致的測量誤差以及與僵尸企業形成有關的遺漏變量,都有可能帶來潛在內生問題。為此,該研究構造了僵尸企業比重的工具變量(IV)進行兩階段GMM 方法進行估計。工具變量的構造參照Nunn等[30],選擇樣本初期城市國有企業份額與前一年全國國有資產負債率的乘積作為城市僵尸企業比例的工具變量。原因在于,僵尸企業主要集中在國企之中,將樣本初期城市國有企業份額作為前定變量相對于城市僵尸企業比重指標滿足“外生”和“相關”兩個工具變量必要性假設。為增加時間維度變化,進一步將樣本初期城市國有企業份額與城市僵尸企業占比指標前一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相乘,得到工具變量IV。表4顯示:在第一階段回歸中,Kleibergen?Paap rk WaldF 統計量均明顯大于10的經驗臨界值,拒絕了弱工具變量假設。在緩解相關內生問題之后,列(1)至列(4)城市僵尸企業占比指標系數都顯著為負,證實了僵尸企業影響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外部性特征,結論具有一定的穩健性。但與基準回歸相比,僵尸企業解釋變量系數絕對值都有所降低,在緩解內生問題之后,僵尸企業導致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高估問題有所緩解。
3. 4 異質性分析
該研究進一步探討了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異質性。首先對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大規模企業與小規模企業、融資約束強與融資約束弱企業進行樣本分組設定。基于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以及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數據庫的匹配數據,企業異質性的界定方式如下:第一,企業所有制方面,國有企業是指注冊為國有企業或者國有及集體資產占比超過50%的企業,其他企業界定為非國有企業;第二,企業規模方面,首先識別年度企業就業人數中位數,將企業就業大于中位數的界定為大規模企業,反之則為小規模企業。第三,企業融資約束方面,首先計算企業融資約束=凈利息/上一年負債總額,進一步識別年度企業融資約束中位數,將融資約束大于中位數的企業界定為融資約束強企業,反之則為融資約束弱的企業。基于樣本分組,表5中列(1)至列(6)報告了異質性樣本結論。結果顯示,第一,列(1)與列(2)中,城市僵尸企業比重對非國有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系數顯著為-2. 891,但對國有企業的影響不顯著。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在資金、勞動、土地以及資源能源的獲得上存在諸多劣勢,僵尸企業的資源擠占效應和市場破壞效應對非國有企業的負面影響更大,不利于其正常生產性投資、創新研發投入、污染治理投資的增加。結果,僵尸企業對非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表現出更強的抑制作用。第二,列(3)與列(4)顯示,與規模較大企業相比,僵尸企業對規模較小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更顯著、且影響作用更大。企業規模體現了企業產業鏈供應鏈地位和風險抵御能力,由于邊際成本較低,其對僵尸企業印發的污染外部性具有__較好的成本分擔能力,因而可能對僵尸企業的影響不太敏感。相比而言,規模較小企業面臨著更大的僵尸企業資源擠占效應、市場破壞效應及一系列金融衍生風險等,受僵尸企業影響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更大。第三,列(5)和列(6)顯示,城市僵尸企業比重對融資約束強的正常企業負面影響更大。在銀行主導的金融結構下,民營企業融資貴、融資難問題突出,對于一些原本資金流動性緊張的企業而言,僵尸企業占據了大量的優質社會信貸資源,強化了正常企業的融資約束,不利于正常企業的技術研發投入和污染治理投資,對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產生了不利影響。
4 機制分析
4. 1 模型設定
探討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的影響機制,關鍵在于檢驗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及分解項的影響,這有助于為深入分析微觀機理提供經驗判斷。本研究基于中介模型思維,分別設定模型(7)至(9)并定義為基礎模型、機制模型和聯合模型。基礎模型為基準回歸模型。機制模型中,被解釋變量為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分解變量M,分別是技術進步gtc、純技術效率gptc 以及規模效率gsec 等。聯合模型為將中間機制變量M 加入基準模型。機制的顯著性判斷步驟是:第一,基礎模型中核心解釋變量顯著;第二,判斷機制模型(8)和聯合模型(9)中機制變量M 系數顯著性,若顯著,則間接效應為β2 ×β3,否則中間機制不顯著、間接效應不存在;第三,聯合模型中僵尸企業比重zrate 系數,體現了其影響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直接效應,若不顯著則直接效應不存在。
近些年,對中介效應模型的爭議日漸增多,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聯合模型中機制變量影響被解釋變量的支撐理論分析,導致機制變量存在潛在內生問題、造成“偽相關”或“偽回歸”等問題。事實上,規范的經濟學分析并不排斥中介模型的機制檢驗思維,科學應用中介機制模型,需要在探討中間機制影響被解釋變量環節,完善有關理論支撐,為兩者存在的統計相關性提供理論基礎[31]。文章中,機制變量(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變動、規模效率變動)作為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分解變量,具有嚴謹的內涵界定和理論基礎,使得其能夠有效避免中介效應模型存在的典型問題,確保估計結果的科學性。
4. 2 影響渠道
基于中介效應模型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的分解結果,表6呈現了微觀機制檢驗結果。列(1)為基準回歸結果。列(2)至列(4)顯示,城市僵尸企業比重的增加顯著抑制了正常企業的技術進步、規模效率提升,導致其分別降低了0. 800和0. 801個百分點,然而卻發現,僵尸企業促進正常企業純技術效率顯著增加2. 141%。僵尸企業不利于企業技術進步、降低了企業的規模效率,可能與其對正常企業的創新研發擠出、企業資源的擠占和對市場機制的破壞有關。相比而言,純技術效率變量卻顯著為正,意味著僵尸企業反而提高了正常企業的管理效率,對其內部資源配置效率表現出一定的積極優化作用,與正常企業應對僵尸企業資源擠占、非市場化競爭下的自我生產調整有關,僵尸企業的存在倒逼其通過節約資源投入、優化生產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削減生產投入等,表現為短期內管理效率提升,但這一效應可能是以僵尸企業破壞市場為代價的,不具有持續性。進一步,結合列(5)聯合模型可知,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直接效應為-1. 619%,系數絕對值有所下降,計算不同機制渠道的貢獻份額可知,僵尸企業通過技術進步、純技術效率變動、規模效率變動等機制的間接效應分別為-0. 07%、-0. 261%和-0. 782%(計算方式分別為-0. 800×0. 088、-0. 122×2. 141 以及-0. 801×0. 976),三者之中規模效率損失最大,說明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的破壞主要是通過資源擠占、抑制正常企業生產規模擴大來實現的。
4. 3 渠道異質性
在異質性分析與微觀機制討論基礎之上,表7進一步報告了企業所有制、規模和融資約束視角下的微觀機制異質性。結果顯示,Panel A中,僵尸企業對國有企業表現出顯著的技術進步抑制效應,并且這一效應高于非國有企業。對非國有企業的純技術效率變動、規模效率變動分別表現出顯著提升與抑制作用,但此二條渠道在國有企業中均不顯著。Panel B中,僵尸企業影響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微觀機制僅在小規模企業中顯著,在大規模企業中均不顯著。Panel C中,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僅在融資約束強的企業中顯著,在融資約束弱的企業樣本中均不顯著。綜上可知,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微觀機制具有顯著的異質性特征,在非國有企業、小規模企業、融資約束較強的企業樣本中,均表現出顯著的技術進步、規模效率變動的抑制作用,對純技術效率改善的促進作用等。非國有企業、小規模企業以及融資約束較強的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使得其對僵尸企業的資源擠出效應、市場破壞效應等風險防范能力不足。由于所有制歧視的存在,非國有企業在市場中往往面臨著較強的資金、人才、土地等資源約束和不公平市場競爭待遇,導致中小企業難以獲得信貸資源支持,面臨著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多層次資本市場化體系不完善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融資約束難題。
4. 4 微觀機制拓展分析:基于企業生產率與綠色創新視角
為深入探討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環境生產率以及綠色創新的影響,研究通過匹配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數據庫和專利企業數據庫,設定四個微觀機制變量:①勞動生產率lp,采用單位勞動工業總產值(企業工業總產值/企業就業數)度量。②資本生產率cp,采用單位資本工業總產值(企業工業總產值/企業資本存量)度量。③環境生產率so2,采用企業污染排放強度(單位工業產值SO2排放水平)度量,這一指標越大環境生產率越小。結合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分解理論,上述三個變量體現了技術效率的內涵與特征。④企業綠色技術進步gpa,采用企業綠色專利授權數度量。綠色專利來源于依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綠色專利清單》中在線檢索工具(https://www. wipo. int/classifications/ipc/en/green_inventory/),筆者在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SIPO)專利數據庫中分年度檢索綠色技術專利數據,并根據IPC分類號識別、匹配、加總企業層面綠色專利授權數量。考慮到綠色專利分為替代能源、交通、節能、廢物管理、農林、行政管理和核電等七大類,參照齊紹洲等[32]的研究,僅選取直接相關的廢棄物管理類、替代能源類和節能類等三類專利加總,作為企業綠色創新活動的核心衡量指標。相關變量均取對數處理。
表8報告了機制檢驗結果。列(1)與列(2)顯示,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不過,后者未能通過顯著水平檢驗。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僵尸企業具有就業擠出效應[5],加劇了正常企業熟練工人、技能人才的流出,也增加了企業雇傭成本和企業新就業人員適應性成本,通過以上渠道降低了正常企業勞動生產率。列(3)顯示,僵尸企業加劇了正常企業的污染排放強度、降低了其環境生產率。原因在于,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的投資擠出效應,顯著增強了正常企業在污染治理投入、污染設備引入方面資金約束,加劇了正常企業的污染排放。最后,根據列(4)估計結果,僵尸企業降低了正常企業的綠色專利數,不利于正常企業綠色創新,但未通過顯著水平檢驗,這一結論,與上文中綠色技術進步渠道不顯著相互印證。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該研究基于新近公布的2006—2014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工業企業污染數據庫的匹配數據,分別基于FN?CHK修正方法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識別僵尸企業、測算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指數,探討了僵尸企業對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負面影響及機制。為緩解數據遲滯問題,同時基于2004—2018年上市公司僵尸企業的識別以及省級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測算數據進行了交叉驗證分析,結論穩健。結果顯示:第一,僵尸企業不僅造成了自身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7. 9%,還不利于其他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僵尸企業占比增加1個百分點,則正常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下降2. 733%,最終,僵尸企業的存在使得總體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絕對下降了3. 27%,相對水平下降22. 4%。第二,僵尸企業對于非國有企業、小規模企業以及融資約束強的企業影響更為顯著。第三,僵尸企業抑制了正常企業技術進步、規模效率提升,而且微觀機制在非國有企業、小規模企業以及融資約束較強的企業樣本中更顯著。研究還發現,僵尸企業顯著降低了正常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環境生產率水平。
針對相關結論,該研究的政策啟示有:①加快推動僵尸企業處置,協同推進高質量發展和環境保護。僵尸企業造成了宏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損失3. 27%,拖累了中國高質量發展與綠色轉型。未來要充分認識僵尸企業的環境負外部性特征,加快推動僵尸企業精準處置,淘汰環境污染嚴重、盈利能力弱、創新動力不足、低效率的僵尸企業。堅持市場出清的原則,不斷優化兼并重組方式,激__發部分僵尸企業的市場活力,促進治愈僵尸企業。建立科學的僵尸企業評價體系,充分考慮僵尸企業評價的動態性、多元性特征,在既有僵尸企業識別的國家標準、CHK標準、FN?CHK標準上,結合新發展格局構建生態文明建設背景,加快融合環境污染、效率改善、創新能力、企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創新僵尸企業的識別標準,并將其作為進一步僵尸企業清退工作的基礎。②持續深化市場體制改革,創造公平競爭市場環境。積極鏟除僵尸企業“茍延殘喘”的制度土壤,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全面實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消除企業所有制歧視,形成高效規范、公平競爭的國內統一市場,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另外,國企是僵尸企業的重災區,要求持續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通過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交叉持股,優化企業內部治理結構。③構建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降低企業融資約束。僵尸企業對規模小、融資約束緊的企業破壞性更大。要求不斷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不斷規范和發展主板市場,大力推進風險投資、新三板、創業板、科創板、北交所建設,積極拓展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更好地解決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何帆,朱鶴. 僵尸企業的處置策略[J]. 中國金融, 2016(13):25-27.
[2] 馬紅旗,申廣軍. 規模擴張、“創造性破壞”與產能過剩: 基于鋼鐵企業微觀數據的實證分析[J]. 經濟學(季刊), 2021, 21(1):71-92.
[3] 譚語嫣,譚之博,黃益平,等. 僵尸企業的投資擠出效應:基于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J]. 經濟研究, 2017, 52(5): 175-188.
[4] 王永欽,李蔚,戴蕓. 僵尸企業如何影響了企業創新: 來自中國工業企業的證據[J]. 經濟研究, 2018, 53(11): 99-114.
[5] 肖興志,張偉廣,朝鏞. 僵尸企業與就業增長:保護還是排擠?[J]. 管理世界, 2019, 35(8): 69-83.
[6] 金祥榮,李旭超,魯建坤. 僵尸企業的負外部性:稅負競爭與正常企業逃稅[J]. 經濟研究, 2019(12): 70-85.
[7] 孫博文. 清潔生產標準實施對污染行業僵尸企業的處置效果[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21, 31(11): 48-58.
[8] 吳清揚. 僵尸企業如何影響企業污染排放:微觀環境數據實證[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21, 31(11): 34-47.
[9] 孫博文,張友國. 中國綠色創新指數的分布動態演進與區域差異[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22(1): 51-72
[10] 紀洋,譚語嫣,黃益平. 金融雙軌制與利率市場化[J]. 經濟研究, 2016, 51(6): 45-57.
[11] KWON H U, NARITA F, NARITA M. Resource reallocation andzombie lending in Japan in the 1990s[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15, 18(4): 709-732.
[12] TAN Y, HUANG Y, WOO W T. Zombie firms and the crowdingoutof private investment in China[J]. Asian economic papers,2016, 15(3): 32-55.
[13] 王守坤. 僵尸企業與污染排放:基于識別與機理的實證分析[J]. 統計研究, 2018, 35(10): 58-68.
[14] CABALLERO R J, HOSHI T, KASHYAP A K. Zombie lending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Japa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8, 98(5): 1943-1977.
[15] RAY S C, DESLI E.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omment[J].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1997, 87(5): 1033-1039.
[16] FARE R, GROSSKOPF S, PASURKA C A. Environmental productionfun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J]. Energy, 2007(32): 1055-1066.
[17] 焦國華,江飛濤,陳舸. 中國鋼鐵企業的相對效率與規模效率[J]. 中國工業經濟, 2007(10): 37-44.
[18] 許江波,卿小權. 僵尸企業對供應商的溢出效應及其影響因素[J]. 經濟管理, 2019, 41(3): 56-72.
[19] 李旭超,羅德明,金祥榮. 資源錯置與中國企業規模分布特征[J]. 中國社會科學, 2017(2): 25-43, 205-206.
[20] 喻坤,李治國,張曉蓉,等. 企業投資效率之謎:融資約束假說與貨幣政策沖擊[J]. 經濟研究, 2014, 49(05): 106-120.
[21] 李鵬升,陳艷瑩. 環境規制、企業議價能力和綠色全要素生產率[J]. 財貿經濟, 2019, 40(11): 144-160.
[22] 聶輝華,江艇,張雨瀟,等. 我國僵尸企業的現狀、原因與對策[J]. 宏觀經濟管理, 2016(9): 63-68,88.
[23] 邵帥,尹俊雅,王海,等. 資源產業依賴對僵尸企業的誘發效應[J]. 經濟研究, 2021, 56(11): 138-154.
[24] 盛丹,李蕾蕾. 地區環境立法是否會促進企業出口[J]. 世界經濟, 2018, 41(11): 145-168.
[25] 豆建民,汪增洋. 經濟集聚、產業結構與城市土地產出率:基于我國234個地級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 2010, 36(10): 26-36.
[26] CHUNG Y H,FARE R, GROSSKOPF S. 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 Journal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7(51): 229-240.
[27] FUKUDA S, NAKAMURA J. Why did zombie firms recover in Japan?[J]. World economy, 2011, 34(7): 1124-1137.
[28] 孫博文,柳明,張偉廣. 僵尸企業識別研究綜述:修正與異質特征: 基于企業產品創新的視角[J]. 宏觀質量研究, 2019, 7(3): 79-98.
[29] 陳登科. 貿易壁壘下降與環境污染改善:來自中國企業污染數據的新證據[J]. 經濟研究, 2020, 55(12): 98-114.
[30] NUNN N, QIAN N. US Food aid and civil conflict[J].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2014, 104(6): 1630-1666.
[31] 江艇. 因果推斷經驗研究中的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J]. 中國工業經濟,2022(5):100-120.
[32] 齊紹洲,林屾,崔靜波. 環境權益交易市場能否誘發綠色創新:基于我國上市公司綠色專利數據的證據[J]. 經濟研究, 2018,53(12): 129-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