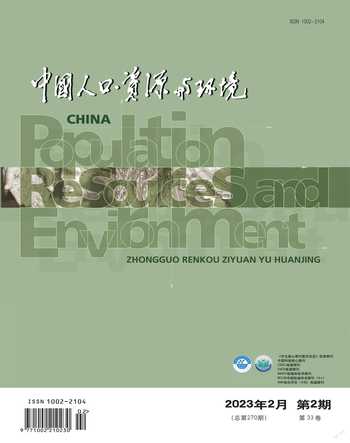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變
張國興 張婧鈺



摘要 黃河流域是鞏固小康社會建設成果的重要戰略區,實現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有助于提高流域地區經濟實力、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該研究通過改進的CRITIC賦權法對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定,然后利用均衡熵模型、基尼系數和核密度估計進行時間分析,在此基礎上通過障礙度模型分析影響其高質量發展的因素。通過研究發現:①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整體上呈現平穩波動的發展趨勢,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的均衡熵存在較為明顯的時空差異。②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整體差異正在逐年下降,河段內差異貢獻率變化比較平穩,河段間差異有所下降,超變密度貢獻率有所上升。③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密度函數在研究期內變化較小。函數曲線拖尾情況較不明顯,呈單峰形態,并且峰值有所增加,極化現象逐漸增強。④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影響最大的前5位障礙因子隨時間變化有所變動。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大發展維度對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度具有明顯差異,其中生態發展對整體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度最小。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建議:①加強黃河流域頂層設計,理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間的關系,應從國家角度做好黃河流域區域環境保護、產業優化轉型、資源有效利用、污染防控治理及文化傳承保護。②構建黃河流域“大治理”格局,注重東西聯動的區域發展戰略,形成以點帶面的區域發展局面,突破原有經濟地理格局。③打造黃河流域動力源,聚力突破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困境,全面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區域輻射力。
關鍵詞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生態保護;高質量發展;時空演變
中圖分類號 F299. 27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3)02-0124-10 DOI:10. 12062/cpre. 20221011
黃河流域又被稱為“能源流域”,流域內富含多種礦產資源,其中以煤炭資源儲量最為豐富,約占全國總量一半以上。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作為以資源開發為主的區域,在黃河流域城市總數中占有相當比例,生態安全壓力最為明顯。如何推進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實現高質量轉型發展成為落實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國家戰略的關鍵。因此,該研究以黃河流域36個資源型城市為研究樣本,探討分析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變規律,期望為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轉型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1 文獻綜述
生態平衡、社會穩定是現階段資源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需求下不可突破的最后一道防線,對保障城市生態系統正常運轉、支撐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隨著資源開采程度的不斷加深,資源型城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能源枯竭、環境受損以及經濟發展緩慢等各種客觀問題,嚴重制約著資源型城市發展的速度和質量。Ross 等[1]指出很多資源型城市正在對自身發展做出根本性的改變以求達到資源產業與非資源產業的平衡增長。Kochergin 等[2]指出資源型地區知識經濟的形成受到資源詛咒效應和路徑依賴效應的雙重影響,自然資源豐富的區域可以通過結構性經濟政策向知識型發展過渡。進入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受重工業發展及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資源詛咒負面影響初步顯現,再加上替代能源沖擊等一系列外部影響產生了眾多制約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因素。對于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困境,宋煜[3]指出制約資源型城市轉型的主要因素在于產業結構不合理、政府服務能力低于預期、可持續發展機制落實難度大三個方面。隨著高質量發展成為近些年來資源型城市轉型的主要目標,各地政府致力于尋求既能促進經濟發展,又能維護生態社會和諧的綜合發展路徑。劉純彬等[4]指出資源型城市綠色轉型由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四方面共同提供發展轉型的內生動力,通過企業綠色經營、產業綠色發展、政府綠色監管實行轉型。孫曉華等[5]提出要根據地區特色因地制宜選擇城市發展戰略,資源衰竭型城市應選擇差異化的轉型發展方向。
黃河流域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難點地區,其高質量發展程度與社會轉型及深刻變革息息相關。任保平等[6]提出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要堅持生態優先,推進黃河流域系統性治理。金鳳君等[7]認為黃河流域以重化工為主的單一產業結構加重了生態環境負擔,要想實現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必須處理好城市經濟結構與流域生態安全的關系。資源型城市作為生態壓力最大的地區之一,其高質量發展成效更是重中之重。對于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效果和能力,部分學者通過實證數據對其進行評價。喻登科等[8]根據“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構建指標體系;謝遠濤等[9]通過創新環境、創新投入、創新產出和創新績效來衡量資源型城市創新能力;沈路等[10]從經濟全面發展、社會協調發展、環境友好發展三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
此外,也有部分學者以高質量發展作為切入點研究其影響機理、資源利用、產業升級等方面。從影響機理的角度來看,高志剛等[11]通過研究發現政府創新支持對資源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存在積極影響,制度質量能通過激勵政府創新支持從而促進高質量發展;王曉楠等[12]認為人均GDP和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對資源型城市轉型效率存在正向作用。從資源利用來看,李婉紅等[13]基于調節效應研究自然資源稟賦與產業結構轉型的關系;丁一等[14]通過SSBM模型測算資源型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從產業升級方面來看,鄭飛鴻等[15]實證分析了科技環境規制對中國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的倒逼效應和門檻效應;李博等[16]通過DEA模型研究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互動關系。還有一些學者基于全國層面[17]、省域層面[18]、特定區域[19]等角度對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進行深入研究探討。
縱觀國內外已有成果,學者們對資源型城市轉型、高質量發展等研究已經擁有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關注到了中國資源型城市高質量轉型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得出了頗有啟發性的結論,為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對黃河流域這一承載著“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重大國家戰略”的特殊地理經濟區研究相對較少,忽略了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的特殊性。為此,該研究運用改進的CRITIC 法測度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狀態,對2010—2020年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時空演變及阻礙因素進行分析,可為現有研究提供補充和借鑒。
2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測度
2. 1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特征
黃河大致呈“幾”形自西向東流經青海、甘肅、內蒙古等9個省份,流域內煤炭、天然氣等能源十分豐富,是中國重要的能源支撐基地。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指依資源而生、因資源而立的城市,這些城市大多依托資源開采加工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容易陷入路徑依賴的陷阱,存在著生態環境脆弱、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綠色發展水平低等眾多問題。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數量多,分布廣,因為其獨特的地理環境與歷史底蘊,除了其他資源型城市所通有的城市特征外,還具有獨屬于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的城市特征。
2. 1. 1 資源型城市生態底子較差,環境承載力弱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所涉及的生態脆弱區種類繁多,黃河流域上游主要涉及林草交錯生態脆弱區和復合侵蝕生態脆弱區,環境差異性較高,植被景觀容易破碎;中游的黃土高原是全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區域之一,黃土高原土質疏松,植被覆蓋較少,涵養水源能力較低;下游的黃河三角洲是依托于黃河自身攜帶的泥沙沖刷沉積而形成的,并且三角洲的植被演化出現逆向發展,生態系統較為脆弱。
2. 1. 2 資源型城市以能源產業為主導,資源稟賦差異較大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主要以能源化工、原材料加工等產業為主導產業,歷史遺留問題較為嚴重,缺乏具有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并且不同城市所擁有的資源能源儲備差別較大,水資源主要集中于青海省和四川省,石油資源主要集中于下游的濮陽市、東營市等,煤炭資源主要集中于中上游的鄂爾多斯市、石嘴山市、大同市、焦作市和慶陽市等。不同的資源儲備類型使得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各具特征。
2. 1. 3 資源型城市間經濟聯系不緊密,民生發展較弱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的跨河段聯系度不高,區域分工協調發展意識不強,高質量協同發展相關的機制體制尚不完善。因為制造業等其他產業發展較為緩慢,對資源利用不夠徹底,導致高耗能高污染項目不斷重復影響城市發展。另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程度相對較低,醫__療、教育等重要社會資源提升空間較大,重要商品和民生物資的儲備有待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2. 2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測度方法
2. 2. 1 改進的CRITIC賦權法
CRITIC賦權法是基于對比強度和指標沖突性計算指標權重的一種方法。對比強度通常用標準差的形式表現,指標沖突性通常用相關系數體現,該方法可同時兼顧指標變異性和指標相關性[20]。該研究采用CRITIC賦權法對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標予以賦權,在一般CRITIC賦權法的基礎上,用離散系數代替標準差作為對比強度,從而能更好地體現數據的離散程度。
2. 3 指標體系構建與數據來源
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容是使中國從之前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向更為科學的發展模式轉變,即從人與自然相離散的狀態向人與自然互相融合的狀態轉變,從經濟、社會和生態背道而馳的局面轉變為三者并駕齊驅的新格局。高質量發展是一個系統性的過程,需要眾多因素共同在其中發揮作用。該研究在遵循科學性、全面性、系統性等原則的基礎上,參考師博等[25]的研究成果,從經濟優化升級、生態安全健康和社會和諧幸福三個方面利用改進的CRITIC 法對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具體評價指標見表1。
2. 3. 1 經濟優化升級
高質量發展不唯經濟發展不代表不重視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一直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經濟優化升級需要考慮經濟穩定性、強度、開放性、高級性、合理性與科學性。①經濟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對未來的經濟發展狀況進行預測,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增長在合理范圍內進行波動,用GDP增長率表示。②經濟強度表示一段時間內區域的經濟活力,經濟強度越高經濟活力越強,要素資源流通效率越高,采用人均GDP 衡量。③開放性體現出了資源型城市與外界經濟交流的程度。合理利用外資有助于推動技術進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和擴大就業,該指標用萬元GDP實際利用外資額衡量。④產業結構高級化有利于中國產品市場向生產鏈高端進行延伸,有效聚集生產要素,推動傳統重化工業進行改造升級,用產業結構高級化即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比重體現。⑤產業結構合理化可以使生產要素達到最大化利用程度,推進中國產業格局合理升級,借鑒干春暉等[26]的研究,利用泰爾系數反映產業結構合理化。⑥高質量發展需要科技作為內生助推力,科學技術的進步能夠大幅度減少產品成本,促進經濟發展[27],用萬元GDP科技支出表示。
2. 3. 2 生態安全健康
生態安全健康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基石,體現出城市經濟綠色發展的結果,生態安全健康既要考慮污染排放也要考慮污染治理。污染排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通過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并對排放的污染物做無害化處理,減少對周圍生態環境的傷害。選取單位面積廢水排放量、單位面積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單位面積工業煙(粉)塵排放量作為對污染物排放量的衡量[28],采用污水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和全年空氣優良天數代表當地政府對污染物處理的力度,最后用綠化覆蓋率作為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基礎評價。
2. 3. 3 社會和諧幸福
社會和諧、民眾幸福是國家發展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成果要普及到每一個民眾。采用城鎮登記失業率衡量民眾就業情況,就業情況與居民收支息息相關,良好的就業情況可以增加居民收入;用每萬人擁有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衡量城市教育水平;用每萬人擁有醫生數代表城市所提供的醫療水平;用人均道路長度表示居民所擁有的交通設施水平;用每萬人互聯網用戶數表示城市居民接觸新型設施的程度;用每萬人公共圖書館藏書量表示城市免費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水平。
根據《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黃河流域綜合規劃(2012—2030年)》的分類,黃河流域共涉及37個資源型城市,因萊蕪市2019年被歸入濟南市,故基于數據可獲得性不在該研究范圍內,因此研究對象為36個資源型城市。主要數據來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1—2021)、各省市統計年鑒與統計公報,部分缺失數據通過插值法進行填補。
3 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時空演變分析
3. 1 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時序演變
3. 1. 1 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時間演變趨勢
圖1顯示,研究期內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均值為0. 438,整體高質量發展水平圍繞發展均值呈現平穩波動的趨勢,不同年份間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小,并未出現大幅度變動。
研究中將高質量發展水平分解為社會、生態和經濟三個維度,研究期間內經濟維度得分均值為0. 102,社會維度得分均值為0. 092,生態維度得分均值為0. 244,三個維度得分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從經濟優化升級方面來說,該方面得分最高在2011年為0. 112,最低在2019年為0. 084,對整體得分的貢獻率最高為26. 01%,最低為19. 9%。經濟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助推力,在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低于預期,誠然有部分外部因素影響,最主要原因依舊是資源枯竭使得資源依賴性產業發展減緩,導致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受限。從生態安全健康方面來說,該方面得分最高在2013 年為0. 259,最低在2016年為0. 235,對整體得分的貢獻率最高為58. 9%,最低為52. 67%,均超過50%。生態安全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前提,從圖1可以看出生態安全對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推動力約等于社會和經濟兩方面之和,資源型城市一直較為重視城市環境安全,實行經濟、環境共同發展。從社會和諧幸福方面來看,該方面得分最高在2012年為0. 101,最低在2019年為0. 082,對整體得分的貢獻率最高為21. 87%,最低為19. 43%。社會和諧、人民幸福是一直以來政府所追求的目標,但從實際情況來看,發展的成果并沒有很好地普及每一個民眾,仍存在發展改善空間。
3. 1. 2 資源型城市均衡熵時間演變趨勢
因為2010、2015和2020年分別對應“十一五”“十二五”和“ 十三五”的收官之年,故選此3個年份作為時間節點進行分析。從圖2可以看出,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的均衡熵存在較為明顯的時空差異,同一時間點不同資源型城市均衡熵存在差異,同一城市不同時間點的均衡熵變化也較大。均衡熵主要將城市當前高質量發展水平與耦合協調度相比較從而估計城市未來發展潛力,一般認為均衡熵超過1發展潛力較大。2010年時,均衡熵最低的城市是大同市,均衡熵為0. 912,最高的城市為慶陽市,均衡熵為2. 150。2015 年時,得分最低的是棗莊市為0. 932,得分最高的是呂梁市為2. 121。2020年均衡熵最低的城市為淄博市0. 900,得分最高的為延安市1. 832,最高城市與最低城市之間的差值從1. 267縮小到0. 936,表明城市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差異有所減少。
縱向來看,2010年均衡熵超過1的資源型城市共有13個,2015年下降到10個,2020年上升到11個,總體個數變化不大。相比于2010年的均衡熵值,2020年數值有所上升的城市共有14個,約占總數的38. 89%。其中,數值增加最大的為臨汾市,上升了0. 827,數值減少最大的為慶陽市,下降了0. 418。臨汾市在研究期間,著力擴大政府投資和招商引資力度,促進消費數額回升,穩步推進現代農業和旅游業發展,減少資源依賴性企業,重點實施扶貧救助,落實解決環境歷史遺留問題,群眾幸福感不斷增加,環境內生驅動力發展和諧,城市發展相對均衡,未來仍可繼續發展。從內部驅動情況來看,慶陽市均衡熵數值下降主要受經濟方面的影響。慶陽市是典型的能源化工城市,過去主要以開采加工為主導產業,因城市資源儲備減少導致經濟發展圖1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趨勢大幅減速,經濟增長和財政增收的動力不足,__政府負債壓力較重,并且產業轉型升級任務艱巨,重大支撐項目相對較少,基礎設施瓶頸制約仍比較突出。
3. 2 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空間演變
3. 2. 1 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差異及其分解
2010—2020年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流域整體基尼系數、河段內基尼系數、河段間基尼系數以及貢獻率計算結果見表2。
(1)表2顯示整個研究期間內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基尼系數均值為0. 033,整體上呈現先降低再增加后減少的倒“N”形,說明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差異正在逐漸縮小。2010—2011年、2016—2018年兩個時間段內基尼系數高于整體平均值,其余時間段內基尼系數低于整體平均值,即流域差異具有不斷縮小的傾向。從演進過程來看,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基尼系數2010—2016 年呈現波動趨勢,整體比較穩定。2016—2017年基尼系數迅速從0. 033上升到0. 038,自從2017年高質量發展的概念提出之后,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大力推進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開發清潔能源,加強上中下游聯系,高質量發展差異不斷縮小,截止到2020 年縮小為0. 030。
(2)從表2整體基尼系數和河段內基尼系數可知,研究期間內上游、中游及下游的基尼系數均大于整體流域基尼系數,并且隨著時間發展中游的基尼系數逐漸大于上游和下游系數值,表明不同河段內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差異明顯。上游基尼系數整體呈現階梯型下降趨勢,從2010年的0. 133下降到了2020年的0. 054, 降幅接近60%。中游從2010年到2016年變化較為穩定,2017年略有上升達到最高點0. 103,隨后開始下降。下游除2016年偏離程度較大之外,總體在均值0. 065附近波動,無大幅度增降。
(3)由表2河段間基尼系數可以看出,上-下游之間相對差異在逐步減小,上-中游之間相對差異無太大變化,中-下游之間的相對差異略有增加,且上-中游、上-下游和中-下游之間的基尼系數均超過整體流域平均水平。上-中游基尼系數整體變化較為平穩,并未出現大幅波動。上-下游基尼系數自2011年之后就呈現出下降的趨勢,從2011年的0. 125下降到2020年的0. 059,降幅約達53. 15%,表明上下游之間高質量發展差異明顯縮小。中-下游基尼系數自2010年之后開始逐漸上升,在2017年達到最高點0. 133之后開始下降,表明中下游高質量發展差異前期有所增加隨后又不斷減小。
(4)從表2貢獻率結果可知,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河段內差異變化比較平穩,河段間差異與超變密度的變化態勢相對較大。其中,河段內相對差異貢獻率最大,基尼系數變化較為平穩,基本維持在均值左右浮動。河段間基尼系數總體上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從2010 年的35. 87% 下降到2020 年的27. 3%,表明河段之間產生的高質量發展差異正在不斷縮小。超變密度從2010年的27. 81%上升到2020年的39. 01%,也就是說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較高(低)的地區出現了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高)的城市,且這種趨勢正在不斷擴大,導致超變密度貢獻率持續上升。總體來看,要縮小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差異不僅要注意河段間的聯系合作,更要關注河段內城市的共同發展狀況。
3. 2. 2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動態演進
基尼系數主要刻畫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相對差異及其來源,核密度函數可以通過曲線形態的演變判斷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絕對差異。選取2010、2015和2020年3個時間節點,采用核密度估計描述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具體變化見表3。
從分布位置看,在流域整體及中游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核密度曲線密度函數中心在研究期內變化較小,上游密度函數中心出現明顯右移,表明上游高質量發展水平隨著時間變化有所增加,下游密度函數中心先是右移后是左移,表明下游高質量發展水平先上升后下降。
從分布態勢看,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相對穩定,中游地區略有增加,上游地區和下游地區發展差異呈現縮小趨勢。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核密度曲線表現出主峰高度上升,寬度逐漸變窄的趨勢,意味著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絕對差異有縮小趨勢。上游變化趨勢與整體相似,但是相對于整體變化的幅度更大。上游高質量發展差異縮小的主要原因是甘肅省的金昌市、白銀市、武威市和張掖市四個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得分有所增加。甘肅省持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生態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以及文化旅游業,加快科技產出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深刻吸收祁連山生態問題教訓,大力進行污染治理和生態保護變革,促進高質量發展。中游核密度函數相對于2015年峰度有所上升,寬度輕微增加,表示區域內高質量發展差異有輕微增加,但整體變動不大,影響較小。下游高質量發展核密度曲線峰值上升,寬度有所減少,說明下游高質量發展差異有所減小。
從分布延展性看,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拖尾情況有所緩解,相對來說更向中心靠攏,呈現收斂趨勢,意味著區域內部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的城市有所提升,趨近于地區高質量發展平均水平,呈現出追趕效應。得益于黃河流域一體化政策的實施,黃河流域內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間紛紛開展多領域合作,加強經濟聯系,深化產業合作,有效改進上中下游高質量發展分散的情況。上游核密度曲線呈現右拖尾情況,表明地區內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發散趨勢,主要原因可能是黃河流域上游地域較廣,部分城市經濟發展較為落后,且主要支撐產業為重化工產業對環境污染較大,再加上城市基礎設施較為落后,民眾生活幸福感和滿意度不高,導致相比中下游發展差異較大。下游核密度曲線呈現右拖尾情況,主要原因可能是淄博、東營等長期以來發展較好的城市不斷吸引周圍要素集聚,削弱了城市對周圍的溢出效應,導致區域內分布不收斂。
從分布極化性看,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高質量發展呈單峰形態,并且峰值有所增加,極化現象逐漸增強。上游從2010年的分散轉化為2020年的單峰形態,主峰峰值高于側峰,主要極點仍是發展水平較高的資源型城市。中游從多極化轉變為單極化,內部發展更為均衡,下游始終保持著單極化趨勢。
3. 3 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因子
在研究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整體態勢之后,選取2010、2012、2014、2016、2018及2020年作為代表年份,對影響其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因素進行分析。因指標較多,在這里選取障礙度排名前五的障礙因子進行具體分析,具體結果見表4。總體來看,對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影響最大的前5位障礙因子隨時間變化有所變動,但每萬人擁有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產業結構合理化、人均GDP 3個障礙因子每年出現的頻率為100%,每萬人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出現頻率為83. 33%。其中,每萬人擁有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和每萬人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常年位于第1、2 名,對高質量發展影響__較大。經濟強度、產業結構合理化等指標對高質量發展水平均有影響。經濟穩定增長是一個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前提條件,穩定的經濟環境會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條件,民眾對未來抱有希望,消費投資正常進行從而促使社會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緊密聯系,一方面經濟增加可以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演進,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也會促進經濟進步。另外,高素質勞動力占比不斷增加,有助于推進產業升級轉型,是經濟增長的新優勢。因此,今后發展的重點應放在增加教育投入、優化產業結構、提高居民基本收入水平等方面。
從圖3可以看出,經濟、社會、生態三大發展維度對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度具有明顯差異。生態發展對整體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度最小,原因可能在于資源型城市積極優化城市產業結構,尋找替代清潔能源,通過新興技術與科技成果轉化等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減少對環境有害的污染物排放,因此與其他維度相比障礙度較低。經濟維度和社會維度對高質量發展的阻礙度不相上下,都呈現出波動的趨勢。一方面反映出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相對較為緩慢,城市產業結構布局不夠合理,創新投入產出不如預期,開放性仍有待加強,另一方面反映出資源型城市社會基礎城市建設、文化建設等不夠完善,醫療資源和教育資源仍較為稀缺,今后應重點關注。
4 結論與建議
4. 1 結論
資源型城市實現高質量發展對緩解黃河流域環境壓力,滿足人民生活需要,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該研究從經濟優化升級、社會和諧幸福和生態安全健康三個方面構建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通過分析其時空特征從而識別其關鍵障礙因素,得出主要結論如下。
(1)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平穩波動的趨勢。不同年份間高質量發展水平差異較小,并未出現大幅度變動。黃河流域資源型各城市的均衡熵存在較為明顯的時空差異,同一時間點不同資源型城市均衡熵存在差異,同一城市不同時間點的均衡熵變化也較大。
(2)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差異正在逐漸縮小。研究期間內中游的基尼系數逐漸大于上游和下游系數值,表明不同河段內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存在明顯差異。上-中游之間相對差異比較穩定,上-下游之間相對差異在逐步減小,中-下游之間的相對差異有所增加。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河段內差異貢獻率變化比較平穩,河段間差異有所下降,超變密度貢獻率有所上升。
(3)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核密度函數在研究期內變化較小。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與中游相對穩定,上游地區和下游地區發展差異呈現縮小趨勢,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拖尾情況較不明顯,上中下游核密度曲線均呈現右拖尾情況。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整體高質量發展呈單峰形態,并且峰值有所增加,極化現象逐漸增強。
(4)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影響最大的前5位障礙因子隨時間變化有所變動。每萬人擁有普通高等學校專任教師數和每萬人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常年位于第1、2名,對高質量發展影響較大。三大發展維度對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度具有明顯差異,其中生態發展對整體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度最小。
4. 2 建議
基于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時空演變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幾方面的建議。
(1)加強黃河流域頂層設計,理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間的關系。作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產業優勢和產品優勢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應從國家角度做好黃河流域區域環境保護、產業優化升級、資源高效利用、污染防控治理以及文化傳承保護。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大部分產業層次較低,主導的多為重化工企業,技術型、服務型產業發展較弱,整個流域產業具有明顯的重化工特征。因此,可以通過建立黃河流域產業特區,主要以展示黃河文明作為宣傳要點,使得黃河流域天然擁有的自然景觀、歷史底蘊同文化資源、經濟發展相結合,從而促進本地區所具有的資源優勢向產業優勢轉變,打造黃河沿河畔文明旅游區。城市轉變應以延伸重要產業作為著手點,逐步優化自身產業結構,舍棄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產業,重點發展電子物流、線上服務、金融商務等生產性服務業,激發市場活力,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不忘自身環境保護與歷史傳承。
(2)構建黃河流域“大治理”格局,注重東西聯動的區域發展戰略,形成以點帶面的區域發展局面,突破原有經濟地理格局。中國先后施行過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但這些戰略對東西橫向影響較弱。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戰略應更能體現黃河水自西向東流的地理特點,減緩東西差距。中心城市作為區域高質量發展的典范,對周圍地區有一定的輻射作用,可以很好地將東中西三個區域串聯起來。因此,應以發展較好的城市作為相應的中心城市,建設互聯互通的信息網絡,健全有效合作機制,提供發展經驗供其他城市學習借鑒。還應發揮高質量發展城市的帶動作用和聚集作用,吸引更多高層次人才以及更多的生產要素流入,增強該地區的吸引力,擴大對外輻射面積從而惠及更多資源型城市,在黃河領域形成以點帶面的多核心發展局面,朝著更高質量的綜合發展進發。
(3)打造黃河流域動力源,聚力突破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高質量發展困境,全面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區域輻射力。通過加強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夯實流域高質量發展基礎;通過鞏固糧食和能源安全,突出流域高質量發展特色;通過培育經濟重要增長極,增強流域高質量發展動力;通過對內對外雙向開放,提升流域高質量發展活力。著重注意產業結構升級調整,加大技術創新投入力度,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加快推動產業數字化、城市數字化,發展低排放、低能耗的新型綠色產業,減少對環境的沖擊,實現長久發展。并且應該不斷加大教育投入,穩步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培養一批高素質人才,提供高素質人才就業和創新平臺,深化校地、校企合作,發揮人力資本產業園和“人才有價”平臺作用,同時加強環境管理與環境修復,維持生態環境和諧,為銜接上下游打下良好的生態基礎。
參考文獻
[1] ROSS D P, USHER P J. From the roots up:economic developmentas if community mattered[M]. Croton?on?Hudson,New York: BootstrapPress,1986.
[2] KOCHERGIN D G, ZHERNOV E E, LOGACHEV V A, et al. Resourceregions and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knowledge?based development:escaping the resource curse[R]. 2021.
[3] 宋煜. 資源型城市轉型的困境與出路[J]. 人民論壇,2018(13):94-95.
[4] 劉純彬,張晨. 資源型城市綠色轉型內涵的理論探討[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9,19(5):6-10.
[5] 孫曉華,鄭輝,于潤群,等. 資源型城市轉型升級:壓力測算與方向選擇[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20,30(4):54-62.
[6] 任保平,張倩. 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設計及其支撐體系構建[J]. 改革,2019(10):26-34.
[7] 金鳳君,馬麗,許堞. 黃河流域產業發展對生態環境的脅迫診斷與優化路徑識別[J]. 資源科學,2020,42(1):127-136.
[8] 喻登科,黃悅悅. 中國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J]. 創新科技,2022,22(4):21-30.
[9] 謝遠濤,李虹,鄒慶. 我國資源型城市創新指數研究:以116個地級城市為例[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54(5):146-158.
[10] 沈路,錢麗. 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空間關聯及影響因素分析[J]. 統計與決策,2022,38(13):26-30.
[11] 高志剛,李明蕊. 制度質量、政府創新支持對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基于供給側視角[J]. 軟科學,2021,35(8):121-127.
[12] 王曉楠,孫威.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轉型效率及其影響因素[J]. 地理科學進展,2020,39(10):1643-1655.
[13] 李婉紅,李娜. 自然資源稟賦、市場化配置與產業結構轉型:來自116個資源型城市的經驗證據[J]. 現代經濟探討,2021(8):52-63.
[14] 丁一,郭青霞,秦明星. 黃河流域資源型城市土地綠色利用效率時空演變及影響因素[J]. 農業工程學報,2021,37(19):250-259.
[15] 鄭飛鴻,李靜. 科技環境規制倒逼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升級:理論模型與雙重效應分析[J]. 軟科學,2021,35(12):22-28.
[16] 李博,秦歡,孫威. 產業轉型升級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的互動關系:基于中國116個地級資源型城市的實證研究[J]. 自然資源學報,2022,37(1):186-199.
[17] 譚俊濤,張新林,劉雷,等. 中國資源型城市轉型績效測度與評價[J]. 經濟地理,2020,40(7):57-64.
[18] 袁曉玲,王軍,張江洋. 中國省域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評價與比較研究[J]. 經濟與管理研究,2022,43(4):3-14.
[19] 張夢朔,張平宇,李鶴. 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績效特征與評價方法:基于東北地區的實證研究[J]. 自然資源學報,2021,36(8):2051-2064.
[20] 張立軍,張瀟. 基于改進CRITIC法的加權聚類方法[J]. 統計與__決策,2015(22):65-68.
[21] 王淑婧,李俊峰. 長三角城市群高質量綠色發展的均衡性特征及障礙因素[J]. 自然資源學報,2022,37(6):1540-1554.
[22] 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1997,22(4):515-531.
[23] 張卓群,張濤,馮冬發. 中國碳排放強度的區域差異、動態演進及收斂性研究[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22,39(4):67-87.
[24] 劉軍,邊志強. 資源型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研究:基于新發展理念[J]. 經濟問題探索,2022(1):92-111.
[25] 師博,張冰瑤. 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經濟高質量發展測度與分析[J]. 社會科學研究,2019(3):19-27.
[26] 干春暉,鄭若谷,余典范. 中國產業結構變遷對經濟增長和波動的影響[J]. 經濟研究,2011,46(5):4-16,31.
[27] 黃慶華,潘婷. 長江經濟帶科技創新水平測度及其協同力提升政策建議[J]. 創新科技,2022,22(3):32-41.
[28] 張國興,蘇釗賢. 黃河流域中心城市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構建與測度[J]. 生態經濟,2020,36(7):3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