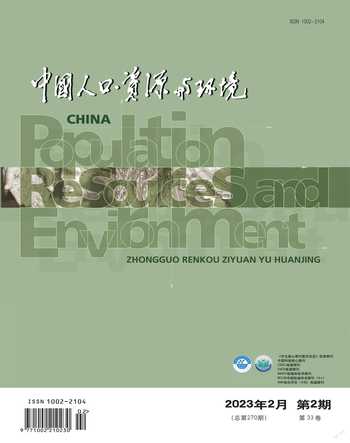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優勢、機制與進路

摘要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對推動脫貧戶從外力幫扶框架中提升自生發展能力,實現生計轉型具有重要意義。從決勝脫貧攻堅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精準脫貧戶”面臨的生計資本和政策框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脫貧戶生計逐漸從以務農為主的“單一型”生計向以擁有抗風險沖擊能力的“多元型”生計轉型,從以解決溫飽為核心的“生存型”生計向以實現可持續穩固脫貧的“發展型”生計轉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建立的,通過“財產聯合”或“勞動聯合”實現“再合作”的經濟形態,能夠把包含脫貧戶在內的廣大農戶組織起來對接“大國家”和“大市場”。通過構建“賦權-增能-包容”的分析框架,識別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理論機制,即通過賦予脫貧戶更充分的農地產權、自由擇業權和市場參與權,將國家資源和政策內化為可量化、可折算的經濟利益,走出“集體產權模糊論”的困局,讓脫貧戶能夠公平分享集體經濟收益;通過在賦權中增能,有效拓展了脫貧戶的發展機會和生計空間,提升了脫貧戶生計轉型能力;加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包容性在黨的領導下能夠賦予脫貧戶機會更加公平、參與權更加保障的制度環境,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為此,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后扶貧時代,只有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領導、宣傳示范、制度供給、要素投入、生產經營、動力培育、聯合管理等“七大”體系,才能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更好地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把脫貧戶完整納入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關鍵詞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脫貧戶;生計轉型
中圖分類號 F321;F328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23)02-0143-10 DOI:10. 12062/cpre. 20221008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中國在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后,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關鍵在于推動脫貧戶從外力幫扶框架中提升自生發展能力[1],實現脫貧戶生計從“生存型”向“發展型”、從“單一型”向“多元型”的雙重轉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政府組織產業扶貧、產業振興的重要載體,也是貧困地區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內生性力量[2]。2018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制定實施貧困地區集體經濟薄弱村發展提升計劃,通過盤活集體資產、入股或參股、量化資產收益等渠道增加集體經濟收入”,同樣在《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也提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進一步提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完善產權權能,將經營性資產量化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從實踐維度看,貴州塘約村“再集體化”[3]、山東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4]等集體經濟發展實踐表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已成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但不可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雖然已被部分村域的發展所證實,然而在全國來看尚未形成良好的發展格局。因此,在學理上理清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內在機理,在實踐上闡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具體進路,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1 文獻綜述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農村的具體實踐形態,其發展遵循了馬克思主義集體所有制下“合作生產”的理論思想,是消除絕對貧困和推動脫__貧戶生計轉型的強大動力,也是脫貧戶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質保障[5]。因此,關于脫貧戶生計轉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及其功能的相關問題也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關注。
1. 1 關于脫貧戶生計及其轉型研究
生計作為“一種生活的手段或方式”,20世紀80年代被引入貧困治理領域[6],“解決貧困人口生計”被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作為消除貧困的主要目標,英國國際發展署提出的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被廣泛應用于農村貧困治理領域,在解決農村貧困問題時開始關注生計問題[7]。以阿瑪蒂亞·森為代表的能力貧困理論把貧困定義為社會生存、適應及發展能力的低下,因而實現貧困戶的可持續穩固脫貧,就應該提高貧困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這種能力亦被稱為可行能力,構成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的核心范疇[8]。根據這一框架,農戶會根據自然環境與社會政策、家庭生計資本的變化對生計進行調整,表現為重新組合生計資本或者重新選擇生計活動[9-10]。因此,貧困戶生計并沒有一種固定的模式,而且總是根據生計資本、生態環境、社會政策的變化處于不斷的調適過程之中,這種調適和轉變的過程就是貧困戶生計轉型的過程[11]。在中國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之后,脫貧戶面臨的生計五邊形(物質、人力、自然、社會、金融)空間向外擴張,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占比逐年上升,脫貧戶自生發展能力穩步提高[12]。新時期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應以促進包括脫貧戶在內的全體農村居民的生計轉型為根本導向,即推動脫貧戶從外力幫扶框架中提升自生發展能力,實現生計向“發展型”和“多元型”轉型[13-14]。
1. 2 關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及其功能研究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消滅雇傭勞動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一個集體的、以生產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15],是無產階級徹底擺脫貧困的根本出路,“在這種社會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將生產得很多,使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完全自由地發展和發揮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16]。遵循這一理論思想,農村集體經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工作中的立基之石[17],早在1931年就提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18],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經歷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的發展探索,形成“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制度框架,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逐步形成“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探索出農村集體經濟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19]。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村走向新型集體經濟的道路,但這并不是“走回頭路”,而是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再合作”,不僅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而且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實現了“黨的領導、共同富裕、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機融合,破解了農戶“動力”與“能力”的矛盾和農村經營“統”“分”困局,與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顯著的契合性。加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內生于鄉村社會“公有制”形式的經濟組織,具有合作傳統、組織基礎和治理優勢[21],能夠把包括貧困戶在內的廣大農戶組織起來,讓脫貧戶有能力參與市場活動和對接國家資源,并將其內化為自我發展能力,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22]。
綜上所述,在全面擺脫絕對貧困之后,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應納入鄉村振興的總體框架,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23]。有別于已有文獻,該研究回歸后脫貧時代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這一現實問題,從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把脫貧戶組織起來對接“大國家”和“大市場”的優勢出發,構建“賦權-增能-包容”的分析框架識別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內在機制,并在實踐上闡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具體進路,以期為更好地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提供鏡鑒參考。
2 后脫貧時代脫貧戶生計轉型的特征事實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貧困戶的生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和扶貧政策框架的變化而變化,2020年脫貧攻堅戰的勝利標志著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推動減貧進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新階段,導致“精準脫貧戶”的面臨的生計資本和政策框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脫貧戶生計逐漸向“多元型”生計和“發展型”生計轉型。
2. 1 從“單一型”生計向“多元型”生計轉型
土地自古以來就是農戶維持生計的基礎和第一就業空間,1949年以后黨和人民政府圍繞農戶的貧困問題,在全國開展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全國無地或少地的3億農民共分得約7億畝(1畝≈666. 7 m2,以下同)土地[24],1958年1月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嚴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動,廣大農戶被限制在土地上,絕大多數貧困戶生計是以務農為主的“單一型”生計。改革開放后隨著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和規模龐大的民工潮的逐漸興起,非農產業逐漸成為包括貧困戶在內的廣大農戶的第二就業和增收空間,貧困戶生計也逐漸從傳統純農業生產型向農業生產為主型、非農活動為主型轉變[25]。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脫貧戶面臨的生計資本和制度環境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鄉村產業振興和三產融合步伐不斷加快,依托農業景觀、鄉村文化和生態環境,發展特色產業、鄉村__旅游、休閑農業等已成為主流趨勢,脫貧戶生計從以務農為主的“單一型”生計向以擁有抗風險沖擊能力的“多元型”生計轉型也成為必然趨勢。
2. 2 從“生存型”生計向“發展型”生計轉型
貧困戶在不同階段面對的現實需求是不同維度、不同層面的。改革開放初期,面臨吃不飽飯、經濟低效、發展緩慢的實際,貧困戶生計以解決溫飽、維持基本生存為主要目標,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和大規模開發式扶貧,貧困戶生計也開始擺脫以解決溫飽為核心的“生存型”生計,持續三十年的“1978年貧困線標準”是按1978年價格每人100元為貧困線確定低水平的溫飽型貧困標準,直到2008年以2000年價格每人865元為貧困線確定基本滿足溫飽的貧困標準[26]。黨的十八大以來,決勝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有脫貧戶完整達到了“兩不愁三保障”脫貧目標,極大拓展了生計資本邊界,其中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脫貧戶住房安全拓展了物質資本的邊界條件,教育扶貧提升了脫貧戶的人力資本水平并阻斷了貧困代際傳遞的可能,“兩山論”的實踐和生態扶貧拓展了脫貧戶的財富邊界,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改變了脫貧戶面臨的社會環境,普惠金融的發展拓展了脫貧戶的信貸可及性。因此,后脫貧時代脫貧戶面臨的是容易返貧的脆弱性問題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相對貧困問題,生計也由以解決溫飽的“生存型”生計向以實現可持續穩固脫貧的“發展型”生計轉型。
3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新優勢
脫貧戶是通過打贏脫貧攻堅戰達到“兩不愁三保障”的脫貧目標,家庭年人均純收入超過了當地農民的貧困線識別標準,實現“精準退出”的原貧困戶,但如何讓脫貧基礎更加穩固、成效更可持續,必須完整地解決好“扶上馬送一程”中“送一程”的問題,推動脫貧戶提升自生發展能力,實現生計轉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建立的,以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價值導向,集體成員通過合作與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27],能夠通過“再合作”的發展包容性把脫貧戶組織起來對接“大國家”和“大市場”,對接“大國家”能夠實現國家資源和政策的精準對接,并將其內化為自生發展能力;對接“大市場”能夠提升脫貧戶市場參與能力和水平,形成可持續生計。因此,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僅是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的重要經驗,而且在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具有獨到優勢。
3. 1 組織脫貧戶對接“大國家”
新中國成立后,經過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運動,依托生產大隊、人民公社等把廣大農戶組織起來,不僅鞏固了黨和國家在農村工作的基礎,而且極大地降低了國家與農戶之間的交易成本,改善了農戶的生產經營條件。改革開放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讓農業生產重新回到小農戶的組織形式,但沒能很好地解決農業生產“統”的問題,農村經營陷入“統”“分”困局[28]。在貧困地區,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村民自治組織有名無實,所謂的集體經濟組織早已名存實亡。進入21世紀以來黨和國家推動的農業專業合作組織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并未實現與小農戶的有機融合,大量分散的脫貧戶不僅無法表達自己的實際需求,也無力融入政府組織的大項目,難以對接“大國家”[29]。加之絕大多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被大戶和精英控制,成為套取國家補貼的假合作組織,導致分散的脫貧戶難以對接國家巨大的扶貧資源,而且扶貧資源配置的“精英俘獲”加劇了農村社會的分化[30]。
中國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實踐表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依托自身的組織基礎和治理優勢,把分散的脫貧戶和一般農戶組織起來,把分裂的農村社會重新整合起來,以合作與聯合再造村社共同體對接國家資源和政策,實現組織再造基礎上的賦權增能,可以有效解決“大國家”與“小脫貧戶”之間交易成本過高和資源供需不匹配的問題,提高國家向農村轉移資源的利用效率。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投入從2013年的381億元增加到2020年的1 465億元,累計達6 600億元,而且同期各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累計投入高達15 980億元,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徹底消除農村絕對貧困提供了基礎性支撐,但也導致農村形成巨大的扶貧資金資產存量,加之“脫貧不脫鉤、脫貧不脫政策、脫貧不脫幫扶”的政策要求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序推進,國家將繼續向農村轉移大量資源。以陜西臨潼區為例,2021年全區投入各級財政銜接資金5 715萬元,采取“龍頭企業+集體經濟+產業+脫貧戶”的模式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19個脫貧村年經濟收入全部超過5萬9_↘9_魗元,帶動脫貧戶5 395戶。可見,在后脫貧時代用好這些資源的關鍵在于發揮基層黨組織強有力的組織帶動作用,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把廣大脫貧戶組織起來對接國家資源和政策,并將其內化為自我發展能力,才能實現脫貧戶生計轉型,更好地“送一程”。
3. 2 組織脫貧戶對接“大市場”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小農戶作為“小塊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這塊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種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讓他養家糊口的限度”[31],在生產方式選擇上,“小農生產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對自然的社會統治和社會調節,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32],這就決定了小農生產與先進的生產力無法相融,也直接導致農戶陷入貧困。因此,傳統小農生產的未來出路在于合作化,即在尊重小農意志的前提下,通過示范和提供社會幫助的方式改造傳統小農。然而在脫貧攻堅之初,中國大多數貧困村的集體經濟陷入空殼化,集體經濟收入幾乎為零,經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部署和努力,2020年全國貧困村的村均集體經濟收入超過12萬元,集體經濟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跨越式發展,極大地增強了村級組織自我保障和服務群眾的能力。
在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后,實現脫貧戶生計轉型應納入鄉村振興的總體框架,圍繞“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現實要求和“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充分發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包容性和組織動員能力,通過“勞動聯合”或“財產聯合”把脫貧戶完整納入集體經濟的發展軌道,從而提升農業生產的組織化、規模化和機械化水平,這不僅符合農業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也實現了組織脫貧戶對接“大市場”的要求,使得脫貧戶在市場中的生存力和競爭力有效提升。另外,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為村級組織的正常運轉和激活鄉村沉睡資源提供物質保障,基層黨組織、村委會(居委會)能夠為脫貧戶的生產生活提供更好的服務,進一步激發了脫貧戶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也為提高村集體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創造了優勢條件。在曾深度貧困的新疆沙雅縣,通過土地整理增厚集體經濟“家底”,2020年19個村、6 253戶拿到分紅收入200. 51萬元,其中奧圖拉庫勒達西村通過土地平整新增3 500畝耕地,集體經濟“家底”在230萬元以上,除改善居住生活環境等,還用到支持發展果樹、蔬菜、花卉等高附加值農業經營中,帶動脫貧戶增收。可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載體,能夠組織脫貧戶進行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和對接“大市場”,提升脫貧戶參與市場的能力和水平,并將其內化為自我發展能力,賦能生計轉型。
4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內在機制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通過財產聯合或者勞動聯合,實現“再合作”的經濟形態,能夠把脫貧戶組織起來對接“大國家”和“大市場”,并嵌入科學適宜的自生發展能力培育機制,形成“賦權-增能-包容”的治貧框架,這不僅是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歷史經驗,也是后脫貧時代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必然選擇[33]。因此,從“賦權-增能-包容”的分析框架(圖1)出發,識別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內在機制,對于更好地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意義重大。
4. 1 賦權:分享收益扶持脫貧戶
傳統的貧困理論譜系把貧困問題單純地理解為經濟問題,強調收入平等對貧困治理的極端重要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在資本主義“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下,“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__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34]。無產階級作為物質產品的生產者,卻被剝奪了物質產品的占有支配權,所有的產品都歸資本家占有和支配,這樣“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跡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34],可見,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貧困化的根源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及其衍生權利的缺失。阿瑪蒂亞·森在《貧困與饑荒——論權力與剝奪》一書中明確指出貧困、饑餓及社會不平等的根源在于“權力的喪失和剝奪”,即經濟衰退和物質匱乏并不構成貧困產生的全部原因,在“食物生產富足”的經濟繁榮時期,也可能存在因權利分配不均而引發的嚴重“饑荒”問題。因此,貧困治理必須賦予并保護貧困群體的權利,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重視權利的合理分配。比如,湖北省京山市城畈村作為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村,2016年開始推動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造,綜合評估發現集體經營性資產達到1. 57億元,確定集體經濟組織成員1 815 名,通過以戶籍人口設置基本股、以家庭勞動耕種年限時長設置勞齡股,進一步考慮到集體經濟發展、脫貧戶等特殊人群的利益訴求,增設集體股、特殊股和貢獻股,配置股份49 116. 5股,保障脫貧戶能夠從集體經營性資產收入中分得紅利[35]。
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的全面小康時代,脫貧戶對以土地為載體的集體資產的功能訴求已不再局限于保障生存,而是希望獲得更多的發展權益,實現了從生存理性到發展理性的歷史性轉變,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必須保障脫貧戶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賦予脫貧戶更多的財產權利,構建“多元賦權”的改革方案。首先,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集體”屬性的核心在于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不斷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科學確定集體成員身份,明晰農村集體資產歸屬,賦予脫貧戶等集體成員更加充分的農地產權。其次,脫貧戶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下通過“共同生產、統一經營”實現“勞動聯合”,通過土地、資產、技術等入股實現“財產聯合”,不僅賦予脫貧戶更加自由的擇業權和更加充分的市場參與權,而且理順了集體和個體的物質利益關系,形成了經濟上的利益共同體。第三,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把分散的脫貧戶組織起來對接國家向農村巨大的資源投入,并通過集體成員權將其分解和量化,確認產權身份,為脫貧戶分享收益和參與市場創造條件。因此,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賦予脫貧戶更充分的農地產權、自由擇業權和市場參與權,而且這些權利已被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化為可量化、可折算的經濟利益,走出了“集體產權模糊論”的發展困局,建立了脫貧戶和集體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脫貧戶有了穩定可持續的增收渠道,生計也向“發展型”轉化。
4. 2 增能:提升能力發展脫貧戶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無產階級消除貧困的根本出路在于“剝奪剝奪者”,對于農業工人而言,“只有首先把他們的主要勞動對象即土地本身從大農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奪取過來,轉變為社會財產并由農業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種,才能擺脫可怕的貧困”[36],表明作為無產階級之一的農戶要徹底擺脫貧困,不僅需要“社會財產”的賦權,也需要“勞動聯合”,其中蘊含著“提升能力”的減貧思想。同樣,阿瑪蒂亞·森賦權反貧困思想的實質就是“賦予權力、使有能力”,舒爾茨進一步提出“能力貧困”假說,即農村貧困主要源于農戶人力資本匱乏、健康狀況低下、自由流動受阻等可行能力的剝奪,因此,引入現代生產要素改造傳統農業,不僅要引入農業機械、優良種子、化肥等“物”的要素,還需要對農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培養具有接受能力、能夠運用新生產要素的“人”,而且“各種歷史資料都表明,農民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與其耕作的生產率之間存在著有力的正相關關系”[37]。可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必須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要求,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提升脫貧戶自生發展能力。比如,陜西漢中南鄭區福成鎮堅持黨建引領,圍繞“村村有集體積累,戶戶有產業覆蓋,家家有增收渠道”目標確定村集體優勢主導產業,推行“黨支部+合作社+脫貧戶+農戶”等合作模式,實現所有脫貧戶利益聯結全覆蓋,脫貧群眾累計分紅收益300萬元以上,脫貧戶穩定增收成果得到不斷鞏固拓展。
在賦權中增能,向貧困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百年減貧實踐的核心線索[38]。在絕對貧困治理階段,國家主導的大規模資金、物質、人力等資源要素向農村大量集聚和疊加,短時間內支撐農村貧困人口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的發展目標,但是重外力幫扶、輕內力提升的治理偏向導致脫貧戶自生發展能力缺失,這就需要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階段強化內生發展激勵,提升脫貧戶的生產技術能力、經營能力、合作能力[39]。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多元賦權盤活了農村集體資產,通過優化配置內部生產性資源,不僅強化了脫貧戶對各類產權的實施能力和市場參與能力,而且有效改善了脫貧戶生計資本質量和生計轉型能力。另外,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以“集體組織”支持的脫貧戶技能培訓、教育普及大大提升了脫貧戶的人力資本水平,拓展了脫貧戶的生計轉型能力和生計空間。根據2021年4月25日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發布的數據,自2016年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__開展試點以來,核清農村集體資產65 000億元,集體土地等資源65. 5億畝,確認集體成員9億人,全國共有53萬個村完成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導致脫貧戶不再依附于土地以農為生,從事“單一型”農業生產經營的脫貧戶占比逐年下降,來自非農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可見,農村集體經濟通過給脫貧戶賦權,有效拓展了脫貧戶的發展機會和生計空間,提升了脫貧戶生計轉型能力。
4. 3 包容:機會均等富裕脫貧戶
傳統減貧的“涓滴理論”認為貧困人口的收入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增加,政府不需要針對貧困人口的扶貧政策,只需實現經濟增長就能緩解貧困[40]。但由于資本的“逐利”本性及資本與勞動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異質性,市場主導的經濟增長和社會財富的增加不僅難以解決貧困問題,甚至會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實踐也證明經濟財富的持續快速增長不僅沒有向貧困人口“涓滴”,而且導致貧困狀況更加惡化。為了更好地解決貧困問題,學術理論界開始尋找新的減貧理論,Chenery等[41]提出的增長再分配模型,強調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目標一體化,成為“親貧式增長”或“益貧式增長” 的理論溯源,2000年世界銀行提出“益貧式增長”,強調社會利益均等化。考慮到“益貧式增長”只側重度量貧困人口收入增長的局限,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提出“包容性增長”,旨在通過消除權利貧困和社會排斥、實現機會均等,這是治理包括收入、健康、教育、社保等多維度貧困問題的前提和基礎[42]。“包容性發展”作為一種更具人文關懷的貧困治理理念,把包容性增長的內涵邊界進一步拓展,更加強調公平、全面和共享,在貧困治理中突出機會平等和參與公平,從而實現成果共享,這一理念也始終貫穿于中國貧困治理的偉大實踐之中[43]。例如安徽長豐縣吳山鎮立足本地特色實施集體資產收益項目,發展各類設施大棚種植產業,探索出集生產、銷售和技術“三位一體”的經營模式,解決了脫貧戶、監測戶的就近就業問題,而且以“老弱病殘”無勞動能力為參考依據,開發公益性崗位,實行不同檔次的分紅,帶動脫貧戶穩定增收。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包容性不僅實現了“物的聯合”,而且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了“人的聯合”,在解決絕對貧困向治理相對貧困的銜接過渡期,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與實現脫貧戶生計轉型存在內在一致性。首先,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包容性在黨的領導下能夠牢牢掌握利益分配的主動權,不僅能夠對接國家和社會注入的巨大資源,而且能夠把土地和產業增值收益留在集體和脫貧戶手中,脫貧戶可以根據集體成員資格享受股金和返利。其次,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包容性在組織方式上可通過土地置換、集體贈股、設置公益崗等方式,把脫貧戶完整納入集體經濟的發展軌道,讓脫貧戶能夠公平分享集體經濟發展紅利,拓寬增收渠道,實現生計轉型。再次,脫貧戶“組織起來”能夠大大降低社會治理、養老、養小的成本,而且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包容性能夠改善農村醫療救助、生活救濟、互助養老、教育補助等公共服務的供給狀況和服務水平。最后,后脫貧時代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需更加關注體面生活和精神富足,將“包容”的維度進一步拓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包容性能夠賦予脫貧戶機會更加公平、參與權更加保障的制度環境,保障脫貧戶更多選擇機會和獲得幸福的權利,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
5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實踐進路
后脫貧時代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能夠把脫貧戶組織起來對接“大國家”和“大市場”,通過“賦予權力、提升能力、包容性參與”賦能脫貧戶生計向“多元型”生計和“發展型”生計轉型。然而現階段全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尚未形成良好的發展格局,只有約40%的行政村建立了集體經濟組織,超過70%的村集體經濟年收入不足5萬元[44]。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能通過行政命令、“歸大堆”的方式強制推廣,正如馬克思強調的那樣“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31]。因此,只有順應脫貧戶對美好生活的新企盼,理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邏輯關系,打通“堵點”,補齊“斷點”,才能更好地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把脫貧戶完整納入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
5. 1 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領導體系,保障“組織”賦能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成就充分證明“做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組織在農村領導核心地位的弱化和集體經濟的空殼化,是導致農村發展滯后和農戶陷入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新時代新征程中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必須在黨的領導下不斷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領導體系,把脫貧戶組織起來更好地對接國家資源投入和參與市場競爭,只有這樣,才能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首先,黨能夠統領一切、協調各方,發揮好村黨組織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領導核心作用,在黨組織(村黨支部)的基礎上建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才能確保中央政令暢通、決策落地生根,實現黨的領導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高度融合,確保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姓公不姓私”,__最大限度地維護脫貧戶的利益。其次,選準配強黨組織(村黨支部)領導班子,通過“穩”“培”“引”選擇頭腦活、懂經營、會管理、責任心強的優秀人才進入村“兩委”和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班子,全面提升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的綜合能力和領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能力,走“能人”帶動脫貧戶轉型發展的路子。最后,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把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作為根本任務,賦予脫貧戶更加充分的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帶領脫貧戶走向共同富裕的堅強戰斗堡壘。
5. 2 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宣傳示范體系,強化“認知”賦能
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旨在通過互助合作,把不同農戶組織起來集體發展經濟,不是發展集體經濟[45]。新時代新征程中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是“一大二公”,而是在黨的領導下遵循入社自由、權責清晰、利益共享的原則,在“確權”基礎上通過合作與聯合將脫貧戶和一般小規模農戶組織起來實現共同發展的經濟組織,這與人們理解的傳統集體經濟有著本質區別。因此,后脫貧時代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必須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宣傳示范體系,推動思想觀念上的“賦能”。首先,從理論上講清楚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不是走回頭路,而是黨的領導下建立在“確權”基礎上的集體經濟組織,能夠真正賦予脫貧戶權利、提升脫貧戶能力,讓老弱病殘也都能有保障,是引領脫貧戶實現共同富裕的治本之策。其次,通過對相關領導干部和村“兩委”領導班子組織集體培訓、網絡培訓強化對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政策宣講,充分利用廣播電視、數字網絡及新媒體宣傳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意義、優惠政策、組織方式、先進典型,提高黨員干部和群眾對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政策知曉度。最后,用好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改革發展成功案例,強化“示范引領”,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涌現出一批“典型案例”,如貴州塘約村的“再集體化”、山東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等,要進一步放大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領效應,讓脫貧戶看到實實在在的收益,激發脫貧戶參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積極性。
5. 3 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制度供給體系,實現“政策”賦權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抓手”,從實踐上來看全國已有約40%的行政村建立了集體經濟組織,而且在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方面有很多成功探索;從政策支持上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中均明確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獨特的法人地位和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為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創造了良好的制度環境。但也應該看到當前支持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制度供給不足和政策資源碎片化問題,因此,為更好地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必須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制度供給體系,凝聚政策支持合力。首先,完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章制度,明確政府、村“兩委”及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邊界和成員權利,強化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市場主體地位,在政策上講清楚脫貧戶分享集體經濟紅利的權屬條件。其次,發揮財政金融的政策引領作用,撬動整合各類涉農資金,設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探索建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制度化資金投入體系。最后,把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納入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與特色產業發展、文化傳承創新、生態環境保護等各類政策有機銜接起來,探索建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綜合性政策支持體系。
5. 4 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要素投入體系,實現“資源”賦權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是黨在農村政策的立基之石,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必須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將脫貧戶和一般小規模農戶組織起來,優化生產要素組合,不斷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要素投入體系,在黨的領導下實現資源使用的內外結合、共同賦權。首先,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和穩定的土地承包關系,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把明晰產權作為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起點,持續推進集體經營性資產股份合作制改革,賦予脫貧戶更加充分的財產權,明確的權屬關系將激發脫貧戶推動生計轉型的內生動力。其次,發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組織動員優勢,能夠在更大范圍激活鄉村沉睡資源,整合脫貧戶小而散的資源,優化村域內資源配置,改善土地、水利、交通等農業生產經營條件,延長農業產業鏈,為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注入更多動力。再次,發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對接“大國家”的優勢,國家在打贏脫貧攻堅戰中向農村投入的資源存量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中進一步注入的資源增量,只有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才能對接和用好這些資源,并將其內化為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內生動力。最后,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既要用好資本,也要約束資本,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以規范有序和互利共贏方式引入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才能既容納資本進入農村,給集體經濟發展注入活力,同時利用黨在集體經濟組織中的領導優勢維護脫貧戶的利益。
5. 5 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生產經營體系,實現“模式”增能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決勝脫貧攻堅戰的決策部署和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不斷推進,許多貧困村新型集體經濟實現了從無到有、從有到強的跨越式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趨勢。2022年印發的《“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提出“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豐富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的有效實現形式”,為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生產經營體系創造了良好的政策條件。因此,推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有效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應該充分用好政策機遇,秉持“因地制宜、因村制宜”的發展原則,依托村域產業特色和稟賦優勢把脫貧戶組織起來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具體來看,在集體經濟初始稟賦好、有產業優勢的村域應圍繞農業現代化、農村三產融合發展組織化聯結、專業化生產、市場化運營的產業主導型集體經濟,把脫貧戶納入中國式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道路;在沒有集體資產、發展產業難度大的村域應鼓勵多種運作方式,通過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投資入股龍頭企業,吸引外出務工經商能人帶資金、帶項目回鄉創業,引導脫貧戶利用土地、勞動等入股,發展入股分紅型集體經濟;有文化資源優勢和自然資源優勢的村域應該在黨組織(村支部)的領導下圍繞鄉村全域旅游、農業生產經營把脫貧戶組織起來發展生產服務型集體經濟。另外,必須用好政府資源進村、鄉村全面振興等政策機遇,進一步完善農村道路交通、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為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生產經營體系,更好地提升脫貧戶自生發展能力創造良好的“硬”環境。
5. 6 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動力培育體系,實現“市場”增能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在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基礎上把脫貧戶和一般小規模農戶組織起來對接“大市場”,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是承認脫貧戶等個體與集體權屬關系基礎上面向市場的“合作生產”,提升了集體經濟組織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和脫貧戶個體的市場參與能力,對形成推動脫貧戶生計轉型的市場化機制具有重要意義。首先,完善農村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健全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體系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制度,賦予農村集體資源資產完整的市場交易權,明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權屬關系和獨立的市場主體地位。其次,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取得法人資格的規定要求,借鑒現代企業制度和管理辦法,在“政經分開”“折股量化”的制度框架下健全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法人治理模式,建立村“兩委”領導班子和集體經濟組織領導班子“雙向進入”機制,完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制度,提升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市場參與能力和水平。最后,把脫貧戶組織起來的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作為獨立的市場主體,改善了單個脫貧戶在市場中的弱勢地位,提升了脫貧戶在農業生產資料獲取、農產品銷售及務工工資等方面的議價能力,為實現脫貧戶生計轉型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
5. 7 創新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聯合管理體系,實現“利益”包容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通過“勞動聯合”和“財產聯合”把脫貧戶組織起來,以差異化的“確權”實現了脫貧戶個體與集體之間的利益聯結,賦予脫貧戶等集體成員以收益權為核心的各種財產權利,走出了集體經濟產權虛化和集體收益“精英俘獲”的困局,增強了脫貧戶與一般農戶之間、個體和集體之間的利益關聯。首先,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在堅持集體所有制前提下的“確權”,將集體成員權以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具體化,明確了集體成員的資格身份,形成了一套集體和個體產權互認、共融的聯合管理體系,使之真正實現可流動、可增值,以此維護脫貧戶的利益,賦能脫貧戶生計轉型。其次,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必須堅持“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盡可能把脫貧戶完整納入集體經濟發展軌道,通過優化股權比例設置、集體收益分紅等方式確定集體成員的持股份額,開發公益性崗位,建立起一套傾向于保障脫貧戶利益的產權執行體系,防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被大戶控制或者壟斷,警惕“精英俘獲”現象的出現。最后,優化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在普通個體、管理干部及村集體的分配機制,脫貧戶等普通個體獲得“工資+分紅”、管理干部獲得“工資+績效獎金”、村集體獲得“企業上繳經營收益+土地等集體股權收益”,另外,村集體的集體收益將用于改善村域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以此支撐脫貧戶生計轉型,不斷滿足脫貧戶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參考文獻
[1] 王建洪,李伶俐,夏詩涵,等. 制度性合作機制下脫貧戶生計可持續性評價與脫貧政策效應研究[J]. 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6(5):68-76,192.
[2] 丁忠兵.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協同扶貧模式創新:重慶例證[J]. 改革,2020(5):150-159.
[3] 張慧鵬. 集體經濟與精準扶貧:兼論塘約道路的啟示[J]. 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6):63-71.
[4] 陳義媛.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與村社再組織化:以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為例[J]. 求實,2020(6):68-81,109.
[5] 習近平. 擺脫貧困[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193.
[6] CHAMBERS R,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
[7]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livelihoodsguidance sheets[R]. 1999: 68-125.
[8] 李明月,陳凱. 精準扶貧對提升農戶生計的效果評價[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9(1):10-20.
[9] TSVEGEMED M,SHABIER A,SCHLECHT E,et al. Evolution ofrur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a remote Sino?Mongolian border area:across?country analysis[J]. Sustainability,2018,10(4):1011.
[10] 孫晗霖,劉新智,張鵬瑤. 貧困地區精準脫貧戶生計可持續及其動態風險研究[J].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9,29(2):145-155.
[11] 王娟,吳海濤,丁士軍. 山區農戶生計轉型及其影響因素研究:以滇西南為例[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4(5):133-140.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N]. 人民日報,2021-04-07(9).
[13] 汪三貴,胡駿. 從生存到發展:新中國七十年反貧困的實踐[J]. 農業經濟問題,2020(2):4-14.
[14] 陸遠權,劉姜. 脫貧農戶生計可持續性的扶貧政策效應研究[J]. 軟科學,2020,34(2):50-58.
[15]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3.
[16]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2.
[17] 耿羽. 壯大集體經濟 助推鄉村振興:習近平關于農村集體經濟重要論述研究[J]. 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2):14-19,107.
[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8冊)[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664.
[19] 高鳴,蘆千文. 中國農村集體經濟:70年發展歷程與啟示[J].中國農村經濟,2019(10):19-39.
[20] 張弛. 中國特色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理論基礎、新特征及發展策略[J]. 經濟縱橫,2020(12):44-53.
[21] 孔祥智. 合作經濟與集體經濟:形態轉換與發展方向[J]. 政治經濟學評論,2021,12(4):83-108.
[22] 徐鳳增,襲威,徐月華. 鄉村走向共同富裕過程中的治理機制及其作用:一項雙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1,37(12):134-151,196,152.
[23] 崔超.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J].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2):89-98.
[24] 王小林. 新中國成立70年減貧經驗及其對2020年后緩解相對貧困的價值[J]. 勞動經濟研究,2019,7(6):3-10.
[25] 楊倫,劉某承,閔慶文,等. 農戶生計策略轉型及對環境的影響研究綜述[J]. 生態學報,2019,39(21):8172-8182.
[26] 鮮祖德,王萍萍,吳偉. 中國農村貧困標準與貧困監測[J]. 統計研究,2016,33(9):3-12.
[27]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N]. 人民日報,2016-12-30(1).
[28] 李天姿,王宏波.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現實旨趣、核心特征與實踐模式[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2):166-171.
[29] 賀雪峰. 鄉村振興與農村集體經濟[J].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72(4):185-192.
[30] 邢成舉,李小云. 精英俘獲與財政扶貧項目目標偏離的研究[J]. 中國行政管理,2013(9):109-113.
[31]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8,70.
[32]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8.
[33] 羅必良,洪煒杰,耿鵬鵬,等. 賦權、強能、包容:在相對貧困治理中增進農民幸福感[J]. 管理世界,2021,37(10):166-181,182.
[34]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91,49.
[35] 楊磊,王俞霏. 多元賦權:農村集體資產股權劃分的邏輯與制度功能[J]. 北京社會科學,2020(4):105-116.
[36] 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1.
[37] 舒爾茨. 改造傳統農業[M]. 梁小民,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135.
[38] 鄧金錢. 中國共產黨百年減貧的歷史方位與理論貢獻[J]. 上海經濟研究,2022,34(7):50-59.
[39] 郭曉鳴,王薔.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治理相對貧困:特征、優勢與作用機制[J]. 社會科學戰線,2020(12):67-73.
[40] DOLLAR D, KRAAY A .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 Journalof economic growth, 2001, 7(3):195-225.
[41] CHENERY H B , AHLUWALIA M S , BELL C , et al. Redistributionwith growth[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42] 黎藺嫻,邊恕. 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與貧困:包容性增長的識別與分解[J]. 經濟研究,2021,56(2):54-70.
[43] 黃承偉,徐麗萍. 中國包容性增長與減貧:進程與主要政策[J]. 學習與實踐,2012(7):67-75,2.
[44] 解學智. 加大金融對村集體經濟的支持力度[J]. 中國銀行業,2020(6):34.
[45] 黃延信. 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亟需更新觀念[J]. 農業經濟與管理,2021(4):48-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