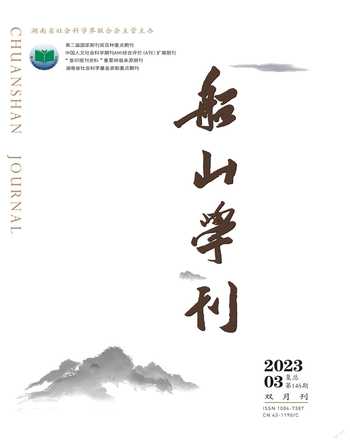《近思錄》在日本的傳播
摘要:程朱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和意識形態(tài),對周邊各國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近思錄》在宋元之際傳布日本后,身處東亞文明圈中的日本同樣把它提升到顯要的理學經(jīng)典之位,將其定為僅次于《四書》《五經(jīng)》的讀本,為青年士子入道的階梯。日本著名儒學家貝原益軒著《近思錄備考》,是江戶時代日本最早產(chǎn)生的《近思錄》注解、講讀類文獻,在日本《近思錄》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作為貝原益軒的早期著作,《近思錄備考》在文獻征引、注解內(nèi)容方面反映了其早期的儒學思想,在文獻研究上具有版本價值。
關鍵詞:貝原益軒《近思錄》《近思錄備考》朱熹
作者鄭春汛,上海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上海200436)。
江戶時代在幕府和諸藩大名們提倡朱子學的背景下,朱子學的政治地位空前,社會從上到下形成了爭相學習、研究、傳播《近思錄》的風尚,因此產(chǎn)生了大量《近思錄》重刻、翻譯、注釋、講讀、仿編等本土衍生文獻,多達數(shù)百種,遠超中國同時期。其中學術價值較高、占比較重的是朱子學者們或儒臣們因講學所創(chuàng)作的注釋、講讀文獻,如貝原益軒《近思錄備考》、中村惕齋《近思錄鈔說》、宇都宮遁安《鰲頭近思錄》、澤田希《近思錄說略》、佐藤一齋《近思錄欄外書》、中井竹山《近思錄標記》、中村習齋《近思錄講說》、安褧《近思錄訓蒙輯疏》等等。《近思錄備考》是日本著名儒學家貝原益軒的早期著作,也是中國理學經(jīng)典《近思錄》在日本傳播過程中誕生的第一本注解、講讀類本土文獻。得益于貝原益軒博學廣識及深厚的學術功底,《近思錄備考》既有指導初學的實用性,也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清初著名學者朱彝尊評價它:“這是在中國聞所未聞,未曾出現(xiàn)過的好注解(日文直譯)。”[1]3陳榮捷評價它:“日本注以此(筆者注:指澤田武岡)與貝原益軒、宇都宮遁安,與佐藤一齋為最好。”[2]110 “為日本研究《近思錄》標準之作。其后學者多參考征引之。”[2]109《近思錄備考》在日本《近思錄》研究的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將結合貝原益軒的學術生平,探討《近思錄備考》的文獻征引特點、學術價值以及版本價值。
一、貝原益軒的學術生平
貝原益軒(1630—1714)名篤信,字子誠,號益軒,筑前藩(今福岡縣)侯侍醫(yī)貝原寬齋第五子,日本江戶時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儒學家、教育思想家、博物學家。據(jù)貝原好古著《益軒先生年譜》記載,益軒先祖為吉備津神社的神職人員,益軒幼年受母親影響信奉佛教。14歲在仲兄存齋影響下悟“浮屠之非”,始習“四書”并隨其父習醫(yī)藥。18歲成為筑前藩二代藩主黑田忠之的侍從,21歲因過錯被免職成為浪人,來往于長崎、江戶等地以醫(yī)謀生。27歲時被第三代藩主黑田光之召回成為藩醫(yī)。28歲得藩費資助游學京都,36歲學成歸藩,被聘為儒臣。70歲辭去藩職專事著書立說,卒年85歲。貝原益軒學問廣博,一生著述宏富,從儒學至樹藝、文學、神祇、醫(yī)學、衛(wèi)生、制造之類無不包羅,逾百余種。板倉勝明評價其“博學強記,和漢之書,無不窮綜,其著述之富,與羅山白石相頡頏,裨益天下后世,匪淺鮮也。”[3]247
作為儒學家的貝原益軒,成年后其儒學思想發(fā)生過兩次轉(zhuǎn)變。早期的貝原益軒游學京都,與松永尺五、山崎暗齋、木下順庵等儒學大師及醫(yī)學者向井元升、稻生若水、黑川道祐等有學術交往。此時的貝原益軒既修朱子學,又習陸王學。據(jù)益軒自著《玩古目錄》記載,他在讀書初期好讀陽明學書籍,曾讀過12遍王陽明的《傳習錄》,但在36歲讀明朝陳建《學蔀通辨》后,始棄陽明學,成為純粹的朱子學者,是其思想第一次轉(zhuǎn)變。《益軒先生年譜》云:“先生嘗好陸王,且玩讀王陽明之書數(shù)歲,有朱陸兼用之意。今年始讀《學蔀通辨》,遂悟陸氏之非,盡棄其舊學,純?nèi)缫病!盵3]247-248此后貝原益軒將朱子奉若神明,他在《自娛集》中說:“后世之學者知經(jīng)義者,皆朱子之力也。……吾輩不逮之質(zhì),雖不能窺其藩籬,然心竊向往之,故于其遺書也,尊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3]248帶著對朱子的崇敬,這一時期的貝原益軒致力于講讀和注解、傳播朱子學文獻,39歲左右創(chuàng)作了《近思錄備考》《小學句讀備考》《朱子文范》《大學集要》等朱子學入門著作。
但是隨著益軒對朱子學研究的深入,知識體系逐步完善,46歲時益軒開始反思、質(zhì)疑朱子。他在《大疑錄》中說:“予幼年誦朱子之書,尊其道,師其法,服其教,然于其所不解,則致疑思而審擇,未嘗阿所好,是欲仆他日之開明耳。”[3]248貝原益軒在懷疑中摸索深思,84歲時著《大疑錄》《慎思錄》系統(tǒng)表述了自己觀點中與朱子不同的部分,是其思想第二次轉(zhuǎn)變。他不同意朱子“理先氣后”的說法,提出了“氣一元論”的觀點。即否認朱子的理氣二元論,主張理氣不可分,理是氣之理,不能離開氣而獨立存在,天地間都是一氣,萬物皆由氣生成,太極、陰陽、道都只不過是氣的不同表現(xiàn)形式,并在此認知基礎上將朱子“格物窮理”進一步延伸發(fā)展為“博學之功”,注重通過實際考察窮盡諸物之理,將朱子學“格物窮理”與經(jīng)世致用的實證主義方法相結合。他在《慎思錄》中說:“吾曹受昊天罔極之恩也,逾于他人,何以報其德之萬一乎?如解釋于經(jīng)傳,發(fā)明于義理,古人作者既備矣,求之前修之書而足矣,況區(qū)區(qū)庸劣,豈能容啄于其間乎?別事又不能為,唯欲作為國字之小文字之有助于眾庶與童稚者,必待后輩而已,庶幾有小補于民生日用云爾。”[3]260“雖小道鄙陋之事,茍有裨民用者,撰述之亦惟事也。”[3]260因此貝原益軒晚年不再注經(jīng)釋傳,而將主要精力用于宣傳民生日用之學,用本國語言創(chuàng)作了《益軒十訓》《大和本草》《筑前國續(xù)風土記》等在民間膾炙人口的佳作。當時的學問書籍多用漢文書寫,而益軒的著作用通俗易懂的日文書寫,使一般大眾也容易理解。相比起同時代其他儒學家主要針對社會乃至統(tǒng)治階級層面的思考,益軒則將關注的眼光更多地投向下層平民,對當時江戶時期平民教育的發(fā)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貝原益軒與《近思錄備考》
據(jù)中日交流史料,《近思錄》等朱子學文獻在南宋時就已經(jīng)傳播到日本,鐮倉時代(1192—1333)和室町時代(1336—1573),朱子學文獻的研究和傳播主要局限于禪僧和上層貴族中。到了江戶時代(1603—1867),德川幕府以武士為統(tǒng)治階級建立了新的幕藩制度,選擇朱子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以維護社會關系穩(wěn)定。德川幕府的歷代將軍及諸藩大名均崇信朱子學,聘請游學于京都、江戶的朱子學者作為儒臣在藩內(nèi)講學成了當時的社會風尚,如幕府聘請林羅山、肥后藩聘請那波活所、尾張藩聘請堀杏庵、會津藩聘山崎暗齋等。貝原益軒京都游學之后也被聘為筑前藩儒臣,為藩中子弟們講授朱子學。
朱子學是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核心而構建的“四書學”體系,這個體系的內(nèi)在結構是以《小學》《近思錄》為邏輯起點的。《四書》《五經(jīng)》與《小學》《近思錄》的關系,清儒施璜的解讀十分明確:“《五經(jīng)》以《四書》為階梯,讀《四書》無入處,不可以言《五經(jīng)》。《四書》以《近思錄》為階梯,讀《近思錄》無入處,不可以言《四書》。《近思錄》以《小學》為階梯,讀《小學》無入處,不可以言《近思錄》也。欲升《五經(jīng)》之堂室,必由《四書》階梯而上。欲升入《四書》之堂室,必由《近思錄》階梯而上。欲升入《近思錄》之堂室,必由《小學》階梯而上。”[4]自序3可見進入朱子學學術系統(tǒng)的次序是《小學》—《近思錄》—《四書》—《五經(jīng)》。日本朱子學者也遵從同樣的學習次序,如《暗齋先生年譜》記載,江戶名儒山崎暗齋講學,“先《小學》,次《近思錄》,次《四書》”[3]294。同為入門書籍,《近思錄》的地位比《小學》更重要。據(jù)李方子《朱子年譜》載,(淳熙)十有四年(1187)三月,(朱子編次)《小學》書成。先生“既發(fā)揮《大學》以開悟?qū)W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5]4。可見《小學》的定位是“訓蒙”讀物,并未真正觸及“四書學”的學術內(nèi)核。而對于《近思錄》,朱熹說:“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6]2629表明在朱子學體系中,《近思錄》起到登堂入室的作用,是研讀《四書》的正式開端。
江戶時代在幕府和諸藩大名們提倡朱子學的背景下,朱子學的政治地位空前,社會從上到下形成了爭相學習、研究、傳播《近思錄》的風尚,因此產(chǎn)生了大量重刻、翻譯、注釋、講讀、仿編等《近思錄》本土衍生文獻。《近思錄備考》是貝原益軒作為儒臣為藩中子弟講學時所準備的參考資料。《近思錄備考》跋云:“學者之于經(jīng),未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是以敢私記,以備他日之考索云爾。” [1]82以及同時出版的《小學句讀備考》跋云:“與諸生講此書,因訓詁之難解,旁搜傳記而摭有資于講說者為編,以備他日之參考。”[1]624表明其編撰目的是通過訓釋經(jīng)文幫助初學者疏通經(jīng)義,在需要的時候“以備參考”,這兩部書亦因此得名“備考”。這一時期貝原益軒不僅編撰了《近思錄備考》,同時編撰了《小學句讀備考》《朱子文范》,先后于寬文8年(1668)、寬文9年(1669)出版。江戶時代版業(yè)發(fā)達,但寫本因其低成本、傳抄便宜的特點也被廣泛使用,與刊本并行。江戶時代學者講說《近思錄》的風氣盛行,但《近思錄》的本土衍生文獻寫本、抄本約占七成,刻本相對較少。而此時的益軒篤信朱子,受《近思錄》影響,“體心行身”地奉行并傳播朱子學,因而十分重視朱子文獻的出版?zhèn)鞑ィ恳粫桑H自與書肆聯(lián)系商談,將所編之書刻印出版。他在《小學句讀備考》跋中說:“程朱之書,航海傳于我者,蓋三百余年于此矣,然而《小學》《近思錄》之行于世也,未備于二紀,真為可恨焉。我曹幸生于今時,而得見此書而講習之,當徒事空文而不能體心行身,則不幾于侮圣賢者乎!”[1]624他甚至仿照《近思錄》,精選朱子語錄纂集成書,仿編了一本《朱子文范》。據(jù)《益軒先生年譜》記載:“此頃信朱文公之學術愈篤,好讀其文集。乃窮鄉(xiāng)晚出,為不能閱其全集之人,纂輯精要而為五卷,使久野正的加訓點,自補正之以行世。是為《朱子文范》也。”[7]18與朱熹在《近思錄》序中所言:“以為窮鄉(xiāng)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后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8]328其編撰目的如出一轍,足見益軒受《近思錄》影響之深,《近思錄備考》也是研究益軒早期儒學思想的重要文獻。
三、《近思錄備考》的文獻引用特點
宋元以來,如同《四書章句集注》代替《四書》傳播一樣,葉采的《近思錄集解》在東亞儒學圈實際也是代替《近思錄》來流傳的。葉采作為朱熹的再傳弟子,其《近思錄集解》有兩大開創(chuàng)之功,一是依據(jù)《近思錄》內(nèi)容擬定了各卷篇名及內(nèi)容提要,這種綱目提要的創(chuàng)建使《近思錄》原書體例顯得更加明晰完備。二是葉采注常常引用朱熹語來注四子語,彌補了《近思錄》中未收錄朱子語錄的缺憾,使程朱理學思想內(nèi)容的表現(xiàn)更趨明朗,發(fā)揚光大了該書主旨。因此葉采《近思錄集解》影響深遠,成為后世《近思錄》注解、續(xù)編、仿編者所倚重的范式,在整個東亞包括日本風靡一時。江戶時代產(chǎn)生的日本《近思錄》注解、講讀類本土文獻大部分也是在葉采《近思錄集解》的基礎上完成的二次創(chuàng)作,如陳榮捷所說:“葉采之注在日本甚為通行,日本注家?guī)捉匀廊~注。”[8]3《近思錄備考》也是以葉采的《近思錄集解》為底本進行的二次注解。《近思錄備考》問世以后,因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和實用性,得到了日本學者和學子們的廣泛接受和認可,為之后的日本人注解《近思錄》豎立了標桿,長期被后人模仿引用,陳榮捷評價它:“引朱子及其他理學家甚長,亦附己見,為日本研究《近思錄》標準之作,其后學者多參考征引之。”[2]109指出《近思錄備考》在文獻引用上具有特點,而且學術價值高,對后世影響大。它的引用特點和學術價值從以下幾個方面可以體現(xiàn)。
(一)引用廣博,訓釋詳盡
《近思錄備考》引用經(jīng)史子集各類著作近200種, 在訓釋字義時除了引用常見的《爾雅》《說文》,還用到了《增韻》《韻會》《字匯》《五車韻瑞》《小補韻會》《海篇》《續(xù)韻符》等。訓釋文義如《易》類引用就有《易說統(tǒng)》《周易本義》《議易傳》《易嫏嬛》《易經(jīng)蒙引》《東坡易傳》《周易古今文全書》;《小學》類有《小學合璧》《小學章句》《小學衷旨》《小學句讀》《小學集注》《小學纂疏》《小學集成》,其豐富翔實可見一斑。在闡釋義理上除了征引到朱熹、張栻、許衡、薛瑄及朝鮮李退溪等著名理學大儒的著作外,還涉及盧孝標、胡宏、程若庸、范念德、吳澄、胡炳文、程鉅夫、李南黎、丘濬等在日本知名度不高的宋、元、明理學家80余人,從時間和地域跨度上體現(xiàn)了貝原益軒廣博的學識和宏大的學術視野。
益軒作《近思錄備考》是為初學者掃除跨文化閱讀帶來的障礙,使本土初學者能夠得于辭而能通其意,因而與葉采注的“微言大義”不同,《近思錄備考》訓釋詳盡,具體到字詞讀音、釋義、句義、典故出處、典故原文。如《近思錄》卷二第92條原文中有:“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9]87全句43字。葉采注:“遜,順也。遜此志則立心已定,務時敏則講學為急,如是則所修乃日見其進也,說見《尚書》。”[9]87葉采注文僅34字,較為簡略,用字甚至比經(jīng)文還要少。貝原益軒注:
《書·說命》:唯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蔡傳》:遜,謙抑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云云。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朱子曰:遜順其志,抑下這志,仔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又曰:既遜其志,又須時敏。又曰:為學之方,只此二端而已。○李氏曰:為學之道,常以卑遜自下為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呂氏曰:為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與為學工夫相背。○陳氏曰:驕與怠最害于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述而》篇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敏,速也,謂汲汲也。“逮”,《字匯》音第,作‘音大者非也。“非所聞也”,《說命》:匪說攸聞。注:甚言無此理也。 [1]706
先后引用了《尚書說命》《尚書蔡傳》《論語述而》《字匯》等3種經(jīng)典、1種字書,以及朱子、李氏、呂氏、陳氏等4位理學家語錄,共8種相關文獻276字,層層遞進來注解,用字量是葉采注的8倍,其詳盡程度可見一斑。對此,日本學者室鳩巢解釋道:“朱子之書,盛行中國,中國儒者有志理學者所素傳習而通知,不待表章纘述。”[3]252因為科舉制度,中國儒生們從小就熟讀各種經(jīng)解經(jīng)注,具有一定知識儲備與接受基礎,可以直接進入義理階段學習,所以葉采、何基、楊伯巖、柳貫等宋代古注解均以“微言大義”闡發(fā)義理為主,不需要重復字詞訓釋這些基礎知識。日本初學者并沒有中國儒生同等的閱讀基礎,考慮到日本民族文化特點,《近思錄備考》這種基礎性本土化入門注解可謂應運而生,因此極具實用性,出版后即得到廣泛傳播和認可,為日本后期《近思錄》注解、講讀類文獻的著作開創(chuàng)先河,極大推動了朱子學在日本的傳播。
(二)注解以“明代四書學”舶載本為主體文獻群
16世紀后半期以來,中國的雕版圖書成為日中貿(mào)易的主要輸出品之一,通過海上貿(mào)易流通到日本的中國古籍被稱為“舶載本”。因明代科舉與四書的深厚關系,產(chǎn)生了以《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為代表的大批“明代四書學”的注疏和學習用書,同時由于明代商業(yè)出版普及,雕版圖書的大量印刷促進了“明代四書學”書籍的流通,也促進了書籍流入日本,舶載本是為朱子學向日本傳播的途徑之一。江戶時代,舶載本到達貿(mào)易港口長崎后,要先經(jīng)長崎的幕府官員“書物審查”,由幕府選購一些必要的書籍,余下的再由藩國、民間書店競相購買。幕府和藩國一般委派儒臣負責這項工作,除了選購,還要對這些書籍進行“點校”增加日文訓點,貝原益軒也曾擔任此項工作。在17世紀的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中村惕齋、安東省庵、貝原益軒等,通過舶載本接觸到了中國科舉制度下的朱子學即“明代四書學”,擴大了對朱子學接受、認知的深度和廣度。日本列島的思想、知識也被納入了東亞同時代的儒學圈。
《近思錄備考》定位是面向日本初學者的入門注疏本,貝原益軒在編撰時將選購舶載本獲得的明代“四書學”注疏書進行了篩選,他以明代科舉標準下的朱子學為正統(tǒng),挑選了《四書大全》《五經(jīng)大全》《性理大全》《四書蒙引》《四書存疑》《四書講述》《四書鄒魯指南》《四書翼注》《四書節(jié)解》《四書直解》《四書說統(tǒng)》等書作為引用文獻。其中貝原益軒最重視的書是《四書蒙引》和《四書存疑》,他在《讀經(jīng)總論》中說:“(《蒙引》《存疑》《淺說》)以朱子為宗,初學之徒不能理會于朱注者,須以此等說為階梯。”[7]19《四書蒙引》《四書存疑》作為科舉用書,排斥當時流行的陽明學系,擁護正統(tǒng)朱子學,非常符合貝原益軒初棄陽明學篤信朱子的學術立場,因此《近思錄備考》引用《四書蒙引》高達57次,《四書存疑》31次。此外,他認為《性理大全》《四書講述》《四書說統(tǒng)》等十余種書對初學者也有一定幫助,因此每種引用也有數(shù)次到數(shù)十次不等,形成了《近思錄備考》的鮮明特點。
(三)引文內(nèi)容精當
《近思錄》除了在引文范圍、種類上有特點,其引文的內(nèi)容選擇也十分精當,準確地闡釋了朱子學理論中的難點。如《近思錄》卷六第十七條,有“先公太中諱珦……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8]199-200講程珦為寡婦外甥女主持再嫁的事,而同卷第13條有程頤語錄:“孀婦于理似不可取……然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8]198程頤認為寡婦再嫁為失節(jié),而程頤的父親卻為自己的寡婦外甥女主持再嫁,于是有門人向朱子表達了疑惑,《朱子語類》卷九十六載,(門人)問:“取甥女婦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綱恁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6]2473朱熹的回答有些許無奈,默認了理論與實踐的分離情況,使得程頤的理論顯得“自相矛盾”,初學往往難以領悟。對此,其他學者作注或避而不談,或模棱兩可。如清張紹價《近思錄解義》說:“嫁甥女,見其慈。慈恕故能篤恩義,剛斷故能正倫理。犯義理不假,則無不正之倫理。”[10]645認為程珦的做法雖“犯義理”但是合乎“倫理”;朝鮮李瀷《星湖先生近思錄疾書》說:“早孀再嫁,世之通行,而太中之恩義可見,故只取其大義耶?” [10]645認為“恩義”屬于倫理“大義”,是可以不遵循“義理”的,均認同朱子學理論中倫理與義理是有矛盾的。貝原益軒《近思錄備考》則不談程珦嫁甥女的事件本身是否失禮,而是引《五雜俎》的一段話來探討“孀婦再嫁”這個問題:“《五雜俎·八》曰:圣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即今國家律令,嚴于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豈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責于婦人女子也。”[1]758解釋了程頤提出的“孀婦似不可取(娶)”論屬于“圣人制禮”的范疇,是對士君子提出的修身齊家要求,并不是對婦人女子或普通人的要求。益軒通過精準恰當?shù)囊淖⒔猓棺x者明白,程珦嫁寡婦外甥女的行為,表面看似與程頤言論相悖,但實際并不影響程頤理論的核心。
四、《近思錄備考》益軒自注的學術價值
貝原益軒在注解中除了纂集、征引他人注解,也常常提出自己的見解,即陳榮捷所說的“亦附己見”[2]109。《近思錄》收錄周敦頤、張載、二程語錄共622條,但益軒并不是每一條都為之作注,而是根據(jù)學生學習需要,挑選有學習難點的條目作注,因此《備考》實際注解的條目為558條。益軒在《備考》中以“愚謂”發(fā)表個人見解139處,以“案”或“愚案”補充個人考證研究100處,共計239處個人創(chuàng)作,這些自注集中體現(xiàn)了貝原益軒的學術思想,極具學術價值,體現(xiàn)在以下兩點:
(一)富有創(chuàng)見
如《近思錄》卷四第十一條:“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yǎng)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8]145此條為程顥門人邢恕的語錄,與朱熹在《近思錄》序中的說的專錄“周子、程子、張子之書”主旨不符,引起許多學者不解,如日本學者佐藤一齋在《近思錄欄外書》中說:“此《錄》限四先生之語,文公《前引》可證,況邢恕于程門為叛人,無由獨載其語。”[11]340朝鮮學者李瀷在《星湖先生近思錄疾書》中說:“此《錄》只載四先生言,其余門人說話則無有矣。邢恕一條緣何以得載于《遺書》中?朱子又緣何而采之此《錄》?況恕,程門之叛卒,其為言不過修飾外面而無所實行。”[10]468代表了很多學者心中的疑問。也有學者則通過主觀推測使之合理化,清茅星來《近思錄集注》說:“此程子述邢恕之言如此,亦不以人廢言也。”[10]468認為此條邢恕語錄是經(jīng)程顥轉(zhuǎn)述的,也算程子語錄;清李文炤《近思錄集解》說:“和叔非能立誠者,程子乃不以人廢言耳。”[10]468認為這就是邢恕語錄,但都認同記錄邢恕語錄是為了體現(xiàn)程顥踐行《論語》提出的“不以人廢言”的品德,將注釋重點轉(zhuǎn)移到“大義”上,以主觀推測使《近思錄》中出現(xiàn)“四先生”之外的邢恕語錄合理化。貝原益軒則通過版本考證提出了更合理的解釋。益軒注:“案,《二程類語》‘邢字上有‘與字,然則是亦程子之言也。”[1]731貝原益軒通過版本比對考證,證明這條語錄在其他版本上是有“與”字的,作“與邢和叔言”,實際是程顥對邢恕所說,仍屬于程顥語錄,是版本問題造成了“邢恕語錄”摻雜于“四先生語”的矛盾假象,比之清儒的主觀推測更讓人信服。日本后學佐藤一齋等學者接受了貝原益軒的觀點,佐藤一齋在《近思錄欄外書》中直言:“邢恕上有‘與字,為程子語,《遺書》則與本書同……《類語》為是。”[11]340
(二)具批判精神
程朱理學在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處于官方哲學地位,又因為科舉的關系,中國儒生們對朱子及朱門后學葉采等人的學說也多持尊奉的態(tài)度,不敢直接表達質(zhì)疑。早期貝原益軒也對朱子奉若神明,篤信不疑,但這種信任是建立在對比過佛學、陽明學及廣泛閱讀的基礎上獨立思考的結果,與中國科舉制度下的尊奉不同。因此貝原益軒雖篤信朱子,但并不“愛屋及烏”地篤信朱子門人葉采,《近思錄備考》中,貝原益軒對于葉采注中不信服的地方會直接加以否定。如《近思錄》卷十第二條中有“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8]250句,葉采注:“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9]252貝原益軒注:“王觀濤《四書翼注》云:‘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即天下之民歸心也,只論個得民心可以有天下的道理。愚謂:王說可據(jù)。葉氏注‘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之說,恐未是。”[1]787 明朝的王觀濤在《四書翼注》中只敢委婉陳述己見,并不敢直指葉采之非,而貝原益軒則明確表示葉氏注“恐未是”。貝原益軒的批判精神對后世學者影響深遠,此后的日本本土代表性《近思錄》注解、講讀文獻如澤田希《近思錄說略》、安褧《近思錄訓蒙輯疏》、佐藤一齋《近思錄欄外書》、中村惕齋《近思錄鈔說》等,對葉采注均有明確批判性表達。日本社會因為不受中國政治意識、學術傳統(tǒng)、門派之爭的束縛,且沒有科舉制度,因此雖然同處東亞儒學圈,江戶時代的朱子學者們并未將朱門后學葉采視為絕對權威,在處理學術分歧時也敢于直陳是非曲直,表現(xiàn)出獨立的批判精神和充分的學術自信。
五、《近思錄備考》的版本價值
《近思錄備考》作為創(chuàng)作于17世紀的日本古文獻,除了學術價值,還有作為古文獻特有的版本價值,裨益于當代的《近思錄》版本研究工作。《近思錄備考》是以葉采《近思錄集解》為基礎進行的二次創(chuàng)作,其中保留了部分流傳于日本17世紀的《近思錄集解》葉采注文原貌,極有參考價值。葉采《近思錄集解》完成于宋淳祐八年(1248),初成之后就有抄本、刻本出現(xiàn)。自南宋至清末七百余年時間里,《近思錄集解》不僅在國內(nèi)廣泛刊刻傳播,而且還向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地傳播,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版本系統(tǒng)。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葉采《近思錄集解》版本為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元刻本,此版本與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元刻明修本、清康熙年間邵仁泓重刊仿宋本、四庫全書抄本分屬不同的版本系統(tǒng),幾種版本之間內(nèi)容文字互有異同。而日本流傳的《近思錄集解》在內(nèi)容文字上與我國現(xiàn)存的幾種版本系統(tǒng)又有不同。如《近思錄》卷十四第二條“顏子,春生也”[8]306句,臺北元刻本、國圖元刻明修本的葉采注均作:“顏子亞圣之才,如春陽坱北,發(fā)生萬物,四時之首,眾善之長也。”[9]314其中‘坱北一詞,清邵仁泓刻仿宋本、四庫抄本中均作‘盎然,兩種版本的字形和讀音存在巨大差距,且“坱北”一詞似文理不通。以貝原益軒《近思錄備考》中保留的葉采注文作為橋梁,則可解釋這種差異原因。貝原益軒注:“(葉采注)坱圠。《字匯》:坱,於黨切。圠,乙黠切。坱圠,無垠際貌。《楚辭》:坱兮圠。王逸注云:霧氣,昧也。《賈誼賦》:坱圠無垠。”[1]811“坱北”一詞在貝原益軒注本中作“坱圠”,從發(fā)音到字義都注解十分清楚,“坱圠”為古漢語常見詞匯,意為‘漫無邊際貌。“坱圠”與“盎然”,古音相近,意義相近,與清邵仁泓刻仿宋本、四庫抄本的字形差異在訓詁學上屬于同源性的“一聲之轉(zhuǎn)”,而臺北元刻本、國圖元刻明修本作“坱北”則是因為“圠”字與“北”字字形相似而導致的刻誤。再如《近思錄》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條,也是全書最末一條,原文:“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圣人。”[8]326臺北元刻本并未收錄此條。國圖元刻明修本、清邵仁泓刻仿宋本、四庫抄本雖收錄有此條,但均無葉注部分,從國內(nèi)現(xiàn)存文獻看,葉采似沒有為此條作過注。而《近思錄備考》中卻罕見保留了此條葉采注部分內(nèi)容:“(葉采注)游山諸詩。《二程全書》五十四卷《明道文集·游鄠縣山詩》十二首,并序載之。案,此年嘉祐五年,明道二十九歲。”[1]818根據(jù)《備考》體例,“游山諸詩”四字為葉采注文,表明當時益軒所見《近思錄集解》的版本附有葉注“游山諸詩”等語,與國內(nèi)版本不同,為《近思錄集解》的版本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
結語
日本流傳的數(shù)百種“《近思錄》本土衍生文獻”是在接受《近思錄》及歷代注本的基礎上形成的,分為日文訓點類、注解講讀類、日本學者仿寫類。其中最具特色的文本,是以《近思錄備考》為代表的日本講學者、研究者在閱讀解說《近思錄》及其整理本的過程中,加以注解、講評而形成的講讀文本,數(shù)量幾乎占現(xiàn)存日本流傳“近思錄本土衍生文獻”的一半。關于《近思錄》內(nèi)容的本土化解說和具本民族特色的講讀,反映出六七百年間日本學者、讀者對《近思錄》的認知、消化與反饋。《近思錄備考》作為第一本針對日本初學者所編撰的《近思錄》本土化注解、講讀文獻,開啟了日本《近思錄》本土注解講讀類衍生文獻的先河,為《近思錄》在日本的傳播以及朱子學的普及做出了突出貢獻,在日本《近思錄》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近思錄備考》的文獻征引特點以及益軒自注的學術價值向我們展現(xiàn)了貝原益軒早期的儒家思想形態(tài),以及江戶時代初期《近思錄》在日本傳播的本土化接受狀況,同時其作為古籍的獨特版本價值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
【 參 考 文 獻 】
[1]益軒會.益軒全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73(昭和48年).
[2]陳榮捷.朱學論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3]朱謙之.日本的朱子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施璜.小學發(fā)明.刻本.安徽:紫陽書院,1698(康熙三十七年).
[5]李方子.重刻朱子年譜.刻本.安徽:紫陽書院,1700(康熙三十九年).
[6]黎靖德.朱子語類:第7冊.王星賢,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
[7]辻本雅史.貝原益軒和《大學》.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2).
[8]陳榮捷.近思錄詳注集評.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9]葉采.近思錄集解.程水龍,校注.2版.北京:中華書局,2020.
[10]程水龍.《近思錄》集校集注集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1]佐藤一齋.近思錄欄外書.程水龍,陶政欣,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編校: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