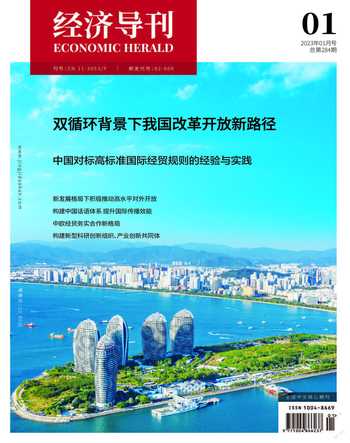數字中國戰略與新一輪全球化
許正中
黨的二十大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以胸懷天下、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戰略格局提出了我們未來的發展路徑。
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結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發展數字貿易,建設以數字中國為引領的強國戰略。
世界處在一個新的十字路口
無論是西方以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為主體的哲學思維還是東方解決人和人之間關系為主流的思維,現在都共同面臨著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三大洪流。這里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世界技術革命的新突破,這就是數字文明的較量。
這一次的技術革命同以往完全不同,最大的市場是技術集群、技術服務的突破。在這個突破中,國家、區域包括世界各地“灣區”之間的競爭,重點越來越集中到新技術突破的速度以及產業化的競爭。技術突破的速度越來越快,社會的發展也給我們提出新的要求。業內專家認為,這一輪疫情讓數字經濟提前了30年,烏克蘭危機又讓數字經濟超前50年。這意味著一個時代的漸變過程已變成了突變過程。我們對這一事態的發展,以及它對未來歷史走向的重大意義,要給以充分的估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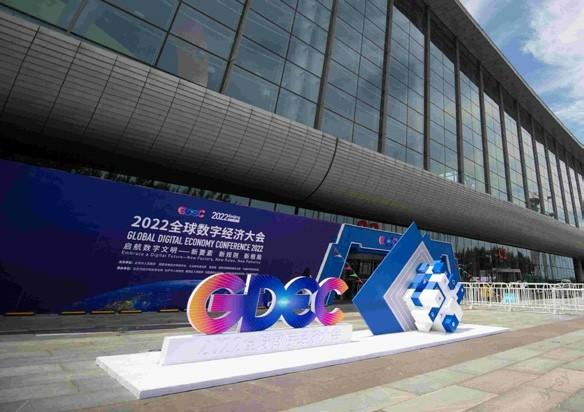
數字技術正在徹底改變經濟社會運行邏輯的基礎。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生活不斷追求的高效率、高質量、低成本、高滿意度,將會被共生、共享、共用并相互賦能的新型運作模式、運行規則所取代,并在形成數據驅動、軟件定義、平臺支撐、服務增值和智能主導的新的技術發展趨勢,數據生產要素形成新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重構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進而推進主導技術的變化、關鍵生產要素的變化,進而形成新的生產方式的變化,乃至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不一定都是線性推動的。種種跡象表明,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世界數字科技生態,呈現出越來越多的類腦特征;諸多數字技術的出現,都與互聯網大腦的各種神經系統的發育相關,未來的世界將成為產業大腦、智力大腦和城市大腦的競爭。
產業大腦促進產業鏈長、頭部企業,平臺的頭部企業成長和競爭,而不是一般的頭部企業的競爭。城市大腦實際是政府大腦。智力大腦是社會大腦。
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挑戰
未來中國的發展,存在幾個重要問題。
第一,城市化紅利走到盡頭,需要換賽道。城市化能解決人均GDP約2萬美元的發展空間。現在我國人均GDP約12000美元,美國是69000美元。它是怎么達到這個程度的?主要是數據價值化,將每個人的數據進行市場價值開發,又能解決2萬美元的增長空間。我近期去調研了幾個地方,特別是三一重工的數字化給人印象深刻,其中一個人一年的產值是1000多萬元,這是財富井噴。
第二,拓寬創新空間。深圳市的創新發展包含很多空間概念,城市創新空間能解決人均收入5萬-8萬元。以城市化、房地產需求帶動的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空間,但我們要思考如何換道。因為財富的空間承載需要更換賽道。
基于這樣的考量,我們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要翻過三大障礙:
第一個是“卡脖子”問題,即部分關鍵核心技術(如芯片)沒有掌握在我們手里。
第二是“卡腦子”問題,主要是思想、科學。像Google Scholar中的百科全書(電子版)的形式,放在Google Scholar里,但美國政府對我們實行封鎖,導致我們在知識信息檢索方面遇到很大的障礙。
第三是“卡嗓子”,我們要提升國際話語權。現在我們很多人很關注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但“卡腦子”、“卡嗓子”問題也同樣不可輕視。
對于中國的發展和雄心勃勃的遠景目標,美國有很強的危機感。本世紀初,美國還是世界絕大部分國家最大的商品供給國,但是到2019年,美國商品供給就縮到北美,在歐洲就是零星的地區,像英國、法國這些國家。
在向新的發展方式轉變過程中,一定要了解我們的對手,以及我們的任務和使命。美國把中國定義為第一競爭對手,這不取決于我們的意愿。但客觀上我們與美國之間的競爭是長期的,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其中一項,就是要把數字中國的建設作為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它不僅是一個經濟領域的任務,而且將引領我們進入一個文明時代。
從中美貿易沖突到烏克蘭危機,地緣政治的需要正在成為全球產業鏈重組的重要推手。將來我們要成為科技大國,但現在西方的地緣政治和冷戰思維還是他們戰略思維的主流。2022年4月,美國財長耶倫在公開演講時說,“我們的目標應該是實現自由但安全的貿易,將經濟問題與包括國家安全在內的更廣泛的國家利益考慮分開,將越來越困難”。美國正在進行從“離岸外包”到“友岸外包”的戰略轉移。
同月,歐洲中央銀行行長拉加德說,烏克蘭危機可能證明,它對歐洲和其他地區也是一個轉折點。“它使得供應商國家所屬的聯盟變得更加重要。跨國公司仍將面臨著在成本最低的地方組織生產的強烈動機,但地緣政治的需要可能會限制他們這樣做的范圍”。她說,經濟效率將不再是貿易和投資關系的唯一驅動力。
當前全球化存在的問題
當前全球化正遭遇逆流。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認真考慮幾個問題:
第一,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正在衰落,但是它的衰落是不是必然意味著以中國為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的開始?這里非常重要的是,要讓“中國+”成為外資和大多數跨國公司在新形勢下的必然選擇。
第二,美國和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斗爭方式不一樣。美國出手往往是以軍事和安全事務主導,中國是以經貿事務主導。中美之間的博弈將是長期的。2016年,中國的GDP達到美國的60%,而美國在歷史上對所有GDP達到其60%的國家都進行了打壓,它先后打壓了聯邦德國、蘇聯和日本。1975年蘇聯的GDP達到美國的71.2%,1995年日本GDP達到美國的71.3%。2021年中國GDP達到美國GDP的77.1%。美國對中國進行打壓是必然的。

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還面臨一些重要的考驗。第一,中國人均收入接近2萬美元了,我們還是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從近代以來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看,到了人均3萬美元時期,大概率會發生社會重大變革。在現代化進程中,要維護國家的社會穩定,這是一個大問題。在具備這個條件之后,低于3萬美元進行社會重大改革的,只有塞拉利昂沒有亂,塞拉利昂當時人均收入幾千美元。當中國的GDP總量相當于美國的130%-140%時,美國才有可能心平氣和,進入戰略伴生時期。現在我們還處于戰略相持時期。
新一輪全球化,呼喚世界性公共產品的供給。在數字經濟條件下,除了傳統的社會基礎設施的數字化之外,還要鋪就技術性社會基礎設施,比如IPV6、5G、6G,等等;同時還要鋪就制度性社會基礎設施,比如標準的商務服務、法務服務、政務服務;還有安全性基礎設施。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國作為大國,要提供一些關鍵性的世界性公共產品,這既是擔當也是必需。
世界新一輪技術革命將推動新一輪技術改造,構建萬物互聯的智能世界。近期美國馬斯克搞的星鏈計劃,將在外層空間部署42000顆人造衛星,現在計劃每天搞64顆;所發射的衛星可以回收,火箭可以重復使用。目前美國在天上已經有4000多顆衛星了。所以數字經濟讓創新生態系統成為國家、地區新的角力點。要把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政策鏈、資金鏈深度融合,形成促進創新的文化和制度生態環境。對我們來說,這是最大的國際國內的挑戰。
第三,創造人類文明的新時代。1847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新觀念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他說,只有運動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滯不動的。世間所有的東西都在運動和變化中。
在新一輪技術革命過程中,中國要為數字時代全球治理貢獻力量。我們近期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創新,比如為世界經濟增長開辟了更多的空間,也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提供新的思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的推動,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擁護。同時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新的貢獻。我們提出“一帶一路”作為對外開放實踐的重要平臺。
中國的兩大優勢
引領新時代最關鍵的就是要堅持高水平的開放。真正的高水平的開放,在制度設計方面,全球價值鏈時代的理想世界是“三零”,就是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我們參加的RCEP就是如此,進而推動倒逼我們的改革與發展。我們經過多年建設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供應鏈,現在我們要在這個供應鏈基礎上增加供應鏈的價值,形成供應鏈價值增值中心。
當然中國有兩個非常強大的優勢。一是超大規模市場,中國有14億人。根據梅特卡夫定律和達維多定律,在數字社會里面,一個區域的經濟價值或產品的價值,與和它關聯的移動末端的數量的平方成正比。中國的移動末端將近12億。美國總人口還不到4億。同樣一個產品,一個服務,中國的附加值是12的平方144,而美國僅是16。
雖然我們國家平臺經濟的國際化率很低,但我們培養的騰訊和阿里巴巴兩個平臺進入了世界前10強。這兩個企業最大的國際化率不到8%,而亞馬遜是28%(或43%),Facebook是56%以上。我們這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太強了。
第二個優勢是全球制造中心。我們在向供應鏈、產業鏈的中高端攀升的過程中,中心配套和集群,特別是融合式集群的優勢會一直保持下去。這跟我們國家的梯度發展是非常緊密的。
二十大報告提出要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在制度型開放下,才能夠抵御“灰犀牛”“黑天鵝”等事件產生的重大沖擊。越開放的地方,實際上它越穩定,封閉就將自我出局。
構建域外治理體系,將成為數字時代的內在制度要求。近期我們在做稅收金稅工程,因為數字技術是全球普及的,這樣我們能增加稅收上萬億。稅權是構建域外治理的調度閥,但首先要建立在產權、知識產權、股權這些方面。
二十大全面推動制度型開放進入了新的時代,制度開放主要是要通過市場化、國際化、法制化,引領創建新型的全球發展環境。
二十大提出,我們要引育全球現代化產業體系。引育就是不僅要引領,還要培育,主要是讓中國成為領導產業的策源地。要解決重大產業需求、重大技術突破;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在新發展格局下推動雙循環發展,以內循環帶動外循環,打造世界級戰略高技術產業集群。
(編輯 季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