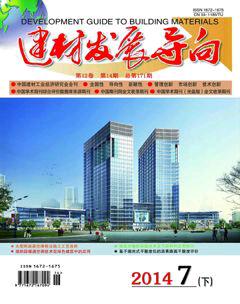淺談超高重力式擋土墻施工技術(shù)
吳桐
摘要:為進(jìn)一步加深人們對(duì)于擋土墻施工的認(rèn)識(shí),下面筆者基于自身多年工作經(jīng)驗(yàn)的積累以及總結(jié),結(jié)合某工程實(shí)例,就超高重力式擋土墻施工技術(shù)進(jìn)行詳細(xì)地闡述,望通過文章內(nèi)容的介紹,可為今后同類型工程的建設(shè)提供相應(yīng)的參考依據(jù)。
關(guān)鍵詞:超高重力式;擋土墻;施工;技術(shù)
根據(jù)擋土墻斷面設(shè)計(jì)幾何形狀或者其自身的受力特點(diǎn)來進(jìn)行劃分的話,可將擋土墻劃分為以下幾種,即扶壁式、重力式、懸臂式、半重力式以及衡重式等,在這之中,又以重力式擋土墻的應(yīng)用最為廣泛,這種類型的擋土墻主要是借助于墻身的自重來保持穩(wěn)定。本文就超高重力式擋土墻施工技術(shù)進(jìn)行詳細(xì)地研究與分析。
1工程案例概述
該工程屬于道路工程,施工總長度為255米,填方高度在15-20米區(qū)間的,長度是170米,而填方高度在20米的,其長度是105米。施工場地填方路段附近有相應(yīng)的居民建筑,且還有相應(yīng)的風(fēng)景景區(qū)。該工程填方路段處于該地某公園山體坡腳,其坡度相對(duì)較陡,地表屬于殘坡積粘土層、第四系雜填土以及耕植土,覆蓋層的厚度在0.5-1.0米之間。據(jù)統(tǒng)計(jì)調(diào)查可知,該線路經(jīng)過地段巖溶比較發(fā)育。此外,巖溶形態(tài)主要以地表淺部溶溝以及石芽為主,在巖體內(nèi)主要是懸臂巖體、溶孔以及垂直溶洞等,其中溶洞呈全充填或者半充填的狀態(tài)中。
2工程設(shè)計(jì)方案
在本文所闡述的這一工程中,擋土墻的荷載為A級(jí)荷載,所用材料為C25片石混凝土,其中上下層新舊混凝土間借助于接槎石來實(shí)施連接,且接槎石之間的距離為1.2米。在基礎(chǔ)結(jié)構(gòu)的設(shè)計(jì)上,將擋土墻基礎(chǔ)放置基巖上,其中基巖的分化程度盡量保持在中微風(fēng)化,且擋土墻的前趾嵌入至完整基巖內(nèi)深度不可低于1.5米,在基底內(nèi)沒有巖溶,清楚其內(nèi)部的各種填充物,同時(shí)還應(yīng)用高標(biāo)號(hào)的混凝土來實(shí)施回填處理。對(duì)于不同擋土墻的墻身高度,所選用的擋土墻基礎(chǔ)結(jié)構(gòu)形式也可有所不同。當(dāng)墻身高度大于14米且低于20米的時(shí)候,所用基礎(chǔ)應(yīng)該為A型。為使擋土墻和基礎(chǔ)圍巖之間所產(chǎn)生的這一摩擦力得以提高,防止在壓力的不斷作用下?lián)跬翂Τ霈F(xiàn)滑移現(xiàn)象,可基于原仰坡上,在A型添加相應(yīng)的榫頭結(jié)構(gòu),以此使基礎(chǔ)和基地圍巖之間的鍥接能力得到提高。如果擋土墻的墻身高度大于10米且低于14米的時(shí)候,所用基礎(chǔ)應(yīng)該為B型。
擋土墻的墻身混凝土結(jié)構(gòu)主要是利用分段以及分層來實(shí)施模筑,其中分層高度是2米,分段的長度是15米。沿著線路的具體走向大約每隔15米設(shè)置一道相應(yīng)的沉降縫,該縫的寬度為2厘米,可利用泡沫板或者膠泥來實(shí)施填塞。為使混凝土墻身結(jié)構(gòu)間整體性得到提高,于擋土墻墻身高度在6-20米間沉降縫位置處增設(shè)相應(yīng)的榫頭結(jié)構(gòu)。為轉(zhuǎn)換以及分解主動(dòng)土壓力,在原有的設(shè)計(jì)上優(yōu)化設(shè)計(jì)擋土墻墻背,即在原有的設(shè)計(jì)上每兩米是分層高度,并以此作為分界來逐層進(jìn)行臺(tái)階的修筑,其中臺(tái)階的寬度是75厘米。混凝土墻身的結(jié)構(gòu)形式如圖1所示。
圖1混凝土墻身結(jié)構(gòu)形式
3超高重力式擋土墻設(shè)計(jì)與施工
3.1設(shè)計(jì)計(jì)算
第一,土壓力。結(jié)合施工現(xiàn)場的具體地形地貌情況與有關(guān)需求,在本文所闡述的這一工程中,用C25片石混凝土,擋土墻的墻身高是20米,在墻頂以上填石,擋土墻背后的填石容重為20kN/m3,且內(nèi)摩擦角為35度。填石和擋土墻背之間摩擦角為18度,當(dāng)擋土墻墻背和豎直面之間的夾角為28度時(shí),墻背俯斜為1:0.53,擋土墻的墻身頂高為75厘米,設(shè)計(jì)荷載是A級(jí),且防撞墻每延米的重量為8.32kN/m。按照公路橋涵設(shè)計(jì)規(guī)定的相關(guān)要求,在土層特性沒有變化,且有汽車荷載作用,作用于擋土墻后主動(dòng)土壓力標(biāo)準(zhǔn)值β為0度的時(shí)候,可根據(jù)庫倫土壓力來計(jì)算。除此之外,根據(jù)城市橋梁荷載設(shè)計(jì)規(guī)范中的相關(guān)要求,計(jì)算填層厚度,即0.78米。通過上文內(nèi)容的闡述可知,作用于C25片石混凝土擋土墻主動(dòng)土壓力為33634kN,填層底面為6.9米,主動(dòng)土壓力垂直分力為23989kN,主動(dòng)土壓力水平分力為23574kN。
第二,擋土墻抗剪強(qiáng)度與基底應(yīng)力。將C25片石混凝土擋土墻基礎(chǔ)嵌入至微分化-中分化白云基巖中,所嵌入的深度不可低于1.5米,結(jié)合施工現(xiàn)場的實(shí)際地質(zhì)情況與相關(guān)規(guī)范要求,通過對(duì)比判斷擋土墻巖石地基的基本承載力。此外,在運(yùn)行過程中,C25片石混凝土擋土墻墻身最大剪應(yīng)力為0.77MPa,該值符合設(shè)計(jì)需求。
第三,穩(wěn)定性。在對(duì)擋土墻穩(wěn)定性進(jìn)行計(jì)算時(shí),要計(jì)算兩個(gè)穩(wěn)定系數(shù),即抗傾覆穩(wěn)定性以及抗滑動(dòng)穩(wěn)定系數(shù),其中抗滑動(dòng)穩(wěn)定系數(shù)可借助于以下這一公式來進(jìn)行計(jì)算,即Ke= ,Ke表示的是抗滑動(dòng)穩(wěn)定系數(shù),通過計(jì)算得抗滑動(dòng)穩(wěn)定系數(shù)為2.12,抗傾覆穩(wěn)定系數(shù)為3.57。通過上述內(nèi)容的分析可知,不管是抗傾覆穩(wěn)定系數(shù),還是抗滑動(dòng)系數(shù)均符合公路設(shè)計(jì)規(guī)范中的規(guī)定。
3.2施工
第一,模板。一為模板選用:擋土墻墻面?zhèn)人媚0鍨榻M合式的鋼模板,模板的高度為2米,長度為1.5米,厚度為5毫米,利用M16螺栓將各鋼模板連接,為防止模板接縫間出現(xiàn)漏漿現(xiàn)象,在模板間進(jìn)行0.5毫米公母扣的設(shè)計(jì)以此來過渡。而擋土墻的兩側(cè)面以及強(qiáng)背面所用模板為定形組合鋼模板,這種模板的高度為0.5米,長度為1.0米,厚度為5毫米,且鋼模板間同樣用M16螺栓來連接。除此之外,為防止模板和基面接頭處所存縫隙發(fā)生漏漿問題,在施工現(xiàn)場用M10砂漿來實(shí)施封堵。二為模板的加固:在擋土墻墻面某側(cè)的模板,可用木支撐來加固以及固定,或者增設(shè)相應(yīng)的水平桿來實(shí)施加固,并且于模板內(nèi)側(cè)位置假設(shè)相應(yīng)的臨時(shí)斜支撐或者斜拉撐來加固。由于擋土墻墻背以及兩側(cè)面組合鋼模板的加固以及固定和墻面一樣,在此筆者就不再一一進(jìn)行闡述。此外,擋土墻間榫頭用木板來加工,在刨光以后再用U形卡來固定。
第二,混凝土工程。在混凝土工程中主要包括兩個(gè)方面的內(nèi)容,即混凝土灌注與片石回填。在混凝土灌注上,所用混凝土全部是商品混凝土,在現(xiàn)場自制滑槽,配合汽車輸送泵來實(shí)施澆筑施工。在片石回填上,采取的是汽車式起重機(jī)以及人工拋填配合方式,首先于汽車式起重機(jī)的吊鉤位置增設(shè)一個(gè)相應(yīng)的鋼筋籠,接著裝入已經(jīng)清洗干凈的片石,當(dāng)將其吊到片石填方位置時(shí),再人工來實(shí)施拋填。
第三,排水工程。為避免擋土墻背后出現(xiàn)積水問題,防止由于積水而破壞填層以及擋土墻墻身結(jié)構(gòu),在施工中,應(yīng)于擋土墻墻背分臺(tái)階位置設(shè)置相應(yīng)的泄水孔,同時(shí)在擋土墻背后大約2米這一區(qū)間進(jìn)行級(jí)配碎石的回填,并設(shè)置相應(yīng)的隔水層。除此之外,若有必要,可通過透水試驗(yàn)來對(duì)擋土排水系統(tǒng)施工質(zhì)量進(jìn)行檢查。
4結(jié)語
綜上所述,隨著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速度的加快,信息技術(shù)水平的提高,擋土墻的應(yīng)用也隨之增多,且形式也越來越復(fù)雜。鑒于此,為進(jìn)一步深入認(rèn)識(shí)擋土墻,提高擋土墻施工質(zhì)量,本文結(jié)合某工程實(shí)例就超高重力式擋土墻施工技術(shù)進(jìn)行了詳細(xì)地闡述,通過本文內(nèi)容的介紹可知,在施工過程中,應(yīng)結(jié)合工程要求來予以合理設(shè)計(jì),同時(shí)還要加強(qiáng)排水工程、模板以及混凝土工程的施工控制,嚴(yán)格按照施工技術(shù)規(guī)定與要求來施工,從而確保其施工質(zhì)量達(dá)標(biāo)。
參考文獻(xiàn)
[1] 文暢平,楊果林.地震作用下?lián)跬翂ξ灰颇J降恼駝?dòng)臺(tái)試驗(yàn)研究[J].巖石力學(xué)與工程學(xué)報(bào),2011,30(7).
[2] 劉文治,康小宏,王瑞等.高填土邊坡多級(jí)擋土墻土壓力觀測試驗(yàn)研究[J].云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25(3).
[3] 謝新生,王錦葉,湯巍等.透水重力擋土墻的應(yīng)用研究[J].路基工程,2010(5).
[4] 趙雪茹,張光碧,王海祥等.UM模型下不同墻背坡比重力式水工擋土墻可靠度分析[J].廣東水利水電,2012(2).
[5] 李穎,姜少琳,楊啟超等.重力式錨桿擋土墻在高速公路中的運(yùn)用[J].山東交通科技,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