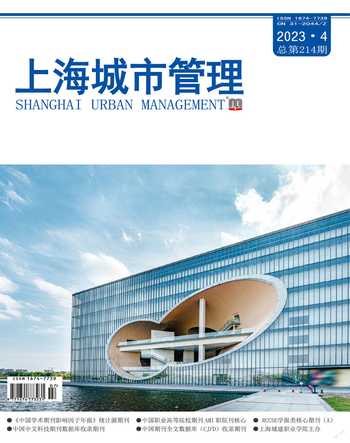共富工坊、政企社協同與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張丙宣 李爽 趙陸蓉 潘譽勻
摘要: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找準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有機社會的結合點,建立共富共同體。以杭州市東湖街道的共富工坊為例,構建組織創新和政企社協同的分析框架,研究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研究發現,黨建引領的共富工坊是一種共富共同體,通過組織創新和跨界協同,它將基層政府、轄區企業和社區的各種差異化需求和資源整合起來,實現企業增效、群眾增收和社區善治等多重目標的兼容共存。同時,共富工坊的功能逐步從經濟功能向社會功能、政治功能拓展。未來仍需要堅持系統觀念,統籌謀劃不斷拓展跨界協同的領域,創新組織模式推進資源整合,打造有用管用的共富共同體,以持續改革創新構建包容、有韌性、可持續的社會。
關鍵詞:共富工坊;組織創新;政企社協同;共同富裕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3.04.007
一、問題的提出
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找準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有機社會的結合點,以改革創新推動建立共富共同體。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指出,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推動有利于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不斷取得新突破,著力破除制約高質量發展和高品質生活的體制機制障礙。近年來,浙江、山東、江蘇、廣東等地的共富工坊、畝均論英雄、數字經濟“一號工程”、“兩進兩回”行動、農業科技特派員制度、共富合伙人、共富聯合體、村企結對富民興村等典型經驗,成為共同富裕創新實踐的鮮活樣本。同時,在推動高質量發展、區域協調發展、收入分配制度、精神文明建設等共同富裕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的改革創新不斷深化。那么,地方政府通過改革創新推動共同富裕的方式是什么?應當如何拓寬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在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上,現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四個方向。一是市場化取向。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強調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要素資源暢通流動,創新產業發展模式,[1]不斷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力,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推動高質量發展。[2]二是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的視角。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強調通過改革創新破解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性障礙,尤其是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3]社會保障制度、[4]集體土地制度、[5]數字普惠金融[6]等方面的改革。三是技術創新的取向。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指出,區塊鏈、數字平臺是共同富裕的技術支撐,需要充分運用數據要素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創新創業,[7][8]以數字賦能推進物質精神共富和農業數字化轉型。[9]四是發揮社會機制的作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強調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鄉賢、社會組織、基金會等多方治理主體共建、共治、共享,[10]推動多種社會機制之間融合共存、互補協同,[11]不斷激發社會的創新力。
需要指出,上述四種研究取向為研究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提供了理論基礎,并已經或正在被用于實踐,對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讓全體人民共創共享美好生活。共同富裕包括豐富的內涵,不僅包括物質富裕,還包括精神富裕。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系統性工程。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實現共同富裕,往往需要多種機制的組合與協同。近年來,作為公共管理理論前沿,協同治理、平臺治理越來越強調,利益相關者之間跨界合作的重要性。創建空間或界面,將各方利益相關者及其不同的技能、資源、知識或需求集聚起來,推動多方合作,以實現多方共贏的目標。[12-13]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如何找到多種機制的結合點,重新組合和協同多種機制,創新共同富裕的載體和模式,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問題。在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中,共富工坊是以組織創新驅動政府、企業、社區等多種機制協同的共富共同體,為研究經驗層面的共同富裕提供了生動的樣本。
共富工坊是共同富裕的一種實踐創新模式。針對企業招工難、社區低收入群體、老人和“寶媽”等就業難以及社區治理群眾參與不足等問題,通過黨建引領推動社區、企業和黨組織結對共建,共富工坊利用社區閑置場地,引導企業將適合外包的生產加工環節布局到社區,吸納社區低收入群眾、老人和“寶媽”等群體家門口就業,推動居民增收、企業增效,形成社區活動群眾積極參與的良好氛圍。與上述四種取向不同,社區共富工坊不是在多目標之間作出權衡和取舍,而是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和組織功能,促進政企社協同,將多種利益相關者聯結起來,實現多種機制的組合和多個利益相關者目標的兼容。
為此,本文以杭州市東湖街道的共富工坊為例,研究政企社協同推進共同富裕的機制。東湖街道位于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資源豐富。街道黨工委通過開展全域黨建聯建工作,推動政企社協同,搭建共富工坊助推全域組織創新,為企業降本增效、群眾增收和社區共建共治提供了有益的經驗。作為典型個案,共富工坊為思考政企社協同推進共同富裕提供了理想的樣本。
二、組織創新與政企社協同:分析框架
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并非唯一。要實現共同富裕,需要運用系統思維和系統方法,堅持共建共治共享,組合多種機制,創新組織模式,開展跨領域協同創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強調,堅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基層治理共同體。實際上,堅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設治理共同體,是建立有序和活力的良性社會的路徑,這對社會治理如此重要,對實現共同富裕也是如此。實現共同富裕,仍需堅持共建共治共享,建設共富共同體,構建包容、可持續、有韌性的社會。其中,共同體的邏輯、組織創新和政企社協同是以共富工坊為代表的共同富裕實踐探索的核心。
共同體的邏輯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價值理念和底層邏輯。共同體邏輯鼓勵利益相關者優先考慮他們的共同價值觀、實踐和追求,從而激發信任、互惠和道德責任,形成有助于約束利益相關者的共同體驗、價值觀、信念與規則,[14]形成集體身份和團結的集體,[15]建立新秩序。共同體邏輯還強調,通過獨特的組織形式,建立利益相關者區別于共同體以外成員的邊界,只有當利益相關者被視為位于組織邊界以內時,它們才能訪問社區資源,建立共識、信任、互惠,激勵利益相關者建立情感上的聯系,形成共同的身份和歸屬感。[16]要理解共同富裕的實踐創新,需要從共同體的邏輯出發,研究組織結構和協同合作過程。
作為共建的方式之一,組織創新旨在構建合作的結構和載體。與勞動力、土地、技術、資金和數據等生產要素一樣,組織創新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林毅夫強調,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內生于要素稟賦結構,持續的發展需要依賴技術創新和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17]組織創新推動要素的重組和要素結構的升級,將生產要素整合起來轉變成生產力。[18]從組織的角度看,共富工坊是一種組織創新。與家庭作坊相似,共富工坊也具有生產功能,建立在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上。但與家庭作坊不同,共富工坊具有顯著的公共性,是基層黨委政府與企業共建的產物,將企業生產的部分環節引入社區,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就業服務,促進物質和精神的共富,推動居民參與和社會共治。實際上,共富工坊是政企社共建的組織形式,基層黨委政府扮演著合作的領導者和推動者的角色。
作為共治的實踐之一,跨界協同推動共同富裕實踐創新的持續、擴展和升級。共同富裕等復雜的社會問題并非任何單一治理主體可以憑借技術性方案一勞永逸地解決,而需要利益相關方的協作。協同治理強調將公共和私人利益相關者聚集在公共機構的集體論壇上,參與以共識為導向的決策過程。[12]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本地相關組織等都是協同治理的參與者,他們對政策結果承擔真正的責任。當然,跨界協同必須由強大且獨立的組織推動。[19]在基層黨組織的推動下,共富工坊將企業、社區和富余勞力的差異化需求組合起來,開展政企社跨界協同治理。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工程。按照構建共富共同體的邏輯,通過組織創新和跨界協同,各地搭建的共富工坊,將多種機制和利益相關者納入進來,并實現了多方共享發展成果的目標。這是理解以共富工坊為代表的共富共同體創新的基本思路。需要指出,以共富工坊為代表的共富共同體并非建立類似鄉村或小群體一樣的熟人社會,而是以利益連接為紐帶,以促進物質富裕為手段,在有限的共同勞動和生活體驗中,為異質性流動性社會建立基本規范,形成最低程度的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將社區的物理空間轉化為社會生活的公共空間,重建陌生人社會的共同體。基于此,下文以杭州市東湖街道為例,在描述共富工坊改革創新實踐基礎上,深入理解以改革創新推動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三、東湖街道共富工坊的探索實踐
東湖街道是一個典型的城市郊區,具有獨特的“產城融合”特征。該區域的企業和流動人口多,低收入者多。為了解決低收入群體就業難增收難、企業季節性臨時性用工需求大以及招工難等問題,東湖街道黨工委堅持黨建引領,打造共富工坊,建立政企社跨界協同推進共同富裕的載體和平臺,重塑社區組織體系,使社區服務更加精細化、多元化和本地化,有效破解了企業招工難、富余勞動力就業難、社區治理參與度低等一系列難題。
(一)共富工坊的興起
東湖街道立足民生,關注民情,通過黨建統領和搭建就業共富平臺,多措并舉,推動充分就業和高質量就業,實現居民創收,助力共同富裕。該街道下轄48個社區,轄區有上萬家企業。該區域的低收入群眾、老年人和靈活就業人員(例如“寶媽”)的就業難以及企業招工難,政府助推企業降本增效的壓力以及居民家門口就業增收的愿望,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共富工坊的建立。
第一,政府倡導。政府倡導和政策推動是共富工坊快速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共富工坊由街道發起創辦,社區提供平臺承辦,專業機構參與運營,社區工作人員設計社區公共空間,為工坊提供場地支持。在共富工坊1.0時期,社區黨支部書記帶頭,深入居民摸排閑置勞動力、低收入農戶、技術技能人才等信息和崗位需求,走訪了解需求,社區以“搭臺子”的形式,搭建起用工單位與從業人員之間的“傳送帶”。在共富工坊2.0時期,社區共富工坊的日常運行已交由專業機構負責,形成穩定的供貨企業和從業人員,社區對工坊只發揮政治和組織作用。
第二,企業共建。街道轄區具有豐富的企業資源,臨時用工需求量大且就業機會多,社區內也有充足的富余勞動力,臨時就業需求高。隨著企業進駐工坊,通過工坊對接的勞動力資源,企業季節性臨時用工的難題迎刃而解。特別是對于用工需求集中、經營波動較大的服裝企業,共富工坊為他們解決了臨時性用工問題,提高了企業的整體運營效率,進而提升了企業效益。共富工坊符合社區和企業的利益,通過政企社的合作共建,實現工坊長效運營。
第三,居民參與。居民是共富工坊的重要參與者之一。共富工坊運用市場機制,為靈活就業人員提供了就業機會。共富工坊成立初期,社區工作人員通過公告欄宣傳和入戶推廣的形式,吸引了社區富余勞動力來工坊務工。共富工坊為社區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提供了一個家門口靈活就業的平臺,既為企業降低用工風險和增加了收益,同時也提高了居民的自我保障能力,促進居民創收,達到物質共富的目的。例如,龍船塢共富工坊已經吸納本社區及周邊村社20多名居民靈活就業,人均每月增收1000~2000元,同時還推薦了200多名居民去企業工作。
(二)黨建引領,推動基層組織創新
共富工坊建設是抓黨建助共富的創新載體。在社區共富工坊的運行中,基層黨組織發揮著統領作用,堅持黨建引領,充分發揮黨建聯盟的優勢互補作用,以工坊黨建帶動基層治理,助推基層組織模式的創新。
第一,黨建統領。街道以“情滿東湖”黨建品牌為抓手,著眼于民生和民情,通過社區基層黨組織聯合推進、黨員干部聯動和成員單位聯合推動等舉措,把轄區內企業的一部分生產加工環節布局到社區。同時,發揮流動黨員的先鋒作用,號召更多居民加入工坊,共建社區共富工坊。發揮社區流動黨員多的優勢,社區黨支部組建居民紅色業委會、樓道黨支部等功能性黨支部,定期舉辦流動黨員主題活動和樓道支部活動,引領和培養黨員成為“工坊骨干”,并將工坊骨干培育成黨員,實現社區黨員和工坊骨干的相互培養。這些舉措讓共富工坊成為建設“紅色根脈”基層堡壘的新載體,工坊骨干成為社區黨建工作的重要支撐力量,深入到樓道、深入到群眾中去,夯實了基層的群眾基礎。
第二,構建黨建聯盟,打造紅色工坊。作為黨建聯盟工作中的一環,共富工坊為轄區內組織共建、資源共享、事務共商提供空間,有助于深化政企社合作。社區黨群服務中心憑借紅色力量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拉近與周邊企業及社區居民的關系,樹立紅色企業文化,建立黨員職工隊伍,引導企業黨組織與社區黨組織結對共建。定期召開黨建聯盟聯席會議,掌握聯盟片區內各小區勞動力狀況和企業發展實況,分析聯盟片區企業項目適配度和群眾需求度,將部分適合外包的生產環節引入社區。此外,共富工坊還擁有一支由社區黨員組成的“紅管家”志愿服務小隊,協助管理黨建聯盟,加強黨建引領作用。
第三,黨建推動社區組織形式創新,將行政管理與社會自治有機結合。在共富工坊的運營中,面對來自各種主體的多元需求,基層黨委通過全域黨建聯建,成立了共富工坊,推動組織方式的創新,為提升治理水平提供最優解。在開展社區工作時,社區黨支部主導,功能性黨支部深入群眾和企業,了解社區和企業的需求,制定資源清單,并建立了多元主體的交流和共治平臺。針對小區居民反映較多的問題,召開由社區、物業和居民代表三方組成的聯席會議,集中討論解決方案,加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完善城市基層管理體制,創新組織運行體系,促進基層共治。黨建推動了基層組織模式的創新,加強了社區黨支部的建設,促進了群眾自治組織建設。
(三)整合工坊功能,打造和諧社區
共富工坊以共富為宗旨,鏈接企業、居民、社區,契合參與主體利益,激發社區內生活力,增強基層黨組織的社會、政治功能。社區利用閑置公共空間建立起集技能培訓、就業和勞作等功能于一體的共富工坊,規模化運作后,聚焦提升社區內生動力,推動企業和社區合作、社區和居民的良性互動。
第一,發揮共富工坊的經濟功能,推動居民增收和企業降本增效。共富工坊通過將“富余”勞動力轉化為“富裕”勞動力,幫助企業解決臨時性工人缺口,緩解企業旺季招工難問題,降低用工和場地成本,實現參與主體共贏。作為一種創新的共富模式,共富工坊為企業和居民提供了一個互惠互利的合作平臺。通過將部分產業造血功能移入社區,企業幫助低收入群體、居家老人和家庭婦女等就業弱勢群體實現靈活就業,促進居民增收再就業。在轄區內存在著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這些企業往往存在季節性、周期性用工荒的問題。在政府引導下,邀請企業黨員干部加入黨建聯盟,加強社企聯系,及時有效了解企業情況,解決企業降本增效難題。
第二,發揮共富工坊的政治功能,提升基層治理的效能。在共富工坊的建設中,基層黨組織扮演著“推動者”和“引導者”的角色。當共富工坊開始形成內生動力時,通過挖掘社區能人,組建自治組織,引導居民從被動參與向主動參與轉變。優化利益分配機制、擴大轄區企業規模、吸引外來投資,共富工坊讓居民就近靈活就業,提升了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號召力。例如,某電子科技有限公司與社區黨支部結對,承諾為社區電梯提供免費檢修服務,實現發展成果惠民利民。共富工坊還起著牽引作用,成為政府與居民之間溝通的良好媒介。群眾需要一個反映自身訴求的窗口,而社區也需要一個窗口,打破隔閡,深入群眾。共富工坊在這方面發揮了媒介作用,有效促成社區和居民的溝通,化解社區政策、服務和居民需求不匹配、不平衡的矛盾。
第三,發揮共富工坊的社會功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其中首要任務是解決居民參與不足的共性問題。社區共富工坊不僅是加工生產和群眾增收致富的車間,而且還是居民業余時間最喜歡的聊天空間。社區工作人員定期前往共富工坊了解民情民意,引導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治理。工坊為社區居民提供交往和活動的場所,也為社區工作的開展和居民矛盾調解提供了一個空間。社區共富服務綜合平臺圍繞共富工坊升級打造,形成共富服務、生活保障、醫療衛生“三大中心”,一站式提供就餐、康養、幼托等需求,滿足工坊就業居民及其他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四)社會治理功能植入,激發工坊活力
社區共富工坊以社區黨支部為核心,以社區為主體,聯合其他單位共建共治。東湖街道形成了以黨建引領為中心,黨支部、網格長、物業、業委會、居民代表和共建企業等六方協同的多元共建共治共享服務模式,增進了社企、社群聯系,促進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
第一,建立志愿服務團隊,促進居民融合。共富工坊勞動者經過培訓,成為社區一支相對穩定的志愿者服務力量。例如,龍船塢社區共富工坊的“紅管家”志愿者服務隊伍廣泛參與社區矛盾的就地化解之中,提高了社區服務能力。現實中鄰里交往的淡漠使得社區居民渴望充滿人情味的“歸園田居”式的社區生活。社區工坊成為鄰里生活和交往的場景之一,促進了社會參與和社會共治,旨在打造一個和諧、穩定、繁榮的社區。
第二,共建共治共享社會治理新格局。共富工坊匯聚社會閑置勞動力,利用富余勞動力創造穩定的安居樂業環境,助力基層治理。工坊的運營開拓了城市社區治理的新途徑,豐富了社區居民的生活。工坊為老人、婦女、低收入群眾等弱勢群體提供了自力更生的機會,讓他們在工作中體會共同富裕要靠勤勞智慧,同時促進社區居民的互動和交流,提升他們的責任感和獲得感,助力社區治理,營造和諧的社會環境。共富工坊作為一個利益聯結平臺,優化社區人才、資金和技術等要素的資源共享機制,居民在工坊運營中共享社區資源,增加了日常社會交往的機會,重新凝聚了社會共識,促進社區融合,促進鄰里和睦,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共建共治共享一個美好的社區。
第三,創新社會治理。共富工坊采用了一種基于共同利益和互惠互利的協作模式,將政府、企業和社區居民結合起來,共同推動社區的發展和進步。共富工坊在物質層面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和休閑場所,在精神層面為社區居民提供人文關懷,提高社區凝聚力,促進社會和諧。政府引導企業將生產加工環節布局到社區,為其提供更便捷、高效、低成本的生產加工服務,幫助企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市場份額和影響力,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形象。同時,共富工坊通過舉辦各種活動,促進社區居民之間的交流和合作,增強社區凝聚力和活力,植入社會治理功能,推動全社會共治。這種協作模式形成了“決策共謀、發展共建、建設共管、效果共評、成果共享”的良好局面,共同打造包容、可持續、有韌性的未來。
四、深化政企社協同推動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杭州市東湖街道共富工坊的實踐表明,實現共同富裕應該堅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系統謀劃,找準多種機制的結合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重組多種機制實現政企社協同,打造以共富工坊為代表的共富共同體,達成多方共贏局面。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多樣的,為拓寬共同富裕的路徑,未來需要堅持系統觀念,拓展政企社協同領域,創新組織模式推進資源整合,打造有用管用的共同富裕載體。
(一)堅持系統觀念,統籌謀劃不斷拓展政企社協同的領域
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堅持共建共治共享,運用系統思維,統籌謀劃,兼顧多重目標、多種主體和多種機制,實現多贏共贏。實際上,政策目標之間的沖突是普遍存在的。[20]政策分析需要一個替代工具理性的、能夠處理沖突政策目標的分析方法,溫希普提出了“解謎”的方法,即不是在多個目標之間做選擇,或者強加某個使沖突目標之間可比較的標準,而是嘗試找到一種方式,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目標。[21]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制定綜合性社會方案。與加劇收入、財富和機會不平等的新自由主義方案不同,施瓦布主張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社會性方案,在這種方案中,企業不再僅僅追求短期利潤,政府的職責是維持機會平等,打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確保所有利益相關者貢獻公平且分配公平,關注制度的可持續性和包容性。[22]因此,通過共建共治共享,尋求整合和實現多個沖突的目標,重塑整體性政策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思路。
統籌謀劃拓展政企社協同的領域。動員專業合作社、產業農合聯、基層供銷社等組織,結對幫扶社區弱勢群體,實現戶人均收入持續增加,建設具有“造血”功能的共富載體。秉持共建共贏的理念,充分發揮龍頭企業、行業協會商會、基金會和鄉賢等主體的積極作用。以集體資產入股等方式,積極推進社企共建共贏新模式,實現企業發展和村社集體經濟增收,讓群眾致富同頻共振。同時,鼓勵引導新鄉賢回歸家鄉,投身家鄉建設,促進項目回歸、資本回流和人才回鄉。鼓勵鄉賢成為發展的“智囊團”,鼓勵村企共建慈善公益基金,用于困難群眾臨時救助和公益事業的發展。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牽引作用,用市場機制解決社會問題。企業參與是推動共同富裕的有效方式。社區原有勞動密集型產業多,在政府引導下,入駐共富工坊,有效緩解企業旺季用工難題,同時減輕用工和場地成本。引入第三方運營工坊,緊盯供需兩端,為企業降本增效。社區通過送技能,進入工坊,居民可以就近在家門口靈活就業,穩步增收,提升技能,為高質量就業創業打下基礎。共富工坊的各參與主體利益契合,成為工坊運行的內驅力,有助于各主體實現共贏。
(二)創新組織模式,推進資源整合
實現共同富裕需要持續深化集成改革,創新組織模式,以組織模式的新跨界整合政企社資源。社會進步通常是技術創新和組織模式創新同時進行的結果。應當打破條塊分割、資源分散等壁壘,整合部門資源和力量,推進財政、民政、人社、文化、教育、科技、金融等部門的協同合作,形成“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工作體系。發揮組織優勢,開展“組織聯建、企業聯社、干部聯戶”活動,推動政策、企業、資金、勞動力等要素的重新整合。跨系統貫通,將共富工坊建設納入黨建聯盟組織體系,成立共富工坊志愿服務小隊,走訪轄區企業、鏈接資源。
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引領作用。發動社區黨員干部成為協調服務員,著力解決共富工坊等共富共同體建設運營中的各項問題。統籌推進區、街道、社區之間的跨層級協作,聯動第三方平臺,為工坊提供運輸、配單、質量監管等兩端服務,促進降本增效,提高工坊運作整體效能。黨建統領整合社區資源,盤活社區現有公共空間、閑置勞力等“沉睡資源”。同時,開展上門助企服務,宣講助企紓困政策,使“政策找人”取代“人找政策”。這些努力將有效促進勞動者增收、集體經濟壯大、企業經營增效,集成資源,匯聚共富共同體建設的合力。
打造全鏈條產業幫扶促共富模式。整合區域同一特色產業內所有生產經營主體、行業協會、服務組織,圍繞社戶對接推動低收入群眾增收這條主線,力促產、供、銷、技術和金融服務等方面深度融合。依托縣鄉兩級農合聯,以低收入群眾為主體,采取精準施策、合力幫扶的原則,做到扶志與扶技扶智并重、產業與就業銜接并重、生產與生活改善并重、生活與健康提升并重、一戶多策與綜合施策并重,突出“就業+產業”精準化雙重幫扶促共富模式。
(三)重塑利益聯結機制,打造有用管用的共同富裕載體
如何找到有效市場、有為政府和有機社會的結合點,重塑利益聯結機制,因地制宜建立適合當地的共富載體,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問題之一。老齡化、人工智能和全球氣候變化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使得傳統社會契約失靈。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沙菲克強調應該構建更加慷慨且更具包容性的社會契約,使人們共同分擔一些風險。[23]打造共同富裕的載體,需要以問題為導向,聚焦群眾的急難愁盼問題,通過重塑利益連接、突出功能集成、服務事項下沉,鼓勵基層探索,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
重塑利益連接機制,構建開放包容、可持續性發展的共富共同體。實現共同富裕,往往不是依賴一個主體或一種機制,而是需要依靠利益聯結機制將多種主體、多種機制結合起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完善利益聯結機制,不能富了老板、丟了老鄉,要通過就業帶動、保底分紅、股份合作等多種形式,讓農民合理分享全產業鏈增值收益。”[24]需要面向市場,不斷完善利益聯結機制,將群眾、集體的資產等資源納入產業體系,通過產業鏈、供應鏈、利益鏈融合,推動產業發展,實現企業發展和群眾增收的多重目標,解決共富共同體的自我造血問題。
不斷拓寬共富共同體的功能。建立以共富工坊為代表的共富共同體,是一個包容開放、功能不斷拓展的過程。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封閉、排斥和對變化的恐懼,譬如美國的郊區化過程中,建立永久性的中產階級社區,實施了對商業和制造業等不受歡迎的事和人的一系列嚴格限制,[25]本質上是一種對變化的恐懼而采取的自我封閉行為。相反,我們應該采取開放包容的態度,將共同富裕從經濟領域的物質增收不斷拓展到社會生活文化領域。通過將有限的、有意義的生產活動與社區生活空間創造性地融合,建立責任共同體,賦予社區空間更多社會和生活意義。將生產功能重新引入社區,促進群眾增收,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內容之一,但并不是全部內容。通過促進社會融合,建立居民共同的社會和文化身份,增強歸屬感,實現精神上的共富,不斷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需要指出,每種共富載體和模式都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我們需要正視這些問題。共富載體和模式產生于特定的政策、經濟和社區環境中,因此,這些因素的變化可能會給共富載體和模式帶來難以預料的沖擊。尤其是市場機制,共富工坊的產品市場競爭力和經濟下行的大環境從根本上限制了共富共同體的效用邊界。實現共同富裕不意味著不需要政府,共富載體不能取代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兜底保障作用。因此,在正視共富載體的局限性的基礎上,我們需要嘗試推動多個共富共同體的疊加重組,從一個領域到另一個領域,產生協同效應。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說明:本文系“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系列研究重點項目“共同富裕的探索與實踐——浙江建設示范區的體制機制改革探析”(21WH70098ZD)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郭曉鳴,丁延武.以城鄉融合促進共同富裕的戰略思考[J].經濟縱橫,2023(3):8-16.
蔡昉.如何利用數字經濟促進共同富裕?[J].東岳論叢,2023(3):118-124.
李實,朱夢冰.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促進共同富裕實現[J].管理世界,2022(1):52-61.
楊穗,趙小漫.走向共同富裕:中國社會保障再分配的實踐、成效與啟示[J].管理世界,2022(11):43-56.
程漱蘭,李爽.新中國農村集體土地制度形成和演進的歷史邏輯以及若干熱點問題探究[J].中國農村觀察,2022(3):19-31.
劉心怡,黃穎,黃思睿,等.數字普惠金融與共同富裕:理論機制與經驗事實[J].金融經濟學研究,2022(1):135-149.
沈文瑋.數字技術促進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與實踐路徑研究[J].政治經濟學評論, 2022(6):175-191.
唐任伍,范爍杰,史曉雯.區塊鏈賦能共同富裕實現的技術支撐、價值內涵與策略選擇[J].改革,2023(3):1-14.
楊大鵬.數字賦能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踐路徑和對策[J].中國軟科學, 2022(S1):71-75.
顧昕.共同富裕的社會治理之道——一個初步分析框架[J].社會學研究,2023(1):45-67.
徐鳳增,襲威,徐月華.鄉村走向共同富裕過程中的治理機制及其作用——一項雙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1(12):134-151.
Ansell,C.and A.Gash,Collaborative Platforms as a Governance Strategy[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2018,28(1):16-32;
Emerson,K.and T.Nabatchi,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s[M].Washington,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5.
Thornton,P.H.,Ocasio,W.,&Lounsbury,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structure and proces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Rao,H.,Monin,P.,&Durand,R.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oque Ville:Nouvelle cuisine as an identity movement in French gastronom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3,108,795-843.
Georgiou,A.and Arenas,D.Community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A Review and an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J].Organization Theory,2023,4(1):1-22.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M].蘇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艾倫·格林斯潘,阿德里安·伍爾德里奇. 繁榮與衰退:一部美國經濟發展史[M].束宇,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Kania,John,and M.Kramer.Collective impact[J].Stanford Social Innovation Review,2011(1):36-41.
Thacher,D.,& Rein,M.Managing value conflict in public policy[J].Governance,2004,17(4):457-486.
Winship,Christopher.Policy analysis as puzzle solving,in Moran,M.,Rein,M.,&Goodin,R.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克勞斯·施瓦布,彼得·萬哈姆.利益相關者[M].思齊,李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米努爾·沙菲克.新社會契約[M].李艷,譯.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
羅伯特·M.福格爾森.中產階級的噩夢: 1870-1930年的美國城市郊區化[M].賀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23.
Workshops, Government-Enterprise-Community Collaboration
and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Zhang Bingxuan, Li Shuang, Zhao Lurong, Pan Yuyu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dentifying the integration point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establishing a commun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key issue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in Donghu Street, Hangzhou, in the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cross-over collaboration, the paper studied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 led by party building was a kind of common prosperity community. Through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terest linkage it integrated the various differentiated needs and resources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communities under its jurisdiction, established a mechanism for linking interests, and expanded the functions of workshops from economic functions to social functions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In the futur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he system thinking, to make overall plans t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field of government-enterprise social collaboration, to innovate organizational models to promote resource integration, to create a useful and effective common prosperity carrier, and to achieve inclusive, resilient and sustainable society through continuous reform and innov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workshop;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government-enterprise-community collaboration; common prosperity
■責任編輯: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