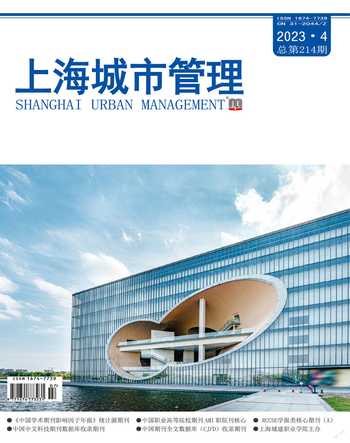新發展階段我國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研究
劉程
摘要:我國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模式仍然存在許多深層次矛盾。立足于新發展階段的新形勢、人口流動的新趨勢及其管理與服務的新要求,亟需推動我國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模式向包容性治理轉型。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強調“以人為本”“權利理性”“協作共治”“平等共享”,其核心是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流動人口的合法權利、促進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深化戶籍制度、社會福利制度、財政體制、農村土地制度等配套改革,需要健全跨部門跨地區協同治理機制、多元共治機制以及流動人口的自治機制。
關鍵詞:新發展階段;流動人口;包容性治理;公共服務;權利保障;社會融合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3.04.008
人口流動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引擎。有研究顯示,人口流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20%—30%。[1]在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新發展階段之后,我國正面臨著經濟增速放緩、區域與城鄉發展不平衡、人口陷入極低速增長和負增長、逐步邁向中度和重度老齡社會等嚴峻挑戰。與此同時,流動人口也出現了增速放緩、流動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年齡流動人口斷層風險加劇等新趨勢。立足于新發展階段的新形勢、人口流動的新趨勢及其管理服務的新要求,亟需推動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模式實現向包容性治理的轉型、推動流動人口平等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真正落實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從而為新發展階段的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提供可持續的要素支撐。[2]這既是加強與創新社會治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會影響到有效解決新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實現前景。
一、我國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模式的現實矛盾及原因分析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在資源匱乏條件下優先發展重工業,國家實施了嚴格限制人口流動和控制城鎮人口規模的政策。20世紀80年代之后,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勞動力剩余與城市勞動力不足之雙重矛盾的凸顯,我國出現了農村勞動力向城鎮地區的大規模流動現象,國家逐步有限度地放開了戶籍制度限制(包括藍印戶口、小城鎮戶口等)。進入本世紀以來,戶籍制度改革從促進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進一步過渡到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進入到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階段,并實施了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推動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常住人口全覆蓋、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等政策。與此同時,各地還形成了治安管理拓展型、大人口機構統籌型、專業機構協調型等多樣化的人口流動管理與服務模式。[3]
有研究認為:這些改革逐步打破了制約人口自由流動的制度性障礙,顯著地促進了人口的空間橫向流動和社會縱向流動。[4]但也有研究指出:這些改革并不徹底,流動人口仍然面臨各種顯性或隱性壁壘。[5]而且,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體制中仍然存在許多深層次的張力。[6]比如,中央倡導的公平正義、包容共享等執政理念,被一些地方政府權宜性地演化為基于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選擇性吸納(如“經濟接納,社會排斥”“吸納人才,疏解所謂‘低端產業人口”)。[7]地方化和碎片化的福利制度安排,使得流動人口難以獲得平等的福利地位。具有聯邦主義特點但地方政府財權事權不匹配問題突出的財政體制,導致地方政府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能力和動力不足。在發展不平衡的城鎮化格局下,流動人口的大城市偏好與落戶政策的中小城市導向之間的矛盾難以化解。缺乏公平合理的市場化退出機制的農村土地制度,也限制了流動人口“帶資進城”與全面融入城市的機會。
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工作機制同樣存在許多矛盾。在管理與服務主體方面,條條分割和條塊分割式的碎片化管理制約了流動人口管理服務資源整合與工作協同的實際成效。[8]在屬地化管理體制下,流入地實際承擔管理與服務工作但缺乏制度激勵,流出地政府則參與不足,因此難以形成“一體化”和“一盤棋”式的工作成效。在政府主體之外,各類社會主體與流動人口自身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在管理與服務方式方面,仍然存在“重管理,輕服務”的路徑依賴。在流動人口群體與利益訴求分化的背景下(尤其是新生代流動人口、城市流動人口、高學歷流動人口、家庭化流動人口、老年流動人口、自雇或創業型流動人口、農村回流人口等),流動人口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呈現出縱向增加、橫向擴張的趨勢(如廣義勞動權利、家庭團聚、子女教育、精神文化生活、社會參與等),更加凸顯了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模式的內在矛盾。在管理與服務績效方面,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仍顯滯后,流動人口的勞動力市場地位(職業地位、薪酬回報、工作條件、勞動強度、就業穩定性與失業風險等)、居住條件與生活境遇、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社會融合等方面處于系統性弱勢地位。[9]為了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勢必要推動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模式實現向包容性治理的轉型。
二、治理理論與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
包容性治理理念源于治理理論。治理理論的代表人物詹姆斯·羅西瑙認為,治理(Governance)是受共同目標支持并由多元主體參與的活動。[10]奧斯特羅姆等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論,并闡釋了它在提高決策合理性與有效性、降低策略成本與信息成本、克服搭便車行為等方面的優勢。[11]朱利安·愛德蘭博的互動治理(Interactive Governance)理論倡導各利益相關主體廣泛參與決策和執行過程。[12]赫爾曼·哈肯的協同學理論認為:通過系統內部各要素及其與系統外部的有序協作,可以實現資源最大化利用和整體功能放大的協同效應。[13]佩里·希克斯的整體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理論強調部門間主義、跨功能合作、跨組織邊界整合等,推動了跨部門協同治理理論的完善。[14]
在針對移民治理的研究中,亞歷山大·貝茨進一步指出:良好的移民治理必須滿足效率(Efficiency)、公平(Equity)、合法性(Legitmacy)和權利(Rights)要求。[15]西方移民治理政策主要集中于移民準入控制、權利保護、社會經濟融合等方面。[16]其中,移民準入控制包括準入條件限制、配額限制、非法移民的合法化等。移民權利保護主要指保護移民所擁有的發展權利。移民的社會經濟融合既包括流入地通過制度安排而進行的社會吸納,也包括移民自治以及在多元文化主義理論影響下的多元協同共治。
建立于治理理論與移民治理實踐的基礎之上,包容性治理又融合了包容性發展的“平等”(機會)、“參與”(過程)、“共享”(結果)理念,強調以“以人為本”代替“以物為本”、以“權利理性”代替“技術理性”,推動實現協作共治與平等共享。[17]它意味著各級政府要積極承擔包容性發展的責任,推動流動人口平等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從而將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真正落到實處。[18]
三、新發展階段我國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
流動人口包容性治理的核心在于切實面向流動人口及其家庭全生命周期所需,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流動人口的合法權利、推動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其重點是優化就業創業服務與勞動權益保護、提供公平普惠的教育與培訓服務、保障流動人口及其隨遷家屬的健康權益、優化安居服務與改善居住條件、提高社會保障覆蓋率與保障水平、推動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和社會融合。
優化流動人口的就業創業服務和勞動權益保護。為流動人口廣泛提供職業介紹、政策咨詢、職業培訓、就業援助等就業服務。加強勞動監察執法力度和對違法用工的懲處力度,完善欠薪保障資金的差別化征繳、申請和墊付、追償機制。完善勞動爭議仲裁和調解制度,探索在司法程序、法律援助、訴訟費用減免、司法救助資金保障等方面給予弱勢流動人口以傾斜性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多元化法律援助體系,為流動人口提供普惠可及的勞動權益保護服務。推動建立企業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推動流動人口參與工資集體協商,保障其逐步合理提高工資水平的權益。發揮稅收政策(如企業稅費抵扣)的調節作用,引導企業積極開展流動人口在崗和轉崗培訓,提高流動人口的勞動技能。將符合條件的流動人口納入創業培訓補助范圍,為流動人口創業者提供優質配套服務。
為流動人口隨遷子女提供優質公平普惠的教育服務。強化基本公共教育投入,保障隨遷子女接受普惠性義務教育的權利。逐步擴大學前教育、高中階段教育與職業教育資源向隨遷子女的開放力度,切實滿足隨遷子女的學前教育和高中階段教育需求、賦予更多隨遷子女就地參加高考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同時,加大職業教育投入力度、擴大職業教育補助范圍,健全產教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為有職業教育需求的隨遷子女提供優質和適應勞動力市場要求的職業教育服務。
切實保障流動人口及其隨遷家屬的健康權益。通過完善社區公共衛生服務、“送健康進企業”“互聯網+醫療服務”等方式,不斷提升流動人口聚集地區的公共衛生服務可及性,推動流動人口及其隨遷家屬平等享受各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通過“抓兩頭(兒童和老人)、帶中間(勞動年齡人群)”的方式,逐步彌補流動人口公共衛生服務的薄弱環節。強化高危行業與崗位的職業病防治工作,嚴格落實高危行業與崗位從業流動人口的定期體檢機制。廣泛利用社區、企業、新媒體等渠道,向流動人口普及健康知識、倡導健康生活方式。
構建適應流動人口需求的多樣化住房保障體系,切實改善流動人口的居住條件。通過出臺土地和稅收優惠政策等手段,引導流動人口集中的開發區、產業園區、大型集貿市場、大型企業與工廠等按照“政府規劃、企業投資、市場運作”的模式,提供公租房、員工宿舍等符合流動人口需求的住房資源。在城郊農村集體土地上,探索由村鎮集體經濟組織通過自行開發運營、聯營、入股等方式建設租賃住房,并有效覆蓋流動人口等各類人群。在優先關注事關城市實現人才集聚、發揮人口紅利的核心群體的基礎上,推動將更多流動人口納入各類保障性住房的覆蓋范圍,通過實物配租、貨幣補助等方式滿足流動人口對保障性住房的基本需求。因地制宜地通過整村改造、局部拆建、綜合整治等方式,統籌推進城中村、城邊村、棚戶區的改造與治理工作,多管齊下地優化流動人口的居住條件。
提高流動人口社會保險的參保率和統籌層次,完善社會保險的異地對接機制,并為經濟困難者和特殊流動人口提供必要的社會救助服務。完善廣泛覆蓋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險體系,并通過約束性規定和優惠政策引導用人單位積極為流動人口投保。同時,加大對自由職業者、小商販、中低端服務業從業人員參保的政策支持,切實提高其從業人員的參保率。逐步提高社會保障基金的統籌層次,配套建立區域間成本分擔和利益補償機制,逐步實現社會保障異地對接的“零障礙”。深化醫療保險異地就醫住院費用直接核查與結算改革,擴大基層直接結算定點醫院的覆蓋范圍,并逐步調整流動人口在異地基層醫療機構就診的結算標準。鼓勵養老保險采取靈活的繳費年限規定,探索建立分段計算、量化折算與合并享受養老保險權益等政策,加快暢通養老保險的異地遷移渠道。逐步有條件地將流動人口特殊困難群體納入低保和醫療救助范圍;積極利用公益慈善等力量,加大對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流動人口家庭的救助幫扶。
推動流動人口的社會參與和社會融合。簡化流動人口在現居住地或工作單位選區參加選舉的程序,保障流動人口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確保公共政策制定過程能夠充分吸納流動人口的利益訴求。在各級黨代會代表、人大代表等的產生以及評選各類榮譽稱號時,確保吸納一定比例的優秀流動人口。引導流動人口積極參與社區居委會選舉、參與社區議事活動,充分發揮流動人口中的優秀分子和積極分子參與社區建設、聯系和服務流動人口的橋梁與紐帶作用。充分發揮群團組織、居委會、社區活動中心以及各類社會組織的功能,廣泛開展流動人口普法教育、市民素養教育以及地方語言文化、生活習俗培訓等活動,推動流動人口實現社會文化融合。
四、流動人口包容性治理的制度改革
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推動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還需要優化城鎮化布局,深化戶籍制度、社會福利制度、財政體制、土地制度等制度改革,從而從根本上化解流動人口治理過程中的深層次矛盾。
構建科學合理的城鎮化布局。逐步形成以都市圈為主體、以中小城鎮為網底的城鎮體系,鼓勵多樣性的城鎮化模式。加快都市圈內部資源共享,推動大中城市的人口、產業和功能向郊區和周邊地區轉移擴散。通過完善配套設施與加強資源配置、增強中小城市(尤其是縣城)與小城鎮的就近吸納與安置能力,引導流動人口基于風險與收益、機會與資源、家庭生命周期與個人發展需要等因素而有序選擇流動、就業和定居。
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深化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擴大實行城市群內戶口通遷、居住證互認、戶籍準入年限累計互認等制度,探索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口制度。探索超大城市不同區域的差異化戶籍政策,有序放寬郊區新區的戶籍限制。逐步推動公共服務與福利保障脫離戶籍載體獨立運行,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擴大到所有公共服務,實現戶籍制度的“去等級化”和“去價值化”,逐步破除隱性戶籍壁壘。隨著戶籍身份附著福利的減少,將會為流動人口獲得平等機會與待遇、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創造良好條件。
建立低標準、均等化、可轉移的“國民待遇”和差別化“市民待遇”相結合的新型福利制度。在國家層面,明確所有社會成員均可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的目錄和執行標準,并作為“國民待遇”統一納入基本公共服務的個人賬戶,推動流動人口普遍享受到一體化、可轉移的公共服務。在此基礎上,鼓勵各地根據實際能力逐步提高公共服務標準,作為差別化的“市民待遇”(如地方增補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地方性的養老金標準、保障性住房等),并逐步賦予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基本同等的“市民待遇”標準。
建立健全事權財權相匹配的財政體制。落實“人地錢掛鉤”機制,擴大中央與省級財政對流動人口治理的轉移支付力度。簡化財力性轉移支付的內部結構、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的比例,并探索建立縱向轉移支付與橫向轉移支付相結合的財政制度,增強地方政府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稅收共享份額,推動形成地方財政收入隨流動人口規模擴大而增加的機制。積極探索投入多樣化、運行市場化、使用社會化的保障機制,引導民間資本、社會資金、外資通過適當形式有序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形成具有可持續性的資金保障機制。同時,督促各地政府按照常住人口調整財政分配結構,將流動人口納入教育、社會保障、醫療、就業等相關民生支出的測算范圍。
健全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推進農村土地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保障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和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等權利。建立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機制,完善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相關權益退出機制。在對農村土地和農民住房進行確權、登記、頒證的基礎上,遵循自愿、合法、公正、有償原則,因地制宜地采取有償轉讓、出租等多種流轉形式,保障農村轉移人口對承包土地、宅基地、農房和集體資產股權享有更大的處置權,保障農民“帶資進城”的權益。
五、流動人口包容性治理的多元協同機制
構建多元協同治理體系是流動人口包容性治理的必然要求。在這一體系之下,政府需要轉向“有限治理”。對于那些涉及廣泛共同利益的公共服務,政府必須積極承擔責任、以實現公平;對于可以市場化的公共服務,政府可以在做好統籌規劃的基礎上向私營部門和第三部門購買公共服務,以提高服務效率與服務質量。在政府系統內部,中央政府需要對下“放權賦能”,流入地政府需要主動承擔治理職責,流出地政府需要成為協同治理主體。同時,公眾、各類社會主體和流動人口自身也需要成為治理過程的積極參與者。
健全流動人口治理的跨部門資源整合與協同機制。建立縱向到底(由中央到基層)和橫向到邊(跨部門)的流動人口信息登記與共享機制,系統整合戶籍登記、就業登記、房屋租賃、衛生健康、社會保障、子女入學等各類數據,實現流動人口基礎信息的互聯互通與資源共享。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統、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補充采集數據,為流動人口動態監測、公共服務需求識別與精準供給等提供信息支持。設立高層次、有權有責的流動人口工作牽頭部門(或協調機構),建立聯席會議制度、資源共享制度、定期通報制度與目標考核機制等,實現各部門分工明確、協同有序的共治格局。[19]同時,建立健全流動人口治理重心下移的長效機制,推動流動人口治理工作落實落地。
建立健全流動人口治理的跨地區協同與聯動機制。通過協調利益、明確權責,在人口流入地與流出地政府之間廣泛建立跨地區工作協同和聯動機制,加強流動人口的信息共享、職業指導與職業介紹、勞動培訓與教育、勞動權益保護、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合作,逐步實現流動人口治理的跨地區“一體化”。人口流出較多的地方政府要積極組織開展勞動技能與勞動政策培訓(比如農村“兩后生”勞動預備制培訓與職業教育)、勞務輸出服務,密切配合流入地的治理工作(如人口信息核實與反饋、醫療保險異地結報對接),并積極開展針對流動人口留守家庭成員的各項公共服務(如留守兒童的義務教育、留守老人的養老保障與醫療服務);同時,通過實施優惠政策和優化服務,支持流動人口將資金、技術、經營方式等帶回家鄉,反哺欠發達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加快推動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
完善社會參與的多元共治機制。引導企業等經濟組織在保障流動人口基本勞動權益的基礎上,不斷提高其廣義勞動權利(如體面勞動機會、工資增長機會、繳納社會保險、職業培訓等)。工會創新組織形式與入會方式,強化自身獨立地位、職能權威及履職能力,并強化地區間、部門間的工會聯動機制,有效維護流動人口的勞動權益。共青團、婦聯等為流動人口搭建聯系政府部門的制度化渠道,通過集體協商、對話協商、調解仲裁等途徑,保障流動人口的各項合法權益。社區積極開展轄區內流動人口的信息登記,并引導流動人口積極參加社區議事、決策等活動;同時,為流動人口提供必要生活援助、融合教育、法制宣傳服務等,加快流動人口的社區融入進程。社會組織積極承接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為流動人口提供就業創業咨詢、法律援助等專業服務,不斷提升公共服務的可及性、覆蓋率與服務質量。
健全流動人口的自治機制。引導與扶持行業協會、同鄉會等流動人口自組織開展信息溝通、訴求傳遞、成員支持、矛盾協調、權益保障等服務,發揮其節約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和滿足多樣化治理需求的比較優勢。吸納綜合素質好、有較高威望的流動人口加入基層管理隊伍及社區自治組織,代表流動人口行使民主管理與監督權利,并產生凝聚民心、匯聚民力的作用。同時,引導流動人口積極積累人力資本、提高綜合素養,開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積極實現社會文化融合。
六、結語
流動人口的包容性治理吸納了治理理論與移民治理理論,融合了“包容性發展”的平等、參與、共享精神,并致力于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保障流動人口的合法權利、推動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合。通過治理體制機制的配套改革,將有助于化解流動人口治理過程中的深層次矛盾,有助于提升流動人口治理的能力與動力,有助于提高治理的回應性、參與性與治理績效,從而真正實現相關主體廣泛參與治理、共享治理收益的目標。這將為有效應對新發展階段的新挑戰和實現經濟社會健康、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提供保障。
說明: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轉型時期普遍性社會焦慮的形成、分化與治理研究”(19BSH131)、團中央“青少年發展研究”課題“青年優先發展理論與公共政策研究”(22JH06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郭田勇.我國流動人口規模為何先增后減[EB/OL].(2019-02-25)[2023-06-11].http://www.rmlt.com.cn/2019/0225/540320.shtml.
任遠.包容性治理城市流動人口[N].光明日報,2016-10-2(7).
肖周燕,郭開軍,尹德挺.我國流動人口管理體制改革的決定機制及路徑選擇[J].人口研究,2009(6):94-101.
Shen T Y, Lao X, Gu H Y. Migration Patterns and Intention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a:The Road for Urban Dream Chasers[M].Springer,2022.
Hong R J,Tseng Y C,Lin T H.Guarding a New Great Wall:the Politic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s and Public Provision in China[J].The China Quarterly,2022(251):776-797.
唐有財.雙重轉型、雙重張力與流動人口治理框架的建構[J].社會科學,2015(6):78-85.
Wang C G.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Realizing the CitizensRights of Migrants.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2018(2):11-31.
周學馨.從流動人口管理走向流動人口治理[J].探索,2009(4):121-125.
Lao X,Zhao Z H,Gu H Y.Revisiting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s Among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ese Cities:Spatial Differences and Multi-Level Determinants[J].SAGE Open,2022(2):1-16.
詹姆斯·羅西瑙.沒有政府的治理[M].張勝軍,劉小林,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拉里·施羅德,蘇珊·溫.制度激勵與可持續發展[M].毛壽龍,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Edelenbos J.Institutional Implications of Interactive Governance: Insights from Dutch Practice[J].Governance,2005(1):111-134.
赫爾曼·哈肯.協同學——大自然構成的奧秘[M].凌復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
Six,P.Holistic Government[M].London: Demos,1997.
Betts,A.Global Migration Governan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劉小敏,張桂金.西方勞務移民社會治理研究[J].社會發展研究,2015(1):209-233.
徐倩.包容性治理:社會治理的新思路[J].江蘇社會科學,2015(4):17-25.
鄭杭生,陸益龍.開放、改革與包容性發展——大轉型大流動時期的城市流動人口管理[J].學海,2011(6):76-80.
陳豐.流動人口跨地區服務管理機制銜接研究[J].社會科學,2014(1):91-98.
Research on Inclusive Governa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Liu Cheng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20002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till many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model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new trend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s,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to “inclusive governa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spirit of “people-oriented”, “right rationali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equal sharing”, and calls for accelerating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protecting legal right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social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inclusive governa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governance systems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inancial system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construct and improve the cross-sector and cross-region cooperative mechanism, multi-subject co-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self-governance mechanism of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floating population; inclusive governance; public service; right protection; social integration
■責任編輯:王? 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