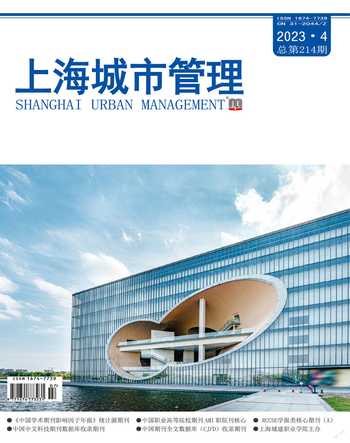土地發展權視角下超大城市集體土地租賃房規劃建設的思考
居曉婷

摘要:利用集體建設用地發展租賃住房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契機和方向之一。引入土地發展權進行理論分析,集體土地租賃住房建設是在不改變所有權的前提下,由集體經濟組織行使用途變更、強度提高的權利。在分析超大城市試點經驗的基礎上,總結當前集體土地租賃房建設的兩大核心問題,即收益分配機制的不足和系統性規劃體系的缺失。為此,提出要完善收益分配制度,保障農民權益;建立完整規劃體系,合理配置土地發展權;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更多元的政策支持。以此為突破口,拓展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及地上房屋的權能,賦予完整的土地發展權,顯化集體建設用地資產屬性,實現多功能復合利用。
關鍵詞:土地發展權;租賃住房;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3.04.010
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已于2020年獲得新《土地管理法》的法律確認①,在全面深化改革和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尋求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合法、合理利用,是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促進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1]與此同時,為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一方面可以擴大租賃房源供給、完善住房租賃體系,另一方面也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實踐方式之一,可以拓寬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利用渠道、積累入市改革經驗,并以此為突破口進一步破除城鄉二元的制度困境,促進城鄉統籌。2017年以來,原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等國家部委陸續發文支持集體建設用地發展租賃住房的試點;2021年,又提出引導多方參與保障性租賃住房的相關意見,利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便是其中的重要舉措之一。尤其是對于人口密度大、城鎮化水平高、土地資源相對緊缺的超大城市而言,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以下簡稱“集體租賃房”)為城市住房問題的解決、為中低收入人群居住權的保障提供了契機,也為低效集體土地的再開發與有效利用、為農民財產權的顯化提供了可能。
本次研究以土地發展權為理論依據,在總結國內超大城市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典型案例基礎上,對存在的問題予以剖析,提出基于保障集體土地發展權的集體租賃房建設的政策建議,以期為集體租賃房建設政策體系的優化完善、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全面入市提供參考。
一、理論基礎與研究綜述
(一)土地發展權、集體土地入市與集體租賃房
土地發展權是包含建設許可權、用途變更權、強度提高權等一系列土地開發權利構成的權利束。[2]土地發展權源于土地所有權,為了約束土地所有權人對土地的無限制開發,空間管制應運而生,從而產生了土地發展權。當前的空間管制已從傳統“二維”的用途管制轉向“四維”,[3]即涵蓋了用途、平面、立體、權益等方面的管制體系。因此,在我國的土地所有制背景下,土地發展權可以分解為四個維度:一是權屬維度,即判斷發展權歸集體所有還是國家所有,對應的是發展權的歸屬問題;二是建設許可維度,即農用地轉變為建設用地的權利;三是用途變更維度,即用地性質改變的權利;四是強度變更維度,通常是強度提高的權利。其中,權屬維度是土地發展權產生的基礎,只有明確了土地所有權,才能確定發展權的歸屬及收益分配;建設許可維度是用途變更與強度變更維度的前提,只有將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之后,才會產生用途變更與強度變更的需求。
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前,按照原《土地管理法》的相關規定,除了鄉鎮企業、村民住宅、鄉村公益設施外,“任何單位和個人進行建設,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須依法申請使用國有土地”(第43條),“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第63條),即只有將集體所有的土地轉為國有,才能賦予其發展權,集體土地的發展權受限。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的要求,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此后,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提上日程。集體建設用地的直接入市,打通了土地發展權不經權屬變更即可擁有建設許可的權利,可以視作權益的空間管制有所放松,在不改變土地權屬的前提下,賦予集體建設用地相應的建設許可權、用途變更權和強度提高權。集體土地直接入市,在不改變所有權的前提下由集體經濟組織行使土地發展權,可以將集體土地因發展權帶來的相關利益保留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即“漲價”歸集體,從而在確保集體土地社會保障功能的同時顯化其財產性功能。
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是集體建設用地入市的途徑之一,是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產物,也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首次進入住宅領域的突破性探索,[4]意義重大。集體租賃房改變了閑置低效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鄉鎮企業用地、村辦企業用地等生產經營性質的建設用地)的用途,改變為住宅用地,同時也改變了用地的開發強度(通常是提高開發強度)。由于權屬屬于集體所有,收益仍然屬于集體經濟組織所有。
(二)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相關研究
2017年,《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方案》發布后,對集體租賃房的研究,多集中于總結試點案例的經驗得失,歸納若干建設模式,剖析存在的問題,提出政策改善建議。有宏觀層面的模式總結,如郭永沛等從主導主體、土地使用權、運營性質等三個維度總結了北京的三種典型模式,并分析了不同模式在村集體收益與風險、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適用性等方面的差異;[5]嚴金海等分析了地方政府進行集體租賃房試點的動力、機制;[6]閆曼嬌等從供給和需求兩個角度了針對北京的集體租賃房政策效果進行仿真模擬。[7]也有微觀層面的個例分析,如張璋等通過問卷調研的方式對北京具體的兩個集體租賃房項目的現狀、問題進行了剖析,認為在項目融資、建設審批、利益分配、實際入住等方面仍存在問題;[8]吳克寧等分析了北京市集體租賃房典型案例的實施歷程,識別政策風險,并提出了政策建議。[9]
從已有研究來看,針對具體城市的經驗總結較多,理論層面的研究較少。本文基于國內超大城市的已有實踐,在集體建設用地入市改革的背景下,從土地發展權的角度剖析核心問題:一是收益分配問題,有利于理順權益歸屬,確保各參與主體的利益;二是規劃響應問題,有利于確保空間管制手段的科學合理。
二、國內超大城市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實踐特征
(一)實踐歷程與典型案例
2017年8月,原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聯合印發了《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方案》,確定北京、上海、沈陽、南京、杭州、合肥、廈門、鄭州、武漢、廣州、佛山、肇慶、成都等13個城市作為第一批試點,允許村鎮集體經濟組織突破原來法律政策規定,采用自行開發運營、聯營、入股等多種方式利用集體建設用地開展租賃住房建設。隨后于2019年新增福州、南昌、青島、海口、貴陽等5個試點城市,并進一步明確了租賃住房的選址原則,強調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監管要求。本文選取北京、上海兩個超大城市,總結集體租賃房規劃建設的實踐特征以及經驗與問題。
1.北京的大規模試點
北京早在2011年就開始了集體土租賃住房的探索,先后啟動了海淀區西北旺鎮唐家嶺村、溫泉鎮太舟塢村等4批5個項目。2017年以后,北京的試點進入穩步推進階段,將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寫入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年)》,從而有了總體層面的規劃依據。北京的試點計劃在2017—2021年的5年內供應10平方千米的集體土地用于建設租賃住房,截至2021年7月,已累計開工6.3萬套,規模居全國之首。[10]北京的試點在全國起步早、建成房源數量多、成效較為顯著,在完善租賃住房供應體系、優化國土空間布局、增加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收益等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總體而言,有以下兩方面的經驗可供參考。
一是規劃引領,科學選址。項目選址首先以落實《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2035年)》為前提,在統籌城鄉發展總體布局的同時,考慮建設用地減量化的要求,推進職住平衡、產城融合。具體而言,首先要符合規劃要求,布局在城市開發邊界內,并避讓永久基本農田、耕地、生態類規劃用地;其次是毗鄰城鎮集中建設區域、就業集中區域、軌道交通站點周邊區域。[11]已供應的集體租賃房項目主要位于北京的中心城區和平原地區的新城內。[12]
二是完善政策,簡化流程。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文件,保障了集體租賃房建設的穩定性和規范性,包括項目準入條件、申報主體、資金籌措、規劃布局、租賃模式、審批程序等多個方面,構建了完整的政策體系。同時,將除立項審批之外的權限下放至區級政府,包括項目預審、規劃、用地、建設等審批權限,簡化了審批流程,大大縮短了審批時長。全國首個運營的集體土地租賃住房項目——北京豐臺泊寓成壽寺社區,從立項到取得工程施工許可證,僅用了5個月時間,比計劃提前了2個月。所有集體租賃房項目均納入了北京市“多規合一”協同平臺,與建設項目辦事服務相關的13個部門在該平臺協同會商,提供“最多跑一次”的服務。
2.上海的點狀嘗試與自發探索
與北京的全面鋪開相比,上海的集體租賃房試點進展相對緩慢,松江是上海唯一的試點區,截至2021年底共有5個項目,其中首個集體租賃房項目于2021年3月投入運營。
松江區首先以土地確權登記為契機,明確了鎮村兩級集體經濟組織的入市主體。全區共有14個鎮級、98個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分別成立了鎮聯合社、村合作社,并辦理了集體經濟組織等級證書,確立了法人資格,從而可以作為集體土地入市的主體。[13]同時,為了規范土地交易市場秩序,完善地價管理體系,上海建立了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交易市場。通過編制《上海市城鄉建設用地基準地價成果(2020年)》,將集體建設用地納入基礎地價管理體系。結合規劃城市開發邊界,劃分城鎮和鄉村區域,城鎮地區設定6大類12小類用途,鄉村地區設定6大類9小類用途,是覆蓋全市陸域范圍、城鄉一體化的建設用地基準地價。
除松江區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嘗試外,上海也進行了使用農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打造鄉村人才公寓的探索。以浦東新區為例,率先在張江鎮新豐村將長期閑置的農民住宅改造為長租人才公寓,探索出一條“政府牽頭、農民供房、鎮企改造”三方合力的路徑。在自愿、依法、有償的基礎上,集體經濟組織與農民簽署協議,統一流轉宅基地房屋,實現集中管理,租期10到15年不等。具體運營方面,有村集體經濟組織自主經營、鎮屬集體企業負責經營、村集體經濟組織委托第三方企業運營等多種模式。鄉村人才公寓的實踐得到復制推廣,成為上海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亮點之一。這一方式將集體租賃房建設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從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拓展到宅基地,但又不同于農民自發的出租行為,是集體土地租賃房供給的創新之舉。
(二)經驗總結
對比和總結北京、上海的實踐,兩個超大城市的集體租賃房建設既有共性,也有差別。
首先,兩個城市都以集體租賃房建設作為化解城鄉二元矛盾、促進城鄉統籌的手段。面對城市住房供給不足和農村土地粗放浪費的矛盾、農村發展動力不足和土地資產大量閑置的矛盾,[14]在人口增長與建設用地總量約束的前提下,超大城市探索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一方面可以拓寬住房供應渠道,為中低收入者提供穩定、可負擔的住房。在存量建設用地有限而增量建設用地受限的困境下,建設租賃住房需要尋找新的低成本供應渠道,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降低了建設用地的流轉成本,增加了土地市場的有效供給,能夠最大限度滿足城鄉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和發展性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可以盤活農村集體閑置資產,幫助農民增收。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入市、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同價、同權”的改革背景下,閑置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及其地上房屋對于村集體和農民而言,是巨大的隱形資產,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能顯化集體土地資產屬性,讓集體農民共享土地增值收益,助力鄉村振興。同時,可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促進城鄉融合發展。農村地區的土地價格普遍低于城鎮地區,開發成本低,更容易吸引企業參與租賃住房,從而打破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給方面的壟斷地位,進一步推動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有利于形成多主體、多渠道的土地供給模式,達到以城市帶動農村、以住房促進發展的目的。
其次,北京和上海在試點政策的供給和響應力度方面有所不同,這也導致了租賃房建設進展和路徑的不同。北京的集體租賃房建設在試點城市中處于領先位置,這與北京的集體建設用地減量化目標相吻合有關。通過租賃住房的開發,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集體經濟組織對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拆補政策的支持,因此北京有積極作為的動力。根據《北京住房和城鄉建設發展白皮書(2022)》的統計,2021年北京共建設籌措了1.5萬套保障性租賃住房,其中集體租賃房的占比接近80%。上海則長期實行國有企業主導國有建設用地進行租賃房建設的方式,產生了路徑依賴,[15]對集體土地的利用往往傾向于自下而上的探索。
三、基于土地發展權的集體租賃房規劃建設主要問題
從土地發展權的視角看,北京和上海的實踐都缺乏收益分配機制的考量,一定程度上導致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權益缺乏保障。同時空間規劃的介入還不夠充分,影響集體租賃房總體布局的科學性,也不利于對租賃住房規模、結構供給的合理預測,進而影響整個住房市場。
(一)收益分配機制待完善
盡管對于集體租賃房而言,其發展權屬于集體所有,理論上收益也應當歸于集體所有。但在實際操作中,集體租賃房建設模式有多種類型,建設和運營主體也較多,利益分配難以形成定論。如在北京的試點過程中,約有半數項目采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國有企業聯營、入股的合作模式,即村集體與企業共同成立公司,其中村集體作為土地供應方,實力較強的村集體還可作為租賃住房建設方,企業則主要承擔租賃住房的建設或運營。該模式中,雖然規定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新成立企業中的持股比例不得低于51%,但剩余的收益分配沒有固定模式,因而在集體租賃房項目的開發建設中,土地一級開發、租賃住房建設和運營等各個環節都面臨著復雜的博弈過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企業的利益分配平衡成為租賃住房項目建設的重要挑戰和核心問題。[4]
(二)規劃體系待建立
北京和上海對集體租賃房建設都從規劃上進行了明確,但是從全市層面看,都缺少整體性的規劃統籌。集體租賃房專項規劃的缺失,也就缺少了空間管制的手段,難以明確實際的供給與需求,從而容易產生集體土地發展權的空間錯配問題。例如,北京根據全市可利用的集體土地資源分布和各區上報的情況,將集體租賃房的供地任務分解至各區,其中中心城區和近郊區的供應量約0.25平方千米,遠郊各區為0.05平方千米左右。[11]這種政府主導的追求供應量相對均等的做法,與租賃住房的實際需求之間很可能不甚匹配。上海雖然已基本完成全市鄉村地區郊野單元規劃(詳細規劃層次)的全覆蓋,但未考慮租賃住房的用地需求和空間預留。考慮到上海的集體租賃房項目數量本身就少,僅針對這些個別項目進行規劃調整,尚可應對,但若需要全面鋪開,則亟需進行全市的專項規劃對供給潛力進行梳理,對租賃房需求進行科學預測,對總體的空間布局進行合理安排。
此外,公共服務設施的配套規劃也同樣重要。集體租賃房項目所在的區域通常遠離配套成熟的城市核心區,本身的公共服務資源就有所欠缺。隨著租賃房的建設,未來將導入更多的居住人口,對文化、體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設施的需求更顯迫切。
四、完善超大城市集體租賃房建設的對策建議
(一)以人為本,保障農民合法權益
充分尊重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意愿,在明晰產權、村民廣泛參與的基礎上,在保障農民住房、公共服務等公益性設施空間的前提下,對閑置集體資產進行盤活利用。
鼓勵多元主體參與。集體租賃房具有價格優勢,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性質,故應以政府為主導開展規劃建設。同時由于集體建設用地的直接入市,土地發展權掌握在集體手中,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應該享有充分的知情權、決策權。考慮到租賃住房開發建設前期投入較大、后期也需要運營維護,社會資本的參與有利于平衡財務成本,提供相對專業的開發、運營服務。因此,集體租賃房的建設應鼓勵多元主體的參與。其中,政府作為監督方,可以在規劃統籌、開發監管、村企協調、租金監管等方面發揮作用。優先鼓勵具有實力的村集體自主開發,對于欠缺實力的村集體,可實行土地使用權租賃、作價入股等聯營方式引入房地產開發企業共同開發建設。同時創新運營管理模式,培育屬于村集體的運營管理團隊,也可以引入專業化、規模化的物業公司進行運營管理。
完善收益分配機制。以集體土地發展權歸集體所有、集體所有代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所有為前提,兼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建立完善集體租賃房利益分配機制和相應的實施細則,構建利益共享、多方共贏的機制。對應多元主體參與的開發建設過程,政府不參與收益分配的過程,但可以通過稅收的方式調節土地增值收益。如在上海松江的實踐中,集體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由松江區財政局統一征收,并在全區范圍內統籌使用,優先用于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低效建設用地減量、基本農田保護、農民集中居住等。[13]集體經濟組織按出資比例或股權比例獲得收益,并引導其通過收益分紅的方式將收益分配給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還可經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同意后按照一定比例作為公益基金,用于農村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管理。對于參與的企業而言,出臺激勵或優惠政策,如稅收優惠、地價優惠等,確保其收回成本、獲取收益。
慎重推動宅基地建設租賃房。按照當前的試點政策,集體租賃房應控制在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范疇內。而上海的鄉村人才公寓屬于“擦邊球”式的引入閑置宅基地作為租賃房,有一定的政策風險。建議近期仍然以閑置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為主,不隨意擴大土地供給的范圍,遠期可結合宅基地的有償退出,謹慎穩妥地利用存量宅基地,防止出現變相的小產權房。
(二)科學規劃,合理配置土地發展權
構建從專項規劃到詳細規劃再到實施方案的規劃和實施體系,一方面確保集體租賃房項目的全局性考量,另一方面也要有具體的規劃設計引導,保障選址布局、開發利用的科學性,符合風貌保護、公共服務配套的要求,合理地配置土地發展權。
專項規劃落實規模與布局。首先要確定可供給租賃住房的規模潛力。以現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為基礎,銜接各級國土空間規劃,在不影響農村宅基地使用、農村公益性設施和鄉村產業項目建設的基礎上,確定集體租賃房的供應潛力。其次,測算租賃住房的需求規模。以現狀調查為依據,借鑒參考國內外產業園區就業人口與租賃住房之間的匹配關系等相關案例,估算產業園區的租賃需求。最后,以匹配需求為準則,考慮租賃住房地塊本身條件以及相關布局原則,提出集體租賃房的規劃布局建議。布局原則包括:一是優先利用存量建設用地,尤其是閑置的工礦倉儲用地,在確保不突破建設用地總規模的基礎上,集約節約利用土地,這對資源緊約束的超大城市而言尤為重要。二是滿足職住平衡要求,推動產城融合發展。考慮到租賃房的承租對象主要為各產業園區就業人群,為實現職住平衡,在選址時應注意與就業崗位之間的距離和交通聯系,尤其是對超大城市而言,能夠促進城市空間資源集約利用、降低交通能耗。北京和上海都提出靠近產業園區、交通樞紐周邊地區等就業人口集中、交通條件便利的區域進行租賃房建設,從而促進職住平衡。
詳細規劃落實用地條件,打造鄉村社區生活圈。以村莊規劃為基礎,建議優先考慮規模大、形狀方正完整的地塊進行開發,盡可能形成一定的社區規模,以便配套公共服務設施。結合鄉村社區生活圈建設,在慢行可達的空間范圍內,統籌租賃住房和就業崗位布局,結合租賃人群的特征分析,合理配置公共服務設施,滿足租客文化交流、科普培訓、衛生服務、休閑娛樂等需求。以不破壞鄉村風貌為原則,對租賃房的容積率、建筑高度、建筑設計等進行管控引導。
實施方案落實具體操作細節。先期進行村民意愿調查,在滿足三分之二村民同意的基礎上,制定實施計劃,進一步細化租賃房項目建設的操作路徑,包括建設模式、時序安排、資金來源、運營計劃、收益分配等。
(三)深化改革,提供多元政策支持
完善金融支持政策。一是鼓勵國有銀行加大信貸資金支持力度,可采取長期低息貸款方式,支持集體經濟組織籌措啟動資金。二是加大政府財政支持力度,可通過政府承租、預付租金的方式提供項目資金支持,建成后納入政府保障性租賃房源統一管理;同時給予集體租賃房項目稅收優惠及水、電、氣等公用事業收費優惠。
簡化規劃用地手續。對符合專項規劃和詳細規劃的租賃房項目,簡化規劃調整程序和用地手續,整合精簡審批事項和審批流程,逐步實現“多審合一”“多證合一”,簡化鄉村建設規劃許可證辦理。
五、結論與討論
集體租賃房建設之于農村,可以盤活閑置資源,增加農民收入,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抓手;之于城市,則可以增加低成本租賃房源,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架起了農村和城市之間資源要素流通的橋梁,對實現城鄉統籌戰略目標具有重大意義。本文對北京、上海這一類超大城市的集體租賃房試點進行了梳理總結,發現在我國土地發展權缺失的現實條件下,對于收益分配、規劃統籌還有不足之處。因此,建議以集體土地發展權的歸屬為依據進行收益分配,保障作為弱勢一方的農民和集體經濟組織的權益;構建完整的規劃體系,合理配置土地發展權。
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是集體建設用地的供給側改革方式之一,可以此為突破口,在未來通過進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如允許自愿有償退出的閑置宅基地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后進入住宅市場。[16]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基礎上,拓展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及地上房屋的權能,賦予完整的土地發展權,顯化集體土地資產屬性,實現集體建設用地的多功能復合利用。
注釋:
①如無特別說明,本文中的“集體土地”“集體建設用地”均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
參考文獻:
林依標,林瀚.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實踐思考[J].中國土地,2021(6):4-8.
林堅,許超詣.土地發展權、空間管制與規劃協同[J].城市規劃,2014(1):26-34.
林堅.土地用途管制:從“二維”邁向“四維”——來自國際經驗的啟示[J].中國土地,2014(3):22-24.
田莉,陶然.土地改革、住房保障與城鄉轉型發展——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改革的機遇與挑戰[J].城市規劃,2019,43(9):53-60.
郭永沛,賀一舟,梁湉湉,等.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政策研究——以北京市為例[J].中國軟科學,2020(12):94-103.
嚴金海,劉紅凱.地方政府土地政策試點實施的動力與機制——基于B市集體土地建租賃住房試點的案例分析[J].中國土地科學,2022,36(5):112-121.
閆曼嬌,陳利根,蘭民均.供需系統視角下北京市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政策效果仿真研究[J].中國土地科學,2022,36(2):63-72+116.
張璋,周新旺,毛昊瑩.農村集體土地建設公租房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調研——以北京市為例[J].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8(4):49-55.
吳克寧,馮喆,黃保華.北京市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典型實例調查[J].中國土地,2019(6):22-24.
北京市人民政府.集體土地租賃房累計開工6.3萬套 建設規模居全國之首 2021年新增開工0.9萬套[EB/OL].(2021-07-22)[2023-03-05].http://www.beijing.gov.cn/fuwu/bmfw/zffw/ggts/202107/t20210722_2446398.html.
嚴雅琦,田莉,王崇烈.利用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實踐與挑戰——以北京為例[J].北京規劃建設,2020(1):95-99.
田相偉.集體土地建設租賃住房的規劃建設與管理——北京的實踐與挑戰[J].北京規劃建設,2021(3):23-27.
費岑.松江區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開展租賃住房建設的實踐與思考[J].上海房地,2021(5):46-49.
柴鐸,林夢柔,范華.集體土地建租賃住房的利益影響機理與多中心治理機制[J].經濟地理,2018,38(8):152-161.
田莉,吳雅馨,嚴雅琦.集體土地租賃住房發展:政策供給何以失靈——來自北上廣深的觀察與思考[J].城市規劃,2021,45(10):89-94+109.
吳宇哲,于浩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住宅用途入市的現實約束與賦能探索[J].中國土地科學,2021,35(5):93-99.
Thinking on the Rental Housing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n Collective Land
Ju Xiaoting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The use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to develop rental housing is one of the opportunities and direc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ollective commercial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This paper introduces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for theoretical analysis. The rental housing construction on collective land is the exercise of rights to change the use and increase the intensity of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without changing the ownership.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ilot experience in mega-cit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wo core issues of the current rental housing construction on collective land, namely, the lack of in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and the lack of systematic planning system. Therefore, we should improve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farmers; establish a complete planning system and rationally allocat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further deepen reform and provide more diversified policy support. Take this as a breakthrough, we can expand the rights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and houses on the ground, give complete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manifest the property of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land assets, and realize multi-functional composite utilization.
Key words: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rental housing; collective commercial construction land entering the market
■責任編輯: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