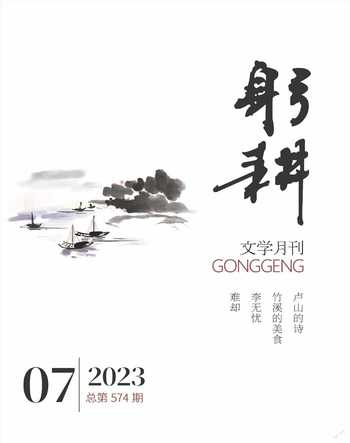老舅
徐玉向
正當(dāng)老舅要邁過水溝時,忽被一聲“賣豆腐的”攔了下來。他歇下挑子,從另一個木托板上抽出一桿帶著鋁托盤的秤,接過遞過來的一小包黃豆。秤,在兩人的目光中輕輕打了一個晃,終于安靜下來。
把豆子倒進口袋,空袋子還過去之后,乳黃色的紗布被揭開了。切刀靈活地在白嫩的豆腐上輕輕一壓,再豎著一按,最后平著刀身插進托板和豆腐中間輕輕一抬,一塊豆腐連著清清的汁被撂到秤上。面無表情的秤砣,亦如幾秒鐘前稱黃豆一般,高高仰起。圍觀者不約而同地微微翹起嘴角。
常常,在院子里老遠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豆腐嘍,豆腐嘍!打豆腐嘍”。 廚房里,母親趕緊朝灶膛添幾把柴,對支著耳朵的我們喊,“可想吃豆腐了?還不快去迎舅舅”。
我們奔出院子,覓著老舅漸漸接近的吆喝聲,在路口站定。隔著一條窄窄的小水溝,幾棵歪脖子柳樹遮掩下的彎彎曲曲小路上,先轉(zhuǎn)出一個忽閃忽閃的木托板。幾根繃得筆直的粗糙麻繩,從小案桌般大小的木托板底下攀向一截黃中透著黑漬的扁擔(dān)。隨著扁擔(dān)忽上忽下微微顫動,木托盤成了蕩漾在波濤中的一葉浮舟。
托盤上蓋著一層乳黃色的粗紗布,一把錚亮的薄薄的切刀,似蹺著腿躺在稻草垛上的孩子,在明媚的陽光下充滿了愜意。一只洗得有些泛白的黃勞保鞋,已穩(wěn)穩(wěn)地隨著晃悠的木托板出現(xiàn)在我們眼前。
見陸續(xù)有人圍上來,老舅趕緊鏟了一大塊豆腐讓我們先捧回家。待他進了院子,桌子上已擺好飯菜。飯后,他把上面掏空了的托盤換到最底層,又理了一下后面的黃豆袋子及一小包零錢。再出院子,我分明看到他的步子似輕快了許多。
從記事起,房前屋后的鄰居在閑時總會叫著我的小名,問我“舅舅怎么賣豆腐的”。我馬上微微前傾稚嫩的肩,右手虛握在肩前,左手掐著腰,晃晃悠悠地走上幾步,再嚎上幾聲“豆腐嘍!豆腐嘍!”約莫剛喊上兩聲,觀者笑得開始抹眼睛。
老舅賣豆腐的印象,似我家小院里的一草一木,從小就刻在骨子里。自大舅定居?xùn)|北后,老舅就成了家里的“當(dāng)家人”。上有父母,下有四個孩子,此外,還有人情往來。農(nóng)閑之時,他就想辦法補貼家用。
每天清晨,老舅就挑著豆腐離開家。除了趕臨近的幾個集市,他大多在方圓二三十里的村莊轉(zhuǎn)悠。到了十幾里外的我們村時,基本是接近晌午。
老舅加工豆腐的地方有兩處,一處在打麥場上的土坯房里。寬敞的數(shù)十家場連成一片的東北角,隔著一條小溝靠近大馬路的地方,孤零零地立著一間茅草屋,門口停著一輛上了車幫的架子車。屋子并不大,正中間是一個八仙桌大小的石磨。磨有三層,石基上面是一個大磨盤,再上面有兩個緊緊咬合在一起的小磨盤。首層的磨盤有個洞,像一個小漏斗,第二層有個豁口,下面放著一只木桶。每個磨盤都刻著一道道的深痕,似放大了的老年人臉上的皺紋。幾只桶擺在墻角,除了盛著水和泡好的黃豆,其中一只桶裝滿白糊糊的豆?jié){。墻上的木樁上掛著一把刷子。
一頭黑驢,被蒙著眼睛,套著桿子默默地圍著磨盤打轉(zhuǎn)。舅媽不斷地朝磨盤上加豆子,隨著吱吱呦呦的磨盤轉(zhuǎn)運,一股股乳白色帶著些許豆腥味的漿汁流進木桶。幾只笨重的木桶陸續(xù)被裝滿,老舅伸手搬到架子車上運回家。有時,在家的表哥們也會搭把手。
老舅家堂屋和西面的屋子沒有砌隔墻。西北角,一面貼著墻的大灶上面,置著一口讓我在里面洗澡都綽綽有余的大鐵鍋。灶口正對著西南角碼得整齊的柴火。屋子正中的房梁上懸著一截手臂粗的麻繩,最下面捆著一個樹杈做的掛鉤。掛鉤系著一張紗布濾網(wǎng),下面對著一口大水缸。好在南墻還有個小窗,窗口離濾網(wǎng)不遠。南墻根下摞著一堆裝豆腐的木托盤。
木桶抬進屋子后,先把豆?jié){汁一瓢一瓢地舀到濾網(wǎng)中,一個人專門輕輕推著撐子的把手來回晃動。此時的豆?jié){汁,仿佛搖籃中的嬰兒,開始輕輕翻滾,漸漸沉寂下來。
過濾了雜質(zhì)的豆?jié){再倒進大鍋里煮。大鍋里的熱氣不斷升騰,慢慢充盈在屋子的每個角落。陽光好奇地從窗子溜進來,也僅僅在空空的水缸沿盤旋了一會兒,仿佛就被大鍋的杰作唬得止住了腳步。
椅子上的我,再也坐不踏實,伸著脖子直勾勾地瞅著熱氣在半空中不緊不慢地跳舞。也不知道熬了多長時間,咽下多少口水,直到舅媽拿來兩只空碗,再掂起長臂鐵勺伸向沸騰的大鐵鍋。
平放在八仙桌上的碗,似乎已裹不住隨時都要升騰而去的白白嫩嫩的豆腐腦。仿佛不帶一絲人間煙火氣息的家伙,就這么橫在粗糙的大瓷碗里,直挺挺地勾著我的魂靈。它那蒙蒙的又微微發(fā)亮的表面,清晰地閃著我口水折射出的光芒。一股說不清的香,直透腦門。此時的我,趴在那張八仙桌上,一邊瞇著眼盯著碗,一面對著同樣一臉笑容的小表哥。舅媽灑向碗中的那一小勺白糖,成為這道美味最佳佐料。
柴火一把把向灶里填,熱氣一縷縷向外鉆,大鍋咕嘟嘟地響。在努力吞咽美食的剎那,我猛然瞅到灶臺前埋頭燒火的老舅,他的身上似被水澆過一般。
做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把豆腐裝進模具,也就是那些木托板。木板上鋪上紗布,運到水塘邊的平地上,壓上石塊瀝水成型。
除了做豆腐,老舅還順帶做些千張,有些地方叫豆腐皮。這些同樣受到鄉(xiāng)下人的歡迎。聽大人們說,做豆腐和豆腐皮過程中產(chǎn)生的豆腐渣,現(xiàn)在成了圈里豬兒的美食。
我一直以為,身高一米八幾的老舅也就是一身力氣,干點粗活還行,誰能想到他打笆斗也是行家。家里人說,他以前經(jīng)常編東西,只是我去的次數(shù)少沒看見罷了,家里裝糧食的大笆斗就是他的手藝。
我恍然想起母親曾經(jīng)說過,舅舅家那一帶傳承著柳編的手藝。柳編的材料并不是柳樹,而是一種筷子般粗細一兩米高的杞柳,俗稱“條子”。
淮河大堤以及水洼溝渠兩側(cè),都是種杞柳的好地方。路邊的幾個池塘,經(jīng)常漚著一捆捆割好的條子。有一次我看見表哥從田里運來一架子車條子,我以為是柴火,幫忙往下搬。哪知看起來輕飄飄的家伙,我用盡力氣也搬不動。表哥和舅舅扛起來就往塘里拋,有些還在上面壓了石塊。其他幾個塘邊也是黑壓壓的一片,那是別人漚的。
階下一排池塘,每個池子都蓄著綠汪汪的水。南側(cè)靠路的一邊拴著牛,北側(cè)就漚著條子,只有中間才是麻鴨們的地盤。只要條子在池塘里過了夜,小魚小蝦都喜歡往里鉆。麻鴨們鬧騰一陣后,拍拍翅膀繼續(xù)在池面巡游,條子卻一捆一捆地被鋤頭撈起,擱在塘邊的空地上淋了水直接被運走。
條子漚好之后接下來就是抽皮。抽皮的工具也很簡單,一個鐵條模樣的物件,緊緊卡在上面,順著條身一溜皮就開了,揭了外層褪色的皮,露出條子精貴白嫩的身體。剝完皮的條子,在院子里晾曬后打成捆存陰涼處備用。
午后的陽光,閑得百無聊賴,似周身沒了骨頭一般晃晃悠悠地向歪脖子柳樹上靠了過來。樹下正埋頭編笆斗的老舅,連眼皮子都懶得抬一下。偶爾有熟人路過,他才抬起頭利索地打個招呼。
一只四腳矮凳,穩(wěn)穩(wěn)托住老舅的身軀。兩捆白嫩嫩的杞柳條子緊緊疊在一處,靠著板凳的一捆已完全打開,只剩下十幾根。他的背似一座堅實的山梁,額頭藍灰的帽檐,隨著雙手上下翻動忽前忽后地顫動。他的眼半瞇著,唯一的一絲精亮,都聚集在面前的家伙上,生怕有一點兒閃失。接口縫隙大小,壓條疏密,腰身圓塌,無不在那道精光里盤算著。匯聚了幾十年手藝的那點精神頭,不亞于任何一臺精密的儀器。
老舅的嘴里銜著一截約五六十厘米長的細條子,左手撐著笆斗架慢慢翻轉(zhuǎn),右手連連往下挑壓,一只腳抵著笆斗的底座,另一腳半伸著。腳前擱著一把用破布條纏著的刀片,以及一柄木榔頭。
老舅右手食指裹著布條,左手食指和右手的其他幾根手指肚上,布滿累累傷痕,虎口處則是一層厚實的蒼黃老繭。小蘿卜一般粗的手指頭,此時似一臺靈活的機器,錯落有致地翻動著。才幾分鐘的工夫,剛接上的條子鉆進笆斗間的縫隙,只剩下一小截尾巴。老舅順手把口中的條子接上,繼續(xù)挑壓。笆斗在他手中輕輕轉(zhuǎn)動,笆斗壁一點點往上攀,估計用不了多久就能收口了。
打笆斗的工序前后約莫有十多道,從收割到收口,每一道都馬虎不得。老舅打笆斗的地方,多數(shù)在自家臺下的院子里。有時也在池塘邊上,有時在院門口。有時也會看見家里的幾個舅舅湊在一起,一人一張凳子,一邊不緊不慢地編物件,一邊閑聊。這種光景比較少,印象中僅有一次。其他都是在各家門口獨立操作。
然而,笆頭有大有小。大的可以裝下半袋糧食,過年時蒸的饅頭沒地方存,基本放在笆斗里。小的裝零食,也有墊上舊衣服放雞蛋的。每逢出嫁的姑娘生孩子,在第12天的時候,娘家人就會成笆斗地裝上馓子、雞蛋去探望。當(dāng)一笆斗笆斗的禮物被抬下來,娘家人的臉面仿佛一下就有了。
打簸箕看起來要比打笆斗稍簡單一些。老舅卻說,“再簡單的活不該省的一點兒都不能少。”
打簸箕的條子不能太干。直接抽了皮的杞柳條子,水汽太重,用這種條子打的簸箕容易變形。抽皮陰干之后成捆的條子,在用之前先放清水里稍泡一會兒,略帶水,骨頭不硬,而腰身亦有彈性和韌度才好。
簸箕因敞開面積大,經(jīng)常用來簸東西,極易損傷。有些為了延長它的使用壽命,就在底部加上幾條細長竹片。
簸箕在鄉(xiāng)下使用相對頻繁。在太陽升起的某個清晨,迎著風(fēng),簸箕在主人的手中開始勞作。伴隨著一陣忽上忽下的扇動,糟粕則被吐向半空最終落在了地上,它的身體里只剩下糧食的精華。
除了打笆斗和簸箕,老舅還打鋪籃、搲扁、糞箕子、提籃、筐等,皆是鄉(xiāng)下人居家過日子常用的物件。他將打好的東西,一摞摞地存在雜物間。每逢有集,他就用腳踏車載著幾摞去換零花錢。向西,幾里外就是千年古鎮(zhèn)長淮衛(wèi),或者,從村子北面上了大壩,坐輪渡到淮河對岸的沫口。
磨豆腐,打笆斗簸箕,都是老舅在農(nóng)閑時的手藝,土地里的莊稼才是本分,至少,讓一家老小不餓肚皮。大河灣邊上的土地,以沙土為主,只能種小麥和黃豆,不能種水稻,要想多拾掇點錢就得另想別的法子。
自我記事起,老舅家那一帶興起了種西瓜。上好的莊稼地一般舍不得騰出來,就利用河壩兩側(cè)的灘地。
一年夏天,趕上老舅一家去瓜地收瓜,準(zhǔn)備第二天拉到更遠一些的臨淮零售。摘到一半,天上開始落雨點。先是黃豆粒大小,七零八落地往下拋。風(fēng)呼呼地卷起來,扯得瓜庵上的塑料布嘩啦啦響。老舅趕緊招呼大家把剛挑好的瓜往車上搬。
西瓜地是長條子形狀,一頭是大壩下面,另一頭連著一條幾尺寬的土路。平時,從南到北走上一趟也要幾分鐘,何況手里肩頭都是沉甸甸的西瓜。若是尋常物件,背上走時也算穩(wěn)當(dāng),周身滾圓的西瓜,幾個擠在一個蛇皮袋里,隨著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地前行而時不時地打起晃。此時,又不敢格外用力,成熟的西瓜,碰一下都會炸裂,無法拿到集市換錢。
天上的黑云像懸在頭頂上,雨似催命一般,眼看就要開始往下倒。老舅嫌我們小孩礙事,把我們趕到路邊的瓜庵里。他一手提著一個袋子,像拎小雞一般奔向地頭。他頭頂?shù)牟菝辈恢螘r被大風(fēng)捎走了,小褂子混著雨水汗水粘在背上。
瓜地邊上的溝里,開始濺起混濁的積水。所有的瓜都運回了,架子車還差半筐才能裝滿。老舅轉(zhuǎn)身又走向瓜地。小小的瓜庵,在風(fēng)雨中開始搖擺起來。頭頂,雨水嘩啦啦地往下砸,腳下,雨珠撲撲地往里鉆。隔著塑料布間的小小縫隙,在蒼茫的雨幕中,我只看見一個高大的模糊背影在瓜地來回穿梭。過了一會兒,連這背影也不見了。
雨停之時,我們走出瓜庵,周圍已汪洋一片。界溝和地頭排水渠里的水往外漫。瓜地里漂起些小西瓜,隔壁地里的莊稼不見了腦袋。路上,原先放架子車的地方,只留下兩道深深的車輪印。
傍晚,我們提著一小袋香瓜到家時,老舅剛從鄰居家轉(zhuǎn)回來。鄰居昨天才從臨淮賣瓜回來,他去打聽了一下行情,除了問哪里好賣,最主要是價錢。天熱時,西瓜價錢倒好說,無非賣高賣低的事情,很少會再拉回來。雨后的很多事情就不好說了。如果明天繼續(xù)下雨,這車瓜有些危險了。
第二天早起,天空飄著濛濛小雨,老舅和那車瓜已在去臨淮的路上了。
印象中,在忙碌的一天中,老舅最愜意的事就是端著小酒杯的時候。
從條幾下面摸出一個塑料桶,即現(xiàn)在常見的能裝五斤的白色塑料桶。酒杯,一兩的大杯子,表面的釉已不多,唯杯底的瓷分外光亮。他高高提起酒桶,酒水如一條線,不緊不慢地注入杯中。一杯將滿,他利索地一轉(zhuǎn)腕子,那道光亮的線立即被攔腰掐斷,沒有一滴灑在桌面。無論桌上有沒有下酒菜,他都瞇起眼,小心地端起杯子。輕輕抿上一口,他緊皺的眉頭立刻舒展開來,仿佛一天的勞累也煙消云散了。
盡管,老舅喝酒喝得勤,且量大,我卻認為他不是個嗜酒的人。每次他與人劃拳的時候,自始至終只響亮地報一個數(shù)“五”。
“五”是什么?酒令的五代表“魁首”。這是老舅在以另外一種方式表達對酒桌上的對手,以及一切生活上困難的藐視,是一種對生活的信心。這,大概也是老舅只在喝酒時才能道出的心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