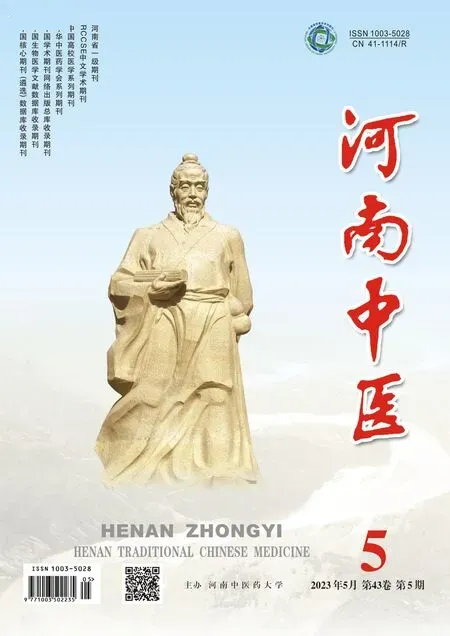浮針療法治療呼吸系統疾病淺析
張玉,周勝紅
1.山東中醫藥大學,山東 濟南 250014; 2.山東省中醫藥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014
浮針療法[1]是利用特制的一次性浮針針具在局限性病痛周圍的皮下組織進行掃散手法的針刺方法,因其進針深度在皮下,像浮在肌肉上,故取名“浮針”。其適應癥多年來不斷拓展,從一開始治療四肢部的軟組織傷痛、頸肩腰背痛、內臟痛、頭面部疼痛等疼痛性疾病拓展到內科病等非疼痛性疾病,其中,浮針療法治療呼吸系統疾病的臨床研究屢見報道,但以往對浮針療法機理的研究主要針對疼痛性疾病,而對呼吸系統等內科疾病治療機理的研究非常少,故本文對浮針療法治療呼吸系統疾病的文獻報道進行回顧性分析,并結合傳統中醫理論和現代醫學試探析浮針療法治療呼吸系統疾病可能的作用機制,茲以述評如下。
1 浮針療法概述
浮針療法是符仲華教授受腕踝針的啟發并對《黃帝內經》刺法進行提煉總結,經過多年臨床實踐不斷改進的成果,其淺刺至皮下疏松組織,針尖直對病所進行掃散,以其獨有的掃散動作和浮針針具為標志性特征,并配合相應的再灌注運動,是一種新型針刺方式。尋找患肌上的肌筋膜觸發點作為浮針進針點是浮針療法中非常關鍵的環節,患肌(pathoiogical tight muscle)[2]是符仲華首先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運動中樞正常肌肉放松時,出現病理性緊張的肌肉。患肌理論[3]是從患肌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病痛的發生、發展以及指導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的基礎醫學理論,其貫穿和指導浮針醫學的臨床和科學研究全過程,是浮針醫學的靈魂和核心。浮針進針點借用了西方myofascial trigger point(簡稱MTrP)[4]這一概念,其定義為“位于機體組織內可被觸知的緊帶區的小節中,一個高度容易激發的觸痛點”[5]。浮針療法的病理機制目前傾向于解釋為能量危機學說[6],簡單來說,在骨骼肌的興奮-收縮耦聯過程中,肌質網對Ca2+貯存、釋放和再聚積大量增加,容易導致肌肉持續攣縮,出現結節、條索或局部緊張,并壓迫血管,使血液供應減少,能量供應不足,而乙酰膽堿的釋放、持續去極化、Ca2+的運動、肌肉的收縮這些復雜的過程都需要大量的能量,肌肉攣縮導致能量供應不足,能量危機反過來又加重肌肉攣縮,如此反復,循環無端,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浮針療法的目標就是打破這一惡性循環,解除壓力,恢復局部能量供應。
浮針療法針具的演變從一開始使用毫針,后因效果不夠明顯、毫針彈性大不利于掃散動作、容易刺破血管等諸多不利因素,促使創制了獨有的浮針針具,并歷經多年的不斷改進。除了針具的改進,浮針進針點也從最開始沿襲張心曙教授[7]的腕踝針療法在腕踝部的6個縱區內進針到后來逐漸轉變為病灶局部周圍左右上下皆可。浮針療法在操作、療效、診斷等方面都獨具特點,除了標志性的掃散手法和再灌注運動外,浮針療法按照部位選取進針點,在病灶周圍進針,不同于傳統針刺深度深達肌層,浮針療法為皮下淺刺,將傳統針刺中的提、插、捻、轉的行針手法改為在皮層平掃、滾動,加大了刺激量的同時不要求得氣,減輕了患者痛苦,特制的針具也更有利于延長留針時間。與傳統針刺相比,浮針療法取效快,進針點少,皮下淺刺安全無副作用,更易為患者接受。
2 反阿是穴與筋膜學對浮針療法“非經絡”現象的解讀
浮針進針點具有非穴位性和多向性,表面上看這些“非經絡現象”似乎和腧穴無關,傳統的針灸治療學也無法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但也有學者提出浮針進針點和反阿是穴之間有某種相似性和聯系[8]。反阿是穴最早由張文兵[9]等提出,是與阿是穴相反的一種取穴方法,是在按壓時患者當即感到疼痛消失或減輕處施行針刺的一種療法,正如《靈樞·五邪》曰:“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張文兵等[9]認為,反阿是穴常位于肌纖維最緊張的部位,其下可觸及緊張甚至條索狀肌纖維,這剛好與浮針療法中在患肌上尋找肌筋膜觸發點作為進針點的原則不謀而合。而反阿是穴實質上歸屬于漢代以前經絡學說的內容,在漢代以前,人體處處是腧穴,“經脈本無定數,陰陽術數而定之”[10],只不過在腧穴的發現、形成、歸納過程中,無數腧穴被淘汰了[11],最終演變建立了以十四條經絡線為主要內容的經典經絡學,而那些被淘汰的腧穴中就包括反阿是穴。有學者認為,這些被淘汰的穴位中,理應包含很多類似今日的浮針進針點,并預言浮針進針點日后勢必也會經歷類似的淘汰過程,最終留下的“最佳浮針進針點”多半會是腧穴[12]。據此浮針療法的“非經絡現象”在漢代以前的傳統經絡學中得到了解讀,其不僅解決了以往浮針療法無法用傳統醫學解釋的疑惑和阻礙,而且還原了漢代以前經絡的最初面目,將漢代以前的經絡內容重新帶回人們視野[13],所以浮針療法依然無法脫離傳統醫學,是傳統針灸學基礎上的拓展和延伸。
現代醫學研究的筋膜學說也已經證實了人體處處是腧穴這一現象。原林等[14]提出了筋膜學的概念,認為人體可能存在第十大功能系統——支持與儲備系統或自體監測和調控系統。從筋膜學角度來說,中醫經絡實質上是全身非特異性結締組織所構成的筋膜支架,結締組織在人體遍布全身的解剖特點奠定了“人體處處是穴位”的基礎,筋膜學認為穴位是在進行刺激時能產生較強生物學信息的結締組織部位,穴位與非穴位本質相同,只是在進行刺激時穴位能產生更強的生物學信息,經絡是前人對能產生較強生物學信息部位的歸納總結。黃泳等[15]認為,腧穴數量的多少取決于刺激量的大小,穴位和非穴位的區別在于刺激量的大小。原林等[16]認為,筋膜學的發現使挖掘新穴位成為可能,且基于針體對筋膜組織的作用方式,可考慮通過增粗針身對針具進行改進,而浮針療法中具有反阿是穴穴位性質的肌筋膜觸發點、增粗的針管和掃散動作與這兩點遙相呼應、恰好吻合。從筋膜學角度解讀,浮針針具在進刺與掃散過程中,對局部筋膜組織產生牽拉,牽動筋膜內豐富的神經末梢和感受器產生神經信號,促進血液淋巴循環,并釋放增強化學信號,激活筋膜系統自體監控功能,使干細胞向功能細胞分化,從而發揮修復作用。浮針療法的“非經絡”現象在西醫理論筋膜學下得到了解答。
3 浮針療法在呼吸系統疾病中的臨床應用
于波[17]運用浮針治療慢性咽炎45例,沿胸骨切跡上緣,針尖刺向喉結,有效率為97.78%。呂中廣[18]運用浮針治療慢性咳嗽20例,在氣管、胸鎖乳突肌、后頸和上腹部附近尋找肌筋膜觸發點作為進針點,有效率為100.0%。張宏如等[19]運用浮針治療慢性咽炎31例,選擇穴位尺澤、天突、扶突為進針點,有效率為100.0%。周雪等[20]運用浮針治療急性期慢性阻塞性肺疾病20例,選取肺部聽診啰音明顯處或膻中、定喘、膏肓共5處作為進針點,治療后肺部聽診、血氣分析和肺功能測定均有所改善。張新藝[21]運用浮針治療“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肺氣腫,慢性支氣管炎)1例,使附分透大杼,肺俞外側透向肺俞,患者預后良好。張懷月等[22]運用浮針治療感冒123例,選取咳喘、膻中、咽四穴進針,有效率為99%。陳紅根[23]運用浮針治療干咳20例,取背部胸椎附近患肌作為進針點,有效率為95%。張勇強[24]運用浮針治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61例,選擇膻中、雙側風門、雙側肺俞進針,患者預后良好。徐呈超等[25]運用浮針治療急性支氣管炎1例,并在胸鎖乳突肌、胸大肌、斜方肌、斜角肌、腹直肌、豎脊肌等處尋得患肌進針,患者基本痊愈。
以上浮針療法治療呼吸系統疾病的臨床文獻研究中,最明顯的差異為進針點選擇的不同。筆者發現,慢性咽炎、支氣管炎、慢性咳嗽這類與肌肉相關性較大的氣管、咽部疾病都選擇了患肌上的肌筋膜觸發點作為浮針進針點,而感冒、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這類與肌肉相關性較小的外感或肺部疾病選擇了穴位。雖然患肌理論目前仍是浮針尋找進針點的首要指導思想,但是隨著浮針作用機理研究的逐漸深入,越來越多的學者發現穴位作為進針點也能發揮良效。對內科病的治療浮針進針點究竟應該選擇患肌還是穴位,目前暫未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中醫學理論將皮部理論和近治、以痛為腧、《黃帝內經》刺法理論[26]作為對其的解讀,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這種籠統的回顧性解釋前瞻性不足,對于后世浮針療法的發展的指導意義不大,而應該把更多的工作重心放在現代解剖等基礎研究上,以期發掘浮針療法更大的價值[27]。然而無論是選擇肌筋膜觸發點還是穴位作為進針點,浮針療法治療呼吸系統疾病都具有明顯優勢,治療機理可從皮部淺刺、刺皮刺衛和肺主皮毛等中醫理論結合臨床研究和現代醫學研究等不同方面嘗試對其進行闡述。
4 浮針療法治療呼吸系統疾病的作用機理
4.1 以皮部淺刺理論為基礎,五臟論為依據《素問·皮部論》曰:“凡十二經脈絡者,皮之部也。”狹義的皮部,即十二經皮部,是十二經脈功能活動反映于體表的部位。淺刺法最早源于《黃帝內經》,并在其中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論述,在針具方面根據針刺深淺劃分為九種,其中,镵針、員針、針、毫針用于淺刺[28];在刺法上總結出“浮刺毛刺”“揚刺”“半刺”“直刺”等五種淺刺法。皮部理論是淺刺法形成的理論基礎之一。付于主任根據多年經驗將十二皮部理論和現代解剖、組織功能學說相結合提出了“皮部淺刺”理論[29]。該療法主要通過針刺皮部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并將皮部淺刺的解剖學位置定位為皮膚組織,將皮部淺刺的深度定為真皮層[28],現代醫學研究也證明,真皮層中的免疫細胞是皮膚中最重要的適應性免疫學細胞[30]。
根據“五臟論”,浮針“皮部淺刺”可治肺疾病。《素問·皮部論》曰:“余聞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異。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病之終始,愿聞其道。”可見,皮部有皮、脈、肉、筋、骨五體之分,《靈樞·官針》又曰:“凡刺有五,以應五臟。”故又有刺皮、刺脈、刺肉、刺筋、刺骨五刺之分,分別對應五臟,簡稱“五臟刺”。“五臟刺”的核心內容是根據疾病的臟腑辨證結果,選擇與相應臟腑對應的深淺不同的組織結構部位(皮毛肉筋骨),正如《素問集注·官針》云:“五臟之氣外合于皮毛肉筋骨,五臟在中,故取之外合而應于五臟也。”可見,五臟外合五體,五刺內應五臟,皮刺與五臟中的肺臟相應,故浮針“皮部淺刺”可治肺疾病。
從胚胎學、生物進化學方面來說,肺與皮同源,刺皮即刺肺,浮針“皮部淺刺”可治肺。有學者報道稱,早期胚胎期,肺和皮毛都是由外胚層發育而來。人體中僅含有的18 g硅元素,其分布部位為肺與皮毛[31]。歐陽兵[32]認為,肺是生物進化過程中為了適應內呼吸而產生的特異性的皮毛。楊如哲等[33]、陳震霖[34]均認為,在沒有肺的生物進化階段都是通過身體最表層實現氣體交換,進化出肺臟的低等生物和高等哺乳生物,皮膚仍然保留著呼吸和散熱功能。所以從現代醫學角度來說,浮針的“皮部淺刺”很有可能對肺疾病有治療作用。
現代醫學認為,浮針通過對皮下疏松組織以某種特定的作用形式對疾病起著治療作用。樊海龍等[35]認為,皮部可能存在與經絡有聯系的物質基礎,刺激該物質能產生經氣并抵達病邪治療疾病,皮部刺激法通過經絡在皮部固有的交通信息的物質基礎而激發經氣產生治療作用。原林等[14]提出中醫經絡的解剖學基礎可能是分布于全身的筋膜結締組織。宋思源等[36]認為,浮針是通過刺入皮膚后的針刺機械力發揮作用。針刺通過影響皮膚機械感受器、成纖維細胞形態結構和肥大細胞脫顆粒等,實現針刺的機械力信號向生物信號傳導,起到治療疾病的作用[37]。浮針刺入皮下結締組織后,通過NTC換能將機械信息轉化為生物電流[38],一方面,通過針刺機械信息產生細胞的構架重整[39],另一方面,使結締組織產生壓電效應[40],最終都能啟動局部和遠程的蛋白質合成來調節病變部位生理病理狀況。陶嘉磊等[41]認為,浮針本質上是通過解除橫絡卡壓、經脈不通治療疾病,浮針通過粗大的針身,在推力的作用下穿破增生粘連,貫通組織通道,恢復血液運行與組織代謝,掃散的同時觸發神經末梢和各種感受器,引起電化學反應,使血管舒張、肌肉松弛,最終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
4.2 以針至病所理論和刺皮刺衛理論為操作、作用方式《靈樞·九針十二原》云:“刺之要,氣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云。”強調了“得氣”和“氣至病所”的重要性,然針灸療法不僅包括十二經經氣循行基礎上的“氣至病所”理論,還存在大量不以顯性感傳為依托的調節途徑,如在十二皮部層面上以“衛氣”為基礎的“針至病所”理論。“針至病所”理論是許榮正[42]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在辨證、辨病、定性、定位的基礎上,以針尖靠近病所或朝向病所來治療臨床疾病的一種治療理論,主要治療結聚性疾病,強調病灶局部取穴及針尖朝向病所,這與浮針療法針尖直對病所治療周圍局部疼痛類軟組織疾病有異曲同工之妙,且二者皆以皮部為治療層面,并通過以針調氣、以針引氣達到治療目的,故“針至病所”理論實質上可作為浮針療法的理論基礎。《靈樞·官針》曰:“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針,無針傷肉,如拔毛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這里的皮下淺刺取的“皮氣”指的極有可能是“衛氣”。《素問·痹論》曰:“衛者,水谷之悍氣也,其氣剽疾滑利,不能入于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可見,衛氣彌散力強,不受經絡約束,可行于脈外,充散于腠理間。有學者稱“得氣”源于“衛氣”,是“針刺的衛氣效應”,認為《黃帝內經》淺刺主在衛氣[43]。還有學者認為,淺刺作用于皮部,就是要充分發揮衛氣的作用[44]。還有學者也認為:“刺十二皮部,運其刺衛之功。”[45]可見,皮下淺刺實質上是通過刺激循行于皮部層面中的衛氣起到調節作用。許榮正等[46]認為,皮部的衛氣運行是針至病所與浮針療法的原動力,其“慓疾滑利”的特性結合人體經氣固有的自然調節性和趨病性,共同構成了浮針療法在皮部層面針至病所的治療學理論基礎。可見,“衛氣”是浮針療法的動力來源和信息傳遞介質,“針至病所”為浮針療法的具體操作方式,“以針調氣、以針引氣”是“針至病所”的作用形式,三者共同構成了浮針療法的刺皮刺衛理論和針至病所理論。
《靈樞·營衛生會》曰:“人受氣于谷,谷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水谷精微傳于肺,在肺中與自然清氣相合為營衛之氣,而后宣于皮毛,其中,清氣為衛氣生成的必要組成部分,而清氣的吸入依靠肺的呼吸運動,清氣的合成以肺為場所,可見,衛氣的生成和運行都與肺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張志聰《靈樞集注·卷二》云:“衛者,陽明水谷之悍氣,從上焦二出,衛出表陽,故曰衛出上焦。”可見,衛氣還需要通過肺的宣發功能布散于周身才能發揮衛表功能。由此可見,無論是衛氣的生成運行,還是衛氣正常功能的發揮,都與肺關系密切,故浮針刺皮刺衛的過程中,通過“針至病所”的針刺方式,“以針調氣、以針引氣”的作用形式最易引氣至肺,使肺疾病趨于調和。
4.3 肺主皮毛理論中皮毛對肺的影響肺主皮毛理論最早出自《黃帝內經》,“肺主皮毛”的哲學基礎源自古代的五行學說,《類經·疾病類》曰:“肺主皮毛,應金之堅斂而保障全體,悍御諸邪。”古人認為,肺和皮毛都具有“金”堅固收斂的特性,可以保護機體,防御外邪。《明醫指掌·咳嗽論》曰:“夫肺居至高至上,主持諸氣,……外主皮毛,司腠理開合,護衛一身,如天之覆物。”肺主氣,宣發衛氣于皮毛,保證皮毛發揮保衛機體、防御外邪的作用。可見,古人已經認識到肺具有防御免疫功能,還通過宣發衛氣達肌表發揮衛表功能,現代免疫學研究也逐漸證明了這一點。李浩等[47]認為,“皮毛”的含義不是只有皮膚和毛發這一表層含義,還指肺的免疫防御功能,相當于人體的第一道防線——呼吸道黏膜。胡作為等[48]從現代免疫學角度也證明了呼吸道黏膜和皮膚的免疫功能是協同一致的。趙國榮[49]認為,肺的非呼吸功能體現在肺對生物活性物質的代謝功能及相關炎性介質等方面,宣發肺衛能治療非感染性疾病。王益平等[50]認為,肺主要通過機械性防御作用、化學性防御作用、巨噬細胞吞噬作用、胸膜的免疫作用完成其防御作用。趙強等[51]認為,黏膜免疫系統和皮膚免疫系統的提出為“肺”與“皮毛”免疫關系提供了基礎,呼吸道黏膜和皮膚在免疫功能上協同一致。可見,從免疫學角度來說,浮針皮下淺刺很有可能同時激發皮膚和肺的免疫調節機制,通過一系列免疫細胞和炎性介質的作用治療肺疾病。
肺與皮毛在解剖學位置上都具有主表通外的特點,浮針通過刺皮可治肺系外感病。《靈樞·師傳》曰:“五臟六腑者,肺為之蓋”,《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天氣通于肺”,肺覆蓋諸臟,五臟中解剖位置最高,且通過氣管、咽喉、鼻等呼吸道與外界相同,而“皮毛主表,言在外”,可見,二者在居位上都具有主表通外的特點。王曉穎等[52]也認為,皮毛之疾不單指皮膚病變,還有病位在表、病變初期的含義。很多臨床研究也證實,治肺可從皮治,如穴位貼敷等外治法可治療肺系疾病,曾火英等[53]采用穴位注射治療咳嗽,魏丹[54]運用肺俞刺血拔罐治療咳嗽等都是肺系外感病可從皮治的佐證。
從疾病感傳角度來說,外邪侵襲機體,必先于皮毛而入,浮針刺皮實質上是從源頭上外邪延緩甚至阻止了從皮毛繼續向肺臟傳變。如《景岳全書·咳嗽論》云:“夫外感之咳,必由皮毛而入,蓋皮毛為肺之合,而凡外邪襲之,則必先入于肺。”《素問·咳論》云:“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皮毛衛外不固,外邪由表入里,首先犯肺,導致肺失宣降出現咳、喘、鼻塞、頭痛等一系列肺系外感疾病表現。有學者研究表明,寒冷刺激后,牛肺血流量增多,肺動脈壓力增高,可見,外邪侵襲皮毛對肺的影響。
5 小結
本文從皮部淺刺理論、五臟論、針至病所理論、刺皮刺衛理論、肺主皮毛理論等方面并結合現代醫學研究嘗試闡釋了浮針療法治療肺疾病的機理。將反阿是穴溯源至漢代以前經絡學說內容,為浮針的“非經絡現象”賦予了傳統醫學下的新依據,給現代針灸學中穴位的選取帶來了新思路,為浮針醫學歸于主流針灸學科體系做出了貢獻。筋膜學的發現也為浮針進針點的選取帶來了新啟發,穴位作為浮針療法治療內科病的組穴之一日漸普遍,也為浮針現代機理研究帶來了新方向和新依據。目前,浮針療法機理的研究依然不足,勢必影響學科的發展,日后的工作重心應該放在大樣本雙盲對照實驗和動物實驗上,盡快建立浮針治療內科病的進針點選取原則和規范,正確處理古籍和新針灸流派的關系,勇于打破針灸學科的保守和固化,實現自我創新以謀求更好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