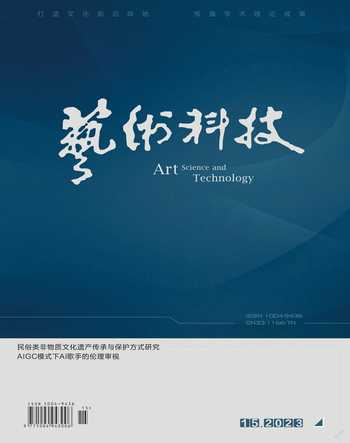從“構架—肌質”和“召喚結構”看新批評與接受美學的融通
摘要:文章基于“構架—肌質”說和“召喚結構”理論,分析新批評與接受美學的融通。新批評是20世紀的一個形式主義文論派別,其早期開拓者艾略特和瑞恰茲分別提出了“非個性論”和將“語義學”引入文學批評的理論觀點,都體現了對“詩”本身研究的重視。蘭色姆是新批評的真正奠基者,他將新批評稱為“本體論”批評,提出了“構架—肌質”說,其對“構架”和“肌質”的闡釋,實質上是對詩本身即“文本”的闡釋。蘭色姆的“構架—肌質”說是新批評的重要理論,他認為“構架”是“詩的表面實體”,而“肌質”則“使詩成為詩”。伊瑟爾的“召喚結構”是接受美學的代表理論,他認為文本具有五個語言結構層,體現出召喚結構的文本性;同時,文本具有空白和未定點,召喚讀者通過想象等方式填補,因此文本具有召喚性。盡管新批評是一個“文本中心”的流派,但是如蘭色姆的“構架—肌質”說,其實隱含著對接受者的關注;接受美學雖然是一個“讀者中心”的流派,但是如伊瑟爾的“召喚結構”理論,也重視文本的召喚性。新批評雖然以文本為中心,著意于文本研究,但也曾論述過、隱含著讀者接受的重要性,促進了接受美學的形成和發展;從理論傾向上看,接受美學的創立,導致文學研究的中心從文本轉移到讀者接受上,即從“文本中心”轉變為“讀者中心”,體現出接受美學對新批評“文本中心論”的反撥。
關鍵詞:“構架—肌質”說;“召喚結構”;新批評;接受美學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3)15-00-03
新批評是“文本中心”的流派,但是如蘭色姆的“構架—肌質”說,實質上隱含著對接受者的關注;接受美學雖然是一個“讀者中心”的流派,但是如伊瑟爾的“召喚結構”理論,也重視文本的召喚性,強調了讀者的能動作用。
1 “構架—肌質”與隱含的接受者
1.1 “構架”:詩的“邏輯核心”
蘭色姆認為“構架”是“詩的邏輯核心”[1]。他認為“構架”是伴有“肌質”而產生的,肌質具有重要性,但是構架也不可缺少,構架為肌質提供附麗之所。構架承載著整個詩篇,其與肌質的適配性影響著讀者對一首詩好壞的評判。
詩具有包容性,其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可以對世界本體進行觀照,“構架”和“肌質”作為詩性存在映射了生命實在的有機整體性,既包含理性的價值判斷,又包含感性的審美情趣。詩的構架實質上隱喻了世界的理性部分,它是一種邏輯內核,需要滿足詩歌的思想邏輯性和讀者閱讀時的智性需求。當讀者在閱讀一首詩的時候,往往會先整體地認知其思想、主題。即使這首詩敘述的內容是虛構的,讀者也會根據自己的理性標準檢驗其內容,以考量其思想合理性。因此,蘭色姆客觀地承認讀者的智性需求——讀者是具有認知和審美能力的“智性”讀者,詩歌的邏輯構架體現出的包含作者價值判斷的思想內容需要接受讀者的理性檢驗。
1.2 “肌質”:使詩成為詩
內含豐富個性細節和情感體驗的“肌質”是詩的文學性的主要體現,“肌質”承擔著體現詩歌本體性的責任。當“構架”滿足讀者的智性需求之后,讀者會將注意力轉向對“肌質”部分的感知與接受,這時讀者才真正開始進行感性審美。“肌質”是細膩感性的,它擔負著呈現世界本體任務的詩歌的一部分,展現世界的豐富性和偶然性,體現出一致性背后的異質性。“肌質”能觸發讀者的審美情趣,隱含著鮮活的生命存在。
詩作為文學本體能映射世界本體,接受者通過閱讀詩,能從中感知到包含著不同個體的經驗、感受、情感的異質性世界,并且能結合自己的認知和體驗感性地對詩歌進行審美接受,從而在詩的對立調和中認識、體悟到復雜世界的審美意蘊。詩的邏輯構架需要滿足讀者的智性需求,但有時讀者閱讀時常常只關注作品傳達的思想觀點,過于重視作品的理性和科學性,忽視了其文學性、審美性。詩豐富的“肌質”化表達需要接受者進行感性審美,這種感性審美又充分體現為詩的“肌質”部分,能喚起接受者關于“美”的情感。接受者在詩中可以感知他人對世界的不同審美體驗,在讀詩的過程中又會結合自己的體驗產生新的審美感受,這是抽象化、概念化的科學論文無法賦予的。
作家通過作品的“肌質”部分再現對世界的感性認知;接受者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結合自己的審美經驗獲得新的、豐富的、個性化的審美體驗,與邏輯構架承載的理性的思想觀點、價值判斷相結合并超越它們,最終接受者得以在對肌質的感性審美中,完整地領略世界本體的審美意蘊。
2 “召喚結構”:文本對讀者的召喚
伊瑟爾提出“召喚結構”的概念,他認為,文學的意義產生于文本和讀者的雙向交互作用中,召喚結構作為文學文本的一種特有結構,其交流性具體體現在語音語調層、意義建構層、修辭格層、意象意境層和思想感情層這五個語言結構層中。
語音語調層是讀者閱讀文本時最初感知到的語言結構層。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文本是語言符號的組合體。語言單位具有語音和語調,不同民族語言的語音語調不盡相同,即使是相同民族的語言,在不同語境下也會呈現出語音語調的變化,或是出現同音異詞、同詞異義的現象,從而引起作品意義的變化。
意義建構層在文本語言結構層中至關重要。文學語言作為對日常語言的提煉、加工[2],其表達意義也會隨作品中相關生活場景、對話語境而變化,因而存在語義空白和未定點。文學語言保留了日常語言的部分特點而又不同于日常語言——它具有創新性、超常性和反常性。文學語言使用超常的構詞策略,在具體的文本語境中賦予詞句反常的新義,因而產生了語言上的“偏離效應”。由此,文學文本存在意義不確定性,讀者在閱讀時需要結合具體語境解讀文本,通過想象、聯想等方式進行閱讀再創造,以填補相關意義空白和未定點,建構作品的內在意義。
作者創作時,往往不囿于平實的語言描寫和敘述,這就是文本的修辭格層——增強語言文字的文學性和審美效果。修辭手法多不直接表現寫作對象,轉而描寫中間對象,借此間接反映真正的寫作對象,所謂“言在于此而意寄于彼,玩味乃可識”。修辭手段的運用使語詞本義和其在作品語境中的實際意義發生了分離,產生語言挪移現象。讀者需要通過創造性閱讀來填補這些“言意空白”,體味作品意義。
意象意境層則不能通過文字直接呈現,更多是心理活動的產物。前述的三個語言結構層留存的空白和未定點不會消失,而是隨著讀者的審美接受進入意象意境層。在建構作品的意義之前,意象之間存在空白域,它們是獨立的、零散的,因而不能構成完整的意境。意象的空白和朦朧性召喚著讀者通過文本解讀、語言感知、想象聯想等進行審美再創造,從而構建完整的意境,重構作品意義。姚斯提出“期待視野”的概念,即讀者作為接受主體,在閱讀過程中會受到個人先在的審美期待、審美經驗等既定心理圖示的影響。因此,不同讀者對作品中所見意象的再造不盡相同。
思想感情層位于文本的最深層。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時,通常是先把握內容,再在此基礎上解讀思想感情。語言文字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讀者借其重構了蘊含個人獨特審美體驗的意象意境,但這并不是審美接受的終點——意象意境中包含著更隱匿的、更深刻的思想感情。中國古代詩論中有“詩無達志”說和“詩無達詁”說,分別是指詩歌意象、意境存在空白、未定點,因而具有多義性,可以傳遞多種多樣的情感。這一層的空白、未定點更多地體現為接受者的“心理偏離效應”。
3 新批評與接受美學:從各執一端到發展融通
新批評在立論上傾向于“作品”這一要素。接受美學反撥新批評中排斥讀者的“感受謬見”,在立論上傾向于“讀者”這一要素。新批評與接受美學雖然無法避免各自立論時的傾向性,但是可以發現二者在藝術審美上存在某些共通性。
3.1 文本分析:重視語言形式
新批評較早在文學理論中使用“文本”這一概念,文本即“以文為本”——文學應回到它的本體,其常使用文本(text)代替作品(work)以凸顯閱讀對象的獨立性、自足性和客觀性。蘭色姆提出“構架—肌質”說,認為與形式對應的“肌質”才是“使詩成為詩”的審美核心。
接受美學認為文本具有召喚性,其存在空白和未定點,召喚讀者參與閱讀再創造,并通過想象、聯想等方式填補它們,即文本存在召喚結構。召喚結構又具有文本性,讀者需要分析、品味五個文本結構層,從而在審美閱讀接受的旅程中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填補文本中的空白、不定點以建構作品的意義。在文本的五個結構層中,語音語調層、意義建構層、修辭格層屬于語言層,意象意境層和思想感情層屬于心理層。語言層即文學形式方面的內容,雖然它處于文本結構的外層,卻是基礎性、至關重要的,存在大量空白和未定點,需要接受者結合個人的閱讀經驗、審美期待等仔細分析、感知。語言層和心理層由外而內,逐層遞進,召喚讀者能動地參與閱讀再創造。
3.2 讀者接受:隱含與顯在
新批評以文本為研究中心,視文本形式為文學本體。“感受謬見”力圖排除“讀者”這一具有主觀隨意性的因素,將文本看作封閉、靜止的語言客體。但是,作品無法完全脫離讀者獨立存在,需要批評家或其他專業讀者在閱讀中完成。
蘭色姆提出“構架—肌質”說,認為構架是一首詩的邏輯內容,它需要滿足讀者的智性需求以激發他們閱讀時的智性興趣,從而進一步感知詩歌的肌質部分。感性細膩的肌質無法被散文轉述,是詩歌的本體和讀者的核心審美對象。因此,蘭色姆的“構架—肌質”說實質上也試圖為讀者提供科學、規范的文學閱讀接受方法。“構架—肌質”說新批評理論雖然以文本為研究中心,卻是在讀者或批評家的閱讀接受視野中展開的。新批評隱含著對讀者的關注,讀者需要在閱讀活動中細讀文本以分析文學文本的形式。及至接受美學,接受者代替文本成為文學批評研究的中心。伊瑟爾提出“召喚結構”理論,認為文本具有召喚性,存在空白和未定點,讀者需要通過想象、聯想等方式進行閱讀再創造以填補它們——文學作品的意義產生于讀者和文本的雙向交互作用之中。而蘭色姆理論中隱含的接受者主要是具備一定專業文學知識的智性讀者,這種“理想讀者”需要盡量客觀地對文學作品展開細讀與分析。
新批評雖然隱含著接受者,但這種接受是被動的,文本依然是靜態的、封閉的;接受者未能和文本進行動態交流,需要依附文本才能存在,他們更像是理性的文本分析者,而非感性的文學審美者。但是,新批評預設的“理想讀者”依然為能動的、有創造性的、具有感性審美能力的讀者參與文學接受提供了積極因素。新批評和接受美學屬于不同文學批評范式,但是都嘗試在讀者或隱或顯的閱讀接受中分析文本以發掘其審美內涵,實質上都重視讀者在文學批評中的作用。
3.3 審美觀照:感知世界與認識自我
“構架”是詩歌能被科學散文釋義的邏輯內核,它隱喻了世界的理性部分,這一功能科學論文同樣具備。但是,感性細膩的“肌質”作為詩歌的特性無法為科學論文所代替——與文學形式相對應的“肌質”才是詩歌的審美核心,是使詩成為詩的部分。讀者通過分析文學形式來感知文本的“肌質”,獲得不同于純粹工具理性的豐富情感體驗。語言作為形式因素屬于“肌質”,蘭色姆強調部分是詩歌的形式本體,即希望通過其“構架—肌質”說反抗工具理性對文學接受者感性審美的壓抑[3]。蘭色姆認為詩歌具有包容性,理性的邏輯“構架”和感性的細膩“肌質”共同構成詩性的生命存在,對世界的理性和感性部分進行審美上的對立調和以呈現世界本體。
伊瑟爾提出“召喚結構”理論,認為文本存在空白和未定點,召喚讀者能動地參與閱讀再創造以填補它們,在文學接受時會發現言意空白,需要結合個人的期待視野通過閱讀再創造加以填補。由此,讀者在發掘、建構文學作品意義的同時感知世界。在文學閱讀接受過程中,讀者與文本進行動態的交流與互動,發掘、建構作品的意義,從而在個性化審美接受中由領略文學世界轉而感知現實世界。作品部分內容對現實世界進行否定,因而間接否定了參與閱讀接受的讀者的先在閱讀經驗、認知習慣、審美期待等舊視界,他們需要根據文本重構新的、行之有效的接受方式。接受者在文本的召喚下展開個性化、創造性的文學閱讀,嘗試建構作品的意義并實現其審美價值。接受者結合作品批判、否棄、反抗工具理性對審美個性的壓抑以真正認識內在自我,正如伊瑟爾所說:“意義構成,不僅包含著從相互作用的文本視點中出現整體性的創造……通過形成這一整體,我們能形成我們自己,發現一個我們至今還沒有意識到的內在世界。”[4]
由此,新批評和接受美學都試圖使接受者在閱讀、分析、欣賞文學作品的過程中感知世界并認識內在自我,實質上都達成了文本與接受者的共生,實現了文學作品對現實世界和接受者內在自我的審美觀照。
4 結語
接受美學對接受者主體地位的關注是美學和文論研究的重大突破,但是其部分理論也存在著如“唯讀者”的缺點;新批評建構了一套關注文本、仔細分析文學形式的批評模式,但是這種模式本身又是囚所。對于新批評和接受美學,研究者們仍需進行更深入的思考與辯證分析,在研究理論的同時將其作為研究方法。
參考文獻:
[1] 趙毅衡.新批評文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104.
[2] 朱立元.略論文學作品的召喚結構[J].學術月刊,1988(8):43-49.
[3] 張燕楠.新批評“架構—肌質”說的本體論意蘊[J].文藝爭鳴,2014(7):83-87.
[4] 沃爾夫岡·伊瑟爾.閱讀行為[M].金惠敏,張云鵬,張穎,等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376.
作者簡介:莫炎奇(1999—),女,江蘇常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文學理論。